- +1
李公明|一周书记:被终结的夜晚与……不屈服的睡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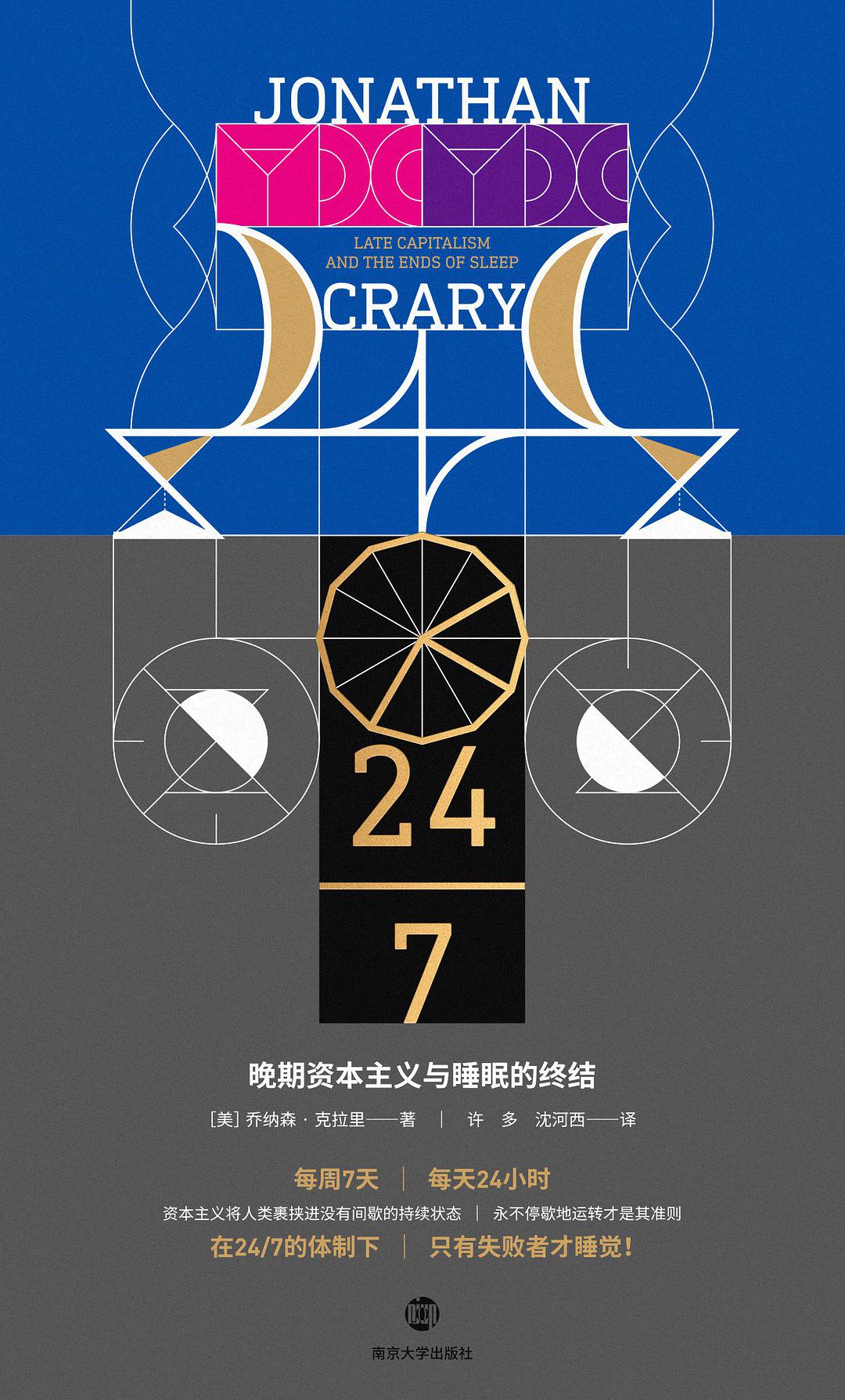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美] 乔纳森·克拉里著,许多 / 沈河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192页,48.00元
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的小册子《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原书名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2013;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该译本之前有2015年版,本文据新版)握在手里有点像一把轻便趁手的榔头,正好用来敲击资本主义夜幕下的栏杆。
从书名中的“24/7”,不难想到指的是二十四小时与七天,进而会想到与工作时间制度的关系。在职场中早就有了996、007,从延长工作时间发展到模糊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界限。007工作制当然不是真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而是所谓的“弹性”,雇员要自我加班或随时听命,实际上是一种无时间界限的超负荷工作制。无时间界限还只是一种表象,更为内在的是被压迫感和无意义感,如果所处氛围中还弥漫着职场PUA,日子就更难熬。可以说,在其身上浓缩了时下流行语汇中的“三无”问题:无奈、无意义、无希望。但这不是克拉里这本书所要谈的主要问题,虽然它也包括有关于工作时间的论述。对于007来说,“24/7”是更高一层的侵蚀与控制,超越了加班、工作时间等职场概念,而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与人的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关系。克拉里以被终结的夜晚、被剥夺的睡眠和被极度损害的注意力、感知力与时空感为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与整体性体制的发展趋势,让我们“始终牢记,就晚期资本主义而言,我们不过是维持经济运行的最终可支配单位”。(Nicholas Lezard, The Guardian)
什么是“24/7”?作者讲得很清楚: 24/7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七天的缩写,意思是全天候提供服务。这是一套支撑持续工作与市场消费的全球建制,已然运转多时,“然而现在,一种新的人类主体正在形成,与24/7体制更紧密地配合起来。”(第8页)也就是说,“24/7”彻底超出了工作时间的概念,成为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之下的一种新的生活体制。其根本要义就是彻底消弭工作与休息、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时间与空间等生命要素之间的界限,生产与消费行为失去任何停顿的节奏,人被裹挟到一种以不同方式持续运转的机械与麻木的状况之中。从工作时间的专制扩张到生活空间与人的精神空间的专制,在科拉里看来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与强大的技术力量的结合。
谈到科技,克拉里在开头讲了一个实例。美西海岸的白冠雀在季节性长途迁徙中可以七天不休不眠,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在长时间无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希望获得一些可应用在人身上的知识——使一个士兵能七天连续作战不睡觉,同时还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高昂的斗志。“从历史上来看,与战争相关的发明创造最后都将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第8页)“无眠工人”与“无眠消费者”其实是一体的,是资本主义整体性生产体制所期待的产物。
“24/7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16页)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的视觉教育中,光亮的城市与黑暗的城市截然对立,后来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灯火辉煌。现在克拉里要我们想象和思考的是,“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你暂时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26-27页)正是在这种想象之中,才会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和欧洲太空联盟合作的一项研究计划,该方案设想发射一系列卫星到太阳同步轨道上,每颗卫星上装配的抛物面反射器能把太阳光反射回地球并照亮十平方英里的区域,亮度接近月光的一百倍。这项计划的初衷是给高寒地区的工业生产和自然资源开采提供照明,后来发展到希望能覆盖整个大都市地区,以降低电力照明的能源消耗。这些科学家认为可以改变地球的昼夜交替,从此以后只有白天没有夜晚。这计划当然引起各方反对,最终没有实现,“但无论如何代表了当代社会对未来的想象,即永久照明的状态与无休止的全球交换和循环系统是不可分割的”。(10页)从前面所讲的无眠工人、士兵到这个没有夜晚的地球,被终结的夜晚与不愿屈服的睡眠构成了克拉里这本小书的核心主线。
出现在书名中的“睡眠”的确是一个关键词,虽然该书最终的核心主题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但是围绕睡眠的政治与经济史无疑是该书的重点内容。“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17页)当饥饿、口渴、性欲甚至对友情的需要都陆续被生产与消费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化的对象的时候,虽然以睡眠为中心的商品也不断在开发,但是睡眠本身还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毫不妥协地拦截着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的行为,表明我们生命中还有一部分时间仍未被资本殖民,仍未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人们的睡眠时间不断缩短,对睡眠的侵蚀正遍及各地和步步进逼,熬夜之后已经很难以睡到自然醒作为补偿。更有现实意味的是,“最近的研究显示,很多人夜里醒来一次或多次查看短信或数据,这种人的数量在大幅增长。电子设备上都有‘睡眠模式’的设置,这种语言上的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却是很普遍的。电子设备能够在耗电量低的休眠状态下运行,这种观念改造了睡眠,使睡眠变成仅仅延迟或弱化运行的状态。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21页)接下来克拉里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为资本主义扩张辩护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他们认为不存在无法改变的自然,不相信人的生命机能有什么区别于机器的本质特性,如果新的药物可以让人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是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为什么要反对呢?“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22页)
说“失败者才睡觉”不是开玩笑,难道你还没有发现,“睡觉”有时候已经成为无所作为、无奈、没有希望的代名词?“洗洗,睡吧!”克拉里的表述很形象:“受到各种力量推崇的是那些能在信息环境里持续参与、联络、交流、回应或处理事情的人。他们注意到,在这个星球上的富庶的地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大部分边界都已瓦解,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工作与消费。在他们联结主义的范式里,最有价值的是为活动而活动,‘永远都在做着什么,在移动,在改变——这才能给你带来声望,而不是稳定,后者往往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24页)知道科比为什么那么成功吗?据说在2007年赛季他放弃之前穿的8号球衣而改穿24号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一次进攻有二十四秒,是希望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场比赛每一次进攻都能全身心的投入!”不知道克拉里是否曾经从这里找到关于“24/7”的灵感。
对睡眠的强行剥夺肯定是一部极为久远的历史,但是在现代政治与科技的背景中那种施虐的性质与残酷才充分暴露出来。克拉里指出剥夺睡眠作为一项酷刑可追溯至许多世纪以前,但是其系统使用却与电灯和持续扩音手段的出现相伴而生,在与之相配合的其他手段的背后除了有技术专家之外,还有研究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家。他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一”事件之后酷刑作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进入了美国公众的视线,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酷刑,主流媒体更是拒绝承认剥夺睡眠是酷刑。(11-12页)看来,对剥夺睡眠的残酷性的认知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取得共识。
什么是睡眠?睡眠的姿势虽然是躺平,但并不是真的无所作为。克拉里从生产与消费的视角来论述,指出睡眠在人的生理需求之外,还是拒绝工作、拒绝交往、拒绝消费的表现,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依赖注意力的情况下,它的抵抗力就越变得强大。睡眠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体制企图最后控制人类的高地,同时也是克拉里心目中抵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最后战壕,他要告诉人们:睡眠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需求,更是抵抗“24/7”体制的最后阵地。“对于24/7的资本主义的完全实现而言,睡眠是仅存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27页)这么看来,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当然会呼吁保护睡觉的权利。
既然睡眠是对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最后可能性,那么保护睡眠就是保护对抗资本主义的力量。问题是,如何才能保护我们的睡眠,克拉里虽然极力寻求,但是无法提供一套完美的行动方案。全书最后的这段话像是有史以来最有气魄的关于“梦”与“睡眠”的宣言——“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梦,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梦:一个共享的世界,它的命运是没有终点的。一个没有亿万富翁的世界,它的未来不是野蛮主义的或后人类(post-human)的,历史也可以呈现出另一番样貌,而不是被物化为灾难的梦魇。有可能——在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状态下,包括幻想或白日梦里——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以睡梦为开端的。这意味着睡眠是一种彻底的中断,是在拒绝全球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重量。这也意味着在睡眠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无奇的地方,可以一再上演更重要的开端和新篇章。”(179页)以睡眠来中断什么和拒绝什么,以一个睡梦取代所有的梦,全世界无睡眠者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失眠,获得的将是一个共享的世界。
克拉里作为视觉艺术、电影和摄影研究的专家,对于社会景观的变迁与人的主体感知方式与能力的变化有很敏锐的观察和思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出版的《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90)和《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1999)分别研究了十九世纪以来历史语境中的“观察主体”的出现、观看方式的演变以及整个社会视觉机制的深刻变化,其中对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与消费的发展与人类主体的感知方式及注意力的调节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深刻的洞察。在《 24/7》 中,克拉里把战后消费和电视媒介的发展普及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转折点,一直延伸到八九十年代以后兴起的互联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与高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渗透重塑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克拉里的研究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急剧扩张必然产生24/7的压迫性体制及其常态化运作,人类生命被裹挟进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是其突出特征。他的研究表明,“24/7”体制不断重塑人们的时间观念和生活习惯,通过尽可能加快工作与消费的节奏,强化对人们的行为和主体意识的控制和监视,以匹配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与消费扩张,同时对于削弱个人的反抗意识和能力也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正如我们早已发现和洞察的,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带来的任何一种管控和压迫都可以找到它的合理证成。有时这种合理化来自个人的认识误区或错觉,自以为高技术、快节奏和在按键上的自我选择证明自己仍然拥有自主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进行整齐划一的自我管控,无处可逃。选择和自治的幻觉正是自动管控的全球系统的根基所在。”(66页)在更多地方,你会听到有人说当代技术从根本上是一套中性的工具,能够以不同方式被利用,包括服务于解放政治。但是阿甘本认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机器所塑型、污染或控制”;他令人信服地说:“机器的臣服者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机器。那些依然宣扬类似论点的人,自身就已被媒介俘获,是媒介的产物。”(67页)因此,我们只能眼看着数码人格化和强制性技术是如何剥夺了人的自主意识,从技术的普及化来看连老年人或流浪人群也不能幸免,除非他们自甘被抛弃在社会生活之外。
克拉里相当重视在西方的思想与艺术发展系谱中挖掘相关资源,他在该书中以睡眠、人性遭到的异化以及对资本主义扩张的抵抗为中心,在思想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挖掘出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脉络与碎片,或者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的盲点或缺陷。毫无疑问,有关睡眠和光线的思想史与文艺史遗产是在阅读该书的时候值得特别注意的。
从亚里士多德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对睡眠的认识和评价一直是稳定的,但从十七世纪开始“逐渐有人认识到,睡眠与强调生产力和理性的现代观念不兼容,笛卡儿、休谟和洛克仅仅是众多诋毁睡眠的哲学家的个别代表,理由是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意识和意志占据优先地位,功利性、目的性和利己的能动性之类的概念备受推崇,跟这些概念相比,睡眠失去了价值。”(19页)在我看来这也是在性问题之外身体与灵魂的博弈的另一种思想表现形式,灵魂在其中一定要压抑身体,要占据主宰性的地位;也是人的主体性理论的高扬,人的能动性找到了形象化的打击对象。在十九世纪中叶,人们进一步认为睡眠与清醒的不对等关系就是高低等级的差异,睡眠使人退化到更低级、更原始的模式中去。叔本华反对这种观点,颠覆了这种等级秩序,认为人类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把握住存在的“真正核心”。克拉里的总结颇有启发性,他认为睡眠的不稳定地位与现代性的特殊运动方式有关,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力量与任何固有的二元区分结构(如神圣与亵渎、狂欢节与工作日、自然与文化、机械与有机)都无法兼容。因此,任何固执地把睡眠看成“自然”的说法都变得无法接受。(20页)这就不难明白,“自然醒”为什么是不可原谅的。
睡眠的性质虽然是自然的,但是对个人来说又是脆弱的。只要想象一下我们在夜幕下的城市中离开任何建筑物,或者置身于荒山野岭,睡眠肯定会成为一个问题。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里有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人在睡觉时是毫无防备的,因此共和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是保障睡眠者的安全。但是霍布斯想象的共和国是有阶级性的,只能为有钱阶级的睡眠提供安全保障。“有产者与安心睡眠的权利或特权间的对应关系源自17世纪,依然存在于今天21世纪的城市里。今天的公共空间都经过全面规划,防止人在里面睡觉,其手段本质上是残忍的,经常包括把长椅设计成锯齿状,或把表面抬高以防有人靠上去。城市里到处有人无家可归,社会对之不闻不问,这里面包含了多重剥夺,但没有比露宿街头更危险和更不安全的了。”(39页)说得很真实。
在艺术方面,克拉里重点分析了英国画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在1782年左右创作的油画《夜里的阿克莱特棉纺厂》(Arkwrights Cotton Mills by Night),他关注的是画面上的棉纺厂在夜空下的窗户透着煤气灯的光,表明时间与工作的抽象关系经历了理性化的编排,“这种观念认为,可以一刻不停地、全天候地生产运行,并源源不断创造利润。这幅画展示了一个特定场景里,一支包括许多童工的劳动队伍,12个小时连轴转地操作着机器。马克思明白,时间的重组(尤其是劳动力时间)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密不可分的。”(88页)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影片《飞向太空》(Solaris)中,他发现作者最先预见到,即使在一个昼夜通明的世界里还有会幽灵在某个地方存在,“在经历了反复的拒绝与压抑之后,幽灵终会重返人间,确认这一点,是通往自由或幸福的途径”。(31页)
克拉里认为,最能让我们明白睡眠就是革命的道理的是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他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创造性地指出醒着和做梦是相互作用的,是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的一部分。在布勒东那个时代流行的左翼思想认为做梦是无力的幻想,与献身革命的实践是对立的,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布勒东看来,真正的革命也是欲望和幻想领域的革命,他认为梦中的景象和欲望对于理解真正的社会变革是非常关键的。(154页)
更值得思考的是,克拉里把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与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资本主义扩张看作是激烈斗争的双方,从中展开关于“24/7”体制的斗争史叙事。他认为六十年代特定的政治运动对体制性发起了各种非正式挑战,在多个战场展开了多元的斗争;年轻人不再把幸福与所有权、占有物品和个人地位等同起来,不再相信社会地位会向上流动的骗人的承诺;工作的中心性和必要性也受到他们的普遍挑战,在体制性层面上的“退出”使他们具有杀伤力;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使公众对和平主义更加认同和对战争受害者抱有同情。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代被污名化,事件和参与者成为被嘲笑、被妖魔化和被轻视的对象。克拉里说这恰恰证明六十年代的文化让统治者感到极大的危机感,同时指出伴随着对六十年代的否定的,是全球金融资本转化为更加残酷的形式、日常生活进一步被货币化。(157页)他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说明对于同情、互助与共享精神的颠覆:美国有的州颁布法律,那些给无家可归者或未登记在案的移民提供食物的人会被判刑。(160页)对此我感到难以置信,于是向一位研究美国法律的青年学子求证,他说是的,但在2016年这些州法律被判违反第一修正案而被废除。
接下来通过讨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克拉里指出该书对于理解当代日常生活的变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萨特的理论肯定了特定群体的自发性。克拉里从中提出的追问是: 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的革命潜能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时代里,“什么样的相遇才能够带来新的形式、新的反抗力量,以及它们会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样的空间或时间?”“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仁们在1917年的革命中都利用了手头所有可资利用的通信技术,但他们从来没有把它们上升到特殊的神圣的高度……。”(168页)他力图要打破人们对于网络媒体的作用的神化心理,“所有把社会媒体当成救命稻草的社会动荡历来都只能热闹一时,最终变得无足轻重”。(170页)
那么,在被终结的夜与不愿屈服的睡眠之间,不要再打游戏、追剧和刷手机屏幕了。让自己睡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