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15岁就开始梦想做妈妈的我,失去过三个孩子
原创 Lisa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181个
在陪伴Lisa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比起她在想要成为一个妈妈的路上所经历的这些,说什么都显得太轻易了。作为编辑面对这个故事的情感是复杂的,我必须一遍遍地看,又一遍遍地掉泪。谢谢她的勇敢,愿意去面对这三次重大的创伤,并写下来,不逃避,不沉溺。我不认为这个故事会让人恐惧生育,它让人看见当无常碾过一个个体时是多么冷酷,也让人看到,一个人可以怎样面对生命中的无常,在哀伤之后,仍然有力气去拥抱它。(依蔓)
文 | Lisa
编辑 | 依蔓
这是全市知名的三甲医院,候诊的走廊却出奇得窄。产科B超室的门口,孕妇们挨挨挤挤,各自扎堆聊天。我一个人坐在角落,垂着头,双臂交叠,挡在腹部前面。和身边的一个个大肚子比起来,我平坦的小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唉,闷死了。”坐在旁边的孕妇突然站起来,硕大的肚子朝向我,卡其色的毛衣后面,我几乎能清晰地看到肚脐的轮廓。
“为什么是我?!”我盯着那个肚子,心里想着,把下嘴唇咬得生疼。
一个奇怪的念头冒出来:医院旁边就是动物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离开这里,我要带肚子里的孩子去动物园看看。
“宝宝,我们走。”我在心里说,越过一个又一个大肚子,逃了出去。
01
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次明确产生“等我有了孩子……”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在15岁。那时候我的身体快速发育,有天晚上洗完澡出来,发现卧室的窗帘开着一条很大的缝,“哎呀,你怎么不把帘子拉好!”我回头冲我妈喊。她头也不回,“没事儿,看不到的。”我在心里暗暗生闷气:“哼,等我有了女儿,我一定给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我想有个女儿——不,我几乎确定,我以后会有个女儿。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
从那开始,我会在自己的日记本最后留两页,上面列着一个单子,叫做“等我有了孩子,我要……“所有求而不得又说不出口的爱、尊重、保护、包容,全都被我记在里面,像是包了个鼓鼓的锦囊,等到自己成为妈妈的那一天,打开,兑现。
差不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同学走在路上,偶尔会有小孩子误把我们叫做“阿姨”。同学很生气,抓着小孩子要求改口:“叫姐姐!我是姐姐!”我就只是在一边笑。
我喜欢被叫做“阿姨”。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成为“姑姑”,在老家那个砌着灰色墙砖的长长的胡同里,我把红包塞给堂哥怀里的娃娃,用食指轻轻碰了下她的小脸蛋。她张开嘴“啊啊”了两声。那感觉真好。很多年里我都在回味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吃了一颗阿尔卑斯奶糖,巧克力味的那种,吃到一半糖漏到了心里面,化开了,痒痒的,暖暖的,麻酥酥的。
后来我发现,那种感觉在其它一些时刻也会出现。
比如初中上篮球课,瘦小的女同桌来了月经还偏要打,打到一半疼得直冒汗,脸色煞白,呼哧呼哧喘着气。我冲上去叫停,把她扶到一边的石凳上坐下,让她把整个身体靠在我肩膀上,汗珠沿着脖子淌下来,流到我手背上,我没动,就一直撑着胳膊让她靠着。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在我心里荡漾开。
再比如高二的时候,班里有个年纪比我们都小两岁的女孩子,被选送到高三插班,突击“少年班”。我那时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利用“职务之便”跑去看她,发现她压力很大,就买了个本子,发动全班同学给她写鼓励的留言,趁检查跑操的时候送到他们班的队伍里。她嘿嘿笑起来的脸,在路灯底下特别好看。
慢慢地我发现,同学开始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后缀——“XX姐姐”,我笑纳了这个称呼。它让我觉得被需要、被喜欢。
记得有一次班级团体活动,带活动的心理老师问大家,如果要在团体里选一个人做妈妈,你会选谁?选好以后,把自己的手搭在她肩上。一分钟后,我左右肩膀上交交叠叠,落下了很多只手,超过团体的一半。
所以当26岁的我,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出“我愿意”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夕阳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摇椅上晒太阳,孙子孙女在一旁打闹着呼啸而过,然后我们喊着“小心,别跑啦”,起身想追却追不上,孩子们笑作一团。
成为“妈妈”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从来都不需要考虑,它就像春晚的《难忘今宵》一样,是一项确定无疑的安排。而且,是一种幸福的安排。
但我从未想过,这条路,如此艰难。
02
“这个孩子……可不太好啊。”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正躺在妇产科B超室的床上,盯着B超大夫挂在颈间的粉红色带子看,觉得很刺眼。带子的一端连着电脑,另一端连着探头。我的肚子被抹满黏糊糊的液体,探头在上面划来划去。
“这是你第几个孩子?”她侧过头来问我。我把视线从带子上移开,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想回答,却说不出话。陪我进来的朋友上前走了两步,替我回答:“第一个。”我瞥到她看了我一眼,但我不敢看她,死死盯着她拿在手里的手机。手机屏幕亮着,是相机状态。哦,她刚刚说,要帮我拍下孩子的第一张照片。
我突然很想侧头看一看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可身体像冻住了一样,完全无法动弹。
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第一个孩子,刚刚13周大,就这样被宣告“先天发育不良”。那一年,我28岁。
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走出B超室的。记忆中的下一个画面,就是我坐在B超室外的椅子上,盯着手里的B超单一遍遍地看。“露脑畸形?右上肢缺如?”这是B超单上的最后一行字。我看着那两个问号,心想,问号就说明不确定吧?会不会误诊?是不是搞错了?
先生在一旁握着我的手,没说话。他历来不会安慰人。很久,他凑近我耳边说:“亲爱的,你已经很努力了。”我一下子绷不住,鼻子一酸,眼泪滚了下来。
我确实很“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努力”就是我的信仰。在备孕的一年半、怀孕的三个月里,我像备战高考一样,恨不得把每个知识点都学到、每道模拟题都做一遍。我把各大备孕网站上有价值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在白纸上清晰地画出早晨7点的体温曲线,把排卵试纸标上时间依次填好,听从医生的建议按照排卵监测的结果安排房事。发现怀孕后,我郑重地把“大姨妈”APP的状态改为“怀孕”,认真记录“孕期日记”,谨慎安排饮食和作息。
可是我忘了,考试有正确答案,人生没有。我以为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命运却给我出了一道残酷的“加试题”。
“哎呦,这么不好啊。”这是我的主治医生看到B超单,说的第一句话。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没事啊,还不算晚,我马上给你安排住院。对了,我们医院还不能出这种产前诊断,我给你联系上级医院,你马上去那做个鉴定,把结果拿回来,就能马上做了。”她的语速飞快,连着用了好几个“马上”,好像我肚子里是什么怪物,要立刻、迅速、采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把TA杀死。
“想明白了就好。”吃完晚饭,妈妈拾起我面前的饭碗,用纸巾抹了一把桌子,但没有看我,“畸形的,说什么也不能要。”说完,很利索地转身走了出去。
“畸形”?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盘里的剩菜,满脑子都是这两个字。
“TA是我的孩子!”我想向所有人呐喊。可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人回应。
第二天,我去了上级医院,在妇产科B超室门外的角落里缩着,像是等待最终宣判的罪犯。可是当排号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后悔。我想,如果这就是我和孩子的最后一面,我会不会后悔没有好好爱TA?我还没有认真和TA说过话。
于是,我带TA去了动物园。我们去看了金丝猴,孔雀,斑马,长颈鹿,我给TA讲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来动物园被长颈鹿吓哭的故事,我告诉TA爸爸属猴,很爱玩,很喜欢小孩,会是个好爸爸,我和TA在长凳上拍了张自拍,照片里,我右手摸着小腹,微笑看向前方,样子很温柔。我想,我要把最幸福最美的时刻留给TA。
等再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下班。原本挤满人的走廊里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孕妇,一脸疲惫地靠在墙上。
B超室里,一个画着浓妆的大夫拿过我的单子,没有看我,反倒很兴奋地招呼后面的几个小大夫:“来来,这个你们看看。”然后,她让我脱下裤子,双手抱腿,把探头伸进了我的阴道。“看到了吧,露脑畸形。”她指给小大夫们看。小大夫们也很兴奋,纷纷凑上前看,指着屏幕交头接耳。“很可能是羊膜带的问题”,浓妆大夫又说,展开了她冗长的宣讲。
整个过程,探头在我的阴道里粗暴地捅来捅去,身边的白大褂们兴奋地看着屏幕里我的孩子,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我是发着抖走出那家医院的。几乎跌坐在医院门诊楼入口的花坛上,我哭得岔了气。我在心里想,孩子,这个世界,你不来也好。
住院之前,我把留了5年的及腰长发剪掉,和我给孩子写的信一起包在一个很精致的荷包里。荷包被我小心地缝起来,偷偷塞进病号服的口袋。医生给我的阴道塞下引产药的时候,我死死攥着那个荷包,脑子里是两天前,给我做检查的小护士误以为我是产检,让我听的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像小火车一样,那么昂扬、茁壮。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每宫缩一次,我都觉得,是我的孩子在挣扎,TA说TA很难受,TA说TA不想死。
我是在卫生间里产下TA的。先生叫来小护士检查胎儿,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小护士找了很久,低声耳语:好像还少一条胳膊。我一边疼得发抖,一边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们:是,我的孩子没有右上肢。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我的孩子”这四个字说得特别重。
我曾经在日记里给TA起了个小名叫“小猴纸”,因为TA和先生都属猴,我想,这或许是上天的安排。3个月后,我在那个叫做“小猴纸”的文件夹里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题目是《宝宝,妈妈要往前走了》。写下那行字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忘掉TA,那像是一种背叛。
事实证明,我没有。
03
再一次见到早孕试纸上的粉印,是一年半之后。我又惊又喜,自己在卫生间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照一遍,拍了照拿到阳光底下再看一遍,过两小时重新测一遍,然后把两个试纸排成一排,对比颜色是不是有不同,确认不是自己看花了眼。
等到三条试纸显示出三道粉印的时候,我给先生发微信:“我好像怀孕了。”过了一会儿,收到三个鼓掌的表情。我想了想,回了一个“嘘”。
我太害怕失去了。经历了上次的流产,再加上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尝试找到孩子发育不良的原因未果,我对医学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对“顺利”二字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的自我保护机制响起了“滴滴”的警报声,它要求我冷静下来:“不要高兴太早了!”
我把怀孕这件事小心地封存起来——不仅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6周胎心胎芽,12周NT筛查,16周无创DNA检查,就像打怪升级一样,一关一关地过。每过一关,我都会小小地窃喜一下,然后那个声音又会跳出来:“不要高兴太早了!”
所以在怀孕5个月之前,我没有给孩子起名字,没有着手请月嫂,没有置办过任何婴儿用品,几乎没有和腹中的孩子说过话。导师作为极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看我一路小跑赶去上课,吐槽我说,你哪像个孕妇啊!我变成了一个和上次截然不同的孕妈妈,就好像采用和上次完全不同的态度,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最紧张的是21周“大排畸”,我提前在各类论坛上搜集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脑积水,兔唇,心脏动脉狭窄……每一项都看得我惊心动魄,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看下来,并想好了每一种情况的对策。
那天气温很低,我在B超室外冻得打哆嗦,先生把他的羽绒服脱下来套在我身上,可还是冷。“我……有点紧张。”我看了他一眼,又很快低下头去。半天,他挤出一句:“没关系,咱已经很努力了。”“直男,”我心里想,“连安慰人都不会,只会说‘很努力’。”
躺在B超室的床上,我一动不敢动,甚至喘气都不敢喘粗了。大夫拿着探头在我肚子上划拉,上,下,左,右,侧面,正面,挨个照了一遍。探头抬起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孩子……是正常的吗?”
大夫这才看了我一眼,有点错愕:“哦,正常,正常的呀。”
“我……”我支支吾吾,“我上回有一次不良妊娠。”
面无表情的大夫突然笑了:“嗨,没事儿,正常的,哪能两次都砸中啊。”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像给我松了绑,突然有点想哭。一直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
走出B超室,差点迎面撞上先生,他就站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瞪着两只熊猫眼,紧张兮兮地看着我。“喏,”我骄傲地手一扬,把手里的B超单展示给他看——上面满满的,每一项后面都是“勾”。
“咱孩子厉害吧!”我嘚瑟得很,边走边颠儿了起来。
“别蹦,别蹦。”他在一旁拽着我的胳膊,脸上挂起一个月牙笑,但很快,又打了个哈欠。我看着他放松又疲惫的脸,开他玩笑:“我看,咱孩子就起名叫‘困困’吧。”
其实那段日子对我们来说,异常艰难。我的博士生涯进入最后一年,论文却屡次被拒,迟迟发表不出来;婆婆癌症复发,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放化疗一段时间后还是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先生的事业遇到很大挫折,资金流断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房子二次抵押贷了款。就在检查前一晚,先生还在医院陪床,婆婆高烧不退。凌晨6点,他才从医院赶回家,陪我去了医院。
很多时候都会有种“人到中年”的沧桑感,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好累啊,从此以后就要过“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了,把孩子带到这世间,真的是对的吗?我能让TA幸福吗?我有做妈妈的能力吗?但很快,这个想法就被内疚感吞噬,我使劲摇摇头,把它甩在脑后。
有了打满勾的“成绩单”,我和家人终于敢把孩子的存在公诸于世。大姨高兴地在视频里说:“快让俺看看,这孩子,是福星啊!”真的是福星。那年过年前后,我的论文终于发表,工作有了着落,先生的事业也开始好转。唯一的遗憾是,婆婆还是在腊月二十九去世了。
三十那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愿你身披铠甲,而内心柔软。2018,我们来了!”
30岁的我,终于开始放心拥抱孩子的到来。购物车很快满了:奶粉、奶瓶、奶嘴、湿巾、浴巾、身体乳、爽身粉、小凉席、小枕巾、小衣服、小袜子、婴儿肥皂……爸妈正式“到岗”,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收快递。
怀孕26周的时候,我预约了一家私人机构照四维彩超。收获的成品,是一段小宝宝烦躁不安手脚乱动的视频,和一张抱着脚丫啃脚趾的照片,还有一双粉色的小袜子——啊,原来是女儿!真的是女儿!
我问先生,给闺女起个啥名字好啊?他的反应时间超出我的预料,“一好”,他很快回答,“一女子嘛。”看来是早就想过了。
“真土。”我嘲笑他,“我想叫她‘慢慢’。”我想告诉她,不要像妈妈这样急吼吼的只顾赶路,人生很长,不要着急,凡事慢慢来,没关系的,妈妈陪你。
但还是有担心的事情,就是早产。这也是后期产检,医生唯一提醒过我的事。
因为我患有“子宫不全纵膈”。简单地说,就像女人的子宫本来是个大开间,而“纵膈”就是在中间打了一个隔断,有的人是完全隔开了,叫“完全纵膈”,而我的情况是,只隔开了一部分,而且检查显示纵膈并不长,在上一次怀孕期间,10周的时候就几乎看不到纵膈了,说明胎儿是有可能把它撑开的。但毕竟对孩子来说,生长的空间还是小了,所以早产是可能的。
事实上,这个纵膈的存在,也是我备孕期间跑各大医院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反复咨询要不要动手术把它切掉,得到的答案不一,差不多各占一半。最后,是一位83岁的妇产科专家说动了我,她说,即使切掉也不能完全切除,而且切掉以后就像剖腹产一样,成为疤痕子宫,万一胚胎着床到疤痕处会很危险,胎盘植入子宫破裂怎么办,孩子生不了,命都可能没了。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采纳她的建议,可能也和我的恐惧有关:我太害怕“万一”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怀孕过程会是顺利的。“万一”又被我碰上了“万一”怎么办?
可没想到,我碰上的,是另一个“万一”。
某个周五的晚上,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在内裤上发现了一点褐色分泌物。我很紧张,拿出胎心仪听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150次左右,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过两小时再听,还是正常。第二天,褐色分泌物还在,胎心还是正常。那天是周六了,我在的医院没有专科急诊,我犹豫要不要等到周一。因为在北京,医院是不收不在自家医院建档的孕妇的。到周日早上,我终于不放心,去了医院。急诊科把值班的产科大夫叫了来,她检查了我的宫颈说,可能是有点宫颈糜烂,回去注意休息,又开了周一的B超单给我。
周一的B超显示,一切正常。
有时候我在想,人这一生,到底要面对多少风险?倘若真的能够平安终老,该是比中彩票还要难吧?每次你以为自己做了万全的准备,但命运都会冷冷地告诉你说,太天真了。
当时,我以为最坏的情况就是早产,于是把之前积累的关于早产儿的知识拿出来重新梳理了一遍,形成了一个包含早产儿护理注意事项、早产儿物品准备清单、早产儿发育大致阶段等等内容的文档,我甚至还关注了一个成功养育23周早产儿的妈妈的公众号。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建档的医院是为数不多建有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医院。我在日记里写,宝宝,不管出现什么状况,妈妈都可以应对,妈妈会保护好你。但你现在还太小,妈妈不忍心你受苦,你再坚持一下,再长胖一点壮一点,好不好?
但我终究还是没能保护好她。
04
一周后的某天夜里,大约12点,我感觉肚子有点胀,鼓鼓的。像是小腹憋了气,着凉的那种。“会不会是下午吃了半个雪糕导致的?”我在心里想,仔细体会着那种感觉。“会是宫缩吗?我记得不少孕妇说孕晚期会有假性宫缩的。”我不放心,又不想吵醒家人,蹑手蹑脚地爬起来用胎心仪听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正常的呀,我换了个姿势侧躺,那种感觉好像消失了。但过了二十分钟,好像又出现了。我默默打开事先下载好的记录宫缩软件。
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我好想冲到那个世界的那一刻,把那个犹犹豫豫的孕妇从床上揪起来,狠狠摇着她的肩膀说:“别等了!快去医院!立刻!马上!”可是没有如果。
我是个对疼痛耐受力很强的人。十几年的痛经史让我练就了一套和疼痛相处的“武功”,我甚至可以通过深呼吸想象那种疼痛是身体之外的东西,就像“灵魂出窍”一样。但这样的功夫在那一晚并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对疼痛敏感一点,或许就能抢先一步救了孩子的命。
等到那种胀痛变得清晰而有规律,我把先生叫醒:“不行,咱们得去趟医院。”那是午夜2点钟。
我家距离医院的车程,大概40分钟。一路上,先生闷闷的不说话,像在想事情。我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要住院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万一要住NICU,我们卡里有没有这么多钱?这时候,我感觉孩子好像动了动,“没事儿,”我故作轻松地调侃,“可能咱闺女就是觉得最近对她关心不够,想刷个存在感。”先生也配合地笑了笑,握住了我的手:“嗯,希望咱孩子没事。”
等到了医院急诊,挂上号、简述了病史、测了体温血压、进到诊室等大夫,已经3点多。等了有一会儿,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小大夫才进来,开始问诊。“多少周了?”“32周+4。”我回答。“什么症状?”“嗯,好像有点宫缩……”“上床吧,听个胎心看看。”
小大夫拿着胎心仪在我肚子上到处试,却总是找不到规律的心跳。“孩子今天动了吗?”她看着我问。“动了啊!刚刚来的路上我还感觉动了!”我急着回答,觉得不够,又补了一句,“12点我还听胎心了,正常的。”我解释着,好像在极力证明什么。
“是吗?怎么找不到呢?”小大夫一脸困惑,“再做个B超看看吧。”说完,她推门出去找仪器了。
等待的10分钟无比漫长。空荡荡的诊室里只有我自己,躺在床上听着电脑运转的声音,我觉得周身发冷。“闺女,别闹了,快出来吧,别吓妈妈了。”我在心里说。“不要乱想!肯定是虚惊一场!”心里有个声音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了出去。
B超机器来了。可是小大夫的表情却越来越困惑。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再问什么。我也没有,我不敢问,好像不问,就不会有坏消息。5分钟后,上级大夫赶了来。是H主任,我认识她。她也在我肚子上划了一会儿,然后表情很复杂地看向我。我不敢看她,躲开了她的目光。
“亲爱的,”她很轻地说,“已经没有胎心了。”我感觉自己心脏开始猛烈地跳,呼吸越来越急促。H主任过来拉起我的手:“你爱人来了吗?我把他叫进来好吗?”我没有回答她,话已经到了嘴边:“是我来晚了吗?”“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好确定是什么原因……”H主任解释着,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觉得头顶上方白色挂灯的灯光好刺眼,自己的两条腿在发抖,我想让它们不要抖了,但根本控制不住。
先生去办住院手续了。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电脑桌面,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凌晨4点钟。我的所有感官好像停止了工作,一下子没了感觉。脑子里有个想法冒出来:凌晨4点?这是不是做梦啊?我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快醒了?怎么还不醒?
直到先生办完手续,推开门,站在我身后,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时候,身体里突然有股力量开始翻腾,我把头抵在他胸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声音很大,我甚至能听到四周的回声。那个声音告诉我,这是真的,我的孩子,她离开我了,是我把她弄丢了。
我被安排进了产房,看着缩宫素一滴一滴,沿着长长的管子进入我的手背。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反复交代注意事项、问诊、签字。我根本没有时间悲伤,医生要我记录宫缩间隔,留意自己的阵痛反应,如果有任何不适马上叫她们,为了应对可能的大出血随时准备剖宫产。我对那几个小时的记忆,大约就是——越来越频繁的阵痛,不断来检查宫口开到几指的医生,吊瓶里滴着的液体,还有旁边隔间的孕妇们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我好羡慕她们,我觉得自己连呻吟的资格都没有。
8个小时的阵痛过后,我生下了她。接生的医生凑过来问:“你要看看吗?”我点头。孩子被擦得很干净,放在我的头左侧。我扭头看她,她那样小,那样软,黑黑的卷卷的头发,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我身边,就像睡着了一样。我伸出右手触碰到她的皮肤,是温热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的女儿,她是不是还活着?她已经8个月了啊,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怎么说走就走了?
我至今很感谢那个医生,我并没有看过她的门诊,但因为她的善意,我和我的女儿见了一面。那短暂的半分钟,让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个天使,”我想,“也许人间太令她失望,我太让她失望,所以她离开了。又或许她完成了任务,所以匆忙回到了天上。”
医生最后的诊断是胎盘早剥,很凶险。说可能是因为胎盘长到了纵膈上,脐带突然掉落导致缺血——“‘可能’,又是可能!”我在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可能要落在我的孩子头上!”我好恨自己。那一晚,我的孩子,她都经历了什么啊?她是不是很早就开始难受了?如果我早一点去医院,哪怕早半个小时,是不是就能救了她?为什么好好留在这人间的,是我?我不配啊。
最难的时候,反复刷一部美剧“This is us”,里面妻子对丈夫说,你的孩子,远比你想象之中更爱你。If you love them hard, they will love you back. Even if you are not good enough, you make mistakes, they will forgive you. 看到这里的时候,哭成了傻子。我想,我的孩子,她用了全部生命来爱我,陪我度过至暗时刻,教我学会放慢脚步,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在那样危险的境地里,选择让我完好地幸存。可我,却没有好好爱她。我应该再好好抱一抱她的,告诉她,妈妈也很爱她。
有很多时刻,会想起她。想起我靠在墙上,低头看着凸起的肚子,和家人开玩笑说,“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了。”想起坐在电脑前改论文,她突然踢了我一脚,好像在说“好无聊啊,陪我玩一会儿!”想起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她就开始兴奋地“乾坤大挪移”,我无奈地摸着肚子说“闺女,你怕不是个‘夜猫子’吧。”
就在生下她的第二天,我的QQ邮箱跳出来一封邮件,是我两周前拍的孕妇照。照片上,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淡蓝色连衣裙,手托着肚子,眼睛看向前方,眼神坚定,温柔,又有力量。
我小心地把那些照片包起来,和给她买的小衣服、小凉席、小玩具,还有给第一个孩子的荷包,一起放在整理箱里,搬家的时候还带着。26周时她啃脚丫的B超照,也被我偷偷塞到了钱包最里层,一直带在身上。我不想忘记她。我想让她看到,我在努力活成一个让她骄傲的妈妈。
05
“咱们去雍和宫拜一拜吧。”第二年的春节,妈妈突然提议。正在电脑上打字的我抬起头,迎上她的脸,她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垂下头,没有做声。
我妈不信佛的,事实上我们全家都没什么宗教信仰。记得妈妈说我1岁之前总是哭,没日没夜歇斯底里,像是要把整个肺都哭出来,很多人劝她去拜一拜,她很坚定地拒绝了,后来我自己慢慢就好了。现在她提出要去拜一拜,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可我不想去。
失去女儿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以最快的速度答辩、毕业、搬家,换了新的环境、开始新的工作,认识了和之前毫无交集的同事,刻意不去见以往熟悉的人,就是为了把“过去”硬生生切断,换个“崭新”的自己,努力活着。那些疼痛、悲伤、绝望,被我统统打包起来,放在某个角落,不舍得丢掉,却也不敢触碰。
“妈,我……我不想去,”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我不愿想起那些事,新的一年了,我就想好好往前走。”
妈妈怔了一下,垂下眼,“哦,好。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希望咱家平平安安的。”
“我知道。”
“嗯。”
“妈?”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不想要孩子了呢?”说这话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爸妈是那种从我结婚那天起就开始给孩子攒尿布的人。孩子,在我们家被赋予了太多意义。
“那就不要,”妈妈居然很快回答,“我和你爸没意见。”
我看着妈妈端着饭碗离开的背影,突然有点想哭。我知道她其实很传统,在她的观念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都是“不正常”、甚至“离经叛道”的事,她回答得那样快,显然早就想过了。
我也想过。这几年医院跑得多了,再加上身边亲人连生变故,愈发感到生命的无常。对于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并顺利陪伴TA长大这件事,我越来越感到风险重重。我想,把孩子带到这世间,难道不是自私的吗?即使有了孩子,TA能健健康康地长大吗?我这么想要个孩子,究竟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还是真的爱TA?这份爱,会不会把孩子绑架?那么多的女性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世俗的“应该”,我却把自己困在“生育”的圈里,是不是太不争气了?
“做妈妈”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开始慢慢松动,不再像之前那样笃定。但还是会担心,如果就此放弃,十年之后,我会后悔吗?到那时候,我会不会怪今天的自己?
就在这样的摇摇摆摆间,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
先是住院手术,把不全纵膈切掉了——我知道,相比于切掉的风险,之前受的伤是我更不敢承担的风险。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因为乱跑撞在门框上,脑门磕破缝了好几针,事后爸妈狠狠地把门框锯掉的场景。我在心里对孩子说,孩子,妈妈把那个伤害你的纵膈切掉了,你在哪里啊?还会回来吗?
接着,我等了三个月,终于约到了生殖中心最有名的专家。那段日子常常往那跑,认识了很多在求子路上历经坎坷的夫妻。有的做过8次试管都没有着床成功,还在准备进入下一个周期;有的好不容易怀上了双胎,孩子却双双停育。很多女性已经不再工作,她们带着小马扎、食物和水,驾轻就熟地坐在拥挤的走廊上,我看着她们疲惫的脸,第一次对“做妈妈”这件事产生了恐惧:真的要这样吗?为了成为母亲,需要放弃掉部分甚至全部的自己吗?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这样自私的人啊。
而我,却难得成了“幸运”的人。前前后后两个月,我做了十几种检查,最后一次去看诊的时候,那位专家快速翻着单子,头也不抬地说:“你不需要再来看我了。你没问题。”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赦免”了——真的吗?原来我是正常的吗?曾经的种种涌上心头,一阵酸楚。
或许,我可以再试一试?
06
这一次,孩子是在年末来的。2020年12月30日,早孕试纸上明显的印记,宣告着,TA来了。那天,恰好本学期的课程结课,我给学生们订做了“签语饼”,每个小饼干里夹着一张纸条,每一张都不同,是我送给他们的新年祝福。我自己也抽了一张,饼干吃掉后,纸条上写着:“愿你身披铠甲,而内心柔软。”
我心里一个激灵——那是我在2018年新年,写给孩子的话。是她要回来了吗?
但是,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有个化验的指标不大好,也有少量出血。紧张地跑去看医生,医生只说,没什么能做的,等着吧,优胜劣汰。
我躺在床上不敢动,尽可能让自己不去胡思乱想,但还是控制不住地上网查资料,焦虑不安。那时赶上先生出差,却被突然的疫情隔离在外地,慌张到极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可能……就要放弃了。”“好啊,放弃就放弃,”他说,“咱们可以养只小狗,你说吧,柴犬?柯基?还是边牧?咱们小区有一只柯基,特别喜欢我,每次碰到都要扑上来舔我……”我听着电话那头他蹩脚的安慰,突然又感到内疚——我怎么能想放弃呢?孩子如果知道,会对这个妈妈多失望啊。
热心的朋友打来电话安慰,说自己当初怀孕也是出血,血流得吓人,别人都说保不住了,但她坚信孩子一定会没事的,现在娃都3岁了呀。
是吗?是我不够相信TA吗?可是如果孩子本来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我应该强求TA吗?人生实苦。我想到《心灵奇旅》里的那个22,如果TA就像22一样,看尽了人生酸甜苦辣,但并不想来人间走一遭呢?
奇迹没有发生。我在家里自然流产了。我和这个孩子短暂的缘分,停在了7周,TA的胎芽刚刚长出2毫米。
2021年元旦的时候,单位曾经搞活动抽奖,我抽到的是毛绒公仔,一只穿着毛衣的小牛。我把它放到办公桌上,对着自己的肚子说:小牛,欢迎来到咱们家。现在,我把小牛公仔放在了自己那个特别的整理箱里。有时候我想,如果有天堂,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会见面吗?他们如果聊起我这个妈妈,会说些什么呢?
以前读博的时候,学校里有一片牡丹园,很大,就在荷塘旁边。每年四五月份,春天把所有植物的叶子全部染绿之后,各色的牡丹就像赶集一样抢着绽放。那片牡丹的花期并不长,最盛时也就一周时间,很容易错过。
原本我是不大喜欢牡丹的,感觉太过艳丽。但2018年的4月,我曾经和先生散步路过了牡丹园,那年的牡丹开得很早,有一朵白牡丹,在一片粉红正红紫红中间,开得那样骄傲又舒展,我突然来了兴致,俯下身去闻,先生拍下了那个瞬间。
那是我和女儿的最后一张合影。
那年以后,每年的4月,我都会再回到那片牡丹园,坐在园子旁边的长廊下,和曾经来过我生命中的孩子说说话。我想,他们去了哪里呢,有没有再来人间看一看?我努力活成的样子,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吗?
今年回去的时候,我迎面撞上一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从台阶上跑下来,一个没刹住,打了个趔趄,我上前扶住她,她抬起头看向我。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有点害羞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很快又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哈哈哈哈谢谢阿姨!”小女孩咯咯笑着,跑远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四五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玩投沙包,玩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回家,每个小孩子的妈妈就会在自家门口大喊:“回家吃饭啦!”然后大家恋恋不舍地分手,一路咯咯咯笑着朝各自的妈妈跑去,小小的身影在斜斜的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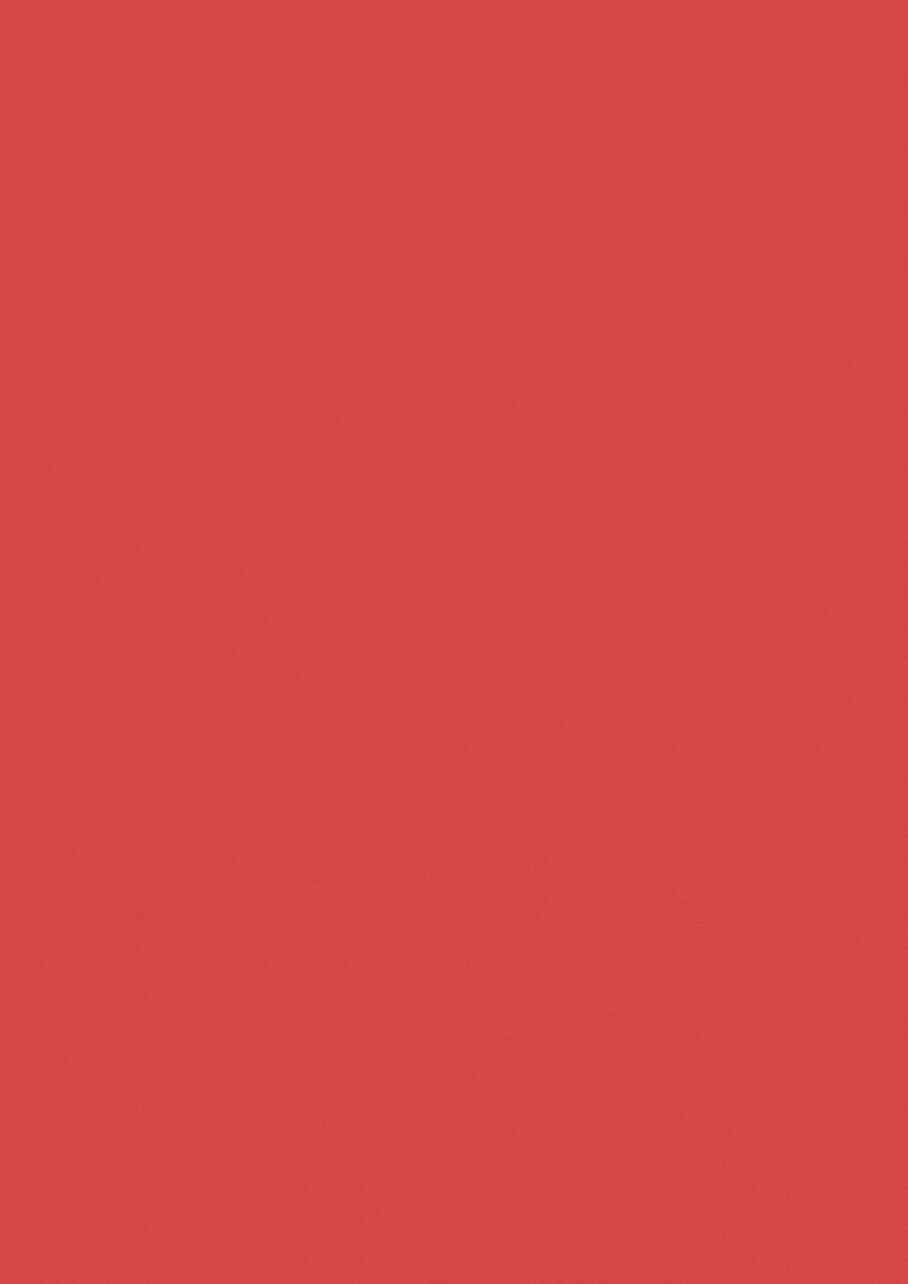
在6月的三明治短故事学院里,有几位女性作者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和生育、流产、身体有关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你会看见,关于女性的议题,被讲述和讨论的,还远远不够。点击阅读前两篇作品:
作者后记
来短故事写作,于我而言就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约会。早在半年前就加了小助理的微信,每个月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什么工作太忙啦,坚持不了啦,来大姨妈啦,各种。最后“精心”选了最忙的一个月,第二天开班,前一天晚上才下定决心加入。
其实是很忐忑的。故事在心里埋了太深太久,回忆被打开的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水的很沉的皮球,被扎漏了,很多细节一下子涌出来,钻心得疼。有很多时刻想要停下逃走,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点赞和鼓励是续命的。就像怯生生的小朋友,摔倒了擦破皮,疼得掉了泪,想跑到家长那里要抱抱,又怕被批评“怎么这么不小心!”
好在,三明治不单给了我抱抱,还时不时亲亲举高高。我从第一天提笔连“流产”这个词都不能碰,到开始能够直面那些创伤、疼痛,还有温暖。越来越体会到写作带来的疗愈,就像很喜欢的一部美剧This is us里面的台词,you took the sourest lemon that life has to offer and turned it into something resembling lemonade。
犹犹豫豫迈不开步子的时候,依蔓对我说,“故事被坦诚地看见和讲述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力量了。不要怀疑它。”嗯。我想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想给别人带来力量。我想让更多的姐妹知道,所谓“过去”,过不去也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带着一部分的过去,往前走。
人生无常,幸而我们还有爱。要爱自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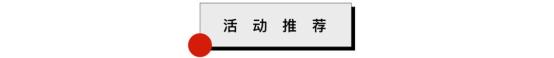
把生活变成写作,把写作变成生活
三明治是一个鼓励你把生活写下来的平台
原标题:《从15岁就开始梦想做妈妈的我,失去过三个孩子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