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雕塑艺术如何……形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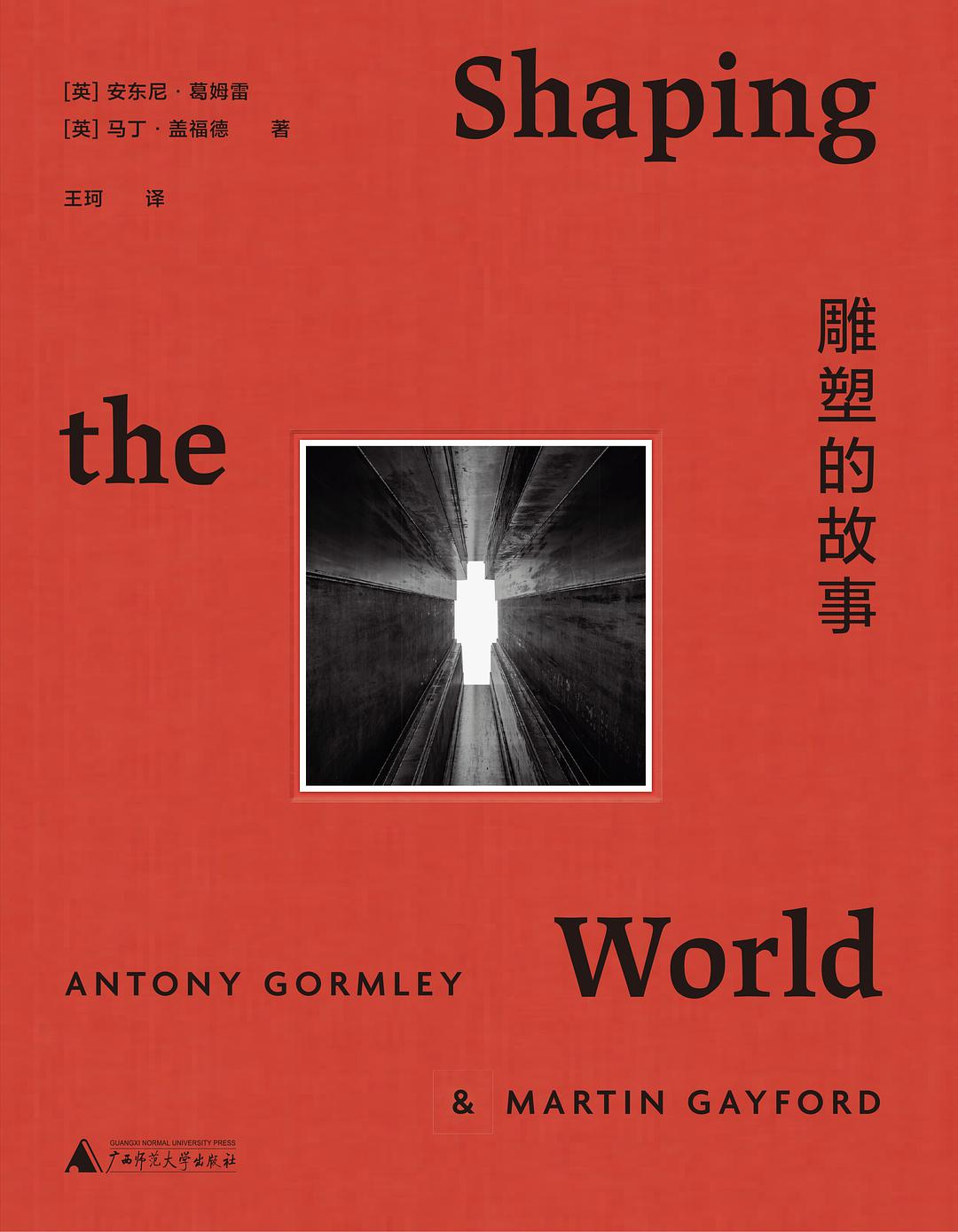
《雕塑的故事》,[英]安东尼·葛姆雷 / [英]马丁·盖福德著,王珂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392页,298.00元
英国著名诗人、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爵士(Sir Herbert Read)曾经说过,艺术史就像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其连贯性有赖于对一个原则的果断选择。我相信这是他撰写现代绘画史、现代雕塑史和艺术的形式起源等著作的经验之谈,值得思考的是连贯性与原则的关系以及“果断选择”在历史写作中的意义。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与写作者如何思考“连贯性”的问题、如何确立自己的原则、是否愿意或敢于“果断选择”,这些问题都隐含深意。
似乎是巧合,最近在读英国著名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和艺术批评家马丁·盖福德(Martin Gayford)合著的《雕塑的故事》(原书名: Shaping the World:Sculpture from Prehistory to Now,2020;王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的时候,正好在深圳当代馆参观了“超凡与人间—— 苏新平与克里斯多夫·勒·布伦”展览,阅读与观展的体验不但相互契合,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里德爵士所讲的连贯性、原则和果断选择非常吻合,而且超出了艺术史写作的视野:艺术家的创作同样需要有自己的连贯性、原则和果断选择的勇气。
《雕塑的故事》,中译本的书名很朴实,也符合该书的主要内容,两位作者在对话中讲述的就是雕塑的故事。但是原书名“Shaping the World”的原意和该书的核心观念是“形塑世界”,对话所围绕的中心是雕塑艺术与世界的本质性联系,并且如副标题所言,有一条从史前到今天的历史叙事脉络,这就是支持它的连贯性的“原则”。很显然,它所讲述的并非一般的雕塑家及其作品的“故事”,而是通过讲述雕塑如何形塑世界来重新形塑我们对于雕塑以及对于世界的看法——正如有评论所说的,它实际上是“颇具挑衅性的”(sometimes provocative)。讲到这里,马上想到在“超凡与人间”展览中展出的苏新平雕塑作品《行走的人》,在展场中围着这件作品转了几圈,我当时就有它是sometimes provocative的感觉。在展厅里间隔出来的三个狭小空间中,各有一个近四米高的疾走中的人。四面墙壁,出口低矮,仍然义无反顾,紧握拳头,迎风疾走——当有些人跪下的时候,他迎风疾走。去年苏新平在悦来美术馆“六个盒子:当代艺术展”中首次展出了雕塑作品《行走的人》,那是四个行走的人迈着大步分别走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当更多人急着涌向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们仰天昂然四散而去。或许他的挑衅性就在于“行走”中的隐喻:个人的、去中心的、无畏的、无方向的疾走,完全颠覆了某种我们曾经熟习的前进叙事,而且能够在“语言探索”中获得妥妥的合法性。一部世界艺术史在我看来,有些杰出的创作常常有这样的节奏:“寻衅”而不“滋事”,没有挑衅性的艺术史必将是僵死的、媚俗的。

行走的人 405×130×455cm 玻璃钢 苏新平 作 2021 深圳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苏新平在谈《行走的人》时指出这件作品“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与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联。当下的种种问题既让我震惊,又令我困惑和无奈……。题材的选择和思想观念应该是一致的,而观念与语言方式和方法也应该是一致的。”与他早期表现人的题材的作品相比,他说“今天更关注的是个人的处境和生命的价值”;同时他也强调在这组新作背后的价值观和之前有很大的关联性,里面有他的情绪、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其中的内容与回忆、伤感和乡愁有关。那几个迈向不同方向的“行走的人”,正是以决绝的行动宣泄出那种震惊、困惑之后的爆发性情绪。在深圳的这次展览中他还有一件雕塑作品《聚》(高约四米)竖立在展馆外面,整个作品就是十只紧紧地交叉相握在一起的手指头,有点像一件被紧紧捆绑和裹扎之后的非人肌体,它所表达是爆发前的无奈与愤怒。从《聚》到《行走的人》,正是对“个人的处境和生命的价值”的深刻揭示和精准表现。
更为巧合的是,参观展览的这一天正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仙逝的消息在微信上刷屏的时候,苏新平的这件人物雕塑作品使我突然领悟到从中或许可以找到表现一位保持自由精神与人格尊严的历史学家的一束艺术之光:不是文化浩劫之后士人的仓皇奔散,更不是攀附权势时的疾趋,而是义无反顾地肩负文化天命而前行求索。想起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所讲的,先生的著述学说或时有不章与可商,但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不可磨灭的。眼前的这尊“行走的人”虽然完全无法在外表样貌上与一位儒雅通达的学者文人建立联系,但是其在人心飘零、海内戚戚之际不堕自信、坚毅表达、昂然前行的精神内涵,在我看来竟然就有了内在的联系。或可援引艺术创作的接受美学,“行走的人”中的隐喻的确具有可以投射的张力。
安东尼·葛姆雷在“前言”中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雕塑?他言简意赅地唤起了我们的陌生感和深邃感:“在这个由物构成的世界里,雕塑是奇怪的存在。而且我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雕塑变得越来越奇怪。但是有那么一些主题,跨越了地域、文化和语境,将历时千万年的雕塑创作联系在一起。所以,‘雕塑是什么’这个问题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密不可分,那就是:‘人类是什么?’”(第6页)这几乎就是对全书的核心论题“形塑世界”的精炼概括,令我有点惊讶的是把“雕塑是什么”与“人类是什么”联系起来的思维和表述竟然出自一位雕塑家的笔下。作为艺术批评家的马丁·盖福德在“前言”则说的很谦逊和朴实:“我通常是通过文献和博物馆的展品来审视艺术史的,难免有所隔阂,这次却有幸和一位正在创造艺术史的人同行,借助他的专业视角进行观察,对我而言是难得的机会。”(第7页)之前葛姆雷就说过盖福德写的米开朗琪罗传使他读得心醉神迷,认为只有盖福德能够真正从时代和艺术家内心出发来揭示艺术家的贡献,在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和惺惺相惜是很难得的。在我阅读经验中,一流的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的严肃而深入对话往往能谈出许多艺术史家难以说出的话,他们对艺术的创作与审美体验不是仅从文献阅读与研究中可以获得的。盖福德接着说,“我们的探索早已突破了所谓‘雕塑’的传统疆界。我们会探讨巫术、仪式和舞蹈,也会畅谈那些由光线、人的行为以及虚空构成的作品。以上所有元素,都能够作为塑造世界的原材料而发挥作用,并被赋予人性意义。”(同上)更具体地点出了该书的一些重要论题和关于“塑造世界”的解释。
顺带要说的是,马丁·盖福德在2016年就出版了与大卫·霍克尼合著的《图画史:从洞穴到电脑屏幕》(A History of Pictures: From the Cave to the Computer Screen;万木春等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也是非常精彩的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对话式著作。从艺术与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和叙事方式而言,现在这部《雕塑的故事》正可以看作是《图画史》的续编:从洞穴到电脑时代的雕塑史。
《雕塑的故事》到底如何突破了“雕塑”的传统疆界,如何在整体性的意义上重新审视那些“能够作为塑造世界的原材料而发挥作用,并被赋予人性意义”的雕塑元素,从该书的叙述结构中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空间中的人体、脱离墙壁、高地、原野与立石、树木与生命、明与暗、泥土与造型、虚空、形体与块面 、青铜时代、身体与建筑、巨像与奴隶、时间与死亡 、衣纹与解剖、行为与事件、畏惧与拜物、收藏与选择 、工业与重金属、塑造一个变化的世界……。一方面因为该书不是教科书式的雕塑通史著作,因而在叙事结构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的对话的确如里德爵士所言,果断选择了一种使连贯性得以实现的原则,就是要从各自的创作经验、审美评价中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雕塑如何形塑世界,如何影像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观看。从这些论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来看,更是远超出传统雕塑史所能涵盖的范围,它们与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建筑学以及历史图像学等都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要思考雕塑如何形塑世界,首先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唤起一种陌生感:雕塑是一种物体,一个物质世界,一种表现为材料的讯息;自从人类存在,它就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扩张,证实着人类的思考、感受和创造能力的进化。从人工制品与雕塑的元始性,盖福德想到《约翰福音》的第一句“太初有道”已经被考古学家改写,葛姆雷马上接上去说“应该说‘太初有物’才对!我之所以选择雕塑作为毕生的事业,正是为了逃避语言,以有形的方式交流。雕塑是直面事物本来面目的工具,有助于我们从物质层面了解事物。”(16页)
但是,雕塑作为太初之“物”,其实还是离不开“道”。当我们今天面对那些远古时代遗存下来的巨石柱(群)的时候,对存在的惊讶、震惊也就是对远古制作者的意志和力量的震惊。葛姆雷在谈到五六千年前法国布列塔尼的卡纳克巨石林的时候说,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它们看起来像冰川漂砾,其实是从露出地表的片岩中分离和制作出来,是艺术史学者欧文·帕诺夫斯基提出的“塑造的意志”(the will to form )的惊人呈现。盖福德则进一步追溯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尼采认为人类都受到这种意志的驱动;因此才有了帕诺夫斯基的观点:人类有一种将事物和地点重新塑形以赋予其人的意义的冲动。(56页)这种“塑造的意志”就是使“太初有物”的内在源泉。说到底,还是回到席勒那句感慨的话:“啊,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
对雕塑的思考当然离不开绘画,第二章“脱离墙壁”讨论的起点就是雕塑与绘画的比较。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以至盖福德说对它能延续到今天感到既诧异又好玩!在绘画与雕塑分别属于二维图像与三维物体这一根本区别之外,两者的共性是“源于人类塑造形象的本能”(葛姆雷),另外绘画与雕塑在审美上或视觉上也是互通的,甚至在物质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因此盖福德说“就像本书中的插图一样,一幅画可以代表一件雕塑”。(30页)这里所谓的代表是指视觉呈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还进而讨论了在真实景观中的雕塑同样可以被感觉为一幅图画,观者往往有置身于图画中的真实感觉。盖福德说绘画与雕塑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历史上许多艺术家集雕塑家和画家于一身,能够同时以两种方式进行创作。(31页)远的不说,苏新平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读本科时的专业是绘画,但也上过雕塑课;虽然他后来主要以版画和油画成名,但他把创作视野延伸到影像、雕塑等门类,自觉打破专业、学科和表现题材领域的限定。雕塑《行走的人》缘起于2010年他创作的油画作品《奔波的人》,在雕塑《聚》之前就有了纸本色粉画《无题3号》,在黑红色背景中的一排紧握的手指。
雕塑家葛姆雷说,雕塑一经完成,世上就多出了一样之前不存在的东西,世界由此而改变;雕塑要求世界靠边站,给自己留出一席之地;在物质层面,绘画是脆弱的,必须依靠画框、墙壁等作为依托,而雕塑不用。“对于一件好的雕塑来说,经历风霜只能让它更加迷人。”(29页)很真实也很诗意,难怪他的《别处》(1997年)、《行星》(2002年)等作品的确具有经历风霜的物质性和诗意的力量。据说苏新平的雕塑《行走的人》将会以更大的尺度矗立在城市的公共广场上,它将经历的风霜当然会使它更加迷人。
谈到公共雕塑,历史上的统治者、权贵阶层利用雕塑彰显统治威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作品多不胜数。另外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这些雕塑又会遇到湮灭的命运,这是雕塑如何形塑世界和改变人们对历史看法的重要视域。盖福德指出,“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制造彰显权力的形象中,如国王后像、总统像、皇帝像。达·芬奇那匹巨马如果铸造成功了,也会是这样一座象征权力的纪念碑。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建造和竖立纪念碑。而它们又往往被人遗忘,乃至被推倒。”(229页)这些象征权力和压迫的大型雕塑的盛衰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的政治史,彼得·伯克在他的《图像证史》中专门有“掌权者和抗议者”一章,论述在雕塑、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压迫权力与视觉图像的关系。他指出,统治者的形象往往在风格上表现出必胜的信心;历史学家也广泛同意这些统治者的雕像和绘画可以在维护体制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大出版社,2008年,86、80页)但是在葛姆雷和盖福德的对话中,他们的焦点更多落在作为历史遗产的统治者雕像的处理上,而且涉及到最近的公共政治思潮,因而尤为难得。
葛姆雷首先谈到他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城外的一座公园里看到了许多塑像与一些当地政治家的塑像堆放在一起,“从这样的角度,你既能感受到这些雕像所代表的权力与分量,也能看出它们如今多么无用。”但是他认为“雕塑一向被用作疏导民众激愤和政治抗议的避雷针,同时又像五朔节花柱一样,供人们寄托记忆、举行仪式。”因此主张应该把这些雕塑保存下来,“无论它们象征的是善还是恶,我们都应该谨记”。(229-230页)然后他马上跳跃到去年夏天发生的黑人抗议活动,人们同样想起了雕像,强烈要求把各种各样与殖民主义、奴隶贸易有联系的雕像从基座上移除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塑像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转而改变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应该妥善保存这些雕像,后人应该会感谢我们的。(同上)这是把雕塑与历史记忆以及开放的政治愿景联系在一起的合理想象。
面向未来的雕塑应该是如何的,迄今为止的当代雕塑史其实已经作出了展望。第十四章“行为与事件”论述了改变我们看待雕塑和世界的方式,很有启发。盖福德认为从去年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歌剧《伍采克》中,可以看到雕塑这门艺术的界限十分模糊,它能够扩展到仪式、宗教、电影、戏剧等多个领域。(284页)接着他回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艺术家约瑟夫· 博伊斯(Joseph Beuys)的行为艺术,分析了他在1974年创作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所表达的理念。曾经与博伊斯长期对话的葛姆雷很清楚他想表达的是对二战后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文化的反抗:“博伊斯想要表达的是:等等,我们不能就这样忘记过去,我们需要抚平创伤。”(286页)盖福德说,他的行为艺术提醒我们,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行为的产物,整个创作的过程就是行为艺术。于是,像吉尔伯特和乔治双人组那样的身体表演、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展厅里坐了三个月与观众对视、有些艺术家以割伤身体作为行为艺术等等,不断竞争的仪式、表演、观看、震惊,行为和事件比形塑物体更为重要。
最后盖福德说,“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关于艺术的根本问题:艺术品应该放在哪里?” 葛姆雷的回答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博物馆。我们能不能创作一件对生活有所助益的艺术品,而且能像欣赏天空、山峦、树木那样与所有人分享,在时间流逝与四季更迭中永存?” “我想,雕塑的意义也在于此—— 为创造未来提供基础。”(379页)这是关于艺术的大哉问,全书最后是跨页图像,葛姆雷的雕塑《别处》(1997年),一百个铁铸的人体在站在海水之中。答案肯定就在人与自然的永恒关系之中。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