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忌:我希望能写出一代人的来龙去脉
张忌:我希望能写出一代人的来龙去脉 原创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理想国imaginist

《如父如子》
人到中年,张忌开始写作一部“野心之作”,他曾表示自己要在《南货店》里写满100个人物,并且不是一笔带过式的拼凑。
这本书的缘起看似偶然,却折射出张忌切肤的生命经验。2016年,经历了爷爷的去世后,张忌开始将目光投向自己上一辈的故事,深入到家乡小城一家供销社(南货店)浮沉四十年的历史。
不论是供销社还是南货店,对今天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陌生的词汇。但在四十年前的中国,这里却代表着中国人对生活的向往。在一家小小的店铺里,人们来来往往,各色人等的故事也就徐徐展开。

张忌
代表作:《南货店》《出家》《搭子》等
谈及对当下时代对物质的迷恋,张忌认为物和人是不能严格区分的,物是人的反应,他有怎样的精神世界,都会在物上忠实的反应出来。我们不妨把《南货店》理解为是一部通过物来映照出人的真实一面。
《南货店》是张忌自长篇小说《出家》之后的最近力作,也是是一部“见自己”的作品。如今《南货店》面世,也完成了这位作家“见众生”的蜕变。但是他也说,不论写了多少芸芸众生,但在这些人的身上,你看到的全部是你自己。
这是2021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第二期,对谈嘉宾是入围作品《南货店》的作者张忌,请大家持续关注后续更多作家访谈。
01.
“我的写作没有那种特别沉重的母题”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以下简称“文学奖”):张老师你好,我们就从你的最新长篇小说《南货店》谈起把,你在很多采访里谈到自己创作这本书的缘起与自己的家庭有关,你能不能具体谈谈一段偶然得知的家族往事为何就激发了《南货店》的写作?
张忌:2016年,我爷爷去世,在葬礼上父亲跟我谈起了爷爷的身世,说“有一年的下雨天,爷爷的父亲披着一领蓑衣出门,去余姚打官司,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句描述让我生出了很复杂的情绪。一个人的一辈子,浓缩成了一个画面。参加葬礼的子孙集聚一堂,他们都来源于画面里的那个人物,但他却简单成了几乎空白。这一刻,我觉得我有一种强烈的写作欲望,我想知道我上一辈的人经历了什么,他的过去与我的现在又有怎样的联结。随后,我便开始写《南货店》,我希望能写出一代人的来龙去脉。

张忌
文学奖:家庭问题,尤其是父子关系是很多中国作家的母题,《南货店》隐约是你父辈的事情,你的父亲就是在供销社工作的。你觉得父辈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张忌:我的写作没有那种特别沉重的母题,我跟我父亲还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中国式父子关系,谈不上和解。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人的生活,我做了这样的尝试。但可能《南货店》里体现了几组不同的父子关系,会给人这样一个感觉,我在试图叙述某种父子关系,这更多的只是一种巧合,对我来说,我的小说都是以人和人的关系开始,比如父子,比如夫妻,比如姐妹之类,我觉得人生存的方式,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方式。
文学奖:这本书的人物特别多,据说你有野心“要在小说中写满100个人物,不是一笔带过式的拼凑,而是立体的生命呈现。我不过多插嘴,让每个人物自己说话,生成时代变更下的江南图景。”这几乎看作是张忌版的《人间喜剧》,具体到写作技巧,你是如何表现这么多不同人物的细节的?日常生活里你会有意识地搜集这方面的素材吗?
张忌:这可能是一个作家的野心吧,写作最难的就是写人。如果一个小说有机会展现足够多的人,每个人又有可能写得有血有肉,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充满了巨大吸引力的。
作家肯定是心灵特别敏感的一群人。在我过往的生命里,我肯定是有意无意地储藏了许多真实的人物。他们进入我的脑子后,又在不断的生长,组合,分离。当你某天的写作突然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就自然出来了。
写作肯定是有技巧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技巧这个东西太细碎,太个人化了。我只能说,你得跟你笔下的人物保持恰当的距离,不要试图控制他,不要试图替他说话,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小说的面貌应该不会差。
02.
“物和人是不能严格区分的,
物是人的反映”
文学奖: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70年到1990年代,正好也是中国变化最为剧烈的时代,你在写作的时候为何没有再写下去,处理新千年之后的人物命运呢?就个人来说,作为70年代末生人,你的青春几乎是伴随着《南货店》故事展开的,文学内外,你对书中涉及的时间段有何特别的情感?
张忌:其实,这本书还有下半部分,有许多人物和故事,也已经在我脑子里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写。将一个小说分开两部分来写,这在我的写作经验里还是第一次。
原来我设想将小说写到90年代末,新世界到来的时候。但在写完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情绪有些变化,因为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年代,如果继续用《南货店》里面的人物和故事线写,并不足以表现90年代,或者说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我在进入90年代以后,将小说暂停了。当然,从某种程度来说,写到这里,这个小说也可以结束了。但我应该还会再写,写出来后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的一群人。我感觉自己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描写90年代的方法,但我还不太确定,得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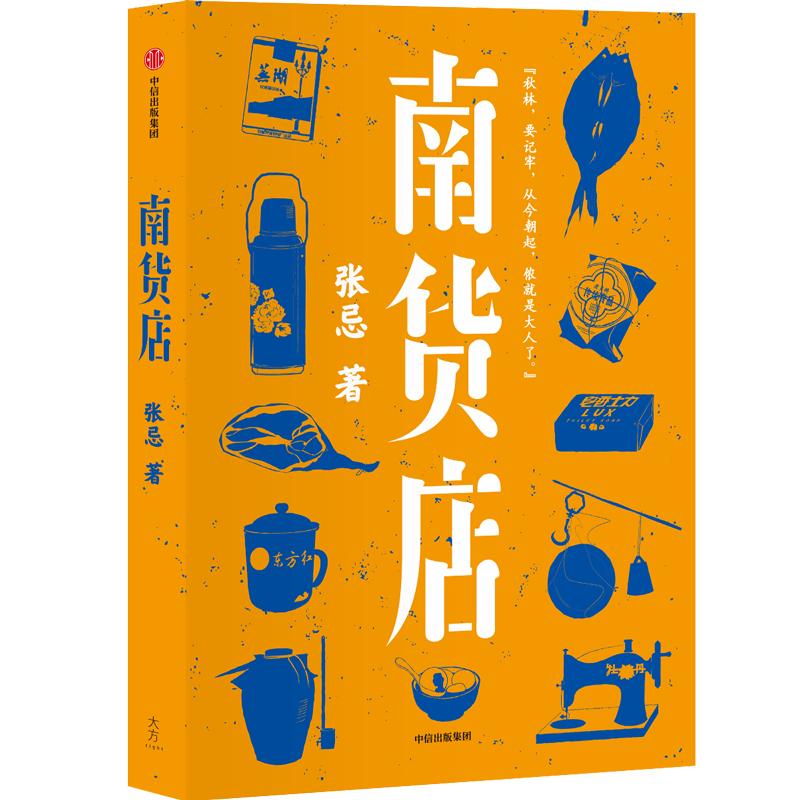
《南货店》
张忌 著
文学奖:对物质的精细描摹是《南货店》的一个特点,书里的饮食器物都似乎有了自己的温度,你平日也喜欢收藏,那你如何看待自己对物质的细腻书写,在一个拜物教的时代,你觉得这种对“物”的崇拜是不是一种精神性的症候?或者说,你是把人的精神寄托在物质上来写作的?
张忌:我小说里对物的情感,跟我生活中对物的情感发生的时间是一致的。在我35岁之前的小说里,很少看到这种对物不厌其烦的描述。我35岁之前,更喜欢跟人打交道。35岁以后,却似乎更喜欢跟物打交道了。
当然,物和人是不能严格区分的,物是人的反映,他有怎样的精神世界,都会在物上忠实地反映出来。再谈到小说,我觉得物能成为小说的一个方法。对物的一个真切的描写,就是对人的一个真切的描写。我觉得文学创作有一条铁规,你永远不能直着来。所以在描写人物的时候,特别描写心里状态的时候,我尽量不让他直接说出来,但又不能不写,这个时候,物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描写对象,它能从另外的角度来映照出人的真实一面。
文学奖:你是在疫情期间完成这部作品的,身处一个巨大的动荡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张忌:在疫情的时候,这个小说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疫情期间写的是这个小说的结尾。疫情是突如其来的,所以人会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每个人都在直面生死,很沉重。但过了一阵子,因为电视也好网络也好,时刻都在铺天盖地的宣传,突然又觉得一切都没那么沉重了,甚至生死也不是那么重要,它变成了一个日常的事情。所以,在那种情绪下,我完成了南货店的那个关于悼词的结尾。我不知道这个结尾是不是最适合这个小说的,但它跟疫情这个重大事件的确是发生了某种特别具体的联系。
文学奖:从《出家》到《南货店》中间隔了好几年的时间,这几年中你在做些什么?你觉得写作这两本书的时候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你也谈过如果没有进入中年,自己不会写作《南货店》,你觉得一个人的写作和人生状态的关系是什么?
张忌:没有特别做什么,就是正常的生活,工作,赚钱,养孩子。我没有创作焦虑,也没有写作成瘾症。生活肯定是要远远大过写作这件事。当然,我也没有绝对地离开小说这件事,这几年虽然没有写,但一些小说里的东西始终在我脑子里生长,等到差不多了,我可能就会写。
从《出家》到《南货店》,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会变得平和一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写《出家》的时候,正好听到有个作家说,小说家写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把人物写死。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所以在写《出家》的时候,会刻意的让人活下去。但在《南货店》的时候,我就不做这种事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是真诚的,那他的小说肯定跟他真实的年龄和想法是保持一致的。我以前看那些老年文字,觉得写得寻常,但现在去看,却觉得里头惊心动魄。古人将每个年龄段进行划分,而立,不惑,知天命之类的,这不是发明,而是一个经验的总结,年龄不同,写作出来的景观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03.
“只有叙述上的冷静,
才能完成写作上的某种残酷”
文学奖:你说过《出家》是“见自我”的作品,而《南货店》是“见众生”,从自我到众生,恰好是文学的两种不同的面向,这标志着你的人生观或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吗?
张忌:我刚开始写完《南货店》的时候,我觉得它和《出家》完全不一样,《出家》是见自己,《南货店》是见众生,但后来我觉得,其实《南货店》也是见自己。似乎你的笔下写了芸芸众生,但在这些人的身上,你看到的全部是你自己,你是用自己来写芸芸众生。再往后,我看《出家》,说《出家》是见自己似乎也不大准确,他见的是自己,但这个自己,也是众生。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有趣,见自己和见众生,似乎是文学的两种不同的面向,但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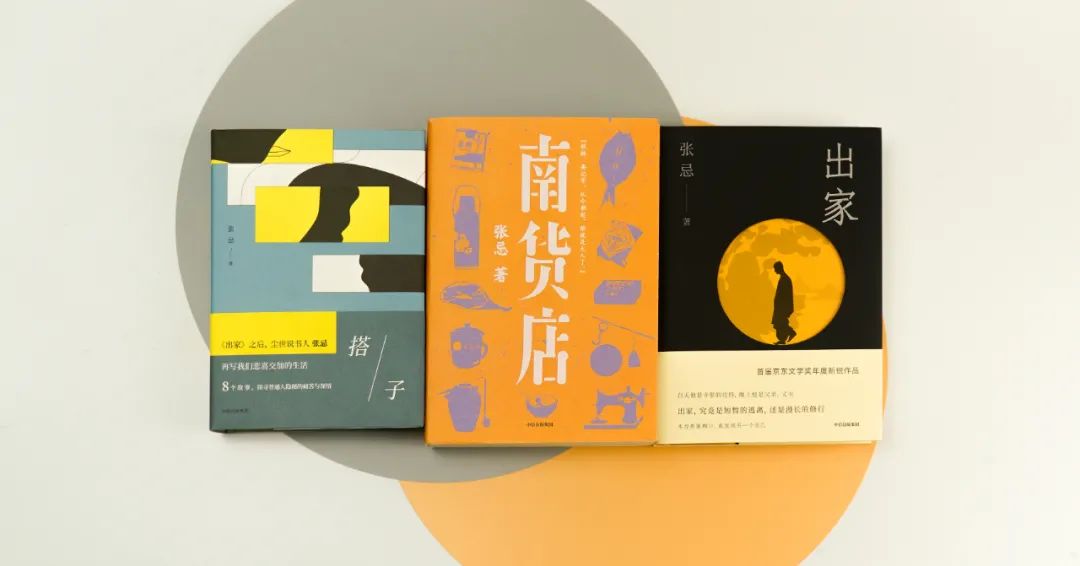
张忌作品,从左到右依次为:《搭子》《南货店》《出家》
我现在特别怕说人生观和文学观这些东西,因为我的这些东西也一直在变化,我对说出来的东西总有些不确定。对我来说,这或许已经成了一个警醒,让我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妄下判断。
文学奖:某种程度上,处理“改革开放”带来的阵痛和变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文革后的当代文学从“伤痕”“寻根”走来,似乎一直无法摆脱宏大历史的召唤,你认为自己是有意识地处理时代和个人的关系吗?这种对改革带来伤痛的反思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又一个新的思潮吗?
张忌:我不大关心别人的写作,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会关心,同行们在写什么,期刊上最近在发些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什么题材。但现在我不怎么关心,我只对自己的写作做出判断,比如我脑子里会有好几个想写的东西,我会跟它们进行交流。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告诉我,你可以写了,我准备好了,我就开始写了。
我对宏大历史之类的不大敏感,相对来说,《南货店》可能会对大时代的表现显得直接一点,但这不是我的写作秉性,我之前写的《出家》就是比较私人化的一个小说。总体来说,我会根据具体题材的气质来处理小说,没有特别的预设。
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反思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思潮,这我不知道,我不考虑这些宏观的东西,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我的所有趣味和气力都放在处理小说的人物,小说的细枝末节上。
文学奖:《出家》是一个讽刺性的作品,但也让人感动。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哪里?你有宗教信仰吗?你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信仰是否还有其价值?当然出家也可以看成是主人公的逃离,在这个意义上,你有过想要逃离什么的时刻吗?
张忌:《出家》的灵感来自于好奇,其实我所有小说的起点都来自于好奇。当我对某个人群,某个行当产生了巨大的好奇,但又没有答案,我就会想办法写个小说,试图来解答自己。我谈不上有宗教信仰,但我的家庭,从我的外婆,到我母亲,还有其他一些亲戚,他们大多信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佛教会更有亲近感一点。不管在哪个时代,信仰肯定是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有多大,要看具体的人。我不大喜欢或者是没能力去高屋建瓴的总结一个特别大的东西,所以时代和信仰的关系,我谈不出什么特别好的见解。
逃离这个词语是当时编辑给出家这本书找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还蛮准确的。特别是当人意识到生活的某种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欲望会显得特别不可抑制。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逃离,你在文字里构建出了另外一个人生,你在里面体验,经历,这是最好的逃离的方式。
文学奖:你的小说常给我一种在追求日常生活里的戏剧性的感受,所写作的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却屡有惊人之举,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是你刻意追求的吗?
张忌:我写作的时候,很少有一个预设,就算写《南货店》这样体量的小说,我也不会列提纲什么的。我经常说自己喜欢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下写东西,想太清楚了,下笔就没意思了。所以你说的这个效果,肯定不是我刻意的。我觉得这跟生活本身是一样的,生活的表面总是异常平静,但这种平静下面往往是暗流涌动。在小说里头,这种平静和汹涌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反比,只有叙述上的冷静,才能完成写作上的某种残酷。
文学奖:我看你的《搭子》《胖大海》等几篇小说,最难受的地方在于你总在人物最尴尬和难受的地方戛然而止,不给出一个让人安慰的救赎,不像一般作家给人物安排一个过得去的结局,你为何这样安排呢?
张忌: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不可能特别铺张的去展现什么,它只能截取,而在什么位置截取,取决于作家的判断和想法。所以,不同的作家会选择在不一样的地方开始和停止。
至于我的小说,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总会试图跟我达成某种协议,他们会在某一刻告诉我,好了,到此为止吧。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然后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我就会把小说结束。
04.
“小说肯定是要表现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
文学奖:你和弋舟的对话里谈到读《海上花列传》的感想,你说“它就像在那里放了一个摄像机,忠实完整地记录着一切。这样的小说,你是看不到作者的,在小说里,作者这个身份是消失的”。
在你看来,好的作品里作家不应该出现,能不能谈谈你的原因?那你认为小说里应该体现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吗?或者也可以这么问,你的个人经验是如何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的?
张忌:小说肯定是要表现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我的意思是,这个态度和价值观,跟其它读到它的人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不能说作者这个就是高于读者,甚至作者的这个就是标准答案。
我说的作者消失其实是一个创作态度和创作技巧的问题。我特别讨厌有些作品,写着写着,作者就会出来卖弄他的见识。作者的态度是要的,但它需要隐藏在小说里。有些作者似乎总是担心读者看不到,总是在显赫的位置将那些话讲出来。对于这样的小说,我会特别粗暴的将其归为小说技巧不够。
小说其实是一个作者比较诚实的反应,你的审美,你的思考,肯定是要表达出来的,但这个表达要合适,要恰当,不能让人看了倒胃口。
文学奖:金宇澄的《繁花》之后,方言写作一度被媒体炒作,从你的作品里也能依稀看到宁波方言的印记,但基本还是标准的普通话,近年来文艺圈似乎兴起一种“南方意识”,“南方电影”“南方文学”的概念陆续被制造出来,对此你怎么看。你觉得是否存在一种属于南方或者江南的文学传统?
张忌:我可能是属于文艺圈边界的人物,我居住在一个小地方,跟核心离得比较远,所以文艺圈流行什么,我不是特别关心,我也不是太确定现在是不是有太多南方的东西正在被提出来,或者正在发生。而且,南方不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不能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就应该被归纳在南方这个名词里面。我也不觉得南方这个词语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不能说用点方言,小说里多下点雨就是南方了,至少在写作这个范畴里,我觉得南方还没有成立。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南方作家的作品,大多还是面容模糊的。
我很喜欢《繁花》,对于我来说,觉得金老师的繁花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繁花》并不是一个崭新的作品,从我的角度看,他反而是一个很旧的作品。我能在繁花里看见我们的文学传统,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等等。他在当下这么西化的一个写作环境里,能取得这么大的反响,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的一个正统,而我的小说观,恰巧是在这个正统里面的。至于方言,严格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写的是一个方言小说,这个语言,也是在我认为的这个小说正统里面的,就是中国式的一个语言方式。我是特别在乎语言的一个人,我觉得不管小说发展到哪一步,语言永远是它的立身之本。而我认为中国作家能用的最好的语言,就是这种语言。
文学奖:你在其他的访谈谈到自己对《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及汪曾祺小说等作品的喜爱,从中可以窥见你的文学脉络,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详细谈谈你的阅读史以及受到哪些作品和作者的影响?你的小说颇有一些明清传奇的味道,这是否与你的阅读密不可分?
张忌:我的阅读跟普通人的阅读应该差不多,大家看的东西,我都看,学生时代我喜欢张爱玲,喜欢沈从文,《平凡的世界》我也喜欢看,陆文夫的《美食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后来我又喜欢一些外国文学,比如大江健三郎,比如库切,再后来,我就特别喜欢你提的这些作品,类似《金瓶梅》,《儒林外史》这些小说。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小说受了谁的影响,但通过阅读和写作,我觉得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审美了,这个审美是跟我们的传统对接的。在这里,县城这个名词就体现出它的独特性了。和大一些的城市相比,县城的开发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相对来说,它更保守,更传统,更中国。我一直在这里生活,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会跟这种传统和保守对接得更加紧密。所以,当我到一定年纪的时候,看到明清小说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繁花》这样的小说,我会觉得特别亲切,我会觉得那就是我想写的东西。
05.
“作家已经没有底气说什么好读者了”
文学奖:我在媒体报道里知道你长年生活在一个叫做宁海的县城,你为何坚持在县城写作?看得出来,你笔下的人物往往也是小地方的小人物,你觉得县城生活带给你哪些滋养?在你看来,这种生活方式是有意识地某种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抵抗吗?
张忌:我不是坚持在县城里生活,也不是坚持在县城里写作,其实这个话题谈得多了,就显得刻意了,变成许多大城市里的文艺工作者嘴巴里说的“下生活”了。我出生在这里,我的父母在这里,我的生活关系在这里,那我自然就在这里生活了。而且可能你对南方的,特别是宁波这边的县城不是特别了解,它跟现代都市没什么大的区别,非要说区别,那可能是文化生活这些要弱一点,比如博物馆,大的体育赛事等等,其它的都一样,包括这里的房子也很贵,在淘宝买东西也包邮。
回到写作,在这里生活,对我的写作肯定是有营养的。因为我一直生长在这里,如果我生长在别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可能是你说的那种性格比较弱的人,我喜欢在熟悉的地方生活,我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力很差。另外,我喜欢在小一点的地方生活,地方小了,会更有安全感一些,具体到写作上,写作的那股气也会集中一些。
文学奖:你觉得作家的理想读者是什么样的?你是否与这样的读者以某种形式相逢过?
张忌:在当下的一个环境里,我觉得作家已经没有底气说什么好读者了,太多的消费品出现,阅读成了罕见的事,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读者,至于是什么读者,这个话题就太奢侈了。我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我没太考虑过所谓理想读者的事,我只能说我希望有一本理想的书。一本书出来后,它跟作者和其他人的关系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在一个平台上面对这个小说。对我来说,一本书出来,如果每个看到他的人,都能从中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自己,那就是特别理想的一本书。
原标题:《张忌:我希望能写出一代人的来龙去脉》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