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被重组的眼睛与 ……数字图像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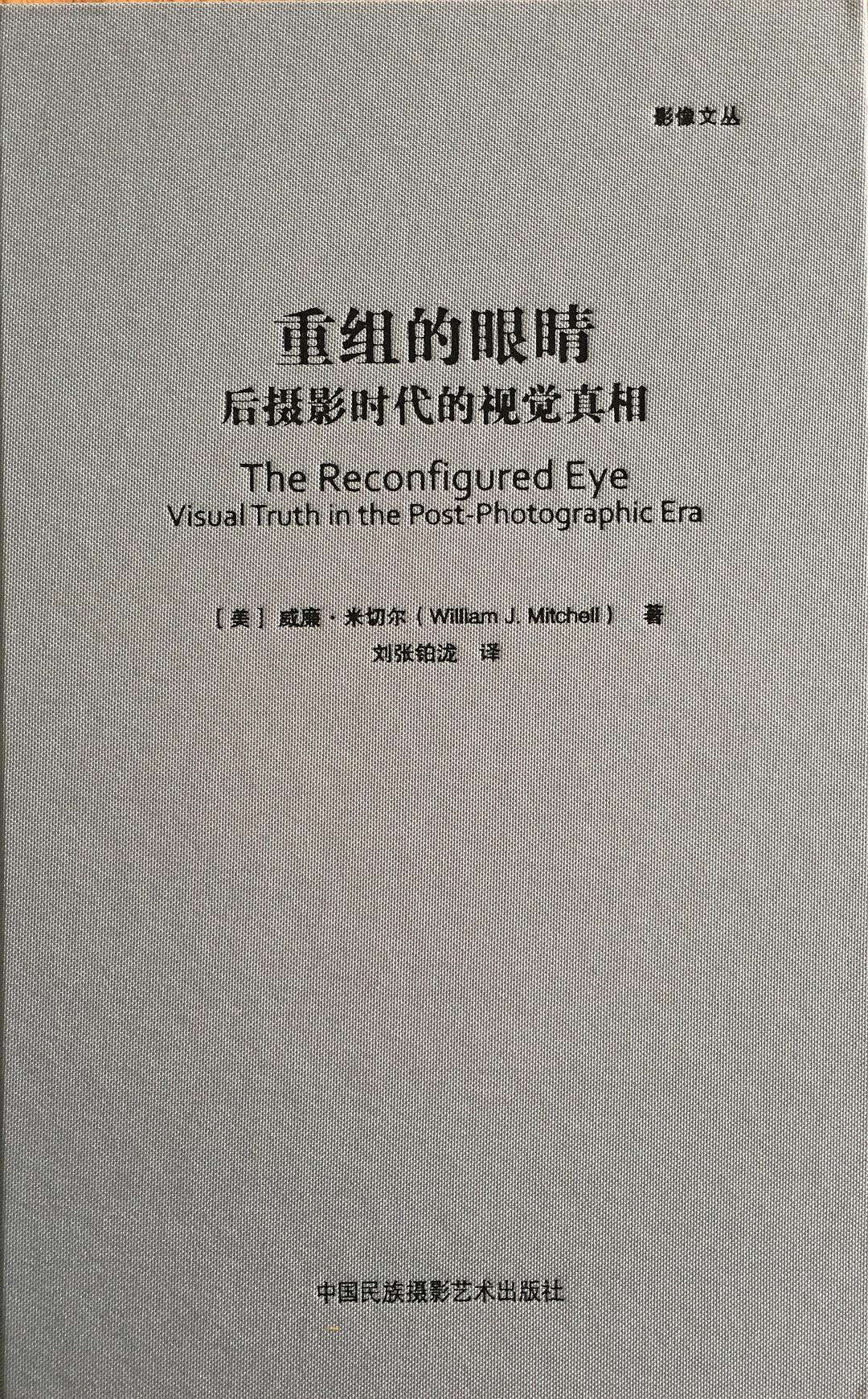
《重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 [美]威廉·米切尔著,刘张铂泷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版,310页,78.00元
威廉·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的《重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原书名The Reconfigured Eye Visual Truth in the Post-Photographic Era,1992;刘张铂泷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从传统影像与数字图像在科学技术上的区别和颠覆性的巨大变化入手,深入分析了后摄影时代的图像生产、传播、消费机制的真实状况与发展前景。作者个人的学术背景是从建筑学、设计学延伸到媒体艺术与科学,曾任麻省理工的建筑学院院长和媒体艺术与科学项目负责人,该书是从他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授的研讨课和设计工作室课程中发展而来的。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和深厚学术功力使这部在三十年前完成和出版的著作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理论性,在今天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学术价值,在我很有限的阅读经验中它更是一部关于数字影像与技术及其视觉机制关系的出色著作,也是我最近思考被遮蔽的眼睛与被压抑的视觉性等问题的重要参考读物。
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被遮蔽的眼睛”更多指向研究者面对图像时产生的认知盲区,其原因主要产生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语境、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偏向等因素。但是,米切尔的“重组的眼睛”把认知盲区前移到数字图像的生产技术之中,“被遮蔽的眼睛”在数字图像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被转化为“重组的眼睛”,因而所产生的不仅仅是面对图像的视觉盲区,而且更是被重组的眼睛所接纳的视觉谎言和认知误区,这就是后摄影时代的视觉性真相。米切尔指出,“数字成像技术的运用愈发广泛地趋于机构化,反过来这种技术也在重新塑造机构、社会实践以及信仰的形成。一个由数字成像系统构成的全球化网络正在悄无声息地把自身建构成去中心主体的重组之眼。”(129页)值得注意的是,“重组的眼睛”是伴随着数字成像技术对研发机构、社会实践和信仰体系的重新塑造而实现的,这与“被遮蔽的眼睛”的形成过程有着不同的维度,但是在主体观看的视觉机制与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关系层面上,具有相通的学理与阐释性。
米切尔显然十分重视分析从传统图像到数字图像变化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状况及其实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发表的《立体镜与立体照片》(The Stereoscope and the Stereograph, 刊登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第3期,1859年6 月)中就把摄影影像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制,把世界看作是可以被摄影掠夺的对象,把照片看作是具有认知作用的可以交换的“国际通货”。(82页)苏珊·桑塔格更是把整个摄影生产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潜在的邪恶同伙: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供应数量庞大的娱乐以便刺激购买力和麻醉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伤口;相机以对大众而言的奇观、对统治者而言的监视对象的手段这两种方式来定义现实,因此“影像的生产亦提供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社会变革被影像变革所取代。消费各式各样的影像和产品的自由被等同于自由本身。把自由的政洽选择收窄为自由经济消费,就需要无限地生产和消费影像”。(83页)她说的虽然是传统影像时代,但是放在今天仍未过时。在数字成像时代则出现了一种崭新、后工业的影像经济机制,整个地球表面成了一个不断展开的奇观和被永远严密监视的对象。任何人再也无法保证影像是视觉真相,甚至不能保证影像是有着确切意义和价值的能指。(84页)在这里可见米切尔的批判性思维是非常精准和深刻的。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图像学的建构性研究,米切尔提供的数字技术分析视角和阐释力量在传统的历史史料学、图像学、艺术史等学科中是难以具备的。在数字技术层面上研究图像本身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变化,这种视角容易被专注于“图史互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所忽视,但是米切尔在该书中不断以娴熟而专业的知识指出认识技术变化的本质对于研究图与史关系的重要意义。比如第五章“数字笔触”中关于数字影像处理技术的系统、详细和通俗的阐释,最后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从传统摄影到数字影像处理与“观看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170页);在接下来的第六、第七、第八章中分别论述了虚拟相机、合成着色、计算机拼贴的原理及其与数字图像的属性、特征等视觉机制和意识形态、伦理规范等外部特征的紧密联系,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数字图像本身的硬核知识。当我们谈论历史图像学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建构和保持其开放性的时候,这些无疑都是坚实的基础。
对于数字图像之诞生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发展,米切尔的认知和预测极为敏感和深刻。例如关于数字成像系统在二十世纪的探索之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与擅长类型学和植物学的人在十八世纪时扮演的角色相似:向人们展示前所未见的奇异事物,开拓潜在可殖民化的地区。(19页)我想他说的十八世纪的类型学应该是指十八世纪中叶的布隆代尔(Jacques-François Blondel)按照功能将建筑进行分类以及十八世纪末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又按照形式将建筑拆解分类所共同开创的现代类型学。至于18世纪的植物学,肯定首先指向林奈(Carolus Linnaeus)在1753年发表的《植物种志》所确立的双名制和以生殖性状(花)作为重要分类根据的贡献,或许他还想到了由英国植物学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于1787年创刊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植物学在十八世纪取得的成就也的确与殖民和帝国主义有联系。
在这里可以看到米切尔的建筑学与科学史的学术背景对他研究数字成像的历史性意义的深刻影响。在1992年该书完成并出版的时候,那时的数字图像还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三十年后的今天根本不可相比,但是他已经极为敏锐地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当电子手段实现了视觉传感器与解读及智能指导之间的连接之后,越来越复杂精密的图形识别和景物分析系统就能够检查生产产品中的缺陷、侦测行李箱中的爆炸物、识别人脸、处理金融支票等等,同时被应用于米歇尔·福柯所讲的监视、规训和惩罚之中——自动识别嫌疑犯罪者、摄像头读取车辆牌照从而追踪人的活动等等。“数字成像系统中的电子小矮人已经变得越来越繁忙;对这些系统获得的数十亿计字节的视觉数据进行自动判读,已成为科学、工业和商业运行的例行程序。”(23页)今天我们的出行所必定要遭遇的扫码、人像识别等等正是三十年前米切尔所讲的“例行程序”。米切尔在注释中提到马修·特克(Mathew Turk )与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面部特征识别》( Eigenfaces for Recognition,刊登于《认知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今天当我们站在人像识别摄像头前的时候,不应忘记那些电子小矮人是如何进入认知神经系统的。同时更要看到,数字成像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真正恐怖是使“屠杀成为了一场电子游戏:死亡在仿效艺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Gulf War)中,关于战争报道的电子游戏效果分析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抱怨“这不是一局任天堂的游戏”。(33页,注释10)
图像的谎言无处不在。“我们开始意识到,从对照片无伤大雅的强化或润色,到潜在地误导甚至对影像内容有意识地欺骗性改动,这中间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将会让我们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自以为隔绝在摄影的客观、科学的话语与合成影像的主观、艺术的话语之间那条界限,似乎已处在瓦解的边缘。”(26页)对数字影像的人为处理背离了已经确立的摄影真相的体制,一个随意挪用摄影的碎片并把它们重组成虚构东西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颠覆性的、不受控制的影像黑客世界。1990年8月《纽约时报》有一篇摄影评论作出这样的预言:“未来,报纸和杂志的读者们很有可能会把新闻图片视为插图,而不是报道,因为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区分未经处理的影像和经过处理的影像。……总之,照片将会显得不再像从前那样真实。”(27页)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了一个邪恶的纪录部门(Records Department),以精良的设备伪造照片,米切尔说现在任何拥有个人电脑的人都可以伪造照片了。很显然,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使用“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我亲眼所见因而相信”等语言来描述对图像的观看。
随着数字影像在世界范围的电子信息经济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交换物品,影像的真实性、原创性概念随之受到挑战,有关版权的伦理和法律的困境也随之出现,许多在前数字时代建立起的传统标准和法律已经不再适用。从信息管治来看,“网络时常跨越法律管辖的界限,很有可能把影像副本置于执法机关和管制机构的职权之外。这就带来了监管的难题。政治审查员们将会发现,他们将越来越难防止煽动性的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影像侵入他们的领地……”(79页)对于传统的新闻摄影来说,数字影像的生产与发表也是颠覆性的:新闻摄影师把数字图像发送到编辑部之后,经过图片编辑、计算机图形技术员等工序的选择、处理叠加在一起,是否会造成图像的欺骗?如何控制证据价值的不断退化?如何保证一张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如果影像存在欺骗或诽谤,谁应该承担最终道德和法律的责任?(81页)这些问题至今难以在理论上和法规上作出明确的阐释和规定,在现实中也只能在个案中视乎各种因素、力量的介入而解决或不了了之。
在论述如何考查照片的真实性的时候,米切尔提到了历史哲学家在不同语境下给予相当关注的程序问题(58页),让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问题回到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米切尔在注释(88页,注释31)中引证的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1967)提供的基础性讨论,以及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检查证据:法官与历史学家》(Checking the Evidence;The Judge and the Historian)的观点。金兹伯格批判了认为历史档案就像一张让人轻信的照片的观点——“一种透明的媒介……一扇打开的窗子:让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现实”。米切尔指出,判断照片的合理性与真实性的能力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话语环境(它引导我们关注的方向,也确立了证据和知识的界线)中建构起来的,与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持有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58页)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之后,一段意大利水泥工厂的视频片段被当成毁坏的核反应堆的视频在美国电视网络上流传;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冰川中发现一具已保存了四千年的木乃伊,一家奥地利报纸发表了一张声称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AT)的木乃伊大脑照片,说可以证明这位史前人曾患有癫痫病,而实际上这只是一张上下颠倒的一个二十世纪男人的胸腔照片。米切尔认为这两个例子都与观众受知识结构的局限有关。
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E. Peary)曾以照片证明他的探险队在1909年4月6日抵达了北极点,但是这些照片却引起争议,质疑者认为它们只展示了探险队员在一片毫无特征的冰丘地形之中,在任何大雪纷飞的野外都能拍出来。国家地理协会分析了照片中的投射阴影的角度,结论是它们确实与皮尔里宣称他拍摄这张照片时北极点的太阳高度相一致。但也有人反驳,认为测量阴影角度时的误差幅度大到足以让它们作为经过检验的证据变得毫无价值。(61页)因此,“有时一个影像中呈现的视觉证据可以用来支持不同的论断,而我们需要判断其中哪一个更为合理。当涉及一个影像的宣传价值时,这个问题就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论”。(62页)米切尔以罗伯特·卡帕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倒下的士兵》为例,但是他要论述的是“照片中的视觉证据似乎与人们相信文字说明是真实可信的完全一致”,所依据和针对的是这张照片1937年在《生活》杂志第二次发表时的文字说明——“罗伯特·卡帕的相机在科尔多瓦前线拍摄到一名西班牙士兵头部中弹倒地的瞬间”。他引用了菲利浦·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在《第一位伤亡者》(The First Casualty)中的说法,认为诸如“一名军人在作战训练中滑倒”这样的文字说明同样也与该照片的视觉证据相一致,指出在评价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时,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它所呈现的视觉证据是否能够支持文字说明的内容,此外还要关注文字说明是否能够更加可信地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相一致,最后他倾向于同意奈特利得出的结论:这张照片“并不像它第一眼看上去那样清晰明了地呈现了事实”。(63页)其实,关于这张最早发表于1936年9月23日出版的法国杂志《视》(Vu)上的题目全称为《忠诚的民兵在死亡的那一刻,木里亚诺山丘,1936年9月5日(Loyalist Militiaman at the Moment of Death, Cerro Muriano, September 5, 1936)》的照片的真实性,目前比较得到认同的研究是指出照片确系伪造(摆拍、非纪实),不是摄于木里亚诺山战役所在地,而是在大约三十英里外的埃斯佩霍。但是米切尔关注的是与照片同时发表的文字说明,这提醒我们应该重视研究摄影照片的发表与传播中的图文语境问题,而今天许多被作为“图史互证”史料的图像在复制传播中时常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初语境。米切尔在88页的注释32 中提到小威廉·埃文斯(William M. Ivins, Jr.)在《印刷品与视觉传达》(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1969) 第38页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在十五世纪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中配有大量名人和豪宅的木版画,用同一块木版制作的图像被冠以不同的标题,使用在不同地方,同一张图像被用来作为十一座不同城镇的插图。在今天使用这张图像的研究者就应该知道图像与标题之间真实关系。
在数字影像时代,一个影像文件可以被无限次地复制,使我们必须抛弃传统的作品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变异体不断变异和扩散的世界。而且传统的影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在数字影像的消费中完全可以产生新的影像文件,因此应该将数字影像视为散播在全球高速网络中的图像信息,可以形成新的具有自身动力和价值的智能结构;数字复制的时代正在接替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75页)第九章“如何用图片来行动”分别从图片的功能、指示与存在、替换、跨时代的合成、伪造与虚构、图片如何影响我们等六个方面论述在传统图像与数字图像在使用与行动中的不同表现和与观看机制的关系,是在前面的技术性论述基础上对图像的使用机制和复杂的可能性的综合性论述。作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伪造照片的人举起的不是一面朝向世界的镜子(mirror),而是狡猾地邀请观察主体踏入的一面镜子(looking glass ),就像爱丽丝走进的那个世界,那里的事物完全不同了——事实与谎言和虚构在那里变得难以区分,无处不在的悖论时时威胁着确定性的地位。为了准确地把握这一切怎么可能如此,我们不仅要考察照片和伪照片(pseudo-photographs)是如何生产的,还要考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它们的潜在用途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们是怎样被挪用和交换的,它们怎样与文字还有其他图片相结合,在叙事中发挥作用,它们又是怎样具有让人信以为真或激起人的欲望的效果。”(267-268页)
读到最后,发现全书最后一章“墙上的影子”虽然只有几百字,却极为概括地表述了何谓“重组的眼睛”和“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我们曾天真地相信摄影,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数字成像的出现不可挽回地颠覆了传统摄影似乎有着牢不可破的证据价值的属性,逼迫我们在解读影像时保持更为谨慎警惕的态度,我们必须再次面对本体论上想象和真实之间无法根除的脆弱区别,让我们直面言语意义固有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所谓“墙上的影子”就是在柏拉图洞穴中的墙上闪烁不定的影子,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意义,或是保证它们的真实性。(309页)实际上,作者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是:数字技术的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重组了人类的眼睛和视觉机制?在数字影像主导的后摄影时代,图像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视觉真相是否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彻底消失?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图史互证”研究的基础性研究,作为史料的图像的生产技术必然制约着观看图像的眼睛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图像分析机制,这是一片主动前移的和更具基础性质的研究地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