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汪晖:“横向的”二十世纪的政治时刻(下)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用两句话概括了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之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访谈的下半部分,汪晖教授首先讨论了鲁迅及其老师章太炎与“二十世纪”的关系,继而分析了中国的“二十世纪”与世界史的关系,以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关系。

澎湃新闻:今年是章太炎和鲁迅逝世八十周年。您能分别谈谈他们与“二十世纪”的关系吗?
汪晖:章太炎和鲁迅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和政治历史的各个领域,他们是现代中国体现“二十世纪”精神的象征性人物,并且,他们体现“二十世纪”精神的方式是极其独特的。过去这些年讲康有为讲得比较多,章太炎讲得比较少。客观地讲,章太炎的东西比较难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技术上难度比较大。而章太炎的思想里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但充满紧张和悖论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他是激烈的排满主义者,强烈要求把中国理解成一个民族,虽然他也知道民族本身带有政治和文化的内涵。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要和民众、“民”的观点(引车卖浆者流、普普通通的人民),和他们的力量的挖掘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又对整个现代世界的基本的逻辑,尤其是资本主义逻辑给予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并且还试图给出一些原理性的说法,这是他最独特的部分。他借鉴了诸子学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庄子和佛学,又借鉴了德国哲学思想、印度的思想,综合成为一个针对现代的批判性思考,如果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个肯定性的乌托邦著作,章太炎的一些理论著述可以称之为“否定的乌托邦”或者“否定的公理观”。他写了《四惑论》《五无论》,对当时的“进化”、“公理”、“物质”、“自然”都给予激烈的批判。章太炎所批判的对象其实是构筑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文明等级论的主要内容,但同时他又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因此,我们要追问,怎么解释他的民族主义和他的“现代性批判”(包括他对工业、政党、议会的批判)之间的关系。

章太炎在1910年前后写了《齐物论释》,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哲学阐述。他关于破除名相,关于语言和现实、命名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今天依然有启发。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他是最早从基本原理的层面,对这个进程本身的逻辑展开批判和反思的人物。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的再解释本身也很有意义,他的《四惑论》《五无论》并没有妨碍他以非常深刻的方式介入对中国传统的理解。
如果和周边地区做一下比较的话,比如在日本,可以找到福泽谕吉和严复的对应性,但很难找到章太炎这样的人物,鲁迅也同样如此。鲁迅的思想深受章太炎思想的影响,我这两年讲《故事新编》就在重新讨论这些问题。《故事新编》讲上古,涉及诸子学,其中鲁迅对墨子、老子、孔子、庄子这几位人物的解释都有章太炎的影响。当然鲁迅和章太炎并不完全一样,鲁迅工作的时期是在“五四”和三十年代,尤其三十年代出现了左翼,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所以鲁迅是在另外的语境中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鲁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得很多了,总之他们两位的确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批判性的头脑(所谓critical mind),他们在所有领域里都有贡献,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思想遗产。

澎湃新闻:把二十世纪作为革命的世纪,无疑能够解释中国、苏联,但对资本主义阵营,对美国、法国、德国,它们的二十世纪似乎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世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六十年代”,但未必有“二十世纪”。那么中国的“短二十世纪”是如何与世界史发生联系的呢?中国的“短二十世纪”是在世界史的内部,它符合历史的方向,要终结之前的世界史,还是说,它在世界史的外部,只是某种例外?如果中国的“二十世纪”没有终结,会不会有改变世界史的潜力?
汪晖:二十世纪发生这些事不存在外部问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不只是涉及两个国家的问题,它们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这两场革命使得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规范意义和垄断性被打破了。欧洲六十年代的运动,当然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无论他们对苏联如何进行批判,但前提是苏联发生了革命,更不要说中国革命还在试图寻找突破,从而给他们启发。尽管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幻觉,可是这些事情相互之间的关系只能放在同一个脉络下才能理解。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对这两场革命中发生的各种悲剧的反思。反思和批判都是必要的,但从哪里出发来反思,从哪里出发来批判?是以欧洲的十九世纪为规范来批判二十世纪吗?或者,是以传统模式来贬斥这个时代吗?“二十世纪”作为“异物”是对十九世纪的既定规范的扬弃,后者不能自洽了,不能不被挑战性地接受了。比如刚才提到的二十世纪的“政治”这个范畴,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的思想里,“政治”也试图超越国家范畴在所有领域里展开。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创新,我仍然给予一个非常高、非常正面的评价,尽管如今从传统的角度围绕五四运动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
在今天不存在简单的例外性。中国对世界的变化的影响,到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晰,还要再看以后的变迁。可能问题会很多,不过可以基本地设想,再过几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会怎样,恐怕现在的这些争论都该结束了,需要有新的争论出来。
澎湃新闻:“二十世纪”终结了。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有一个著名的开头:“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您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的序言中也写道:“九十年代”“看起来与‘漫长的十九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二十世纪’相距更加遥远”。那您怎么看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呢?这是“十九世纪”的功劳还是“二十世纪”的功劳?
汪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说“变成了一个世界”,是说原来在资本主义之外设想的、与资本主义体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类型终结了。今天世界的基本条件、基本机理是全球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没有国家和社会可以例外,但是中国的成就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此,今天中国的性质也同样无法简单归类。
中国的国家自主地位、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准、社会运行当中其他条件等等,都是在二十世纪获得的。中国革命有双重性,它要完成的任务并不都是“二十世纪”的任务,还包含了“十九世纪”的使命,现代化、工业化、国家建设这些任务都是十九世纪就确定了的,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在我看来,保留“中国革命”和“短二十世纪”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重叠和有所区分是必要的。“短二十世纪”意味着一些更激进的方面,可以说是由十九世纪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反现代运动发展而来,并将这个运动从资本主义的“内线作战”模式转化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外线作战”模式;但“中国革命”则要处理所有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了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计划。没有所谓的现代化过程很难设想“中国革命”,但反过来说今天还要讲“短二十世纪”,因为“短二十世纪”同时包含了对这个过程的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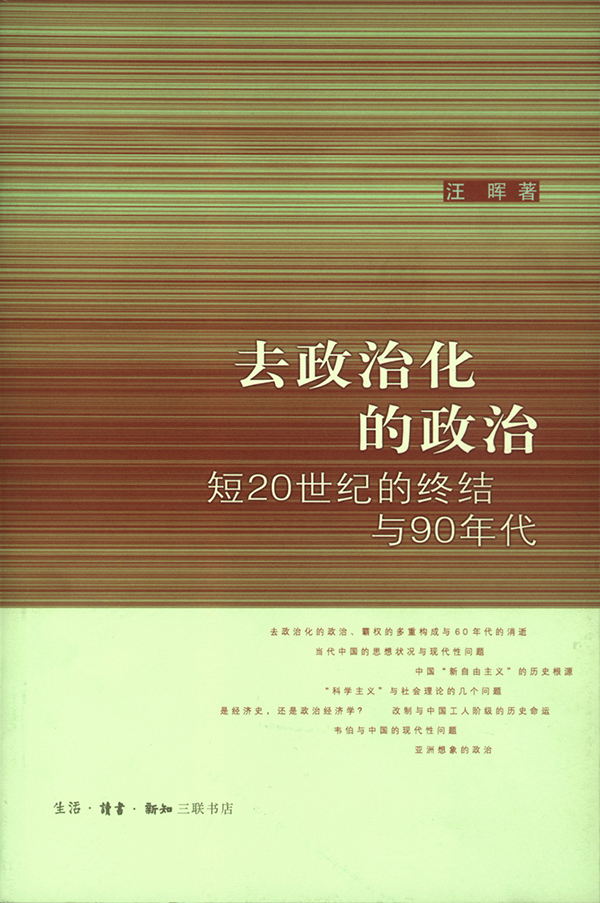
我们讲“去政治化”,讲“短二十世纪”的终结,意味着原有的范式再度成为了支配性的范式。如果经济逻辑或金钱逻辑可以渗入政党、国家、教育机构和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迫使人们服从其软的或硬的逻辑,重新政治化就是必要的任务。二十世纪主要依靠政治的能量对这个范式和过程进行促进、限制和改造,“改造”成为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政治话语。其实过去许多语词是有分寸的,例如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主要的看法并没有说否定、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在实践中这个分寸未必掌握得当。顾准、孙冶方在1950年代末期对价值、价值规律、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讨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运用、发展和限制价值规律或资产阶级法权。运用、发展和限制就是政治的过程,让它存在,不但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还要发展它,但同时要限制它,这就是两重的逻辑。这里的核心是分寸,而不是简单地肯定和否定,即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和发展这种权利,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限制其逻辑。相关的辩论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在苏联和中国展开(社会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有百万富翁,百万富翁等不等同于资本家,这些会不会再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时候会教条化、僵化,又由于这种教条化和僵化,以致将辩论转化为简单批判,但克服僵化、教条化的方式不正是展开理论的论战吗?毛泽东最好地总结过中国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即他认为革命有两个主要的内部敌人,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经验主义,而这两者是不能分开来叙述的。为什么?因为教条主义把能动的政治教条化,使它失去政治性,是去政治化;经验主义认识不到今天的这场能动的实验是前所未有的创新,认为可以延续旧的经验以延续政治,同样也是去政治化的。所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无法把握二十世纪的特征,这两个错误都是革命政治中的去政治化的症候,是方法上的问题。
我们总结二十世纪的教训,特别是它的悲剧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外部的原因,比如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入侵,各种旧势力的攻击——现在不少人一边讲人权,一边讲民国热,竟不觉得混乱?还有一些悲剧是必须完成十九世纪的使命所致:十九世纪的现代化必然会导致分化,革命政治需要对它限制,需要进行自我否定。而就革命政治的内部而言,由于其丰富性、广泛性在这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它也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另外一面。二十世纪的政治和实验不能从历史里自然地衍生出来,需要通过能动的创造,但这又不是凭空创造,不是乌托邦主义。这是个行动的世纪,是最具有行动力的时代,是想到了就要去做,投身实践,从现实中创造发掘未来,是讲究效果与动机的统一的时代,所以是行动主义。但在投入现实寻找可能性的过程中,的确有可能“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苏共的、自己原来革命本本上的一些教条,也有可能凭着经验,过去怎么做现在还这么做,而意识不到现实的极速变化,意识不到现实需要被再理解、再发掘。对革命的再思考,也需要从动机与效果两个方面展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是内在于革命世界观的检验视角。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忽视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新颖性,它们是革命政治内部的两种去政治化路径。尽管前者常常被看成是狂热政治,继而被误认为是政治化,而后者则被看作是切合实际的——其实,经验主义未必切合实际。毛泽东立足于二十世纪政治的能动性做出了这两点概括,我想,不断的行动主义的实践才是二十世纪政治过程的重要方向,也是判断二十一世纪能否继承这一遗产的尺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