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正经大学者谈但丁有没有比丹·布朗的小说更烧脑?
【编者按】10月28日,改编自丹•布朗小说《地狱》的电影《但丁密码》上映。在原著小说中,丹•布朗运用了大量但丁《神曲》的典故来架构线索,可谓是情节中的烧脑担当。
而作为最正统的“西方正典”,但丁的《神曲》一直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核心文本。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史诗》一书中对但丁和他的《神曲》有专章讨论,一起来感受下这究竟是可以当做电影的扫盲贴,还是更劲爆的烧脑。
本文摘自书中《但丁•阿利基埃里》一章,由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但丁•阿利基埃里的生平足以当作一首激宕的诗歌,在《地狱篇》和《炼狱篇》之间,它更接近后者,而与《天堂篇》相距甚远。至今所见的但丁传记多半短绌,不足传写他的天才,唯有乔万尼•薄伽丘所撰第一部传记例外。朱塞佩•马佐塔允洽地称其为“近乎但丁所著《新生》(La Vita Nuova)的自我意识的虚构作品,在想象上呼应但丁在其著作之中练达的自我戏剧化”。我们无须为此惊讶;一如莎士比亚,但丁的思想和想象力何其瑰大,单个传记作家、学者、批评家往往只能观览他那无可比拟的全景的一个角落。向学生推荐莎士比亚传记之时,我总是选安东尼•伯吉斯的《莫可比拟太阳》,一部颇有乔伊斯风格的小说,以莎士比亚为第一人称叙述者。
高贵的但丁自视为先知,至少堪可追配以赛亚或耶利米。我们可以揣想,莎士比亚没有类似的自许,哈姆雷特、福斯塔夫、李尔王的创造者与杰弗里•乔叟——赦罪僧、巴斯妇的创造者——具有太多相契之处,而乔叟轻訾但丁。一个人须峨然如乔叟,方可嘲讪但丁,况且在乔叟这里,显然也是赞赏胜过分歧。
若要谈论世界历史之中的天才,便不能不说但丁,因为在所有的语言天才当中,唯有莎士比亚的丰赡赛过但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莎士比亚重新打造了英语:他使用了二万一千个单词,其中一千八百个是他自造,信手翻开一份报纸,无处不见莎士比亚式的词汇,并且通常是无意间使用的。然而莎士比亚的英语承袭自乔叟,以及新教《圣经》的主要翻译家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设若莎士比亚不曾撰写一字,英语也会照样流传下来,一如我们而今所见的模样,然而但丁的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意大利民族语言,泰半归功于但丁。他是民族诗人,正如在任何说英语的地方,莎士比亚是民族诗人,在任何德语主宰的地方,歌德是民族诗人。没有哪位法语诗人赋有如此无可置疑的卓荦地位,连拉辛或维克多•雨果都不能够,也没有哪位西班牙语诗人如塞万提斯一般占据中心地位。然而但丁虽在本质上构筑了意大利文学,却决计不会自视为托斯卡纳人,更不是意大利人。他是佛罗伦萨人,至死不渝的佛罗伦萨人,在世五十六年,而最后十九年羁旅外省。
对于但丁的读者来说,有几个日期至关重要,首先是1290年6月8日,但丁挚爱的理想或者理想化的挚爱贝阿特丽切逝世,诗人时年二十五。据但丁自述,他对贝阿特丽切的爱慕如同我们所谓柏拉图式恋爱,只是任何关于但丁的事,都只能称作但丁式,包括他的天主教信仰(Catholicism)。他将1300年复活节设为《神曲》中启程的虚构日期,于1314年写成第一部并且是最恶名昭著的《地狱篇》。在生命的余下七年里,他的气运非凡,有幸赋就《炼狱篇》和《天堂篇》,从而得以在逝世近一年前完成这部宏大的诗歌。

莎士比亚终年五十二岁,但我们未尝因此而有所失,因为他在逝世前三年便已停止写作。然而我们会觉得,倘若但丁再活四分之一世纪,以逮及八十一岁这个“完美”年纪——九乘以九,出自他自创的完全不可破译的数字命理学期望——会创造更多文学成就。但丁在《飨宴》(Convivio,第四卷,24)告诉我们,生年在第七十年终止,但是倘若我们仍然存活,便有可能臻及崇高:
从而关于柏拉图——我们可以肯定他禀赋绝佳的天性(既在他的天性之内,也是由于苏格拉底初见他时为他摹状的面相特征),并且活到八十一岁,正如图莱在《论老年》之中所述。我相信设若基督未尝有十字架受难,遵照生命的天性,得以尽其天年,八十一岁之时,他会从肉身变作永生。
但丁期待八十一岁之时发生什么变化?他会在此生再见到贝阿特丽切这位“九”姑?乔治•桑塔耶纳在贝阿特丽切身上看到一种基督教的柏拉图化。E. R. 库尔齐乌斯将她看作但丁的私人和诗歌的灵知(gnosis)的核心。她和基督年及八十一岁之时原应经历的变容之间具有重要关联,因为依据她的情人所撰《新生》记载,她的死亡过程,就是九次完成九这个完美数字。在二十五岁,她从肉身化作不朽之身。《神曲》通篇,但丁又是暗示又是直白地告诉我们,他就是真理。苏菲主义的殉道者哈拉智(Hallaj)因宣称自己是真理而死,虽说美国人的基督教(以其种种形式)之中,此类宣告十分寻常。我与持异见的摩门教徒、浸礼会诸教派,以及很多五旬节教派交谈,这些人皆率直地向我保证,他们是真理。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皆不会自称是真理。贝阿特丽切若不是真理,《神曲》就行不通,只是反过来说,若没有但丁,无人会知道曾有一个贝阿特丽切。我以为这一点再夸张也不为过,而且我从来不能理解,但丁何以克服这个可能性:他私人的贝阿特丽切神话是一种异端,丝毫不亚于神格之内的女性原则或者索菲亚这个诺斯替神话。现今,很多有识之士视但丁为天主教义的界定标准。术士西门(Simon Magus)在商埠推罗(Tyre)一家娼寮发现他的海伦纳,宣称她既是特洛伊的海伦,也是堕落的索菲亚,或上帝的智慧。撒马利亚人西门向来被基督教徒诛伐,实是第一个浮士德,勇悍果敢、极富想象,如今普遍地被看作施伪术的。但丁在一位佛罗伦萨年轻女子身上发现未堕落的上帝的智慧,并且将她奉若神明,奉上天界。一如术士耶稣,术士西门属于口头传统,而但丁——除莎士比亚之外——是所有西方历史和文化所宗正的大诗人。然而我们不该忘记,但丁师心自任,并不逊于西门。但丁僭夺诗歌权威,自立为西方文化之枢。
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中心地位何其殊异!但丁强要我们接受他的个性;而莎士比亚因其窅渺的超然,即便在十四行诗中,也不免躲闪藏遮。在《新生》中,但丁把我们淹没在他对一位几乎不相识的年轻女子的非凡爱慕之中。他们九岁时初见,只是这个“九”警戒我们不可照字面意义理解这个故事。九年之后,贝阿特丽切初次与他说话,街上相遇之时一声正式的问候。此后另有一二次问候,他为掩饰真情而极富诗人气质地向另一位女士示爱之后,她有一次冷脸待他,在一次聚会上,贝阿特丽切与旁人凑趣,取笑她这位苦情的仰慕者——这似乎是他们之间的全部交往。关于这段微薄的事实,最好的评注出自阿根廷寓言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说,“我们肯定这是一桩不幸的、迷信的爱”,得不到贝阿特丽切的回应。
我们可以谈论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中年轻俊美的贵公子那“不幸、迷信的爱”,但在同一组诗章中,莎士比亚堕入黑暗女士的地府,至于这一段爱恋,我们须用其他词汇描述。以新柏拉图式一词形容但丁对贝阿特丽切的爱慕,实在相当不敷,可是我们又能如何定义那样一种爱?热衷于自己所禀赋的天才、自己所创作的缪斯,在任何旁人身上,这样一种激情堪为阴暗的自我偶像崇拜,而在这位中心人物身上,却不是。贝阿特丽切这个神话或角色与但丁的毕生事业相融合;在一种关键意义上,她就是《神曲》,你若置身于这部诗歌之外,就不可能理解她。然而但丁虽将她表现为真理,你却切不可误把她当作基督,基督是道、真理、光。
研究但丁的学术著作非常有益于理解《神曲》的絮繁之处,但无助于我理解贝阿特丽切。相比《神曲》,她在《新生》中的基督论倾向更显著,虽则她时或使我联想起诺斯替主义者所谓“天使基督”(Angel Christ),因为她打破人类与天使之间的等差。神人交融可能是或也可能不是异端观念,这完全取决于如何表现这样一种交融。在我的印象里,但丁的识野不是奥古斯丁式或托马斯派,然而虽有赫尔墨斯神秘主义倾向,却又不是赫尔墨斯派信徒。但丁并非要与神话等同,相反地,他殚力要神话与他等同。人在上帝面前不等于上帝在人面前,尤其是在贝阿特丽切面前。
也许这话听来古怪,因为但丁不是威廉•布莱克,敦促我们仅崇拜他所谓的人形神圣。然而但丁早年便说过贝阿特丽切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赋予整座佛罗伦萨城,不只是属于但丁独个人,虽然他是唯一称颂这个奇迹的人。但丁后来斥责他的挚友兼诗歌导师圭多•卡瓦尔康蒂未曾一道称颂,然而但丁之于卡瓦尔康蒂的关系,便如莎士比亚之于克里斯托弗•马洛,笼罩着影响焦虑的阴影。但丁暗示说,如果卡瓦尔康蒂认可贝阿特丽切,他便早已得了拯救,我们会相信这句话吗?一种同享的原创性还会是原创的吗?

作为读者,我们大可将但丁传闻中的神学留给他的考据家,但是你若不先接受他的贝阿特丽切,就读不了但丁。在但丁这里,她无疑是上帝的化身,他拒不将其看作与化身相竞逐的存在。他深执她是他所拥有的幸福,且先不论那幸福是什么;没有她,他就找不到他的救赎之途。然而但丁不是被诅咒或被拯救的浮士德,也不是死于真理之手的哈姆雷特。但丁一心营求的是胜利,是全然辩护,是实现了的预言。但丁以孺慕之爱,将他的“父亲”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 )和维吉尔奉上超验地位,而后坚定地将他们掼在一边。他承认他在诗歌上的“伯仲手足”(至于卡瓦尔康蒂,则是颇阴沉地认可之),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旅伴。在《神曲》之中,他是否说服我们相信,贝阿特丽切不只是他个人的天才创造?但丁既在他的诗里也在诗外,正如贝阿特丽切在《新生》中也是一样。她是否有一种真实性,使旁人也能祈求于她?
莎士比亚最瑰大的人物能够走出戏剧,活在我们构想他们的意识之中。贝阿特丽切走得出来吗?但丁的个性如斯鸿大,再容不得任何旁人;走向永恒的朝圣旅途占据整个空间。虽说在其他任何诗人那里,这是诗歌的缺憾,而在但丁这里,这根本算不得缺憾。在但丁这里,这是诗歌力量,依仗绝对的原创性而生机喷薄,一种不会因无休无尽的解读而走味的盎然生意。
奥古斯丁反对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y)——坚执自信和骄傲不足以逮及上帝。引导和协助是必要的,并且这两者只能来自上帝。还有比但丁更张狂的傲慢,比但丁更固执的自信么?他将自己刻画为朝圣者,借重引导、抚慰、协助,但是作为诗人,他不是要改变信仰的基督教徒,而是得到召唤的先知。他果真要费心说服我们相信谦卑么?实际上,但丁的英雄气概——精神的、形而上的、想象的——使这位诗人成为如同贝阿特丽切的奇迹。
幸运的是,他把自己表现为一种个性,而不是奇迹。我们对他如此熟悉——在本质上,而不只是轮廓概略——从而能够接受他在《神曲》中那些得来不易的转变。确实,在《神曲》里,唯有他能够改变,因为其他任何人都已定形,尽管《炼狱篇》的居民须经历锤炼的过程。《神曲》里每个人皆生动得悖妄,而就类型而言,他们不会再有变化。由于但丁差遣给他们说的话或做的事,从而令他们不能再有所改变。这使得彻底的启示成为可能:但丁替我们对他们下了定论,无可置疑的定论,并且总能令人叹异。接受了最后的审判之后,你能否仍然拥有个性,这是一个漂亮的问题。
作为但丁的创造,贝阿特丽切的个性极其单薄,因为出世在佛洛伦萨之前,她显然有作天使的前世。但丁在《新生》中向我们展示的她姝若天人,也有着严厉的一面,在《神曲》之中更加彰显她待他的严厉姿态,虽只是为修辞起见。在真实生活里,她颇漠视这位理想化情人,而死后却无比关心他的救赎,实在是骤变。她是但丁的天才或更好的天使,这是明白无疑的,从而便使得这一突变容易为人接受。雷尔提(Laertes)恻然叹息,被弃的奥菲利娅死后会成为守护天使,料想大抵加入了霍拉旭最后所祈告的那班天使当中,我们若用心思量,这颇使人诧异。但丁长久以来都准备着自己的成圣过程,早已开始训练他的贝阿特丽切了。
但丁如斯戛戛独造,迄今没有哪位作家能够接近,纵使约翰•弥尔顿或列夫•托尔斯泰也不能企及。正如博尔赫斯所说,莎士比亚的遁避技艺高妙,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不是任何人。而但丁就是但丁。无人能通过将但丁历史化而将他开消,抑或仿效他勇悍无畏的自我神化:卡瓦尔康蒂若能长寿,无疑会创作更遒劲雄浑的抒情诗,但他不太可能写出“第三约”这样的书,而《神曲》似乎就是这样的书。莎士比亚的天才这个问题永远超乎我们的理解力,然而但丁的天才是一个答案,而不是一个问题。除了三个世纪后的莎士比亚之外,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诗人在14 世纪20 年代末完竣其独部最伟大的文学艺术著作。若要与《神曲》抗衡,并且在某些方面超越之,你须将莎士比亚三十九部戏剧当中最出色的两打视为单个实体。然而在但丁和莎士比亚之间,实难排序:尝试阅读《炼狱篇》之后再阅读《李尔王》,或者阅读《地狱篇》之后再阅读《麦克白》,会生起一种古怪的不安。这两位最重要的诗人大相扞格,至少这是我的体会:但丁意欲其读者评断贝阿特丽切是他灵魂之中的基督;由于诸种原因,我们很多人可能为此而不自在,但是倘若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里暗示,对于诗人来说,那俊美的年轻贵族(譬如南安普敦,或者其他什么人)是基督的预表,而这位诗人继而撰写《哈姆雷特》和《李尔王》,我们会多么惊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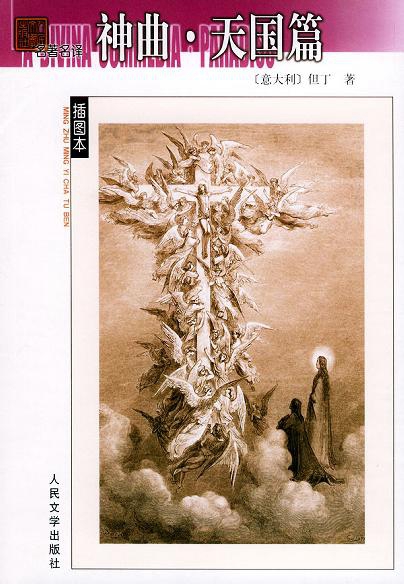
对于能够沉酣于《神曲》原著的读者来说,贝阿特丽切便不是难解之谜,因为意大利批评家研究但丁的路数迥异于英美学者,并且他们对于但丁更为世俗的观念也渗沥下来。我看重詹巴蒂斯塔•维柯的见解,他认为但丁若不是如此该博神学,连荷马也要被这位托斯卡人比下去。但丁与弗洛伊德(以及神秘主义者)一样,认为性爱崇高是可能的,这与他的友人卡瓦尔康蒂相抵啎,后者认为爱是必须经受的一种疾病。但丁把弗兰切斯卡及其情人的保罗判为奸淫而发落到地狱,却因在殊异于(在他眼里)神圣的贝阿特丽切的女人面前淫亵而知名。但丁与莎士比亚意气投合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二人皆能高妙地描摹或他人或自己所遭受的性爱之苦:
然而在这潮湿绿林里燃烧爱的火焰之前
连溪流也会转头爬上山坡,
便似年轻女子心里燃烧的火焰,
为了我,她愿在石头之中沉睡我的生命,
或如野兽食草,却见她的衣衫投下影子。
这节诗出自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翻译的“如石的”(stony )六行六节诗《致昏暗的光》(“To the dim Light”),是但丁的“石头诗”之一,热烈地献给一位冷美人。贝阿特丽切不若莎士比亚风格;而冷美人颇似莎士比亚的风格,并且完全可以成为十四行诗中的黑美人:
损神,耗精,愧煞了浪子风流,
都只为纵欲眠花卧柳,
阴谋,好杀,赌假咒,坏事做到头;
心毒手狠,野蛮粗暴,背信弃义不知羞。
才尝得云雨乐,转眼意趣休。
相比起将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悲剧基督教化这样的企图来,以虔诚信仰研究但丁倒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但是这样的出发点可能比女性主义的敌意——倾向于怀疑但丁将贝阿特丽切理想化的动机——更加有害。但丁赞美贝阿特丽切,赞得轰轰烈烈;而他对于这段单相思的称颂是更棘手的问题,除非我们缅想隐微的童年记忆,自己爱上一个几乎素不相识之人,也许永远没有再见面的人。T. S. 艾略特警敏地揣测,但丁初恋贝阿特丽切之时,必定早于九岁,而数字学的范式确实可能诱导他将这段经验挪到两三年之后。因为不是身为但丁,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利用这么早的异象,但丁的大半成就便是他在其上构筑了伟大。
若说贝阿特丽切的本原是普遍的,那么她在《神曲》之中成为奥义的形象,但丁私人的灵知,因为但丁正是借藉她、通过她来断言知识,而这知识绝不似他的大多注疏家所能允准的那般传统。《地狱篇》永恒的丑名未尝掩盖《炼狱篇》奇辟横肆的文采,并且入情入理地被推崇为首位。令读者感觉艰难无比的是《炼狱篇》,而这困难代表了但丁最不容置疑的天才时刻,它凌跨了想象文学的界限。再没有哪部著作可与《炼狱篇》相提并论,或许安达卢西亚人苏菲•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麦加启示录》(Meccan Revelations)中某些片段尚能比附。阿拉比在麦加遇见他的贝阿特丽切。尼珊姆(Nizam),麦加的索菲亚,如同佛洛伦萨的贝阿特丽切,是上帝现示真身的中心,使伊本•阿拉比改变信仰,转投一种理想化、升华的爱。
年及七十一岁之际,我还没有充分的准备阅读《天堂篇》(身为犹太人,我反正也去不了那里),而我也开始畏惧《地狱篇》,这实在是虽崇高却可怖的著作。我确实时或重读《炼狱篇》,在其令人激赏的《神曲》中篇的译文前言,W. S. 默温以华赡的文辞道尽了我的理由:
在这部诗歌的三篇之中,唯有《炼狱篇》发生在地上,如同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的双脚踩在地面,走过一片沙滩,爬上一座山……抵达山巅,在那里,希望掺和着痛苦,而痛苦将这篇颂歌带入活生生的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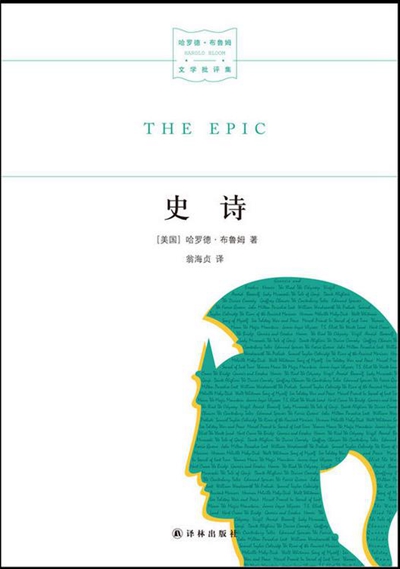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