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都,这个城市可以让我们撒点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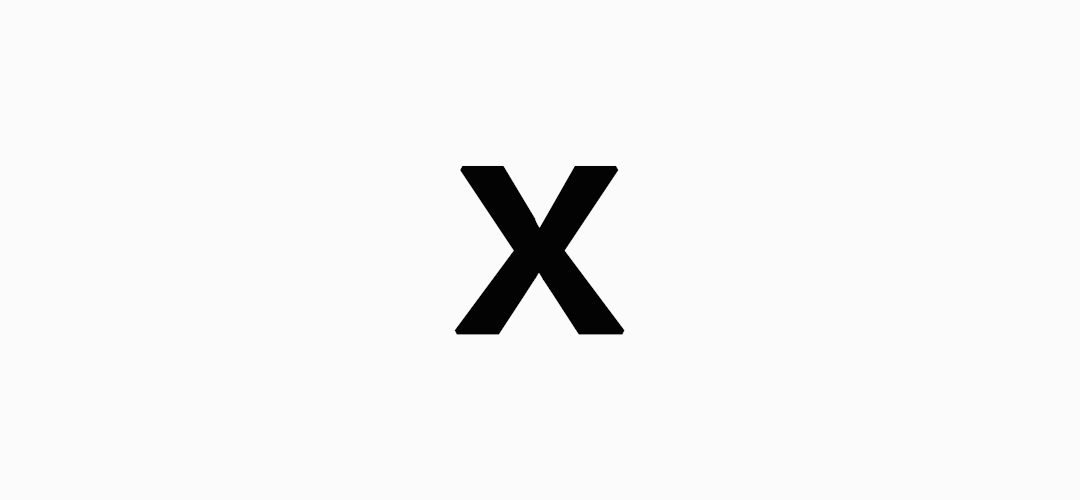

貌似我们都是在世俗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带着点人味与人间的气息生活着,从一开始学习、工作就在既定的知识范畴里,自我被知识和文化包裹着,我们姑且称之为成长。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带着点批判与批判中的觉醒要重建一个自我,才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便是在俗世中行走,知识也变的不一样,味道里也开始带着点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徐浪的节奏是建筑的节奏,有那么点摇滚青年的意味,也有对生活孜孜不倦的热情,在日常设计中,都带有一种“刻骨的深刻”,但外在的他总是给人一种“更为实在的质地”,如同他的设计,过程是一种自我的深刻介入,建筑成为了一种理性思想的实现。
城市记录者合造社的徐浪,将带领我们走进一苇书坊和他经常去吃的成都街头的小海鲜,一面知识,一面俗世生活,他没有把自己界定在某一类建筑里,带我们走进他理解的一种“反归类”的俗世人间。
第一幕
有酒、有故事、一个书店
或许,可以让我们在雪地上撒点野

藏在成都玉林巷子里的独立书店,有着浓烈的八零后文青的味道,随处可见的影展广告,有书、有酒、有故事、有态度。
邵兵(以下简称“邵”):今天带我们去一苇书坊和小海鲜,是怎样计划的?
徐浪(以下简称“徐”):我们先去一苇书坊逛一下,那个书店其实也不是我设计的,是我一个哥们儿阿钟(钟梓洵)设计的。但是选择这个空间,是因为我觉得它和人的连接特别近,一苇书坊的老板阿俊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成都“连接”的朋友也挺多,一般请朋友玩都会在那,你上次不是问我吗?在这个城市除了办公室和家,我待的时间最多地方就是一苇书坊。
邵:需要花钱办卡吗?(哈哈)
徐:肯定需要,一个城市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小书店和独立书店,让你很舒服的待着,你老去蹭人家的(哈哈)。
邵:是不太好意思。
徐:不是不好意思,我脸皮很厚,我肯定好意思,我怕它被我蹭没了。

邵:昨天,受你影响我又重新听了一下崔健。
徐:我好久没有听崔健的了,但是每次听都还挺爽的。
邵:你多久没听了?
徐:现在车里放的是我读大五的时候听的歌,好像是2003年还是2004年出来的,我读大五是在2005年,当时我在重庆,也买了这张专辑,当时没觉得有那么好听,当时对崔健的认知只是《花房姑娘》,但现在听这个,真觉得崔健牛X,真的是牛X。
所以,这个可能是你说的符号性的东西,你老是期待他给到你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兴趣和创作状态,其实都是在往高处走的,我当时也只是大五的一个小孩,就觉得崔健应该是那种状态,但其实人家不是,人家早就已经是另一种状态了。
邵:我最早听的就是《假行僧》、《花房姑娘》、《一无所有》,还有《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你内心还是挺摇滚的一个人?
徐:我比较喜欢摇滚。

邵:是很凛冽的一种东西,情绪里还是有点激荡,包括内在的那一部分。比如我们聊到“反归类”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你给自己划定的,或者你会觉得那个不自由?
徐:是有这么一点,不是觉得不自由,应该是没有意识到自由这个事的时候,行为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最开始是困惑,后来找到一个不自由的东西,反而用不自由解释自己被束缚的状态。
邵:我做不到你这种状态,我觉得你还挺纯挚的。别人问我说跟徐浪接触这么多次,他是怎样得一种状态,我会首先觉得你很建筑,骨子里很建筑,我觉得你的人和你的建筑都很建筑。包括“知识”,我们其实在自然的恩赐中都是我们的知识里的一种状态,我们如何来用知识,如何体会知识这件事就会显得很重要了,或者那是一种对待知识的情绪和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你很摇滚,并且,多数建筑师可能也会偏爱摇滚乐。



合造社在邛窑遗址公园里的工作室|2017
徐:我觉得建筑师是喜欢摇滚的,我发现很多建筑师不喜欢Hip-Hop,喜欢摇滚,但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其实在文化上有点同源。上个世纪60年代的整个摇滚是一个顶峰时期,跟当时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普遍存在一种先锋意识,60年代的建筑学也挺先锋的。我是觉得60年代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是最后一个先锋的时代,也许,今后还会有,就是那种思想上的激进、先锋。
邵:思想的淬炼,在每个时期里都会有激荡,文明是这样一个动态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定点的东西,是一个段落式的。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了的,有时候我们会回看多少千年之前的状态,但是我们何尝不是在多少千年之内。



波尔坦斯基心跳博物馆|2018
邵:上次我们说起知识这件事,“反归类”和知识放在一起这件事有意思,知识似乎也带有了一种态度,你是只听崔健还是?
徐:没有,我这两年突然听崔健,是因为互联网会根据你的喜好来推荐,突然推到了崔健的《超越那一天》,刚好是这个专辑,我突然想起之前有这个专辑,整个专辑又重新听了一遍。
邵:昨天晚上发了朋友圈以后,我还认真把歌词看了一遍。我发现他还是有很多爱的东西在里面的,但他不是极其个人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有温暖和爱的东西,大家听,可能是听崔健的思想。
你知道为什么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对你公司发生火灾这件事这么好奇吗?因为你给我说的时候,你把火灾这件事说的好像日常吃饭一样平常,我还在想你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状态?
徐:我也在想,为什么当时的状态没有觉得特别丧,或者特别不爽,也是因为这个事本身比较大,就比如说你在平时生活里面丢了一台电脑,或者被偷了你会很沮丧很长时间,但是这个事它很大,再加上它是在一个大的事里面,又没有那么大。当时是晚上一点钟,我说回办公室一趟,就发现起火了,就马上报警了,如果我没有晚上一点钟回去取车的话,可能上下楼全都烧起来了,那个事比起我们自己遭火灾大多了,所以,当时还觉得很庆幸、很幸运。

工作室因火灾烧残的书放在门口展台以提醒大家
邵 :你跟阿俊是怎么认识的?
徐:我们认识也是很奇妙,是一个朋友介绍的,那时候阿俊到我住的地方找我,晚上我们一块去吃了一个串串,一块喝酒,聊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就认识了。
邵:我第一见到你,你还说了一个关键词:小舍得。感觉头一次有一个建筑师跑过来跟你说,有没有看过电视剧《小舍得》这件事,不聊建筑而说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徐:《小舍得》可能就是前几个月看的,我姑娘现在一岁九个月,虽然没有经历那个状态,但是看到《小舍得》里面所有表达的那些事,就觉得太真实了,他完全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故事,而且马上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是因为太有代表性了,能很真切的感受到社会的声音就在你的耳边。
邵:你比较关注孩子上学或者家庭,或者现在孩子们的一种状态。
徐:再加上我们最近几个项目又跟儿童有点关系,也是关于建筑的,幼儿园这些项目。我发现之前去理解建筑这个事,我在有小孩之前也没这么觉得,现在有小孩之后再回想我那时候的状态,我觉得那时候是做不了幼儿园的,我不会理解那种状态,没有那种生活经验,没有那种社会的痛点的感知,当时单身汉的状态,可能考虑的就是建筑、形式、空间状态这些。后来发现那些东西可能也很重要,但在一个社会话题面前,你做的这个事情,就要去深入到一个社会话题、社会事件里面去,并且还要去解决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之前,我不会觉得建筑学这个学科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感觉它是一个关于纯粹的知识、纯粹的创造,也觉得建筑是一个拓展知识边界的学科。但现在我会觉得这个学科其实和社会是密切相关的。


兴隆湖儿童艺术中心的竞赛方案|2020
邵:前面戴眼镜的是阿俊吗?
徐:哪里?噢,对,坐在外面的这个。
邵:他有点知识分子的感觉,好像学霸都长这样(哈哈)。

邵:俊哥好!邵兵,一直听你的名字听了好久。
阿俊(一苇书坊主理人,以下简称“俊”):你好你好!你们不是三点到的吗?
徐:我是三点从办公室出发然后到这。
俊:好的(哈哈),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日常状态。
邵:“一苇书坊”这个字体是怎么来的?
俊:这是当时设计师选的字体。我们当时让徐浪的同学阿钟(钟梓洵)来设计这个书店,最早是找的徐浪,但当时他正在做心跳博物馆那个项目,没时间做这个,他就推荐了阿钟。

邵:这里的书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俊:书店核心就是选书,一苇书坊除了有这个核心,还有另外一个核心,就是选啤酒。

邵:你和徐浪是怎么认识的?
俊: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说,书店开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两年多了,最早知道他是在当时一个建筑类的微信群里。当时我还在做文旅,他也会偶尔会在群里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比较有意思,包括他当时那个黑色的头像。
我们在线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咖啡馆,一个朋友组织的沙龙《城看》,也是在聊一个关于社区营造的话题。那天下雨,活动结束了以后还有对谈交流环节,但没多久大家就散场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并没有互相认识。后来,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嘉茂约我们吃火锅,说他以前的一个领导,之前一起共事过的同事想在明月村做民宿,我们也就认识了。当天,就跑到他家里喝酒,我们聊到半夜两点多,因为太困了我们就提前散场了,后来就 经常一起约着聊天、喝酒。

邵:你觉得徐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俊:因为我以往接触的建筑师,给我的印象大多是那种传统的理工男形象,觉得他们状态其实跟我接触的IT男有点像,大部分就是画图、去工地、汇报方案等等,没有自己的生活。但浪哥他关注当代艺术的东西很多,在他家里面能看到他收藏的很多作品,包括我们后来去他家看球,2018年世界杯期间我们经常去,看球的也没有他的同行,大多数是艺术家。通过他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玩的艺术家,我觉得他不像我印象里的建筑师。
邵:不像传统中理解的建筑师的状态。
俊:因为他关注人文方面的东西特别多。我是觉得建筑师也好,艺术家也好,都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或者说社会价值存在,他不是单纯的去做一个作品,他与这个时代,与当下的人有很强的关联,浪哥当时做的夯土房子在艺术公园里的状态就特别好。

邵:我那天问他,我说成都有一个地方是你一直会去的,他想了半天,突然说:一苇书坊,一定是要去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会想去很多地方,但就这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能不能把这个阐述一下?
徐:说明两个问题,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中枢。
邵:是你的中枢还是?
徐:不,是一类人的中枢,大家可能都会约到这来,你的交友范围可能还是这一类的。
邵:一边是人文,一边是知识,中间有酒、有咖啡,很少会在书店里面有一个酒的状态。
俊:主要是为了满足我,第一是我个人爱喝酒,第二是卖酒比卖书赚钱,单纯靠卖书利润很低,还有咖啡。也是想简单一点,让大家在这里可以自在一点,其实我现在挺怕做得特别精致,很网红的空间。
邵:有点日常的、粗糙的东西要留下。对于知识和“反归类”这件事,是说不管是哪一类?还是哪一种行当?都可能要冷静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徐:你觉得知识和冷静有关系吗?

邵:我是在想,你是否在你心里有明显的有界限,就是哪一类你是不去的?这个地方常来,一定是跟你自己心灵和内在有一种勾连的状态,那么多地方你都没有去,为什么只选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在“自我”之外。
徐:我是一个不想自己被归类,但其实自己是最喜欢去归类的,我已经归类了。
邵: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一苇书坊这一类了。
徐:其实不是,来一苇书坊原因我觉得还是人的连接。
邵:那么多人,你朋友不少,为什么单单是这里?
徐:就是舒服,自在,一说喝酒,一说去哪里聚一下,有这么几个人,我们就去一苇书坊,直觉里马上冒出来,就是这个书店的气场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窗口。
邵:你总结过吗?来的频次多会是因为什么状况?
徐:要么因为不忙,要么就是碰到一个喜欢来一苇书坊的朋友,或者喜欢来一苇书坊的甲方。
邵:是不是所有甲方都来过?
徐:第一次是带赖总(赖国平)来一苇书坊,也会和赖总经常约着来一苇书坊喝点酒。因为甲方状态不一样,赖总是挺享受生活的,感觉挺享受那种生活的状态,我感觉我又被他带动了。
邵:我觉得一苇书坊这个位置很好。
俊:东、西、南、北过来都比较方便。
邵:就是城市中的一个日常,也并没有要在哪做一个很高门槛的书店,或者一定要很漂亮,现在很多书店是热闹的、精致、打卡的,把知识标榜成为一种时尚和美的对象。真正的书店可能就是这样,在街头买本书,坐着读一会书。

徐:周边是玉林路,这一片还挺有趣的,我挺喜欢这种状态。
邵:这个城市很宽容。
徐:城市的宽容度,就不用走得太近。
邵:你当时选地方选了多久?
俊:没有刻意选地方,刚好坐在咖啡门口,有一个店面在出租,然后我就过来看一下,上面写着“房屋出租”,没有转让费,那时候九点多快十点,我给房东打电话,接了以后说:“你做书店的话,我们还是蛮欢迎的”。当时知道装修成本,还有前期铺货,三个月就弄完了,时间比较紧张。
邵:你转行跨度还是蛮大的?
俊:不算转行,本来你就喜欢这样的空间。希望做一些活动,当时我们想做这个书店,更多目的是想把它做成一个文化空间,而不单纯是卖书,更多是希望大家能够到线下来,做一些沙龙也好,平时读书会也好,能够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在里面。
邵:读书会是常态吗?
俊:今年才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是一个经济学类别的。线下沙龙会请学者、作家来讲,读书会我们希望是普通读者。

邵:人总是会不自觉作出选择。你直觉觉得可以就来,但你一定是归好类了,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归类?是被归类还是反归类,还是说不用归类?
徐:我觉得归类这个事在本质上来说,它不是说事物本身就有一个类型,事物本身是没有类型的。归类这个事,是为了人能够更方便的去理解和传播而做的一件事,比如说档案学,是太庞杂的一个体系,你要快速的去找到一个东西,是为了便捷,但当你把这个归类当做你的目标,你的档案就被禁锢了,我们会把档案看作是知识,是所有人类有史以来积累的知识。
归类的方法是让人们更方便的进入这个知识体系,但如果你把这个知识体系当做一个目标的话,你的面向不是未来的,你的面向是过去的,我是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归类,进行快速认知的方法。如果你把归类当做一个目标的话,会抹掉你面对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对过去的事物进行归类。
邵:一定会对自己归类吗?
徐:会,你的归类里,也会对应并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的行为而进行归类,比如第一次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要去约会的话你得快速的去介绍自己,随之也回想起我之前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做一个归类,你把这个东西非常便捷的传递给她。
邵:就是各种信息归类之后,从这里抽出一条信息线直接可以使用。
徐:传递给她,但是,面对未来很难归类。比如跟老婆生一个小孩,我去归个类是到底生男孩还是女孩,还是第三类,没有人那样做,面对未来,就让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自然而然的发生。

邵:这个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我搞明白了一件事,你为什么来这?虽然已经被归好类了,我已经知道这个体系是什么,但是有一个自我的东西需要去一个地方,所以在这。
不仅仅是因为人,这里让你感受到了自我,喜欢去那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在想“反归类”的时候,其实是你自我内心的一个东西在跃动,在说“我不要”。如果阿俊这个书店里的书不用挑,可以随便进,但是挑或许就是阿俊的特质,挑的好不好是其次,但我一定要挑,这就是我,我一定要挑完了才放进来,这是“反归类”这件事。
成都也有这样一种特质,是一种不被归类的状态,这个很有意思,是一种不确定的、跃动的状态,很自我的那一部分,恰恰这也是我们喜欢成都的原因。
俊:比较自在。
第二幕
大逻辑里的生长力及小模块的自发性
日常可以有千万种,每一种都是鲜活的

在玉林路的街头走一走,有街、有路、有巷,没有规律,没有尽头...
邵:昨天在市民广场,看到城管追着小贩跑,三分钟后又回来了,城管叔叔很有热情,这帮商贩也很有热情,那种感觉一直在这里。我自己感觉浪哥的大多数思想来自于建筑知识范畴之外。
徐: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在我们团队还挺强调结构体系,比如说木结构、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可能这个事一般来说在设计院里面做施工图的时候才去做的事,我们在概念方案的时候就会先确定这个,这是一种归类,但是这种归类是为了让团队更快速有效的认知到我们做的东西整个体系架构。
邵:就是说去怎么做建筑?
徐:对,就是怎么做建筑,它的构造应该是采用什么,混凝土建筑你的构造方法板厚、梁厚完全不一样,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强调这个东西,我们在讨论建筑的时候,比如,我上一个是用钢结构,我内心里面的反感觉得这个真的不想用这个做了,这也是一个归类。
我们讨论方案的时候出发点肯定不是结构性的,肯定是感知性的,你去到一个自然保护的区域里面,你是感知那个场所,可能那个场所给你很敏感的东西,你把它捕捉到,这些东西确定之后还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态度,你再去想结构体系应该用哪一个表达,而不是说你的目标一定要做一个什么类型的东西。你很难说,我完全摒弃了归类,我只是说归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标?
邵:在你心里它不应该是目标。
徐:不应该是目标,有可能是手段,是战术,是技术措施。

邵:刚才讲到一点,一个是知识,一个是职责。徐浪这个建筑师他做的状态,这两个东西是互相纠结、互相影响的状态,抽离一个建筑出来。从开始看到场地就开始纠结、抽离、纠结,最后,找到那个状态,可以是谁打败谁,不知道,你在意这件事吗?
徐:不在意。
邵:最后谁战胜无所谓,比如,知识如果战胜直觉。
徐: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对结构特别迷恋,当时我是这么去想的,就觉得在结构层面的创造力和创新是建筑比较基础的、比较底层的创新,底层的基础被创新以后,上面用的肯定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迷恋结构这个事。
上次在跟李烨讲的砖混房子,上面是什么?下面是什么?最后生成另一个结果,这套东西我越来越觉得不对,我觉得知识是很大的范畴的一个界面,也是大过很多东西的一个世界。但还是会觉得索然无味,我也会发现老在一个知识里面去想知识的突破,这个肯定有问题。

阿:牵制你的灵感,以及你创作时候的知觉。
徐:对,你去到一个地方,比如,光从哪一个地方照进来,早上八点是什么地方照射进来,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你产生新的兴趣,可能会发展成不一样的设计方法。每个项目和前面一个项目有很大的不一样,一方面你给自己塑造一种知识,马上在自己的框架里面会被类型化,可能下一步想的就是怎么去打破这样的类型。
邵: 人都是这样的,但你的边界感比较清晰。比如,你说你相对比较喜欢晚上一个人去办公室画图,有一个比较挺安静的环境。

徐:玉林,是特别成都的一个地方。
俊:就是晚上我们会聚会的地方。这些老街区,玉林这一带你只要不影响交通政府是鼓励你摆摊,这样的话城市就有烟火气,这里不单单是本地人来,更多的是游客。比如,成都的那首歌把小酒馆唱红之后,从下午到晚上人就会特别多。
邵:浪哥面对这样的老街区,这一类如果你来改造会怎么做?
徐:一下子确实没有想好,我是觉得这种街区不要成片的改造。如果成片改造的话,可能改出来是另外一种城市状态,可能还是类似于像高新区那样,你不能说高新区不好,它是在一个空间逻辑下面做出来的东西,它也很光亮、整洁,它有它的秩序,它有它的舒适。如果我们觉得它是一件好玩的事,就不要一大片、一大片的整改了。

邵:你说的一大片是整个区域不能那么粗狂的来做改造?还是说要分解成小模块来做?
徐:如果整个街道按照某一种立面方式整体改造。我觉得改的话,立面只是非常表象的一个东西,核心改造内容应该是“引入内容”,假设这个街道引入的都是很有趣的店铺或者很有趣的人,这些店他们对自己就会有一个品质要求,这个品质是每个人自己定的,始终都是有品质的。
比如,一苇书坊可以按某一种方式改,你改出来之后吸引了这样一批人,你有你的人气,你有你的经济逻辑,不能只是改造一个建筑形象,我觉得建筑形象在这个片区是失效的。

邵:为什么?
徐:我们谈建筑形象,所有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目标和逻辑。现在城市规划学目标和逻辑就是更加有效的城市治理,更加有效的经济效率,更加有效的空间生产。
邵:你刚才说的内容是生活本身还是什么?
徐:也许是生活,也许不是生活。比如,我们如果做工作室的话可能不是生活,和工作相关,但是也可以和生活相关,工作和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不分的。
邵: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它重新整理,整理它的内容,之后我再说哪一个模块怎么去做,而不是说,一下就改一大片,还是有点粗犷。
俊:对,肯定是自发的,每一个店面后面的老板,他觉得在这里做面馆合适,另外一个老板说可能做烧烤、火锅店合适,这些都是自发的。
邵:跟一苇书坊一样,阿俊哥是有标准的,我希望是什么状态,每一个像阿俊哥这样的人来做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
俊:这一排全是五金类的,卖日常用品。
邵:这种小店,也不用那么精致。
徐:但它可以有精致,相当于它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一苇是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这是另外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没有说一定你得按照什么方式走。

邵:所以浪哥我觉得你还是情有独钟的,对很多事情在自己习惯的氛围内会有舒适感,会给你很多松驰、舒服的状态。刚才我看阿俊哥,他整体状态感觉还挺靠谱的。
徐:很靠谱。
邵:很让人信赖的一种状态,并且在他这样一个小书坊里面,来的都是学者教授,他能做到这一步,把这种力量带到社区,带到普通街道上,这个还是很厉害的。浪哥希望自己职业化吗?
徐:我希望我们团队职业化,因为团队的这种职业化对于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好事,会有一个团队的性格,我对我自己的希望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开阔,在团队职业化的同时还能带着团队朝着更开阔的视野,朝着更开阔的方式去走,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重要。
第三幕
吃小海鲜,谈及名与利
它不是目标,但可以是手段

在农贸市场里面吃三文鱼,也许是另一种新奇的体验。
邵:你怎么会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徐:也是朋友推荐的,你看着这里伞上颜色是鲜艳的,光线撒在半透明的太阳伞上,看到这个,我也就会想做一个“膜结构”的房子。
邵:这儿是你经常会来?
徐:这一家店我就来过两次,因为没有其他分店,我后来去的小海鲜离我们办公室很近,骑车也就700米。

邵:做建筑师和赚钱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你怎么看?
徐:我觉得赚钱的这个事,其实和你的职业没有太大关系,特别是十年之前觉得建筑行业赚钱比较多一点,今天会觉得IT行业赚钱比较多。但其实所谓的行业赚钱多,是自己赚钱多吗?并不是,你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这个行业附带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赚钱这个事真的不重要。
邵:你这话,一般人听了会觉得特装X(哈哈)。
徐: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在心态上一定要觉得它不重要。
邵:那天跟几个朋友聊起,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对大家对生活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把这个事归为应急状态之下的一种反应,是我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徐:反正我觉得赚钱这个事和你自己的本事、能力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
邵:你不觉得有本事就能赚到钱吗?
徐:有本事没有赚到钱的人多了去了,什么五车八斗的,格局很高,肯定生活不愁,但是也没有赚到很多钱,跟这个真没有关系,所有赚到的钱可能还是社会给你的。建筑师的这个行业,你身在60年代、70年代,也是赚不了钱。
邵:还是时势造就。你不觉得赚钱可以是有赚钱技能的吗?比如,是否把建筑作为一种赚钱技能这件事?
徐:如果把建筑作为一种赚钱技能,你可能会越来越赚不到钱,我觉得太在乎钱这个事反而会赚不到钱。钱这个东西它的本质,是一个人的赚钱能力和背后相关的社会信用度,是一种社会认知的信用度。
邵:其实是社会或者时代给你的,这个我认可。
徐:建筑师往前推50年真赚不了钱,可能再往前推个200年,那个时候的建筑师是匠人。有一首诗里曾经提到过,名字我忘记了,大概是说做瓦的工匠他们家是用不起瓦的,都是草棚。那个时候建筑师是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这都是现代社会给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邵:从开始选小海鲜和一苇书坊这两个发生场,我在想浪哥你的城市记忆点是什么?你挑了这样两个地方,一个是跟家庭或者你在这个城市的朋友圈有关系,一个是跟你自己记忆有关。
徐:可能是成长的经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像重庆。
邵:可能不是在学校的那种情节,而是其他城市的成长的情节,也是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过程中留下的那部分。你觉得在这里吃与在日料店里吃有什么不一样?
徐:我就觉得挺神奇的,在一个农贸市场里面吃三文鱼,有那么一点神奇。
邵:小海鲜,除了你跟爱人吃过,还有跟谁?
徐:跟同事来吃过。遇到好吃的,我反复带不同的人吃,自己觉得特别好吃,但是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知道,但我会带他们去。

邵:要谈西南建筑,可能绕不开汤桦老师和刘家琨老师。他对这一批学生,或者这一代学生影响都是极大的,对你有影响吗?
徐:有的,其实我在家琨老师那里,只是实习了三个月,但我觉得他在观念上对我的影响还真的挺大。
邵:你说的观念是什么?
徐:我现在很难用某一句话去总结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刘老师的职业态度和方式,对我的建筑影响还挺大的。可能是“对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建筑”影响挺大的。我现在很难去说某一个具体的观念,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记得是大四的时候在刘老师那实习,他说:从重建工出来的学生是有一个标签的,标签就是造型能力特别强。
邵:你说造型能力是指?
徐:是一种“形态的能力”,空间的丰富程度也会很高,那套东西重建工会玩的特别好。当时,我在刘老师那里实习也曾做过一个方案,我都忘了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哈哈),他对我是批评的语气说的,我印象特别深,他是在做建筑,不是在做文学。文学,其实就是个人的创作,关起门来写一本书,卖不出去无非就是自己写的烂。
建筑这个东西,你每做一个,调动的都是其背后的物质性的东西,是关乎整个社会生产的过程,这些都要被搅动起来,其实,最后的呈现依旧是一个物质性的结果。后来我再想起刘老师的话,给我的影响是,我可能会比较强调像建筑的语言和语义。
徐:后来,我会比较在意建筑学的整个语言结构,今天回忆起刘家琨老师所说的这个事。

邵:建筑所呈现的物理空间和社会性是挂钩的。汤老师和刘老师对西南地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从内心里觉得,从他们身上会汲取很多养分,不只是建筑,还有他们人的状态,包括做建筑师的状态都会有影响。提到社会性这一点,建筑的社会性或许是目前城市最大的课题,也是需要建筑师出来解决的。你自己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哪些养分?
徐:我觉得还是一种状态。
邵:是要找到一种建筑师的状态?
徐:很难说你的状态要成为刘老师或者成为汤老师,你在他们身上明白“状态”,这个事就挺重要,最终你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状态,一种属于自己建筑职业里自我舒服的一个状态。
邵:你说倒要舒服,首先是自处,自己跟建筑相处这件事,你如果愿意了,那个状态或许就是你的状态。你似乎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努力,比如,名的问题,利的问题,这两件事对你来说,其实是排在建筑后面的。另外,还有你生活的状态和你做建筑的状态,两种状态之间,其实也会相互促进。
徐:“名”和“利”的问题。钱,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绝对是有定数的,我早生40年我可能赚不到钱,晚生40年可以赚很多钱。赚多少钱和建筑状态没有关系。名,还挺重要,它是你的社会信用,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成名,是社会认知的信用。

邵:这是你的状态之一,你会想让所有人都相对舒服一点,所以,跟你在一起,会感觉很舒服。现在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兼容。这或许也是一种作为建筑师的修养,是一种自内而外的东西,是有点人味的状态,两种感受在一起,也并不是说是极其分裂的感觉,但也有分裂,但或许你可以掌控的游刃有余。
所以,社会信用这件事,有社会信用才有建筑的社会性,不是说“名”本身,也包括“利”的产生,也不是目的,不仅是建筑师,任何职业都是如此,社会信用促生了你的社会价值,其次,会通过你的职业手段带来社会性。
徐:你的社会信用会被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之后,你其实更容易找到和你相匹配的或者是气场相合的合作者、业主、伙伴,社会信用会让你的理念、设计的认知,以一种更没有障碍的方式去输出和达成,但也可能会比较痛苦,也可能会有一个错位。
邵:今天你谈的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前置,不是目的导向,不是目标导向,包括你的房子,还有“名”这件事,钱往后退。甚至小海鲜、一苇书坊,都像是你的参与过程,当然也包括建筑,包括晚上去办公室画图。这样一个路径,可以说是你跟成都的关系,就是徐浪的一个网络,是这样展开的。但是社会性也会促生你对这个城市发生直接关系,因为你是一个建筑师。

徐:为什么像建筑师、艺术家这样的职业总会和理念、观念相关,“名”这个东西,对这一类职业的人其实很重要,而且它是非常的重要,可能没有这个“名”,你的职业状态是不成立的。
邵:或者,它成为一种驱动力。
徐:对,可能你的目标里会存有更好的观念,能够输出给这个时代,输出到这个城市,但是,“名”是作为一个手段来推动这个事,如果你没有名的话,这些观念当然是输出不了的。
邵:它同时也会是给你的一个约束力,约束力会产生一个责任,在一定范围之内要达成一个好的结果。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