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别人的动物园”与……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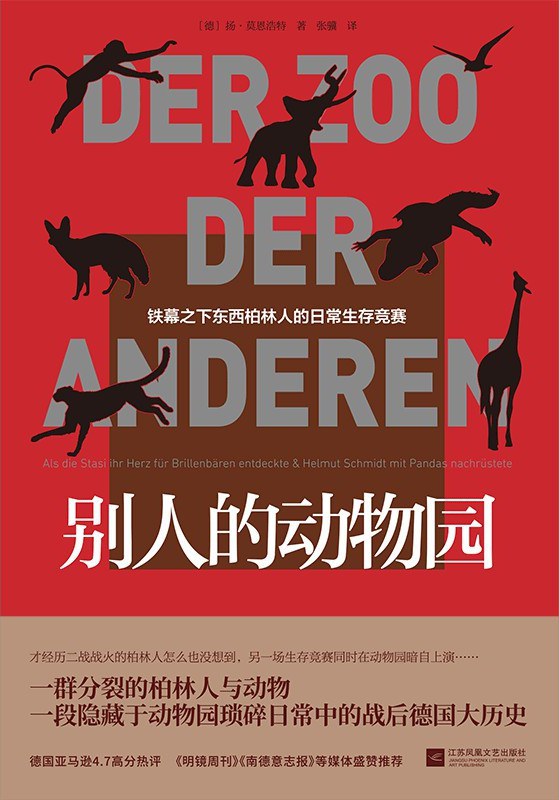
《别人的动物园:铁幕之下东西柏林人的日常生存竞赛》,[德] 扬·莫恩浩特著,张骥译,凤凰联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288页,58.00元
扬·莫恩浩特(Jan Mohnhaupt)的《别人的动物园:铁幕之下东西柏林人的日常生存竞赛》(原书名:Der Zoo der Anderen :Als die Stasi ihr Herz für Brillenbären entdeckte & Helmut Schmidt mit Pandas nachrüstete,2017;张骥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是一部相当独特和很有意思的“动物园政治学”,原书名中那个副标题比较长,而且直译过来显然不太适合。现在中译本的副标题比较恰当地描述了该书的实质内容,就是冷战中发生在东西柏林之间的生存竞赛及其实质。德国记者、作家扬·莫恩浩特多年来在《每日镜报》上为柏林的两座动物园撰写报道,另外著有历史调查作品《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动物》(Tie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他对这两座动物园的历史与现状都很熟悉,使该书读起来既有现场感,同时更有关于历史和政治的深度分析,使一个另类的动物园史题材被赋予了有普遍性的现实意义。
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在当时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休闲场所,还是两种制度的某种标志:分裂、竞赛、厌恶对方,但是又无法忽视对方。在两位动物园领导人身上都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如极端的专业、敬业、勤奋、极度酷爱动物园事业,他们都把动物园事业放在优先的位置,心里只有动物,连家庭生活也要往后靠。动物园园长不仅是一份职业,而且更是毕生使命。尽管各自所在的制度环境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把动物园打理好。对于动物园园长这个职位来说,西柏林动物园的海因茨-格奥尔格·科略斯(Heinz-Georg Klos)园长和东柏林动物园的海因里希·达特(Heinrich Dathe)园长无疑都是非常称职和成功的。但这不是发生在普通年代中的职业竞争,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制度竞争、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因为柏林人似乎比世界上其他城市的人都更酷爱动物——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一样,有那么多动物变成了公共生活中的“名人”——才让这种竞争通过动物园而表现出来。正如作者所说,“两家动物园都互相为彼此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德国处于分裂,柏林情况特殊,只有在这种形势下,两家动物园才能如此发展,两位园长才能这样一展拳脚。两家动物园是他们城市的象征,代表着各自的社会制度:西柏林动物园(Zoo)是西柏林这座孤岛上的珍宝,一个物种的大杂烩,在其每一个角落里都能感受到西柏林这座‘围墙之城’的逼仄。而在‘铁幕’的另一边,东柏林动物园(Tierpark)希望展现的理念是宏伟和广阔。……大概只有在冷战时期分裂的柏林城,两位动物园园长才有可能在各自的‘半城’中享有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序言”)通过讲述“别人的动物园”与“自己的政治”的故事,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冷战史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段真实历史,其中有些来自动物园的故事细节不但生动有趣,而且折射出在冷战政治下普通人的不屈理想与生存法则。
关于“围城之城”的逼仄,德国卡塞尔大学的历史学家米珂·洛舍尔(Mieke Roscher)认为柏林的隔绝状态造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被特别强烈地凸显出来,在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来自边界的包围感”,“在某种程度上,西柏林和东柏林本身就是两个动物园”。因此动物园更像一片“心灵上的自留地”(Rückzugsorte)而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块净土。(“序言”)这是关于孤岛城市的空间政治学和动物政治学的绝妙分析,在世界动物园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动物园的存在意义被精准定位,而同城中的“别人的动物园”则意味着别人的制度、别人的社会政治以及与“我们”的生存竞争。
关于动物园的世界,过去我们大概会知道是否拥有大象、狮子、老虎等大型动物是动物园规模等级的标志,却未必都很清楚只有大象才是威望的象征,拥有大象的数量才是关键因素。西柏林动物园园长科略斯就很为此感到自豪。但是东柏林动物园园长达特也有瞧不起科略斯的资本,因为科略斯只是兽医出身,在当时动物园园长的世界里有个传统:读过大学的动物学家比兽医出身更符合园长这个职位的形象。从组织管理能力来说,科略斯显然十分出色,他能从政治家和企业家的钱包里光明正大地抠出钱来,能够维持和联邦德国政府的紧密联系,提升自己动物园的经济和政治价值。东柏林的达特也同样出色,他不仅因其专业知识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深受民众喜爱,而且能在他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做出近乎奇迹的成绩:“能够给自己和自己的动物园创造一些不受民主德国束缚的自由空间,这才是重要的。”(“序言”)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意义不仅超出了动物园的生存竞赛,甚至也超出了达特在主观上的政治认知水平,在冷战研究中具有相当另类的重要意义。另外,达特不仅是东柏林动物园园长,而且还掌管着中央检疫站,负责从社会主义阵营向西欧运输动物的检疫工作。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世界之间还保存的各种交往纽带中,以动物的名义进行的交往未必是最不重要的。
说到动物园与政治,作者在“序言”中有一节的小标题就是“动物园——政治之地”,他认为虽然达特和科略斯在各自体制内都把这场“大动物游戏”玩得精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在政治上还是略显幼稚:达特一直以为他从来没有被“史塔西”监视过,科略斯居然敢推荐他的前任鲁茨·赫克(老纳粹、戈林的老朋友)担任德国动物园联合会的荣誉会员。“只有当政治对他们的动物有重要意义的时候,他们才会对政治感兴趣。达特和科略斯就是两个‘动物人’(Tiermenschen)”(“序言”)——这个词常用于描述动物园和马戏团从业者,形容他们更善于与动物而不是与人打交道,更何况与人的政治打交道?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只能适应自己那个世界的“动物人”,他们的那一套做法“如果到了对方的世界,他们都会遭遇惨败”。(“序言”)
柏林动物园建成于1844年,二战前园内动物共有一千四百多种,四千多只,是德国最古老、也是当时世界上拥有动物种类最多的动物园。1943年11月22日晚上,七百五十三架英国轰炸机在柏林上空倾泻下两千五百吨炸药。有二十一处大火在动物园里肆虐,在动物园未被转移走的两千只动物中,有七百只不幸遇难。有流言说有些动物在轰炸中从动物园逃走了,其实那些在炸弹中幸存下来的动物早就被吓得不敢逃走,只想蜷缩在废墟之中;就连鹰和雕也呆立在被摧毁的笼子的枝丫上,也不再飞翔。
1945年7月1日,柏林动物园重新对外开放。 许多柏林人把自己家的宠物(主要是鹦鹉)带到这里,让它们在动物园能得到更好照料。 在“柏林封锁”期间,市民用从自己口粮里节省下来的卷心菜饲喂他们的动物大明星。代理园长卡塔琳娜•海因洛特(katharina Heinroth)和她的同事艰难地重建动物园。德国从1949年开始被分割成了两个国家,柏林处于四国占领的状态,但是柏林动物园的大明星、公河马“柯瑙什卡”与东德莱比锡动物园的母河马“格蕾特”仍能冲破敌对政治的界限而走到一起;柏林被分为东、西两半,但对于绝大多数柏林人来说那条边界线只是存在于纸面上,东柏林市民还是可以到西柏林去。在边界线上位于东柏林一边的特雷普托(Treptower)火车站常有东德警察查问乘客,人们如果回答是去选帝侯大街喝咖啡或者看电影,人民警察就会以老师训学生的口吻说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也有电影院和糕点。”但是如果你回答说“嗯,我要去动物园。”警察就说不出什么了,因为民主德国的首都的确没有动物园。(33页)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1953年10月,东德当局决定在东柏林新建一座颇具影响力的动物园,减少东柏林市民去西柏林看动物园。新动物园被纳入“国家建设工程”,可供使用的土地有一百六十公顷,是西柏林老动物园面积的足足五倍,海因里希·达特被任命为新动物园园长。1955年7月2日,东柏林动物园正式开业。1956年底,海因茨-格奥尔格·科略斯接替卡塔琳娜·海因洛特,成为西柏林动物园园长。就这样,同城的两座动物园的竞争故事正式拉开了帷幕,“别人的动物园”成为政治竞争的对手。刚开始的时候,达特想维持和西柏林动物园做友好邻居的表象,“但很快,这些就再也不是他自己能掌控的了”。(59页)
达特不关心政治,但并不等于他忽视政治。达特很会利用西柏林动物园的存在,为建设东柏林动物园谋取政府的支持。在他写给政府的申请物质投入的报告中,总是会提到“我们就不会落后于西柏林的那个动物园”“西方正在睁大双眼盯着我们的发展”等等。“敌人”的存在才是养活“我们”的最好理由,达特早就对这一套机构要生存、要发展的法则了然于心,而且他也的确没有虚构一座“别人的动物园”来骗取经费。动物园之间的竞争离不开动物品种、数量和场馆建筑及设施的竞争,有人曾这样描述两位动物园园长之间的竞争状况:“一位要是买了一头小驴,另一位就马上买一头大驴。” 西柏林的科略斯曾经对记者抱怨说,“我要是开一辆大卡车去拉动物,达特就能调来一整节火车车厢的动物。”但是科略斯也会利用东德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当他以“人无我有”作为竞争手法的时候,建议西柏林市政府建一座全新的类人猿馆,就是看到了东德缺少外汇因而肯定买不到猿猴,另外还看准了装猿猴的栅栏笼子需要铁管,而在东德那边铁管子比外汇还难搞到。(94页)但是达特也有他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的优势,他的东柏林动物园只有四百余名正式员工,当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可以动员那些来自监狱、疯人院和残疾人中心的人参与一些简单的工作。(164页)总而言之,因为有了“别人的动物园”,竞争就是必然的、全方位的。
1963年6月,东柏林动物园新建的猫科动物馆——被誉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动物馆”和“一座实现社会主义的里程碑”的阿尔弗雷德-布雷姆馆正式开馆,达特精心挑选6月30日这一天举办开业仪式,因为这一天也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主席、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七十岁大寿。虽然知道他本人不会来,但是相信他“会在远方面带慈祥地听手下汇报此事。而且,这场活动让东柏林市长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又有机会在一片隆重的气氛中剪断开业彩带了”。更有意思的是,达特有本事让艾伯特喜欢来东柏林动物园参观,因为他知道市长艾伯特十分喜欢被公众认出来,所以每逢艾伯特来东柏林动物园参观,达特总会提前设计好让一个班的小学生候在附近,然后让孩子们在途中“偶遇”这位东柏林市长,并欢呼着向他打招呼。(123-124页)你可以说他是个马屁精,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在他心目中,只要对动物园有利的事就必须做。在这方面,他的竞争对手、西柏林动物园园长科略斯也是完全一样的。正如作者所说,“在政治场中,科略斯的言行和铁幕另一边的达特一样务实——也可以称之为幼稚:只要是服务动物园的,就都是好的”。(191页)科略斯想方设法要吸引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来动物园,他对勃兰特说“带您儿子一起来吧,他也一定会喜欢这里的”。那位十一岁的小勃兰特当然会喜欢来这里,因为他能和父亲深度游览动物园,能收到动物园水族馆馆长维尔纳·施罗德送给他的一张印度毒蛇的皮——而别的孩子却不能。“他并不知道隐藏在这些特权背后的意图”,但是孩子的父亲,那位市长大人当然知道科略斯的用心,却也乐在其中,因为他对西柏林动物园之于这座城市和市民的意义有着清楚的认识。(121页)只要不想在位置上无所作为,更不用说对所从事的事业有强烈的使命感,体制中的官员大概都会无师自通地学会这一套,况且这些小技巧已经可以说是很廉洁奉公的。
在东柏林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达特的动物园中的美洲黑熊馆有一块的金属牌子,写道:“馆中熊谷由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捐款修建。” 或许因为这样,达特才有底气把那些在东柏林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和横幅都从东柏林动物园清理出去,西方媒体也给予了认可性的报道。莱比锡动物园的迪特里希对此看得很清楚,“达特能肆意地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海报阻挡在他的东柏林动物园之外,能以呼吁发起募捐的行为惹恼那些大领导,这是因为他享有完全不同的威望”。(107页)达特可以在动物园里让管理员不受打扰地和他们的西德同事见面,连他的研究爬行类动物的儿子法尔克也会充分利用这个场所请西德某位蛇类专家来做个报告,次次都会座无虚席。“这种所谓的临时活动只有在东柏林动物园才能举办,在那些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的大学里,这绝对是不可能的。”(166页)作者曾经在“序言”中指出达特能够在自己的动物园里创造一些不受束缚的自由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谈到不仅是东柏林动物园,在莱比锡动物园也有这样的自由空间,主要是因为“在动物园的高墙之内,逐渐形成了一种亚文化。那些和社会主流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比如那些不同政见者、怪人、边缘人”。(163页)情况更突出的是在莱比锡动物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莱比锡动物园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但很多人都是活跃的基督徒。可以这么说,当时的莱比锡动物园就像敌视国家的一座小小的孤岛。这也与这座城市本身独特的性格有关”。(164页)仅存在铁桶般社会中的孤岛现象,只能出现在动物园的思想自由空间,这是冷战史研究中的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议题。
达特对自己的海外关系也从不避讳,在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份关于他同“非社会主义经济领域联系”的调查表中,他承认自己以会员身份参与国际动物园园长联合会的活动、以国际动物园杂志编辑的身份和全世界都有联系。他也知道在自己的员工中间有些人负责汇报动物园职工中弥漫的不满情绪,比如在“非官方雇员报告”中就曾提及职工们抱怨建筑过程中的施工质量低劣等等。(167页)我相信达特知道这些都无伤大雅,因为建筑材料的缺乏与质量低劣一直是东德的老大难问题;或许他还会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总得要让那些眼线拿出点成绩。达特的声望在东柏林还是有点管用的。如果西边的动物学家在过境关卡说自己要去东柏林动物园或者去找达特,一般他不用经过进一步的搜查就会被放行。还有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说明达特有点有恃无恐。有一次儿子法尔克的学校要求达特夫妇签字确认家里没有收看西方电视节目,达特拒绝了,理由是“我的职业要求我获得广泛的信息,因此我必须阅读国际期刊,收看西方电视节目”。老师听得目瞪口呆,而别的家长们听说达特反对签字都很高兴,于是整个班成了学校里的特例。(127页)
1961年8月13日凌晨,从东德通往西柏林的过境关卡被全部封锁。随后几天,那道由混凝土构成的壮观建筑围绕西柏林延伸开来,柏林场成为柏林未来几十年独一无二的象征。西柏林动物园和东柏林动物园之间的战线也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再也无需为争取对方游客或因对方游客而费神了。在此之前,从西柏林来的游客让东柏林市民大为不满,他们抱怨说西边来的游客在东柏林动物园里把所有吃的喝的都买走了,还把餐厅里的好位置都占上了,在1957年5月东柏林市政府的文件中曾有这样的记录。(93-94页)从今以后,动物园园长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取悦游客,“他们之间的竞争现在也变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代理人战争,两人和他们的动物园都代表着各自的政治体制”。(115 页)只有动物园笼子里的主人没有意识到封闭的新时代已然降临,它们仍然像往常一样仰天长啸,“……这些动物的声音还会冲破柏林墙的阻隔,一路向东,飘到东柏林动物园上空。仿佛这座城市还是完整如一的”。(118页)西柏林动物园一下子失去了超过一百万的参观者,科略斯因此恳求西柏林市政府给予更多补贴,新局势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他也不用担心有游客流失到东柏林动物园了。但是到了1963年12月,柏林墙建成两年半之后,拜通行证协议所赐,西柏林市民又能去东柏林了。(121页)
在东德人如何翻过柏林墙逃往西德的故事中,来自动物园的故事可能还是比较新鲜的。东柏林动物园是东方和西方阵营之间最主要的动物转运节点,每天都会有装着动物的运输箱运抵这里,或者由这里发出。格尔德·摩根(Gerd Morgen )是负责动物隔离站和运输工作的管理员,他在同事的协助下成功地躲藏在一只由苏联运来的母麋鹿的大木箱子里,逃到了西柏林。他的同事当然要受到查问,据说是由于达特园长的干预,或许是达特说过“这些人对我的东柏林动物园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话,那些员工才免于牢狱之灾。
时代终于要掀开新的一页。1989年10月,足足有八十万被憋了许久的东柏林人“利用他们新赢得的自由,来到西柏林动物园,观赏那些同样被憋了许久的动物。动物园也给予了游客两周之内免费参观的福利”。(220页)西柏林动物园大门处排起了三百多米的长队,园里的惊叹声此起彼伏,但偶尔也能听到孩子们挑刺的声音:“我们的大象馆比这个大多了。”向东十五公里以外的东柏林动物园内只留下少数人值班,每个员工都想亲眼看看柏林墙到底是不是真的倒掉了。
随着柏林墙的倒掉,“别人的动物园”还在,但是各自的政治故事当然要改写了。政治气氛越来越弱,动物园应该关心的只是如何吸引游客和保护生态系统的问题。竞争继续存在,但不再是政治化的。作者最后说,在那个政治对抗的年代,两位曾经是伟大的动物园园长都让各自的动物园走出柏林、蜚声海内外。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对那个时代的回忆——那个动物园是政治之地的时代,那个各自对立、心里只有“别人的动物园”的时代。(246页)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