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游戏论·文化的逻辑|鲍德里亚与医疗游戏的游戏药方
“Games are serious, more serious than life.”(游戏是严肃的,比生活更严肃。)
Baudrillard, 1979, p.133[1]
“The world is a game.”(世界是一场游戏。)
Baudrillard, 1993a, p. 46[2]
电子游戏面临的许多质疑都围绕这样一组矛盾展开:作为一个休闲、娱乐甚至是放纵、狂欢的“私人”领域,同时作为一个对青少年具有潜在启蒙和教育功能的“公共”新媒体,电子游戏应如何平衡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它营利性的目的?
可以认为,严肃游戏之所以被发明,就是为了平衡上述矛盾。1970年,克拉克·阿布特(Clark Abt)[3]提出严肃游戏(serious game)的概念,他认为,严肃游戏是一种不以享乐为主要目的的游戏,它明确地将教育目的附于游戏机制与叙事中,在保证玩家参与游戏的自愿性以及游戏行为的自由性之同时,也使游戏的设计概念、内容发生了严肃性的转向。如此,严肃游戏打破了游戏单一的娱乐性质,拥有教育、说服等功能。最初,严肃游戏多用于教育、军事等有限的领域,如今严肃游戏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及健康、军事、教育、政治、生态保护等诸多领域(lvarez J & Djaouti D, 2011[4]),不少学者考察了医疗类(Sliney A & Murphy D, 2008[5])及城市规划类(Poplin A, 2014[6])严肃游戏在实践领域内的功用,也有学者探讨了政府、企业管理与严肃游戏间的关系(Whitson J R, 2014[7]; Schrape N, 2014[8]; Steffen P. Walz, 2014[9])。
严肃游戏涉及的设计概念、目标及框架等辩证内涵(Mitgutsch K & Alvarado N[10]),实则牵涉一个终极问题:游戏对于当代社会意味着什么?游戏能否有消遣娱乐以外的功能?
一、游戏的终极模糊:鲍德里亚开启的哲学思辨
对于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鲍德里亚致力于从文化和语音的角度反思后现代社会,特别是针对现实物质基础的能指(the signifier)和所指(the signified)之间的符号表征关系(the sign)。鲍德里亚提出了拟像(simulacra)的概念,直指后现代文化中充斥着拟像,它们是某种壮丽真实的投影,能遮盖真实并异质其本源,让真实化为乌有;拟像社会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里充满没有本源的复制品(copy without the origin),与所谓的真实再无确切的对应关系,拟像是自身纯粹的拟仿物。[11]从197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思考了数字化、后工业经济、非物质劳动、媒介化和拟像的问题,并在诸多文章中用电子游戏作为分析对象。[12]
在鲍德里亚的年代,很多评论家都视电子游戏为洪水猛兽,对其怀有戒备之心。鲍德里亚对游戏的态度正面得多,针对“游戏对于当代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鲍德里亚至少认为游戏是一种多少令人愉悦的上瘾物质。鲍德里亚如是说:当我们身在游戏中时,我们也受到保护,不受理性社会和常规真实的残暴束缚。[13]游戏令人上瘾之处,在于与真实有所距离的虚拟性;游戏提供给现代人的,是一种逃避的美。有意思的是,鲍德里亚对于真实和虚拟的价值判断是这样的:社会真实很残暴,且束缚人;虚拟(游戏)令人快乐,人们可以短暂地远离社会真实。
鲍德里亚认为游戏对当代社会的另一种贡献是“热情”(passion)。[14]尤其在年轻人对性、身体、工作、政治的积极性都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他们对游戏的热情依然熊熊燃烧(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这种热情能燃烧到国家不得不颁发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律法)。游戏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来自何处呢?除了游戏本身能为年轻人带来轻松愉悦的基于情感体验的可玩性、挑战性、虚拟性、趣味性以外[15](Stenros J, 2014),鲍德里亚认为,游戏还具备某种民主性。[16]因为在游戏规则面前,每个玩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我们所知的最后一种民主。
需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既不是游戏爱好者(或者说他喜欢的“游戏”是他的文字工作),也不是游戏研究者。鲍德里亚之所以多次提到游戏,主要因为相较于其他文化形式,游戏更能代表拟像社会的未来。鲍德里亚没有真正活在电子游戏的时代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鲍德里亚积极写作时,电子游戏对政治经济脉络的影响力还不那么强势。当今社会,游戏已经成为一种足以与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比肩的文化生产形式,它正以可见的势态反推其他经典媒介文本的生产:例如在《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失控玩家》(Free Guy)等电影里,游戏化叙事彻底革新了电影对时空的安排,游戏中的闯关机制打破了传统叙事时空的一维性及不可逆性,在重复载入的回合制游戏叙事中,观众们仿佛置身于游戏中。与此同时,游戏程序里的男主与现实世界中女主的相逢与相爱消融了游戏与现实的空间区隔,为观众书写了一场超越次元的游戏浪漫;在电视剧《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Death&Robots)塑造的赛博世界中,一名舞女为了躲避杀手的追杀而展开无休止的追逐。在这场追逐中,凶手与被害者的身份不断转换,荒诞的循环式叙事打破了影视叙事的逻辑性,颇有一种玩家身份随意切换、游戏情节重复载入之感,且只有电子游戏玩家才欣赏得来其中妙处!
游戏设计的理念也已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游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鲍德里亚观察到的逃避,转变成积极而有深度的介入。这种介入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严肃游戏作为一种游戏子类型全面兴起。随着科学研究不断突破,越来越多科学家注意到游戏对玩家的正面功能,例如游戏提供的认知、社交和公益刺激,对少儿、老年人、残障人士和孕妇等弱势群体亦大有裨益。近年,各游戏公司亦纷纷推出公益游戏和社会责任项目,为民众提供了有益、有趣、有内涵的游戏产品。本文关注的医疗类游戏就是典型的严肃游戏,这类游戏模拟了医疗场所、医疗用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进行着以“玩”为载体的健康传播活动。
诚然,鲍德里亚认为游戏所具备的民主性正经受侵蚀。由于商业机制的侵入,符号商品拜物教控制了为玩家带来自由、解放与快乐的游戏世界,本土氪金机制的加入异化了鲍德里亚眼中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拥有更齐全的装备及角色的“高级人民币玩家”成为游戏中的“优势阶层”。与此同时,当这种由“氪金”所带来的快感被消磨殆尽后,游戏公司又通过高密度、限时性的游戏活动逼迫玩家向无趣、琐碎的游戏玩法屈服。在享乐与消费的规训下,人们日以继夜地在游戏中投入时间与精力。由此,游戏的“快乐法则”被“消费法则”抹消[17],“自由法则”被“欲望法则”转移,鲍德里亚所言游戏的民主性也在这种被迫的享乐中破碎。
不过,鲍德里亚并未真正生活在游戏的时代,游戏的神秘面纱在他的时代也未被完全揭开。因此,他对游戏的研究尚算粗浅,对游戏的态度也是模糊的。然而他的思想依然可以帮助我们解析严肃游戏。特别是在全民“战疫”的两年里,一些医疗电子游戏应运而生。这些医疗类电子游戏(后文简称“医疗游戏”)的严肃性及教育性使其成为严肃游戏的一种,打开了以往游戏中可玩性、趣味性的内核,将一种忧郁的、死亡的色彩引入游戏叙事中,丰富了严肃游戏之教育、政治、军事、生态保护、经济的类目。基于对医疗游戏的检视,本文对话鲍德里亚的哲学思考,并继续他未完成的哲学思辨,考察游戏如何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再现现实中的医疗问题,如何促进玩家在这场沉浸式的体验中重新审视现实问题?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医疗游戏可以为当代人的心智发展提供哪些营养?医疗游戏的极限又在哪里?
二、将愉悦、热情与可玩性糅入严肃议题
本文关注的医疗游戏主要分三种。第一种是在公共卫生教育当中越来越被广泛使用的医学教育类游戏——或许相比游戏,它们更像是具有游戏性的医学教育类应用——这类游戏模拟了人体、医疗仪器、医疗场所,玩家(一般为医学生)在游戏中进入虚拟的医疗场所,评估现实医疗场所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并在医疗模拟器中提高自身在医患沟通、团队合作、手术操作等方面的能力(Sliney A & Murphy D, 2008)[18]。典型的例子来自教育管理解决方案公司(Education Management Solutions)开发的《模拟药剂师》(SimPHARM),其基于网络虚拟病人护理培训平台,为医学生提供了一个跨职能的医疗培训中心或远程学习地点,从而创造出真实的临床问诊经验。《模拟药剂师》根据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原理等医学理论,以及最新药物的清单、类别、配方及副作用信息建立医学和生物模型。准确的模型为医学生了解现实生活中不同病人对疾病和药物的反应提供了渠道,同时也为医学生的医学实践提供了高容错度的虚拟空间。
另一种是医疗灾难类游戏。它模拟了疫情在社会中的爆发与流行,将现实世界的传染病忧虑引入游戏世界。在这类医疗灾难类游戏中,玩家扮演的角色从现实中的“病毒受害者”变为“病毒传染者”,这种与现实截然相反的游戏设定在展现瘟疫的残酷性之同时,也通过复杂的游戏机制保证了游戏的可玩性与挑战性。譬如在《瘟疫公司》(Plague Inc)中,玩家需体验一种病原体如何在全球肆虐。玩家对病毒传播策略、地点的选择以及各国政府的防疫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病毒的传播(Mitchell S & Hamilton S N, 2018)[19],他们正是从这种反向的身份设置中直面了传染病所带来的死亡恐惧。
最后一种是医疗纪实类游戏。与医疗灾难类游戏的虚构性、残酷性不同,此类游戏一般以个体的视角设置游戏情节,并模拟瘟疫中诸如测温、辟谣、医患沟通等日常琐事。《逆行者》(2020年)与《真相战纪》(2020年)这两款微型公益向游戏便是医疗纪实类游戏的缩影。它们以2019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全过程为时间线,选取医患、家庭、谣言等较微观的视角作为游戏的主要元素,从而铺设游戏情节。家人间的牵挂、社会中的互助等温情的游戏叙事手法将玩家对游戏趣味性的、挑战性的追求转向了对现实瘟疫背后人性的关注。
从对这些医疗游戏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此类游戏代表的是人性对于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的拟像”的顽强抵抗。鲍德里亚曾指出后现代文化生产的特征是拟像对于真实本源的脱离,且操控当代人的多重感官和文化价值。[20]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游戏是逆拟像之流而上的勇士——无惧真实的残忍,且致力于将愉悦、热情与可玩性糅入严肃议题。
首先,医疗游戏游戏化地再现了现实世界,致力于拆卸真实与虚拟之间的高墙,通过再现医院问诊、疫情爆发等现实事件的残酷性,唤醒玩家对于那些处于苦难中的人们的关注与同情。比如在《模拟药剂师》中,动态学习算法赋能于这类医疗保健模拟技术,为每位学习者模拟他们的诊断所带来的后果。相比现实中涉及生死的残酷医疗实践,这类医疗游戏为学习者提供了试错的机会,在降低学习者对医疗实践的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充分锻炼了其医学实操技能。另一个典型的医疗游戏是BreakAway Games开发的《生命体征:ED》(Vital Signs: ED)。作为急诊科医生的玩家不仅需要不断学习处理创伤病例的方法,还需应对检查室中需要分诊的病人。同时,电话、文书工作等也会干扰玩家的临床判断,急诊室的压力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瘟疫公司》则为玩家呈现了病毒的传染过程以及政府对疫情的干预。在游戏中,玩家调整病原体的类型、来源国、扩散媒介、传播环境、感染表现,从而能体验到病毒怎样会以更快的速度席卷全球。各国政府关闭边境、消灭野生动物甚至牺牲病人等抗争病毒的方式则会阻碍病毒的传播。各国的确诊及死亡痊愈的人数、疫苗研发的进展等数据在游戏中的动态呈现,极大地增强了游戏模拟现实瘟疫的真实性(Mitchell S & Hamilton S N, 2018)[21]。

图1 《生命体征:ED》的游戏界面
其次,医疗游戏还需平衡严肃性和可玩性,即维持鲍德里亚所言玩家的“热情”。为了平衡营利性及人文性,游戏设计者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玩法、输赢及策略等游戏机制保证游戏的可玩性,繁复的玩法提高了玩家在游戏行为中获取的情感回馈。《触摸手术》(Touch Surgery)是一款临床智能手机程序,其通过模拟腹腔镜术、股骨髓内钉术、肌腱修复术等常见外科手术,为医生及医学生提供虚拟的临床实践机会。该游戏对现实手术的拟真使游戏难度无限接近于真实手术,其低廉的游戏成本也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培训成本(Kowalewski K F & Hendrie J D & Schmidt M W.et al, 2017)[22]。在《瘟疫公司》中,病毒发源地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程度、医疗救助水平、政府防控力度都会对游戏结果产生极大影响,而这需要玩家对各国情况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与此同时,病毒的发病症状、传播途径等特征都会对政府的防疫政策造成影响,因此,玩家还需对医学知识及人体结构有所了解。复杂的玩法使这类医疗游戏对玩家发出更强烈的“享乐”与“获胜”律令,在这种“成功欲望法则”规训下,玩家不断调整游戏策略,连“氪”带“肝”。
再次,医疗游戏还承担着心理学意义上的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功用,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叙事治疗是一种心理疗法,即通过邀请看诊者讲述自我与他人的生命故事[23],让人们看到自己面对的问题深具社会建构的面向。通过“问题的外化”,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只被问题牵着鼻子走,他们也有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就这层意义而言,医疗类严肃游戏将现实中的瘟疫作为游戏叙事背景,玩家作为医生、政府、辟谣者、科学家等角色参与到游戏中,在多元的游戏故事线中,玩家不同的游戏操作会导向不同的游戏结果。由此,玩家从游戏中的享乐者变成居安思危的建设者,从旁观者转向积极的参与者。
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系列医疗游戏便跳脱可玩性的框架,用极具克制性的游戏叙事为玩家讲述真实故事。交互式游戏《逆行者》通过病人、医生及医生家属三个视角,描述了疫情中不同个体的遭遇;《真相战纪》则将疫情中的谣言拟人化,玩家在游戏中采取的不同策略都能决定谣言“诓”的形态。这类游戏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玩家(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在极具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也许我们不是研发疫苗的科学家,不是奋战一线的医生,不是能在一夜之间消灭瘟疫的“超能力者”,但我们也绝非游离在游戏世界中束手无措的光标与建模。在医疗游戏的世界中,每一位玩家都能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审视瘟疫,用个人的能力对抗瘟疫,并在充满克制的疫情叙事中拥抱现实社会中的人性与温情。
实际上,疫情叙事(outbreak narrative)作为疫情文化(Pandemic culture)的关键部分,是学界在剖析疫情背后的文化现象的重要视角。其作为一种被建构的话语,一般伴随着对个人、群体、种族的污名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着社会对传染病的态度(Mitchell S & Hamilton S N, 2018)[24]。这种疫情叙事在涉及瘟疫题材的医疗游戏中尤为重要,究竟是通过直白、无情甚至夸张的叙事方式模拟疫情的残酷性,还是通过叙述疫情背后的个体故事呈现疫情残酷性下的人性温暖,这构成此类游戏两种不同的叙事策略。与《瘟疫公司》的叙事策略不同,《逆行者》与《真相战纪》按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间线梳理游戏情节,并将疫情期间出现的故事、图片融入游戏叙事中,从而在游戏中更加克制、温暖、真实地讲述疫情。游戏设计者在《逆行者》中设计了三条平行的故事线:不幸感染的患者、在前线“战斗”的医生以及医生背后的家人。该游戏正是通过这三个视角娓娓道来疫情背后的故事。医生进入诊室前在防疫服上画上笑脸,独自在家的妻子看着与此时正在一线的丈夫的合照,疑似患者们在深夜里等候检查与治疗,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因病重晕倒在地的患者,老爷爷在得知能够出院后说“终于能看见老伴了”……一个个取材于现实故事的剧情使这款游戏有了一种“日记”的色彩,人文向度与个体视角的游戏叙事方式极大地增强了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代入感,玩家们将个人经历与意识代入游戏过程中,并个性化地解读游戏情节。与此同时,游戏内容饱满的感情降低了玩家对游戏可玩性的要求,也将以往严肃游戏残酷的叙事转向一种温情叙事,从而使玩家在感知疫情残酷之同时,也从中获得精神的疗慰。
最后,分析医疗游戏时,不能忽视游戏设计的视觉、听觉符号维度——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在商品消费活动中,符号(词语、图像)与指涉物(物品、功能)之间发生了断裂,决定双方之间关系如何重构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欲望。那么在严肃游戏当中,在游戏设计者希望重建游戏符号系统与现实关联的过程当中,如何维持玩家的欲望呢?
本文所关注的医疗游戏给出了积极答案,它们将存在于疫情中的病毒、谣言、重要人物等要素符号化与可视化,从而将现实世界的元素与游戏世界巧妙缝合,为玩家制造更具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在《真相战纪》里,疫情中的谣言被拟人化成美男子“诓”,每当“诓”出现时,游戏界面的主色调就会变成代表危险的黑色与红色(图2),强烈的反差色调带给玩家一种压迫感,谣言在疫情期间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在这一视觉符号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游戏中,“诓”的形态会因谣言在社会中的传播及影响程度发生改变,当整个社会被笼罩在谣言的阴霾下,“诓”就会变成一个个巨大的黑影隐匿在每个人身后,这也隐喻了疫情期间谣言四起的情形。

图2 谣言的拟人化形象“诓”
在《逆行者》中,许多在疫情期间有着重要意义的符号都被作为游戏叙事的重要元素。例如在防护服背后的笑脸是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们相互鼓舞、互相辨认的标志。现实中一个个深入人心的事件被设计成游戏中重要的视觉符号,共同书写游戏背后鲜活的生命故事,呼唤玩家们关注现实世界。
三、享乐范式与超越:医疗游戏的极限
综上所述,电子游戏向来不只消遣娱乐这一个功能,以医疗游戏为代表的严肃游戏反映了人们对电子游戏的新想象。本文提及的几款医疗游戏,其教育、说服、警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电子游戏中的娱乐范式,人们不再单纯地关注从游戏的可玩性中获取的愉悦情感体验,而开始在游戏叙事中怀抱现实世界。这种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糅合的趋势与移动设备的发展不无关系。手机游戏的移动性打破了以往主机游戏对于玩游戏的地点与游戏世界的严格关联(Stenros J, 2015),数字化、移动化改变了现实世界与游戏世界的连接关系,我们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言的“拟像”的最终阶段(Baudrillard J, 2005)。而在如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下,鲍德里亚认为的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步之遥”亦逐渐不复存在(Coulter G, 2007)[26]。游戏活动的流动性使社会的每一角落都能成为玩家的游戏空间,游戏实践与玩家的日常生活、社会互动与文化语境缝合在一起(Richardson I, 2011)[27]。由此,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发生内爆,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被打破,人们在游戏空间与城市空间中穿梭,在虚拟与现实暧昧不明的界线中观照现实世界,成为了游戏世界中的“社会人”,现实世界中的“游戏人”。
在结束本文的论证前,还需谈谈医疗游戏的极限。
第一,在模拟真实世界的规则之时,鲍德里亚认为游戏比现实世界更平等、严肃,也即前文所引“Games are serious, more serious than life”。在这里,经济能力、种族、阶级等因素不是划分玩家等级、优劣的标尺,每个玩家都能“升级”“通关”,也会因“卡关”而失败。游戏规则与游戏机制成为游戏世界唯一的“法律条文”。然而,本文指出,游戏空间在现实中是一种“异托邦”式的存在,游戏里的玩家可以颠覆日常生活空间约定俗成的“节奏”与“韵律”,重回到起点,可以迅速升级、进化,不断提升完成任务的技能,任意地使用前人制作的“攻略”获取胜利。但人类在时间的一维性及不可逆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可以,多少医务专业人士与政客想回到2019年早冬的武汉!),现实的生活没有攻略,没有捷径,也没有重新载入,我们只能在在由分秒日月年组成的时间规则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也即,鲍德里亚所说的游戏玩家可以不停试错而达到成功的这种机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医疗游戏中的升级、胜利机制或许会使玩家沉浸于“一步登天”的想象,忽视了瘟疫背后高昂的试错成本。
第二,尽管医疗游戏试图将忧郁的色彩引入游戏,但游戏题材的严肃性、残酷性等可能会被游戏的狂欢遮蔽。尤其当玩家与游戏所呈现的瘟疫之间的现实距离较远时,他们易沉浸于游戏机制的挑战性所带来的情感满足,而忽视游戏背后所呈现的复杂社会症候。只有当瘟疫真正发生后,即在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灾难事件重合时,玩家才会开启对医疗游戏的严肃性的感知能力,传染病威胁及死亡恐惧才会取代其可玩机制为玩家带来游戏快感。在此意义上,尽管游戏将瘟疫中人性、死亡的残酷呈现在屏幕中,但这种残酷是有限度的。
第三,医疗游戏始终要面临对其游戏性(playfulness)的责难,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如果它过分真实,人们就会失去热情。比如,相比严格意义上的游戏,《逆行者》与《真相战纪》更像是一部讲述疫情背后故事的纪录片。如果用公共性对其进行评判的话,它们无疑是成功的。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从中窥见疫情时期更多的“逆行者”以及“普通人”,亦可从中学习相关的防疫知识。例如,在《逆行者》中,当病重的患者查看体温计,玩家需要左右滑动游戏按钮以调节画面清晰度(图 4)。这种从模糊、重合逐渐走向清晰的游戏画面,模拟了感染者在疫情中的发热、眩晕等症状,从而增加了玩家对新冠肺炎症状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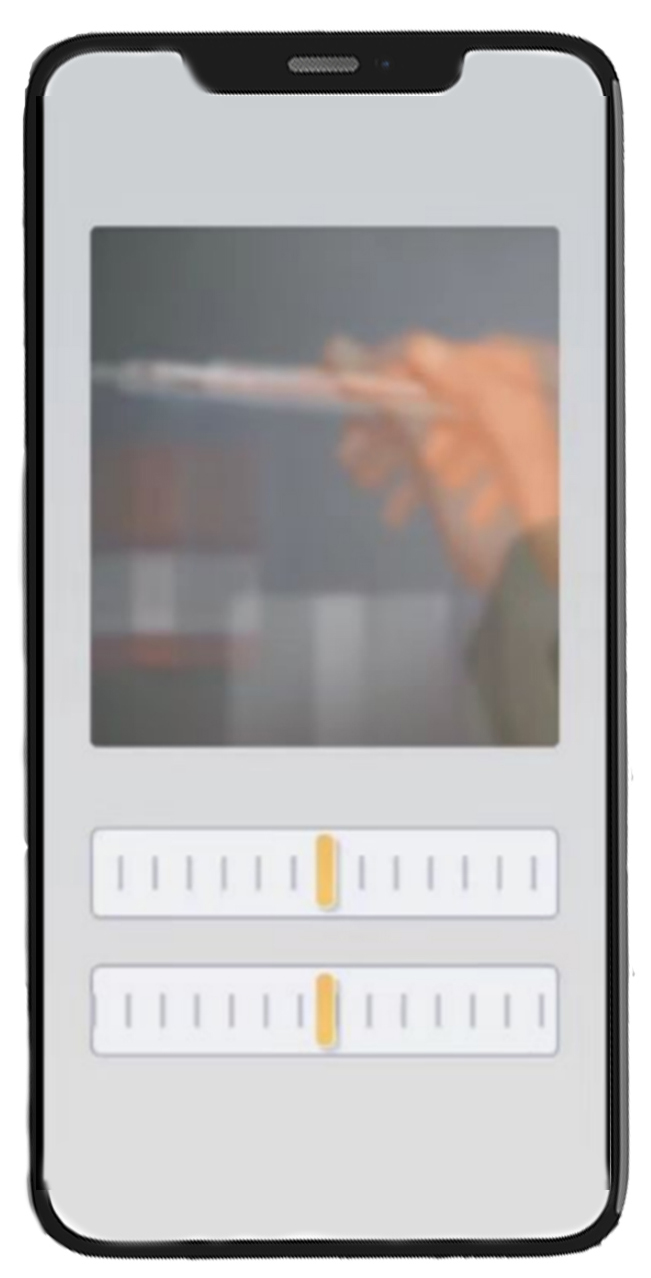
图三《逆行者》的游戏界面
然而,如果从游戏的可持续性以及营利性标准考虑,这两款游戏显然不及兼具挑战性及教育性的《瘟疫公司》。在《逆行者》中,简单的交互形式构成该游戏主要的游戏机制。洗手、测量体温、佩戴口罩、擦拭照片等重复、琐碎的行为则是玩家在游戏中的主要任务。二十分钟的游戏通关时长压缩了游戏的叙事空间,单薄的游戏剧情、简单的交互机制、幻灯片式的游戏文本削减了游戏的可玩性,也降低了玩家们再次进行游戏的欲望。
不过,尽管当下的医疗游戏仍有弊端,但这类游戏对严肃性、公共性、专业性的讨论,的确打开了我们对游戏的理论与实践的想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游戏。在游戏的“超真实”趋势下,现实世界被游戏世界反噬,我们在游戏世界中获取的认知逐渐入侵现实世界,并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医疗游戏为玩家带来的知识、恐惧亦或感动,都在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对个人、社会的认知框架。在这种享乐与严肃、可玩与不可玩的高度关联中,游戏的享乐与严肃范式间的矛盾被削弱了。游戏的享乐既可以是游戏机制上的趣味,亦可以是游戏内容本身;游戏的严肃既可以是现实症候的残酷展现,亦可以是温情叙事中的共鸣与感动。此时,医疗游戏为人们叩开了亦真亦幻的游戏世界的另一扇大门,而对于电子游戏应用边界的思考与想象,才刚刚开始。
注释:
[1] Baudrillard, J. Seduction. Montreal, Canada: New World Perspectives. 1979.
[2] Baudrillard, J.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M. Gane, Ed.). London: Routledge. 1993a.
[3] Abt C: Serious Gam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4] Alvarez J, Djaouti D,“An introduction to Serious game Definitions and concepts.”Serious Games & Simulation for Risks Management, 2011, Vol.11, No.1, p.11-15.
[5] Sliney A, Murphy D. JDoc, “A serious game for medical learning//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IEEE, 2008, p.131-136.
[6] Poplin A, “Digital serious game for urban planning:B3—Design your Marketplace!”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14, Vol.41, No.3, p. 493-511.
[7] Whitson J R. Foucault’s fitbit, “Governance and gamification.” The gameful world: Approaches, issues, applications, 2014, p.339-58.
[8] Schrape N, “Gamifica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2014.
[9] Steffen P. Walz; Sebastian Deterding, "Game State? Gam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Gameful World: Approaches, Issues, Applications , MIT Press, 2014, p.501-512.
[10] Mitgutsch K, Alvarado N, “Purposeful by design? A serious game design assessment framework”,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undations of digital games. 2012, p.121-128.
[11] 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12] Galloway, A. R. Radical Illusion (A Game Against).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4, 2007, p.376–391. https://doi.org/10.1177/1555412007309532
[13] Baudrillard, J.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New York: Verso. 1993c, p,67;该诠释亦参考Coulter, G. Jean Baudrillard and the Definitive Ambivalence of Gaming.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4, 2007, p.358–365.
[14] Coulter, G. (2007). Jean Baudrillard and the Definitive Ambivalence of Gaming.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4, 2007, p.358–365.
[15] Stenros J, “Behind games: Playful mindsets and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The gameful world: Approaches, issues, applications, 2014, p.201-222.
[16] Baudrillard, J. The perfect crime. New York: Verso. 1996.
[17] 周思妤.从“氪”到“肝”——从《阴阳师》看卡牌收集养成游戏的意识形态策略.文化研究, 2019(03), p.180-191.
[18] Sliney A, Murphy D. JDoc: A serious game for medical learning//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IEEE, 2008, p.131-136.
[19] Mitchell S, Hamilton S N. "Playing at apocalypse: Reading Plague Inc. in pandemic culture. "Convergence, Vol.24, No.6, 2018, p.587-606.
[20] Baudrillard, Jea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21] Mitchell S, Hamilton S N. "Playing at apocalypse: Reading Plague Inc. in pandemic culture. "Convergence, Vol.24, No.6, 2018, p.587-606.
[22] Kowalewski K F, Hendrie J D, Schmidt M W,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mobile serious game application Touch Surgery™ for cognitive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of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J]. Surgical endoscopy, Vol.31, No.10, 2017, p.4058-4066.
[23] Gallant, P. Michael White: In Memoriam: Therapist, Teacher, Innovator.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Vol.34, No.4, 2008, p.427-428.
[24] Mitchell S, Hamilton S N. "Playing at apocalypse: Reading Plague Inc. in pandemic culture. "Convergence, Vol.24, No.6, 2018, p.587-606.
[25] Baudrillard, J.The intelligence of evil or the lucidity pact. London: Berg. 2005b.
[26] Coulter G. Jean Baudrillard and the definitive ambivalence of gaming[J].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4, 2007, p.358-365.
[27] Richardson I, “The hybrid ontology of mobile gaming.” Convergence, 2011, Vol.17, No.4, p.419-430.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