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易大经︱1月读书记
《壮岁集》,陈凡著,香港何氏至乐楼丛书之三十四,1990年印

《壮岁集》薄薄的,仅五十一页,收旧体诗一百余首,词十二首。大抵和他那辈的文人作家会写毛笔字一样,旧体诗也属于必修课,然而究竟有没有成就,还要看诗人的天分与兴趣。这部诗集最为豪华的是序跋阵容:依次由出版方至乐楼何耀光、钱钟书、饶宗颐三人写序,黄裳作跋,能让后三位一起“站台”的待遇,可能陈凡之后无人享受了。
马文通先生还送了我一本香港作家也斯的《记忆的城市 虚构的城市》,这两本书都是茶叙中我提到比较感兴趣的,实在感谢。我还他一册《日本古典俳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诗苑译林”丛书之一,扉页上有“马文通藏书 1984.10.3购于广州北京路”字样,并钤盖“马文通藏书”朱文方印(书上还有一行我写的“〇五新年东川路旧书店” )。其实十多年前,在广州淘书的人对这个藏书标记应该不陌生,记得友人张晓舟也买到过,还写了文章。但大家都不知道马文通即翻译过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布罗茨基等俄国文学名家的马海甸先生。后承马先生见告,当年祖屋失窃,自他青年时便开始搜集的藏书才会散见于广州各大旧书店,他每次回广州也会淘一些。我买到也是一种书缘,附记于此,算是记录此地书林的“一段小沧桑”吧。
《忘山庐日记》(上下),孙宝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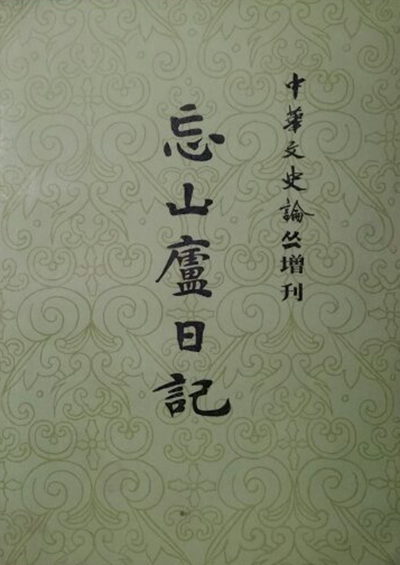
宝瑄的父亲诒经曾任光绪朝户部左侍郎,哥哥宝琦先后做过顺天府尹和驻法、德公使,入民国后做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岳父则是李鸿章的哥哥瀚章。但他的仕途似乎一般,历任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主事,见证了邮传部成立前后的种种变化和风波,比如尚书三天两头换一个,下面的人当然无所适从。岑春煊做事雷厉风行,宝瑄很是欣赏,可惜马上又被朝廷调去了四川。最后待下来的尚书陈玉苍,与他尤其不相得,一度搞得他要辞职。
宝瑄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性喜读书,他的这部日记,最早命名为《梧竹山房日记》(“林鉴唐名其斋曰竹柏山房……而余斋前有梧、有竹,因亦自颜曰梧竹山房”),后改今名(读《永嘉禅师语录》“余因自号忘山居士,名其庐曰忘山庐”)。他天天读书,甚至连去上班的路上(坐轿子里)也在读,不仅读中国书,还读西洋书,做大量的笔记,发大量的感想,所以他的这部日记内容实在庞杂得很,个人精神、物质世界的记录都保留了,是很好的研究样本,可以见到晚清民国间的知识分子看西方和救亡图存的内心世界。
宝瑄爱写诗,格调高古,与晚清诗人们的积极用事有区别。他有诗描写当时的新潮事物,如咏德律风、自来水等,也是一时风气,不独他一人(夏敬观便以五古咏飞机),但他大部分的诗,都有魏晋人气质,比较旷达,如和陈玉苍顶撞后,便写了好几首,大有排遣寄托之意。他的日记,写景状物,描摹宛如小品文,可见他的文学天分(郑孝胥的日记也有此特点,确是文学大家),谈诗论艺,每每也有自己的看法。宝瑄据说被评为晚清四公子(历来说法不一,此为余绍宋记载,四人为丁惠康、谭嗣同、陈三立、孙宝瑄),他身上确实有点二代的戆气,除了不太鸟上司外,又如动辄称自己的哥哥为“邻居”。日记里有些地方也挺魏晋范的,如:“晡,至厂肆,欲购《中西度量权衡表》未得,在会经堂见有贩骡来者,肥健可爱。”这个人是不是也很可爱?
去年读《郑孝胥日记》,经常见到有“慕韩(按,即宝琦的字)来”的记载。现存《忘山庐日记》里有两处提到郑孝胥,均非交往记录。有意思的是,一度与郑孝胥谈婚论嫁的名妓金月梅,宝瑄也是其粉丝之一(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粉丝、郑孝胥的情敌,是周一良的叔祖周立之),有十八处之多。宝瑄第一次记金月梅,在辛丑年(1901)三月三日(巧的是,也在这年,郑孝胥三月十四日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金月梅),有次宝瑄在楼下,听到金月梅在楼上鞭笞养女,不下来见他,十分生气,拂袖而去。最后一次记载已是1908年,在山海关附近偶遇。他对金月梅评价不算低:“月梅人极伉爽,善应对,落落有丈夫气。”不过金月梅后来这三个人都没跟。
中华书局的点校者序言里提到上古版出版较早,学界关注较多,并做出了许多成绩云云。一时手痒搜索了几篇,其中一篇谈宝瑄与友人邵二我的关系,罗列了邵出现多少次,每次大概谈什么(像我这样,呵呵),而对邵是个什么样的人,生平如何,却没有介绍。还有一篇写孙宝瑄喜欢看杀头云云,只引了一则,其实孙宝瑄日记里有两则提到杀头。然而是否可以归为他喜欢看杀头呢?
《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

另外一册即《林纾家书》。林纾给几个儿子的信,简直操碎了心,并非儿子都不成器,而是他的面面俱到细心体贴语重心长,跟今天做父母的很像。中国人的诫子书,并非一律板着面孔,也并非只有《傅雷家书》一部洋溢着父母之爱。他叮嘱儿子林璐在学校要记得“落后”,这个思想很有意思。不愿意参与社会运动,固然体现他的保守风格,但他看重一心做学问,不也很值得尊敬吗?可惜的是,他谆谆教诲的这个儿子,最终也没有继承其衣钵,在给另一个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林纾已经放弃这个晚上带着老婆出去看电影的年轻人了。
林纾家书的注解中提到了陈璧,即孙宝瑄的顶头上司陈玉苍。陈氏为福建侯官人,与林纾为世交:“陈纪为玉苍伯世兄,汝当加意和睦,不可口角失欢。彼此为世兄弟,即同手足也。”民国后陈璧寓居北京,林纾家书还透露了当年陈璧的一件惨事。陈璧侄儿陈绳寓居陈府,辛亥革命起,陈璧避居天津,给陈绳管家,结果管得太严,被其仆人董氏杀害,嫁祸于陈璧父子:“陈玉伯之侄伯台(陈绳之字)被人杀死,投尸井中。刻尸已起出,外间谣言,咸谓为玉伯所杀。刻下巡警、侦探日五六人将玉伯守住,不知起诉后如何。年老遇此奇惨之事,殊可悲也。”(1913年11月25日信)后来林纾写信给军政要人徐树铮申诉此案,加上陈家请了黄远庸等律师,陈璧父子终被无罪释放。孙宝瑄卒于1924年,但他的日记仅保存至三十五岁那年(1908),对老上司的这件奇案,不知这位至情至性的公子会在他无所不包的日记里作何评价——最早的1893年的日记里,便记录了二周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舞弊案被定监斩候一事。
《缪钺先生学记》,缪元朗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