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吗?
原创 陈嘉映 理想国imaginist

我们能否理解他人的痛苦与快乐?
每当面对“感同身受”的问题,都会想到鲁迅先生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很多人借这句表达人与人之间难以理解彼此感受的隔膜和疏离。然而,鲁迅先生还写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关”其实就是一种共情力,人们可以通过这种联结感知彼此的苦难,并做出回应。毕竟,如果不能感同身受,为何疫情流调里“最苦的人”,能引起我们深切的关怀?面对遭受网暴的少年,我们也会感到愤怒和痛心?
我们可以用哲学中的“他心”问题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感同身受。“感受”是一种玄妙难以细致描绘的东西。这就好像当一个人说梨子酸的时候,其他人真能感觉到同样的酸吗?每个人感受到的酸是否一样?他心问题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问题,也是思考与他人关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哲学家陈嘉映在新近思考力作《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中,就他心问题展开了探讨,是“人同此心”还是“人心隔肚皮”?理解他心问题这个悬案,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所处的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可以了解他人的感受吗?
节选自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01.
感受不同于甲虫
单簧管的声音,我不是完全不能描述,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单簧管的声音饱满圆润,我承认,饱满圆润没说出很多,但多多少少说出了一点儿。同样,我告诉你梨子酸,这也是在描述它的滋味。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甲虫,形状、大小、颜色、斑点。一般说来,视觉印象可以描述得很细,味觉、听觉描述起来比较困难。你说这种咖啡很香,怎么个香法?你说是浓香,似乎仍然离说清楚还差得很远。我们会想,这是因为我们的视觉词汇格外丰富、味觉词汇太贫乏了,如果多造出一些味觉词汇,我们就可以像描述视觉一样来描述味觉了。就像我们用整数说不清 6.4 是多少,我们发明了小数,我们就能够说清楚了。
维特根斯坦列举了三个可说不可说的例子,接下来就问:那我们为什么不多造出些词汇来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这么想就想偏了。你多造语词就能说出来吗?我后面会说明,语词不是造出来跟世上的东西一一对应的,世上的物件、品样无穷无尽,我们的语言却容不下太多的语词,如果我们有一亿个词,这种语言就无法工作了。这是个 assertion,我没做论证啊,当然,可以论证,论证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但我们没有时间每一点都做论证。是的,感知十分丰富,哪怕吃一口梨子、喝一口红酒,更不用说坐牢的那种经验,细说起来都极其丰富。但我们不是靠多造词汇来应对这种丰富性,而是靠有限词汇的无限组合来表达。这等于说,我们在理知的层面上来表达感性内容。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造出多少词汇,问题在于,描述单簧管的声音和描述甲虫有一点根本的不同之处。我们说过,在谈论我们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并不是在谈论感觉,而在其他感官那里,你很难脱离感觉自身来描述感觉到的东西。你说梨子酸,这是在描述感觉吗?抑或你是在描述梨子这个对象的性质?好像都是。反正这不同于说这个梨子半斤重,或者勃朗峰高 4810 米,酸是梨子的性质,但这个性质你非得通过亲身感知才能知道,这种性质总是连着你的感知。
你描述甲虫的时候不是在描述感觉,“描述感觉”指的是描述梨子的滋味、单簧管的声音之类,你说到酸,说到音色,是连着你的感觉说的。你无法脱离了感知来描述酸本身——除非你在谈论化学。描述得更细帮不上什么,不管我给你讲述多少坐牢的细节,你似乎仍然不能真正体会坐牢是什么感觉,再增添多少细节似乎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问题不在于造出更多词汇,不在于描述得细不细。我可以告诉你梨子酸,你说,是,梨子酸,可是那是个什么酸法,那我就接着告诉你,果酸那种酸,不是醋酸那种酸,接下去,我还可以描述得更细一点儿。再说了,你说勃朗峰高 4810 米也一样啊,你没有告诉我零头,也许勃朗峰高 4810.154 米,这之后还可以量到微米、纳米。事情似乎正好相反,你说得更细,告诉我梨子的酸度是多少,反而离感觉更远了。你变得客观了,但离开感觉更远了。你描述甲虫的样子,就像你描述这个盒子是方的,你是在描述你感知到的东西,不是在描述你的感觉,这么说吧,你是在描述感觉到的对象,而不是你的感受。你问:感觉能不能传达?你实际上问的是语言能不能传达感受,而不是能不能描述感知到的东西。
那么,语言能不能传达感受呢?我们可能想,既然我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我就可以把它描述出来,就像我要是知道一只甲虫长什么样子我就能把它描述出来。但你也可能跟着维特根斯坦说,不对,感受不是对象——你描述不清你盒子里的甲虫,你可以打开盒子把甲虫拿出来给我看看,可是你描述不清你心里的感受,无法打开心扉把感受拿出来给我看看。所谓掏心窝子、打开心扉,靠的还是言说。

而我要说的恰恰是,言说感受和言说甲虫是两个大不相同的语言游戏。甲虫放在那儿,我们看,我们描述,不管看得仔细不仔细、描述得适当不适当,这都跟它是谁的甲虫没关系。甲虫是个外部对象,外部对象跟谁都不连着,感受却总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把你的感受端出来,无论怎么端,包括用语言端出来,它就变得跟一个对象似的,跟你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了。无论你怎么描述,你都只能把它作为 what 来描述,所以,感知到的东西也是在理知的层面上成形。你能够描述出来的,永远都是理知化了的感受。所以,你无法把感觉作为感觉说出来。
就好像感觉是扎根在你的心里的,一旦说出来,就把感觉拔出来了,怎么都没说出那种切身性,你要是一心想说出感觉本身,说出那个 thatness,你可能会非常沮丧,不管说了多少,总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说到感觉的丰富性和切身性,要是只说这两样,我会说,成问题的不是丰富性,而是切身性。世界也无穷丰富,但只有要言说心里的感觉的时候,才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言说世界的时候就没有。
维特根斯坦说感受不像甲虫,说得非常对,也非常重要。但这里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感受不是对象;另一件事是,你要是去描述感受,你只能像描述对象那样去描述。正因为这里有一个矛盾,结果,无论你怎么描述、你描述得多细,我似乎还是不能把捉你的感受。
02.
我们可以了解他人的感受
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别人的感受了吗?也没那么邪乎。你说你胃疼,我就知道你胃疼,而且大致知道你感觉到的胃疼是什么样子。你站在十米跳台上,说,我好害怕,我就知道你害怕,不仅在理知层面上知道你害怕这个事实,而且大致知道你害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怎么知道的?很简单,因为我站在那儿也害怕。单簧管的声音饱满圆润,这话没告诉你很多,但你要常听单簧管,他一说你就知道。你给我讲你坐牢的感受,我说,哦,我太知道你的感受了。什么时候你最信我这句话呢?我也坐过牢,我有过类似的感受。“你没经历过就不会真正知道坐牢的滋味”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你坐过牢,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我说梨子酸,你明白了,你吃过酸梨子,或者酸杏什么的,如果你没吃过任何这类东西,我说梨子酸,你还是不明白,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感知。
你说你感到悲伤,我理解你的悲伤,那是因为我和你是差不多的人,如果你的整体思想感情跟我不一样,我就无法理解你的悲伤。你不难了解一个跟你相似的年轻人的心理活动,但你很难理解商朝人是怎样感受这个世界的。当然,我们更难知道狮子是怎么感知这个世界的,或者蝙蝠是怎么感知这个世界的。内格尔那篇名文问蝙蝠感知的世界是啥样子,这个问题不是内格尔第一次提出来,这是个古老的问题,惠子在濠梁之上就问过庄子鲦鱼是否能感知快乐,但内格尔在一些当代问题的上下文提出来,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
咱们两个看到一只蝙蝠,我能够想象你看到的跟我差不多,但我无法想象蝙蝠眼里的世界,这么说吧,你不管跟我有多大差别,咱们两个都是用眼睛看,而蝙蝠是用超声波来看,超声波“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怎么用超声波来确定远近、确定形状?这个咱们无从想象。当然,不能从这里倒推,要是你不能了解蝙蝠怎样感知世界,你也就不能了解我怎么感知世界,于是,他心问题就永远成了一个悬案。

心智哲学里有个所谓“知识论证”:你获知了关于痒的所有非心理方面的知识,你仍然不知道痒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有一个 Mary,从小生活在一个密封屋子里面,这屋子里就黑白两色,没有其他颜色,她掌握了一切物理学的知识,她知道红颜色是多少光频、绿颜色是多少光频,命题知识她统统知道。终于有一天,门开了,她走到外面,看见花红柳绿,她能认出那是红颜色吗?
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物理公式,这个设定有点儿夸张,其实问题很平常:你没吃过酸的,人家给你形容一番酸是个什么滋味,你是不是就能知道酸是个什么滋味?有人说能,有人说不能,你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站在哪一方,Yes or No ? 无论你站到哪边,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前人也提供了不少理由来支持你。
电脑人最后能否有感觉、有意识,面对的也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引进另外一两个视角才能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但我告诉你我站在哪边,我会说:你得尝过酸东西,别人告诉你梨子酸,你才能知道怎么个酸法。物理公式没办法教给你感觉。我知道你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感到过,而且也知道你跟我差不多。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差不多?是啊,你自己想想,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跟你像不像的?当然是从他的举止进退知道的,也从他的言说知道,包括他对自己感受的言说。我知道另一个人跟我很不一样,也是这样知道的。
你们听出来了,我这里讨论的是个老话题——他心问题。我能不能知道另一个人心里的东西?人们为此争得不亦乐乎,一方说,不能,人心隔肚皮,我永远无法知道你胃疼,最多是在猜测你胃疼;另一方说,能,你捂着肚子龇牙咧嘴,这种种表现就是你胃疼。在我看来,争论双方似乎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都把世界简单区分为我和我之外的其他一切。你也许可以这样谈论先验自我,但经验自我不是这样子的。并没有对话纠缠之外的自我,直到有了自我意识,人才变成孤独的人,在自我意识之前,人并不孤独。

他者也不是一式的,你和他不同,你和我是对话者,不是完全的他者。知道一个他人的感受,不同于知道蝙蝠的感受。你饿的感觉大致就是我饿的感觉,我家小猫皮皮饿的感觉可能有点儿不一样,但也差得不多。但蝙蝠饿是什么感觉我就不大知道了——蝙蝠和我实在没太多相像的地方。但这也看你要说什么,鲦鱼在水里游来游去自由自在,你一跺脚它们立刻惊散了,你于是知道它们感到自由自在和受到惊吓的区别。我可能讲得比较乱,概括一下吧,我怎么知道我感到的酸就是你感到的酸?其一,我必须感知过酸;其二,你我方方面面都差不多。
03.
需要自己先有感受
然后连着他那个人了解他的感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是你我在十米跳台上的感觉差不多,那就用不着你说什么,我也知道你害怕。那么话语不就多余了吗?我看你重重撞到石棱子上,鲜血直流,龇牙咧嘴,你啥都不用说,我自然知道你疼。
大多数时候的确是这样。不过,人和人不一样,也许你一贯胆子大,也许你是个跳水老手,我害怕,你不一定害怕,于是我要问问你,你说害怕,我想,原来跳水老手也会害怕,你说不害怕,我想,跳水老手是不害怕的。我是个跳水老手,根本不害怕,但知道你会害怕,因为我曾经也害怕来着。当然,我也可能把当年的感觉忘得精光,看见年轻人热情洋溢地为理想奋斗,完全不能理解了,也许,在智性层面上能够知道,甚至能够预言他将如何如何行动,却感觉不到年轻人心里感到的东西了。我们是会忘的,只是别忘个精光就好。
我们前面说过,感知有一种切身性,就是说,感知与感知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听人说他的感受,总是连着感受者来听的。感受总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所以,要听懂你对你的感受的描述,我不仅需要知道这种感受,而且得知道它是你的感受,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两个人都爱,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可能很不一样;两个人都苦恼,一个为政府腐败苦恼,一个为自己没捞到好处苦恼,苦恼的质地会很不一样。

传达心里的感受跟描述一个对象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我们小时候学习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区别这两类语言游戏。你领会另一个人的感受,靠的是将心比心,你自己就得有这种感受,或者某种类似的感受——“类似”当然也是个 slippery word,这里又引向想象力问题,但我们暂时不去管这些。你得有这种感受,然后你还要知道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能通过你吐诉苦恼直达你的感受,我从你这个人来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言辞更像是个辅助手段,引导我了解你的感受,“愁”这个字不刻画愁,你说你愁,可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有点儿像商场里的标志,指示电梯在哪儿,你站在标志对面,抱怨说,电梯长得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你傻掉了。同样的道理,梨子是酸的这句话并没有说出酸是什么味道,它像是一道桥梁,把你感到的酸和我感到的酸连起来。如果说的是更复杂的感受,那就要看讲述者的技巧了,技巧高超的作者能让没有坐牢经验的人多多少少体会到坐牢的滋味。
他心问题是个大题目,包括很多分支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我说梨子酸,你也说梨子酸,但我们怎么知道我感到的酸就是你感到的酸?也许这么问更清楚:我怎么知道你叫作 “酸”的那种感觉跟我叫作“酸”的那种感觉是同一种感觉?这么高深的问题,我当然处理不了,不过,你们听到这的时候,隐隐约约会知道要是我来思考这种问题,我大致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困扰哲学家,但好像不困扰小孩子,他们好像“天然”相信你说的酸就是他感到的酸。他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学会“酸”这个词,跟他学“苹果”这个词没什么两样,似乎并没有什么格外的困难。妈妈让他吃苹果,捡了个苹果而不是捡了个梨给他。他被玻璃划伤了,妈妈问他疼吗;被蚊子叮了,妈妈问他痒痒吗而不问他疼吗。他于是知道,疼是指被玻璃划伤后的那类感觉,痒痒是被蚊子叮了后的那类感觉。毕竟,妈妈指着苹果教孩子苹果,她也天然相信他看见的是个苹果,看见的不是头大象,虽然她也没有深入到孩子的感知中来查验他的视觉意象是什么样子的。
但妈妈怎么能断定人被蚊子叮了之后产生的是同一类感呢?她的确相信这个,但那也不是完全先验地相信。你简简单单主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能不行。因为很明显,我们刚才也说了,两个人面对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受,对我是西施虞姬,对你是嫫母夜叉。我看见西施浣纱,一心想凑到西施身边,也假装洗个汗衫啊什么的,可是鱼啊雁啊,一看西施过来都吓跑了。当然,我也有点儿知道它们的感觉,我看见巨灵神就是那感觉。这种例子满地都是,我就不多举。就说酸,你可能不觉得酸,我觉得酸得倒牙。
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妈妈很有道理相信大家的感觉差不多。既然人饿了都要吃,那么,人被蚊子叮了会有差不多的感觉,这似乎也没什么格外奇特的。还不止于此,幼儿被蚊子叮了会去搔痒,也愿让你为他去搔痒;被玻璃划伤了他不去搔,而是哭喊,你去搔他的伤口他不但不乐意,而且哭喊得更凶了。他被玻璃划伤了不哭不喊,无动于衷,妈妈触碰伤口他也无所谓,那妈妈要觉得古怪了,三次两次,要怀疑孩子患有痛感缺失症。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通常能够知道他心,从知道孩子伤口疼到知道阿庆嫂的心思,路漫漫兮。“人心隔肚皮”“此中最是难测地”,这些话大致都成立。一方面,生盲做手术张开了眼睛不能自动辨识出红的绿的;但没坐过牢的人却有可能知道坐牢是什么滋味,你不用去当小偷也可以多多少少知道小偷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你听奥德赛讲他的旅行,能够体会他的感受,但总不能完全像亲身经历那么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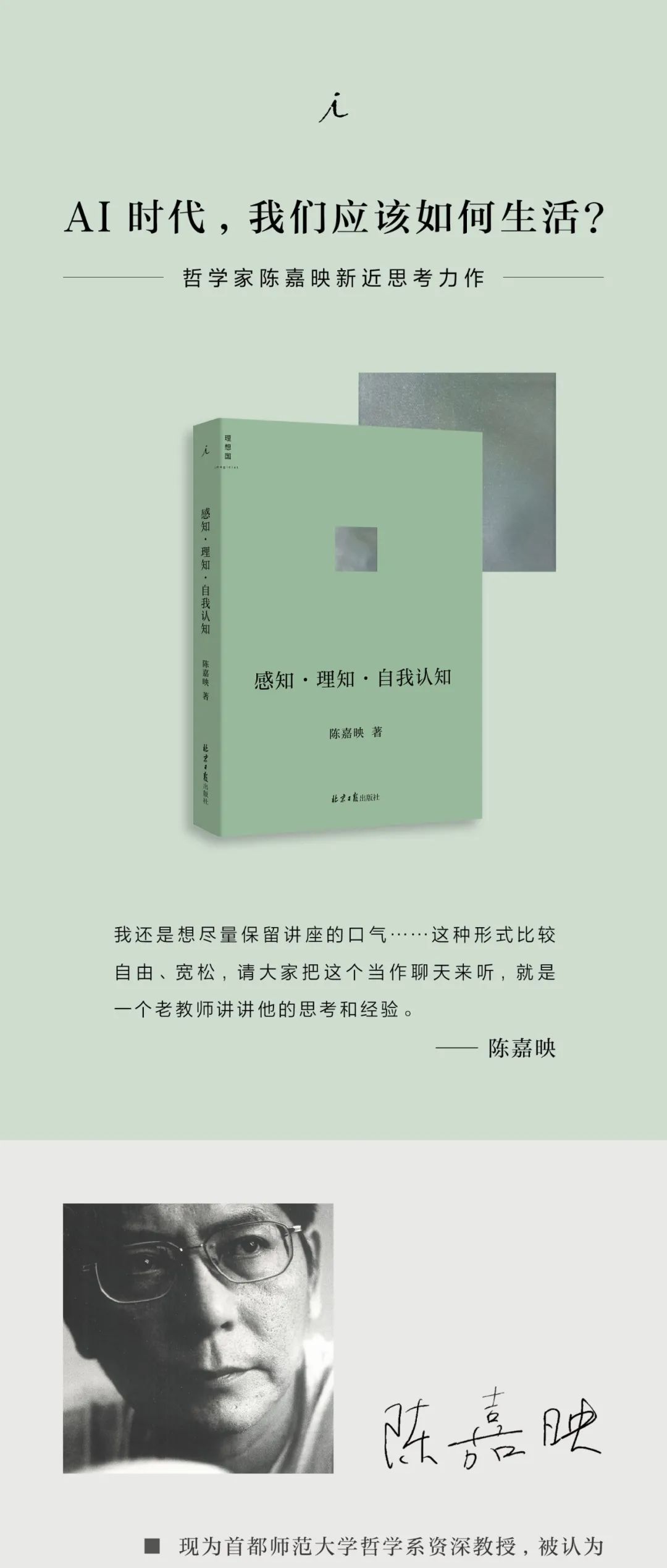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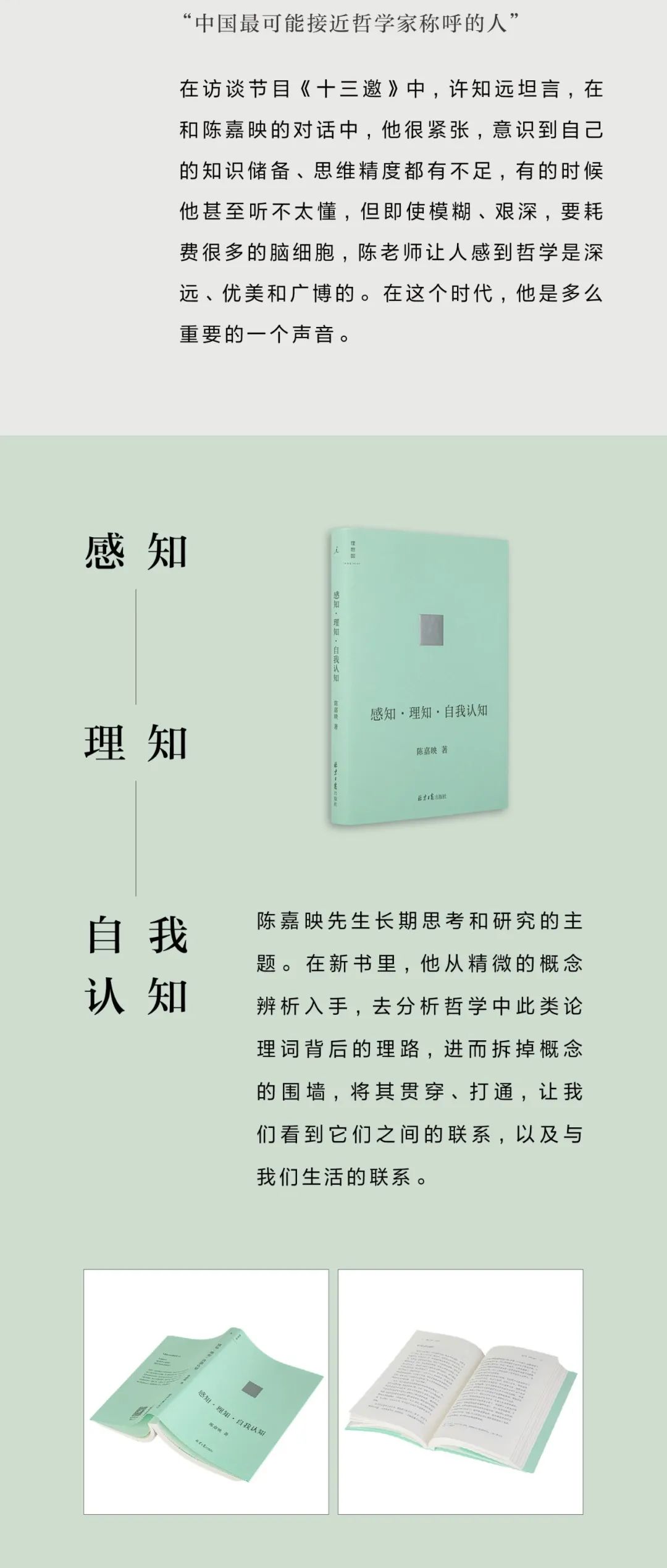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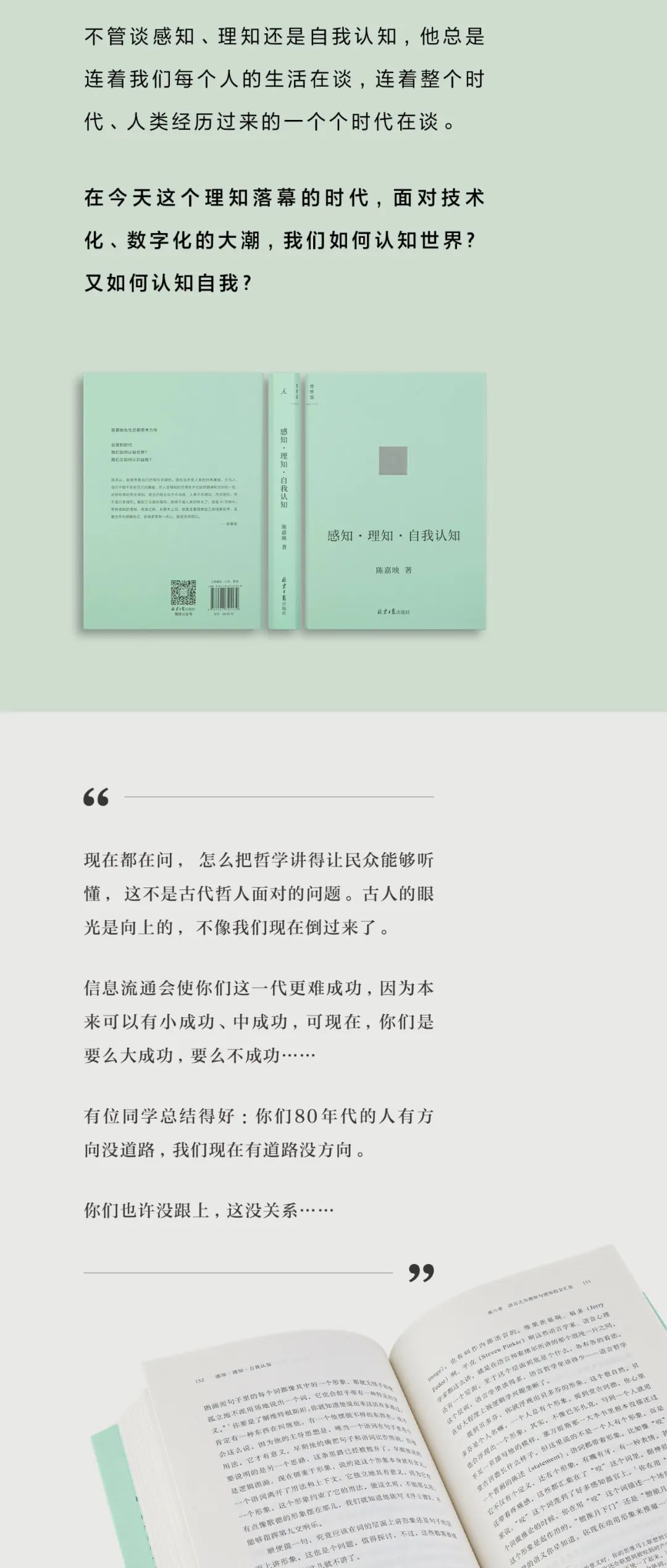
原标题:《“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