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家族志 | 失乐园,复乐园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编者按: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采访并文 | 王雅婷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编辑 | 林子尧
我在想:人在诞生之时就被预先放置在某个地点(就像上帝将亚当放置在伊甸园里),并依附于某个地点。在迁徙的过程中,人从原来的土地上剥离,又附着在新的土地上,从属于另一个地点,但土地不从属于人类。从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起,土地就不属于人类了。如果之后在别处重建家园,对迁徙者(如亚当与夏娃)而言,这不过是在流浪旅途上搭建栖身之所。但是对迁徙者的孩子(如该隐、亚伯)而言——这个他们诞生时被放置的地点——则是家。孩子们的第一个家。
我想问的是:在人类的迁徙途中,在土地的复得与复失的过程中,家如何依附于物存在,又超出于物延续下去?
家的超空间形式存在于代际之间的精神体验的传承。我想,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无论我们的人生轨迹如何不同,我们对家的记忆总是能追溯到出生时的那个家,因为我们都曾经是孩子。家的记忆源于子辈对父辈栖身之所的认识。
一:老房子

关于樗岚村旧村改造的新闻报道,人名标记为奶奶所写
人与土地的关系——丧失、迁徙、重建的情节在人类历史上不断迭代。我家的故事也可以从此展开,当我说起“我(最初的)的家”,我是指爷爷奶奶的家,被称为“老房子”的那个家。我的家在山东烟台莱山区海岸线边缘樗(chū)岚村。2005年之前,它被称为樗岚村,一块城市中的农村飞地。2005年经过旧村改造,它更名为黄海城市花园了。
我的爷爷家世世代代是樗岚村的,在当地算是新村望族。相传宋朝时有一个姓王的江南丹江人来莱州府做官,退休后留在了这里。这个村子的人都姓王我的爷爷叫王玉山;奶奶是从几里地外的南塂(jiâng)村嫁过来的,那个村的人都姓杨,我的奶奶叫杨明珠。当地有说法“樗岚王,南塂杨”,是指烟台莱山区这两个比较大的村子,樗岚村有世代经商的王家,南塂村是世代教书的杨家。爷爷奶奶自建的老房子是个平房,三厢房加一个大院子。小时候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老房子里。我由爷爷奶奶养大,老房子就是我的家。
我六岁的时候,旧村改造,老房子被铲平了。那时正是幼儿园毕业的暑假。
小时候,爷爷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光载你的小座椅就带坏了四个!”奶奶说)去海边看海王子。海王子是一个浅蓝色卡通形象的大型充气海豚,黄海游乐城的标志,它就站在游乐城入口处的喷泉水池里,神气活现。它的小马甲上写着“海王子”,我每天都要求去看它。我们穿过村子里的果园,沿着乡间小路,眼看旧村改造的高楼在老房子门口拔地而起。“啊,又到城市了!”小小的我坐在一摇一摇的自行车后座上,仰着头看高楼,天真无邪地感叹。要是散步完又回到家,我就会感叹,“啊,又到农村了……”爷爷也学我,“啊,又到城市了!”“啊,又到农村了!”两个人一路上如此,乐此不疲。
有一天,你说完“啊,又到城市了”之后,不会再接上“啊,又到农村了”。因为农村已不再存在。
我知道附近几家的邻居都搬到了高楼里,我的邻居们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爸爸对我说,我们要搬家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和妈妈、奶奶、爷爷搬到楼上住。我今天住老房子,把一些东西看守好,明天就都搬过去。
就这样被逐出了伊甸园。老房子被夺走了。
冬天,冰激凌般厚厚的雪堆在镇宅石兽的小脑袋上,厚雪也堆满了褐色的雪松,就在大门外。爷爷就会用厨房的炉子给我烤地瓜干吃,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烤地瓜干。
春天,爷爷带着我去苗圃串门。从家往东走600米左右。苗圃是村里果树育种、嫁接、扦插的实验基地,后来成为爷爷和同事养兰花和桂花的玻璃温室。苗圃里养了孔雀,闪着金光的蓝绿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跟孔雀一样高。回到家后一直用蓝绿色油画棒画画,直到把那个油画棒用完。
从家门口往西走300米,是井(传说有一位农村妇女曾在此投井),井上面是无花果树(另一位妇女曾在此上吊),再往西走,是桥,桥的下方小溪边有一排洗衣服的妇女,用棒槌锤衣服的声音是嘭嘭嘭嘭嘭——我喊“奶奶回家吃饭啦!” 就会有个脑袋回过头来——奶奶。
小时候我由奶奶带大。奶奶带孩子真是稀里糊涂,但又心急如焚。我记得在我不想上幼儿园的一天,和奶奶在床上玩游戏,我一下子跌下了床,后脑勺着地,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离我越来越远的床和奶奶吃惊的脸,随即一片漆黑。待我再睁开眼,已经躺在床上了。还有一次,闷热的中午,本来要哄我睡觉的奶奶却自己仰着酣眠,我爬到梳妆台上,好心把上面的水果刀合上,却掰着刀刃合上,刀刃切进手指,奶奶抱着我疯狂地往诊所跑,手上缠的布浸透血迹……
有天晚上,我仰卧在炕上的专属小窝里,两条小腿举在空中,脚丫贴脚丫,含着奶瓶咕咚咕咚喝奶。我一边喝奶,一边很专注地看着对面空白的墙,看着大人们忙来忙去,听见自己咕咚咕咚的声音,超然物外——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第一次意识到我在观察这个世界,而我在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自己。

黄海游乐城,90年代黄海城市花园的海滨旅游项目
葡萄架、小鹦鹉、门口的石兽、地瓜炉子,你们现在去哪了?也不见有人为你们送别。
是爸爸守了最后一夜,老房子。
第二天爸爸来楼上,空着手。奶奶惊诧,大衣柜呢?啊?都卖掉了?不是让你搬上来吗?都是跟了一辈子的东西,从老辈儿就有了,怎么扔了呢?没场儿放?怎么没场儿放呢!?她气急地指着四周,这新房住得多宽敞到处不能放吗?爸爸只是一脸落寞。
我家的老房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它被毁掉了。具体什么时候推倒的呢?我没关心过。儿童是坦然接受命运的单纯动物。我只知道,老房子、奶奶的炕、我的墙上的画,苗圃、孔雀,都被挖掘机拆解、强暴、最后很不堪地掩盖在灰土里,从世界上消弭了。我们被连根拔起又置于高楼中,而故壤从此灰飞烟灭。
有时,我在想,老房子并没有消失,它以不同形式封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或许它藏匿在奶奶卧室大抽屉的相片簿里;或许,如果我在如今的高档小区的别人家的花园里向下挖,就会挖到我们的葡萄藤,另一个位置能挖到地瓜炉子的碎片,甚至再挖到我贴在门上的绘画。有时,我们在新房吃晚饭时,谁说了一句”真怀念在老房儿的时候……”话匣子就打开了……像是缅怀一位不辞而别的亲人。
二:果园
好在,我们家在南塂郊外的山上还有四亩果园。
小学时代,每个周末我和雅琳妹妹(爷爷的女儿英梅姑姑的孩子)全家到果园里耍闹,葡萄架换做樱桃树,泥巴还是照样玩,更别提爱丽丝漫游仙境般的的植物:荷花丛似的芋头地、幸运草似的花生田……几个小仔在沟壑里头戴着树枝头冠(我妈妈编的,因为她也喜欢玩!)玩游击战,草垛为堡,树枝做枪。
在山里,要爬一阵子山,羊肠小道,路边的野酸山枣可不能采,可酸了!走路要注意脚下,有很多山沟,向下看,树影幢幢黑哑哑莽苍苍一片。我还是度过了比较美好的小学时代。
但是,我长大了。谁还爱那荒郊野外呢?
有一次爷爷吃完饭坐在沙发上,他扇着扇子,跟妈妈说,“也不用给雅婷报那么多特长班,好好把学习搞一搞,让她多放松放松,周末有空可以去果园玩一玩。”
爷爷是老虎一般的面孔,浓眉大眼,英气十足,因为年老而慈眉善目,脸盘更圆了。爷爷从来不过问我的事情,我想做什么,他都支持。我是爷爷养大的,爷爷是我最爱的人。爷爷勇敢、坚毅、乐观、果断、远谋,在村中是英雄一般的人物,也是能把我们家协调得幸福温暖的领袖。他是在我心中是完美的人。有一天傍晚,我坐在爷爷奶奶卧室的窗台上看万家灯火,卧室很昏暗,爷爷躺在床上歇憩。“雅婷啊”,静谧中,爷爷说,“你也不用很怎么努力,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爷爷在果园
不久,爷爷奶奶就去给奶奶家的电脑安装了宽带,爷爷还定期去电信营业厅去缴网费。但是呢?但是我和雅琳妹妹回奶奶家后更黏在电脑前了。爷爷奶奶去卖樱桃啊,三点钟就要把樱桃摘下来,五点钟就要骑着摩托车把樱桃送到农贸市场,卖给樱桃贩子,早上的樱桃才能买上好价钱。初中的时候,我听大人们说要修路,要占地,要把北面和东面的园、还有我们盖得房子都被占了。加上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我们也不爱去了,爸爸妈妈也在劝爷爷奶奶,不如把果园租出去,别操这份心了。我现在也不知道爷爷那时心里是什么滋味,搞了一辈子果树种植,他对果园最有感情,樱桃树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被别人说占就占了,可怎么办呢?兴味索然,身心俱疲,爷爷奶奶在报纸上打广告,将果园租给了别人。我大概有意避之,这些事情都没有过问,我心里知道果园的下场会和老房子一样。
我初四的时候,大概果园荒芜太久,已盖了一层层粗砺如浪的杂草,大概是对他的果树有瘾,大概是不甘心曾经的乐园如今冷清如此,爷爷说他要重振果园,要在仅剩的1.5亩的院子里再盖两间房。
“我想的是,”一次家庭聚餐上,爷爷说,“你们周末可以有一个放松休闲的去处,国胜(爸爸)和英梅(姑姑)带着孩子、朋友到山上玩玩,也挺好。”
爸爸、奶奶都是反对的,搞了一辈子果树种植,实在不想操这份心了!妈妈却很支持,因为她最喜欢大自然了。但大家都是很尊重与理解爷爷,毕竟70岁的老人也要有充实的生活。
爷爷是雷厉风行的人,列出盖房子的必要材料,又骑上他的摩托车,穿梭成立建材市场与郊外的果园了。
果园里的新房子就要完成了,搭建好最后的那根最大的房梁那天爷爷早上走得很早,也很急。路人说他大概5点就骑着摩托车,就出现在从黄海城市花园的小区赶往郊外的果园的莱山区迎春大街上了,当时马路上只有运输水果蔬菜的面包车和进城的卡车。
房子就要完工了!爷爷,那天你骑着摩托车,迎着朝霞飞驰在去果园的路上,有没有想起—— “啊,又到农村了!”我小时候奶声奶气的感叹?
但是爷爷没有看到果园重建的最终时刻。
那一天早上,爷爷死在了去果园的路上。监控显示他在迎春大街的十字路口,离果园还有4公里的地方与运水果的面包车相撞,爷爷和他的摩托车都飞出去好远,最后落到地上。他没有到果园,他也没有回家。是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姑父到医院去接他,最后一次。把他送到殡仪馆。
我没有见爷爷,错过了与老房子的最后告别,也错过了和爷爷的最后告别。
遗体告别仪式上,躺在鲜花里的爷爷就像下午躺在床上歇憩一样,安安详详。
之后的几个月里,大家彼此缄默不言,但是一旦提起,各自的回忆都涌了上来,作为回忆一个亲人。就像回忆老房子那样。
雅婷,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带你去海边看海王子吗?妈妈手托着腮,笑着问我。哎呀,光自行车后面的小座(儿童椅)就带坏了三个……奶奶这时候总是接上这句话。
怎么会忘呢?

大姨夫在果园
爷爷去世,果园成了大家眼里的罪魁祸首。爸爸奶奶都想把果园卖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卖。恰逢大姨夫查出糖尿病,生命危急,出院之后,他圆硕的体型也一夜间消瘦下来。为了保持健康,他跟我妈妈说,你要是卖果园,不如卖给我吧。这是2013年秋天的一天。2014年春天,妈妈开车(我小时候可没有想过妈妈也能学会开车)带我穿行在郊区的公路上,整齐的绿化带,一望无际的平原,新修的马路,都让我超然物外:这哪里是灰头土脸的农村啊!
我望着一望无际的平原,交叉的公路,辽远的高架桥上货车穿行。恍若隔世。倘若你撬开沥青路的硬壳,掘地50米,你就能看到婀娜的山腰,倘若你搭上性命,再向下挖50米,你就寻见那幽邃的山沟,俏立期中的也酸山枣树,还有枝头的竹节虫和蜜蜂。倘若你沿着沥青表皮下的周遭走上一圈,就是我家的果园——历史是一个不断平面化的过程——你看到码齐了的蜂箱,你拾起了沟壑中掉落的树枝头冠、带有余温的树枝枪,你听见我跟你大声说:快跑啊!敌人来了!他们打过来了!我来掩护你,你快跑!
你跑不掉啊,因为沥青如潮水一样漫过来了,而你双脚现在泥滩里动弹不得,看着命运不由分说地向你碾来,酸山枣树怎么躲过呢?注定要被浸没的。果园里的房子怎么躲过呢?注定要被浸没的。但是,当你站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用记忆凿刻出曲折的山腰、结实的山脊,你知道山峦结实的肌体就在你脚下,你用记忆之手抚慰着它。我想,城市蔓延是种癌症,水泥地面对土地的覆盖是人对自然的侵略。
被疏离的最终都要被夺走。但也不必太悲情,因为走到果园里一看,只有我是那个最悲春伤秋没完没了的无用之人。姥姥家的一众干将早把果园收拾得干净利落了。田间的杂草、黄鼠狼窝、马蜂窝、蜘蛛网被一齐端掉,我像检阅军队的国王一般视察果园:一排排整齐的樱桃树、无花果树、柿子树、石榴树,菜园里有茄子方阵、秋葵方阵、西红柿方阵、花生田、黄瓜架子……从茄子丛里探出一个脑袋,是姥姥:“哟,少东家的来了?”
“哈,什么呀,姥姥好。”
他们可真干得一包带劲儿的,每个周末家庭聚会一般,大姨妈家、小姨家、我家,三辆车开过来,全家老小齐上阵,姥姥姥爷、哥哥妹妹、姨夫姑父、姑姑姨姨谁也不落下,樱桃成熟的季节,我们都要忙着收樱桃。晚上,劳累了一天了,我们就在果园里支起架子烧烤,大家坐在葡萄架下,一家老小,听着虫鸣鸟叫。
葡萄架,我妈妈所最怀念老房子的就是葡萄架,她在新建的果园里复刻了老房子的葡萄架。“雅婷,你还记得老房儿的葡萄架吗?”怎么会忘了呢。果园里的葡萄架郁郁葱葱,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寻着故去的亲人。

图2 20世纪70年代,爷爷王玉山奶奶杨明珠在果园
三:爷爷
爷爷生前非常喜欢在茶余饭后讲述他早年的经历。但是我都没有仔细去听,总是以为还有机会。在爷爷去世之后,通过其他家人的讲述,以及我小时候爷爷跟我爷爷家祖上是商人,19世纪,“樗岚王”在烟台港附近成立了“善成仁”商号,有当铺、银行,掌握着烟台市大马路到市立公安局附近的地带,也有商船往返于天津港和烟台港。最兴旺时曾经捐过四品官,因此家门上悬挂光绪皇帝题写的“宠贲龙章”匾额,匾额在文革时期取下来做成面板,至今仍在使用。爷爷的爷爷王存固是胶东军阀刘珍年的外交官,及其聪明,外号“大头”,爷爷的爸爸王执权是驼背的残疾人,但是极具有经商头脑,外号“小东家”。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动荡,“小东家”从天津到烟台的一艘商船,被溃败的国民党抢走,损失惨重,“小东家”从此开始酗酒,钱财尽散,加上家里几代男人抽大烟、两次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家道逐渐衰落。
爷爷王玉山一生命运多舛。儿时丧母,爷爷的母亲在他12岁时因肺结核去世。小时候,我着迷于爷爷讲述他的母亲去世的过程,那是我对死亡的初步认识。和爷爷一起玩的时候,我最喜欢说“爷爷,再表演一遍你妈妈是怎么死的吧!”还有“如果你妈妈现在复活了,你会怎么办?你表演一下吧!”那时并不知道,这有多么残酷。
爷爷的父亲是残疾人,他成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青年农作时地里残留的炮弹爆炸,同伴五人只有他死里逃生,他后背里嵌入一片炮弹皮;中年在杭州工作时被毒蛇咬伤,抢救及时才捡回来一条命;本以为能安度晚年,没想到果园重修的当天,竟遭遇车祸。
但是爷爷自强不息,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爷爷小学五年级辍学,一边光脚放羊,一边照顾残疾人的父亲,还要带两个弟弟。烟台盛产苹果和樱桃,爷爷根据农业发展的需求学习了果树知识。爷爷成为烟台的果树技术专家,被调配到浙江省农科院工作,长年与奶奶、爸爸、姑姑分开。他带回来许多南方树种,移植在烟台。我记忆中小区里一棵雪山一样高大的玉兰树,黄海游乐城里一排排粗壮的雪松,莱山区马路上的绿化树,都是爷爷带人栽种的。
你恐怕不会相信,最后我们迎来的,是爷爷。
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你相信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会在世上漂泊一段时间,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会轮回转世吗?你能感受到你的爷爷的灵魂存在吗?我们都感受到了爷爷的灵魂存在,他的确在保佑我们,以各种形式。奶奶、妈妈、姑姑关于爷爷的连续梦境,家族祠堂外面会向我们点头的竹林,在中元节勾连此岸与彼岸的摇曳火光中,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在我无助地哭着入睡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爷爷的存在。
自然,爷爷走了,其实这期间,两家的曾祖辈都走了,家庭树最高的枝丫已经离开。南京的舅爷爷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2016年回来长久地游玩了一次,他说,在我还清醒的时候,回来看最后一次故乡,让它从此印在我的脑子里),2021年5月,我们家最老的长辈舅爷爷以91岁高龄辞世。2016年,我考上了北大,大家都很开心,但是爷爷没有看到。爷爷走了,这是我最难过的。
失乐园,复乐园;失乐园,复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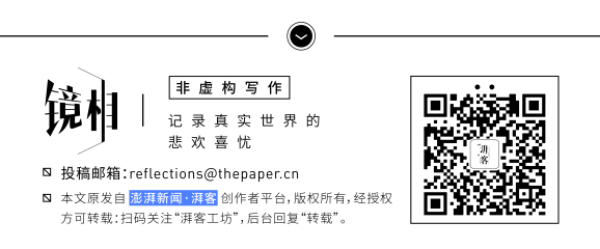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