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张崑评《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中国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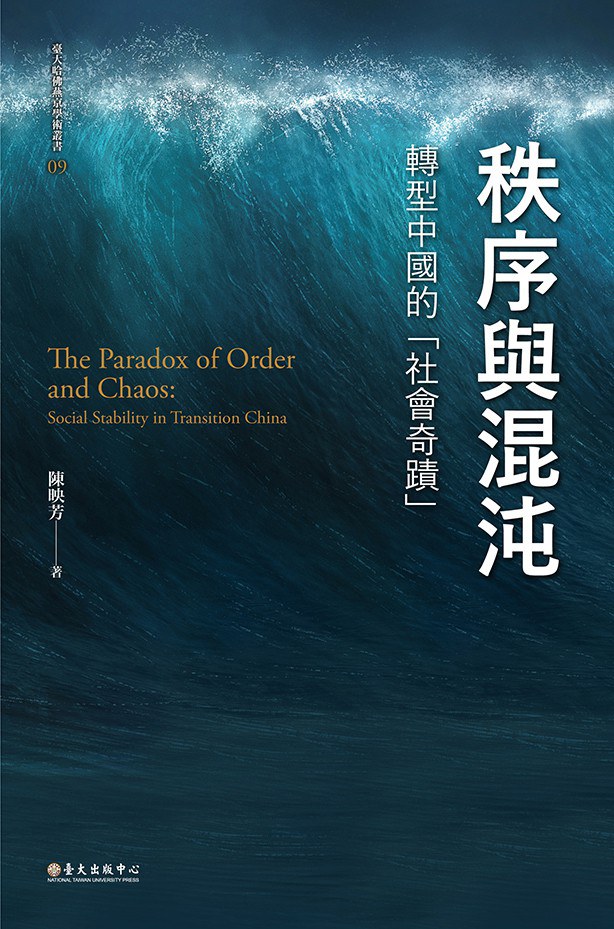
《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陈映芳著,台大出版中心,2021年3月版
“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如今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曾经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由于这种“单位”源于战争年代的“伙食单位”,在一个“统购统销”的“社会主义国家”,谁离了“单位”谁就没有了伙食来源,谁就不能存活。于是,一个人可以没有职务、没有钱财、甚至没有亲人,却不能没有“单位”。“单位制”,曾经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元,不经过它,没有人能理解得了中国社会。
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单位制”开始日渐松动,逐步消亡。那么,在中国,是什么替代了曾经的“单位制”?有社会学家提出,是1990年代的“项目制”取代了“单位制”。可是,会有人这样问吗:“同志,你是哪个项目的?”
社会学家陈映芳教授在《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第一个原创观点就是:“家庭化”。对于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演变研究的学者来说,在对“单位”的消失与去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如同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小王,你结婚了没有?”——原来,逼婚的社会,也是“社会家庭化”的结果。
社会学著作《秩序与混沌》一书分四部分共十二章四百一十页,内容跨越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着眼点落在人们日常生活背后的基本的、又是重大的社会结构性变迁问题上。不过,再重大的叙事,对于社会学来说,都要从个别的人开始,这是从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开始就确立了的原则。马克思责备黑格尔,社会学家责备哲学家,说哲学家在沉思中“从抽象到具体”,讲的都是自己的观念,不是社会现实。这种方法讲出来的历史,都是英雄的历史,而不是人民的历史。马克思就此提出“从个别到一般”,要求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开始,在社会过程中观察一般性的社会现实的形成。于是,作为个别人的一个个普通人也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人公。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原则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科学中最为精髓的思想财富。《秩序与混沌》同样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开启研究:1970年代末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社会剧变,也就是短时间内数百万知青返城的故事。如著作副标题《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所示,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称得上“社会奇迹”。只是,这个“社会奇迹”是如何可能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动力,才可能促成这一“社会奇迹”,进而推动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转型”下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共约一千七八百万“知识青年”被从城市送到乡村生活,然而这一场大规模人口迁移行动并不成功。七十年代末,“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声浪一波胜过一波,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单单就业问题就无法解决。然而,催动大规模“社会奇迹”的,却是最卑微的诉求:“回家”。陈映芳写道:“知青的‘回城’诉求,不仅由个体生活需要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由一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转变成了亲子团聚的人间常情、家庭伦理问题。在同时期云南知青的其他各种请愿书、宣言书、标语口号和诗歌、宣传书等等中,诸如‘骨肉团聚’、‘归来吧,孩子’这一类亲情诉求,有大量的表述。”(67页)许多人人都见过、却从未被注意的东西,到了陈映芳手中,都成为她最有力的论据:纪实文学《我们要回家》、知青纪录片《我要回家》《争取回家》《终于回家》,甚至连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描写邓小平就知青返城问题在中央会议上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时,说的还是一句“让孩子回来吧”,以“回家”的力量“终结了高层内部的争议”(68页)。就此,作者评述道,“知青成为‘孩子’,返城成为‘回家’——家庭及其角色、伦理被各种力量共同启动”,创造了转型中国的第一个“社会奇迹”。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说:“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二章)他的社会契约思想于是从谈论“家庭”成员的关系开始,走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同样,陈映芳将社会“家庭化”,称之为“社会生活正常化”。数百万中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此从城市到了乡村,由市民成了农民,“不带走一片云彩”。哲人或智者在自己的沉思之中,替所有人安排好了他们的生活与命运,这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生活。
陈映芳发现,“家庭化”不仅促成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甚至在中国其后几十年的经济奇迹中,都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又如在国企改革中大批下岗职工在公共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依赖的常常是家庭互助。没有“家庭化”,无论市场化五大改革中最重要的企业改革、还是持续数十年增长的经济奇迹,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陈映芳“家庭化”的发现,由于回到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上,使得曾经看似无比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突然间变得简单了。在中国学界,陈映芳从“单位”到“家庭”的观点,纠正了流传很广的“单位制”转变为“项目制”的观点,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同时是无法绕过的——社会转型的连贯性——问题。正如霍布斯曾提出著名的“分解综合法”,他把问题首先不断分解,分解到不能再分解的基本要素,然后再运用理性使之综合起来,由于“家庭”恰好是“单位制”崩解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所以,基于它的综合,也就使“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变得易于理解起来。
不过,有结构就有等级,就像阿伦特曾说过的,“等级制本身是命令和服从者共享的,双方都认同等级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等级制中他们彼此都有预先规定好的牢固地位”(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88页),一个由家而国的社会,必定有着需要阐释的等级身份问题。从这里,我们就来到了全书的第二大主题“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
在“群众”离开“群众运动的单位”,“回家”之后。全世界所有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都面临一个新问题:“群众”的去向问题。“回家”之后,“群众”是什么身份?他们可能从社会结构中消失掉吗?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起初,在冷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纷纷倒向西方国家、意欲转向公民社会的背景下,很自然地以“公民社会”为参照系去研究。法国著名汉学家、曾担任欧洲最大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谢弗利(Yves Chevrier)1995年曾发表一篇上百页的重要论文《公民社会问题:中国与柴郡猫》(Yves Chevrier, La question de la société civile, la Chine et le chat du Cheshire, Études chinoises, vol. XIV, 2 (automne). DOI : 10.3406/etchi.1995.1237.),几乎把法语世界所有重要的中国研究都囊括在“公民社会问题”这一个总名下连贯处理。说其“重要”,自然有原因。但凡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大都知道有年鉴学派,也很容易知道年鉴学派1970年代的新史学转向。有说法说新史学转向之后,分裂成很多不同的细分学科,因而碎片化了。但那只是他人的看法,不是年鉴学派学者自己的看法。对于年鉴学派来说,每兴建一个学科,都不是起个名字立块牌子的事情,而是需要从学科范围界定、概念术语定义、史料批评、方法论建构、学科意义建构、争议与辩论的历史等几大方面有全面且充分的严肃研究,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细分学科。经过这样的学术建构,一方面,所有的新学科都在底层互通,既跨学科又不碎片;另一方面,把触角伸进包括社会学的其他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着史学一统天下的野心。所以,谢弗利的论文,大有要在年鉴学派新史学之下开辟一门“中国学”的气势。今天我们事后批评说,当时的学者有些想当然地认为“群众”变成了“公民”,然后用“公民社会”作为总线索去观察和评价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这一进路必然难以成功,但这不等于说学者会轻易放弃。有趣的是,十五年后,谢弗利卷土重来。2010年,他为一本厚厚的中国研究论文合集写了近百页的导言,题为《从有问题的城(cité)到可居住的市(ville):20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的史学和史料学》(Yves Chevrier, De la Cité problématique à la Ville habitée: Histoire et historiographie de la société urbaine chinoise au XXe siècle, in Yves CHEVRIER, Alain ROUX et Xiaohong XIAO-PLANES (éd.), dir, Citadins et citoyens dans la Chine d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10, pp.15-101.),处理的仍然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大问题,只是理论框架从“公民社会”回到了韦伯社会学。城(cité)用的是古希腊城邦的内涵,有着世俗化政治共同体的内涵,是韦伯社会学的术语,而市(ville)仅仅是人们聚居的地点,缺乏秩序内涵。仅从题目中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出,欧洲重量级学者放弃了“公民社会”的理解进路,退了一步,要从韦伯社会学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并且确认,中国的城市化也没有走向韦伯所描述的那种世俗化的城(cité),而是停留在可居住的市(ville)。如果我们了解了欧洲学界当代中国研究的这些动向,我们就会知道陈映芳教授如何在“市”的方向上更进一步。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主要的中国研究学者曾经采用的研究进路之变化。可是我们说,无论怎么变,不变的是,这些研究进路始终是用学者的眼光看中国,做出的研究总是“他人眼中的中国”,而总不似“中国本身”。
而陈映芳教授的社会学研究,恰恰是完全回到了“中国本身”,在中国社会自身的演进之中,提出了既非“国民”也非“公民”的“市民”研究路径,其如此独特,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奇特的市民”:过去的“群众”啊,原来你们现在在这里!
九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政府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国家的“国民”,就成为“回家”之后的“群众”的新的可能身份,且是官方所希望的身份。然而在实行中,却因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变了形。陈映芳观察到,在农民身份的现代化过程中,当时不少学者呼吁国家给予农民和农民工更多、更平等的“国民待遇”,可惜进城的农民却不怎么领情,他们更愿意成为“市民”,而非“国民”。
他们对政府引导的“国民”身份毫无兴趣,对西方想象的“公民”身份还茫然无知,但他们很清楚“市民”的好处:沿袭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户籍身份,绑定了包括居住保障、教育资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其他社会福利等各种市民待遇。有了所在城市的户籍,才能享有市民待遇,参与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一保障体系尚未普及到农民,且可能遥遥无期。某种程度上,农民一直都是“国民”,一直都在默默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但与“市民”比起来,农民同样是“国民”,却是不平等的。即国民和国民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相比之下,市民与市民之间,反而更加平等。如此看来,农民追求变成“市民”身份,就再自然不过了。同时,如陈映芳调查中总结的,“农民”的生活原则,是“生存需要原则”。而一旦成为“市民”,就意味着摆脱了“生存需要原则”,提升到“有意义的生活的原则”。这种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是“国民”身份所不能提供的,甚至是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压制的。
从1978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离开故土的农民,离开了传统乡村的熟人结构社会,却既没有成为“国民”,也没有成为“公民”,而是成为了逐利的“市民”。到了这里,我们就发现,陈映芳的社会学著作,不仅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年代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的著作,还是帮助理解经济何以取得发展奇迹的著作。正是这些从“单位”释放出来的逐利的“市民”,在世纪交替“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重新依靠WTO等成熟的国际市场规则组织了起来,身价倍增。一旦如此接轨,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就只有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籍的不同,而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而此时的中国人,在自身的身份上,既不追求“国民”,也无意识到“公民”,还全力向往“市民”,所有这些条件为逐利的国际资本提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天赐机缘:和美国人做同样甚至更多的劳动,却既无政治诉求,也没有权利诉求,只求“有意义的生活”而已。难怪国际资本兴奋地欢呼中国的“人口红利”。是的,正是这“奇特的市民”,吸引了全世界逐利的资本,在他们提供的成熟市场规则之下,“市民”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造就了中国市场的繁荣、经济的腾飞。于是,从“可居住的市(ville)”里那些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而拼搏的逐利的“市民”,开出了一条不同于“公民”和“国民”的“市民”的社会学研究之路,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了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三条道路”。当然,我们说“第三条道路”,并非指恰好是“第三条”,而是借用这个词来表达一种跳出左右为难的困境的新研究路径。
“城市化”一度是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可是,众多研究者,谁又能想到,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最清楚明白的竟然就是“市民”这一线索呢?确实,谁也想不到,这正是社会学的特征。社会学不是沉思冥想的学科,而是行动中获得答案的学科:只要去问问当事人,他想成为什么身份,最好的答案就有了。就是这样,作者紧贴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运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手段,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以最自然而然的方法,找到了这一给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都可能带来兴奋的“市民”研究路径。
《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中有中国社会诸多细节的严肃研究,非止以上两点。但仅仅是以上两点,对一个深度关心着中国命运的人来说,就可能已经可以帮助他打开中国社会二三十年关键变迁的黑匣子,去探索那些难为人知的奥秘。而对于从事中国研究的专业学者而言,这首先是一部严整规范的学术著作,其次是一位有着出众学术直觉的学者的作品,其三是其中遍布着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意识,依然可以引领着诸多后来人继续深入,开辟新的研究。
如果说要对这部蕴藏着仍然有待挖掘的宝藏的作品作出什么批评,首先就是这些“宝藏”埋得还是太深了,要深入阅读,对读者的知识储备有一定的要求。其次,从一位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总是情不自禁地希望作者写出更多如“市民与国民”那样有情节转折的故事,总之,历史学家永远都会责备社会学家说:如果能写得更像历史,就更好了。不过,对于那些深深关注着中国命运、力图求解社会现实问题的读者,相信一定会在阅读中找到足以帮助他们增进理解这个时常令人不知所措的时代的宝藏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