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门户”:傅衣凌学派的治史路径
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说过: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如果说世界上有两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这里表达的意思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先生所说: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具体落实到经济学上看,则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所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则是经济史的流。
这其中告诉人们的信息还在于:历史学正如自然科学中的数学那样是近代以来其他分支学科的基础,进入历史学科的学子尽管似乎已作出了专业的选择,实际上这是一个包容面极大的选择,在这个学科里,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具体、更细微的治史路径的选择。套用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建议成吉思汗对付金政权的策略就是“既不是攻,也不是不攻;是攻而不攻,不攻而攻”。在这个意义上说:进入历史专业的学子是幸运的,它将个人稚年期的选择难题暂时搁置了,因而可以在进入学术之途后,作出更加从容和理性的选择。中国史、世界史;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史等等。
一、治史的基本准入条件
进入一个学科,确实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的,要进入中外历史的深邃时空隧道,既往的先师们已经告诉过我们治史的基本准入条件,大体总结为:阅读文献的能力,掌握外语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走进历史的能力。
阅读文献的能力是治史的基本功,也是决定其学术成就高度的标尺。治中国史者,势必得接触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史源等学科。古人云:“一年视离经辨志”,就是要在拿到一页没有现代标点的文言文后,能够迅速准确地句读且阐述出其正确含义的能力。这些方面是要下死功夫的,事实上进入其中也是趣味无穷的。有了阅读文献的基本能力后,只要一接触到原始文献,我们便能够发现既往阅读者的高明和庸俗,便能够将一段在俗人视为天书的文字中读到历史的鲜活和恢弘。
掌握外语的能力决定了治史者的视野宽度。我们要了解别国对该学术问题的研究状况,需要外语;我们要将自己的学术传播出去,需要外语;我们要与别国的学者开展合作,同样需要外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该特别羡慕那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他们往往是开展跨文化研究的先天娇儿。
逻辑思维的能力说到底是清晰地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能力。在写作上可以用尽量少的文字告诉别人自己的深邃学术思想,在演讲时能够层层推进,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独到观点,让听众听得聚精会神、心领神会、多有共鸣。这一点在当今时代电子阅读没有纸张等资源限制状态下尤其值得推崇的方面。因为我们时常会不自觉地沉溺于长文、长篇大论,最不可容忍的是硬着头皮看完长篇之后,反复琢磨仍不得要领的状态。
走进历史的能力通俗地说就是历史感,每个人的生活阅历本身便可以构成自己读懂历史、认识社会的现成资源,社会学家费孝通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研究、人类学家林耀华用福建古田县黄田镇凤亭村的研究、杨懋春用山东胶州台头村的研究揭示了故乡往往是开展成功学术研究的较佳场域。人类学所倡导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特别注重长期的“参与观察”(至少6个月),这又何尝不是寻找到历史感的最低时间长度啊。我们或许应该鼓励青年学子在走进历史现场时能够更加潜沉一些。社会学更注重当下社会问题的研究,它所倡导的社会调查或许可以短一些。

二、傅衣凌学派治史倡导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山东大学王学典在总结傅衣凌学派的学术理路时说:这是一个“系统清晰、特色鲜明的学派,这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善于透过片断的史料显示历史的归趋,又能从历史的趋向中看出具体史料的意义。”傅先生“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包括契约文书、谱牒、志书、账籍、碑刻等证史,尤重田野调查,以今证古;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等等。”傅衣凌先生及其子弟们真可谓踏破了数双铁鞋,深入穷乡僻壤,搜罗的资料往往是别人不屑一顾的破旧物件,却从其中解读出了真历史。
傅衣凌学派认为可以把历史学做广义的界定,其彰显出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可以做如下归纳:
(一)强调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运用。
凡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人种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生态学、地理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均可为历史学所用,凡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等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研究的方法,既往有学者总结说:“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又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傅衣凌学派的一个特色,傅衣凌先生入大学时读的是经济系,后转到历史系,出国留学又学了社会学,平时还特别留心民俗学,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流行的蓄奴习俗深表痛恨,并认为这导致集中了大量社会财富之阶层生活的骄奢淫逸、社会下层生活的难以为继和基本人权的被剥夺,进而衍生出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导致激烈的反抗斗争,引起玉石俱焚、社会积累被毁灭的惨剧。
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傅衣凌先生形成了自己的若干理论性观点,他说:“长期以来,人们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和西欧一样,自发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立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引伸而来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傅先生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产生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恰在协调各种不可自我调和的矛盾中显示出自己产生的价值,傅先生反对将中国和印度、埃及等地区进行类比而得出管理渠道和人工灌溉设施、举办公共工程、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的要求是中央集权政府建立的原因的结论,是集权国家出现后由于其地位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其众多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大一部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是在乡族社会中进行的,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干预。“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公’和‘私’两大系统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的互动过程。”地方割据和农民战争是冲突的基本表现形态,但是这些往往是短暂的、临时性的,地方割据势力既可以是兴风作浪的始作俑者,或者利用农民起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出面镇压农民的起义,保障自我的利益不受损害。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往往可以利用这些地方势力消除不安定因素,进而收编他们,使他们臣服于大一统的权威之下。
汉代以后,财产所有形态和财产法权观念多元化现象明显,国有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长期并存,难做剖断,司法权的多元性也由此衍生,族规、乡约、乡例都有推行的空间。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性同样存在。因此,虽然社会上出现许多类似欧洲近代化时期的现象,但往往并不具有导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征兆。反而是新旧因素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社会结构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化解各种冲击的能力,商人尽管成邦,成了一个显著的阶层,但他们在政权敲诈下有反抗意识,却又返回去寻求政府给予保护和特权,斗争性不强。
(二)强调对“总体历史”的把握。
法国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也倡导“总体历史”,勒·高夫提倡《新史学》,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的分析方法,这些在傅衣凌先生那里,早也是躬行的实践,因此可以说在当时国际交流尚很稀少的时代,傅先生在中国早已走出了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的路数,只是没有确定这样的命名而已。傅先生能从国家机器、社会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在《秦汉的豪族》一文中认为:豪族来源于六国的故家遗族,人数不少,虽然失去了政权,但他们仍“不愿与齐民齿”,秦始皇反复有徙豪之举,却并不能彻底,而且随着世代的繁衍,豪族还可能壮大起来,它们以“保族”、“收族”为圭臬,延续着自己的文化精神。他们将养客作为自己的辅弼,蓄奴作为维持养尊处优的前提,生活奢靡,行为横肆,往往构成为贫民的剥削者和政权的直接威胁力量,当统治者试图压服他们的时候,一些豪强便可能潜伏下来,衍而成为魏晋时期的门阀。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隶农制,其根源在于高利贷资本、商人资本与土地资本实现了三位一体,中国专制主义政权以官僚、军队实施对地主、商人、农民(隶农)、奴隶的统治,等级界限森严,尽管有科举制度作为激发官僚队伍的更新,但社会的保守色彩明显。奴隶来源有俘虏、罪人、赏赐、买卖、贡献与投靠、犯罪、战争、家生等多种形式,他们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极低,作为他们的主子则往往占田无限,作威作福。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时常表现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
因为佃农制的发达和农民的相对离土自由,于是就在农村中出现了三种劳动力形态,即佣工、佃户和僮奴。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并存,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进一步、退二步的情形。本来农民具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从农村挤出来的过剩劳动力,可成为佣工,为工业发展注力。但事实是那些可能走向新境界的经营地主和富农选择了乡居和离开生产的道路,他们以放高利贷为生,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地主阶层的寄生化更趋显著。他们不断加大着对佃户的榨取,将苛刻收取的地租囤积居奇,再度施加对佃户的剥削,因而导致农民的贫困化,无法实现与城市工商业的有效对接,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更趋加强。
傅先生分析说:“这广大的农业人口向全国各地的自由流动,固然在缓和了某一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促进移住地的经济开发,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不过这大量的农业人口如果过多地向某一地区集中,则必然的会产生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后果,出现有争求雇主的现象。城市手工业的雇工制无法获得健全的发展,主佃关系往往充满了野蛮的色彩,有时衍生出奴隶式的畸形关系。”在江南地区,地主使用僮奴现象普遍。从政治层面看,那些势单力薄的普通之家往往也主动寻求具有政治特权的身份性地主的庇护,投靠到其门下成为奴仆、佃户,胡如雷先生称这种现象为“第二度农奴化”,在傅先生看来,这是新旧因素纠合而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儿,地主将高额榨取的地租用于娶妻纳妾,繁衍众多子嗣,结果往往是财产的分散与浪费,依然无法引向生产领域。被榨干的佃农在独立和自由都被地主控制的背景下,很难求得发展的空间,甚至妻女都可以被主子任意欺凌,有的便举起反抗的大旗。

(三)强调“自下而上”、“上下互视”的治史路径。
傅衣凌先生深爱弗雷泽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这样的民俗学著作,也喜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样的新史学论著,将梁启超倡导的运用家谱、契约等民间文献研究历史方法化为实际的行动,且一发而不可收,这构成了傅衣凌学派的一个显著特色。傅先生强调民间传说、路途传闻、儿提故事都可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傅先生养成了处处留心,事事关心的治学习惯,他勤于访书、读书,亦勤于访人、切磋。
傅先生认识到: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他从谢肇淛《五杂俎》中寻觅到新安商人、山右商人的论题,与日本学者藤井宏交谈后引起共鸣,其后相互交流,共同推进该论题研究的深化。他从阅读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发现苏州洞庭东、西山商人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题目,与南京大学吕作燮交谈后更激发了寻找湖南各地活跃着的洞庭商人的情形。傅先生对民俗的关注是个天然的兴趣,他在《桃符考》中说:在古人心目中,将桃视作驱逐魔鬼、拔除不祥的神秘之物,就像英国人视山柃为有神秘能力的东西,用它鞭打牛马,能让牛马肥壮,但倘若用金雀杖或柳枝鞭打小孩,则小孩不易长大,因金雀枝不会长成大树,柳枝亦较早凋零。傅先生曾深受民俗学家弗雷泽《金枝》的影响,所以对民俗的认识也特别地专业、独到。他指出:以桃驱鬼,曾走过以桃做成人形,即桃人驱鬼的阶段,神荼郁垒被定义为驱鬼神人,配合桃人共同执行驱鬼抗魔的职能。近代的春联与古代的桃符虽然有关联,却失掉了原始民俗的本来意义。傅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考证福建陈氏、黄氏、李氏、吴氏、谢氏、刘氏、邱氏、罗氏、晏氏等都是畲族,其他像许氏、张氏、余氏、袁氏、聂氏、辜氏、章氏、何氏亦有畲族混杂其间。因为“畲与汉人往来频繁,多沾染华风,改用汉姓,亦喜自托于中原仕族之列。”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福建人口构成的历史样貌。

通过相互关照与相互比较,更多地与国际范围内的同行对话,傅先生走到了国际学术前沿。从中国手工业帮会不是单单存在于城市,而是从农村延长到城市去这一事实,傅先生追索出中国工商阶级与封建地主间不但不存在相互的矛盾,反而还存在共通性乃至一身而二任。工商业会馆既存在于城市,又存在于农村的事实让傅先生认识到中国城乡之间的关系也不对立,农村是城市工商行会的原始基地,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在商人会馆中又存在着更小的组织形态,被称做“纲”,细究“纲”的本义,是专营某类商品的商人组织,更早来源于官营的运输组织的称谓,但这一称谓后来有了被泛化的现象。仅在这一点上,与欧洲的经验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傅先生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海外贸易经营者的出生地不仅是滨海地区,而且多有一般内地的商人,江苏华亭、江阴、黄姚是海商聚居的一个根据地,浙江的明州、杭州,亦为海外贸易商人所聚集。傅先生判断:“当时浙海通蕃之风甚盛,浙人通蕃多从宁波、定海出洋,慈溪有积年通蕃柴德美,杭州歇客之家亦均系通蕃的窝主,绍兴则多外商的通事。”福州为中外交通之地,“成化间泉州市舶司移设于福州之后,于是通蕃渐多,省城的河口以及濒海的琅岐、嘉登诸岛之民,无不辍耒不耕,远航海外,而福清的通蕃喇哒,当嘉靖间曾横行于海上。至于泉之安平、漳之月港,尤为中国的海外商人的集中之地。”“漳州梅岭林、田、傅三巨姓,全部三千家,即全靠经商行劫为活。”广东海商去三佛齐、满剌加、暹罗等地的也很多。来自内地的商人如徽商也是海外贸易的重要一支,明嘉靖年间,他们并与福建、广东商人同任管理外商的一切事宜,后来,徽商在广州的十三行、宁波的洋行都有活动轨迹。其他像晋商私舶日本,江西商人如亚刘成为满剌加通事,饶州人朱辅任职于琉球国多年,佛郎机贡使中的火者亚三都是海外贸易的活跃分子。说到福建海外贸易商人,也有不少来自龙岩、汀州。傅先生认为:这么多人在趋利的吸引下,“相率呼群唤侣,麇集而至”,不利于海商资本的集中,而使原始资本的蓄积受到妨碍。当时经营大宗商品丝、糖的有浙直丝客、徽商、闽商、粤商,他们不仅在国际市场竞争,同时也在国内市场相互争夺。傅先生从徐光启的《海防迂说》中发现:“若吕宋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商人间自我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大商人的形成。江淮海商对推动中国南北物资交流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江淮海商因为遭到封建势力的嫉妒而遭遇摧残,海商们成为当时社会结构矛盾、冲突的牺牲品。这些新解释的形成绝非那些停留在阅读狭小范围资料者能够达到的。傅先生感慨:寻找史料的艰辛固然考验着治史者的意志,但从史料中探寻出前人所未发的新知识、新认识,那种欢乐却又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
三、傅衣凌学派的传承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杨国桢先生转向自己的新领域——海洋史这一学术处女地,先做规范概念体系的工作,继而主编出版《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丛书》(10册)和《中国海洋文明史》,愈加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明中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共存的局面,这其中彰显的“天下大同”观与西方近代殖民性、掠夺式的不可持续的海洋文明并不一样,且长期维持着环中国海直至印度洋到非洲东岸的海域的和平贸易局面。杨国桢注重摒弃“陆地思维”,站在海里看中国,呈现出的是与传统史观截然不同的“蓝色思维”。

李伯重教授的《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2)及其最新力作《火枪与帐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在学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李伯重在生产力经济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拓了一条道路”,他长期身处欧美,与国际同行及时对话,且能将西方学界最新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引进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他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江南道路”的理论模式,“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显示出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的“超轻结构”特征,并提出了与黄宗智停滞论相反的“发展论”,这是对傅衣凌学派的重要拓展。

陈支平教授关于清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福建家族文化的研究以及东南中国的研究都成果丰硕。他在研究清代赋役制度时,比较侧重探讨赋役制度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注重分析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之间的距离,因为他利用的实录、档案和方志、族谱已经有效地实现了二者间的对话(《清初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2004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对户籍、易知由单、自封投柜和民间负担等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另撰有《近500年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陈支平坚持“自下而上”的学术理路,在台湾史、台湾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有所推进,《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2009)显示出研究的进一步细致化。

郑振满教授聚焦于家族史研究,注重“私”的系统的研究和宗教碑铭的整理与利用,深化了傅衣凌先生的“乡族论”。《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对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地方行政与社会转型等都有较为深邃的思索,是傅衣凌先生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进一步具体化。其《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于199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2001年出版了英文版,其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近年来,郑振满更加专注于田野调查,且力求使民间历史文献学科化,其用力方向也呈现出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纵深发展,这显示出对傅衣凌学派的重要拓展。
陈春声教授博士论文《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于1992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体现出对傅衣凌学派和中山大学梁方仲、汤明檖一脉的兼融。陈春声教授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注重田野调查和民间资料包括口头资料和书信等的利用与收集,对民间信仰、海洋社会的习俗及其由来、海盗活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及其效果等都作了若干深具理论性和借鉴意义的思考,强调地域脉络在重构历史信仰与仪式中表达的世界观所占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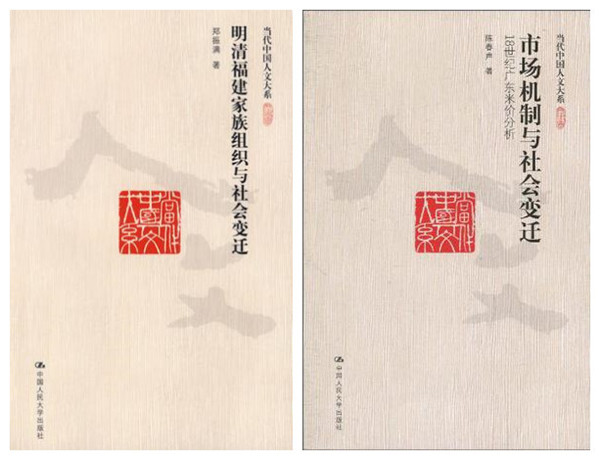
王日根教授较关注民间社会对基层管理和控制的作用,即“民间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机构固然有许多是官方建立的,却不乏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像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这些组织都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深处,不仅对固定居住者,而且也对流动人群实施着有效的社会管理,在历史演进中,官方努力和民间努力经常能相生相助,共同臻于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有些官方的政策或制度就是民间实践成功经验的转化形式,在官方秩序出现纰漏的时候,民间社会有时还能运转正常。在中国政治文明遗产中有一种“官民相得”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继承,这可以算是对傅衣凌先生“私”的系统的一点延伸吧。(《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近年来王日根教授追随博士阶段导师杨国桢转向海洋史,对海疆政策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和总结,200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2015年出版《海润华夏: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2016年出版《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2017年将出版《耕海耘波:明清官民走向海洋历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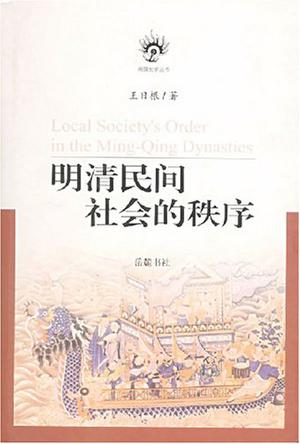
其他像林仁川教授、刘秀生教授、陈学文教授、唐文基教授、蒋兆成教授、郭润涛教授等均属于傅衣凌学派的外围力量。如今,傅衣凌学派已经衍生出更多的传人,像钞晓鸿、刘永华、张侃、林枫等教授均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傅衣凌学派势必将代有传人,薪火绵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