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杉山正明: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
耐人寻味的解读
法国向来以其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作为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导言”中,有如下叙述:一二七六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对于汉人来说,看到中原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持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谢和耐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日本也由栗本一男于一九九○年以『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袭来前夜の杭州』为题翻译出版。方才的引文即出自栗本一男的译著。
然而,只要通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的繁荣的史料时,除了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每次读到类似的文字,都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谁都知道,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
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况,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一个疑问。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在此,姑且将之搁下不谈,若以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亦可译作《百万之书》)为据,他的确是在一二七六年来到东方的。正是杭州在蒙古军前不战而降的那一年。
只是,他并非马上就来到杭州。有一段时间,他是跟随大汗忽必烈,待在夏季的首都上都与冬季的首都大都(现在北京的前身)的。“马可·波罗逗留中国期间,一直待在杭州”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误解。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的这段时间,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也就是说,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么,要引用较马可·波罗更晚的伊本·巴图塔在蒙古军进驻杭州已经半世纪以后的记述就更不合理了。
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
其实,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都显示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谢和耐只不过是直率地表明了不问东洋西洋,从研究者到一般人士都往往会有的“深信不疑”的倾向。撇开上述不谈,谢和耐的著作在生动地描写了贯穿南宋及蒙古时代的“中国近世”大型城市杭州的繁荣这一点上,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著作,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深信不疑”是否可信。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比这个还要麻烦的了。
而且更恼人的是,结论一旦形成,就颇难加以订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但是,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成为“定论”或“通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么一来,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
一二七六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有中国史研究者认为,蒙古军队的行为更让人记恨。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若蒙古军队不慎重地维护秩序,管理杭州内外,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自北宋建国起算的话则已逾三百年,这样的国家与政权消失毁灭,却几乎什么暴动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才真的令人吃惊。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在中国史上,这样的和平过渡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一般来说,中国史上的政权更替若是以某个王朝或政权以武力消灭另一个的形式进行,一定会演变成非常惨烈的事态。我们虽然很容易误以为前近代的中国史是以士大夫或读书人为中心、软实力占优势地位的,但若与日本列岛或朝鲜半岛的历史比较即可知,在中国史上治乱兴亡异常激烈,硬实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点相关,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与此不同,一二七六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或许读者们无法相信,但一二七六年蒙古军来临之后,杭州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什么变了,又有什么没有变?确切的情况几乎不清楚。首都杭州既然如此,那么其他江南各地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
就目前而言,除去几个特殊的话题及事件外,专门研究者从事的有关蒙古治下的杭州与中国南方的确切的实证研究极少。这是今后务必要持续进行的课题之一。
然而,明明没有根据,“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
没有“政治”的繁荣
那么,杭州有什么改变呢?由于蒙古的接收,南宋宫廷及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杭州不再是首都了。这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毋庸置疑的事实。
从秦汉帝国开始到近代,在中国只有首都是大型城市。历代中华王朝,在人口极端集中于首都及中央机构这一点上,具有与世界其他区域相当不同的特殊政治制度传统。与其他城市相比,中国的首都大得极不自然。
如果是支配广大区域的王朝或政权,首都就会有数千人的“正式中央官僚”和作为其接班梯队的“太学”学生,外加至少三十万到四十万的首都军队防卫京畿。
所谓的正式官僚,是指具有正一品到从九品官阶的“流内官”。其下还有不具官阶,负责种种实际事务的数量庞大的下级官吏。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胥吏”。其确切数量虽不清楚,但应该有“流内官”的三四倍。
光看官僚、太学生和胥吏,保守估计也有两三万人。加上还有首都驻军,再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族,数量就会更惊人(不过,胥吏或一般士兵是否都有余力娶妻成家、养育孩子,则另当别论。据说在传统中华王朝中,军人尤其遭到蔑视以及恶劣待遇,因此终生单身者也相当多)。
此外,最重要的是,首都中还有天子及皇族。然后,还有后宫佳丽及宦官、奉仕贵族的各种宫廷仆婢等。其数量也不容忽视。
光是合计以上的人群集团,人口就超过了五十万。这些人单单因为首都这样的理由而存在。而且与这些人的衣食住相关的人群集团也必须考虑在内。想想这些必然的附带人口,其数量就变得相当庞大。
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中华帝国的首都都必定是人口达到一百万左右的巨型城市,这在前近代世界中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即使是在只拥有“半壁天下”的南宋,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
在蒙古完成接收后,皇室、宫廷、中央政府从杭州消失了。首都失去了聚集人群与物资的源头。
当然,要是所有的官僚与吏员都失去工作,那么想必他们的家人与随从也只能流落街头。因此,蒙古将主要着眼点放在沿用南宋原有机能,极尽可能地避免人心动摇或人口流动上,借由制定安定化政策,让大多数南宋旧臣官复原职,能够再度就职于各种军事、行政、经济、宗教等部门。
另外,驻屯于首都内外的士兵之中往南方逃亡者,几乎都顺势向蒙古投降。可以想见,这些以前靠薪饷生活的人们失业后若无人管制,势必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因此,蒙古在考量士兵优劣与本人期望的前提下,将他们派往亚洲各地的战线。在远征日本的第二次“弘安之役”中,据称从中国南方乘船出发的人数达到十万,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些人。
军人们在蒙古到来后急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新的驻屯军被派到杭州来的蒙古士兵,其数量达一两万人。
如果单就以上条件来考量,杭州人口的确是减少了。
总而言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纯粹消费的人口在一时之间消失,经济活动理应衰退。
实际上,在九十二年后的一三六八年,在蒙古舍弃中原退回北方、明军取而代之进驻的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也正是如此。曾为蒙古首都的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再加上明军的掠夺、破坏与焚烧,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其后,一直到永乐帝迁都至此、改称北京、进行重建的五十多年间,除了永乐帝夺取政权前的住处“燕王府”,其余皆是焚毁后的巨型遗迹留下的乌黑凄惨的面貌,道尽沧桑。
然而,蒙古治下的杭州却保持了繁荣。在世界帝国蒙古的背景之下,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于杭州,为其带来了远胜于南宋时期的繁荣。这实在是令人吃惊。这种情况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切的关键恐怕就在于——蒙古时代的杭州,就算没有了南宋宫廷、中央政府,也毫无障碍地迎来了另一种繁荣。这才是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所要传达的、元代杭州充满自由与开阔的面貌。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除却政治的经济繁荣。在政治直接因素较弱的条件之下,仍存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巨型城市。这在中国史上固然不必说,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蒙古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本文摘自杉山正明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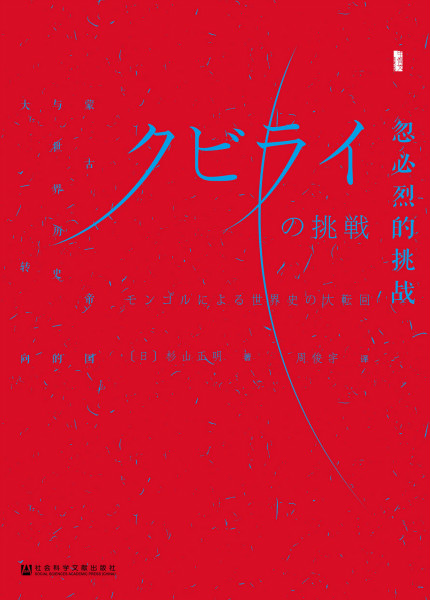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