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酒香草头中的文化,上海郊外春天开花的“南苜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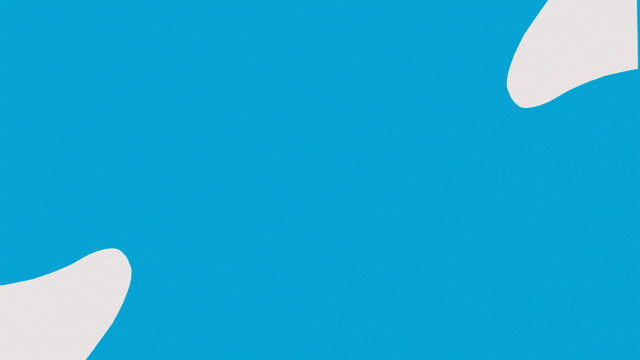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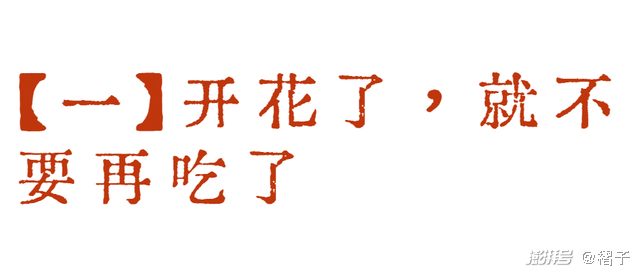
三月的一天,路上的店很多都关闭了,去田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去的地方是一块已经被拆迁的土地,只是还想要种地的农民仍旧过去种植着一些蔬菜。在地里发现了一片草头, 我还很少在地里看见过草头,这次看到的,还是开着花的,很小,淡黄色。这样成熟的草头,看上去有点像酢浆草这样的观赏植物。
采了一些草头,用美工刀割的时候,就感觉纤维更加粗。回到家用白酒炒了一盆酒香草头之后,要比冬天的时候老很多。但说到底,这是站在人自身的角度,对于植物来说,繁衍才是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叫人品尝的时候更加鲜美。但客观上来说,作为一种食物的草头扩大了传播,因为农民会在冬天最冷之时,为怕冷的蔬菜都覆盖上一层地膜。哪怕是作为“半野菜”的草头也不例外。

草头开花的时候,旁边的油菜、青菜还有各种豆荚的花也开了,开着黄花的青菜显得尤其高,由于这里已经不是专门经过规划种植的天地,因此每一块小菜地的规划排布都不一样,沿着河的地方都被大大小小分出来了好几块,有些杂乱的视感。原来还有生产队的时候,农民却绝不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却都经历过。
这里,油菜花的种植面积被压缩得很小,但香味却依旧浓郁,说起来,对于一望无际的油菜田我也提不起什么兴致,想象不过来的时候,就有些虚构的感觉。在经过这片田地的路上,我还看到一处用石灰粉圈起来的水泥地,中间还有大片焚烧过的痕迹,不消说,肯定是有人回到这里,为过世的人烧过“行李”,很可能还是原来跟我们一个村组的,不然也不必刻意跑来这里。不过,到了我这一代,都互相不认识了。
因为几年没有住人,无人种植的地方,竟长满了构树,几乎成了一片构树林子,过去乡下,见到这种树,都是要砍掉的,我后来知道这种树的树皮可以造纸,不过估计我们这边古来没形成过造纸这门生计。
除了割了草头,这趟出行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实际上,所有的蔬菜无非就是人工培育的野菜,日语蔬菜就写作汉字野菜(やさい),这个发音听上去很有节奏,写出来的汉字也挺有禅意。人们可以一茬一茬地割草头,那是因为农民在冬天保护它的生长,但在春天它开出花的时候,它就马上宣告要独自进行生命旅程。

凡是到上海来的同学或者朋友,我总是要推荐酒香草头这道菜。其实,本帮菜里面“草头圈子”是更美味的一道名菜,草头的绿色粗纤维正好中和了猪大肠的肥腻。但是这道菜里面圈子变成了主角,一来猪大肠未必适应每一个人的口味,二来这道菜中,草头本身的风味,怕是要掩盖一些。

在闵行上学的时候,我带同学去召稼楼,草头是每次必点的一道菜,很快,他们也都熟悉了。本来在这样的水乡酒楼吃饭,是很适应喝上一些黄酒的,但黄酒他们却都吃不惯,还喜欢开着吃这些草头就要醉了的玩笑话。其实,草头中的白酒味是极其容易适应的。

过去奉贤人还很喜欢喝当地神仙酒厂酿造的神仙白酒,我们小时候学校还组织秋游去参观过,有的小孩在那里买了一小罐白酒,说要带回家,给大人喝,没想到有的孩子在公交车上打开白酒喝起来,在公交车上颠得吐出来。按一些本地年长者的说法,神仙酒厂出的酒,本来都是用纯粮食酿造的,后来就渐渐假了起来。我爷爷很早之前也喝神仙酒的小罐,是装在一个小型的玻璃杯里,里面的白酒喝完了还可以当作一个酒杯用。
以前烧酒香草头,也是用这种酒。撒进去,草头的味道就升华了。炒草头很快,只有油、白酒和盐就够了,不用再另外加水。不过却最考验火候,大火、快煸,白酒、盐要几乎和草头同时入锅,等所有的菜茎变软了,就马上起锅,这样的草头才会又脆又嫩,最简单风味的野菜,也最好烹饪,一样有一种质朴的感觉。

以前,我总是将草头和故乡奉贤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仅仅在奉贤吃过草头,长大了才知道,上海郊区普遍都能吃到。后来我听说草头这种野菜,出了上海是不再能吃到的,这种想法,估计也信以为真了很久,直到我偶然知道《本草纲目》里就记录过草头,才怀疑这肯定是普遍存在的植物了。

李时珍对草头的叫法,是“苜蓿”。有个日本人岩崎常正认为,李时珍说的苜蓿,应该就是是南苜蓿。因为在他的记载里“苜蓿”是开黄花的。在《本草纲目》中他这样记载:苜蓿郭璞作牧宿,谓其宿根自生,可饲牧牛马也。处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一枝三叶,叶似决明叶,而小如指顶,绿色碧艳,入夏及秋,开细黄花。
如此,我对草头仅仅在上海就能吃到的幻觉就被打破了,因为他说“处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可见这种植物遍地都是了,只是用白酒烹饪草头的做法,不知道是否普遍存在。不过,对草头的兴趣却没有因此打消,发现古人对于这种植物的形容,更具美感,反倒更增添了兴趣。
令我更为惊喜的是,葛洪(另一说为刘歆)对于苜蓿的描述,就更美了。在《西京杂记》里,他这样写道:“游乐苑多苜蓿,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怀风’,又名‘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苜蓿、怀风、光风、连枝草,这竟然都是草头的名字,好像目睹了草头在微风阳光下摇曳的样子,能把寻常所见的野菜,写得如此美妙,估计难脱《诗经》的伟大根基,难怪说不学诗无以言,没有好好浸淫文化,恐怕连草头都吃不懂了,想到这些,不由得追悔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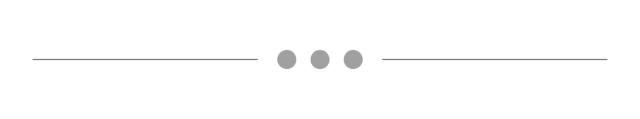
作 者 | 罗家俊
排 版 | 褶子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