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宇文所安推出新作,宋词如何从流行歌曲破圈进化|此刻夜读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韩熙载夜宴图》(原图局部 &《上新了故宫》图)


噢给我节拍 宝贝
让我的灵魂自由
我要迷失在你的摇滚中
漂荡 渐行渐远
Mentor Williams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苏轼
知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于2019年出版的《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初的词》本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中文译本。
在此书中,宇文所安聚焦并追踪北宋时期,词如何从宴饮助兴的表演文本——歌词,历经创作、传唱、抄写、结集诸过程,最终衍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逐渐取得与诗歌并举的正统地位。他一方面从表演实践、文本传播、作者问题、词集编纂与流变等全新角度将词史看成“词集史”而非“词人史”;另一方面又对代表性词人如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分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力图从多个层面呈现词的历时性发展及其作者化、风格化和经典化的过程。
今天夜读,从宇文所安的导读节选中进入宋词的进化之路,一起伴随的还有文人世界的复杂心态。



词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难题。研究宋代的严肃学者并不严肃对待宋词。词所呈现的世界并不是他们所熟知的宋代:旧的贵族政治落幕;在地方精英的支持下,权力从雄踞一方的武将手中转移到中央;中央对各领域的干涉也逐步强化。儒学重新兴起,并发展为更加注重内省的道学。道学最初还是独立于国家朝政之外,到了宋末却已渗透到社会结构和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商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政治理论也进一步获应用到治国之上。学者们熟知的宋代在思想上是个严肃的、试图把事物合理化(如果不是完全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各种层面上寻求清晰的统一性。
然而,跟这个理智的朝代最紧密相连的文体却是词。在词的世界里,人们不关心统一的整体。他们更关心的是失落的爱情,是一刻的悲欢,是一杯酒、一盏茶。大约在1028年,一位高官奉命回京,途中路过晏殊任职的驻地。晏殊办了一场酒席,写了以下词作,让年轻歌妓在宴会上给这位官员表演:
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
这是最温柔的抗议。它殷勤地提醒着帝国的臣仆:除了尽忠职守,为朝廷卖命,他还有别的选择。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晏殊
论者一般对于这种逃避主义嗤之以鼻,但那样就等于草率地放过了宋代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宋朝朝廷及其士人都把看自己看作公共价值的看守者,这是在唐代无法想象的。对于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宋代官员自有一套行事的先后标准。词,又称诗余,是诗的剩余物。宋人在处理完公务以后,对词有兴趣,才会把剩余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词上。而且,词似乎越来越代表着能把人引入歧途的松弛无度和不合规矩。一位士人首先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服务朝廷与家庭。在这之上如若游刃有余,他可以写诗。在这之后如果仍旧有余力,他或许可以写写词。填词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最边缘的活动。
宋词经常抒发对入仕的悔恨,或者劝听众无须进取功名。在歌词的世界中,更加普遍的现象则是,国家、功名、家庭统统消失了;词中只剩下情人——眼前的、想象中的,或者已经失去了的——深深烙在心上,刻入记忆之中。在词的世界里,社会约定俗成的先后等级和价值体系轰然倒塌。
逃避主义本身无甚趣味,然而,逃避主义就像相片的底片一般,其特定形状正好折射了产生逃避主义的那个社会。它暴露了人们体验那个特定社会体系时的真实面貌,也暴露了这个社会如何辜负了人的需求。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道德和政治统一性的追求一点点把人类经验中不符合这种统一性的东西过滤出来,整个社会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被隔离的空间,也就是剩余物,或者说是多余物。活在这个空间里的话语是被藐视的,它们常被称为小词。它们代表了一种抒发个人感性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外面更广大的世界里无法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在那个更广大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往往被词所吸引,有时词对他们的吸引力比任何别的东西都要大。的确,维护统一政权和道德宇宙的理想,首先要把与其对立的力量隔离在另一个话语的禁区里,即便所有人都造访过这个禁区。
在宋代的笔记里,当论家论及一个词人时,语气往往夹杂着一种困惑。这些评论往往说:某某是位极好的诗人(或学者),但他(或他的读者)却只在乎他的词——太可惜了!没有人真的会反思,世俗认可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与实际经验隐含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罅隙。社会公认填词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但由于人们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体现为参与还是否定),词也就取得了意义。
性别在这里也是关键。宋代精英士人惯用的文体越来越排斥女性。唐诗中的男女挑逗、情欲和怀想,全都从宋诗中消失了。本来乐府诗可以让诗人不做自己而扮演另一个角色,但这种体裁在宋诗中所占的份量也大大缩小了。甚至连母亲、妻子、女儿这些严肃的家庭女性角色,在宋代诗文中也仅仅是边缘的存在。
然而,词从一开始就和女性有很强的联系,无论是作为词的表演者,还是词所题咏的对象。传统评论也将男性词人笔下雨条烟叶的这种语句,看作以一种女性化的感性表达。苏轼确实追求一种男性化的词;但是,将苏词标志为男性化的标准,跟标志女性化的标准一样,都是一种以性别划分风格的话语,与性别标志相对不明确的古典诗歌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由于词体一般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文体,词评话语中的性别区隔产生了所谓的男性化词这一副产品。

关于晏殊的一则轶事正好反映了词体的性别区隔:据说,晏殊每日在家中宴客,都不提前准备,客人来了就端出酒食,每每有歌者乐人为宾客表演佐兴。稍息后,晏殊就会让歌伎乐人退下,说:你们已经充分展示了你们的才艺,现在轮到我们展示我们的艺术了。说罢,晏殊就会为客人备好纸笔,跟他们一起作诗。(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
要充分体会到晏殊这种说法的奇怪之处,读者们就必须知道,理论上,上半场宴会时歌女演唱的歌词,其作者正是包括主人晏殊在内的男性词人。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在中国文化中浮现。
我们将会追踪词从11到12世纪初的发展轨迹,看看词是如何从一种表演实践——把歌词写在纸上递给宴会上演唱的歌者——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词自成一体,表现为词人开始编选个人词集,为词集作序,并传播开来供人阅读。至此,词体已逐渐取得正统的地位。然而,即使已经正统化,词仍然是被隔离的——词作常常单独结集出版,即使跟传统诗文一起选入作者的别集中,词一般被搁在车尾,不是跟在诗后面就是在整个文集的末尾。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词人和词迷们的对这种排序有任何异议。然而,文体的隔离同时也给词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相对而言,早期词比较直接地表达追慕之意,或会直接铺写爱情、失恋、欲望等主题。这种直白的表达也逐渐被取代,而隐然指涉这类主题的比喻意象逐渐变为主流,但是,在词人日臻完美的技艺下,在他们对唐诗片段巧妙的运用中,词那如梦似幻、怅然若失的境界却得以延续。
自12世纪以来,古典诗歌便陷入了危机。随着道学的上升,诗被贬斥为不够严肃的追求。历来一直占有文化优势地位的诗统,在道统的轻蔑中崩溃倒塌。当时的诗人围绕着应该如何写诗展开了无休止的讨论。不少人替诗的形式辩护,然而,这些围绕诗歌的争论,却限制在道学的逻辑范畴之内,所触及的都是道学关心的课题,这本身就确保了诗永远不够严肃。词人和词迷却毫不介意。外面的世界日益一体化,他们在这个被隔离开来的空间内,继续快乐地创作。李清照所说词别是一家,最是恰当地捕捉了词人享受这种隔离的状态。

纪录片《历史那些事》中的李清照
在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段内,歌词从表演文本变成一种文学体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许多歌词作品从未彻底离开表演的场域。在表演之外,或者和表演一起,歌词也以手抄本形式在词迷之间辗转相传,通常这些手稿还附有题注和词评。曾慥于1146年为《乐府雅词》写的序里就提及,在他本人收藏的成篇的名公长短句以外,又有百余阕,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的作品。看起来,曾慥所指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手抄本词集,而是一张张写着一两首词的笺纸,有些注明了作者,有些则未标明。这些词作可能是从词集中摘抄出来的,但是曾慥的评论说这些作品脍炙人口,这显示甚至在12世纪中期,这些词作也还在表演和书写之间来回移动,而且流传时不一定附带着相关的作者信息。
词从一种表演文本,或者从一种在词迷之间流传的来历不明的文本,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这一转型并不容易。纵使在讲究版权和网络搜索功能如此强大的当下,我们仍然常常听到一首喜欢的歌而不知道歌词的原作者是谁。我们觉得自己最熟悉的版本就是正版,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调查,却经常会发现一首歌从一个歌手传到另一个歌手口中,歌词发生改动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歌词作者权也有争议。当词成为文学,它们就会按照作者时代先后排列起来。一个文本只应归属于一位作者名下。12世纪的宋代更是如此。一首歌词最终只会跟一位作者关联在一起,原本漂浮游荡的文字最终停泊靠岸。我们将会看到,歌词对这种秩序是非常抵抗的;歌词常常会再次从岸边起锚,又停靠在另一个地方;一首词有时会变成另一个词人的作品,有时又会在选集中以另一词牌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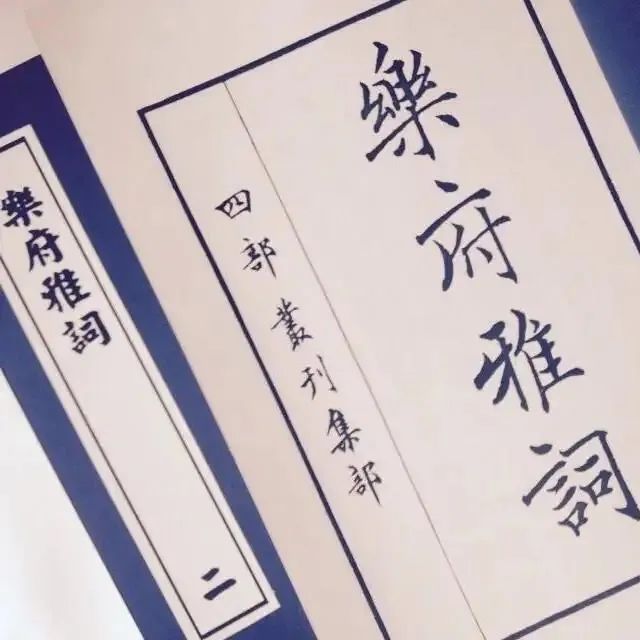
上述方方面面的问题理应跟歌词本身放在一起讨论,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然而,研治宋词的当代中文论著对这一点却不甚着意。论者一般把词和作者的归属看成既定事实。唐圭璋的巨著《全宋词》(1940年初版、1965年重编订补再版、1991年再出新版),在体例上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同时标明文本来源,其中宋词作品互见于多个作家词集的情况也清楚标注出来了。在此之上,后来的学者又试图把重要词人的词作按创作时间先后编年整理。除此之外,有些学者详细笺注了各个词人的词集。我们也有丰富的词论研究资料选,以及大量研究宋词的论著,包括多种宋词文学史著作。
如果我可以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研究成果,那么本书将会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但是我认为在继续探讨其他重要问题之前,我们需要重新梳理目前宋词研究在基本假设和方法上的一些根本问题。问题就出在中文学界的研究一直想把宋词作品纳入一个以作者为归属的文学体系,而忽略了一个事实:作者是由传世书籍所缔造出来的;当我们将词史看作词集史(考虑词的来源及这些书籍的性质),而不是词人史,那么我们对词体演变的理解将会随之改变。
一旦我们打开了文献的潘多拉魔盒,开始考察个别宋代词集的编纂和流传的历史,我们便会看到一个与宋朝诗文迥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本书的主旨不在于描述宋词编选刊刻的种种细节,但会讨论几个尤为重要的案例,并分析其特点。明人和清人常常自诩他们找到了宋版词集,但这些号称宋版的词集常常是被编者校订过的文本,编者为了得到全本,往往会添加新发现的作品,或者删除掉那些被认为并非出自作者的作品。他们的理想版本是宋版,影宋本次之——有的影刻本所依据的宋代底本仍然流传于世,有的则没有了。
在苏轼之前的11世纪所有词集,其现存文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吴讷于1441年编选出版的《百家词》——唯一的例外是欧阳修的词集,现存有两种版本。吴讷《百家词》本身,现存两种抄本均有残缺。13世纪长沙书坊曾汇刊出版一部同样题为《百家词》的词集。虽然吴讷的选本很可能部分基于这部已佚词集而编定,但吴讷的选本跟长沙本所收录的词作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足以使我们怀疑两书的关系。无论如何,冯延巳、晏殊、张先、柳永、晏几道以及其他许多词人的作品最早的文本来源,正是吴讷的《百家词》。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核心的问题上:对于宋代诗文集,我们大多可以根据它们的序、跋、书志目录等信息,复原出该诗文集从作者自己的手稿到现今版本这一过程的大致路线;但是我们没有关于北宋词集的类似信息。我们不太知道词集是怎样编定的、什么时候编定的,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文本在早期流传中有多稳定。假如我们有一部15世纪中期的抄本,而这部抄本抄自13世纪书商的刻本,我们有理由庆幸;但是,至于每部词集如何流传到13世纪的书商手上,我们确实知之甚少——而我们有理由对13世纪书商的顾虑有所警惕。本书试图从有限的信息中梳理出这些词集早期的历史。

本书不打算讨论唐五代词,只有南唐朝臣冯延巳的词集是例外,他的词作是11世纪中期词曲表演常备曲目的一部分。田安(Anna Shields)已经对《花间集》(附有940年写成的序文)做了具体而微的考论。《花间集》在词集史上有一个稳定的位置,但它不是这个延绵的历史的一部分。除了那些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了冯延巳词集的作品以外,直到11、12世纪之交,我们看不到证据能证明当时人知道这一部选集的存在。《花间集》及增补该集的、编年不详的《尊前集》的回归,都应该被视为后代词人重新建构词史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伴随着词成为文学的过程。若非12世纪读者对词体的历史产生了新的兴趣,《花间集》亦不太可能在12世纪被刻印出版,也不会有做工精良的1148年版《花间集》流传至今。再者,没有这个刻版,没有对该集的关注程度,《花间集》这本词选本身也就不太可能留存下来。祖先之所以成为祖先,完全是依靠他们的子孙。现存所见《尊前集》的最早来源也是吴讷的《百家词》,而试图把《尊前集》定位于1070年代前的材料极不可靠。
除了冯延巳词和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的若干作品以外,在《花间集》与11世纪初的柳永、晏殊、张先之间的这段时期几乎什么词作也没有留下来。现存作品中只有很少量的歌词被认为是活跃于北宋第一个五十年的词人写的,即使是在这少量的作品之中,大部分词作也是很晚才被书面记录下来的。换句话说,歌词的实践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关于词的记录却是断裂的。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电视剧照
原标题:《宇文所安推出新作,宋词如何从流行歌曲破圈进化|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