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湃思想周报丨加拿大养老护理风波;纪念阿吉兹·阿罕默德
加拿大养老护理风波
2022年2月,维克多·卡斯塔内(Victor Castanet)的新闻调查类著作《掘墓人》一举登上法国畅销书榜首。该书揭露了欧洲长期护理连锁机构Orpea虐待老人的历史,包括忽视老人的疾病、无法为老人提供充足食品以及尿布等等。多名老人在进入机构迅速消瘦;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月费在6500到12000欧元之间的高端护理机构内。《掘墓人》一书在法国引发了巨大的公众反响。Orpea正在遭受公开调查,并且遭受了股价暴跌。[1]

法国养老机构的老人
上个月,国际企业税务责任与研究中心和法国最大的两个工会联盟,法国民主与改革联盟(CFDT)和法国总工会(CGT)发布了关于Orpea财务不当行为的报告,特别指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 Orpea 15% 的股份,并且在Orpea的董事会中拥有两个席位。加拿大公共雇员联盟呼吁CPP停止资助长期护理部门的虐待行为,并停止营利性护理。[2]
据统计,法国共有7500家供养老住宿设施,约有60万老人入住,他们的平均入住年龄为85岁。这些老人平均患有八种疾病,其中一半患有痴呆症(多为阿尔茨海默病)。更令人震惊的是,由于该行业内有着极为严重的旷工情况,许多护理院都面临着人手不足的窘境。平均每位老人只能获得不到一小时的护理,而私营部门的监管人员平均比公共部门少四分之一。养老院较低的人员配置水平已被证明增加了老年人的负面健康结果,老人往往缺少体位变换和如厕协助;并且有着较高的压疮、骨折、呼吸道感染以及严重跌伤几率。[3]
加拿大公务员工会的秘书兼财务主管坎迪斯·伦尼克(Candace Rennick)宣称,“由于只关心利润的跨国公司削减成本,长期护理院中的老人在大流行期间遭受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加拿大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们的退休收入投资于这些残酷的计划中,为这种虐待行为提供资金,这是无法想象的”。工会响应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的呼吁,要求将长期护理国有化,并将其纳入《加拿大卫生法》的管辖范围。
资助剥削老人的行为
Orpea并不是唯一一家由CPP资助的声名狼藉的长期护理机构。据透露,2020 年,加拿大第二大私人长期护理提供者Revera由CPP全资拥有,其记录的新冠死亡人数几乎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在这场大流行中,营利性的长期护理中心一直被证明有较高的死亡率,较多的经过核实的投诉,以及较低的护理标准。但CPP通过投资该机构获得了巨额利润并实现了避税。
对于许多退休人士来说,养老金是他们安度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CPP投资的不确定性,导致养老金投资界一面承担风险,一面采取激进行动。正如CPP的一位主管所说,“某些国家的人口结构使得(医疗保健)成为了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长期投资。”养老金投资者为老年人护理的潜在利润而欢呼,并且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支持老年人。
2017年《加拿大福利》(Benefits Canada)杂志的一篇文章建议养老基金密切关注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以利用老龄人口的需求。他们甚至把Orpea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基础设施方面,医疗保健房地产已被确定为未来的潜在摇钱树。对长期护理床位需求的增加,被认为是投资者的一个“增长机遇”。
由于加拿大立法保护国内医院建筑不能被私人拥有,加拿大养老基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方面获得盈利的机会。2015年,CPP与美国公司Health Care REIT合作,在南加州收购了一系列医疗建筑。
随着全球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金融界已经把医疗保健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养老基金一直是该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基金在希望安度晚年的人们的支持下,已经发展出巨大的投资组合。
养老金的矛盾
值得强调的是,养老基金的最终责任是以福利的形式支付其成员的退休费用。它的利润被分配给它的未来受益人:当下的工作者们。然而,金融业已将基本必需品确定为获取利润的土壤,该投资在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养老基金在支持受益人的退休生活的同时,也助长了退休生活越来越难以负担的现象。养老的金融化与养老院的阴影笼罩着退休人员,让人感到恐惧。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矛盾?如何保证养老金投资不会剥削它们声称要支持的那些人?《雅各宾》作者汤姆·弗雷泽(Tom Fraser)指出,第一步是将医疗保健的所有方面(从提供医护服务到设立基础设施),从资本积累的范围内移除。正如加拿大公共雇员联盟国家主席马克·汉考克(Mark Hancock)所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父母的生命,以及我们祖父母的生命都不应该成为利润的来源。如果我们要打破退休与金融的复合体,社会再生产的政治经济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帮助有需求的群体寻求价格合适的护理机构,增设可负担的居家护理、家庭医生等等。
第二步是对养老金投资进行民主控制,并将其重新导向积极的政治改革。将养老基金运用到非营利性的目标上,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养老基金应该投资于非营利性的长期护理,或用来建立能够在家中为人们提供护理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网络。
弗雷泽在文末强调养老金是全球范围内退休危机的核心。但是养老基金和长期护理设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退休本身已经商品化。因此,公正的退休生活需要“养老”在各个方面进行去金融化,从而使老龄人口获得他们应得的尊严。[4]在全球许多中老年人群因遭受新冠冲击而提前退休的当下,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引用文章:
[1] https://ici.radio-canada.ca/nouvelle/1858352/orpea-scandale-france-bourse-office-investissement-regime-pension-canada
[2] https://cupe.ca/canadian-pensions-bankrolling-elder-abuse-and-misappropriation-public-money-french-long-term-care
[3] https://www.francetvinfo.fr/sante/senior/soupcons-de-maltraitance-chez-orpea-six-questions-sur-le-fonctionnement-des-ehpad-en-france_4936631.html
[4] https://jacobinmag.com/author/tom-fraser
纪念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1941-2022)
2022年3月9日,印度学者、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的代表人物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与世长辞。近日,The Wire刊出印度学者Shelley Walia的纪念文章,梳理了阿罕默德的思想遗产。

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1941-2022)
Shelley Walia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在理论内部》(也是他众多著作中唯一被译作中文的著作)出版时,正值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生因法国理论的风靡而被卷入虚无主义的漩涡之中,他对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毫不含糊的谴责——因其取代了20世纪60-70年代学术界重要组成部分的行动主义和政治异议——使他一举成名。阿罕默德本人也正是那个行动主义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见证了大规模的去殖民化和世界各地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众多文章中,他指出法国哲学需要对行动主义让渡于文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负责。阿罕默德对包括爱德华·萨义德和詹明信等学者在内的整个学院责任缺失的谴责,引发了众多公开讨论。阿罕默德也像其他左翼学者一样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者,但有一点不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开始认为大学已经变得更像商场,在那里,理论被卖给毫无戒备的学生,然后把他们转化成自由市场的消费者。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些理论的“保质期”是有限的——就像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一样,因此,当代教育不断讲这些概念时,就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同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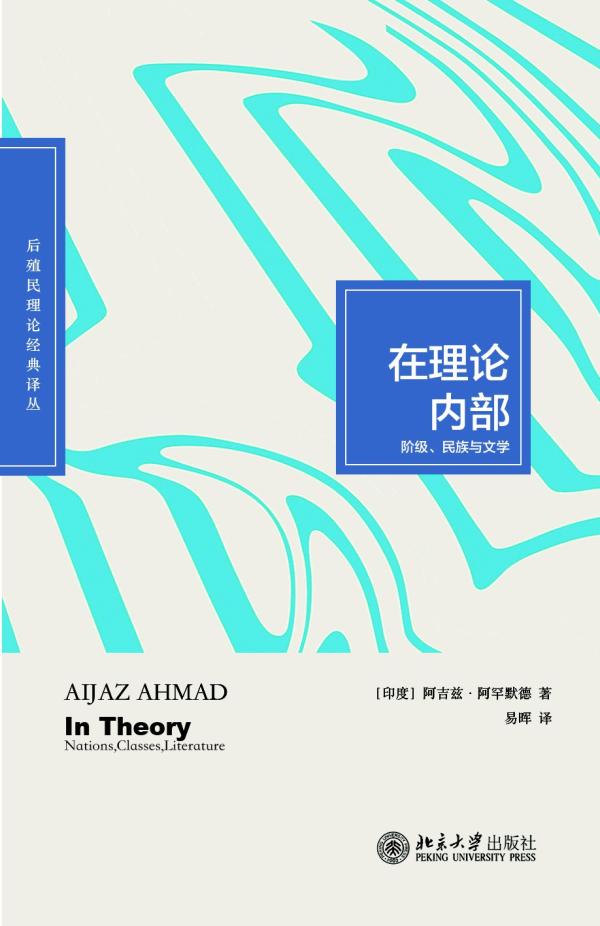
“时髦”的哲学开始被提倡,尤其是被移居到西方的第三世界学者所提倡。“移居”和“流亡”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了当代大学教学和研究的词汇中。“混杂性”不再与创伤和脆弱联系在一起,而是成为新流行语,摧毁着主体性和稳定性。成为“混血儿”已经是一种时尚,像萨义德所说的“文化两栖动物”,阿罕默德写道,生活在底层的真实的人渴望并憧憬着稳定,而西方大学以及印度那些模仿它们的大学则鼓吹流浪,在生活现实和学术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进而他也悲哀的发现自己成为了这个体制中的一名哲学家,其马克思主义批判事实上仅仅会助长了那些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权被剥夺,或成为大规模人口逃亡的一部分。弱势群体生活中的这些痛苦情节与今天大学里教授的“边缘性”(marginalization)和“离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毫无共通之处。
在他对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批评外,阿罕默德的意图始终是要传递人类免于战争、政治迫害和压迫之自由的信息。他所经历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他不知疲倦的热情中显现出来,这与反对体制、为所有公正和公平的事物而奋斗的行动主义有很深的联系。在新左派的斗争中,无论它们在新自由主义的辩护士手中被描绘得多么凶恶,使草根运动能够整装待发进而得以对抗精英主义的反对力量,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阿罕默德为这种“新政治”提出了论述。尽管许多国家的领导层在倒退,但西方世界显然正在形成这种政治。比如,英国工党向社会运动的转型,正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对落后的保守主义领导层的指责,强调左派在草根政治的蓬勃活力和塑造真正的民主社会之必要条件之间所产生的关联。因而,摆在公共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检视和质疑公共政策的制定,首先关注其与大众的相关性。阿罕默德始终致力于检审官方对政策的解释,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把“整个生活方式”放在首位。“新政治”并不仅仅是一些提醒;它是对在草根发起的、旨在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运动构想的真诚回应。
我们失去他的时刻,正逢“世界新秩序”的承诺支离破碎,黑人、犹太人、拉丁美洲人、亚裔美国人和穆斯林被前所未有地边缘化,仇恨犯罪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饥饿和瘟疫等压倒性的危机正等待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在一个日渐变成法西斯主义的世界中,进步的行动主义确实是一种激励。当右翼民粹主义者和左翼教条主义者自以为是地反对自由主义的概念时,阿罕默德成功地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唤醒式的辩护。对他来说,自由主义是他自身的一个基本要素。阿罕默德竭力完善马克思理论,主张开展新的进步运动,并以更加开放和参与性的社会主义形式作为支撑资源。他坚信需要重新发明一种人民的政府,不仅要解决女权政治和生态灾难等紧迫问题,还要设想一个建立在平等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和一个为不一致观点提供支持的政治制度。
参考文章:
https://thewire.in/society/remembering-aijaz-ahmed-a-marxist-rebel-without-paus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