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青年电影人:拒绝被疫情浪费的青春
采访并文 | 格温
编辑 | 林子尧
张博凡是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制片项目毕业的硕士生,也是一位工作在中美两国的制片人。赴纽短短三年,她成为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 Newcomers 项目入选制片人,也成为了Katharina Otto-Bernstein电影基金和GiGadgets创意基金获得者。她制片的长纪录片《盲弈》入围美国最大纪录片节DOC NYC国际竞赛单元;长剧情片《破卵》入围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第10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会。现在,她在寻求一种跨越中美的电影事业。
以下是青年电影人张博凡的口述:
疫情之前的纽约
我在2018年夏末,8月份到达纽约。刚来时,从肯尼迪机场打车到哥伦比亚大学,一路上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更加现代版的香港。开始融入本地生活以后,新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脏脏的国际都市。

张博凡
我是江西赣州人,有时会说自己是“山里面的孩子”,因为赣州山清水秀,有许多好山好水。本科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影视制片管理时,我参与了一些学生短片制作项目,发现和电影很合得来,就选择在大三时申请美国的电影制片硕士。纽约其实不是第一选择——我更想去加州,去美国电影学院。但是面试之后“梦校”发了一封拒信,刚好哥大那边发来了offer,我就想:好吧,其实去纽约也不错。
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制片MFA项目的学制一共是三年。第一年的课程设置很紧张,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这三个方向的学生会在一起上课、完成作业,第二年后才会根据专业分开。导演课每两个星期就要拍一部自己的短片,需要自己找组员、租学校的器材、自己剪辑,然后在课堂上展示,还有编剧课和教如何和演员合作的导演演员课,都有着巨大的工作量,每个星期不是在写剧本就是在拍片子,找别人帮自己拍、也帮别人拍,我和同学们可以说是通过拍片子相互认识的。
我的第一部学生作品,是研一第一个学期的期末作业,叫作《回响》(Reverb)。它讲的是一个小钢琴家克服听障,学习用另一种方式聆听这个世界的故事。当时我对制片理解还没有现在那么深刻,学生作业里,制片人是不出钱的,而是导演出钱,也由导演牵头。那时,我把制片人看作一个服务性的工作,为导演的艺术服务,他需要什么样的演员,就给他找什么样的演员;需要什么样的场地,就跟他一起去四处寻找这样的场地。一个制片人要从各方面给项目提供支持,也包括给导演提供情绪价值。
导演姜敏圭和我在选角上面上花了很大的心思,我们找遍了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去寻找一位会弹钢琴的小演奏家,最终有机会和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小演员叫Alexa Swinton一起合作。当时这个项目只拍了两天,一天在布鲁克林租了一个Brownstone公寓,第二天借用了校园学生活动中心大楼里的一间钢琴房,其实是一个非常低预算的剧本。这部片子一开始剪了十分钟,感觉不是特别理想,便先搁置了下来。
在拍摄一部片子时,也会渐渐加深对纽约这座城市的理解。比如说《邮递员》(Postman)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邮递员在派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位濒死的油画家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场地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定要有一个火车紧挨着公寓、然后迅速地从窗子边飞驰擦过的镜头。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找,导演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火车一定要和窗户贴得很紧,能在屋里感受到火车经过时的震动。当时其实也做了二手准备,是一座没有火车经过、但有漂亮大窗户的屋子,但我们都想要找到最好的地方,就去谷歌地图上,一直翻,把地图放大好几倍,看有没有地铁会紧挨着经过住户,最后我们锁定几个地点,定下来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地铁口,但是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公开租赁的电影拍摄场地。

张博凡在《邮递员》堪景的休息时间读剧本
那里有一条整街道的房子都挨着地铁。我们就一户户敲过去,多数都是否定的回答,但是问到一户时,户主居然答应了!因为他楼上刚好就是一个油画工作室,他的妻子就是一位油画艺术家,他也能理解我们的艺术追求。我们马上堪景,把剧本的人物从本来的老人改成了一个油画家,没有改变他们那边太多的布景,拿来作为主人公的家和工作室。
《邮递员》这个电影的场地几乎都是我们亲自上门协商拿到的,包括邮递员经过的玲琅满屋的古董店、门口养着鹦鹉小鸟的杂货店、有火车在空中穿过的街道书店等等。当时我们在纽约敲了许多扇不同的门,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对我们和拍摄请求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比如有一位老人觉得我们的行为很鲁莽,认为打扰到了日常生活,一句话都不想跟我们讲;有些人会答应,还邀请你去进屋喝茶。打开房门,你可能会看到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可能是一个略显凌乱的油画工作室,你能看到不同纽约人的生活状态,都是大异其趣的。
随着我经手的项目越来越多,我发现最大的难题其实是突发状况。每一个项目的突发状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好的演员在要开拍的前一天放鸽子,突然接到电话要租新的大道具、需要重新定交通计划等,考验临场应急能力。第一节专业制片课,老师就交代做制片人预算表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东西——应急预算,它可能占你项目的6-10%,甚至更多,是永远都不能省略的。
这也变成了我的一个生活技巧,一定要做二手准备,因为事情永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顺利,一定会有意想之外的突发状况发生。
突发状况
我是一个容易感受到焦虑的急性子,对自己大大小小的规划——有细节上规划,有大方向的规划,需要整理得非常有条理,一旦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点偏差,焦虑就会赶上我。
谁都没有料到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这可以说是在读书期间遇到的最大的突发状况。2020年的3月份,疫情在美国开始爆发。我和一位美国导演合作的一个项目,第二天马上就要开拍,然而一夜之间,疫情的消息就开始在整个美国、纽约城里蔓延开来,城市里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有一种声音说,纽约市马上要封城,出去就进不来了。我们的拍摄场地和纽约市有一段距离,并不在市内,于是很多组员开始恐慌,说我们不去拍了。那个时候,项目的钱都已经预付了出去了一半还多,包括餐食、交通、器材、场地等等,但是还是不得不终止了项目,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新冠病毒的真实情况,美国和学校也没有明确的拍摄安全指导规则和意见,医疗保险也是不明确的:比如说染上了新冠,应该怎么赔付?如果没有明确医保,我们剧组不可能负担得起高额的治疗费。

张博凡生活照
我的其他项目因为疫情,也就直接没有拍。那半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一些老片子的后期,还有一个独立长纪录片的后期工作,甚至包括第一部学生作品《回响》,也在疫情期间重新拿起来剪辑。因为疫情很多项目都被截断了,我就和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剪一剪,把后期混响做更精致,然后再投一些电影节试试看,没想到后来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2020年初,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纪录片专业的浦韫鸿导演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做她第一部长纪录片《盲弈》的副制片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想要去做更多的项目、不想停下来,同时我也很喜欢浦导,所以当时就决定一起合作。疫情期间的主要压力还是在她身上,因为那时主要是后期工作,不仅我和她见不了面,她和我们的剪辑指导,一位艾美奖提名的剪辑指导老师,也因为疫情没法见面,所以一直在远程和各方面的人沟通。我则负责找一些创投会、入围,制作宣传文本和物料,然后寻找资金机会,然后有机会拿到资金,制作电影节的策略,考虑在哪里首映,找一些次级代理,如何把我们的片子卖出去。
最忙的是研二到研三的这段时间,我手上不仅有国内的一个长片项目、纽约的一个长纪录片项目,还要准备两个毕设的奖金申请和实习。最忙时是纽约时间和北京时间一起过,因为要跟国内的资方接触、沟通,他们那边安排的是北京时间的下午,我经常要凌晨三四点爬起来打一两个小时电话,然后睡两个小时,过后做纽约这边的项目,就必须马上就换一个时差模式,这样循环往复大半年。因为疫情,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家里面,物理奔跑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身体还算缓得过来。最困难的或许是研二的夏天,因为我性子急,害怕研三来不及找实习,所以很早就开始联系各种不同的人,但是那段时间的反馈也不太好,整个人就开始焦虑,再加上疫情的影响,经济和工作上也不是特别理想,这一切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因为这完全是计划之外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出门走一走是缓解焦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纽约是个有趣、值得一走的地方。有时会叫上朋友一起,在哈德逊河一带逛一逛,那里的风景非常漂亮。
之前,我还喜欢自己一个人去逛艺术馆和博物馆。在哥大的北边一点,有一座修道院博物馆(The Met Cloisters)。那里展出了一个系列的16世纪围捕独角兽系列的挂毯,表现了捕杀的残忍画面,生命和自然的搏斗展示着原始的力量,这和纽约这个大都市本身是截然不同的,让观者从中获得一刻喘息。
作为一个特别着急的人,平时我不管是坐地铁、还是走路,都走得特别快。前两天我和往常一样在纽约地铁站里行走,就发现时代广场转站的一个地下连接口里面,一个戴着大的假发头套、穿着粉色宫廷服的女演奏者,正用大提琴演奏着巴赫。我站在那里,顿时感受到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地铁的转站口匆匆的旅客中间,一个极其悠闲的表演艺术家,一响起琴声,很多人就停下了脚步。艺术存在于这个空间本身就会给人慰藉,让人又发现了自己立足的地方。

纽约地铁里的女演奏者
在研一时拍摄的片子,很多刚好都是疫情时入围了电影节。其实疫情中的线上电影节,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主办方会设计各种小程序,有的比较大的平台可以让你进入他们的程序里走一圈,就像一个小游戏:这边是展映厅,那边是咖啡区,然后还有休息室,虽然是虚拟的,却五脏俱全。
2020年FIRST电影节时,我也没能到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影节,有创投展示单元,结束后还有酒会,有机会去和志同道合电影人进行交流,也可以看到对方的项目,对青年电影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虽然有点遗憾,但是我也参与了所有前期的准备,包括宣传物料的设计,参与感是很强的,而且导演高书和编剧吕默很照顾我的感受,经常更新情况,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整个是线上参与,但是也有很强的参与感。
疫情的那一年一瞬间就过去了,除了和那位美国导演的项目因为资金方面支撑不了重启,是我唯一一个放弃的项目,其他的在疫情之后都已经陆续开拍,很多现在已经拍完了,有的马上要拍。
重启
疫情趋于平稳后,我回到了国内。那时手头上还在进行两个偏项目开发类的加州的实习,每个星期至少要读两个剧本,大部分是英文的,每个剧本读完以后要给几页文字版的总结和评估(美国行业里叫coverage),上交给上级。我和另一个团队也卖出了吕默编剧执笔的长片剧本的版权,开始前期筹备、开剧本会和堪景。同一时间,还开始给哥伦比亚大学两个毕设短片项目整理融资材料、进行前期筹备和远程制片。
现在,我对自己制片的项目有了一些“主权和主导意识”,也就是主观的规划,比如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下一步应该计划什么,预算规模如何、怎样组建主创团队,在选角、选场地的细节问题上,也都给出自己的意见。但我心中有一个想法没有改变,就是作为一个制片人,选择了一个合作者、尤其是合作导演,能给到的最大的、对他和对自己的保障,就是那份信任。选择信任,相信导演的能力、相信自己选择的剧本,也相信做出的和他要一起完成这部电影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疫情,其实最早的计划是毕业以后把纽约和北京都作为我的基地,两边同时做好不同的项目。经过了本科四年,北京就像第二个家,有许多好友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感情上更亲近。纽约,更像一个奋斗的地方。它具有丰富的多面性,第五大道高级时装店的橱窗,曼哈顿随处可见的街头嘻哈艺术家,永远在排着长队的中国城的点心,中国城隔壁就是小意大利,苏豪区华丽的街角咖啡店,各种文化杂然共存,就像一个缩小版的世界。
现在看来,穿梭在两国之间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景,但是现实的状况似乎不太可能,不是选择中国,就是选择美国,因为现阶段隔离就需要一个月,而且来回机票也特别贵。也许需要等三到五年才能知道答案……做电影本来也是看运气和缘分的一件事。
如果足够幸运能在电影业立足,我希望成为一个专业的制片人,有能力同时操盘多个项目,融入中国和美国两边的本土文化和行业,开发出能够被市场都接受的电影类型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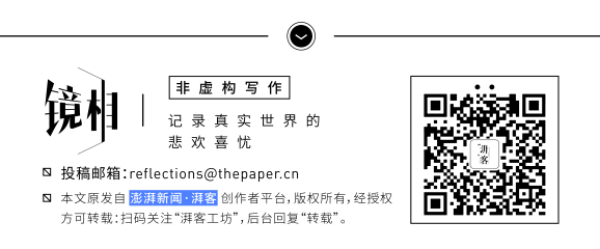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