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右翼观察丨极右翼为什么热爱托尔金?
很少有人会讨厌《指环王》。
不管是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长着毛脚的霍比特人、高贵的精灵、睿智的巫师,还是严谨的语言学与神话设定,读者总能在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中洲世界中找到自己所爱。虽然被誉为英语文学奇幻史诗的开山鼻祖,但是在《指环王》出版的头几十年,它只是英国的小众文学经典。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外地在嬉皮士时代的美国一炮而红后,《指环王》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披头士乐队想要亲自改编和出演改编电影、齐柏林飞艇和平克弗洛伊德等摇滚和朋克乐队发行过《指环王》主题的歌曲,刚刚去世不久的托尔金突然登上了大众流行文化的神坛。

《指环王》海报
随着21世纪初经过彼得·杰克逊改编后搬上银幕并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指环王》再次焕然新生,托尔金的中洲故事一跃成为影视剧改编的摇钱树,《霍比特人》、《精灵宝钻》等等作品先后都被提上了日程。就连原本面向低龄读者的儿童文学《霍比特人》都被大幅增加内容改编为三部曲电影,与此不同的是,描述横跨数万年中洲早期历史的《精灵宝钻》的改编一直搁置到了2017年解决版权争议后,才由亚马逊着手投入超过4亿美元拍成剧集,计划将在2022年9月以《力量之戒》为题发行第一季。该剧从选角阶段引入黑人角色开始,就引起了不少指责片方强拗“政治正确”造型的批评,而到预告片中出现深色皮肤精灵后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换作任何其他奇幻作品中,在幻想种族中出现一些不同肤色的人物都未必会引发如此哗然,而《指环王》一则本身作为史上最成功的奇幻小说实在是万众瞩目,二则中洲世界固然是空想世界观的空中阁楼,但对世界观严谨把控到时间单位都有详细设定的托尔金来说,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了他的个人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构建故事的凡人只能够从自己所知的事物开始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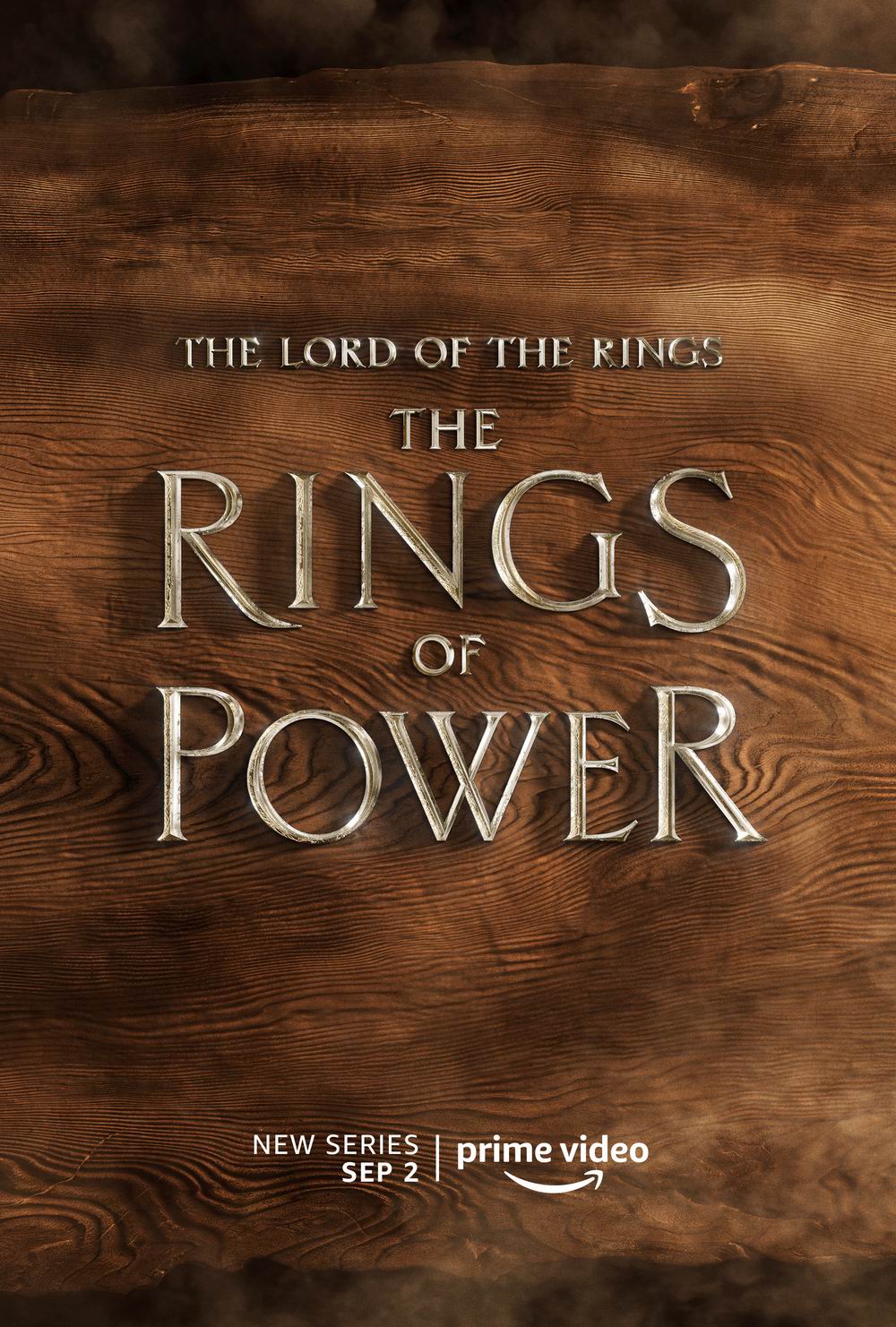
《力量之戒》海报
与叛逆的美国嬉皮士不同,托尔金本人不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还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同时,托尔金身为对古代史诗和神话颇有研究的牛津大学语言学教授,在中洲的世界观设定中大量借鉴了日耳曼、凯尔特等古代传说,有意识地将中洲作为一套英国的现代神话来打造。为此,他赋予中洲严谨、复杂甚至冗杂的设定之余,却坚定地保持着鲜明的正邪对立和简洁的人物塑造,以使古典的、神话性的善恶主题得到突出,以至于有批评认为他的作品情节推动过于简单,类似天降神鹰之类的机械降神桥段泛滥。尽管亲身经历过一战绞肉机一般的索姆河战役前线和摧毁了整个欧洲的二战,托尔金仍不断否认自己笔下堕落的人类世界和黑暗的东方君主是影射和讽喻的寓言,强调不要用《指环王》的故事去比照现实。事与愿违,他不但没能避免《指环王》成为他不理解的嬉皮士生活的新《圣经》,亦未能阻止自己成为右翼的心头好——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受传统主义和新右翼影响的新一代极右青年运动在托尔金作品中找到了共鸣,他们受其启发举行了“霍比特营”(Campo Hobbit)活动,号召参与者回归自然、打破界限,寄望于“霍比特营”能够成为右翼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仅如此,很多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都推崇托尔金,把中洲的诸多故事当成一种道德寓言,并列为青年必读书目之一。
结合托尔金本人的政治倾向与他的《指环王》等作品在右翼社群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力量之戒》的改编会有如此大的反响——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极右对托尔金作品改编方向的争议不仅是夺取话语权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还在思想根源上与托尔金作品所表露的旨趣高度重合。倘若托老复生,很难说他高度右倾的政治观念会不会让他和罗琳一样被“取消”。这也是长久以来托尔金作品面临的悖论:一方面是托尔金本人保守的政见,另一方面是极其广大的自由派读者群体对其做出的解读,二者其实很难调和。但或许,根本没有调和的必要。
托尔金的“非政治”
托尔金在世时并不以政见犀利闻名,更没有什么活跃的政治参与经历,事实上可以说他有意识地保持“非政治”(apolitical),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对政治话题表达见解。托尔金自称不是民主主义者(“‘谦逊’和平等是一种精神原则,被试图将它们机械化和形式化的企图所腐蚀”),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计划者’一旦获得权力,就会变坏”),但是他曾明确表示过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支持(夸赞支持佛朗哥的记者是“当代的阿拉贡”)。这些见解一部分在中洲故事以外的私人书信等作品中有相当直接的论述,另一部分则在他的著作中以他非常厌恶但又无法克制的寓言、象征等形式出现。倘若有人尝试为托尔金确定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他只会落在他广大嬉皮士粉丝的对立面:他反对现代社会、反对大政府、反对工业化、反对城市化、反对离婚、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道德虚无主义、反对平等主义、反对大众民主……唯独在反战、享受具有致幻效果的植物(夏尔的烟草)等等少数问题上,他才稍微显得“现代”些,令他在嬉皮士之间广为流行。

英国作家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
一些书迷很快会翻出托尔金在信中“官宣”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段落,但托尔金的“无政府主义”绝非号召暴力推翻摧毁一切统治形式的无政府,亦非共享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决策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而是夏尔那样社群自治性的“无国家”(stateless)。他的信件原文说,“我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倾向于无政府(Anarchy)(哲学上理解,意思是废除控制,而不是拿着炸弹的人)——或者是’无宪的’(unconstitutional)君主制。”由托尔金把“无宪的”君主制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词就能看出,他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君主制。而从他在《指环王》中对自己认同感最强的霍比特人的描述来推测,托尔金的无宪君主制并非专制君主制,而是类似一种自由意志主义式的自治小团体的联合,同时其君主并非依据某种人类的规定来统治,而是依照大家心照不宣、自觉自主的默契,或者说遵循超验的神的旨意。在他看来,集权的政府会形成一种他称之为“他者统治”(Theyocracy)的心态,也就是说自己在被一些遥远而疏离的其他团体所统治。他在信件的后半部分补充道“对任何人来说,最不合适的工作都是对别人发号施令,即使是圣人(他们至少不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他举例来进一步说明:“中世纪把’nolo efiscopari’作为授予他人主教头衔的最佳理由,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在中世纪天主教任命主教时的仪式时,候任者需要念三遍“nolo efiscopari”,意为“我不想成为主教”,之后才能完成确认。他描绘的理想君主阿拉贡在书中数次主动拒绝获得魔戒和掌权的集会,反映出他对君主和权力关系的认知:只有不想要权力的人才能掌权,这样权力的作用才能最小化。也就是说,托尔金认为任何人类都不应该追求和掌握权力,除非这种权力源于自然,或者说源于更高级的存在。他在另一封信中更加直白地解释了他的理想社会,他提出要解决人类本性的普遍堕落带来的灾难,“唯一的治疗(除了普遍的皈依以外)就是不要战争——也不要计划,不要组织,不要管制。”
与这种极端反对管制的表态有所出入的是,托尔金曾承认自己会乐于恢复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如他所说,“对乡绅点帽致意对于乡绅来说可能糟透了,但对你来说可是好极了。”其言下之意,政治并不应该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去参与的,即便有人享有特权,下层的人也应当遵守这种身份等级制度。如果等级不是出于人类的规定,而是一种天然的、应该得到广泛接受的秩序,那么就应该得到遵守和保持。这从他最有认同感的夏尔的设定中就可窥见一斑。在他的描述中,主要是森林和田园的夏尔孤立且自治,认可人类国王的法理统治但并不真正为其所指挥,虽然有世袭的长官也有选举的市长,但他们只具有名义上的尊贵和仪式性功能,真正在负责管理的是各个家族。托尔金写道:“霍比特人遵循古时君王的一切重要法令,而且通常他们都是自愿遵循法令……那些都是规矩,既古老又公正。”由于耕种和霍比特人特有的大胃口已经占据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夏尔当地不但没有政府,连维持秩序的暴力组织都没有,只有一种实际上管牲口走失的“夏警”(Shirriff)。并且,夏尔内部存在着近似种姓制的等级秩序,就比如山姆的甘吉家族是为弗罗多的巴金斯家族世代服务的园丁,因此山姆对其他几个霍比特人的称呼都是“老爷”(master),特别是图克家已世袭数百年的夏尔长官,巴金斯家则长期是他们的姻亲。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强调霍比特人这样来自边缘的“小人物”在拯救世界的过程当中扮演比血统高贵的国王还重要的角色,以图说明托尔金的某种底层同情,但仔细研究就会感到失望,因为就连这些小人物也还是出身高贵的,唯独故事的真英雄山姆是唯一的例外——当然这还要排除山姆的金发不是继承自众多尊贵霍比特家族所属的白肤族的可能性。
托尔金笔下的乌托邦夏尔“几乎毫无改变,而且代代如此”。在电影中这种状态的确一直延续到战后,但其实在书中托尔金还安排了一段乌托邦被毁的《夏尔平乱》章节。其中描述被索隆腐化的巫师萨茹曼篡夺了夏尔,实行征粮和统一分配,开发自然并修筑工厂,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定(rules,与规矩相区别),把夏警变为了负责实施新规定管理群众的组织——换句话说,使夏尔“社会主义化”了。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这样的夏尔“比魔多还糟糕”。托尔金在这里的意思不能更明白:社会主义是违背天性和美德的邪恶形式,只有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当中美好的传统才能长久不衰。托尔金不但相信人类处于迷信物质主义的堕落中,笔下的中洲也处于不可避免的衰退中:早在诸神创造世界时,堕落的维拉(Valar)米尔寇(Melkor)就已经污染了作为神灵造物的“阿尔达”世界(Arda),因此所有的中洲造物都不可避免地有堕落的倾向,对诸神的信仰和魔法的力量在中洲不断衰退,到第四纪元时就连精灵都已经不再居住在中洲,人类的纪元被视为最平凡的时代。他甚至在构想的《指环王》续集当中设定在阿拉贡死后政治家都变得很平庸,出现很多崇拜邪恶、装成奥克半兽人到处破坏公物的青年秘密团体——听起来像不像当时英国的朋克青年?

《指环王》中的阿拉贡
除此之外,襁褓中就受洗的天主教信徒托尔金在社会习俗层面上也抱有强烈的保守心态。他曾说“基督教婚姻——一夫一妻、永久的、严格的忠诚——实际上是全人类性行为的真理:这是所有男人和女人实现全面健康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无论是堕胎还是性少数问题,甚至是在现在的天主教国家也并不鲜见的离婚议题,托尔金的立场不会和天主教会中最保守的那一派有太大区别。他还曾评论说在这个堕落的时代,男女之间已经绝无可能再产生纯粹的友谊,显然是对当代人控制性本能的能力有非常悲观的判断。在改编电影中,导演高度正面地表现了洛汗的公主伊奥温参战并杀死了索隆的仆从戒灵,而在书中,托尔金更多描述的是其他男人为伊奥温都上了战场而感到悲愤和羞愧(“这是怎样的疯狂或邪恶?”),以至于洛汗军队想要以死谢罪,杀死戒灵的也不是她,伊奥温被用以反衬男人没有尽责,而不是用来颂扬女性突破自己的传统角色。不过,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保守派托尔金当然无法写出能够满足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女性角色,甚至可以说,相对宣扬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家长里短,有精灵夫人加拉德瑞尔这样的女性领袖,还有“惧怕牢笼”的伊奥温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开明。
当然,托尔金厌恶人们把自己的故事想成寓言,特别是那些觉得《指环王》当中描述的魔多和第三纪元大战是在影射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俗人。但这更是因为他不认为《指环王》是一本虚构的小说,而是一套他专门为英国创作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托尔金原本打算为1937年出版的《霍比特人》续写故事,当时他已经决定从书中魔法戒指的源头开始创作未来的《指环王》,然而包括中洲在内的整个“阿尔达”(Arda)世界的起源故事却早在1917年托尔金在前线养病时就已经有了梗概,后来经过数十年也未能定稿,去世后才在其子的编辑下以《精灵宝钻》为题于1977年出版。战地医院里的托尔金起初以创作属于英国人的起源神话史诗为目标,这也可以从童书《霍比特人》当中插入的高尔夫球起源故事窥见一斑:一个古代霍比特战士一锤敲掉名唤“高尔夫”的兽人脑袋之后发明了高尔夫球。尽管直到1951年托尔金仍然向编辑解释说,《精灵宝钻》的目标是填补英语史诗的空白,但他的故事越来越庞大,即便霍比特人居住的夏尔仍或多或少能与托尔金居住的英国中部对应,他已经无法明确地描述这个史诗宇宙与我们的世界的关联,后来他的说法是处于“不同的想象阶段”。身为一个深信上帝的老派天主教徒,托尔金眼中的神话并不意味着纯粹的谎言,反倒是一种“真理”(truth)。因为人类由上帝参照自己形象所作,既然上帝创造世界是从一句语言“要有光”开始,那么人类的语言也自然能有条件地“次创造”(subcreation),为故事创造出一个真实的第二世界。这种真实如同神的话语,多数人不能直接理解,但其背后是这个世界的核心真理。他的故事的确在引导人们去感受作为真理之一部分的道德准则,而他在信件中也确实会承认对部分桥段有明确的意图,例如弗罗多与咕噜的关系意味着慈悲可以得解救,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免俗地把他厌恶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比作魔多或者兽人,但他有意识地避免明确表达这些内涵,以便读者能够发挥自己的解读。
托尔金的政治态度其实非常明白,他向往遵循传统的田园牧歌而非烟囱林立的工业社会,他歌颂深藏于心的道德准则而非由人类意志决定的法令,他赞美人人各具其位的等级制度而不是各自为政的大众政治,他相信人类处在衰退之中,而这种衰退表现在人类对技术、科学、物质的迷信,而丧失了美德。种种偏向保守乃至反动的取向,让他的作品在七十年代的美国红极一时之余,也在欧洲成为了很多右翼组织的必读书目,特别是在传统主义者、战后最著名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埃沃拉(Julius Evola)的祖国意大利。
“霍比特营”
说来巧合,1970年代托尔金在美国声名鹊起时,也在意大利开始流行开来,但和美国吸引反权威的嬉皮士粉丝不同,托尔金在意大利从一开始就和右翼沾了关系。1970年出版的《指环王》第一版完整意大利语译本的作序者是埃莱米勒·佐拉(Elemire Zolla),一个相信“永恒哲学”的传统主义者,和埃沃拉也颇有私交。佐拉当时在序言中总结《指环王》所反映的托尔金道德观与圣乔治和贝奥武夫之类的古代英雄史诗相同,即“不寻求善恶之间的调解,只寻求战胜邪恶”,而不是向其他现代作品一样“色情,沉浸于混乱中,雌雄不分”,并且断定“托尔金的魅力来自于它对这种左翼传统的完全否定。”虽然在古代史诗的类型学上和托尔金本人不谋而合,但是他对托尔金的极端道德主义寓言解读,实际上和托尔金对自己作品的期待相去甚远——因为寓言的寓意是明确的,也就意味着作品当中蕴含的道理是固定的,限制了托尔金所说的“适用性”,允许读者的解读自由。
无论如何,托尔金很快就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流行开来,佐拉对他的解读也奠定了意大利早期读者对托尔金的认识——一个古典道德的卫道士,这在1968年后的欧洲已经非常少见了,在右翼政治势力日渐式微的意大利更是如此。彼时的意大利仍在“铅弹年代”(anni di piombo, years of lead),这个时期一般认为从1964年开始,期间爆炸和刺杀频发,极左和极右都在尝试用恐怖袭击推翻政权,意大利民众以炸弹和子弹使用的“铅”代指当时局势之可怕。长期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为了稳定局势不断地左右横跳,和两边的政党组成政治联盟。与1950年代后就逐渐被排挤出政府的中左翼联盟和遭到镇压的左翼组织红军旅(Brigate Rosse)相比,战后成立的新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MSI)受到了高度的容忍,曾数次与天民党合作执政,当中最极端的皮诺·劳蒂(Pino Rauti)在当选议会议员期间都公开主张使用以政治暴力和恐怖袭击为特征的“紧张策略”来加速社会崩溃和法西斯化,却并没有被政府惩罚。但显然,这种策略并没有为1960年代的意大利换来政治优势,反而是1960年代末开始,天民党逐渐与中左的社会党达成了执政联盟,“新秩序”等新法西斯组织先后被取缔。到1970年代,因为经济危机和1968-1969年的学生和工人的自发运动冲击,意大利共产党和天民党在1976年大选中形成所谓“历史性和解”(Compromesso storico),再次将共产党纳入了执政同盟。这一事件给意大利极右造成了极大冲击,很多人开始责备旧右翼,并转向刚刚在法国诞生不久的“新右翼”(Nouveau Droite)。埃沃拉的思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步入主流,他提出既不要共产主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第三立场”,并在非基督教的传统基础上建立新社会,这些主张为意大利极右反对天民党和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而埃沃拉关于历史处于从黄金时代向黑暗时代过渡的衰退期的观点,也鼓舞了极右反对美国传来的自由化和进步主义思潮。除此之外,托尔金还以沉没的亚特兰蒂斯为原型设定了一个位于中洲西部的高等王国“努门诺尔”,因为意图反叛诸神而被沉没,埃沃拉也同样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存在及其堕落带来的沉没。托尔金的世界在太多问题上不巧地和埃沃拉不谋而合——非基督教的异教形象、历史衰退论、崇拜古典美德等等,而且他还有非常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与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血与土”不谋而合,这让刚刚出版不久的《指环王》成为了新生的意大利新右翼思想通俗读本。
意大利新右翼(Nuovo Destra)的创始人之一马尔科·塔尔奇(Marco Tarchi)在再度风起云涌的1977年学生运动浪潮中萌生了创建新的右翼青年运动的想法。他仿照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形式组织了“霍比特营”(Campo Hobbit),得名自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塔尔奇接受了埃沃拉的教诲,并向法国“新右翼”学来了文化战线的新战术,希望能够通过杂糅了法西斯主义的流行文化和新艺术形式来重振“黑暗时代”人们的精神。在“霍比特营”,人们悬挂埃沃拉设计的凯尔特十字符号代表反基督教保守派的异教倾向,在帐篷里开着关于托尔金的讨论会,帐篷外则能看到把托尔金和埃沃拉的著作并列的书摊。此外,他们还曾有一本期刊《伊奥温》,主要以年轻女性为目标读者,强烈抨击女权主义和性革命的“堕落”。在“霍比特营”当中,不但诞生了不少被《指环王》元素启发的摇滚乐队,还酝酿了未来的极端分子。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支持下,“霍比特营”从1977年办到1980年,最终因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党本身的内讧才停办,以至于后来有不少组织都试图复兴它,到2017年后还有“霍比特营”40周年的纪念活动。
精灵应该是雅利安人吗?
这种对托尔金的“法西斯化”策略同样存在于英语世界,白人至上主义者长期以来都致力于把托尔金的种族观解读为反对种族混合、支持生物种族主义,更不用提他的小政府主义、贵族政治和宗教原则本来就是英美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右派当中最主要的元素。在美国,不乏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改编的电影和剧集嗤之以鼻,认为其扭曲了他们心中的托尔金。同时也有来自左翼的批评,认为托尔金笔下的高等种族精灵都是浅肤色,而邪恶和低等的种族则是深肤色,隐含了某种歧视性的种族潜意识,而电影当中精灵大规模的金发碧眼更加强了这种“雅利安人”印象,这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剧集对精灵外观多元化的考虑。不仅如此,托尔金承认他有意识地把矮人设计得更像犹太人,包括大鼻子、贪婪、矮人语有闪语系的辅音特征等等,并暗示这可以提醒人们犹太人也可以特别好战。另一方面,电影还完美复刻了奥克等低等种族的非人化,有些批评认为这与种族屠杀的心理动机有相通之处。
对英美的新右翼来说,托尔金最好的部分还是对道德世界的简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重建一种卡尔·施密特式辨别敌我的政治。在支持另类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格雷格·约翰逊(Greg Johnson)创办的“逆流”(Counter-Current)网站上,每年都要纪念托尔金,一篇题为《为什么左派憎恨托尔金》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指环王》是一个关于美德、英雄主义、骑士精神和兄弟情谊的经典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的护戒小队代表了客观的善,而他们的对手索伦代表了客观的、反人类的(或者在这里是反人类/精灵/霍比特人/等等)邪恶,旨在通过黑暗和同质化来统治世界上的自由人民。……那么,为什么政治左派会谴责《指环王》呢? 这一点现在应该很明显了:因为《指环王》把他们描绘成真实的样子。这个故事完美地说明了他们的丑陋,从内到外。它们代表着最黑暗的邪恶。因此,他们对这个传奇的政治化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现在所代表的客观和长期的邪恶。”作者认为左派分别与为了权力背叛自己族人的萨茹曼、敏感而自卑的奥克(兽人)和代表阿拉伯人的哈拉德人相呼应,并号召青年组成新的“护戒小队”击败他们,把这些“绝对的邪恶”赶出政治舞台。
正如托尔金认为自己写书是“满足自己”而不是讽喻现实,他并不承认自己是通过魔戒去象征什么。邪恶就是邪恶,不需要象征也能理解。但无论托尔金如何辩白,魔戒的确是有含义的——至少说明熟读日耳曼、凯尔特、芬兰各地传说故事的这位牛津大学教授创作时借鉴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等史诗。但是从他设定了创世神一如·伊露维塔(Eru Iluvatar)来看,他也并没有放弃把自己的一神论信仰加入书中。对天主教徒托尔金来说,真理不是诞生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是一种永恒的、道德化的智慧——这也在他的故事当中得到反映:绝大多数角色基本上都是善恶分明,从出场第一刻起就确定了正邪立场,只有极少数情况才会“被诱惑”,而这种诱惑带来的“背叛”也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作品当中常见的道德挣扎和立场变化,而是简单明了的堕入邪恶。这种“诱惑”及其源头在不同纪元都有不同的化身,由《精灵宝钻》中的堕落神灵米尔寇开始,第二纪元又由黑暗魔君索隆所代表,其复杂性在《指环王》描述的第三纪元末期达到了巅峰,从肩负对抗索隆的白袍巫师萨茹曼最终被索隆腐化,到咕噜、波洛米尔、乃至最后的持戒者弗洛多也被魔戒诱惑而在最后一刻几乎失败,但直至书中最后也无法填补内心的“黑暗和空虚”。米尔寇的邪恶在于为了让自己的意愿而忤逆唯一神,妄图用自己的创造和创世者平起平坐,而索隆的邪恶在于以铸造魔戒为诱饵,哄骗人们在中洲建立一个能与神居住的领域相媲美的新世界,而他们对于力量的贪婪将会让中洲被索隆的至尊魔戒所控制。

咕噜
在《指环王》中,托尔金着力描写了被魔戒诱惑的大小人物,上到被诸神派来监督和对抗索隆的萨茹曼,下到只是恰巧捡到魔戒的咕噜,前者自信可以控制魔戒的力量使之为自己所用,后者则是纯粹的想要占有“宝贝”,托尔金将自己对“欲望”的厌恶贯穿始终。尤为重要的是,他将创造万物放在一个不可触碰的地位,试图夺取神创造的荣光是一种邪恶,这种强烈的宗教观同样是他反对技术进步的基础。由此也就可以推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为什么是十字军式的——通过必要的正义暴力恢复神的秩序(也就不奇怪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和天主教团体联盟的佛朗哥政权)。
尾声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可是大家都爱的《指环王》,是我们有问题吗?我们是不是要准备抵制托尔金?这提醒我们,托尔金本人的意见很重要——阅读托尔金不应该以阅读寓言为前提,“次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就不应该遵循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也不应该试图使之符合我们的道德观念。托尔金之子克里斯多弗·托尔金就对电影的一些合乎时宜的改编颇有微词,引起后续的版权纷争。而这就引出对亚马逊改编《精灵宝钻》的剧集的态度: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本不适合被改编的作品,托尔金本人恐怕也不会赞同其中“政治正确”的改编部分——这只是第一层。而更加彻底的托尔金立场则将是“次创造”意义上,剧集既然要对一个创始神话进行改编,那就不能停留在只是改个肤色、改个造型,肤色、造型都应该有相应的神话支撑,由此一来,对于这些肤色、造型的变化产生之后,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都应该重写。换句话说,那将会是一个去托尔金化的“新中洲”。最糟的结果就是既使用一个更倾向于右翼的作品框架,又试图在不影响原著故事的情况下塞进去进步主义的议程。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批评托尔金太种族主义和批评改编托尔金的人太政治正确/不够种族主义,二者其实都是对的,但是从托尔金对神话所寄托的理想来说,都与他的意愿相去甚远——托尔金本来就没想你去挖掘他的目的,精灵与二十世纪雅利安人神话的关系除了在针对托尔金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外,就不应该存在。托尔金压根不承认作者的创作存在某种潜意识,而只承认创作受限于作者能够获得的材料,因此他的改编者完全可以用托尔金解释作品里有很多世袭制政体时的原话来解释所有的改编:“这可以形成非常有力的故事情节和动机。”毕竟托尔金的创作观念乃至他不承认的创作意图都是前现代的,他所试图恢复的世界已经去而不归,到今天的的确确已经过时。
托尔金肯定不愿承认他要通过将作品政治化以传达道德观念,而倾向于将故事的寓意都说成是审美趣味使然,在今天看来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而在所有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一部分的今天,认为黑皮肤精灵太过政治正确所以冒犯了托尔金的意图,这种绑定了作者意图的“认为”本身就已经足够反托尔金,甚至比出现黑皮肤精灵本身更能让托尔金死不瞑目。所以我们也不必太纠结于如何改编才是最尊重托尔金的——开始琢磨这件事的那一刻开始,托尔金就已经开始在棺材里翻来覆去了,索性让他翻去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