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就像两条相交线,在短暂交叉后渐行渐远 | 三明治
原创 Betty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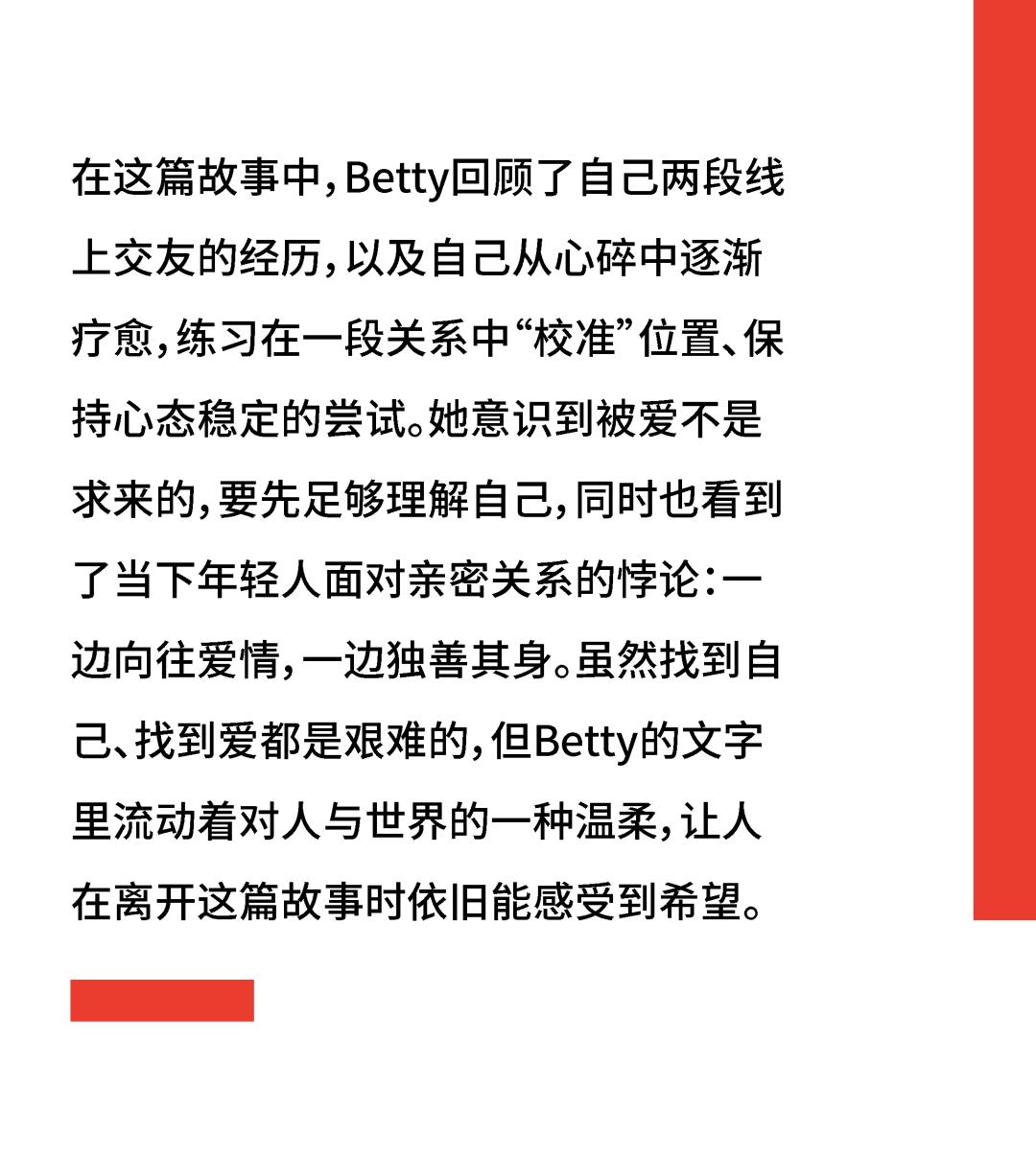
作者|Betty
编辑|恕行
与H初识是在Bumble,一个需要由女生开启对话的交友软件。去年初夏,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外环以外一家偏远的酒店隔离,百无聊赖中开始使用这个软件,台湾男生H是我匹配上的第一批人其中之一。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秀”,封面照留着长发,往下滑动,另一张照片里他双手抱膝坐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用狡黠的目光看向我。他的档案上写着“社会学系PhD,正在思考research plan”,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好奇是什么research”。我们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
开始的闲聊像所有陌生人之间的对话,我们聊美国的生活和饮食,吐槽防疫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还谈起过各自为什么来到Bumble。用他的话说,他使用这个软件的初衷是将它作为一块田野(“好奇心+练英文+认识local+理解女性”),而我告诉他,是因为朋友告诉我这个软件上的男性都很不靠谱,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有多不靠谱。
回看这段对话,我意识到我们谁都没有说实话。正如后来他补充说他不排除hookup,我登录交友软件的原因则是为了从上一段失败的情感中走出来。

上一段感情还未开始便已结束。台湾男生C是我在本科期间的同学,大一一起上同一节课时便有好感。课上的同学们大多不常发言,只有我每节课前都会和老师天南海北地聊天,偶尔视线穿过教室,总能遇见他的目光。真正在意起他是在一次课堂测验之后,我以漏洞百出的知识储备和慢得惊人的反应稳稳坐在班级排名的车尾,而他是第一名。后来的许多次测验,他都是第一名。我一向喜欢聪明的男生。
只是阴差阳错,直到大三结束时我才要到他的联系方式。彼时学校网课,我在北京实习,他在香港上学,想要隔着屏幕追求对方,着实难上加难。自从暑假里与他联系上开始,我的心思就一直被他的消息牵动,有时甚至会在凌晨醒来查看手机。可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动,我会在收到他的信息以后等一段时间:如果他隔五个小时回复我,那么我就过五个小时再回复他;如果他一整天都不回复我,那么我就第二天再回复他。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进一步透支自己,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在初期,与C的聊天还是很愉快的。虽然回复得很慢,但是他会应我的要求在露营以后发给我山里的风景照,也会发很长的文字和我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喜欢从他的视角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欣赏他条理清晰又不失人文情怀的回复。我把这些都当作他对我也有意的证据,兴奋地把他发来的一字一句拿去给朋友们分析。我擅长刨根问底,对一个人有兴趣便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通过网络搜索,我发现他从小便有数学天赋,拿下过无数竞赛奖项。抬头仰望,他的光芒令我心动而又晕眩。
那时的我是如此全情投入,以至于直到暑假快结束时,他说最近心情有些不好,可能不会及时回复信息,我都没有意识到情况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沉寂两周后,我重新打开聊天框,试探他是否已经恢复,并与他约好下学期一起上一节哲学课。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北京边实习边上网课,最期待的就是每周上课时能够透过摄像头见到C。我们变得更加熟悉,他会在聊天时开一些玩笑,可是长久以来那些需要自控与自持才能保持的“酷”劲在我内心最深处堆积。我变得越来越紧绷,越来越急迫地需要在这段关系中得到某种确认,对他的玩笑也经常过度反应。渐渐地,他不稳定的回复时间也让我愈发难受。我小心地提出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聊到一半就走掉,他则回复说与朋友都是这样的。
真正让我“破防”的是,有一天C终于告诉了我暑假时心情不好的原因。他说,当时他以为彼此喜欢的女生突然开始疏远他,他用尽挽回的方法也无能为力,因此心情郁闷。我表面上装作无事,还安慰了他一番,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讲,但内心里的醋坛子已经泼了一地。从此,我不再能够好好聊天,说话变得阴阳怪气,还为了与那位想象中的情敌一争高下而一怒之下申请了英国的研究生。我是那样脆弱,那么不自信,那么患得患失,以至于我把“优秀”与否与“是否被爱”挂钩,将自己不被爱的全部原因归结到那位女生就读于美国的名校,而我仅仅处在留学鄙视链底端的香港。
最终,在我又一次阴阳怪气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复我的信息。无论是我之后分享的一两次日常,还是我发送的新年祝福,抑或是我终于回到香港后的邀约,无一不石沉大海。现在回看,我惊异于自己的锲而不舍,更心疼那种卑微到尘埃中的姿态。
2021年6月15日,我在手机备忘录上写下:被爱不是一件可以求来的事情。

从香港带着一身伤痕回到上海,我躺在隔离酒店冰冷的空调里,回想起那段长达一年的纠葛,依然心有不甘。在使用Bumble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上来便向我坦白自己正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弟弟,也遇到过喜欢展示自己高超中文水平的英国教师,面对形形色色的选择,我很怕自己会想用一段新的感情来填充上一段关系在我身上凿出的黑洞。那样很危险。
于是当我的目光落在H的档案上时,尽管知道他可能是我喜欢的类型,尽管我们的聊天轻松而又自如,我依旧在不断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不要陷进去,不要像上次那样陷进去。
在那些独自躺在酒店的夜晚里,偶尔我会问自己,是不是把H当成C的替身,毕竟他们都来自台湾,也都有一些容易吸引我的特质。每到此时,我都会把自己拉回来,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不要急于在心里给H什么名分。事后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也很有必要的思维训练。
本来我与H约好在解除隔离以后进行第一次约会,结果阴差阳错,我隔离一结束便回老家去了,而当我再次来到上海时,他已经去往深圳。我至今依然记得,一个潮湿的夏夜,当我在老家条件简陋的酒店里再度隔离到生无可恋的时候,H发来了消息。
H:“我最近有点心情不好,你要听我哭诉吗哈哈哈。”
H:“其实我现在有个稳定交往的女朋友,但我一直想分手。我这次到大陆,一个原因就是想当面跟她提,但我开不了口。”
H:“我朋友都说你直接电话讲就好了,何必大费周章得跑到大陆花一堆钱和时间,但我觉得我人真的太好了,不忍心。”
其实,当他说出第一句话时,我的心中便已有预感,然而当真相真的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一丝震惊。用嬉笑代替怒骂,我说了一些类似“你不提分手难道要我替你提分手吗”的话以后,心一横,点开了零点刚刚出结果的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拿到了获得一级荣誉所需的GPA。只要在暑假里修完最后三节不算成绩的课,我就可以顺利毕业了。查成绩前的胆怯烟消云散,一直以来的自我怀疑也暂时搁置。当我为之奋斗四年的结果就这样轻飘飘地展现在眼前时,我竟一时不知道该作何感——原来我也是可以做到的。巨大的荒谬感从心底升腾起来,我庆幸自己没有早早登上H的贼船。
我:“那这么想想,我可能也贡献了一些情绪价值吧。”
H:“你还好哈哈,我觉得我们处于friend zone,你明显没要干嘛。”
我:“是的,我从一开始就给咱们设定了这个zone。”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H既不符合我对恋爱关系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对朋友关系的要求。然而,或许因为他是我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为数不多聊天比较愉快的人,也或许因为我本来就没想把他发展成什么关系,我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

大半个月后的某一天,H告诉我他回到了上海,参观了我们原本约定第一次见面的宋庆龄故居。
H:“我历史很差,去了才知道宋庆龄后来变成你们的人。”
我:“对,这本来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个surprise。”
得益于我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给自己进行的心理建设,也得益于H早早将自己的“渣男”招牌坦诚相告,每当我觉察到自己对他的感情似乎有些松动、变得急于回复或开始期待对方的回复时,都能够有效地把自己拉回“不关心、不在意”的正轨上来。
H是那个会在我面对实习机会无比纠结时帮我一起分析的人,会认真听我讲遇到的其他约会对象并乱开玩笑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一边表示自己尊重女性,一边在关系内出轨的人。认识H的经历让我明白,不要轻易定义一段关系,更不能轻易定义一个人。
如果说与C相处时,我急于把他变成我的男朋友,那么与H相处时,我便是漫无目的的。或许正是这种漫无目的使得这段关系变得健康——我肆意吐槽H的渣男行为,纠正他总说自己年纪大了,和他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发出去的信息就像射出去的箭,我从不盼望着能得到任何回音。这样的关系很松弛,我很开心。
七八月份,我的现实生活十分愉快。虽然海外的暑期网课需要熬夜才能完成,但因为我和妈妈、外公外婆以及狗狗一起住在乡间老宅里,我的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入睡前,我将电脑打开,登录课程页面,然后美美睡去,任凭半夜里老师在屏幕的那一端滔滔不绝。到了第二天上午,我会在起床以后和狗狗玩耍一阵子,接着开始学习昨天晚上落下的功课。每天,我喝很多水,吃健康的食物,做一些运动,学习我喜欢的内容,生活充实而又快乐。
或许是心态逐渐活过来了的缘故,我不再想起C,和H的聊天也越发天马行空。我们从对各自学科的理解聊到中美教育体系的异同,从MBTI人格测试聊到塔罗牌算命,我甚至知道了他在高考时差0.5分没有考上法律系的事。
H:“不是要吹捧你,但其实我不喜欢传讯息,会跟你线上聊天是因为你蛮有趣的,等你解除隔离了可以好好date一下哈哈哈。”
当他表达出对我的兴趣时,我往往会忽略这个信号,而且会在心里给自己加强一些暗示,认定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发展恋爱关系——直觉告诉我,他爱自己甚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他人,与他在一起的我只能沦为他自我意识的陪衬。我不喜欢一段需要时时叮嘱自己不能过分喜欢对方的感情,我不喜欢这样的博弈。
靠着这样的心理暗示,我度过了一个平稳的夏天,然后进入了一个无比郁闷的冬季。

冬季的抑郁与H无关,甚至可以说H的存在是为数不多还能让我感到生活在正常运转的事情。家族中亲戚的意外离世、本科的学长在美国枪击案中丧生、近亲的巨额负债,恶性事件接踵而至,考验着我的神经。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固然与我共同经历着这一切,也给我提供了许多情绪支持,但总有些相看两生厌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压抑、无力。
在这期间,我减少了与所有人的联系,包括H。只是,每当我与他闲聊的时候,我还能短暂地复活,仿佛又回到了上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后来我曾和他谈到过那个冬天的感受——
我:“那段时间跟很多朋友都不能好好讲话,非常容易暴躁,但是在跟你的聊天框里没有,一切还是如常的,我想说什么就说了,所以我才会说神奇,好像在这个小小的虚拟空间里我又能够变回我。”
H:“啊,抱歉,我没意识到你经历这么多事情,不过能听到你跟我聊天是开心的,我很高兴。现在好一点了吗?人生总会有低潮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度过,通常我都是一个人自己消化,但我知道这样不健康,还是要找人聊一下。”
看着这些话,我感到久违的温暖与纯粹。或许我一直以来在追寻的正是这样的时刻,不需要定义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不需要反复确证对方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只需要真诚地表达,就会被真诚地接住。我不会因为这样的时刻而神化这一段关系,只会深深感激在曾经非常艰难的时候有无数双手当中的一双托住了我一下。只要那样一下就足够了。
我与H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当时他被一个女生甩了,正在四处寻求心灵的安慰,我便提出可以和他通话。奇妙的是,他的声音与我想象中完全相同,说话的方式也和我的预期一模一样,浓重的台湾腔,清脆而又甜腻。
“你的声音比我想象中要成熟诶。”H笑道。
在接通电话之前,我曾抛出过一个问题,所以他便直接开始回答我的问题。他所担心的扭捏和尴尬没有发生,我们的谈话就像发生在一对多年不见的老友之间一样,幽默而又随和。
这次通话并没有改变我与他的任何方面,我们依然是若即若离的网友关系。只是现在,回看那段聊天记录,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他的心碎,一件我不同情、只是感到有些惊异的事情。原来他也会受伤,原来他也有不甘心,原来他也感知着全人类在恋爱这道剪不断理还乱的功课上所能感知到的各种情绪。

H在我们的相处中有着诸多可以觉察的前后不一致,比如一边说自己已经不常用微信,一边又在Instagram Story上发布自己与别人的微信聊天截图,再比如一边解除我与他在Bumble上的好友关系,一边在我询问时表示不清楚情况。
若是换作从前我与C相处时,我必定会十分介意,会抓住这些蛛丝马迹,用放大镜仔细研究它们,并且发给朋友们讨论,可是现在我只觉得与我无关——H不是我的男朋友,他爱怎么做都是他的事。实在想知道的时候,我会直接问他,并欣然接受得到的一切答案。与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现在的我更愿意关注自己的内心。
这不代表我没有好奇心。实际上,我已经在网上找到了各种各样关于H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中文名字、Facebook账号、考研时的成绩单、写过的艺术评论,等等。我非常明白,当我花如此气力去stalk一个人时,说明我对他是在意的。对我而言,这是我与H的关系中的最大挑战。
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一旦投入感情就很难全身而退的人,而且我也清楚,自己一旦喜欢一个人就容易将他捧上神坛、将自己贬入尘埃。在任何恋爱关系中,这样的心态都是不健康的,与H这样的人相处尤其如此。我的自信水平在与C的关系中被碾碎,现在好不容易慢慢拾回,我不会允许自己重蹈覆辙——今年春节以后,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实习,开始赚取人生中第一份工资,同时尝试进行大量阅读与写作。我似乎终于开始为自己而生活,尊重自己,爱护自己。
因此,我在这段关系中时时“校准”,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稳定在friend zone。
我曾与H讨论过“期待”这件事,他觉得男生在当今社会中普遍被期待要主动,而我则表示自己没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男生主动与否的行为中推断出对方的意图,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推断毫无意义。一方面,这是属于我的女性力量宣言,“我的感情我主宰”,可是另一方面,这种心态其实并不符合我对核心人际关系的期待。归根结底,我还是向往着两个“恋爱脑”相遇、相知然后相守的感情。斤斤计较让我疲惫,货比三家让我愤怒。
H:“你对核心人际关系的期待是啥?”
我:“是一种互相关怀、不需要保留和顾虑的关系。简单来说,不是全靠技巧来达到的。”
H:“那就是一夫一妻长期关系啊哈哈哈,就去相亲就好了。”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再次确认我与H真的不合适。

平时,我极少与朋友们谈起H。他就像我诸多朋友当中的一个,由一根细细的网线牵着,跨过台湾海峡和广阔的太平洋,在我的生活中保持着微弱的存在感。只有在最初得知他有女朋友还使用交友软件时,我曾出于震惊向几个朋友分享了这件事。直到我意识到最近是与H认识整整一年的日子,我才又与几个朋友谈起了这个人,而他们纷纷表示“有趣”和“原来就是当时那个男生啊”。
这与我认识C时很不同。认识C时,我几乎全程向朋友们直播整个经历。随着我们的关系不断深入,最终分崩离析,我的朋友们也从最初的“吃瓜”状态转变为气愤和替我不值。如果说我从与C的关系中获得了什么,那便是我学会了与朋友们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从而得到他们的陪伴与治愈。同时,我也在与一部分朋友的交流中发现,有些人是真的不爱聊感情类话题。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对自己的感情讳莫如深,还是因为我和他们还没有在这个话题领域内建立比较强的连接,我从他们那里得不到太多反馈。不过,就像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同一类型的心理咨询师一样,我也在探索的过程中慢慢找到了哪些朋友是我可以放心分享感情类问题的。我想,这也是成长。
不和朋友们谈起H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或许这代表着我一直以来的“校准”是成功的。他游离于我的friend zone,却又不是我真正的朋友。
有一次,我与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发生口角,互相生气。我向另一位好友求助时提到,我觉得近期与那位朋友聊天有些疲惫,而与H聊天似乎不会。好友提醒我,即便如此,我与正在发生冲突的朋友在关系上还是更胜一筹,不仅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更因为我们是有底气吵架的关系。
这句话如石破天惊,道出了我与H关系的本质——他不会对我完全真诚,我也无法向他展示最脆弱的那部分自我。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纱,永远朦胧而又隔膜。
“我刚才想到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见面,你会把我当成朋友还是约会对象?”
认识半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立刻把它丢给H。
“我会说朋友哈哈哈,我个人比较相信passion-initiation pattern,相对于friends-imitation pattern。”
H的回答实属意料之内,也让我感到十分安全。更重要的是,这种安全感让我意识到,其实在内心最深处,我对于恋爱这件事抱有许多恐惧和抗拒。
根据H的解释,passion-initiation pattern更像是人们所说的一见钟情,而friends-imitation pattern则更像是大众概念里的日久生情。曾经,在与C的关系里,我对他一见钟情,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也清楚自己是个倾向于一见钟情的人。可是,这种模式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心态去接近他,更无法控制自己对这段关系的心理预期。在那样的失控中,我开始害怕自己。所以后来遇到H的时候,我便极力控制自己不要“上头”。只要我不喜欢对方,我就是安全的。
只是,这样的我要怎么走入一段真正的关系中去呢?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悖论,我一边畅想着拥有“互相关怀、不需要保留和顾虑”的关系,一边步步后退,退回我给自己建起的厚厚心墙里。
或许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一边向往爱情,一边独善其身。

偶尔,在一天的忙碌结束以后,我独自躺在夜色里,感受空气中飘浮的无名怅然。我想,我还是需要爱情、需要爱的。耳机里忽然响起我认识C时常听的歌曲,仿佛把我拉回到两年前的夏天,我是那样谨小慎微,又那样满怀期待。
最近,我与H的关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漠下去,发出去的信息总是要过一两天才能得到回复,因此也很难碰出什么聊天的火花。我大概能猜到他在忙些什么——查资料、写论文、约会各种各样的女生。想起上个夏天,当我们讨论“期待”这件事的时候,他曾说过,朋友也是会流失的,好过就好。现在的我们就像两条相交线,在短暂地交叉以后渐行渐远。
我:“我有个问题,你觉得你在恋爱当中是爱你自己更多一点的人,还是会爱对方更多一点的人。”
H:“你觉得呢哈哈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是愿意花时间的人。”
我没有回复。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杂念,只是想把一个真诚的自己倾倒出来。这次的故事给我一种轻松而又温和的感觉,这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现在,感情生活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重要原因,现在我将它凝结在笔端,勇敢地面对自我和世界。感谢恕行老师接住我所有细碎的情绪,并且帮助我把他们展开、抚平。这次写作是温柔的体验,我很感激。

原标题:《我们就像两条相交线,在短暂交叉后渐行渐远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