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丨一周书记:作为灯塔的……图像志文献库及无名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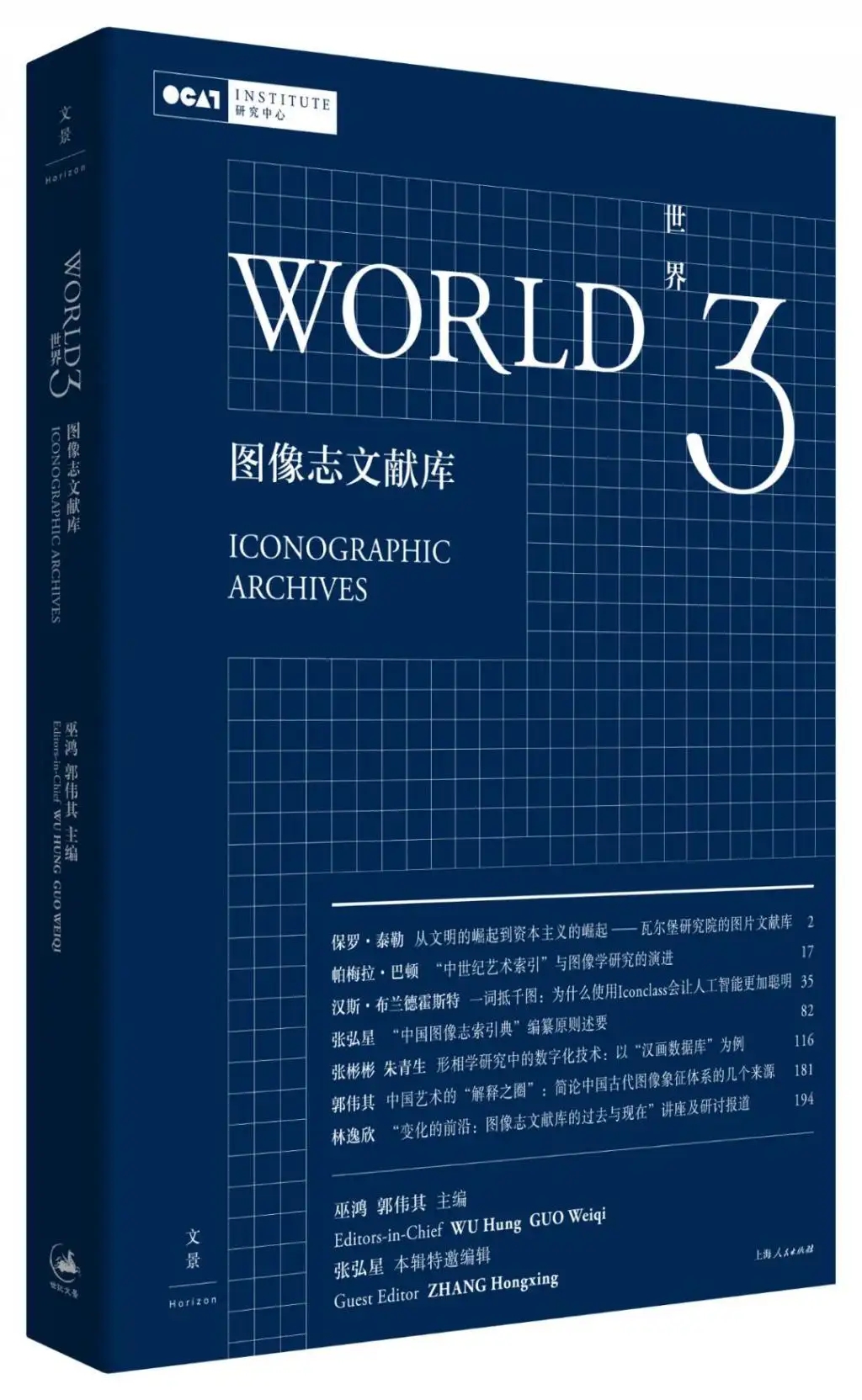
《世界3:图像志文献库》,巫鸿、郭伟其主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版,336页,88.00元
在今天的学术生产景观中,“数据”与“库”已经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记忆的核心平台。虽然与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其他学科相比,以视觉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术史研究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进展相对迟缓,但是在新千年到来之后这种状况已经大有改观,时至今天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今天已经到了回顾图像数据库这类艺术史研究平台的历史渊源、核心意念以及向前辈拓荒者致敬的时候了。更何况,在融合了科技与人文的学术回顾中,不仅梳理出历史脉络,而且从中将必定会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题,使收集、分类、联接、归档、更新等作为图像志知识基础的技术活更加成为视觉历史、艺术史、文化记忆、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激发点。
巫鸿、郭伟其主编的《世界3:图像志文献库》(张弘星任特邀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可以说恰逢其时,正如范景中所说:“这一期的《世界3》表明,图像志及其数据库的建设在推进今天的艺术史研究方面,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本书缘起于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OCAT研究中心于2019年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变化的前沿:图像志文献库的过去与现在”研讨会,会议详情见收入本书“前沿动态”栏目的林逸欣撰写的综合报道,会议的四篇发言经增益修订后收入本书的“专题研究”专栏。全书聚集于五个重要的海内外图像数据库,分析了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及其图书馆的“图片文献库”“中世纪艺术索引”、Iconclass等著名图像志文献库研究案例,介绍了“中国图像志索引典”“汉画数据库”等中国图像志的整理工作。书中共收入了十五位中外学者撰写的十四篇专业论文,通过对若干经典案例的深入分析回应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图像志文献库的建立如何对图像学研究课题作出回应并产生助益?图像复制技术(模拟或数字形式)与图像志文献库的发展以及艺术史研究有何潜在联系?当我们想要建立非西方或无文字社会的图像志文献库时,如何修正如潘诺夫斯基或其他学者的图像学理论,并根据所探询的文化特殊性发展新的词汇术语?现有的描述图像内容的概念和分类方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文化的约束、可以被转译成另一种语言? 我们又如何能够描述、分类和检索图像志内容?
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认为这部论文集不仅学术信息密度很大,而且在方法论上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巫鸿在“编者弁言”中对其主题内容的表述是:“‘文献库’的一般含义是收集和储存文献或图像,但这里所介绍和讨论的‘图像志文献库’远远超过这个简单的实际功能,而是关系到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概念,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如何吸收西方美术史在图像整理这个领域中上百年的经验,加入到有关图像库建设的对话中去,并对建立全球性的图像志文献库发挥出独特的作用。”(第8页)这是对一个看上去是技术性的、具有实际功能的主题很准确的阐释,“文献库”的建设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工作,涉及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学科发展历史脉络以及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视野。巫鸿接着简要地论述了“图像志资料库”的概念和任务。建立图像资料库的目的看起来很明确:把海量的图像实例进行收集、分类和描述,并为进一步的美术史研究和阐释提供资料基础。资料库的收集面向各有不同的时空范围以及独特的编辑理念和方式,但其核心概念都是“图像志”(iconography),即通过对图像的形象分析探究其文本根据和文化意义。特别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宗教的、神话的、历史的或通俗文化中的图像,在未经处理之前是无序的,往往混杂于叠压的时空层次之中,不具有明确的历史位置,也失去了原生的状态和上下文。换言之它们只是散乱的数据而非经过初步消化的研究资料。在美术史学术研究的链条中,图像志资料库以科学和系统的方式大面积收集和整理这些原始数据,将之转化为含有基本历史信息的研究资料和证据。这一转化构成既是具有自身目的性的特定研究项目,同时也自然成为美术史研究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为更高级和复杂的图像阐释准备了宏大而坚实的基础”。(第9页)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不仅是美术史研究链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应该成为历史学科本身的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原生态的历史图像还是从原生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有序或无序的图像,本身就是史料和历史,如何“将之转化为含有基本历史信息的研究资料和证据”,这是历史图像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巫鸿在回应是否有必要建立大规模图像资料库的质疑时谈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建立系统的图像志数据库“做的是以耗时耗力的密集型工作处理成千上万属于不同时期、地点、文化的图像”,“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机构性项目,它的主要‘结论’和贡献在于分类和编目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以及检索和使用的便利”。二是“每个大型图像库从其创立之初都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定位,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念、方法、组织和步骤”。在当下全球美术史研究迅猛发展的时候,“其中包括图像的跨地域流传和跨文化变异。以特定美术传统为基础建立的图像志资料库如何适应这种需要,因此成为一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10页)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该书的作者们共同关心和回应的问题。对于文献库的使用者来说,根据特定需要(如主题、人物、作品、关键词等)检索图像作品及相关资料,其中涉及以某项特定视角为中心的多种形态与性质的资料,从而汇集成一个包含了时空变化、媒介差异、文化语境变迁等丰富形态的知识谱系。用老话来说就是详细占有资料,才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今天更需要补充的是,如何才能详细占有资料,除了客观条件外也需要有问题意识作为导向。这是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得以深入展开的重要基础,是知识生产的关键阶段,今天的数字人文技术改变了过去的全程人工操作,为研究者提供了先进的电子导航仪。
在使用电子数据库方面,我无疑是落伍的。但是从前电子时代来说,应该讲我与“数据库”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交往。我学习美术史的起点就是类似图像志的分类。最近一段时间在整理、搬运堆放在学院工作室的书籍资料的过程中,重新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纸箱,那些一箱箱的卡片资料就是个人的前电脑时代的图像志。我的图像志分类启蒙老师不是瓦尔堡,而是广州美院陈少丰老师。与历史系老师做文献资料卡片不同,陈老师的卡片既有文字资料,同时更多的是图像资料,而且既有剪贴的也有手绘的。1982年初我来美院工作后就跟随陈老师到北京,去故宫、历博看展览时就在一张张卡片上描绘图像、抄录文字,后来到了西安、兰州各地看博物馆也是如此。书籍与报刊作为信息源,在阅读中除了在卡片上抄录以外,剪刀加浆糊的手工方式是必需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陈老师指导下参与中国古代雕塑史的研究与《中国美术通史》雕塑部分的撰写工作,中国文物辞典、各地古代名胜辞典、中国古建筑辞典(分省)等类别的工具书成为信息源中的重要部分。同一部书买三本,两本用于正反两面剪辑,把认为有用的条目剪出来、贴在卡片上,最上面写着主题词,当时的习惯主要是写:朝代、作品名称和地点,写在最上面是方便的卡片柜中翻检。这种卡片其实也就是读大学时非常熟悉的图书馆书目卡片,写论文的时候先把相关卡片找出来,按照写作思路排出先后次序。在本书,帕梅拉·巴顿( Pamela Patton)在《“中世纪艺术索引”与图像学研究的演进》(姚露译)中告诉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一个故事,那就是当查尔斯·鲁弗斯·莫雷( Charles Rufus Morey)教授于1917年开始创建“索引”的时候,最初的形式就是在他桌上的两个鞋盒。里面包含两套材料:一套是艺术品照片;另一套是手写卡片,卡片上有每件作品的创作日期、所在地、媒介、参考书目等详尽信息,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元数据。(21页)这也是我们当年的卡片,可以想象的是,这些一张张抄录、剪贴而成的卡片有很多是始终没有派上用场的,但是那种过程却是与事物、资料感性接触的过程,尤其是手绘器物图像的感受是电子复制根本无法相比的。
无论今天如何可以从审美情感的角度回顾前电子时代的手作方式,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太落后了。巫鸿在他独具一格的学术生涯“回忆写作”文本《豹迹:与记忆有关》(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6月)中,谈到2020年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的时候如何利用网络资源的过程,在顺藤摸瓜地搜寻出形形色色的数据库的时候,发现它们不仅比实体图书馆更大和更便利,“而且能够被创意性地互联,显露出知识的隐藏维度”。因此“近乎崇拜地感叹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实际上它已经如此庞大和深邃,不但任何学者必须使用这种信息来源,而且对它的发掘和利用也在创造新的思想方式”。(195页)于是他“希望感谢的机构特指那些进行了长期无形工作的单位,将巨量文字、图像和实物转化成了网络资源。一个例子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扫描文本,如果网上没有这份跨越两个多世纪、涵盖多个宫廷作坊的官方记录的存在,我绝无可能查寻玻璃镜在紫禁城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清代皇帝对它们的热衷,更无可能重构一些具体的装置场景。还有盖蒂中心的摄影图像档案,所包容的早期照片五花八门、雅俗杂糅,有若来自19世纪50年代的巴黎街头”。(196页)应该注意的是“创意性地互联,显露出知识的隐藏维度”“对它的发掘和利用也在创造新的思想方式”,这些都是对于在数字人文时代中使用网络数据库做研究的深刻认知,而且与这部《世界3:图像志文献库》的主题紧密相关。
保罗·泰勒( Paul Taylor)在《从文明的崛起到资本主义的崛起——瓦尔堡研究院的图片文献库》(姚露译)中谈到,在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数个世纪以来,构成欧洲艺术图像志核心的主题——寓言、古代历史、古典神话、宗教形象和故事——在18世纪下半叶不再流行。……同时,宗教图像志在欧洲艺术中的地位不再显著”。(13页)因此,“难怪当1830 年代宗教图像志开始以一种自觉的研究形式出现时,它的先驱之一、德国人格奥尔格·赫尔姆斯德弗尔( Georg Helmsdörfer)曾经说过,学者们研究艺术作品主题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欧洲人已经与自己过去的文化疏离。他认为,基督教文化不如异教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人所知,原因是后者已由古物研究者和神话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14页)从图像志的角度看欧洲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变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图像的整体性影响研究历史记忆的变化,是从视角和方法论上对“图像证史”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
潘诺夫斯基曾经在给罗莎莉·格林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中世纪艺术索引”,认为它除了提供了绝对丰富的信息之外,它还“激发研究者的思维,向他们提示所有可能的思考线索和方向。如果没有此类的工具协助,这种脑力激发的过程很难实现 。与其说‘索引’是工具,不如说它是一座灯塔……”(24页)我觉得“工具”和“灯塔”都是对图像志文献库最形象的描述,同时我们更不应忘记的是提供这套工具、建立这座灯塔的开拓者阿比·瓦尔堡和他的“无名之学”。
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1975年撰写的《阿比·瓦尔堡与无名之学》(Aby Warburg e la scienza senza nome)的文章中认为,虽然至今“图像学”这个术语被用来指称潘诺夫斯基和瓦尔堡的研究,但即使是一个概要性的分析也足以显示“潘诺夫斯基给图像学分配的目标,与瓦堡在说到他那门关于‘间隙’的学问时心中所想的(目标)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地遥远”。(《阿比·瓦堡与无名之学》,王立秋等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20页)他感慨的是一般人谈如何运用“瓦尔堡方法”(Warburg Method)研究图像的多,而“无名之学”则容易受冷遇。所谓瓦尔堡的“无名之学”,最早是罗贝尔·克莱因(Robert Klein)在1970年说的,他说瓦尔堡是一门虽然存在却没有名字的学科的创始人。(见同上,第1页,注释2)那么,究竟什么是阿甘本所讲的“无名之学”呢?他的表述有点复杂:“最忠实的概括瓦堡‘无名之学’特征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把它插入一个未来的‘关于西方文化的人类学’的计划,在这门‘人类学’中,文献学、民族学和历史学将与‘关于间隙的图像学’融合——作为对Zwischenraum的研究,社会记忆的无休止的象征工作就在此间隙中进行。……只有这门学问,才会允许西方人—— 一旦他超越其种族中心主义的限制——实现对一种将治愈人类的悲剧性精神分裂的,‘诊断人类’的解放性知识。……很可能,这门学问也会一直保持无名的状态,只要它的活动还没有如此深刻地贯穿我们的文化,以至于克服了那些不仅使人文学科彼此分离,也使艺术品和人文科学(studia humaniora)分离、文学创造与科学分离的致命的分割和虚假的级别。”(同上,22-23页)无论阿比·瓦尔堡的图像志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联系与区别是否如阿甘本所言那么遥远,它提醒我们重新思考瓦尔堡那批贴在黑色画布上的照片的深刻意涵:不但是作为社会记忆的图像学,而且是作为人类学性质的引向人类精神的解放性知识的学问——阿甘本认为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克服那些使人文学科彼此分离、也使艺术品和人文科学(studia humaniora)分离、文学创作与科学研究分离的致命分割和虚假级别。
即便阿甘本此论只是一家之言,我们还可以从文化记忆研究的学科领域中看到关于瓦尔堡的相类似观点:“如果说哈布瓦赫是记忆研究领域最容易被记住的奠基者,那么阿比·瓦尔堡或许就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人。这位德籍犹太艺术史家是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领域一位早期的活跃代表(参见Gombrich)。他的著名观点是:为了洞察文化记忆的过程,研究者们不应当再坚守学科壁垒(grenzpolizeiliche Befangenheit) 。此外,阿比·瓦尔堡还关注了记忆的媒介性。他的作品与其说是明确的理论性概念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为后来学者提供灵感的矿山。……阿比·瓦尔堡给今天的研究留下遗产,树立了一个榜样,即如何通过有形客体的层面来趋近文化记忆。(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 页)关于打破学科壁垒和跨学科文化研究,这与阿甘本说的克服学科之间的分离是相同的。所谓“有形客体的层面”其实就是指物质媒介的层面,总要依附于各种媒介的图像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于是最后可以回到阿甘本论述瓦尔堡研究的意义给我们的提示:“瓦堡的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从那些类似形式与内容、风格史与文化史之间的非本真对立的角度来加以阐释。作为一名学者,瓦堡方法的独特、显著之处,不在于他采用了一种新的书写艺术史的方式,而更多地在于,他总是把他的研究导向对艺术史边界的克服。就好像,在这个学科中,瓦堡只对在其中放置能使之爆炸的种子感兴趣。”(《阿比·瓦堡与无名之学》,第3页)话说得很形象也很有深意:把研究导向克服艺术史的边界,在研究中放置能使之“爆炸”的“种子”。在这部《世界3:图像志文献库》中,我觉得各种视角和众多案例都带有这种特征:通过先进的检索与主题分类方法,从艺术史到历史图像学研究都将更为自觉地引向这样的问题意识——不但要把图像放置于边界中的问题语境之中,更要放置于那些问题语境中的能触发“爆炸”的边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甘本所阐释的瓦尔堡 “无名之学”以及发展到今天的图像志文献库,那也是对建构中的“历史图像学”的启示与召唤:在朝向某种更为广义的“人类学”方向中,把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图像学融合起来,打破一切僵化的学科间隔,使之从“无名之学”成长为一门为人类服务的“解放性知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