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岛隆博:论丸山真男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
原创 丽娃河之子 许纪霖之窗
内容摘要
丸山为了批判二战时期的日本政治,欲通过对徂徕的创造性解读引进现代性思维,期待政治进行正确的决断。本论文作者认为丸山对徂徕的解读有“误读”,引起丸山共鸣的应该是对徂徕有重要影响的荀子。丸山为何要“误读”徂徕?丸山留给我们的课题又是什么?本论文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中岛隆博 著 王前 译
原题:以“制作”取代“自然”:论丸山真男“近世日本政治思想史中的‘自然’与‘制作’”,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6辑。
( * 译自小林康夫-中岛隆博著『日本を解き放つ』,东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1月初版,第195〜218页。)
▲ 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略
 ▴
▴中岛隆博
如前所述,徂徕面对的政治课题有两个。一个是要给封建社会所依据的根本规范重新奠定基础,另一个则是为了克服现实中的社会混乱,提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对第一个课题,他把根本规范的正当性归属于绝对化的圣人的制作。可是如果把“制作”的逻辑限定于古代圣人,都封闭在历史的过去里,那么就无法满足解决第二个课题的思想条件。因为一旦圣人制作了道之后,被制作了的道便离开了那个制作的主体,作为客观化的观念其自身就具有正当性的话,结果还是回归到自然的秩序,从那里无法作出针对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只有把“先王制作”的逻辑类推到一切时代,才能彻底确立人(Person)对于理念(Idee)的优势地位,只有这样政治统治者为了克服危机的――面向未来的――制作才有可能实现。对于徂徕来说,圣人的道是具有超越时代和场所的普遍正当性。然而这绝非自然而然就可实现的理念,而是各个时代的开国君主,以每一次制作为媒介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理念的实现不像自然秩序观那样有内在连续性,而是在每次时代更替后经历新的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是非连续的。徂徕在《政谈》《太平策》《钤录》等著作中提出的“由上而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正是建立在这个逻辑之上的。
▴
《丸山真男集 第2卷(1941-1944)》岩波书店 2003年
收录其「近世日本政治思想における「自然」と「作為」」一文
丸山真男追求的政治决断
我上面引用的一节,是年轻的丸山真男(1914-1996)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就的论文的核心部分。在探索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丸山思考的究竟是什么? 请注意文中的这句话:“针对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丸山熟读卡尔·施米特,这里令人想起例外状态下主权者的决断。但是为了克服危机,并非只要做出决断就可以了。当时日本正是因为莽撞做出“英勇的”决断而导致了极其糟糕的状态,丸山肯定很敏感地察觉了。重要的是要能正确地理解需要下决断的“现实事态”。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现实事态”呢?丸山要在“体验新的主体化”里寻求答案。换而言之,观察现实时不是封闭在自然秩序观里任凭事物自然发展,而是Person这个人格作为主体介入现实,通过其“制作”来改变现实,否则无法看清“现实事态”。而这样通过“新的主体化”介入现实,正是丸山用“政治性”这个词来思考的内容。这个时候丸山参照的是荻生徂徕。在他看来,正是徂徕在江户幕府面临危机的时候,为“针对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做了理论上的准备,首次开拓了“政治性”层面。具体地说,就是他把德川吉宗将军的享保改革在理论上定位为“政治决断”。
 ▴
▴卡尔·施米特
(Carl Schmitt,1888-1985)
谁来制定的规范?
徂徕究竟是用的什么样的理论呢?在丸山看来,就是把“先王的制作”扩展到“各个时代的开国君主”身上。所谓的“先王的制作”指的是古代中国帝王们制礼作乐,也就是制定王朝根本规范的礼乐。丸山这样阐述其意义:
先王不用说指的是从伏羲神农开始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者,道=礼乐是他们“尽其心力极其知巧”制作而成的,并非“无论有人无人本来就有的”存在。而这些道的制作者就是圣人。反过来说,圣人就是道的制作者的称呼。如此把圣人概念专门限定于先王这种历史上的存在,这就是把徂徕学跟所有历史上的儒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点。
在此丸山把“先王”定义为古代中国的具体帝王们,称他们为“圣人”。进而他把徂徕学问的独特之处解释为“把圣人概念专门限定于先王这种历史上的存在”。此时丸山脑海里肯定有“圣人可学而至”这个朱子学以降的圣人概念 (到了阳明学则是“满街圣人”)。对把朱子学作为“自然秩序观”的象征来批判的丸山来说,朱子学所代表的圣人观是非政治性之代表。针对这点,丸山说“圣人”必须是古代中国的“先王”那样的政治主体,而且把徂徕解读为批判朱子学,进而把“先王”恢复为“制礼作乐”的政治主体的人。
▴
丸山并没有在此止步,他继续论述到:
但是徂徕更往前走了一步。徂徕学的“道”具体是指唐虞三代这些一定历史时期的制度文物,制作了这些制度文物的人格则是尧舜禹汤那样的历史上出现的开国君主,于是就把这种圣人和道的逻辑关系类推到并非唐虞三代的后世,也就是所有时代的制度和政治统治者的关系上。
这个观点其实不是徂徕的,而是丸山的。把“先王”类推到“开国君主”,那里面也就包含了德川吉宗。我们读徂徕的《辩道》《辩名》等著作就可以发现,他反复讲“先王之道”及其具体体现的“礼乐刑政”是古代多个圣人制定的,是一旦制定就是无法改变的至上原理。而且徂徕跟丸山的读解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徂徕认为圣人制定的东西,普通人不用说了,即便是孔子也无法改变。但对丸山来说,也有很方便地为他所用的一面,因为丸山把徂徕的“先王”解读成了”宗教性的绝对者”。
圣人(=先王)是道的绝对制作者,意味着圣人是先于一切政治社会制度的存在。如果说在自然秩序的逻辑中圣人是被置放在秩序中的,那么把那种观点完全转换以后,当然就是把圣人从那样的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必须给圣人从无秩序制定秩序的地位。在圣人制定以前是“无”,制定以后就是“全部”。
从这段引用来看,丸山把徂徕所思考的“圣人”或者“先王”看作是基督教里从无创造的神那样的存在。对追求现代性的丸山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无法绕过的一道关,在此丸山的确是表现得非常政治神学化:通过非神的古代帝王的一击,世界被创造出来了。
 ▴
▴丸山真男
享保的改革是复古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徂徕的主张威胁到了丸山的立论。因为徂徕虽说主张圣人制作的道无法改变,但并非是宋儒说的那种道本身“万世古不易”,而是承认如果是圣人着手的话可以改变,只不过因为上古圣人之后没有出现过新的圣人,所以事实上没能改变。换而言之,既然古代“先王”之后没有出现新的圣人,那么“各个时代的开国君主”就没有权利进行礼乐的改革。
那么德川吉宗进行的“改革”该怎么解释呢? 对于丸山来说,这个改革正是“各个时代的开国君主”进行礼乐改革的具体例子。然而,对徂徕来说这是拯救中国古代的礼乐理想,使之在日本再度实现的“复古”。
据吉川幸次郎的研究,徂徕是这样想的。“先王之道”在孔子之后,更具体地说是在采用了郡县制的秦始皇以来已经在中国失传了,反而是在实施封建制度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下还有实现的可能性。吉川幸次郎进一步说,徂徕是自视为出现在日本的第二个孔子。也就是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这七位圣人所制定的“先王之道”作为普遍性原理完成后,屡经后世的改变和解释,在中国已经衰落了,是徂徕复兴的。虽说是“复古”,其实是很激进的想法。
 ▴
▴德川吉宗
决定放弃“自然”的丸山
那么丸山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想到有几个重要的理由,其中最大的就是他想通过对徂徕进行解构性批判,把徂徕开拓的更高层次的(也就是利用了“制作”的)“自然”的态度否定掉。因为这个“自然”的态度正是支撑着在丸山眼前展开的“现实事态”的。丸山接着批评徂徕的理论中“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
徂徕生活在寄生于封建社会胎内并将其解体、腐蚀的毒素迅速成长的年代,他倾其全力要把毒素去除掉。既然那种毒素的成长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反动的”思想家。如果说他理想中的制度内容是原始封建制度中的自然要素—田园生活、自然经济、家族主从关系等等,那么徂徕学的体系说到底只是要试图通过“制作”来恢复“自然”而已。这绝不是文字游戏。历史的吊诡常常在于让反动者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徂徕一面诅咒社会性(Gesellschaft)的社会关系,一面选择制作的立场,而这个制作的立场里当然内含了社会性逻辑。
丸山断言“复古的”、“反动的”思想家徂徕的理论核心是要“通过‘制作’的逻辑来恢复‘自然’”,能从这里感受到丸山愤怒的不仅仅是我吧?为何徂徕要让“制作”的逻辑屈服于“自然”呢?为何有了现代的“社会性逻辑”还要很“反动地”维持前现代的自然共同体的社会形态呢? 而且这个反转过来的反动逻辑不正是变了个样子重新出现于现代日本吗?通过对徂徕进行解构式解读,不就可以真正地恢复日本本来可能拥有的“政治主体”吗? 从丸山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充满强烈愤怒的质疑。
体现“制作”的《荀子》
丸山想在徂徕的思想里读出“开国君主”的“制作”逻辑,有意思的是,最好地体现了这个逻辑的是古代中国的《荀子》,可丸山对《荀子》没有多大兴趣。丸山说“孔子和荀子始终致力于实践伦理,排斥形而上学的思考”,“但是徂徕说的礼乐当然并非宋学里说的那种‘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那种抽象的东西,跟荀子的也不一样,他并不关注人精神层面的改造,只是要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在这点上对人性来说就越发是外在的了”。
然而,跟丸山的理解相反,正是《荀子》才体现了丸山要从徂徕的思想里读出的理论,而且荀子对徂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家,徂徕还写过《读荀子》。重要的是,在《读荀子》里徂徕一心要批判的正是由“开国君主”来制定的逻辑。
作为曾经的“后王”的“先王”
在此先思考一下《荀子》里的“后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跟“先王”相对,不是指古代的圣王,而是指现在的君主。跟“制礼作乐”一样,荀子重视的制作还有“正名”。关于“正名”,他是这样说的:“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
作新名是王者进行“制名”这一政治行为,从上面的引用可以知道,新的王者“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认为名没有固有的意思和指示对象,是通过“约定俗成”,名和意义及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才成立的。就这样语言在恣意生成这个权利层次上跟王者“制名”这个政治行为重叠在一起。也可以说导入了历史的维度。王者是通过重新反复“旧名”而制作“新名”,那是因为荀子不需要丸山说的那种“宗教绝对者”,反而是拒斥那样的绝对者,呼唤作为历史的、政治的主体的新王者,就是“后王”:“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荀子·正名》)。
这里说的“后王”要遵从的“旧名”的具体例子,举的是商周等以前的王朝所用的各种“名”。“后王”不是在白纸的状态下来制“名”的,而是重新反复在“先王”之时就已经存在的“名”。换而言之,荀子的思路跟卢梭的“语言起源论”是不一样的。对荀子而言,不需要去探求超越人类历史的大写的起源(特别是天)。我们已经在“名”的反复之中,在历史里面了。这也意味着荀子拒绝了“先王”在古代的“一击”之后这个世界就开始了的思路。重要的不是作为起源的那个大写的“古”,而是跟“现在”连在一起,使新的反复成为可能的“古”才是重要的。并且允许“后王”进行带有差异的反复,跟“古”相比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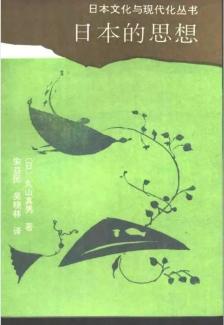 ▴
▴丸山真男著 《日本的思想》
通常认为跟大多数儒家强调古代“先王”相比,言及“后王”是《荀子》的特征。但是《荀子》并没有轻视“先王”,而是想象“后王”这一现在散发着荣耀的王者也存在于其它地方,以前也存在过,把“先王”当作曾经的“后王”来尊重。因此,在《荀子》中重要的与其说是强调“后王”,不如说是设定了把“先王”的业绩在现今重新反复,注入新的生命并进而继承的历史性。
语言间的转换符号
然而,能够共有这种历史性的只有那些都具有“正名”和“礼乐”的社会吧? 也就是说,只有某种程度共用同一种语言和规范的共同体才可以做到。“古”只是通过《荀子》把其创造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而已,完全没有打开新的反复的道路。那么这样一来,令徂徕和丸山苦恼不已的在日本的“先王”或者“宗教绝对者”要进行反复不就困难了吗?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一下《荀子》里对别的共同体的看法。
彼王者之制也,视形执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故鲁人以榶,卫人用柯,齐人用一革,土地刑制不同者,械用备饰不可不异也。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荀子·正论》)。
 ▴
▴荀子
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共同体,在这里跟中华“诸夏”相对比的是“蛮夷戎狄”,他们“同服不同制”。这样的说法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复数性,也就是“不同制”但“同服”。换而言之,承认有根据别的原理而形成的共同体存在。这个看法在谈到外语时更加明显。《荀子·劝学》里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这里荀子论及“异俗”,语言既然是“约定俗成”的产物,那么语言的差异就不是“语言能力”造成的,而是因为后天获得的习惯。这样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需要通过某种变换符号的设定方成为可能,所以荀子说“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荀子·正名》)。当然,这里说的期待拥有转换符号(约定、使符合)跟原初的“约”一样,都是只能回溯上去才能发现的。荀子所说的外语,是指已跟外国有交流(语言的翻译和经济交易)的地区的语言,其沟通的可能性一开始就是有保证的。可以说,即便那种思考还不算充分,《荀子》的视野中已经有其它共同体的存在和跟其交换这样一种眼光了。
作为思考出发点的世界的复数性
既然如此,那么对《荀子》而言的世界的复数性,即便不是超越交换可能性的更为激进的复数性,但已经作为思考的出发点成为前提了。这点使《荀子》对“古”的态度跟别的儒家区别开了。也就是说,“古”并非一击之下就创造了世界秩序的绝对起源,它本身就已经历史化了,跟现在联结在一起,可以有复数个方式。
《荀子》的这种思路,有学者认为对清朝的荀子复兴有重要的作用。石井刚提到戴震依据《荀子》,“乾嘉学术在以‘反宋复汉’为宗旨时,荀子的复兴也就是很自然的结果了”。因为清朝是异民族统治的王朝,所以如果依据“理”这个绝对起源的宋学思路,就无法说明世界的复数性,所以通过《荀子》终于可以召唤研究汉代以前的“古”的汉学了。
 ▴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书影
最有创造性的“古”
在此进入荻生徂徕的讨论吧。比刚才提到的戴震稍微早一点,徂徕就切入了世界的复数性问题。究竟在日本(日本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反复“古”中国的“先王”意味着什么?这是徂徕所追问的核心问题。之所以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受了明代古文辞学派李攀龙和王世贞的影响。
古文辞学派最有名的主张就是李梦阳说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攀龙非常严格遵守了这个主张。但古文辞学派并非单纯主张复古、拟古。至少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以来,中国文学里就一直持续着关于模仿和创造的讨论。之所以模仿“古”,是因为那个“古”最有创造性、不模仿别的就树立了自己的独创性――“模仿,但不可以止于模仿”――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一直到古文辞学派为止的隐密的中心命题。而徂徕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思想转向。在他看来,需要的是寻找最富于创造性的“古”。对那个“古”现在必须直接反复。为此必须舍弃“古”以后加上去的解释,特别是要放弃自己一直学习的朱子学的解释。
然而,困难的是在此参照的“古”,从日本来看,不仅时间上相隔遥远,而且也是空间上相距甚远,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作为heterotopia—异托邦的“古代中国”。这里的困难要超过清朝的戴震构想汉学的程度。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直接接上那个“古”呢?徂徕想到的是语言。如果能精通“古”中国的语言,那么“古”时制定的“先王之道”不就可以理解了吗?于是徂徕的经验就用上了。徂徕曾经为了用唐音读懂经书跟中文口译员交流过,学习过中国当时使用的中文。在此基础上他读破古文辞的文本,从而能够读懂作为“古文”的经书。
先王之道与礼乐刑政
徂徕找到的“古”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看了徂徕在《辩道》《辩名》里的论述可以知道,在徂徕看来“古”的本质在于先王制作的“道”中,具体体现在“礼乐刑政”等统治制度里。在这里重要的是“先王之道”及其具体体现的“礼乐刑政”是由古代多个圣人制定的,并且是一旦制定便无法改变的至高原理。很清楚,一看便知这跟《荀子》里所说的“后王”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徂徕还批判后来的儒家,特别是子思和孟子。因为他们认为“圣人可学而至”,误解了“先王之道”。他还批判后世的朱子学“欲使学者以己意求夫当行之理于事物,而以此造礼乐刑政焉”。跟那样的解释相反,徂徕认为由多位圣人制定的“先王之道”是无法由成不了圣人的后来者增添新的内容的。在这点上,徂徕无论如何是跟荀子划清了界线。听上去也许矛盾,因为徂徕原本就在圣人制作“道”、天与人的分离、特别是经历过语言论转向的语言观等方面受到《荀子》很大影响。比如在《辩名》的开头谈到“名”的起源,谈到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经圣人“命名”后人们才看见的。
然而“命名”这个行为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根据不同的见解自由决定,“名”和事物的关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这样的话会令人困惑,所以需要通过通过“正名”来整理“名”和事物的关系。在这点上徂徕是从《荀子》那里学来了语言的符号性和相互约束的“正名”。在《读荀子》中,徂徕这样写到:“言名虽无固宜,先王制名之始。以天名天,以地名地,此其意。与万民相约,以此为记号,而命之名也。……言于其所与万民相为记号者,辄变异之,则百姓茫然不知其孰为天孰为地,此不宜也”。
然而徂徕并没有跟着《荀子》一起走在“正名”的道路上。因为如先前所述,在《荀子》中,与先王相对,把近时的王看作“后王”,“后王”模仿“先王”的制作(“正名”),再制作新的“名”,也就是新的“道”,而徂徕却想设法剥夺“后王”制作、改变的力量。徂徕要通过下面的强烈主张来约束“后王”。《荀子·正名》里谈到“后王成名”时说“循旧名作新名”,徂徕则说“盖言名者,圣人之所建,不可得而变更也”。对徂徕来说,“新名”也是古代圣人所制定的旧名称,跟“旧名”一样都是“先王之道”的一部分。也就是徂徕说把“后王”的范围限定于古代的圣人,从而消除了以后历史中重新制作和变革的可能性。所以他说“注,后王当时之王,非矣。后王,即周文武也”,如此就把“后王”的范围限定于文王和武王这两位圣人了。
德川幕府实现先王之道
为何徂徕要把“先王之道”追溯到孔子之前的圣人制作呢?其最大理由就是徂徕认为“先王之道”在孔子之后,具体地说是在采用了郡县制的秦始皇之后已经在中国失传了,反而是在采用封建制的德川幕府的治下还有实现的可能性。徂徕是想在日本复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这七位圣人所制作的“先王之道”。为此,徂徕必须跟《荀子》唱反调,主张具有制作“道”和变革力量的圣人“后王”近时不会出现了。在他的思路里,东亚的思想世界中“古代”的一击就是全部,后来者必须不断正确地反复。
徂徕的这种政治构想力通过“先王之道”来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性奠定基础,通过具体的制度改革来实现“先王之道”。如此一来就把古代中国的“礼乐刑政”这个制度封闭在“古”之一击里,把时空都遥遥相隔的日本升格为具有特权的反复者来进行政治运作。
“古”的反复可能性
 《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可是“古”的外部性或是异托邦的力量不会就那样简单地服从徂徕的解释吧。“古”之所以充满创造力,那是因为如同主张“古文”的人们所思考的那样,是因为始终具有开放的反复可能性iterability。关于这点,《荀子》早就说过,尽管带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徂徕是设想通过语言来直接接上“古”,而《荀子》所主张的则是通过重新解释语言来回避“古”之一击这个想法。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导入能够重新反复“先王”之道的“后王”,不走到历史外面去的思路。但是处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徂徕则反过来要通过把“古”绝对化,从而在日本的历史里打开新局面。徂徕所打开的新历史很明显为日后本居宣长的“国学”准备了条件。
从徂徕解放了的“魔物”中发现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丸山。丸山批评徂徕的理论“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徂徕把彻底的“制作”逻辑带入战时的日本,也就是那个“自然”原理覆盖的日本,目的在于把日本解放到世界的复数性和异托邦中去。我认为如果丸山能够倒过来从徂徕走到《荀子》,那么丸山的愤怒(对用“制作”的原理恢复“自然”这一做法的愤怒)也许可以和缓不少吧?
徂徕学导入的主体制作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分成两个。一个是成为变革封建秩序、树立新秩序的理论武器,另一个是剥夺封建社会关系及其观念纽带(五伦五常)的实质性正当根据,使之有名无实。当然前者是积极作用,后者是消极作用。那么在德川时代后半阶段思想史上,对现实起作用的是哪个方向呢?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后者。制作的秩序观在前面提及的《万国丛话》中作为“人作说” 主要是维新后具备了积极意义,如同这个“人作说”的介绍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徂徕无意中唤醒的“魔物”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没有成为从外部打倒封建统治的力量,而是渗透到其胎内,一直从里面腐蚀着封建统治。
从上面的引用可以看出,即便如此,丸山还是想从徂徕唤醒的“魔物”身上挖掘可能性。因为在丸山的思考中,即使知道徂徕学的逻辑里最终还是找不到“为了封建社会的变革不转化为对封建社会变革的绝对保证”,除了重新反复徂徕所释放出来的“魔物”外,无法“对现实的事态做出政治决断”。
那么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接着丸山思考呢?务必请大家也一起来思考。
阅读指南
·关于丸山真男和荻生徂徕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我就举以下两册。
一本是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出版。
这本书1974年出版了英译本,书名为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Masao Maruyama,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在世界各国拥有读者。年轻的丸山对日本思想的介入性解读在书里充分展开。同时阅读丸山的盟友、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的“面对现代性”(Confronting Modernity)(中岛隆博译,《思想》1123号,岩波书店,2017年11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丸山说的“对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的涵义。
另一本是吉川幸次郎的《仁斋·徂徕·宣长》,岩波书店,1975年。
这是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研究日本思想的力作。日本思想需要从更广阔的脉络,特别是中国学的脉络来理解,这本书正是这种实践,对本论文的写作也大有裨益。
·另外,关于“古”之表象的理论著作,可以举出下面这本:
Pocock,J.G.A.1999, 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1:The Enlightenments of Edward Gibbon,1737-176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表象“古代”是什么样的行为呢?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波考克思考了这个问题,特别是考察了在欧洲启蒙跟中国的关系里作为“古代”的中国是如何被讨论的。在对谈中也提到过,在近代欧洲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学问传播到了欧洲,十七世纪埃及也引起了欧洲强烈的关注,由此比圣经所记载的上帝创造更为古老的“古”成了问题。这是大大动摇了圣经以及基督教神学正统性的问题,而且更为麻烦的是对当时的欧洲而言,中国是提供了“没有上帝”也能构成社会的可能性的地方。中国比欧洲更古老,而且提供了基于无神论的社会的可能性,因此使得近代欧洲的学问产生了变化,也规定了启蒙的方式。波考克的书为我们理解徂徕和《荀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译者单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原标题:《中岛隆博:论丸山真男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