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天纲丨把民间信仰当作其自身来观察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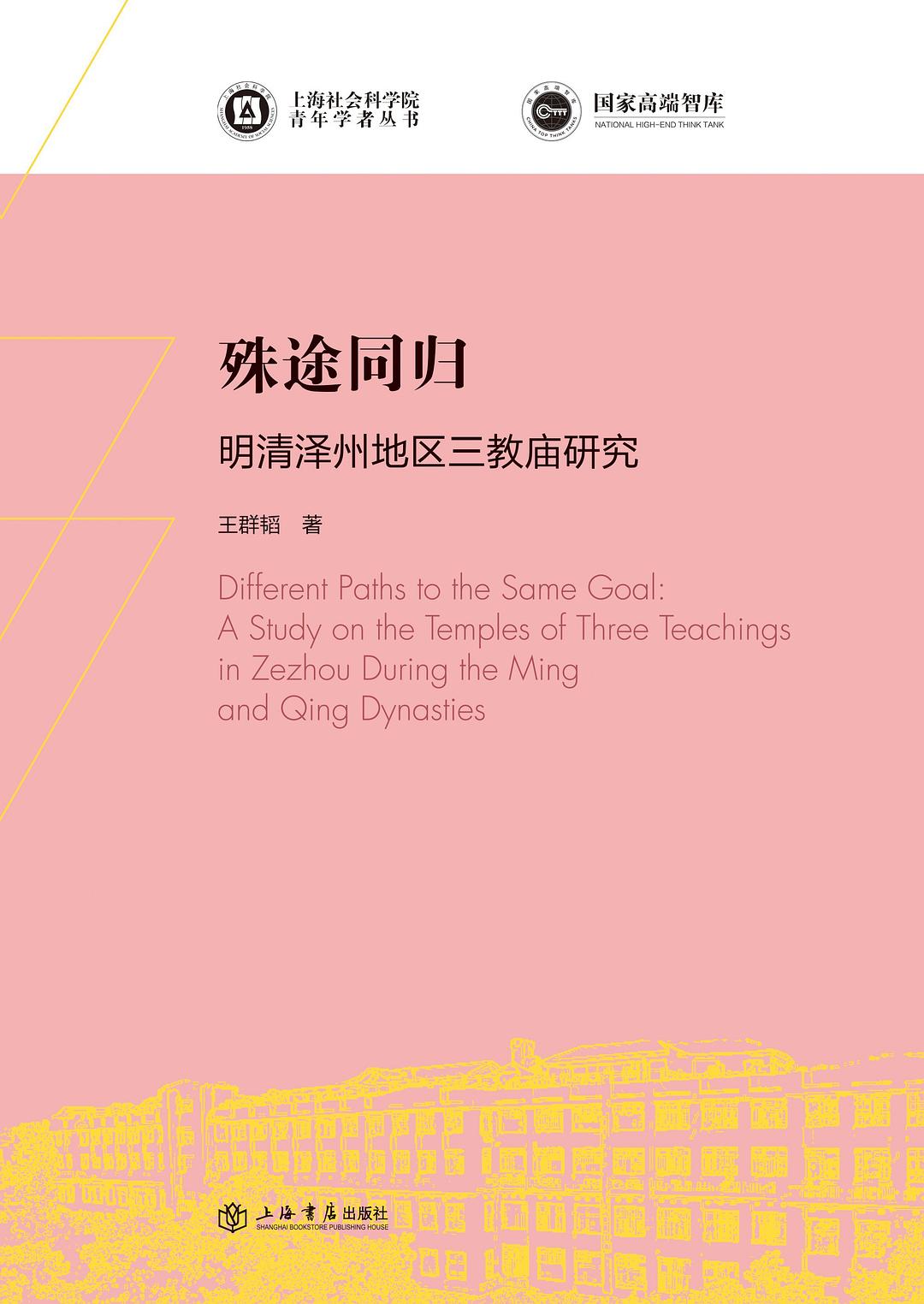
《殊途同归:明清泽州地区三教庙研究》,王群韬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9月版
人们的信仰纷纭复杂,人类的宗教呈现出难以计数的“多样性”;然而,宗教徒、神学家,还有政客们,也会突破重重迷障,用合并、提炼、提升的做法,化繁为简,寻求信仰上的“一致性”,实现信仰上的联合。人类文化分分合合,总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矛盾中彷徨前行,在信仰上也是如此。把世界上的大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合一”确实就是中国宗教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中国古代有“三教合一”,现代有些教派还提出了“五教合一”的说法。不但是宗教家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主张,信徒们还会真的去做种种“合一”的事情,比如合祀、借礼、并香、共庙等等。和西方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东正教、新教)动辄相分的历史很不相同,中国人的宗教,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教,大都倾向于“合”,不太主张“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规定的儒、道、佛的“三教”地位,并不要求三者合一。虽然儒教在王朝体制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在社会上佛教、道教实际上更加流行,并不示弱,因此“三教并立”似乎就是中国宗教的常态。然而,自宋、元、明、清以来,除了“三教并立”的一般格局之外,也流行的“三教合一”神学和实践。主张“合一”的动因有多种,民间有信仰的原因,皇帝有利用的动机,僧侣、道士、儒生也有自己的忧虑和诉求。在儒术独尊的情况下,佛教、道教难以得到官宪的青睐,没有政治优势,比较低调,比较务实,常常是傍着儒教的教义而行。比较来说,儒教高层并不愿意与各种教派人物分享政治权力,常常会“清理门户”,撇清与“释道二氏”的干系。但是,无论如何,在地方士绅那里,在一般的民间信仰中,三教多能和平相处,对应地表达善意,寻找共同教义,吸引到更多香火,这是各种教派、教门都愿意做的事情。于是,我们看到了“三教合一”,几乎和“三教并立”一起,同时构成了中国宗教的另一个常态,这种“多”与“一”的信仰关系,颇可令我们深思与反省。
以前的宗教学者,特别是佛教研究者,做了大量的“三教并立”、“三教合一”的研究。传统的“三教合一”研究,主要是关于教义的讨论,关注的是相关人物、著作、教派和运动。佛教、道教学者为了显示不亚于儒教的正统性,争取神学上的平等地位;儒教学者同情佛教、道教的教义,也会汲取其精华,采纳一些说法。宗教学上常常把这种有内在思想交流的“会通”称为“跨宗教”(cross religion)。但是,这些“合一”之讨论,主要还是“三教论衡”的辨教结果,是教义间的渗透和妥协。我们知道,士大夫的教义研究与一般信众的崇拜实践并不直接相关。民间的香客们对于佛教“圆融”,道教“精一”,儒教“会通”这些教义讨论的兴趣不大,但他们却是“三教合一”的天然信仰者和实际奉行者。民间信仰者到不同的寺庙去拜佛、拜道、拜儒,也可以进同一个寺庙,甚至在同一座大殿里,同时拜祭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以及不同的神祇。对于后一种现象,现在的宗教人类学者倾向于称之为一种“融合论”(syncretism)。如果说我们对于前一种“串庙”现象还有所了解的话,对于后一种“合庙”的“融合论”做法所知则更少。近年来我们对合为一庙的“三教庙”开始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就要归功于王群韬博士所作的调查和研究。
王群韬的《殊途同归——明清泽州地区三教庙研究》对中国宗教“合一”现象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专著的原稿,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博士论文,用他在山西泽州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史籍、方志、碑记、题记等)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北方的“三教庙”。按他的踏勘和考证,发现在华北各地至今还保留着不少“三教庙”。虽然大多已经是民间小庙,且分布在县以下的镇乡农村地区,有的就是在村子里,属于“礼失求诸野”的散乱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把“三教庙”简单地看成是民间自发的“淫祀”,因为它们都有相当久远的来历,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目前确定最早的“三教庙”出现在北宋时期,集中区域是在华北。如太平兴国三年(978),洪洞县箕山有“三教院”;庆历二年(1042),武乡县长乐村有三圣寺。“三教庙”的出现,以一种“合”的形式,破了“三教并立”的格局,儒家士大夫很是诧异。嘉祐年间(1056-1063),蔡州开元寺内有一座“三教圆通堂”,是那种在佛教寺庙里附属的“三教堂”。宋代著名文人梅尧臣(1002-1060)路过该寺庙,留下了一篇《题三教圆通堂》诗,并不是很赞成这种做法。梅尧臣《题三教圆通堂》五律如下:“处中最灵智,人与天地参;其间有佛老,曷又推为三。共以圆通出,诚明自包含;排楹压文础,焕采涂朱蓝。而将置吾儒,复欲笼彼聃;二徒不自晓,恬若均笑谈。越鸟不巢北,代马不嘶南。固亦辨殊土,麟鷟唯时堪。”体会梅尧臣这首诗,他对“三教堂”是一种复杂情感。他以“吾儒”自居,不反对“圆通”,以为可以包含“诚明”。但他对佛教僧侣把孔子、老子“笼”在寺庙大堂,居于佛陀两侧,又感到很不舒服。
和有严格教义和严密组织的西方宗教相比,中国宗教确实有它特有的任意性。中国传统社会对信仰控制较弱的时候,民间就会造出新的神祇,随便建庙。但是,当一种信仰断断续续传承了一千年,就不是简单的“愚夫愚妇”的拜拜行为,已经说明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应该可以用来说明一些问题。“三教庙”的学术研究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和教义上的“三教合一”相配合的祭祀案例。信徒们以“合庙”的香火实践了“合一”的教义,表明中国宗教一直在践行一种“合”的教义,并不是说说而已。王群韬说:“实际上,与思想义理层面的‘合一’相比,三教在信仰实践层面的‘合一’可能更接近‘三教合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特质。”(第2页)最近的宗教学者,大概都同意这个观察和判断。过去的宗教学割裂教义和祭祀,重视宗教教义研究,忽视信仰实践研究,会使得我们得出很多片面的结论,是时候应该得到纠正了。
中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实践,确实有一种主合不主分的倾向。中国古代的宗教和欧洲十九世纪以前不断“裂教”的历史不同,儒、道、佛等建制性宗教的边界并不是泾渭分明,而士大夫和百姓在祭祀中的香火崇拜更常常是三教不分。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一座儒教祠祀会因为请了一位和尚来洒扫而转为佛教寺庙,一座道教宫观会为了招揽香火,加盖侧殿,引入观音、天后、城隍、祖师等,初不论其佛教、儒教。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如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等各主流教派出现的“跨宗教”现象,似乎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学者们还有兴致勃勃地把“三教合一”与当今在基督宗教各主流教派中提倡的“普世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相提并论,这就使得“合一”的研究有了新的意义。
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古代的信仰状况去比附“现代性”,但中国传统各宗教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历来有各种渠道串通一气,这个中西之别是存在的。这种和谐宗教的比较性的说法不是绝对的,因为毁教、灭教的事件在古代中国也经常发生。但与西方宗教相比,儒、道、佛教之间较少冲突,因为有不少“合一”的案例,“宗教和谐”的说法大致能够成立。于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和“文明冲突”的困局中,“合一”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用作对话和交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三教合一”的概念,除了书本教义上的“会通”、“圆融”之外,还有香火崇拜中的“合庙”——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放在一起供奉。教义“圆融”是僧人、道士与儒家文人研讨的事情,香火崇拜表达的各教之间的分合关系,这是要在进到庙里面才看清楚的事情。宗教间的和谐,不单是因为文人在外面提倡,还因为到庙里面烧香的百姓原来就是如此,这才是中国文化在底层的真实基础。
王群韬考察到,在北方地区传承的“三教庙”有不同的名称,如“三教堂”、“三教寺”、“三教庵”、“三教祠”、“三教宫”、“三教殿”、“三圣庙”、“三圣祠”、“三圣宫”等等。祠、庙、寺、庵、宫,在这里看起来有点乱。其实,在明清三教制度中,宗教场所的名称有明确划分,一般把儒教祭祀场所称为“祠祀”,佛教称“寺庙”,道教称“宫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又对应地把与这些场馆相关的神事人员,按习惯区分为儒教的礼生、佛教的僧侣和道教的道士。还有,儒教在文庙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佛教的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和文殊、普贤塑像,道教的三清殿则供奉元始、灵宝、道德三位天尊,而以人世间的老子为道德天尊的化身。如果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三教并立”的话,儒、道、佛之间的壁垒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问题是,“并立”之外,“合一”如何成为可能?王群韬的研究,加上许多前辈学者的成果都告诉我们:民间信仰中也有一股驱动力,它们要求克服不同宗教的局限性,追求统一的超越性神明。把几个神祇联合起来,一体供奉,以此来增强魔力和效应,克服多神、多教的局限性,这也是一种“统一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民间信仰并非天生就是泛神论、多神教,它也有“一神论”崇拜的内在追求。
王群韬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宗教学系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有幸结识。他的导师张志刚教授把他的题目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向这位才思敏捷、腿脚勤快的同道小友探讨起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中国的民间信仰既然被认为只是由乱七八糟的神祇构成的“弥散性宗教”,那么其中有没有对于更高级别的统一神的追求?如果“三教庙”的“合一”崇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性的信仰,这是否意味着“一神论”并非只是宗教家(如耶稣、穆罕默德)的个人主张,只是社会权力(如罗马教会、儒教团体)的强力维持,而是个体信仰者的天然诉求?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持肯定的答案,高兴的是王群韬以他的文献考察和田野调查,帮助我证实了这个肯定。王群韬在本书中写道:“实际上,这类庙宇可能并非‘三教合一’思想向民间社会渗透的直接结果,其真实根源和主要动因,还需要从基层民众自身的信仰实践模式中寻绎。”(第16页)
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宗教学者从事客观研究,引入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深入基层,结合田野调查,对一些民间性质的宗教实践和信仰礼仪做仔细的记录和分析,开始获取成果。在这种宗教人类学的风气下,我们不用教义衡量的俯视角度看宗教,改用“以民为本”的心态去平视民间信仰。王群韬把这个方法论的转变说得很透彻,即“通过呈现中国传统社会知识精英所谓的‘教’(特定信仰传统及其正统观念主导的教化体系)与普通民众所行的‘祀’(祭祀实践及信仰生活的实际形态)之间的差异与张力,确证中国民间信仰生活之于知识精英阶层正统礼法观念的相对独立性,”(第17页)这种因研究方法而生的视野调整,我们通常是用人类学家的判断和研究来支持的,比如:马林诺夫斯基说的“当地人的眼光”(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帮助我们接触到普通人;格尔兹说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帮助我们理解以文化的内部原理。但是,真正将民间信仰作为一个本体来认识,给予它们以独立的地位,则还是来自宗教学对人性的估计,即每个人,每个群体都会有独立的超越性诉求,要追逐一种最高的神明。“独立的”信仰,表现出信众个人选择的特征,是“多”的呈现;“超越性”,则表现出信仰团体的普世诉求,是“一”的升华。
把民间信仰当作其自身,即作为一个本体现象来观察和研究,才能看清中国宗教的本质。任何宗教,只要稍有建制性特征,都会被国家、团体和个人用为工具,达到信仰以外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别的本体,如政治、伦理、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宗教,但是如果是为了理解信仰本身,那就需要转换到宗教学领域,把民间信仰看作是信仰本身。我和王群韬都同意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结论,“将三教圣人组合崇奉的主要动因来自基层社会,体现了民众对三教信仰资源都加以积极利用的意愿。”(转自第208页)在民众自主的信仰行为里,他们为了各种日常生活的原因,祈求神明。当一个佛陀的福报还不够的时候,他们加上了老子、孔子。再不够灵验的话,他们还会转求更多的神祇,关公、城隍、祖师,以及各种娘娘、老爷。这当然是宗教学家过去描述的“多神教”特征,但这种类型的“多神教”也在追求一种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方式的整体性,即一种世间万物被神祇(们)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完美状态。和“一神教”相比,“多神教”的整体性就是空缺一位“独一尊神”。中国的民间信仰并不缺乏整体性,高延(J. J. M. de Groot)等人称“中国宗教系统”是有见地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停留在“三教庙”的权威性,他们对于最高神明的诉求还在继续。我们看到在佛教、道教和民间崇拜红,无论在学理和祭祀中,一直还在寻求终结神明。
虽然我们在目前的宗教学建设中提倡“以民为本”、以信仰为本的研究,但不能否认的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研究民间的信仰,永远是宗教学最有兴味的话题。任何宗教都有其复杂的“政教关系”要研究,而中国的民间信仰与王朝体系的关系与儒、道、佛教同样密切。“三教庙”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民间信仰,它和王朝政治也有密切关系。根据我们在上海嘉定发现的一块《三教堂记》(揭傒斯),元代仁宗皇帝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曾敕令在全国修建“三教庙”。“延祐中,仁宗皇帝尝语群臣曰:‘闻卿等尊周孔者薄佛老,崇佛老者斥周孔。第以儒视儒,佛视佛,老视老,何必纷纷如是耶?’此至言也。此圆通寺三教之堂所以作也。”元代的历史较短,留下的文献较少,我们初步据此推断,正是由于元仁宗的敕封,“三教庙”在宋代以后从民间庙曾经转为官方庙,推广到南方。元仁宗是忽必烈的曾孙,在位九年,推行儒术,翻译经书,恢复科举,对儒家算是相当不错。但是,他这次提出,佛教、道教不要排斥周公、孔子,儒教也不能太骄傲,只“尊周孔者薄佛老”。他提出的三教联合方案,就是“圆通”。按照梅尧臣在蔡州开元寺内看见的“圆通堂”情况,“而将置吾儒,复欲笼彼聃”,那是把佛陀居中,老子、孔子侍在右左,三大教主一起保境安民的样子。
元仁宗的这个“合庙”敕令,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国策,由元世祖忽必烈定下来的,初不称“三教合一”。按草原民族泛神论的简单原理,就是所有的教门、教派都有用,都可以为元朝所用,为蒙古祈祷。《马可波罗游记》这样记载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他要所有的宗教都来大都汗八里朝拜,不同的节日都要庆祝,不同的神祇都要敬奉。忽必烈说:“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图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最高位而真实者受我崇奉,求其默佑。”(《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5页)马可波罗没有说忽必烈是不是已经把释迦牟尼等四位先知合庙祭祀,但把所有宗教放在一起,竞争合作,已经是蒙古人入中华以后的既定国策。元仁宗是忽必烈的四世孙,他把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塑像放在一起,“合庙”祭祀,是元朝宗教政策“中国化”的一种做法,既采用了宋代学者讨论的“三教合一”命题,也用上了北宋时期北方民间的“三教庙”做法。
我们收集、整理、编辑《上海地区儒道佛教碑刻文献》,在嘉定发现了这一座“三教堂”,就是这种儒、道、佛的“三教合庙”。按《嘉定县志》记载:“三教堂,在城七图。元至顺三年,僧善学建,学士揭傒斯为之记。明朝永乐间,道士涛道炫;正德间,道士朱粹然各有增修。”嘉定的三教庙,是一座庙中庙,设在元代嘉定报国圆通寺内。有独立的主体大殿,额名“三教堂”。堂内供的是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和孔子,分列右左。这座佛教寺庙始建于元代至顺三年(1332),地点在嘉定县城北的清境塘边上。寺庙名称就是“报国圆通寺”,元代僧人善学创建,翰林院大学士揭傒斯写了碑记。明代永乐年间,报国圆通寺有道士进入,被改作道观,正德年间还有扩建,位置在城内三图拱星坊。嘉靖县志说在“县治后”。嘉定陶继明老师提供线索,说庙址“八一三”抗战中被日机炸毁,该处现称为福宁弄。
嘉定的“报国圆通寺”,和同城传承至今的南梁古刹“护国寺”应该是没有干系。江南地区稍大一点的佛教寺庙,多冠名“报国”、“保国”、“宁国”、“护国”,就说明国家权力掌控江南,而儒、道、佛教与王朝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利用的紧密关系。嘉定护国寺位于西门内,报国圆通寺位于县城北境。县城有南北向的横沥塘,有东西向的清境塘,都是市河。按《嘉定碑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提供的考证,“清境塘,河道名,横贯嘉定县城。在横沥西者,称西清境塘;在横沥东者,称东清境塘。”800年的古城嘉定,是苏州府内富裕、繁荣的县份,科举发达,财富集中,香火虔诚。“三教庙”能够进到市中心建造,可见王朝力量的强势,也可见佛教、道教在民间根基深厚。
梅尧臣生活的北宋时期,“三教堂”都不是在都城、郡邑里,是在比较偏僻的县城,有的甚至是在乡下的村子里。这里还来不及做仔细的考证,我只是根据王群韬的研究做出“大胆假设”:北宋时期的“三教庙”是北方农村地区的民间信仰,是基层的香客、僧人、道士们首先把儒、道、佛教分别尊奉的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放在自己的小庙里一体敬奉,成为“三教庙”。也就是说,初期的“三教庙”是香火崇拜中的自然而然,还没有和国家和地方的权力建立联系。我们在江南镇乡一级的民间信仰中看到,有大一点的庙,开始就一间房间,很多老爷挤在一起。等到土地、资金落实,建造大庙,才逐步地分设殿、堂、厅、室,每个老爷都有一个专间。王群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相似的情况,老百姓把许多老爷放在一起敬奉,杂七杂八,并非就是喜欢“淫祀”,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空间有限,财力不够。空间不够,财力有限,干脆就“合庙”,好几个神祇挤在一起,造成满当当的寺庙了。
北宋时期的“三教堂”是北方独有的现象,南方少见,所以宣城人梅尧臣才会诧异地描写“其间有佛老,曷又推为三”,才说“越鸟不巢北,代马不嘶南”。到了元朝,或许就是从元仁宗开始,由于皇帝敕令各地建造“三教庙”,这种“合庙”的“三教堂”就推行到了南方,连地处东南海辄的嘉定县也有建造。从清代文献来看,元朝灭亡以后,明清两代的“三教庙”在南方也没有因位朱元璋所谓的“驱除胡虏”而消失。改朝换代以后,南方的汉族百姓保留了这个信仰。多年的香火供奉,肯定有不少灵验事迹,便能够使其成为有着本地传统的民间信仰。清代海宁学者周广业(1730-1798)对江南地区还偶有所见的“三教庙”有所议论,他在《循陔纂闻》中说:“国初有所谓‘三教堂’者,齐、鲁间郡县皆有之,不知何人作俑,雕塑形象,佛居中,道居左,孔子反居其右。”(王群韬所见国图藏清钞本)虽然儒生士大夫反对“三教庙”里把孔子放在一边,但民间认为合理,因而香火不断,明清以来一直有信徒供奉。
“三教堂”在南方不是很强,但在北方地区一直非常兴旺。“三教堂”、“三教庙”,在北方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地区非常流行。儒教人士对于这种以佛教和佛陀为中心的民间信仰一直耿耿于怀,总想伺机取缔。乾隆九年(1744),河南学政林枝春说“豫省合计凡为三教堂者,凡为五百九十余处。”林枝春对“三教堂”中孔子地位屈居于右的状况强烈不满,故而上疏《为崇祀非经仰请饬禁以隆圣教事》,要求朝廷出面加以禁止。然而,乾隆出于王朝友善不同宗教的利益目的,对于佛教、道教并不太反感。他担心的是“异端”闹事,既然不聚民众的香火无害大局,对于儒者的小题大做,也就以弛禁了事。道光十六年(1836),山西学政汪振基又一次提出来要禁止省内的“三教堂”,皇帝“通敕各属即行更正,毋得同庙供奉,……一律更正,以崇正学而昭体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文献编号405003570,转见曹新宇《清前期政教关系中的儒教及三教问题:乾隆朝三教堂案研究》,《清史研究》,2019年3月,均见王群韬书引)也是弛禁。根据王群韬的调查,北方地区的“三教堂”一直保留,现在还有香火。江南地区的“三教堂”原来就不普遍,历代记载不多。但是,嘉定“护国圆通寺”内的这座“三教堂”,似乎是个例外。它在元代听从了世宗皇帝的敕令,迅速建立。以后在明、清改朝换代也没有灭绝,直到清代还屡次重修,可见它的香火延续了好几百年。
王群韬聪颖好学,200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专业,硕士阶段师从程乐松教授、博士阶段师从张志刚教授,十年寒窗,至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一直都在研究华北民间信仰。十多年前,张志刚教授和我相约开拓研究中国宗教,找学生一起做田野调查。此后到北大,就常常见到群韬这位小友到处奔走,勤奋治学。群韬是广西桂林人,研究华北的信仰,咨询于乡村老人,还有方言上的障碍。另外,在哲学形而上训练已经轻车熟路之后,一下子扎到乡镇,在抓不到任何概念可以运用的情况下,独立分析和处理“弥散性”(又曰“乱七八糟”)的民间信仰,难度可想而知。中国大陆的宗教人类学尚在起步阶段,而结合中国宗教的人类学研究更是步履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群韬的研究在方法论、文献学、田野调查积累等方面,一开始就是独立进行,且富有艰难开创性的。
群韬生在桂林,学在北京,工作在上海,现在有了这一份“三教庙”的华北民间信仰研究作基础,将来的学术前景一定广阔。对宗教人类学来说,“地方”(local)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对区域文化不敏感,不能在一个看似相同的概念下按语境区分出的不同的人情世故,大概是不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并不是没有某种文化的体验就不能从事某种文化的研究,而是,研究者要有能力从事多种文化的比较,没有能力就学,就去调查,就去理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就着那么多的“文化多样性”,研究南北不同风俗之间的渊源、特征和差异,也是学习中国民间信仰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中国宗教初看差别不大,“莫非王土”的格局下,似乎是同质的。其实,沉到民间信仰的底层,从乡镇社会看中国,江南、岭南、华北、西南、西北、东北都有非常不同的传统和现状。从中国宗教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候与经典文献和权威著作中的现有说法完全不同,而这正是这一研究引人入胜的地方。
本文为《殊途同归:明清泽州地区三教庙研究》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