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生大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1881.2.9
图为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黎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爱情、发现大海那样,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开篇,博尔赫斯如此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作家们,总是绕不开去阅读他、谈论他、引用他,以及受他的影响去创作——纪德在1922年关于陀氏的六次讲座中谈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生大事”;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正与反”一章的影响,加缪创作了他的随笔《反抗者》;村上春树更是夸张地写道:“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通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还有一类就是尚未通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而国内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事实上也从未止息。鲁迅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1936年)中写道为何热爱陀氏:“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余华也曾写自己二十岁第一次读到《罪与罚》时被炸得“晕头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像是轰炸机一样向我的思绪和情感扔下了一堆炸弹,把二十岁的我炸得晕头转向……这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六十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这每分钟一百二十次的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
后来陀带来的“不断的阅读高潮”又持续诱惑着余华:“我既盼望陀式叙述高潮又恐惧陀式叙述高潮。那段时间我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都觉得味道清淡,如同是尝过海洛因之后再去吸食大麻,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没感觉?”
大概所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都会对这种欲罢不能的“荼毒”难以忘怀,于是他的作品不断被各种知名导演改编,并反复出现在国内外影视作品中——伍迪·艾伦、今敏、李安、滨口龙介的影片里,都能看到他们阅读陀氏的蛛丝马迹;《武林外传》中的吕秀才都不忘致敬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
“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夏仲翼《“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陀氏的面貌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我们整理了陀氏 9 部作品(依出版时间倒序排列)中的名句名段。这些内容你可能早已读过,或者在某些访谈中听到过,当我们再次重读,依稀能从其中辨认出为什么陀氏被阅读、被爱上以及在现在依旧被反复引用或提及的答案。
《卡拉马佐夫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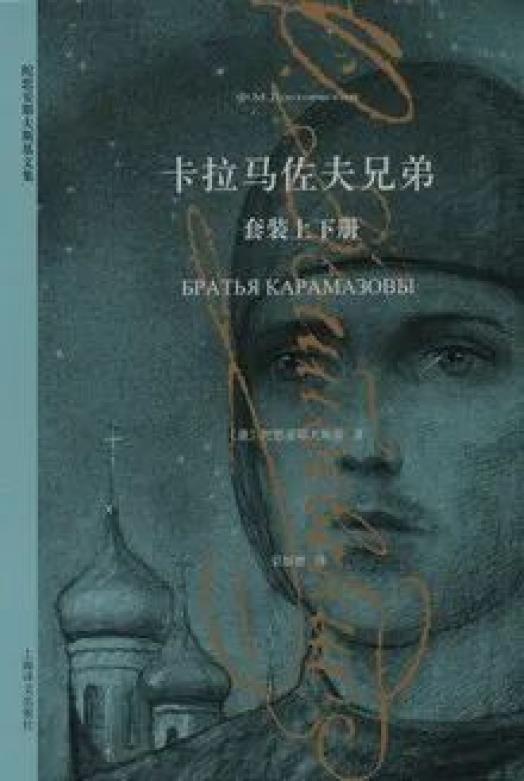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刚才我坐在这里,你猜我对自己怎么说?我说:即使我不再相信生活,即使我对珍爱的女人失去信心,对常理失去信心,相反,甚至确信一切都是混乱、可恶乃至被魔鬼操纵的一团糟,即使一个人绝望时的种种恐怖统统临到我头上——我还是要活下去,一旦从杯中抿了一口,便再也不愿舍弃它,直到把酒喝干为止!不过,到三十岁我一定把杯子扔掉,哪怕没有喝完也扔掉,然后离去……不知道去何方!但是,我坚信在三十岁之前我的青春将战胜一切,战胜对生活的种种失望和厌恶心理。我曾多次自问:世上有没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能压倒我身上这份狂热的、或许有失体统的渴望——生的渴望?结论是大概不存在,应该说同样也是在三十岁之前不存在;过了三十我自己会失去这份狂热,我有这感觉。某些患痨病的黄口道德家,尤其是诗人,往往称这种生的渴望是卑鄙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卡拉马佐夫的特征,这是事实。不管怎样,你身上一定也有这种生的渴望,但为什么它是卑鄙的呢?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向心力还强大得可怕,阿辽沙。就是想活下去,我愣是活着,哪怕不合逻辑。尽管我不信万象有序,但我珍爱黏糊糊的、春天发芽的叶片,珍爱蓝天,珍爱有时自己也不知道——信不信由你——为什么会爱的某些人,珍爱人类的某些壮举,也许我早已不再相信这等丰功伟绩,但仍出于旧观念打心眼里对之怀有敬意。
……
“太明白了,伊万。‘发自五内,发自脏腑的爱’——你说得好极了,你对生活的渴望如此强烈,我说不出有多高兴,”阿辽沙感叹道。“我认为,在世上人人都应该首先爱生活。”
“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
“一定得这样,像你所说的超越逻辑去爱,一定得超越逻辑,那时我才理解其涵义。我早就朦朦胧胧地有这样的想法。你的工作已完成一半,伊万,你已取得一半成果,因为你爱生活。现在你必得为另一半努力,这样你就得救了。”
——第九章 正与反
我得声明在先:我像小孩子一样深信,创痛将会愈合和平复,一切可笑可悲的人类矛盾将会像可怜的幻影一样消失,因为它们是不中用和渺小如原子的欧几里得式人脑可鄙地虚构出来的。我深信,到了世界的大结局,在永恒和谐来临的时刻,将会发生和出现如此珍贵的景象,它足以让所有的心都得到满足,足以平息所有的愤怒,抵消人类所有的罪恶,补偿人类所流的全部鲜血,足以使宽恕人类的一切所作所为成为可能,甚至可能为之辩护,予以认可,——纵使这一切将会实现,但我不接受它,也不愿接受!纵使平行线将会相交,而且我将亲眼看到,不但看到,我还会说平行线相交了,然而我还是不会接受。这就是我的本质,阿辽沙,这就是我的信条。我这话是认真对你说的。
——第九章 正与反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记住这话。阿列克塞,我曾因你的面容默默地为你祝福许多次,现在我让你知道,”长老面带安详的微笑说,“关于你我是这样想的:你将走出这里的院墙,在红尘中你会像一个修士那样做人。你会有许多敌人,但是连你的敌人也会爱你。生活将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将从这些不幸中得到幸福,你将为生活祝福,也促使别人如此——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十章 俄罗斯修士
如今人人都力图最大限度地各自为政,都想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追求生活的完满,其实他们的一切努力并不能得到生活完满的结果,只能是彻底的自我毁灭,因为充分确立自我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陷入十足的自闭。因为当代所有的人都分散成单独的个体,人人都把自己关在洞内,人人都远离他人,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统统藏起来,结果自己不与他人为伍,也把他人从自己身边推开。人在自闭状态下聚敛财富,自以为实力雄厚,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这疯子攒得越多,就在自我毁灭的虚弱中陷得越深。因为人已习惯于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把自己与整体割裂开来;不相信别人的帮助,不相信他人,不相信人类这一观念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他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的钱财和既得权利。可笑的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如今人的头脑都开始无法理解,真正要做到高枕无忧,关键不在于个人如何独自苦干,而在于人们齐心协力。但这种可怕的自闭状态也总有到头的日子,那时人们将恍然大悟,过去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是多么不自然。到那时,人类之子的标识将在天上展现……。但在这之前,仍须坚持这面旗帜,时不时地应该有人——哪怕只是个别人——做出榜样,引导人心从自闭中解脱出来,为大同博爱作出贡献,为大同博爱作出贡献,即使被目为疯子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不让伟大的思想成为绝响……
——第十章 俄罗斯修士
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
——第十七章 尾声

 《纽约,我爱你》
《纽约,我爱你》 《我的天才女友》
《我的天才女友》 《十三邀》许知远 x 罗翔
《十三邀》许知远 x 罗翔《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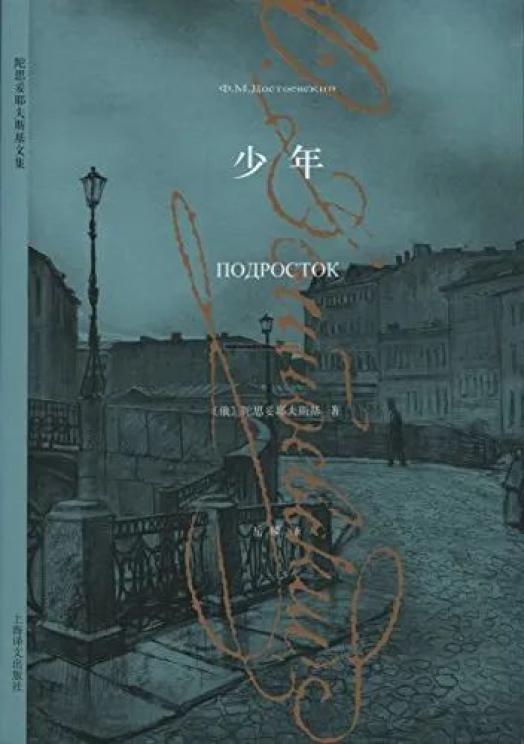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岳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岳麟 译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和道德都归结为一句话:应该从善避恶。
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力量,特别是意志和愿望的力量。要有沸腾的开水般的温度和有烧红的铁一般的温度。
“既然你觉得很无聊,那就努力去爱什么人或什么事业吧,或者甚至简直执着于什么。”
我没有权利评论别人,因为‘我不会感到痛苦的’,而要做别人的裁判官,必须使自己饱经痛苦才有评论别人的权利。
一个俄国人只要稍微脱离对他来说已成为刻板的、合法化的生活习惯的轨道,他立刻就会不知所措。在轨道上一切都明白清楚的:收入啊,官衔啊,社会地位啊,马车啊,拜客啊,差事啊,妻子啊,——但是稍微离开一点,我成了什么呢?就成为一片被风卷走的树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两个月来我极力不脱离这轨道,我爱这轨道,习惯于这轨道了。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悲愁仿佛与快乐混合一起了,变为喜悦的叹息。在人世间就是如此:每个灵魂都会受到考验,得到安慰的。
人们在这样的时刻决定自己的命运,确立自己的观点,一生中只这么一次对自己说:“哪里有真理,就应该到哪里去,以求得真理。”
《群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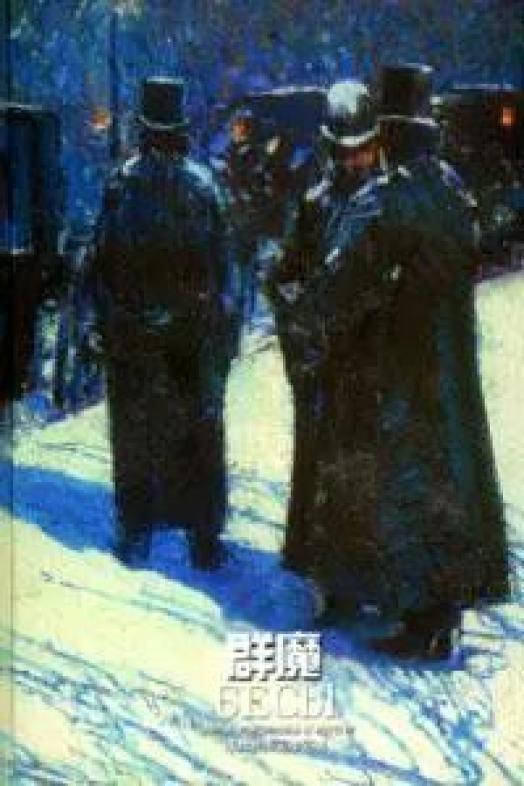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 臧仲伦 译
译林出版社 / 臧仲伦 译难道他们就不明白,要取得一种见解,首要的条件是劳动,自己的劳动,凡事都应有自己的首创精神,自己的实践!不费吹灰之力是永远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只要我们劳动,就会有自己的见解。可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劳动,所以迄今为止代替我们工作的人就会代替我们拥有他们自己的见解。
别人能够想一件事,接着又马上想另一件事。想另一件事我做不到。我毕生都在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
一个人之所以不幸,乃是因为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仅仅因为如此。这就是一切,一切!谁知道了这个,谁就会立刻,马上幸福起来,即刻幸福起来。
我不想祝愿您幸福无边——太俗气了;我也不希望您遭殃;而是向平民百姓的人生哲学学习,只是简单地重复:‘祝您长寿’,并努力设法做到不要太烦恼。



 《丈夫、太太与情人》
《丈夫、太太与情人》《白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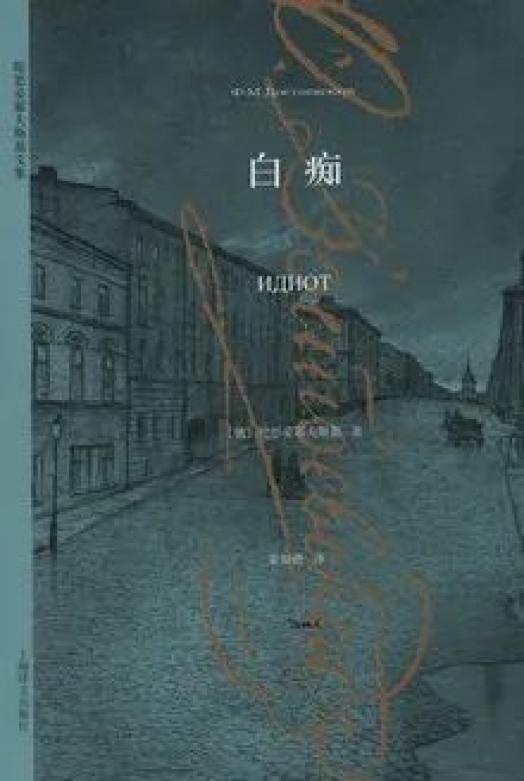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起先,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想到别处去,我曾经坐立不安。我老是考虑将来怎样生活,想去探索一下自己未来的命运,某些时候简直如坐针毡。你们也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时刻,特别在孤独的情况下。我们那儿有一处瀑布,并不大,像一条细细的线,几乎垂直地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色白如练,水声喧嚷,飞沫四溅。瀑布的起落点很高,可是看起来相当低;其实在半里以外,可是好像只相隔五十步。夜里我喜欢听瀑布的声响;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感到异常惶惑。有时在正午前后,我走到山上去,一个人站在半山腰里,周围都是古老、高大、清香的松树;崖顶上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已经变成废墟;我们的小村庄在很远的山下,几乎看也看不见;阳光灿烂,碧天如洗,四周静得可怕。此时此刻,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只要一直往前走,走上很久很久,走到天地相接的那条线后面,谜底便可揭晓,我就能看到新的生活,比我们那里丰富、热闹一千倍的生活。我老是梦想到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里去,那里到处是巍峨的宫殿,到处是轰隆隆的声响,到处是沸腾的生活……。是啊,我梦想的可真不少哇!
我的确不喜欢跟大人、跟成年人在一起,——这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不喜欢是因为不善于跟他们相处。无论他们跟我说些什么,无论他们待我怎么好,我和他们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不自在,有机会离开他们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急于去找我的伙伴。而我的伙伴总是孩子们,倒并非因为我自己是孩子,只不过孩子们对我有吸引力罢了。我刚开始住在乡下时,——也就是我经常到山里去独自忧伤的那个时期,——有几回,特别在中午放学的当儿,我一个人闲步转悠,会遇见这帮闹嚷嚷的小家伙带着书包、石板一路跑,一路喊叫、嬉笑、玩耍,——那时我的整个心灵一下子都会向他们飞去。不知为什么,每次遇见他们,我就产生一种非常强烈、非常幸福的感受。我停下来,看着他们老是在跑步的小腿不断晃动,看着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在一起飞奔,看着他们笑,看着他们哭(因为在从学校跑到家里的这段路上,好多孩子已经打过架,哭过鼻子,又重归于好,还玩了一阵子),我由于心中快活而笑起来,那时我的忧伤便会通通忘掉。在以后的整整三年内,我简直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忧伤,干吗要忧伤?我的全部情趣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从来不打算离开那个村庄,甚至压根儿没想过将来要到此地俄国来。我以为自己将一直待在那里,但我终于看到,我的生活不能老是让施奈德负担;这时就冒出来一桩事儿,它的重要性看来促使施奈德自己催我动身回国,并且代我向国内作了答复。我想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想找人商量一下。也许,我的命运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但归根到底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的整个生活已经改变。我在那里留下的很多很多,简直太多了。这下全部化为乌有。我坐在火车上,心想:“现在我要走到人们中间去;也许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新的生活开始了。”我决心诚实而坚定地去办我的事。与人们相处我也许会感到乏味和难堪。首先,我决心对所有的人都要有礼貌,要坦率。
必定有一种力量比车碾火烧,甚至比二十年的习惯更强大!可想而知,有一种思想比一切灾难、荒歉、酷刑、瘟疫、麻风更厉害,比整个地狱之苦更厉害,而要是没有这种把大家拴在一起、给心灵引路、使生命的泉源永不枯竭的思想,人类是无法熬过来的!请你们给我指出,在我们这个混沌和铁路的时代,有什么能和那种力量相比?……不,我应该说,在我们这个‘火轮和铁路的时代’,可是我说了‘混沌和铁路的时代’,因为我醉了,但也符合实际!请给我指出一种能把当今人类拴在一起的思想,哪怕只有七百年前那种力量一半强也行。最后,请你们壮起胆来说:在这颗‘星’下面,在这张缠住人们的网下面,生命的泉源没有衰竭,没有变得浑浊。别拿你们的繁荣、你们的财富以及饥荒罕见和交通迅速来吓唬我!财富增加了,但是力量减弱了;把大家拴在一起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软了,一切都酥化了,人人都酥化了!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酥化了!
什么是幸福?哦,请相信我的话,哥伦布感到幸福不是在他发现了美洲的时候,而是在他将要发现美洲的时候。请相信我的话,他的幸福达到最高点的时刻大概是在发现新大陆的三天以前,那时哗变的船员在绝望之余险些把船头转向欧洲往回走!问题不在于新大陆,哪怕这块大陆化成灰、不见了也无所谓。哥伦布几乎没看到这块大陆就死了,他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发现意味着什么。问题在于生命,仅仅在于生命,——在于发现生命的这个不间断和无休止的过程,而完全不在于发现本身!
要知道,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分岔多得不计其数。最高明的棋手、其中洞察力最强的也只能料到以后的几步棋;一位法国棋手能预先料到十步棋已经被当作奇迹大书特书。而人生有多少步棋要走?我们无法预料的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的时候,当您撒下您的“慈善”、做无论何种形式的好事的时候,您是在把您的个性的一部分给予别人,并把别人个性的一部分接纳到自己身上;你们互相交流,彼此沟通;只要稍加注意,您就会得到补偿,那就是知识,就是种种最意想不到的发现。您最终一定会开始把您做的事情看作一门科学,它将把您的整个生命吸引过去,也能够充实您的生命。另一方面,所有您的思想、所有您撒下后也许已经被您忘掉的种子,都将得到体现,都将成长发育;得之于您的人还将把它们交给别人。
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人人都爱,爱所有的人,爱一切邻人——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甚至是不自然的。抽象地爱人类实质上几乎总是只爱自己。
 《钢琴家》
《钢琴家》《罪与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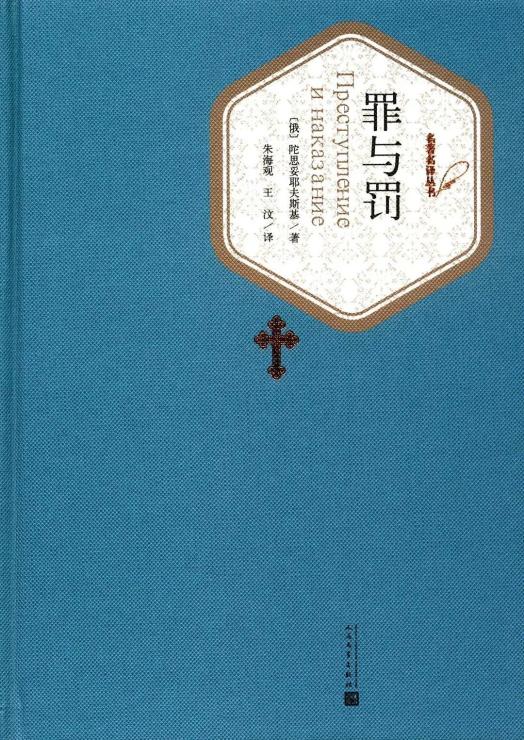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朱海观、王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朱海观、王汶 译人可以主宰一切,可是一胆小,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我真想知道,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迈出新的一步,讲出自己的新见解……
“我喜欢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秋天晚上听手摇风琴伴奏下的歌唱——一定得是潮湿的晚上——那时所有行人的脸都白里透青,带有病容;要么,没有风,湿漉漉的雪花一直往下落,那就更好了,您懂得我的意思吗?而煤气街灯则透过雪花在闪闪发光……”
你可以向我胡说八道,但是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说,那我就会吻你。照自己的意思胡说八道比照别人的意思说实话甚至还好些。照前一种情形去做,你是一个人;照后一种情形去做,你不过是只学舌的鹦鹉!真理不会逃走,可是生活却可以被封锁。
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
在世界上,没有比说老实话再困难的事,也没有比说奉承话再容易的事了。说老实话的时候,只要有百分之一的音符走调,就会立刻产生不谐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出乖露丑。但是,说奉承话的时候,即使从头到尾都是假话,也会叫人高兴,听起来仍旧不无快乐,虽然这种快乐粗鄙,然而毕竟是快乐。奉承话说得再肉麻,至少有一半听上去像是真的。这适用于社会上各种水平的人和各个阶层。
每个人都为自己设想,最善于欺骗自己的人,生活过得最快乐。

 《白箱》
《白箱》《地下室手记》
 漓江出版社 / 荣如德 译
漓江出版社 / 荣如德 译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而这目的本身,不用说,无非就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可是,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漂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
《死屋手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娄自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娄自良 译一切——都是对人的侮辱与凌虐……是呀,人的生命力真强!人是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想,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
但我觉得,可以根据笑声去了解一个人,初次相逢,倘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那么您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好人。
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
任何一个逃亡者所希冀的并不是获得完全的自由,他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想或者换个环境,或者被强迫移民,或者按新的罪行——在流浪中所犯的罪行重新受审,总之,去哪里都行,就是不要留在使他厌烦的老地方,不待在原来的监狱里。
没有一个目的和对目的的追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真正地活着。失去目的和希望,人往往会苦闷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和出狱。

 《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
 《东京教父》
《东京教父》《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娄自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娄自良 译她受了虐待,伤口不能愈合,于是她好像故意要用古怪的举止,用不信任任何人的态度来触痛自己的伤口;好像她自己在欣赏自己的伤痛,欣赏这种痛苦中的利己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样触痛伤口并欣赏自己的伤痛,我是能够理解的:许多受欺凌、被侮辱,遭到命运的迫害而深感命运不公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尽管我们被伤害,尽管我们被侮辱,可是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让那些傲慢而骄横,伤害并侮辱我们的人得意去吧!让他们去诽谤我们吧!别怕,娜达莎……我们要手牵着手出去,我要告诉他们:这是我钟爱的女儿,这是我无辜的女儿,你们侮辱她,伤害她,可是我,我爱她,我要永远为她祝福!……
《白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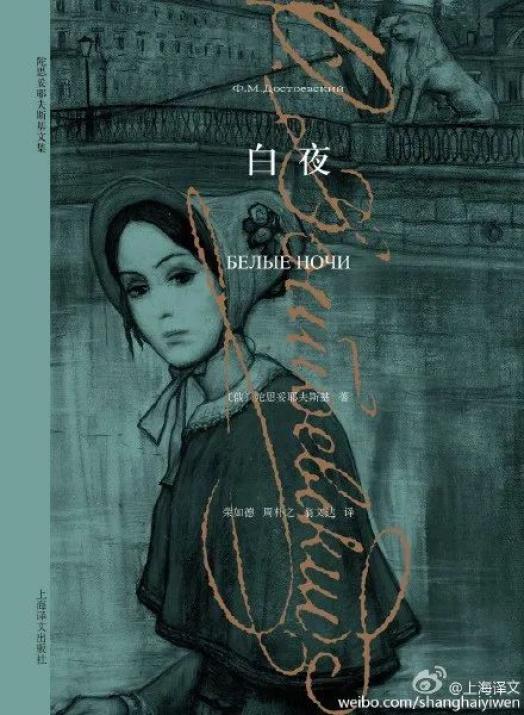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荣如德 译幻想家——如果需要下一个详细的定义的话——并不是人,而是某种中性的生物。幻想家多半居住在不得其门而入的角落里,好像躲在里边连日光也不愿见;只要钻进自己的角落,便会像蜗牛那样缩在里边,或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很像那种身即是家、名叫乌龟的有趣的动物。照例漆成绿色的四壁已被熏黑,可他就是喜欢这间令人沮丧、烟味呛人的屋子,您说,这是为什么?他的熟人为数不多(最后会全部绝种),当难得有人来拜访这位可笑的先生时,他一见来客总是那样狼狈,面色大变,神态慌张,仿佛他刚在屋子里干了什么犯罪的勾当,不是印假钞票,便是炮制几首歪诗寄给某杂志,同时附上一封匿名信,诡称该诗作者已死,他的朋友认为发表他的遗作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您说,这是为什么?
与此同时,我听见人群在我周围生活的旋风中喧嚷、打转,我听见、看到人们在生活——实实在在地生活,看到生活对他们说来不是此路不通的,他们的生活不会像梦境、幻影那样风流云散,他们的生活不断更新,永葆青春,其中没有一时一刻与别的时刻雷同,而胆怯的幻想却是那么无聊和单调得近乎庸俗,它无非是影子和思想的奴隶,是第一堆浮云的奴隶,一旦浮云遮住太阳,忧伤便会紧紧攥住如此珍惜自己的太阳的真正的彼得堡之心,——而在忧伤中哪里还有心思想入非非!我感觉到,它——这种永不枯竭的幻想——终于疲倦了,终于在无休止的紧张状态中枯竭了,因为我在成长,从过去的理想中挣脱出来了,这些理想已告粉碎、瓦解;既然没有另一种生活,就得从这些残垣断壁中把它建设起来。可是,心灵却要求得到别的东西!于是,幻想家徒然在往日的梦想中翻寻,在这堆死灰中搜索一星半点余烬,企图把它吹旺,让复燃的火温暖冷却了的心,让曾经如此为他所钟爱、如此触动灵魂、连血液也为之沸腾、热泪夺眶而出的一切,让曾经使他眼花缭乱、飘飘欲仙的一切在心中复苏!
您倒说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并不像同胞手足那样?为什么最好的人也总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别人,不对人说?为什么不直截痛快地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尽管明知道这话说出来不会毫无反响?可是偏偏每个人都要摆出比实际上严峻的样子,似乎人人都怕让自己的感情很快地外露有损自己的尊严……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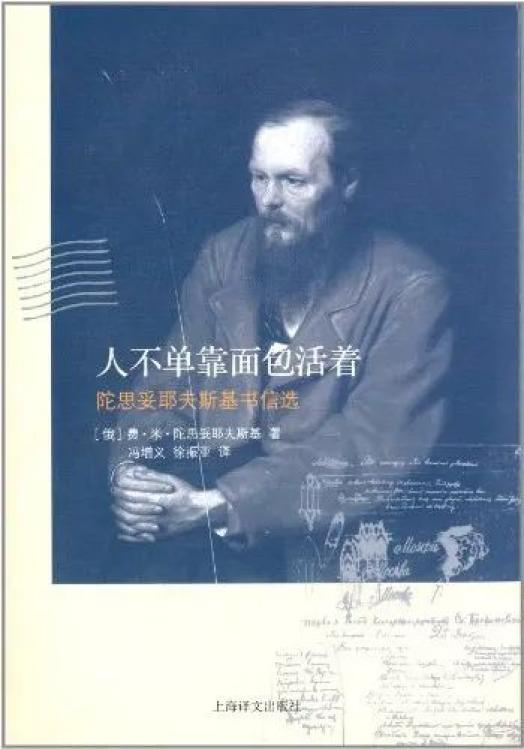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冯增义、徐振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冯增义、徐振亚 译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
每当回忆过去,想到浪费了许多时间,把时间耗费在迷误、错误、无所事事、无节制的生活上,想到我不珍惜时间,多次做出违心和勉强的事情——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非常痛心。生命是一种天赋的能力,生命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无限幸福。
我觉得,我对任何书本都会感到无比高兴,尤其是阅读将对健康大为有益,因为可以用别人的思想克制自己的思想,或按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改造……
即使好人也会逐渐变坏。他们看不到自己身边的活动,却开始按照书本上写的那样抽象地爱人,他们爱整个人类却蔑视个别的不幸者,一见到他就觉得无聊并且避之唯恐不及。
但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在地球上发生的一切,对此有着最高的道义上的原因。我是人,对人间的一切都感兴趣。
 《大师与玛格丽特》
《大师与玛格丽特》原标题:《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生大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