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M.米勒:在森林史上,12世纪中国的一些发展看起来很像16世纪起步的欧洲林业 | 纯粹历史
孟一衡,本名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出生于美国费城,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师从宋怡明,现为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森林史、中国史。他的著作《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中文版最近由上海光启书局出版(列入该社“人与环境”丛书)。该书展现以杉木为主的人工林与宋元明历朝政治经济的交织,考察了约1200—1700年的中国森林史,挑战了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提出的“大毁林”的论断。现特推出该书中文版编辑肖峰对孟一衡的文字访谈。

杉木与帝国: 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
作者:[美]孟一衡 著 张连伟 李莉 李飞 郎洁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9
肖峰:你的老师宋怡明专门为《杉木与帝国》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语,提到你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运用在了环境史这样的新领域,可否说《杉木与帝国》既是一本环境史的书,又是一本早期近代中国(宋元明)社会经济史的书?你在哈佛的求学经历,尤其是跟宋怡明的求学经历,对这本书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孟一衡:我非常幸运能够在哈佛大学跟随宋怡明教授学习。受教于他,我不仅学习了采用宏观视角的社会经济史,还学习了将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利用史料的方法。他教导我关注诸如契约和家谱等日常文献。我在探究的问题显然很大程度上是跟环境有关的,但我的研究方法几乎都来自社会经济史。我也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有些许不同地看待社会经济史。毕竟,中国不仅仅是农场和城市之地——它也是森林之地,这些森林是中国社会演变的核心部分,也扮演了重要的经济角色。
肖峰:环境史是史学的一个新门类,在美国已经很成熟。森林史在美国的历史甚至更加悠久,根据J.唐纳德·休斯先生的《什么是环境史?》,美国森林史学会将起源追溯到1946年,从1959年开始独立存在,在1996年与美国环境史学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发行《环境史》杂志。这意味着在欧美,尤其是美国,森林史研究有自身独立的边界,能介绍一下如今美国、欧洲的森林史研究的大致情形吗?尤其是他们关于中国森林史的研究情况?
孟一衡:就我所知,美国和欧洲的森林史源自林业服务的分支。其中许多林业服务在最初从事新林地的调查工作,尤其是在殖民地和美国西部。这些机构为了试图控制他们的资源而调查森林,此时产生的文献就构成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早期森林史的基础。当然,这导致了它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印度有大量关于殖民地林业的文献,但是殖民地时代之前林业的文献很少。直到最近,关于中国的英语世界研究寥寥无几,大部分来自有中国旅行经历的美国林业专家,比如罗德民(Walter Lowdermilk)斯坦利·D.理查德森(Stanley D. Richardson)。这种情况随着伊懋可发生了改变,如今的年轻学者对中国林业有了更大的兴趣。
大象的退却
作者:[英]伊懋可 著 梅雪芹 毛利霞 王玉山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4
肖峰:你在书里关于中国人工造林的研究对伊懋可《大象的退却》形成了挑战和补充,在中文版序也提到在使用“early modern”术语时有与欧洲林业史研究者对话的意味。弥补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森林史研究的主流叙事的不足,是不是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孟一衡:在欧洲学术界,“早期近代”(early modern)是人们为了理解预演现代,但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期而发展出的框架。欧洲历史学家使用不同的事件作为早期近代的起点——1453年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开始前往美洲的航海。他们通常以法国大革命(1789年)作为“早期近代”的结束。不过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这些时刻都无足轻重。另一方面,我希望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能来读我的书,用“宋元明时期”指称本书描写的历史时段对他们没什么意义。这是一个问题。为了与欧洲历史学家对话,我是不是要将中国的“早期近代”起点定位在跟欧洲一样的时间——大约1450年或1500年?但是在我的书描写的历史时段,这个时间只是中点。或许我应该从中国自身的“早期近代”发端开始?在森林史上,12世纪中国的一些发展看起来很像16世纪起步的欧洲林业。我希望挑战欧洲历史学家,激起他们的回应,所以我将本书描写的历史时段称为“早期近代”。
肖峰:中国有林业历史研究的悠久传统。比如本书的译者张连伟、李莉、李飞、郎洁团队,他们来自素以林业史著称的北京林业大学;为本书中文版提供外审的文榕生先生,延续了其父文焕然先生的研究,他们是历史地理领域从事森林变迁研究的代表;你在著作里还提到了清水江文书,张应强先生的《木材的流动》是对该文献研究的代表作,他和他的同仁还共同推出了“清水江研究丛书”。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参考了中国的哪些研究成果,中国的林业史研究给你有哪些启发?
孟一衡: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中国关于森林的地方历史研究感到相当震惊,包括张应强对清水江地区的研究、陈柯云等学者对徽州的研究。自《杉木与帝国》英文版问世以来,我又发现了更多这样的研究,我多么希望之前就有参考它们!尤其是杜正贞与郑振满最近的文章。我也受到历史地理方法的启发,尤其是将历史数据运用在地理框架内,中国的学者比大部分美国机构的学者都更加看重这套方法。从另外的角度而言,我也觉得中国历史悠久的制度史研究很鼓舞人心。这可能从杜佑就开始了,在现代历史学家当中,我从梁方仲那里学到的最多。
木材的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作者:张应强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2
肖峰:以张连伟教授为代表的译者团队在译者后记中提到,北京林业大学的森林史研究侧重于史料搜集和文献整理,理论研究有所不足。这可能侧面反映了中国林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你是否认为,中国的森林史研究还需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你也提到,欧洲的林业史研究者会按照他们的理念来看待中国的森林历史,中国的森林史研究是否急需在国际学术界有更多话语权?
孟一衡:中国研究者自然会比国外学者更加关注收集历史资料,毕竟,北京林业大学和其他中国机构的学者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史料。没有他们的工作,国外学者要利用这些史料会经历更加艰难的时间。不过,我确实希望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之间可以有更多会面。即便我并不研究德国或英国历史,我也通过阅读关于这些地方的著作了解到许多。最近,我编辑了一部关于东亚森林史的论文集,这本文集揭示了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相似点(以及差异)。我认为这样的交流只会加强我们对森林史的理解,尤其是通过提出我们在其他情形下想不到的问题的方式。
肖峰:19至20世纪的中国一度经历了森林滥伐。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森林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数据表明,在1949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大约8.6%,而根据自然资源部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覆盖率已经达到24.02%。这种情况是我们乐见的。这样的现实情形与你在书中所写的,中国宋元明时期通过人工造林实现了森林的持续发展,似乎是前后呼应的。你在书的结论部分提到,中国还没有走出宋朝开启的森林时代,但是对此没有更多地解释。能展开讲一讲吗?你是否认为如今中国的森林发展延续了宋朝以来的某些特征和做法?

《杉木与帝国》内页
孟一衡:说到这一点,我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在人工造林方面依旧是非常独立的——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如此迅速地提高,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坦率地说,我认为外国人会很轻易地批评中国近期造林项目的缺点。当然,问题是存在的,不过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达到覆盖率接近四分之一的成就,确实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突出意义。尽管如此,我认为造林的历史确实需要人们更多地了解——既包括成就,也包括缺陷。有一种观点不时存在,认为随着煤、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如今是太阳能与风能,我们已经退出了森林的时代。然而,我们依旧非常依赖森林,从森林获得燃料和建筑材料,像气候稳定这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动物栖息地,甚至是娱乐。如果我们视森林为与人类社会不相干的某种东西,那是错误的,就像视森林为供我们随心所欲来消费的“自然资源”一样错误。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我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肖峰:《杉木与帝国》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看到有多位学者发表了书评。尤其是张萌,《杉木与帝国》引用了她的博士论文(也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上海光启书局出版)。她的书评认为,你将1750年作为中国林业转折点的看法值得商榷(《杉木与帝国》认为中国南方森林在1750年具有的延续性在此之后经历了转变,有序的森林体系开始崩坏)。因为1750—1900年其实与此前的历史时期更加相似,种植林业体系并没有在19世纪停止发生作用,或经历剧烈的变化,她认为真正的转折点要延后到20世纪30—50年代。想知道你对此有何回应?
孟一衡:我对张萌的观点既同意也不同意。一方面,宋元明时期发展出的机制大部分持续到了清朝,甚至20世纪初期——有某些显著的变化。直到20世纪30至50年代,土地系统才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方面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从环境的视角来看,我认为1750—180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之前,造林是为了满足木材的需要,减弱了滥伐造成的影响。在那之后,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开始灾难性地下降,不仅在造林的边缘地带,还在造林的核心地区,这导致了19世纪范围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在城市里可能觉察不到木材供应的这些变化,但是在种植森林的地方是可以的。
《人工林:东亚历史上的人与林地》(The Cultivated Forest: People and Woodlands in Asian History)英文版
肖峰:《杉木与帝国》源自你的博士论文,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有正在写或计划要写的书吗?
孟一衡:《杉木与帝国》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写作视角。我希望在森林是怎样被政府管理的这方面了解更多。如今我正在研究受到宗族组织保护的树木和森林,尤其关注在坟墓与宗庙附近种植的树木。除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我还与一些研究风水林的地理学者、人类学家合作。我也与一位对造船感兴趣的毕业生一起做了一点工作,这为《杉木与帝国》提供了一些材料。这是一项有趣的项目,因为我从中接触了西班牙、波兰、印度及其他地方进行造船与林业研究的历史学家。最后,我与一些研究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的同行合作编写了一本关于森林史的论文集,名为《人工林:东亚历史上的人与林地》(The Cultivated Forest: People and Woodlands in Asian History),将在今年12月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深度阅读
从蔡京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中国发生了一场贯穿宋元明的“森林革命”。千万根巨木,不仅营造出繁荣的木材市场,也缔造了东方海军神话。现代林业制度,原来起源于中国而不是西方?帝国兴衰与森林进退相生相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在学者孟一衡推出的《杉木与帝国》一书中,他回溯了中国古代如何充分利用木材兴建房屋和船只,又是如何实行大造林及森林管理,以实现森林环境的动态平衡,这对于今天的生态自然依然有着借鉴与反思意义。
回到明清之际皇家宫殿的兴建初期,巨型木材的短缺改变了建筑思考用其他艺术去弥补其华丽形象,森林滥伐和土地经济作物的更替在研究者看来,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影响,“土地稀缺、人口压力和生态退化相互关联,引发了高地耕种者和低地种植者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是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长期危机的关键因素。”
文/孟一衡
1533年,一位名叫龚辉的中层官员,基于他在明朝西南边疆督木的经历,出版了《西槎汇草》。在这本引人注目的书里,龚辉描绘了明朝伐木工在艰难的地形中砍伐和运输大木的创举,包括使用滑道、“飞桥”和大型绞盘将原木拖上斜坡。他同时揭示了山区的巨大危险,包括瘴气、普遍的饥饿以及遭遇部落和野兽的袭击。但是为什么明朝官员会首选在如此遥远而危险的边疆地区采木呢?正如本章所探讨的,西南边疆是明朝官员督木的仅有地点之一。在其他地方,私有人工林和木材市场是更有效的木材来源。但是西南部的深谷生长着当时仅存的足以用来进行皇宫营建的大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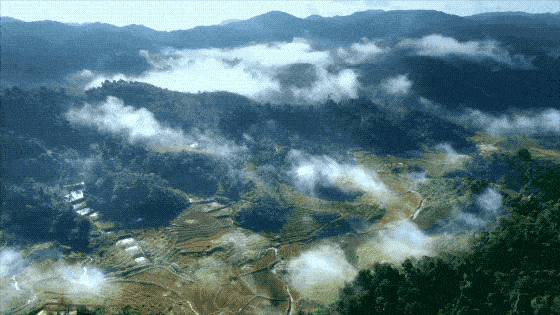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如果说造船业是引领欧洲帝国扩大森林资源的主要推动力,那么在中国,采木前沿最大的压力来自宏大的建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背景之间物质和文化的不同。中国南方的人工林生产的木材足以供应水军。但是不像欧洲宏大的建筑通常取材于石头,中国的皇家建筑几乎完全依赖于大木。在东亚的古典建筑中,建筑的全部上层都是建立在梁和柱的架构上,这种建筑风格实际上非常倚重它的结构木材。因为木材构件决定了每座建筑的基本尺寸,巨大的建筑需要巨大的柱子,而巨大的柱子需要巨大的木材。为造船厂提供木材的人工林扩张是以原始林的减少为代价的,原始林生长着大到足以建造宫殿的树木。矛盾的是,这意味着同样的趋势,一方面对通用林业采取自由放任的方式,另一方面要求国家采用更直接的手段为皇宫获取木材。正是北京宫殿的营建和反复的重建,导致在中国南方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皇木采办,这些工程最终导致长江流域原始林的衰减。
中国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皇家建筑的木材来源地,但明初在该地区的采木工程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之一。在1406—1421年间,永乐皇帝将北京建成了一个规模非凡的帝国首都。据估计,工部从全国各地招募了100万名劳力来修建宫殿。同样,在长江上游的三峡地区,官员命令几十万伐木工砍伐巨大的树木并把它们拖曳到水路。国家征用了成千上万的其他劳动力,让他们沿着艰难的路线随长江顺流而下,沿着大运河上行至北京。这15年的努力代表了明朝指令经济的顶峰。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明朝的皇帝除了从汉族内部派遣伐木队外,还向西南的土司们索要木材。在征服这个地区的过程中,元朝曾把非汉族部落编入土司。这些部落通过他们的世袭统治者上交贡品,而不是通过常规的税收。明朝沿袭并修改了这一制度,授予部落首领名义上的官阶和王权,并规范了贡品和宗主权的形式。在长江上游地区,贡品通常包括巨大的宫廷级杉木和楠木。这创造了一种颇为奇特的象征性物资交换:明朝送出了纺织品,土司穿着这些丝织品来显示他们的品阶;土司送出了巨大的木材,明朝皇帝用这些木材来营建他们的权力大厦。通过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和朝贡索取,永乐宫殿树立了一个未来皇帝难以企及的标准。尽管没有文献保存下来完整的采木计划,但直至1441年,也就是最早的宫殿完成后的20年,仍有38万根木材被保存在仓库里。这个惊人的数字表明,在永乐皇帝的指令下,数以百万计的树木被砍伐。后来,当庙宇和宫殿需要修复时,官员们努力寻找足够大小和质量的木材来代替大量的原木;但最好最易得到的树木已经被采伐了。同样重要的是,后来的朝廷根本无法像永乐皇帝那样大规模地驱使徭役。

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最终,一系列火灾焚毁了皇宫中最重要的建筑,明朝被迫恢复了边远地区采伐。但是,当16世纪的皇帝下令征用新的木材时,他们的官员竭力服务于工程团队,但任务变得更加艰难,他们被迫向更深的山区寻找有价值的木材。土司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并多次为争夺几片残存的原始林而开战。在成本不断增长和木材稀缺的情况下,官方采木在16世纪后期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虽然清初的皇帝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恢复了皇木采办,但他们鲜有成功。到了1700年,就连四川和贵州深谷中可用的大木都已采伐殆尽。正如金田所指,原始林的枯竭甚至迫使皇家建筑发生了变化,建筑变得更加华丽,以此弥补木材构件的规模和自然美的损失。这些皇木采办标志着长江沿岸天然林地的衰减。虽然人们可以增加小商品木材的供应,但他们却无法加速大树的生长以满足宫殿架构的需求。

梁方仲遗稿(全八册)
作者:梁方仲 著 梁承邺 李龙潜 黄启臣 刘志伟 整理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和东方的首都一直从西南输入巨大的木材。汉朝政府曾在四川设立了专门的木官。唐朝专门开凿了一条运河,从西南运送木材和竹子。宋朝也不例外,在11世纪的木材危机期间,四川北部森林遭到滥伐。在那个世纪后期,朝廷接受了从西南部落进贡的木材。在这1000年中,西南木政强化了低地汉族商人和山地非汉族伐木工之间的族群和生态壁垒。在公元5、6世纪的中国南方,流行着汉族商人和木客之间的交易。木客是神秘的群体,他们能够“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然后“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正式化。例如,在1196年,南宋法律禁止汉人进入四川东南部的山区砍伐木材,指示他们“须候蛮人赍带板木出江,方得就叙州溉下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生态伐木的边疆发生了变化,但基本的交换模式惊人地持久。明朝的资料表明,到15世纪,“[汉]斧斤无得而入”长江上游支流丰富的森林。在明朝的头几十年,伐木业继续沿袭早期的方式。有几次,朝廷派遣官员到非汉族部落督采皇木,用于南京的宫殿营建。根据云南东北部的一处碑刻记载,1375年,宜宾县的一位官员带领180名当地劳工砍伐了140根香楠木用于宫殿营建。这些木材可能用于1378年开始的内廷大规模扩建。朝廷将云南东北部的另一个地方指定为官林,并将其最好的树木标上“皇木”的标记,以保留供宫廷使用。然而,朱元璋很快就削减了建设项目,作为他广泛推动自给自足经济的一部分。1379年,他甚至关闭了南京的主要木材场,显然是打算完全停止营建。1390年,朱元璋的第十一个儿子朱椿掌控了四川的木材市场,并把朝贡要求降低到名义上的数额。1393年南京龙江关开放后,朝廷规定,所有未来的建筑项目都应完全依赖关税木材,工部不应进行任何不必要的伐木。尽管名义上试图限制这种行为,然而部落伐木仍在继续。在1387年,珉德,当时的马湖知府,向南京运送了一批香楠木144材。朱椿还用四川的原木在成都建造了自己的府邸。尽管朱元璋试图减少国家的足迹,但明初的政权还是延续了向西南峡谷索取木材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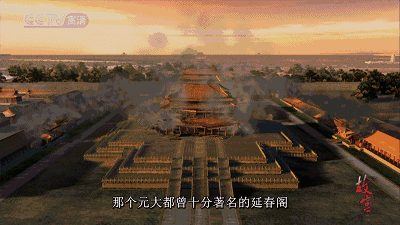
纪录纪录片《故宫》
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经过一番争斗,权力移交到了永乐皇帝,永乐皇帝于1403年将朝廷迁到他在北京的府邸,并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以新的规模将北京扩展为帝国首都。北京还是元大都时的大部分建筑在14世纪末期坍塌毁坏。在1403年至1420年间,永乐皇帝重建并扩充了北京的城墙和宫殿。为了他的宏大建筑,永乐皇帝像他的父亲、兄长,甚至更早的统治者那样,转向了同一片森林:长江上游的巨杉和楠木。1406年,为了准备第一拨建筑工程,他从工部派了一批高级官员去四川、江西、湖广、浙江和山西寻找最大、最美的树木。虽然朝廷最终从这些地方都获取了木材,但超自然的影响显示四川是帝国伐木的主要地点。宋礼报告,在他寻访期间的一个晚上,几棵大树掉进了河里,自行顺流而下。皇帝认为这是神灵的昭示,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神木山。无论是作为历史先例的延续,还是通过神灵的干预,这一地区成为永乐时期最密集的木材采伐中心。在营建北京城的过程中,宋礼曾至少四次到四川寻访。朝廷还派御史顾佐进行高层监管,而宦官谢安在现场待了20年。即使找到了巨木,伐木工程的劳力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官员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不惜重金派遣汉人劳工,还是冒着反抗的风险使用当地非汉族人员。散落在该地区的碑刻提供了这项工程的信息片段。位于四川南部的宜宾县的一处碑文记载了1406年初的一次行动:
八佰人夫到此间,
山溪崛峻路艰难。
官肯用心我用力,
四佰木植早早完。
西槎汇草
作者:龚辉 著
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1
这首诗文表明,这些劳动者可能是从中国内地来到这里。在其他情况下,很明显,劳动力来自非汉族人群。1406年的另一块碑文记载了附近的一个由夷人佰长监督的伐木项目,他让他的110名下属把木头拖运到河里。另一块来自四川东北部的石碑也记录了1406年秋天收到的伐木命令。在此事例中,一个总甲长被派去监管十筏(一筏约80根)木材的采伐和运输,显然是通过使用乡村的劳动力。这些碑文零散地记录了宫殿营建所导致的大规模人力动员,它可能需要在整个西部和西南部进行数以千计的类似伐木项目。长江上游峡谷的伐木只是将木材运往首都的工作的开始。甚至在工作队把一根根木头从山涧里漂出来,绑成木筏后,这些木头还得行进数千公里才能到达北京。为了把木材运到首都,沿河各县指定了专门的“皇木解户”——以漂筏运木为业,替代其他徭役。到达首都后,工人将木材堆放在专门指定的神木厂,这是1407年在通州建立的较大转运中心的一部分。至今通州的一个公交站仍被命名为皇木厂,保留着这一历史遗迹。
几年内,奏报中开始传递伐木工人所经历的种种困难。1413年,朝廷严厉批评了督办山西采木的官员不恤其军民之苦。户部奏报,伐木群体被课以重税,任何额外的要求都会使他们出售田产,卖妻鬻子。1414年,四川部落地区的采木军夫奏报缺粮。1416年,另一群采木军夫受到山西道教信徒的攻击。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些采木工程还是一直持续到1424年永乐皇帝去世。
………………………………………………
孟一衡,本名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出生于美国费城,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中国史。曾任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研究员、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访问学者。
原标题:《M.米勒:在森林史上,12世纪中国的一些发展看起来很像16世纪起步的欧洲林业 | 纯粹历史》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