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公园等候天鹅的人
“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雅克·贝汉在纪录片《鸟的迁徙》中这样说道。
这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不止发生在候鸟与大自然之间。

《鸟的迁徙》
北京南海子公园,几年前摄影师潘清泉在这里救助了一只受伤的天鹅,这只天鹅脖子上套着一个写有“F67”的环志(鸟类环志是世界上用来研究候鸟迁徙动态及其规律的一种重要手段)。不成想与它结下的这段缘分,让南海子后来成为了北归天鹅的驿站。
候鸟似乎有记忆,年复一年翩跹而至。起码“F67”确有记忆。
第二年,老潘又等来了“F67”;前一年它还是形单影只,这次居然带着伴侣来到这里。第三年,一家五口又准时抵达;第四年一下子带来了48只;第五年86只……

南海子公园的天鹅
“我的梦想,”在天鹅日记里,老潘豪气地写下,“就是打造北京南海子天鹅湖,打造一个北京的天鹅湖。在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一边是呦呦鹿鸣,一边是曲颈天歌。”
到底该不该投喂天鹅,如何给它们一个更适宜的生态,人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边界止于哪......这些都成为问题。老潘的“天鹅湖梦”会实现吗?他又是否还在等待着下一年天鹅的到来?
下文摘选自青年作家、知名媒体人司徒格子新书《人间一格》,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1
去年五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满下巴胡子的老潘。北京亦庄南海子公园里,他支着小电动车站在阳光下,张嘴冲我一笑,伸出厚厚的大手。
“就叫我潘老师吧!”他腼腆地说,“咱俩不论辈分……”
我握住他的手,跟着应了句“潘老师”。头天夜里,大舅告诉我,眼前这个魁梧的中年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老姥爷”,比我已然仙逝的姥爷还要高一辈。姥爷整个村的人都姓潘,族谱、辈分纵横分明,状若棋盘。作为山东人,对这一点我已十分熟悉。从小学起便有同班同学是我叔辈,十五岁那年的夏日夜晚,一个同村小姑娘甚至清脆地喊我一声“小爷爷”。如今,在故乡千里之外,这位比我年长十几岁的老姥爷站在眼前。他的一切都让我熟悉,咬字不清的“dong”和“deng”,念不出“s”开头的音,浓重的大舌头。显然,他比我离开故乡还晚,口音更重。
在此之前,我早知道他是一位摄影师,而且颇具想法。疫情开始之后,他找到一片早春的爬山虎,每个星期在上面挂一副口罩,伴随着爬山虎由黄变绿,口罩位置越来越高,但在夏日来临之际,爬山虎日渐成为深绿色,口罩位置越来越低。最终数十张照片叠加出的图片上,爬山虎从左到右由黄变绿,上面是一条口罩组成的抛物线,这成为一份不可多得的比喻。长久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照片得奖,广为流传。
我来的这天,正赶上他主办的天鹅摄影展。南海子公园里两行树荫下,摆满了展板。他从第一幅开始讲起,逐行念出展板上的字。我无心听讲,目光停在照片上。每一幅照片都以天鹅为主题,一只天鹅张开双翅,一对天鹅脖颈比出爱心,一家天鹅嬉水玩闹,一群天鹅在空中滑翔……日光里、月光下、黄沙中、雾霾天,这个优雅的生灵摆出让人窒息的美。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北京还会有一群天鹅低空盘旋。


老潘拍下无数照片,又从影友那里征集佳作,精心做了这场展览。眼下是五月底,公园里并没有天鹅,他索性带我们去看麋鹿。
南海子公园在亦庄,明清两代都是皇家园林,满清入关后,始终担忧旗人子弟失去游牧民族血性,设了几个围猎场所,被选中的南海子便更名南苑。麋鹿就是《封神榜》中的“四不像”,从元代开始成为皇家猎苑饲养的猎物,清代被大量圈养在南苑,等待皇室箭弩临幸。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比利·大卫神父(历史充满不知是否有意为之的巧合,他是第一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发现了这个新奇的物种,将其带回欧洲。在日常用语中,英语世界甚至以此公命名麋鹿(Père David’s deer)。

南海子公园的麋鹿
1894年,永定河一场洪水冲垮了南苑围墙,麋鹿四散而去,被食不果腹的灾民吃掉大半。六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大陆残存的最后一批麋鹿被赶尽杀绝,自此这个本土物种消亡于故土。也许比利·大卫为同名之鹿最大的贡献,便是吸引来一批西方人将麋鹿带去欧洲,不经意间保留了火种。要到整整八十五年后,1985年,英国一位公爵后裔向北京捐献了二十二头麋鹿,它们才在故土重生。
作为最后的栖息地,南海子设了麋鹿苑。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一课就是,历史的教训不能重复上演,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南海子麋鹿成功繁殖后,迅速被送到江苏、湖北等地,在东海之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那也是祖先曾生活的地方。麋鹿保护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到2021年9月,中国境内已经有上万头麋鹿。
老潘讲述这些故事时,我们正走进一个挂满鹿角的房间。
每年十一、十二月,雄性麋鹿鹿角脱落。脱落亦是一次新生,不到一周,全新的、毛茸茸的鹿角便能长出几厘米。他找到一头做了特殊标记的雄鹿,从十一月到来年四月,几乎每周在同一角度拍张照片,记录它从鹿角脱落到再现雄风。老潘管这个叫“时空交错摄影法”。他的摄影理念不管是什么,其中必定含有无穷无尽的耐心。









▲每年冬至前后,公鹿会脱掉旧的鹿角,元旦前后开始长出新的鹿角,为新一年的鹿王争霸赛做准备。来源:潘清泉艺术工作室
我们从房间走向麋鹿苑,途中十几只孔雀拦路开屏,苍鹭晃悠悠飞过天空。时不时地,就能看到有人试图接近孔雀或是其他动物。
老潘不断大吼着让游人远离,他粗犷的外表和高亢的嗓门总是奏效。
麋鹿被围在一片面积广大的草地上,场内稀稀疏疏种了几棵树,一条大河穿梭其中。

南海子公园麋鹿苑
时值午后,一群大鸟落在麋鹿苑中,与鹿群拉开些距离,啄食地上的残渣。我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麋鹿群,它们分成族群,在鹿王周围聚成一簇。从身材和脸蛋看,与牛犊差不多,但头顶的巨大鹿角,却有不容侵犯的威严。到了六月,雄性麋鹿会用新长出来的角不厌其烦地大战,最终胜利者将与一群雌鹿组建大家族,失败者离群索居。在丛林里,赢者通吃。
麋鹿苑之外,一代代保护者看向麋鹿时的心情,却绝非弱肉强食,而是患得患失。麋鹿经历过饥不择食的目光、残杀的目光和猎奇的目光,终于迎来人类友善的目光。将麋鹿重新引回中国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动物园就曾一试,但如此威武的族群根本适应不了促狭的圈舍。针对其他动物的重新引进,野马、高鼻羚羊等,也大多以失败告终。
毁灭一个种群容易,重新恢复极为艰难。在复杂的物竞天择中,人类自我分裂,其中一部分肆无忌惮地毁灭其他物种,另一部分小心翼翼捡起地上的碎片,试图还原出哪怕一个完整的瓷瓶。麋鹿便是那个奇迹般的瓷瓶。它在南海子重生至今近四十年时间,是几代生态保护者共同造就的壮举。

冬天麋鹿的角脱落
2
老潘在2000年来到亦庄,此前他在我家乡的县文化馆工作,又来北京进修,最终落脚在这个崭新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他记忆中,“整个亦庄当时就一栋楼”。他拿起相机,从第一栋楼开始拍摄,用二十多年记录了一座新城几乎从零开始的全过程(这个男人最不缺的就是耐心)。到2021年,亦庄GDP达到近两千五百亿,成为一座繁华的新城。老潘把家安在南海子公园附近,俯瞰麋鹿苑。
2004年,老潘遇上郭耕,他曾是北京濒危动物中心第一位饲养员,如今来这里保护麋鹿。从郭耕这里,老潘学到了系统的生态保护知识,“慢慢地上了这个道”。随后不久,他又与另一位专业人士钟震宇相识。在几代专业人士努力下,麋鹿苑没有建成麋鹿动物园,而是成为大型湿地生态。其中光鹿就有麋鹿、马鹿、梅花鹿、黇鹿、河麂等,鸟类不可计数。曾经的驾校练车场、砖厂、水泥厂、垃圾存放场、废品收购站荡然无存。即便亦庄平地起了无数高楼,成为北京最贵的新城,也未染指这片净土。
他带我们走出麋鹿苑,沿着长河散步。穿过一片树林,眼前数万只飞鸟穿梭在水面、树枝和天空中。只有野鸭安分地在水面划动。他挨个指出名号,苍鹭、夜鹭、池鹭、白鹭、鸳鸯、鸿雁、黑天鹅……对每种鸟类的习性如数家珍。
春夏秋冬四季,鸟类以不同的样貌示人。我来北京十年有余,还未见识过这样一片湿地。失而复得的麋鹿,以自身对生态的苛刻要求,在北京城里无心插柳柳成荫。
3
老潘对天鹅的爱,来自一位颇为不凡的母亲。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自己如何爱上天鹅——
上滑查看更多 ↑
我八九岁的时候啊,家里养着一大群鹅,它们每天生的蛋,是我们家的经济补贴与营养补贴。所以我娘特别地上心,要求我和我二姐每天早上轮流把它们赶到家前面的河里面。
通往河面的是一条斜坡的小道,两边是五六米高的岸堤,有一天我想睡个懒觉,被我娘揪了起来去赶鹅,心情极其郁闷,为啥不让我二姐早起去赶,而让我早起去赶呢?然后揉着眼睛半穿着衣服,趿拉着鞋我就把鹅赶出了院子,心里很是生气,咒骂着这群该死的东西,都怪你们,害得我都睡不了懒觉,真想用手中的竹竿打死它们,可我又不敢真的去打,万一打死了,我的日子也好过不了。
走过下河的斜坡快到水面,看到左右两边五六米高的岸堤时,我一下犯起坏来,我何不把它们从岸堤上赶下去,反正它们会飞,摔死了也不赖我,我可以说是它们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这样也正好发泄发泄我心中的怒气。说干就干,我赶紧跑到鹅的前面把鹅往回赶,它们蒙圈了,什么情况?咋刚出来又要往回赶呢?它们左躲右闪不想回走,但经不住我的大长竹竿纠正路线,好不容易到了岸堤上,它们一个个伸着脖子往岸堤下面看了看,又开始左躲右闪地想逃离,没有一个敢往下飞的。我用竹竿左右地驱赶着它们不准逃跑,突然在后面大喝一声,同时用力一挥竹竿,后面的吓得拼命地往前挤,前面的被后面的一下子就给挤得不下去都不行了。身强力壮的使劲向前扑腾着翅膀飞了出去,大概飞出去二三十米,那姿态优美至极,把我一下子就给看傻了;老弱病残的可惨了,翻滚着身子跌跌撞撞地扑扇着翅膀掉到了下面,还好没看到受什么伤,还能马上向前跑去跟大部队聚拢在一起。我还沉浸在刚才大鹅展翅飞舞的场景里,郁闷的心情早已经拋到了九霄云外。
我没有看够,我想下到河里把它们赶回来再飞一遍,可这次不听指挥了,河床宽广,我一下去它们就分散乱跑,根本聚拢不到一起了,半天也没赶回来,只好作罢,我盼望着明天再赶一次。第二天一早,不用俺娘催我起床,我一早就穿好了衣服,主动要求去赶鹅,不要二姐去赶,让她多睡会,我娘还夸我懂事了。我把鹅赶出门口,快要到斜坡时鹅突然疯了一样地顺着斜坡向下跑,我想跑到前面阻挡都追不上了,一眨眼就跑到河里去了,气得我在后面直跺脚,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们。第三天我还是主动早起床去赶鹅,这次我走在鹅的前面,不让它们提前跑了,哪一个想提前跑我的竹竿就给它打回去,就这样我又把它们赶到岸堤上……
好景不长,我娘发现最近鹅生的蛋好多都是软皮蛋,跟我爹说可能缺钙了,找些石灰和蛋皮压碎了放鹅舍圈里。我积极赶鹅的态度也引起了我娘的注意,有一天早上,她远远地看着我,发现了我的行为,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而是问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说我就是想看它们展翅飞翔的那一瞬间,特别的美。我娘说咱们养的是家鹅,是生蛋的,体形特别肥大,很难飞起来,你这样做会让它们受伤,你的学费还需要用它们的蛋来换,你觉得特别美的瞬间是建立在它们的痛苦之上,即使再美也是丑陋的。我一下子有些无地自容,跟我娘说我错了,我再也不这样做了。
我娘说听人家说新疆有个天鹅湖,你好好学习,长大了有本事了去天鹅湖看天鹅的飞翔,苏联有部《天鹅湖》电影,苏联应该也有个天鹅湖,但是在国外,没有本事可去不了。从此去天鹅湖看天鹅飞翔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
2016年,梦想从天而降。一只从内蒙古乌梁素海飞来的疣鼻天鹅落在了没有完工的南海子公园二期,戴着“F67”颈标和太阳能充电定位器。
显然,这是一只被用来研究的天鹅。此时它体力不足,迫降在湖面上,又被渔网缠住。老潘试图撕开渔网,绝望的天鹅用嘴攻击他,不让近身。老潘只好用棍子挑开网,天鹅重获自由,却发现根本飞不起来。

天鹅F67
彼时已年届不惑的老潘拍过很多次天鹅,熟悉此物秉性。他拿来一袋袋花生和玉米,放在天鹅附近。郭耕建议不要投喂,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需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觅食后它会自行飞走,但投喂却可能让它不惧怕人类(从历史看,一靠近野生动物,人类劣迹斑斑)。老潘于心不忍,在犹豫中选择继续喂食。就这样整整三十九天后,北京湖面结冰之际,“F67”强行起飞。三天后,念鸟心切的老潘,终于在多方打探后等来了影友的消息,“F67”安全抵达山东威海荣成市烟墩角的海湾。
烟墩角堪称老潘梦中的天鹅湖。一九九五年,这里飞来八只天鹅。当地几位农民选择用玉米粒投食(我们山东人面对禽鸟,似乎除了喂花生就是喂玉米,浑然不顾鸟类是否还有其他食欲)。一年年过去,农民们投食也看护天鹅,最终烟墩角居然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迎来一万多只天鹅过冬。天鹅们似乎有记忆,年复一年翩跹而至。起码“F67”的确有记忆。
2017年,“F67”带来了它的伴侣;
2018年,“F67”带来了自己一家人;
2019年,“F67”与其他三十三只天鹅落在南海子公园的湖面上,停留了三天时间;……
2020年、2021年、2022年,每一年老潘都拍到了“F67”的身影。老潘甚至能分出它的队伍,比如,2022年它带来了十二只疣鼻天鹅和五只大天鹅。这只被用作研究的天鹅,向着一个痴情的人年复一年地飞。短短七年过去,在南海子过冬或是过春天的天鹅,年年都有两百多只,今年甚至到了四百多只。

显然,在另一个山东农民的努力下,北京有了自己的“烟墩角”。
4
三月中旬的一个雨天,我来到南海子公园。停好车后,沿着公园步道四处走了走。山桃正在打开花苞,柳条也已暗中变绿。人们带着风筝、零食和孩子进来,享受北京短暂的春光。
湖边只有一顶蓝帐篷,老潘穿着厚实的绿色羽绒服,挺立在帐篷前的三脚架边上。这是一个高台,三层台阶下面是湖边护栏。一百多支长长的镜头对准湖面,他站在最高处,像一头刚打赢的鹿王。早已晒红的脸颊正在脱皮。他大声对我说,已经在这蹲守了整整两周,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寸步不离,早晚各撒下二十斤玉米。
湖中央有摄人心魄的美。远远望去,在一百多只大雁和数之不清的水鸭中,天鹅傲然独立。即便见过很多次天鹅,我依然会为它修长、洁白的身姿震惊不已。除了钻进水中觅食的时候,天鹅每个动作都优雅至极。它扇扇翅膀,无数快门成片响起。雌雄天鹅双吻一碰,便用身体比出了爱心。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天鹅组成小规模队伍,从湖面起飞盘旋。但是这个下午,天鹅耐住性子,始终不想起飞。倒是大雁忍不住三五成群飞了几圈。在四周挺立的楼房映衬下,城市水泥森林中有了难得的一抹灵动。
“这些大雁我成年养着,三百多只了,就是要给天鹅安全感,它们看到湖里有大雁,就知道这里能落。”老潘颇为得意。
说话间,冲突便爆发了。对岸有一对夫妻走到岸边,试图看清天鹅模样。我站在高台下,猝不及防地听到一声惊叫:“对岸的两口子,赶紧离开!赶紧离开!不要惊了天鹅!赶紧离开!对岸的两口子!……”
天鹅胆量的确很小。湖边风波过去后,它们忽然集中游向了湖心。我望向老潘,他望向天空,一只风筝正缓缓升高。
又是一声惊雷:“保安,保安,那边有人放风筝,马上去处理一下!保安,保安……”
很快,风筝降下。几个摄影爱好者来打招呼,显然都知道他就是“潘老师”。他们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退休后以摄影为乐。每天,老潘都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发布天鹅讯息,吸引人们前来。他想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天鹅保护这艘船上站满同行者。老人们退休前的身份让我有些惊讶,有人曾在亦庄开发前负责环境勘测,有人是很早的鸟类保护者,还有市政协委员,不一而足。每个人都想出点主意,甚至有人当场承诺向市政府写个提案。老潘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向人们讲述自己在做什么。
“前天我吸引来了五百多个单反大爷。那阵势,这整片都架满了!”
“最怕小孩放风筝。天鹅一看到风筝,以为是老鹰来了,能不怕吗?”
他正跟我闲聊,天空中一只黑色大鸟俯冲而至,双翼下各有块白斑。老鹰真的来了。老潘认出这是一只黑鸢,与天鹅一样,是国家二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于万军丛中抓了一条鱼后扬长而去,吓得天鹅飞向湖中心,与大雁伸长了脖子聚成一团。动物世界,全无公平。
一个老人兴奋地冲过来。“潘老师,我拍到天鹅飞翔了,真好看!”
老潘没好气地回了句:“你拍到的都是屁股吧?被吓飞的鸟只能离你而去。”
老人低头一看相机,讪讪打了几句圆场。
小插曲层出不穷。整个下午,老潘都在扯着嗓子劝告游人离开岸边,显然,任何警告标志或者警戒线,都挡不住人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几位单反大爷对我感慨,这里是北京难得的拍摄胜地。
“头两天颐和园出现了几只天鹅,您猜怎么着?人公园开着快艇全赶跑了。就怕天鹅把人给吸引去。”
单反大爷和围观的女士们,很快加入老潘的声讨队伍。看到天空升起风筝或是湖边有了人影,便有人自告奋勇冲上前去。最终,鹿王和他志同道合的种群,形成了绝对优势,即便不讲理的游客也不再辩驳。
到晚上六点,天鹅们在靠近老潘拍摄点的岸边集合。十分钟后,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四十七只天鹅排着整齐的队伍,迎着半个月亮冲向天际。

第二天,我又来到湖边。老潘无暇打招呼,身边已经围了十几个孩子和家长。有位家长与老潘相识,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队伍来请他上课。
“你家是哪儿的?”老潘问一位女士。
“重庆的。”
“那你如果从北京开车回重庆,中间要加油吗?去服务区吃饭吗?如果发现一个服务区免费加油、免费吃饭,而且干净、卫生,下次回家你还去吗?”
孩子们哄堂大笑。
老潘把南海子比作天鹅从山东半岛飞回西伯利亚的服务区,源自多年前郭耕向他提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投喂天鹅。这个问题当然永远有争议,老潘纠结良久,选择把电话打回山东,请教有三十五年天鹅保护经验的烟墩角人曲荣锦,他是当地最早的保护者之一,如今在当地开了家颇有名气的农家乐,招待全国各地的天鹅爱好者。
“会不会因为我的投喂影响到了天鹅的迁徙?”老潘问。
“不会!我们这儿当年最初八只,我们保护它们慢慢地变多,现在达到一万两千多只,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投喂它们就不迁徙了,只要到了第二年三月,它们必定要走,现在我们这儿走得还剩下不到两百只了,应该这几天也会走。其实天鹅的食量很大,我们投喂的不及它的食量的十分之一,但这种方式加强了天鹅与人之间的感情,它会永远记得这个地方的。”曲总说。
就这样,老潘坚定了信心,在南海子迎接从海边飞来或是飞去海边的天鹅。
天鹅课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群七八岁的孩子,眼中闪烁着光芒,一个又一个问题飞向老潘。他几乎无所不知。
“小天鹅脖子是灰色的,它爸爸妈妈是纯白的,爷爷奶奶脖子是黄的”;
“天鹅起飞、降落跟飞机一样,都需要一条跑道,所以它得在很大的水面上才会降落”;
“天鹅需要迎风起飞,迎风降落”“天鹅不会被冻死,它迁徙主要是为了找吃的”;
“癞蛤蟆能不能吃天鹅肉我不知道,但你吃了肯定要进监狱”;
“天鹅向北飞到西伯利亚是因为它们在那里出生,也几乎只能那里产卵孵化,比如疣鼻天鹅从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孵化的记录”……
人群中,一位家长高声问道:“西伯利亚在哪个国家?”
讲完天鹅,老潘开始讲凤头、鸿雁,以及眼前出现的其他一切鸟类。他把三脚架调低,将400.mm焦距的单反镜头当作望远镜,让孩子们排着队看湖中心的天鹅和其他鸟类。整个下午他都没办法按快门,围观的大人们也加入了队列。最终这变成一次积极昂扬的生态保护科普,老潘问:“我们以后遇见针对天鹅等鸟类的不文明行为,应不应该制止?”孩子们响亮地齐应:“应该!”
我身后,一位旁听良久的年轻女士轻声感慨:“突然感觉脑袋越小的动物越没有烦恼。”我看了看孩子们,又看向远方脑袋更小的天鹅。

5
在我们家乡,冬春两季有一望无际的麦田。记不清有多少次,我随母亲来到麦田时,惊起几百只大雁。它们鸣叫着飞向村西的岭,然后消失在天际。有时我甚至捡起土块扔进雁群,奋力冲向前方,逼迫它们更卖力地挥动翅膀。老潘有类似的记忆,这位老姥爷不过比我年长十岁有余。
我最早见到天鹅,是在村头一个小小的湖中。它似乎受了伤,静默在如镜面般的湖中心。所有孩童把湖围成一圈,看着这个美丽的生灵垂下脖颈。天黑之前,一个大人拿来将近一米高的花篓,在对岸另外一个大人的竹竿帮助下,扣住了这只天鹅。后来的故事便无从知晓了,但那年月穷,打一只野兔子都可以让全家改善生活。甚至这个片段,如果不是见到家乡人保护天鹅,可能也会在记忆中渐次消失。
记忆中存有更多的片段。经我之手,无数麻雀、仓鼠、蛇和青蛙遭了殃。想必老潘概莫能外。我们小时候,没有人提醒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也没有人在身边用惊雷般的嗓子守护天鹅、孔雀和大雁。有的只是日复一日耕作中,将自然世界中的一切拽入丛林法则。不过一代人之内,这个家乡人居然从随意伤害一切野生动物的乡村小子,变成了野生动物的铁杆侍卫。照我看,他镜头之下的沧海桑田,还没有心底里的巨变激烈。

潘清泉在雪地拍摄天鹅
即便在北京,老潘要面对的也不只是好奇的人群。有人下鸟夹子,有人试图用弹弓打天鹅,甚至一群野狗都打起了天鹅的主意。这群白色天使在不同的眼中各有千秋。老潘像一个行走的暴怒机器,年复一年,七年如一日,在天鹅来临的日子围着这片湖转圈,向每一个妄图不轨者发出雷霆一击。对这位摄影师来说,拍照不再重要,他每天吸引数百名摄影师前来,自己专心保护。
“我的梦想,”在天鹅日记里,老潘豪气地写道,“就是打造北京南海子天鹅湖,打造一个北京的天鹅湖。在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一边是呦呦鹿鸣,一边是曲颈天歌。”
我脑海中始终盘旋的却是另外一个画面,也在他的天鹅日记里。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六点,他来到天鹅湖畔,看到往日两百多只天鹅停留的湖面上,在陆续告别几批后,只剩下了南海子公园圈养多年的一只天鹅。一人一鸟相视无言。头天夜里,最后一批野生天鹅迎着风飞向了北方的家。他硕大的身躯跨上小电动车离开湖边,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一脸。
本文节选自
《人间一格》
作者:格子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2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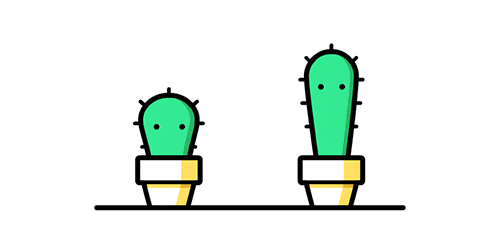
编辑 | Lithium
主编 | 魏冰心
封图 | © Marcin Ryczek;文中天鹅的配图均为潘清泉所摄
原标题:《在公园等候天鹅的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