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口述中国|北京⑧祁淑洪:八国联军进城,父亲一家险些殉死
【编者按】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主编的“口述历史系列”第二辑(《八旗子弟的世界》《城墙之外》《府门儿·宅门儿》《胡同里的姑奶奶》《生在城南》)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在总序中,定宜庄如此写道,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
定宜庄是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她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迄今已有20余年。2009年定宜庄出版了上、下两册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后来又主持北京出版集团的“北京口述历史”项目。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刊发“北京口述历史系列”部分内容。今天选摘的是北京旗人后代祁淑洪的口述。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在我做的所有访谈中,这是第一篇,也是我持续不断地为北京人所做的将近20年访谈的开端。正因为祁女士的讲述如此生动,如此精彩,才给了我日后投入这项工作的兴趣和信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我日后的访谈方向,提供了某种启示。
访谈者按:
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她自述只上过几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以及其他京味作家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异同,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访谈中,她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祁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所说,祁女士的母亲终因不堪此种差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祁女士母亲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儿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促膝谈心,洵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表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特附于此篇访谈之前。
祁淑洪(以下简称祁):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4岁。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儿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人)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风,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十五。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恳求)的工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访谈者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京城分成不同的占领区,东四以北由日军占领,东四南大街以东由俄军占领,以西由意大利军队占领。皇城东北由德军占领,皇城东部由日军占领,皇城东南由英军占领,崇内大街以西东长安街以南由德军占领。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所以才有“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之说。而据祁女士说,他们原先的住址是在北池子,即东城区的南起东华门大街、北至五四大街的北池子大街,正处于皇城东部,是由日军占领之处,与其二大爷“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的说法恰恰相合。)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厕所),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得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得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听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总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得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访谈者注: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次日慈禧太后死,年74岁。二人相差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天。]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戴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
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访谈者注:铁梅为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角色。)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访谈者注: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即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3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工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工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没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捯饬(打扮)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

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访谈者注:《坐宫》是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折。剧中辽朝的铁镜公主(即杨四郎之妻)是旗装打扮,梳的就是两把头。)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
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访谈者注:福字履是旧时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带云头的鞋。)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1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夫,您新禧。”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呆儿(访谈者注:卖呆儿,北京土语,即一个人站在街门口。),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
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

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访谈者注:指1924年“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之事。)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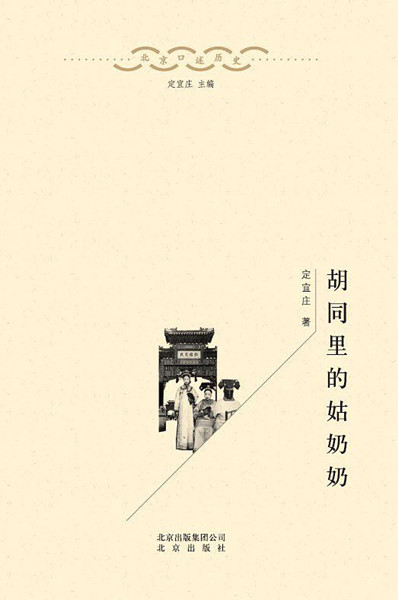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