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遇见动物的时刻

发表在《环境与行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之所以对荒野景观产生依恋,是因为大自然能够满足自主性、能动性和关联性等基本心理需求。那么,在野外遇见蛇的时刻呢?
美国西部长大的作家琼·狄迪恩,曾在她的纪录片《中心难再维系》中分享这样一个颇具哲学的理论:如果你把蛇放在你的视线里,蛇就不会咬你。
同样来自西部地区,亚利桑那州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克雷格·查尔兹有与蛇接触的真实经历,在他的描述中,遇见大自然奇幻和野生动物的时刻,像诗一样美。他的文字如氧气般治愈。
下文摘选自《遇见动物的时刻》,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谁都可能被响尾蛇咬到。在科罗拉多河的下游,一个响尾蛇很多的地区,作为向导和野外教练,我们都是潜在的目标。穿着溯溪短裤和凉鞋,我们背起设备,扯开防水衣,频繁地暴露着自己的皮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倒是希望被咬的是自己,只是为了让响尾蛇不挡道,并且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然而,被咬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在几千米以外河流上游工作的朋友。他在夜间踩到了一条响尾蛇,那时沙漠很温暖,唯一的光线来自周围群星间微蓝的弱光。他穿着溯溪凉鞋,半秒的警告后,一条响尾蛇将指关节长的毒牙和大概40毫克毒液刺进他的脚背。毒液迅速流入他的细胞,立即开始从里向外侵蚀脚和腿。几分钟内,随着心跳将毒素带至全身,他的血管开始出现故障。那个时候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一辆露营车停在犹他州的鲍威尔湖边 © Joshua Lott
我只听到一只船在夜晚的河上独自驶过。消息在营地的帐篷和锅碗瓢盆间沸沸扬扬地传开,一支救援队迅速组成,我的朋友被迅速送到下游的接应处。在去最近医院的五小时路程中,我站着听那静谧而蜿蜒的河流。眺望着夜的穹隆,不知道在那艘离别的船上正发生着什么。
和其他向导一样,我总是在户外。我在沙漠中休假,将前一次漂流旅行剩下的水和食物带到这里,在高耸的仙人掌下搭起帐篷。有几次我差点踩上响尾蛇,脚下一有咝咝的声响身体便会立即跳开,还有几次差点坐到响尾蛇身上。
另一次,在一个凉爽的清晨我尿在了一条响尾蛇上,当我注意到它盘在我脚边尘土中那带有保护色的身体时,已经太晚了。没有一条蛇曾震动空气警告我离开。似乎响尾蛇和我之间建立起了心照不宣的休战协定。我从未用石头砸过它们的脑袋,相应地,它们也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咬我。有时它们甚至还显得彬彬有礼,发着很大的声响离开我脚下的路,将自己长长的、镶着马赛克一般的身体拖到最近的洞里或是岩缝中。我则慢慢避开,不跟随它们,在它们离开时也不会去试着触摸它们吱吱作响的尾巴——虽然有时候那确实很有诱惑力,躲躲闪闪,然后去感觉一条响尾蛇在手指间的拍打。我从未这么做过,最好还是离它们远远的。

© David Becker
无论我多么恭敬,仍然感觉自己是在沙漠的等候室中踱步,等着被叫到。总觉得早上穿起裤子时,一条裤腿的外面会突然冒出一个矛头形状的脑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皮肤骤然剧痛起来,或是在泉水边俯身喝水时,后膝盖或是脖子旁侧猛然剧痛,没有注意到旁边还躺着一条毒蛇。那种恐惧不像是被灰熊撕成两半,或是被美洲豹拽上大树。
这是面对狙击手的恐惧,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冒出一颗子弹,而响尾蛇发出的声响传来时,就已经太迟了。
被蛇咬到的朋友保住了性命。毒液不足以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或是将他置于昏迷的状态,所以他一直保持清醒,在驶向接应处的船底躺着时紧咬着牙。手头上没有匹配的抗蛇毒素,没有办法,只能在伤口上方绑一块布条,寄希望于他不会在路上就死去。然后他被抬下船,经过颠簸的路途穿过沙漠,到达亚利桑那州的尤马,终于他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毒液消退。使用抗蛇毒素是一个危险的程序,抗蛇毒素本身也会致命,所以医生们决定静坐观察,确保他的喉咙不会卡住。他只能等着毒素流出。
响尾蛇带来的远不止死亡。它的毒液是一堆高度进化的药物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有很多滋补能力。响尾蛇的蛇毒因能够治疗某些癌症而出名,它穿透细胞壁的方法——像利牙一样使用锌原子透过细胞膜——同癌细胞在人体中游走的过程完全一样。使用这样的毒液所制造出的药物可以减少血液凝块,有效地刺激病人,使病人能够在短短几小时内恢复肢体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据说,有人将响尾蛇的毒液用于保健。但是这种东西不可轻视,剂量是个极易叛逆的平衡点,死亡随时都在等待。
几天后我见到了朋友,当然我想知道每一个细节。他告诉我,被蛇咬就像灼热的冰镐尖完全插进了骨头。他描述出毒液进入血管时那种沸烧的感觉,一层层的疼痛如何将他整个人摊开。他说我可以掀开盖在他身上的被单。我掀开一看,他的腿和脚都肿得可怕,像煤球一样黑。他的皮肤布满了爆竹般鼓胀的血管,看上去像是要从这样的肿胀里爆裂开。我看到他的眼睛斜向一边,隐藏起频繁的面部肌肉抽搐。
我冲他微笑着,盖上他面目全非的腿。我想这会让他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我满怀崇敬地说:“蛇做的药物。”
他明白我的意思,明白一条响尾蛇存于体内的滋味,他不自然地点点头,重复道:“蛇做的药物。”

多洛雷斯河,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
多年以后我们都离开了那条河,转而做起了不同的工作,但是有几个又回到了这片沙漠中来。我们回到这里,在野地里组织起期盼已久的聚会。离我们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已经十年了,我们中的三个人又一起向墨西哥的索诺兰沙漠挺进。一天晚上,我们搭一个爬虫学家的车走了60多千米,经过满是沙砾的双向车道,进入没有月光的一片漆黑中。我们的计划是让爬虫学家把我们放在沙漠里,带上足够的水,然后自己走出沙漠。这么做纯粹就是为了放松娱乐。我们将要花上近两周的时间,走到沙漠另一边的一个小镇。

科罗拉多山麓
正当我们开着车的时候,一条盘卷的响尾蛇出现在前车灯的光线中,爬虫学家猛踩下刹车。他跳出车门,挥着一根长杆子,杆子的一头上有个网。我都不知道这网是从哪儿来的,好像一下子就从他胳膊下冒出来了。他没有丝毫停顿,立即把网撒在地上,单手麻利地伸了进去。握起的手上一块肌肉扭动了一下。像是从帽子里拽出一只兔子,他将科罗拉多沙漠角响尾蛇举到了前车灯下。他的拇指顶着蛇的头骨,食指铲在它的颌下。蛇的身子向后轻打,而后缠在了他的胳膊上。这条蛇不长,不到1米,但是活生生的。
看到这一切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曾经从卡车里爬下来,观察过地上的蛇,在它面前蹲下来,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看它的舌头在空气中甩动着。可是突然这个人手里就攥着一条响尾蛇,正从不足1米远的地方直视着它的眼睛。就像是直视着湿婆神1那钢铁般的凝视,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我向后退步,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
“哦。”我急促地说,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词。
那条蛇已经开始发怒了。在它的尾巴尖上,一个琥珀色的振动器快速摇动着,发出了嗖嗖的响声。响环闪着光泽,一堆干燥的分节鳞片以每秒钟约六十次的速度震动着。它发出简单而醒目的消息:别碰我。
仿佛是在狂喜之中,爬虫学家陶醉地笑着自语:“啊,它真漂亮。”
我不愿靠近,不敢相信没有危险,过了一会儿,走得近了些。我一动也不敢动,心脏在汗衫下怦怦直跳。
爬虫学家兴奋地转过响尾蛇矛头形状的脸,推到我面前。“看看它。”他说。
我把头缩回肩膀里。
“不了,谢谢。”我咕哝着。
“你看一看吧。”他坚持说。
我整个身子都退到一旁,不过我还是照他说的盯着蛇看着。“没关系,”爬虫学家说,“我控制着它呢。”
我这样想着。握着就已经很不得了了,“控制着它”又意味着什么?我慢慢抬起头,一眼扫过角响尾蛇那愤怒的眼神。它的眼睛在剧烈地冒火,像玻璃球一样,里面点缀着粉尘的颜色,还有和身体相搭配的花纹。整条蛇是贫瘠乡土的颜色和质地。它的表情无法界定,那种一动不动的凝视下无法眨眼或是微笑。
角响尾蛇的头在爬虫学家的手中扭出了3毫米,足以让它张开嘴。我看着它嘴里粉红色枕头般柔软多肉的内壁,针孔般粗细却能吞下鸟蛋、蜥蜴和啮齿类动物的喉咙。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响尾蛇的那对毒牙向外龇着,细长,呈半透明状,如同玻璃做的缝衣针。它们看上去像是“小型外科武器”。我盯着那对尖牙,既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
我们即将要在响尾蛇的国度开始一段漫长的征程,而眼前发生的这一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在墨西哥的野外被响尾蛇咬到会是一件极悲惨的事情,直升机不会来这里救援。虽然我想成为有科学头脑的人,可我仍觉得我们是在给附近所有角响尾蛇传播恶意,这增加了我们的危险。我想让爬虫学家把蛇放下,但我无法这么做。我被“咒符”所镇住。那条蛇合上了嘴巴,我尽可能近地看着它沙砾色的眼睛。它的身体猛烈地扭动,尾巴吱吱地响,无法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了一分钟,爬虫学家从我面前退开,在我们之间找到一块空地,双手一推,把角响尾蛇释放到地面,不是把它扔出去,而是非常麻利地将它放开。蛇飞一样地跑开了。从我身边滑过时几乎都没碰着地面,动作优雅而迅速。
如此的运动力让其得名,它用身体在地面侧向滑行,像一根水做的绳子一样跑开。
除了只有一个肺以外,响尾蛇的身体构造差不多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这其中也包括人类,只不过它们身体拉长了,红色圆珠状的心脏在香烟状的肝脏之上,接下来便是一团肠子和一对狭长的肾。蛇有几百对肋骨,而人只有十二对。肋骨和同等数量的椎骨相连,彼此之间有球窝式的关节,使得蛇能够自由地连接起整个身体。
那条蛇爬过沙漠,朝着我的一个同伴爬去——它并非有意,这一点我确信。它只是想摆脱握住它的人。我的同伴穿着凉鞋,没有动,虽然他很清楚,这种动物会通过面部的孔穴来感知热量,不会被静止的动物所欺骗。作为一个沙漠行者,同伴足够了解响尾蛇,像他这样赤着脚,跳着躲开会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但他像石头一样站在那里,就这样看着蛇爬过他的脚,快速滑过的鳞片擦过他的脚趾。运动的每一份增量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这条角响尾蛇飞快地穿过,从我们的白色头灯光下爬到了黑暗的沙漠中。
每个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肩膀放松下来,拳头松开。有人竟莫名地笑了起来。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希望它不会来纠缠我们。”
爬虫学家在那里告别了我们。随着车尾灯光逐渐在远处暗淡下来,我们留下来的三人在星光中起程。没有人用头灯,我们让眼睛适应起黑暗。沙漠在面前展开,我们注视着地球的表层和远方的天空,数着落下去的星星。
被大风磨尖的黑色砾石躺在此起彼伏的沙丘上。我拖着脚向前走,肩上的水压得我头昏脑涨。我们各自埋头走路,肩膀引着我们向前,大口地呼气吸气,目光在星群中游离。一条响尾蛇的声音在我们之间的地面响起,突然我们都清醒过来,身体马上有了反应。我们看不到蛇,但是很清楚它在什么地方,于是围了上去。听起来是条小蛇,一条年轻的角响尾蛇。我们朝地面看着,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漆黑的土地发着咝咝的盛怒。
有人对它说:“我们刚开始走,没什么可激动的。我们知道你在这儿。”
蛇的声响逐渐变小,然后停了下来。也许它是累了或是渴了,不愿意再耗费更多的能量,或者它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安全了,已经镇住了那些踩到它身上行动迟缓的庞大动物。
我低头看着脚下安静下来的漆黑土地,我想它与周围每一块安静而漆黑的土地没有什么不同。它看上去就像一整片沙漠。谁知道这里有多少条响尾蛇呢?对此感到焦虑的话就不值了。我们转过身,继续前行,走进繁星中。

人在河峡谷壁的剪影 © Joshua Lott
拂晓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从沙漠中一场长长的睡梦中醒来,从睡袋里爬出。晚上某个时候我们把淡水卸下时我把睡袋拿了出来。我们的营地看上去像是一堆瓦砾,废弃在绵延起伏的黄褐色沙丘中。一种空虚萦绕着我,占据了每一条地平线。现在没有风,只有一片静谧而苍白的天空。我站起身,光脚踩在细如食盐的沙子上。还没走三步,我便停在一片新鲜的脚印前,那是角响尾蛇留下的。我随着脚印看到身后的行李,发觉熟睡时一条响尾蛇从我脑袋旁边爬过。它留下了一片优雅而富有韵律的印迹,像是手写的什么东西。沙漠非常柔软,甚至显露出蛇腹上每一片光滑而宽阔的鳞片。我跨过痕迹,避免将它擦掉。随后又遇到了第二条角响尾蛇的印迹,然后是旁边的第三条,接着第四条和第五条交叉起来。
当第一抹光线出现时,响尾蛇们便会在沙丘间的洞孔和硬土层寻找庇护所,在那里它们躲避白天的高温。看上去好像它们整晚都不睡觉,把整个世界描画得鲜活起来,让大地平抹出各种形状,准备迎接太阳。我觉得它们的痕迹很美,但同时知道睡梦中有多少响尾蛇在忙碌后,内心也隐隐不安。我必须要小心才行。
太阳还未升起,我们收拾起东西,继续赶路,每个人都带了45千克重的淡水。光着脚是最省事儿的。没有靴子,我们可以更方便地在沙丘上滑行,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滑不动,而只能在行李的重压下缓慢行进。我们常常弯下身来休息,手掌按在膝盖上。白昼来临,太阳打破了地平线。我们继续走着,直到高温将我们赶到唯一一片灌木树丛的阴凉处。我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我觉得我们是几只笨拙且辛酸的动物,而响尾蛇却可以在周围自由来去,不被察觉,行动起来只有摩擦的窃窃声响,脊椎骨彼此滚动,像碗里的玻璃弹子。角响尾蛇吃蜥蜴和更格卢鼠,尽可能地从自己的身体中汲取水分,而我们则要永无休止地苦苦驮着每一滴宝贵的水源。

极寒带森林 © Olivier Morin
风吹起。它开始灼烧着脸颊,我们举起双手,遮住薄纱一般的沙尘。风不停地吹,不捂住鼻子和嘴的话几乎无法呼吸。我们站起身,背上行李继续走。角响尾蛇的轨迹从沙丘间升起,飞绕在我们周围。
不同种类的响尾蛇会喷出不同的毒液。我知道一个在热带荒岛上被蛇咬到的人。他说他并没有感到意识清醒下的疼痛,而是饱受了二十四小时狂乱的噩梦般的幻觉之苦。在那些几乎遥无止境的时段中,他在脑海中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撕裂开,仿佛陷入了一个囚禁身心的监狱。几乎无法与搭救他的同伴沟通,他只能听到话语的回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毒液消退下去。
很多被响尾蛇咬过的人都谈起过类似的梦,即便是在恢复健康很久以后。尤其是那些从严重咬伤中生还的人说,像是迷幻药物引起的幻觉重现,神秘而恐怖的幻象会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是一生。这的确取决于响尾蛇的种类和毒液的剂量。多数响尾蛇的血毒素都具有破坏组织血液的功能,它能够迅速破坏细胞机能,导致内出血;有些含有的主要是神经毒素,这种毒素能够渗入神经网,将重要器官一个接一个关闭;绝大多数响尾蛇既含有溶血毒素又含有神经毒素。100毫克西部菱斑响尾蛇的毒液可以置人于死地,而莫哈韦沙漠响尾蛇仅需要10毫克,角响尾蛇介于两者之间,第一口咬下去并不总是致命,但非常危险,并有致命的可能,而咬伤发生在几千米外没有道路的沙漠中时尤其如此。
我们赤着双脚在沙漠中跋涉,在行进的过程中,我思考着毒液的问题,打发着空闲。黄昏的时候,我思索着毒液进入体内可能产生的感觉,不知道那会不会封杀我的喉咙,我问自己——像从前无数次那样—我是否会紧张,还是会随口默念祷文让自己受惊的意识镇定下来。第二天黎明,我在大脑中排演着这一幕,想象着自己被蛇咬到,坐在地上,在沙漠中连续一两天扭曲、干呕。我想,经历过这些,自己会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但是我更希望在没有遭蛇咬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

瓦萨群岛 © Olivier Morin
午夜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繁星和同伴在远处走动的模糊轮廓,我感觉自己在方圆几千米的沙漠中散开。对响尾蛇的认知变成了一首歌,一阵鼓点。它变作了周围的每一样事物,与靛蓝的天空、如洗的沙漠、呼吸的律动无法分开。半是醒着,半是梦中,我听着自己仓促的脚步所发出的祷文。我不再害怕响尾蛇了,因为恐惧需要凝思,而此刻,后者已完全脱离了我的范畴。慢慢地,我感觉自己像要飞起来一样。双脚离开沙漠浮了起来。虽然行李仍像一块大石头一样绑在身上,我还是张开了双臂。它的重量逐渐从我身上滑落。我不再为重负而数星星。踏着沙地的双脚像是踩在空中的热气球上,将整个身体向上送。我几乎要笑起来,惊讶于这些年我从未学着像在梦里一样飞翔,每一步都毫不费力地滑行,像在月球上行走。
在纵深的沙漠中旅行时,我发现自己总时不时地期待有轻微的梦境般的幻觉。身上有给人以压迫感的重物,地形又绵延不绝,人会发现他清醒的意识悄悄地松弛下来。这种片段的唯一问题在于,事后我无法回想起到底哪一个才是幻觉:是我确实飞起来了的事实呢,还是我不可能飞的逻辑解释呢?
很像是沉入了那些被蛇咬的人所进入的类似梦境,我们向一个陡峭的沙丘爬去,三个人从沙丘侧面向上挺进,双手扎进沙砾堆起的小山,两脚扒着地面。呼吸急促,肺吃力地起伏着,我们一口气飞到了丘顶,落在了伸向星星的最高处。我们解下行李,随它们滚到一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平躺着大喘着气,现在所做的已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了,这一点我确定。

沿着湖岸露营的人们 © Joshua Lott
最终我们走进了沙漠旁的一个墨西哥小镇。我们像蓬头垢面的流浪者,从沙漠中走出来,有些旁观者走到门口,看着我们经过街道。小镇上唯一一名警察从一个门廊大步迈出,急切地传唤我们离开了纯净的晨光。他把我们的证件看了个遍。我们不怎么在乎,头发乱蓬蓬的,还沾着沙子。他用西班牙语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用西班牙语回答了他。他不相信我们,又问了一遍。我们指了指那褪了色的米黄色地平线,解释说我们是群傻瓜,是群喜欢在荒芜的不毛之地行走的旅行者。他说沙漠里没有水源,有很多响尾蛇,没有人会从那里出来。我们不去辩解什么。我们等着他在那煤渣砖砌成的小屋里打开无线电,慢慢地对着一个黑麦克风重复我们的名字。
那个警察走出来,问了更多的问题。我们告诉了他各自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他又回到了无线电前。他似乎确定我们心怀诡计,但没有丝毫证据。他再次出来,还给我们证件。他估摸着我们讲的是实话,我们的确是群傻瓜。
我们将行李背到了尘土飞扬的街上。第一辆汽车驶来,远远地就能听到声音,这时我们竖起了拇指。一辆卡车停在面前,我们带着行李爬进了车厢,现在行李已经很轻了,里面的水所剩无几。卡车在一条长长的单行道上驶出了小镇,我们倚着车轮罩,热风吹到嘴里。看着沙漠从眼前掠过,我想警察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没错,确实有诡计,也很简单:让步。我们光着脚在蛇的海洋里穿行,像是神秘主义者在赤红的炭火上行走,展示出一层层的自我,变得虚无,无足轻重。我们不是傻瓜。说自己是傻瓜,那是谎话。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那便是长时间、定量地摄取着“蛇药”。
但是不瞒你说,我仍然在等候室里踱步,准备迎接自己被蛇咬到的那一天。这一想法只会让我的眼睛更加锐利,坐不会坐稳,站只踮脚尖。比起从前,我的惧怕没有丝毫减少,只能双膝跪地,不断地祈求蛇再多宽限我一天。
本文节选自

《遇见动物的时刻》
作者:[美]克雷格·查尔兹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202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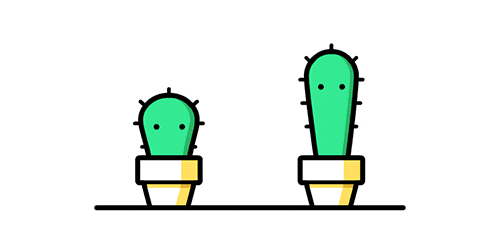
编辑 | 海明威的猫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遇见动物的时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