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往爱尔兰文学的岛屿,和远方命运相似之人漂泊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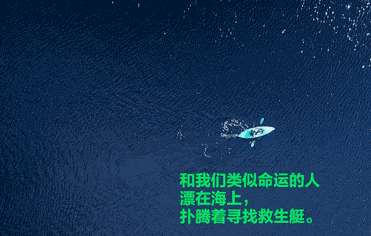
詹姆斯·乔伊斯、奥斯卡·王尔德、W.B.叶芝、萨缪尔·贝克特,谈到爱尔兰文学,我们会想起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字,近年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萨莉·鲁尼也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里。这个小小的国家其实还有更多文学风景值得我们了解。最新一期的《单读》来到文学传统丰厚且依然富有文学活力的爱尔兰,译介在本地文学读者里受到推崇但在中文世界介绍得还很少的、独具一格的十二位当代爱尔兰小说家及其作品。
本期特邀曾旅居爱尔兰、现居英国的作家颜歌和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两位担任客座主编,在他们看来,这些爱尔兰作家的写作关注大时代阴影下漂泊着的个体命运,以文学的眼光进入历史,将“北爱尔兰问题”、移民议题和晚期资本主义图景化为故事背景,刻画底层劳动人民、每个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经历的伤痛,对尊严和救赎的渴望。“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描绘当代人心灵困境上入木三分,那种在空虚的人生中无从找到自己存在意义的颓丧,那种想要与人相拥却发现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隔阂的无奈,我们都是命运相似之人,正在寻找一艘救生艇。”
今天夜读,带来颜歌对爱尔兰文学的阅读感受和推介。

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里的世界(节选)
文 / 颜歌
我是在2015年搬到了都柏林以后开始广读爱尔兰小说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我写小说写了二十多年,读小说的时间就更久,因此,比起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似乎和我的关系更近——如果我无法从文学里进入爱尔兰,那现实的爱尔兰对我来说就是虚无缥缈、远若幻境的。只有拿起书,读了《死者》(“The Dead”),才觉得阿伦码头边上不再只有荒秃秃的红房子,反而充满了小圣诞夜车马往来的宾客欢笑;读了《基拉里峡湾》(“FjordofKillary”),才发现梅奥郡酒吧里酒鬼的呓语不再晦涩难解,倒成了末世荒诞的长短句;读了《欢迎光临》(“Show Thema Good Time”),才会在每次开长途车路过马林加时不再抱怨寡淡的风景和索然的服务站,而是去仔细看这空旷的大地和在这份空洞里寻找意义的人们——对我来说,只有通过爱尔兰的小说,现实的爱尔兰才变得具体而意味深长,现实中人的话语才音律飞扬。这片土地被剥削和压迫了多年,这里的人永远都在苦难里爬行,永远在忏悔自己的罪,祈求无法降临的救赎;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向外敞开着自己,去感受,去表达,滔滔不绝,醉话连篇,诅咒,歌唱,吐出来最是引人捧腹又催人落泪的句子。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因此,也是短篇小说家的国度—整个爱尔兰岛上到底有多少人在写作,具体数字不详,但是作家所占的人口比例一定是惊人地高。

刚刚过去的七月,在西科克文学节(West Cork Literary Festival)上,我在本地酒吧遇到了刚刚被任命为《刺人虻》(The StingingFly)新主编的莉萨·麦金纳尼(Lisa Mclnerney)。她跟我讲起她来之前终于看完了夏季刊的征稿。这次征稿特别面向之前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文学新人。“我本来以为不会有多少稿子,”莉萨跟我说,“你猜猜我们收到多少份短篇小说?”
我摇摇头。“一千两百多份。”她说。
而她需要从这一千两百多份投稿中选出十四篇来发表。“不可能的任务。”莉萨叹口气,嘬一口啤酒。
这一次给《单读》编爱尔兰文学特辑的任务,虽然不如莉萨的任务那样不可能,但也谈不上轻而易举。我的想法是选一些新的、之前没有在中文世界被介绍过,或者相关信息还很少的作家和作品;此外,比起那些因为强化爱尔兰的刻板印象而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的作品,我更愿意选一些在本地的文学读者里受到推崇的作品——但这样的选择思路也可能会带来一个难题。
“很多爱尔兰作家尤其喜欢用本地话、土语,甚至自己造些新词,所以我感觉翻译起来可能会很有难度,我是应该选一些好翻的,还是就选我喜欢的?”我问彭伦。
“就选你觉得好的,翻译的问题我们来解决。”彭伦说。

得到了这样的保证,我第一个就把凯文·巴里(Kevin Barry)的小说放上了我的单子。凯文·巴里是爱尔兰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之一,他充满了方言、俗语、粗话的文学表达深深影响了现在爱尔兰的青年写作者,也是西爱尔兰作家群体中的核心人物。
一直以来,我总是偏爱西爱尔兰的作家。他们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凄风苦雨的斯莱戈、梅奥、戈尔韦,故事里的人讲话总是带着浓烈的口音,有挣扎,有绝望,有暴力,总是一片似乎要摧毁一切的黑暗,而这黑暗里仅有一丝若有若无却引人入胜的光亮。凯文·巴里是这样的,莉萨·麦金纳尼是这样的,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和约恩·麦克纳米(Eoin McNamee)的故事也被这奥克斯山脉下的同一片土地所孕育。
凯茜·斯威尼擅写超短故事。这个集子里的三个故事是我选出来的,拿去问她要不要取个名,她就说不如叫《三个爱情故事》(“Three Love Stories”)吧,我忍俊不禁。“爱情”这个词她点得实在是绝妙,充满了反讽。不用说,她的故事们是借“爱情”之名写生活的荒诞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换言之,是“反爱情”。同样“反爱情”并有一个绝妙标题的还有露西·考德威尔(Lucy Caldwell)的《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All the People Were Mean and Bad”):疲惫的母亲、总是缺席的丈夫、令人窒息的长途旅行、哭闹的女儿和怀着不明善意的陌生男人,第二人称的叙事,正像是孤索的女主角在喃喃自语——读这些故事,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王小波式的问题:到底人生中的相遇是看似毫无意义,实则意味深长;还是表面上充满深意,本质却毫无意义?
妮科尔·弗拉特里(Nicole Flattery)的《欢迎光临》和温迪·厄斯金(Wendy Erskine)的《格洛丽亚和马克斯》(“Gloria and Max”)从不同的侧面来讨论这个存在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故事看似说的是个体人物的相遇,实际上又各自映着大时代的阴影:在弗拉特里的故事里,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都柏林;在厄斯金的故事里,是“北爱尔兰问题”之后的贝尔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光是这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紧迫和张力。“有人说我们这些人只会写‘北爱尔兰问题’,但只要是一个北边的故事——不管故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哪儿可能和‘北爱尔兰问题’无关呢?”我的一个北爱尔兰的作家朋友有一次对我说。
“北爱尔兰问题”是爱尔兰岛上一个巨大的伤口,这伤口被切得太深,腐烂、疼痛得太久了,就算是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后被打了麻醉剂、缝合了起来,才刚刚要开始愈合,又重新被脱欧的种种波澜撕扯开,汩汩流血。
路易斯·肯尼迪(Louise Kennedy)的《剪影》(“In Silhouette”)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鲜血的故事,一个家庭的破灭,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失去兄长,寻找一份似是而非的爱情。第二人称、现在时,把过去和现在,伦敦和北爱尔兰织成了支离破碎又交错相连的一卷。
同样是一个破碎家庭的故事,丹妮尔·麦克劳克林(Danielle McLaughlin)的《部分获救者名单》(“A Partial List of the Saved”)则像是一出轻喜剧,然而,当这轻喜剧发生在北爱尔兰,却有了更多的意味。故事里面没有人死去,但他们的旅途的背景中却满是亡灵:泰坦尼克号的遇难者;被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英国部队杀掉的爱尔兰人,他们的铜像在乡道边立了将近一个世纪。也是在贝尔法斯特,简·卡森(Jan Carson)的笔下栩栩如生的是这座城市里的劳动阶级和底层人民,他们都在身体和精神的疾病里煎熬着。他们找到的救赎是一个从波兰移民来的姑娘,传说,跟在这外国姑娘的身后跳入泳池里,就会有奇迹发生。

在这辑的最后一个故事里,我们将回到都柏林,却发现梅拉图·乌切·奥科里(Melatu Uche Okorie)所写的都柏林和我们从凯茜·斯威尼那里所读到的那个城市大相径庭。一群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难民聚集在都柏林的临时安置所里,煎熬、焦虑,而又无比鲜活。奥科里这个“新爱尔兰人”作家在《小旅馆的这日子》(“This Hostel Life”)里一开头就干了件非常爱尔兰的事——拿自己人开涮:“你知道呐些个尼日利亚人的,他么时时刻刻都想干仗。”像所有其他卓越的爱尔兰作家一样,在奥科里的故事里,英文作为文学语言被拆开解构,又以有机的、地道的方式组合,再响起来,让我们听到众生的声音,各有特色、轻重、乡音,相互间顶嘴、骂架、揶揄,通篇喧杂却又声声入耳,句句都写在又痛又深的现实里。
2017年的夏天,我推着刚刚满月的儿子到都柏林卡布拉(Cabra)的一间诊所,准备给他打预防针。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我的手机里忽然收到了一封邮件。写邮件的人是露西·考德威尔,她说她从《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那里得到了我的邮箱,希望我不要介意她冒昧地来信,她说她正在着手编辑下一年的费伯爱尔兰新小说集(Being Various:New Irish Short Stories),准备收入总共二十一位现在爱尔兰文学界的代表性作家,她又接下去说:“作为小说集的编辑,我想要重新思考‘爱尔兰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很想去拓宽这个概念,这概念应该包含出生在爱尔兰但成长于别处的作家,从别处来但选择以爱尔兰为家的作家,也包括那些不知怎的发现他们自己就住在了爱尔兰的作家。因此,我特别希望你能给这小说集写一篇小说。”——当时,我一手抱着不断扭动的婴儿,另一只手握着隐隐发烫的移动电话,不确定自己是否因为过度缺乏睡眠而产生了幻觉。“‘爱尔兰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好几年以后,编着这一期爱尔兰文学特辑,我的脑子里回响起来露西当时问的这个问题。我应该以什么准则、什么要求——如果我有这个资格的话——去选择收入这一辑的作家和小说呢?

▲ 电影《风吹麦浪》
在我看来,爱尔兰作家都和英文有着复杂的关系,从乔伊斯开始,他们就总要颠覆和解构这原本来自殖民者的语言,把它变得本土,古怪,自我,满是新意;爱尔兰作家们都是创造声音的高手,叙事声音也好,对话也好,句句都有棱有角,栩栩如生;爱尔兰的作家爱幽默和讽刺,不管故事的底色如何苦难压抑,他们永远都可以苦中作乐,让你大笑出声;爱尔兰作家也很会抒情,虽然他们一般不轻易这么干,但一旦抒起情来,一定是要“山无陵,天地合”的——多年了,每次想起《死者》的结尾,我都要流下泪来。
归根结底,爱尔兰的小说家和天下所有的小说家一样,其实是最我行我素的。当小说家进入他们的故事里,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切别的事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变得不重要也不存在了,唯一要紧的只是眼前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风景、世界不断扩大,充实着物品的细节、声音的余韵、植物的触感,将最终覆盖并取代小说家肉身所在的、所谓真实的世界。现在,是进入故事里的世界的时候了。
原标题:《前往爱尔兰文学的岛屿,和远方命运相似之人漂泊旅行|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