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寥寥几笔,乔伊斯就写透了死亡与孤独
今天是爱尔兰作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忌辰。本文为小说酒馆系列101篇,选自他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死者》。
《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短篇都写透了孤独。有的孤独抵达释怀,有的则抵达虚无与绝望。乔伊斯的这篇《死者》让读者走入了生死之间的晦暗地带,这里混合着与孤独有关的一切,每个人或许都会有独一无二的体会。
在乔伊斯的忌辰日,一定没有比读《死者》更好的纪念了。

加布里埃尔没有与其他人一起到门口。他呆在前厅的暗处,抬头凝视着楼梯。一个女人站在第一段楼梯的上部,也在阴影里。他看不见她的脸,但能看见她裙子上赤褐色和橙红色的图案,它们在阴影里呈现出黑色和白色。那是他的妻子。她正倚着栏杆聆听什么。加布里埃尔见她一动不动大感惊讶,也竖起耳朵细听。但他却听不见什么,除了门口台阶上的笑声和争论,只依稀听见钢琴上弹出一些和音和一个男声唱歌的片断。
他静静地站在昏暗的前厅里,试图捕捉那声音唱的曲调,并仰头注视着他的妻子。她的神态显得优雅而神秘,仿佛她是某种东西的一个象征。他自己问自己,一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的阴影里,倾听远处的音乐,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呢?如果他是个画家,他会画下她那种神态。她的蓝色毡帽配以黑暗的背景会突出她那古铜色的头发,而她裙子上的深色图案也会突出浅色的图案。假如他是画家,他会把这幅画称作《远方的音乐》。
前厅的大门关上了;凯特姨妈、朱丽娅姨妈和玛丽·简回到前厅里,仍然在笑着。
“你们说,弗雷迪是不是太不像话?”玛丽·简说。“他真是太不像话了。”
加布里埃尔没有说话,但向楼梯上他妻子站着的地方指了指。现在由于大门已经关上,歌声和琴声都听得更清楚了。加布里埃尔举起一只手让他们安静。歌声唱的好像是古老的爱尔兰曲调,唱者似乎对歌词和自己的声音都没有把握。距离和唱者沙哑的嗓音使歌声显得哀伤,隐隐约约传出的旋律伴随着表现悲愁的歌词:
“啊,雨点打着我浓密的头发,
露水沾湿了我的肌肤,
我的孩子冷冷地躺着……”
“啊,”玛丽·简叫道。“这是巴特尔·达尔西在唱歌,而他整个晚上都不肯唱。哇,他走之前我得让他唱支歌。”
“哎,对,玛丽·简,”凯特姨妈说。
玛丽·简转过身跑向楼梯,但她还没跑到歌声就停了,钢琴也突然盖上了。
“啊,多遗憾呀!”她嚷道。“他要下来了吗,格丽塔?”
加布里埃尔听到妻子答了一声是,然后看见她下楼向他们走来。她身后几步便是巴特尔·达尔西先生和奥卡拉汉小姐。
“啊,达尔西先生,”玛丽·简叫道,“你真不够意思,我们大家正听得入迷,你竟然就那样停了。”
“整个晚上我都跟着他,”奥卡拉汉小姐说,“康洛伊太太也是,可他告诉我们他患了重感冒,唱不了。”
“哦,达尔西先生,”凯特姨妈说,“原来你撒了个无害的弥天大谎。”
“你听不出我的嗓子哑得像只乌鸦吗?”达尔西先生有些粗鲁地说。
他匆匆走进餐具间,穿上大衣。其他人对他粗鲁的回答感到惊讶,但不知该说什么。凯特姨妈皱起眉头,并示意其他人别再提这个话题。达尔西先生站着仔细地裹他的围脖,也皱着眉头。
“都是这天气闹的,”停了一会儿朱丽娅姨妈说。
“是呀,人人都患了感冒,”凯特姨妈立刻接着说,“无一例外。”
“听人说,”玛丽·简说,“三十年了没下过这样大的雪;今天早晨我看报纸,报上说整个爱尔兰普遍下了雪。”
“我喜欢雪景,”朱丽娅姨妈感伤地说。
“我也喜欢,”奥卡拉汉小姐说。“我觉得圣诞节地上没雪就不是真正的圣诞节。”
“但是可怜的达尔西先生就不喜欢下雪,”凯特姨妈笑着说。

达尔西先生从餐具间出来,裹得严严实实并结好了扣子,歉然地对他们述说自己得感冒的经过。大家都劝他,说是太遗憾了,要他在夜风里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嗓子。加布里埃尔望着他的妻子,她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她正站在满是灰尘的楣窗下面,煤气灯的光焰照亮了她那丰润的古铜色头发,几天前他曾见她在火边把头发烤干。她神态如前,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周围的谈话。终于她转向他们,加布里埃尔发现她双颊泛红,眼睛闪闪发光。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愉悦的潮流。
“达尔西先生,”她说,“你刚才唱的那支歌叫什么名字?”
“叫《奥芙里姆的少女》, ”达尔西先生说,“可是我记不清楚了。怎么?你知道这支歌?”
“《奥芙里姆的少女》, ”她重复说。“我想不起这个歌的名字了。”
“这歌的调子真是太美了,”玛丽·简说。“可惜你今晚嗓子不好。”
“喂,玛丽·简,”凯特姨妈说,“别烦达尔西了。我可不想让他心烦。”
看见大伙都准备走了,她领头带他们走向门口,在那里互相道别:
“好了,凯特姨妈,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愉快的夜晚。”
“晚安,加布里埃尔。晚安,格丽塔!”
“晚安,凯特姨妈,太谢谢了。晚安,朱丽娅姨妈。”
“哦,晚安,格丽塔,我刚才没看见你。”
“晚安,达尔西先生。晚安,奥卡拉汉小姐。”
“晚安,莫根小姐。”
“晚安,再见。”
“大家晚安。一路平安。”
“晚安,再见。”
凌晨,天仍然很暗。阴沉昏黄的晨光笼罩着房子和河面;天像要垂下来似的。脚下到处是融了的雪水;只有房顶上、码头的栏杆上和空地的围栏上,留着一缕缕、一片片白雪。路灯仍然在灰朦朦的空中燃着泛红的灯光,河对面“四院”大厦在低沉的天空下巍峨屹立。
她和巴特尔·达尔西先生一起走在他的前面,她的鞋用一块棕色的包袱包着夹在胳膊下面,双手提着裙子唯恐溅上了雪水。她已不再有什么高雅的神态,但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仍然幸福得发亮。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涌动;脑海里思潮激荡,骄傲、快乐、温柔、英勇。

她走在他前面,那么轻盈,那么挺直,他极想悄悄地追上去,抓住她的双肩,在她耳边说些可笑而深情的话儿。他觉得她那么娇弱,他渴望着保护她不受伤害,渴望着与她单独呆在一起。一些他俩秘密生活的时刻突然像星星一样在他的记忆中闪现。一个淡紫色的信封放在他早餐的杯子旁边,他用手轻轻地抚弄着它。鸟儿在常春藤上唧唧喳喳,窗帘上网状的阳光在地板上闪烁:他幸福得吃不下东西。他们俩站在拥挤的站台上,他把一张车票塞进她戴着手套的温暖的手心。他和她一起在寒冷里站着,透过花格窗向里观望,看一个男人在烈焰熊熊的火炉边制作瓶子。天气很冷。她的脸在寒冷的空气里散发着芬芳,与他的脸离得很近;突然他朝炉边那个男人喊道:
“火旺不旺,先生?”
那人因为炉子的响声没能听见。这倒也好。否则他可能粗暴地回答。
又一股柔情蜜意之潮从他心中涌出,沿着他的动脉在温暖的血液里流动。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刻,那些谁也不知道或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时刻,宛如柔和的星光,突然闪现出来照亮了他的回忆。他渴望对她回忆那些时刻,使她忘记这些年他们在一起的沉闷生活,只记住他们那些销魂的时刻。因为他觉得,岁月并没有泯灭他或她的激情。他们的孩子,他的写作,她对家务的操劳,并没有完全泯灭他们心灵深处温柔的情焰。他在昔日写给她的一封信上曾这样写道:“为什么这样一些词我觉得如此乏味和冷漠?是不是因为没有足够温柔的词来称呼你呢?”
像是遥远的音乐,多年前他写下的这些话又从过去回到了他的记忆之中。他渴望与她单独在一起。当其他人都已离去,当他和她二人在旅馆的房间里的时候,那时他们会单独呆在一起。他会温柔地呼唤她:
“格丽塔!”
也许她不会马上听见:她正在脱衣服。然后他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会使她激动。她会转过身来看着他。……

在崴特佛恩大街的拐弯处他们遇到了一辆马车。他对嘎啦嘎啦的车轮声感到高兴,因为他用不着说话了。她正望着窗外,显得有些疲倦。其他人也只偶尔说上几句,指点外面的某个建筑或街道。在凌晨阴沉的天空下面,马儿疲劳地奔驰,后面拖着嘎嘎响的车厢,加布里埃尔又和她一起坐在一辆车里,奔驰着前去赶船,奔向他们的蜜月。
马车驶过奥康奈尔桥时,奥卡拉汉小姐说:
“人们说,你每次过奥康奈尔桥时都会看到一匹白马。”
“这次我看到了一个白人,”加布里埃尔说。
“在哪里?”巴特尔·达尔西先生问。
加布里埃尔指了指雕像,上面覆盖着片片白雪。然后他亲切地向它点点头,还挥了挥手。
“晚安,丹,”他高兴地说。
车在旅馆前停下,加布里埃尔跳下车,不顾巴特尔·达尔西先生的争执,付了车钱。他多给了车夫一个先令。车夫向他敬个礼说:“祝您新年如意,先生。”“祝你也新年如意,”加布里埃尔亲热地说。
下车时,有一会儿她倚着他的胳膊,站在路边的石阶上向其他人道别。她轻轻地倚着他的胳膊,就像她几小时前与他跳舞时那样。那时他感到骄傲而幸福,他为她属于他而幸福,为她的高雅和做妻子的举止而骄傲。但是这时,在又一次激起那么多的回忆之后,他刚一接触到她那富于韵致、奇异而芬芳的身体,便浑身涌动起一阵强烈的情欲。在她沉默的掩饰下,他使她的胳膊紧贴着自己;当他们站在旅馆门口时,他觉得他们已经避开了生活的责任,避开了家庭和朋友,怀着奔放喜悦的心情,共赴一个新奇的境界。
在大厅里,一位老人正坐在一把有椅套的大椅子上打盹。他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支蜡烛,在他们前面走向楼梯。他们默默地跟着他,双脚踩在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上发出轻轻的噔噔声。她在看门人后面登上楼梯,往上走时低着头,纤弱的双肩弓起,像扛了东西似的,裙子紧紧地裹着她的身躯。他本想用双臂抱住她的臀部,紧紧地搂着她,因为他充满了想抱住她的欲望,双臂在不停地颤抖,只是他的指甲用力扣住手心才阻止了他躯体里这种狂烈的冲动。看门人在楼梯上停住,稳住摇晃的蜡烛。他们也在他下面的楼梯上停了下来。寂静之中,加布里埃尔能听见烛泪滴在托盘上的声音,能听见他的心脏挨着肋骨砰砰跳动的声音。
看门人领着他们穿过楼道,打开一个房间的门。然后他把摇晃的蜡烛放在一张梳妆台上,问他们早上什么时间叫醒他们。
“八点,”加布里埃尔说。
看门人指指电灯的开关,咕咕哝哝开始道歉,但加布里埃尔打断了他:
“我们用不着灯。从街上照进来的灯光就足够了。而且,”他指了指蜡烛补充说,“我说你最好把那个漂亮的东西也拿走,做个好人。”
看门人又拿起他的蜡烛,但非常迟缓,因为这一新奇的念头使他感到惊讶。接着他咕咕哝哝道了个晚安,走了出去。加布里埃尔随即把门锁上。

一道苍白的灯光从街灯上射入屋里,像一条长长的光杆从窗户直抵门上。加布里埃尔把大衣和帽子扔到躺椅上,穿过房间走向窗户。他向街下看看,以便稍微平静一下他激动的情绪。然后他转过身,背着光靠在一个衣柜上。她已经脱掉大衣、帽子和斗篷,正站在一面大的时髦的镜子前面解她的紧身胸衣。加布里埃尔停了一会儿,注视着她,然后说:
“格丽塔!”
她慢慢地离开镜子,顺着光束朝他走去。她的表情显得非常严肃而疲乏,竟使加布里埃尔心里想说的话无法出口。不,还不是时候。
“你看上去累了,”他说。
“是有点累,”她回答。
“你不是不舒服吧?”
“不,只是累了。”
她走到窗前站在那里,向外观看。加布里埃尔又开始等待,后来他唯恐犹豫会使他失去激情,便突然说道:
“听我说,格丽塔!”
“什么事?”“你认识那个可怜的家伙马林斯吗?”他匆匆地说。
“认识,他怎么啦?”
“啊,可怜的家伙,毕竟他是个正派人,”加布里埃尔言不由衷地继续说。“他还了我借给他的一英镑硬币,其实我没指望他还。可惜他总不肯离开那个布朗,因为他不是个坏人,说实在的。”
这时他因气恼而发抖。为什么她看上去那么无动于衷?他不知道自己如何开始。她也为某件事气恼吗?要是她主动转向他或走向他就好了!像她现在这样就去和她做爱未免有些粗暴。不,他一定要先在她眼里看到同样的激情。他渴望能把握住她奇怪的情绪。
“什么时候你借给他一镑硬币?”她停了一会儿问。
加布里埃尔极力控制自己,避免对苏格兰人马林斯和他那个英镑的事说出粗话。
他渴望从内心里对她呼喊,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将她征服。但是他说:
“哦,在圣诞节,他那个位于亨利大街的圣诞贺卡小店开张的时候。”
他正处于激怒和欲望的狂热之中,以致没有听见她从窗口走来。她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奇怪地望着他。然后,她突然踮起脚尖,双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吻了吻他。
“你是个很慷慨的人,加布里埃尔,”她说。
加布里埃尔因她突如其来的一吻和对他的赞语兴奋得浑身颤抖,他把双手放在她的头发上,开始向后梳理,手指几乎都没有碰到头发。洗过的头发柔润光亮。他心里洋溢着幸福。就在他盼望时她真的自愿地来到了他身边。也许她的思想一直在与他的共鸣。也许她感觉到了他心中的强烈欲望,于是便突然产生出依顺的心情。现在她如此轻易地依顺着他,他竟对自己刚才那么犹豫疑惑起来。

他双手捧着她的头站着。然后,他迅速滑下一只胳膊拢住她的身子,把她拥向怀里,轻轻地说:
“格丽塔,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她既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倒向他的怀里。他再次轻轻地说: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格丽塔。我想我知道是什么事。我知道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接着突然眼泪汪汪地说:“啊,我在想那支歌,《奥芙里姆的少女》。”
她挣脱他的拥抱,跑到床边,双臂伸出架在床栏上,埋住了她的脸。加布里埃尔一时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着,然后才跟了过去。当他经过那面转动式的穿衣镜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全身,他那宽而挺扩的衬衣领口,他那在镜子里看见时总使他困惑的面部表情,还有他那闪光的金边眼镜。
他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说道:
“那歌怎么啦?为什么使你哭起来了?”
她从胳膊上抬起头来,像孩子一样用手背抹干了眼泪。他自己的声音也意想不到地变得更加温柔。
“怎么啦,格丽塔?”他问。
“我在想很久以前一个常唱那支歌的人。”
“很久以前的那个人是谁?”加布里埃尔笑着问。
“是个我在高尔韦认识的人,当时我和我祖母住在一起,”她说。
加布里埃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种抑郁的怒气开始在他的心底汇聚,他那被压抑的欲火重又开始在他的血管里愤怒地燃烧。
“是你的旧情人吗?”他讥讽地问。
“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她答道,“名叫迈克尔·福瑞。他常唱那支歌,《奥芙里姆的少女》。他非常文静。”
加布里埃尔一言不发。他不希望她觉得他对这个文静的男孩有什么兴趣。
“我能那么清楚地看见他,”她停顿了一下说。“他有那么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的眼睛!眼睛里还有那样一种表情——一种表情!”
“啊,那么,你爱上他了?”加布里埃尔说。“我在高尔韦的时候,”她说,“我常常和他一起外出散步。”
一种想法闪过加布里埃尔的脑际。
“也许那就是你想和那位爱佛丝姑娘一起去高尔韦的原因吧?”他冷冷地说。
她看看他,惊讶地问:
“为什么?”
她的目光使加布里埃尔感到尴尬。他耸耸肩说:
“我怎么知道呢?或许去看看他。”
她默默地把目光从他移开,沿着光束转向窗子。
“他已经死了,”她终于说。“他死的时候才十七岁。那么年轻就死了不是很可怕吗?”
“他是干什么的?”加布里埃尔问,仍然带有讥讽意味。
“他在煤气厂工作,”她说。

加布里埃尔感到受了羞辱,因为讥讽落了空,也因为从死者引出这么一个人——一个在煤气厂工作的男孩。就在他全心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私生活,心里充满柔情、欢乐和欲望时,她却一直在心里把他和另一个人比较。一种对自我人格的羞辱意识袭上了他的心头。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滑稽的人物,扮演一个为姨妈跑腿挣小钱的人,一个神经质的、自作多情的感伤主义者,一个对一群庸俗的人大事演讲并把自己小丑般的欲望理想化,一个他在镜子里瞥见的那种可怜而愚蠢的家伙。他本能地转身背向光线,以免她会看见他额上燃烧着羞辱。
他极力保持他那冷冰冰的诘问语调,但他说话时声音却显得谦卑而冷漠。
“我想那时你爱上了这位迈克尔·福瑞,格丽塔,”他说。
“那时我和他非常亲密,”她说。
她的声音模糊而悲哀。加布里埃尔觉得现在若想把她引向自己原来设想的境地一定是徒劳无望,于是便抚摸着她的一只手,也不无悲伤地说:
“他那样年轻是怎么死的,格丽塔?痨病,是吗?”
“我想他是为我死的,”她答道。
这回答使加布里埃尔心中涌起一种朦朦胧胧的恐惧,仿佛在他希望获胜的时刻,某个无形的、蓄意报复的幽灵跟他作对,在它那个朦胧的世界里正纠集力量与他对抗。但他凭借理智的作用摆脱了那种恐惧,继续抚摸她的手。他不再问她,因为他觉得她会自己告诉他的。她的手温暖而潮湿:它没有对他的触摸作出反应,但他仍然抚摸它,就像那个春天的早晨他抚摸她给他的第一封信一样。
“那是在冬天,”她说,“大约是初冬时节,当时我正要离开祖母家到这里的修道院来。那时他在高尔韦的住所里病了,不能出门,并已写信告诉了他在奥特拉德的家人。人家说,他的病每况愈下,或者说大致是那样。我一直不十分清楚。”
她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可怜的人,”她说。“他非常喜欢我,而且是这么文静的一个男孩。我们常一块出去,散步,你知道,加布里埃尔,像在乡下人们常做的那样。要不是他身体不好,他就去学唱歌了。他有一副极好的嗓子,可怜的迈克尔·福瑞。”
“那么,后来呢?”加布里埃尔问。
“后来,等到我离开高尔韦来这里修道院的时候,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人家不让我见他,于是我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就要去都柏林了,夏天会回来,希望那时他会好起来。”她停了一会儿控制住自己的声音,然后继续说:
“后来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正在修女岛上我祖母家的房子里收拾东西,听到有扔石子打窗户的声音。窗玻璃全湿了,什么都看不见,于是我就那样跑下楼去,从后面溜进花园,在花园的尽头站着那个可怜的人,正浑身颤抖。”
“你没有叫他回去吗?”加布里埃尔问。
“我求他赶快回家去,告诉他淋在雨里会要了他的命。可是他说他不想活了。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眼睛,清清楚楚!他站在墙的尽头,那里有一棵树。”
“他回家去了吗?”加布里埃尔问。
“是的,他回去了。然而我到修道院刚一个星期他就死了,他埋在奥特拉德他老家那里。唉,我听说这事那天,他死的那天!”
她停下来,呜咽得说不出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脸朝下扑在床上,埋在被子里哭泣。加布里埃尔犹犹豫豫地又把她的手握了一会,由于害怕在她伤心的时候打扰她,后来便轻轻地放下她的手,默默地走向窗户。
她睡熟了。

加布里埃尔斜倚着臂肘,心平气和地看了一会她那蓬乱的头发和半启的嘴唇,听着她深沉的呼吸。原来她生活中有过那么一段浪漫故事:一个男人因为她而死去。现在想到他这个丈夫在她生活里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他几乎不再感到痛苦。他注视着正在熟睡的她,仿佛他和她从未像夫妻一样在一起生活过似的。他好奇的眼睛久久地望着她的脸庞和她的头发:当他想着她蓓蕾初绽之际该是什么样子时,一种奇怪的、对她友善的怜悯在他的心灵里升起。他甚至不愿对自己说她的脸庞已不再漂亮,但他知道那不再是迈克尔·福瑞为之慨然徇情的脸庞。
也许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他把目光移向椅子,上面扔着她的一些衣服。一条衬裙的带子垂到地板上。一只靴子直立着,但软靴筒塌了下去;另一只靴子躺在它的旁边。他对自己一小时前的情绪骚动感到奇怪。是什么引起的呢?是他姨妈的晚宴,他自己愚蠢的演讲,饮酒和跳舞,在前厅告别时的欢闹,或者沿河边在雪中散步的愉悦?可怜的朱丽娅姨妈!不久她也会成为一个幽灵,和帕特里克·莫肯以及他的马的幽灵在一起的幽灵。她唱《盛装待嫁》时,他曾在瞬间看见过她脸上憔悴的面容。或许不久他就会坐在那同一个客厅里,穿着黑色的衣服,丝帽放在膝上。窗帘被放下来,凯特姨妈坐在他身边,痛哭流涕地告诉他朱丽娅姨妈是如何死的。他会搜索枯肠地寻找一些可以安慰她的话,而结果却只是找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无用字句。是的,是的:那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
房间的空气使他的肩膀觉得寒冷。他小心地钻进被子里,在他妻子的身边躺下。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要变成幽灵。最好在某种激情全盛时期勇敢地进入那另一个世界,切莫随着年龄增长而凄凉地衰败枯萎。他想到躺在他身边的妻子,想到她多年来如何在心里深锁着她的情人告诉她不想活下去时的眼神。
大量的泪水充溢着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从未觉得自己对任何女人有那样的感情,但他知道,这样一种感情一定是爱情。他眼里积聚了更多的泪水,在半昏半睡中,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正站在一棵雨水嘀嗒的树下。附近是其他一些身影。他的灵魂已经接近了那个居住着大量死者的领域。他意识到他们扑朔迷离、忽隐忽现的存在,但却不能理解。他自己本身也在逐渐消失到一个灰色的无形世界:这个实在的世界本身,这些死者曾一度在这里养育生息的世界,正在渐渐消解和缩小。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 - 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相 关 书 单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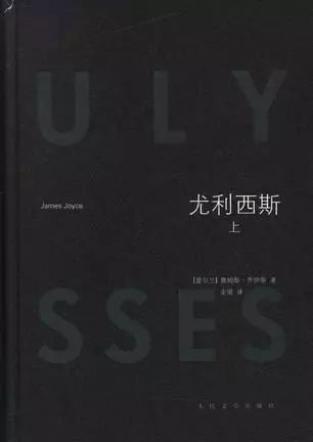
《尤利西斯》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金隄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介绍
《尤利西斯》是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于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日常经历。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语言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本书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并被誉为20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每年的6月16日已经被纪念为“布卢姆日”。
2

《都柏林人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徐晓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介绍
詹姆斯·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都柏林人》是他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置景于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横断面,一个片刻一群人,十五个故事汇集起来,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笔触简练,错落成篇,浮现出苍凉世态,遥远、清冷,然而精致,是上上之品。在同样的底色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集中描绘了一个忧郁敏感、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具有艺术家气质的青年形象。
3

《乔伊斯诗全集》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傅浩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内容介绍
乔伊斯虽然以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而闻名,但喜欢自视为诗人。尽管他的诗名没有小说的名气那么显赫,但他最初和最后的创作都是诗歌。本书囊括乔伊斯存世的全部诗作(及少量译诗),共160首(段),并加详细注释。
4

《致诺拉》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李宏伟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
内容介绍
本书一共收录乔伊斯写给诺拉的四十余封书信,字里行间,呈现出了现代文学的巨匠詹姆斯•乔伊斯感情丰富、感受敏锐、内心赤诚的一面。从这些细腻、痴缠、狂热的文字,人们或许能够找到他与诺拉何以情深如许的原因,或许能够明了乔伊斯在动荡不已的生活中,为什么总是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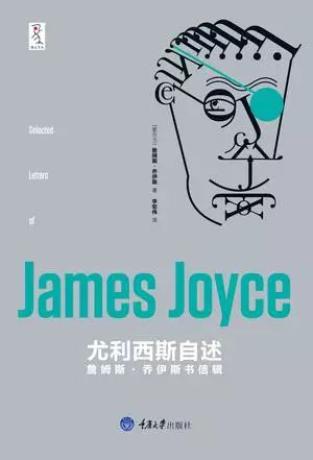
《尤利西斯自述》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译者:李宏伟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
内容介绍
本书为爱尔兰作家、现代文学巨匠乔伊斯的书信选集,共收录近三百封书信。以乔伊斯漂泊一生所停留的几座城市为标志,结合他在文学上创作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分为五部分。这些书信的主要内容有:给家人尤其是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倾吐心中苦闷、生活拮据的家书,给赞助人解释说明《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等作品创作缘由的信函,给叶芝、艾略特等同时代伟大作家的信件等等。
文字|选自《都柏林人》,[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王蓬振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
编辑|pao pao
原标题:《寥寥几笔,乔伊斯就写透了死亡与孤独》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