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玉|路易斯·麦克尼斯:“我为什么要回到你身边?”(上)

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
希尼在牛津诗歌讲座最后一讲“写作的边界”中提出一种尝试:让国土的边界与写作的边界一致,由此勾勒一个完整的文学传统。他将这个传统描绘为五塔阵,“第一座塔位于中央,代表最初的爱尔兰性,岛上原始的圆塔住宅,或许就坐落于路易斯·麦克尼斯所说的‘孕育之山’”;以此塔为中心,南塔是斯宾塞的基尔克曼城堡(Kilcolman Castle),亦是英格兰征服与爱尔兰英化之塔;西塔是叶芝的诺曼风格城堡巴里郦(Ballylee),象征着他通过诗歌去复原被斯宾塞的军队和语言所摧毁的精神价值的努力;东塔是乔伊斯的圆形石塔,位于都柏林湾,《尤利西斯》的开篇场景,体现乔伊斯“将爱尔兰岛希腊化”的尝试。斯宾塞的塔楼直面原始神秘的爱尔兰圆塔,看到教皇、野蛮和黑暗的中世纪;叶芝的塔楼面向它,看到可能的统一,一个通过收回盖尔文化遗产而重获新生的爱尔兰国家;乔伊斯的塔面向它,看到“一个重建秩序的肚脐”,或“一座象牙塔,爱尔兰天主教保守的贞女必须被解放出来,投身欧洲的世俗自由”。最后,从北边进来,是卡里克弗格斯城堡(Carrickfergus Castle)——麦克尼斯最坚固的塔楼:
这座塔楼,奥伦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曾在稳固新教继承权的途中着陆于此;世世代代为英军的驻扎之地;这座塔,在麦克尼斯的视野下,不再仅仅用回避的目光回顾光荣革命和议会之母,而且也能展望一个想象中的爱尔兰,其名字,用麦克尼斯的话来说,“始终如洪钟 / 回响在水下钟楼”。我以为,麦克尼斯以其英国原籍和文化教育,是斯宾塞的一个侧面;以其与康尼玛拉(Connemara)祖上及情感上的关联,是叶芝的一个侧面;以其神话的欧洲意识,是乔伊斯的一个侧面。通过将他的城堡写入诗歌编年史,他圆成了这个图表。他可以被视为一位爱尔兰新教作家,具有英国中心的态度,设法忠于他的厄尔斯特文化遗产、爱尔兰情感和英国喜好。这样,他为北方统一派想象某种完整的爱尔兰以及南方爱尔兰想象分治的北方同时提供了入口和出路。也许尚未有一种政治结构能反映这种诗意蓝图,但麦克尼斯以此方式进入爱尔兰的象征性秩序,也为一种政治秩序的演化带来了希望,一个能包容差异并善于在爱尔兰性、英国性、欧洲性、地球性、生物性以及任何特性的多重可能之间变通的秩序。(Seamus Heaney, “Frontiers of Writing”, in The Redress of Poetry, New York: FSG, 1995, p.14)
希尼认为,从五塔阵的北端进入爱尔兰是最佳的路径。本文即从麦克尼斯的北塔出发,探索这座堡垒如何与其他四座塔楼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个完满且开放的文学地理方阵。
麦克尼斯的北塔:“织物不能拆解它的线”

屹立在贝尔法斯特海湾北岸的卡里克弗格斯城堡
卡里克弗格斯城堡位于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屹立在贝尔法斯特海湾北岸,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诗人幼年时,为城堡的名字感到骄傲,因为传说“卡里克弗格斯”意为“巨人石”;但诗人的父亲即当地的牧师更倾向于“不那么浪漫”的说法——他根据学者的考证,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大海中的岩石”。无论怎样,卡里克弗格斯的历史就是“浓缩版的厄尔斯特历史”(Jon Stallworthy, Louis MacNei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5, p.14)。天气晴好时,这座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会在更加浩瀚的海面上投下轮廓模糊的倒影,影随柔波漾动。麦克尼斯的童年就在这巨大的阴影下度过:
我生于贝尔法斯特的山峦与高架之间
那里有远去的汽笛声和电车的轰鸣:
然后迁往安特里姆烟雾下的卡里克
窄若瓶颈的港口充满泥泞
阻塞诺曼城堡下的小小船只,
码头上闪烁着颗颗海盐晶体;
苏格兰区是一排居民的住宅
而爱尔兰区是瞎子瘸子的贫窟。
……
我是教区长之子,生来是国教徒,
永远无权点燃爱尔兰穷人的蜡烛
(《卡里克弗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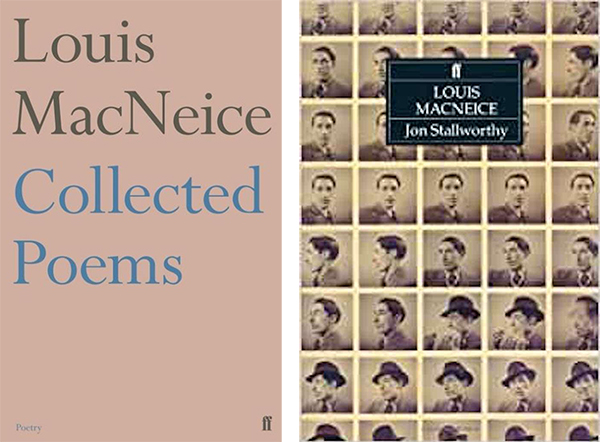
左:Louis MacNeice, Collected Poems, ed. Peter McDonal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7;右:Jon Stallworthy, Louis MacNei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5
麦克尼斯常常以地标记录心灵的成长,这首诗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童年生活。诗中充满对峙的意象:“山峦与高架之间”的逼仄地势象征着社会文化层面的窒息,“瓶颈”“阻塞”“监狱”(39行)“牢笼”(40行)等词语也不断加强这种压迫感。苏格兰区与爱尔兰区的贫富差异;诗人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来自爱尔兰西部,父亲是支持自治(Home Rule)的国教徒。麦克尼斯六岁时,母亲去世。“我以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一艘迷彩的蒸汽船把“我”送往英格兰,“我去多塞特上学”,从此开启他的两地状态(bilocation)。《死亡的征兆》(“Intimations of Mortality”)反写华兹华斯《不朽性的征兆》(“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追忆了北爱尔兰童年的不眠之夜。麦克尼斯在安特里姆的玄武岩中找到体现这种恐惧心境的意象:
北方人那坚硬冰冷的火
冰封在他的血液中,他玄武岩里的火
从他双眼的云母后发出强光
(《贝尔法斯特》)
对幼年麦克尼斯来说,北爱尔兰是一座监狱,南方是避难所——“北方是专制”。前往都柏林则成为暂时的逃避。旅途中,思绪飘渺如火车的烟雾,他无法把思想握在拳中。唯有透过疾驰的车窗,景物才因“不成比例”或者说偏离现实而显得美妙。在一组极富歌唱性的排比诗句中,诗人历数了“经过窗外空间的偶然事物”。“偶然”“随机”等词语暗示了无法把握与不确定性:
我给你不成比例的辛苦付出
与随机幸福:高威海峡的笑声
不负责任地抛出船木与尸骨,
我给你小小的利菲河与巨大的鸥鸟,
我给你金钟树篱和白石灰墙。
我给你诺曼石头的气息,脚下沼泽
发出的声响,殷红的沼泽草,
安特里姆群山鲜明的格子图案,壮马
饮水的黑金水槽,丽日
在海上铺开的黄铜条带。
……
我想给你更多但我无法把
这些握在手中而火车继续前行
(《开往都柏林的火车》)
麦克尼斯自称为“自己国家的旅客”,在爱尔兰找不到归属感。在《诀别》(Valediction)中,诗人不断停车游览,以走马观花的心境穿梭于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基拉尼等地:
把你的车停在都柏林市区,在老照片中
看没有沙袋的塞克维尔大街,会见
爱国者的雕像,历史不死,
至少在爱尔兰,放火杀人是遗产
像掉了钻的空眼窝的旧指环,
哑默的护符。
看看贝尔法斯特,虔诚世俗顽固,
建在回收的烂泥上,锤子在船坞里挥舞,
时间如钢板被击出疮孔,时间
磨砺面容,以苍苍风霜粉饰
头巾和帽檐下的面容:
这是我的母亲城

乔伊斯时期的都柏林,塞克维尔大街
把你的车停在基拉尼,买纪念品
诸如绿石子或黑沼橡,跑到克莱尔,
爬上明信片里的峭壁,拜访高威城,
浪漫我们的西班牙血统,在你的盘底
布施百分之十的悲悯给移民
诗人一边对爱尔兰发起攻击,一边就这种行为展开自省:“诅咒母亲者自遭诅咒。我无法成为 / 其他任何人,除了这片土地孕育的我。”在“我”的记忆深处,是白雾,是船帆,“当我敲击自己的思绪,钟绳甩动它们的尾巴”,发出轰鸣——“回忆即背叛”:
我可以说爱尔兰就是一派胡言,爱尔兰
画廊里面全是冒牌挂毯。
但我不能否认与之相连的过去,
织物不能拆解它的线。
最后,诗人宣布“要为我的血液驱魔 /以免婴儿的襁褓成为我的寿衣”:
并成为你的假日游客,
无论我多么频繁地往来,
别了,我的国,永别
三十年后,诗人回到卡里克,城堡坚固如初,堤岸青碧如故,海水微茫和缓,受惊的儿童尚未好转。诗人“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地貌框架中”:
我们的过去我们知道
但不知它的意义——是否它意头好。
时间与地点——我们伸入现实的桥头阵地
但也是它的屏蔽!离开大海
我们登陆具体的地点而失去
所有可能的鸟瞰之景,真理
源于它本身也为它本身——但不为我。
希尼在这首诗中看到麦克尼斯的双焦距和两地性。他将麦克尼斯与另一位爱尔兰诗人约翰·休伊特进行比较,认为休伊特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北爱尔兰,而路易斯·麦克尼斯则体现了“一个在挣扎中准备诞生的北爱尔兰,容许一部分公民的爱尔兰性并不会损害另一些人的英国性”:
无论我继承的还是习得的
特性,业已成为我童年的框架
仿佛安特里姆红土中迟来的岩石
现如今无法改变它的层次或名姓——
而那孕育之山杳无踪迹。
他指出,《重返卡里克》(Carrick Revisited)体现了麦克尼斯既在两地又超然域外的忠诚。他认为,这首诗的写作源于一种需要,即“跨越自我分界地带,使自己继承的特性与习得的特性和谐共处”:
这就好像麦克尼斯在自身中同时联合了新英格兰人和印第安人。他视自己的北爱尔兰出生地——他的宿命,他进入现实的桥头阵地——为某种既不能取消也不能捍卫的事物。如同休伊特,他成长于分治前的爱尔兰,但是,不同于休伊特,他不允许边界进入他此后的想象:他关于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和历史意义的观念从未凝结为一张红绿相间的地图。在麦克尼斯的心中,这些色彩融汇——或者说如鲜血流入——彼此。他在梅奥(Mayo)的祖先赋予他一个南方的梦中故乡,弥补他在北方的现实故土,而定居英格兰则赋予他一种批评视角,以此看待早先北方环境中特殊的英国性。(Seamus Heaney, “Frontiers of Writing”, in The Redress of Poetry, New York: FSG, 1995, p.198)
《叶芝传》作者罗伊·福斯特也指出:“我们不必放弃自身对爱尔兰性的诉求去想象一种变通的爱尔兰性。在一个东西方共同面对的排外主义圣战时代,能调和多重文化身份的观念尤其值得推崇。”(R. F. Foster, Paddy and Mr Punch: Connections in Irish and English History, Penguin: 1993, p.xvii)他还认为,在关注爱尔兰独立问题的诗人中,叶芝之后当属麦克尼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