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感官城市|上海南京路的气味与情感地图
本文来自爱丁堡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讲者黄雪蕾,在2022年12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校级学术讲座上的分享,包括讲座及互动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春田主持。

2022年3月,上海南京路。高征 图
气味非常重要,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反应和神经反射过程,其背后蕴含着许多价值和意义。
我原先是做电影史的,将近十年前对感官气味研究发生兴趣。新世纪以来,感官研究在国际上方兴未艾,一开始主要由人类学家发起,之后波及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当然,这跟整个大的研究背景,对身体的关注、情感转向等,都有着深刻关联。
南京路好像可被理解为中国现代性的切片。它是上海开埠后,英国侨民在1840年代最早修筑的马路之一,日后发展成整个公共租界的轴心。它基本上是殖民现代性的物质象征,包含了消费主义、现代技术、卫生秩序、中产阶级、世界主义、阶级差序等等。1949年后,它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后,它又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成为旅游地标。
因为复杂的历史和地标价值,可以将它视作一个地理文化文本来考察。
凯文·林奇是城市规划和文化地理学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在城市规划中,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是the mental image。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只是方位地形,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图像。这个精神图像(mental image),是直接的感官认识,加上记忆和历史经验的叠加构成的。他探讨城市,用了绘制认知和情感的地图(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apping)的概念。后来这个词被文学史研究者使用,从地理学拓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
凯文·林奇的书里认为,mental image主要由三部分组成,identity、structure and meaning,人的感官感知,也是形塑所有这些要素的重要媒介。从这个框架出发,我的研究截取了一个长时间段中的三个片段,来看南京路的气味和情感地图的变化。
1850年代是形塑南京路identity的重要阶段。就感官而言,“祛味”(deodorization)是突出特点。随后一个世纪,南京路的空间结构和意义日趋复杂。到了1930年代,南京路最重要的精神图像,跟物质主义和奢靡相关。到了1950、1960年代,我想强调的是,“再祛味”(Re-deodorization)的操作是如何进行的。
先来看1850年代形塑的嗅觉形象。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它放到全球史背景中。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西方的大都会,比如伦敦、巴黎等,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纷纷开始大规模城市改造工程。Kevin Lynch在书里提到,现代城市规划中,都市空间的可读性是个重要考量,嗅觉无疑也被调动去读解空间,去形塑空间的可读性。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兴起于1840年代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这跟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恶化息息相关。英国的议会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卫生事务,把卫生问题放到了公共领域。当时流行理论认为,臭气、瘴气会引发疾病,因此“祛味”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普遍认为的现代气味革命的开端之一。
还有殖民话语中的感官等级秩序。当时的西方人游记作品中,印度、非洲等殖民地和人民都被打上脏臭标签。关于中国“China stinks”的论述也不胜枚举。
总之,在这几个综合要素作用下,英国侨民来到上海开始建设南京路时,有意无意把“祛味”作为打造城市空间的重要指标。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对南京路的metal image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实际政策和操作层面之外,我想首先强调隐形的,对时间、身体和记忆的操控。
来看1856年7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一段记录。它是有关南京路粪秽和气味管理的第一则我能找到的记录。一位殖民官员被指派在早上6:00-8:00,驻扎一艘船在福记码头。Park Lane是南京路的前身,街上所有住户,必须在这个时间点把“filth”(基本是指粪秽)倒到这艘船上。为保障实施这一措施,他们还派了一名“苦力”监督,而且是佩戴徽章的。
这里可以看到殖民现代性管理的一些典型要素。这次会议记录,不仅说明了粪秽在殖民卫生管理中的重要性,也可看到现代性中的时间感与身体感的再塑造。
整个工部局会议记录反复提到中国人太不遵守时间秩序。叶文心教授研究民国上海企业文化时,强调了海关大钟的意义,这一机械装置设定了一个公共时间,将其内化到城市生活和市民感知中。这个例子中,南京路的气味地图与时间感被人为勾连起来,形塑了南京路这一独特的identity。当时对华人社会来说,南京路的管理跟华人市政管理形成鲜明差异,《申报》等中文报纸上有许多讨论。此外,感官感受会成为记忆,层层累加,变成城市精神图像的一部分。
再举个小例子。1938年的《字林西报》上,刊登了名叫Stinky的读者来信,是一位法国人,他抱怨早上上班路上,总跟粪车发出的刺鼻臭味相遇。他建议,法租界当局应该分发一些法国香水,比如Lentheric这个品牌1930年代开发出的名为“上海”的香水。他又开玩笑说,调香师的灵感一定不是早晨八点的上海领事馆路的味道。
这样的历史文本,带领我们去想象这座城市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又与化妆品工业和香水的物质文化勾连起来,对文化记忆的形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再看一个比较具体的气味管理的操作手段。当时管理气味,尤其在上海,重要的手段是填平沟壑。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天然地貌沟渠纵横。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中,沟渠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西方公共卫生理论中,水,尤其是死水臭水,被视为天敌,加上新的生产和交通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引入,上海的沟渠在19世纪后半期被大量填埋。即使非常小的坑洼,也被认为是滋生臭气污染的温床。早期工部局会议录中,有无数记录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技术手段是修建下水道。巴黎和伦敦的下水道,成为19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化身,上海的下水道修建几乎同期展开。1860年左右,当时英国侨民已开始修建下水道网络。南京路是网络上的重要轴线。下水道在文学想象和感官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义。将污秽驱逐出视觉、嗅觉的感官场域,也是西方现代性的胜利主义的物理象征。这一提升现代都市可读性的过程,也意味着生态的人为重构和感官感受的再分配。而且,这样的重构和再分配往往是权力不对等的产物。
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的巅峰。这座半殖民地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图像,与物质主义、世界主义和奢靡颓废紧密相连,留存到今天的“魔都”形象。
气味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可以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刘呐鸥的短篇小说《礼仪和卫生》,发表于1930年代,是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作者描画了南京路街道的三种空间类型,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气味和感官感受。
先看第一种空间类型。它是现代办公楼,主要集中在南京路靠近外滩的地方。男主人公启明是一位律师,在写字楼上班。他替一位太太打赢离婚官司后,在阔太太中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办公室里每天都有绸缎的摩擦声和香水胭脂的气味。
接下来一段,更详细地描绘了这样一个春日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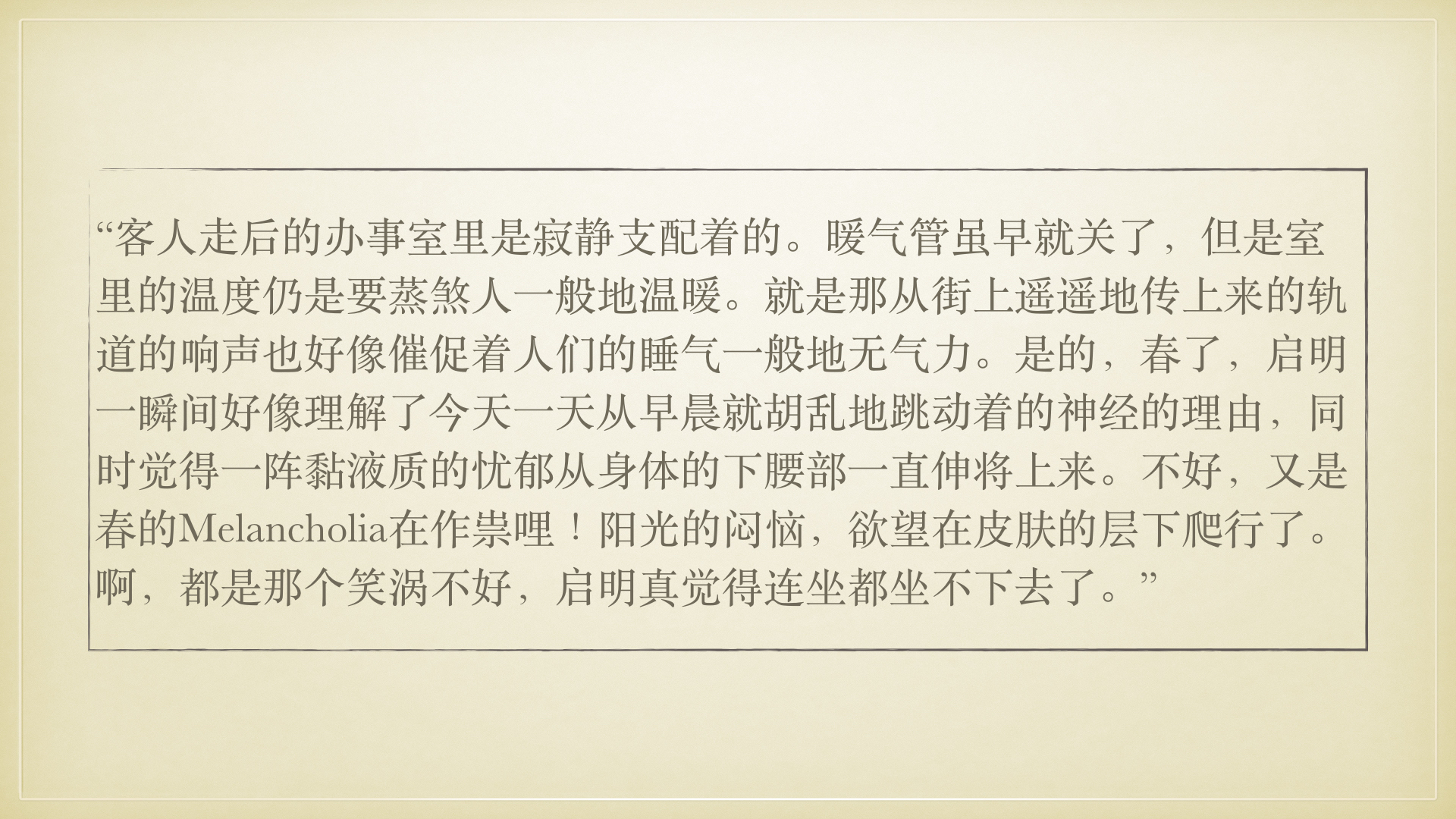
这是典型的新感觉派的描述,强调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的综合体验,令男主人公欲望蠢动。现代办公空间里的气味和感官感受,其他新感觉派作品中也常出现。比如,穆时英的《烟》里描述男主人公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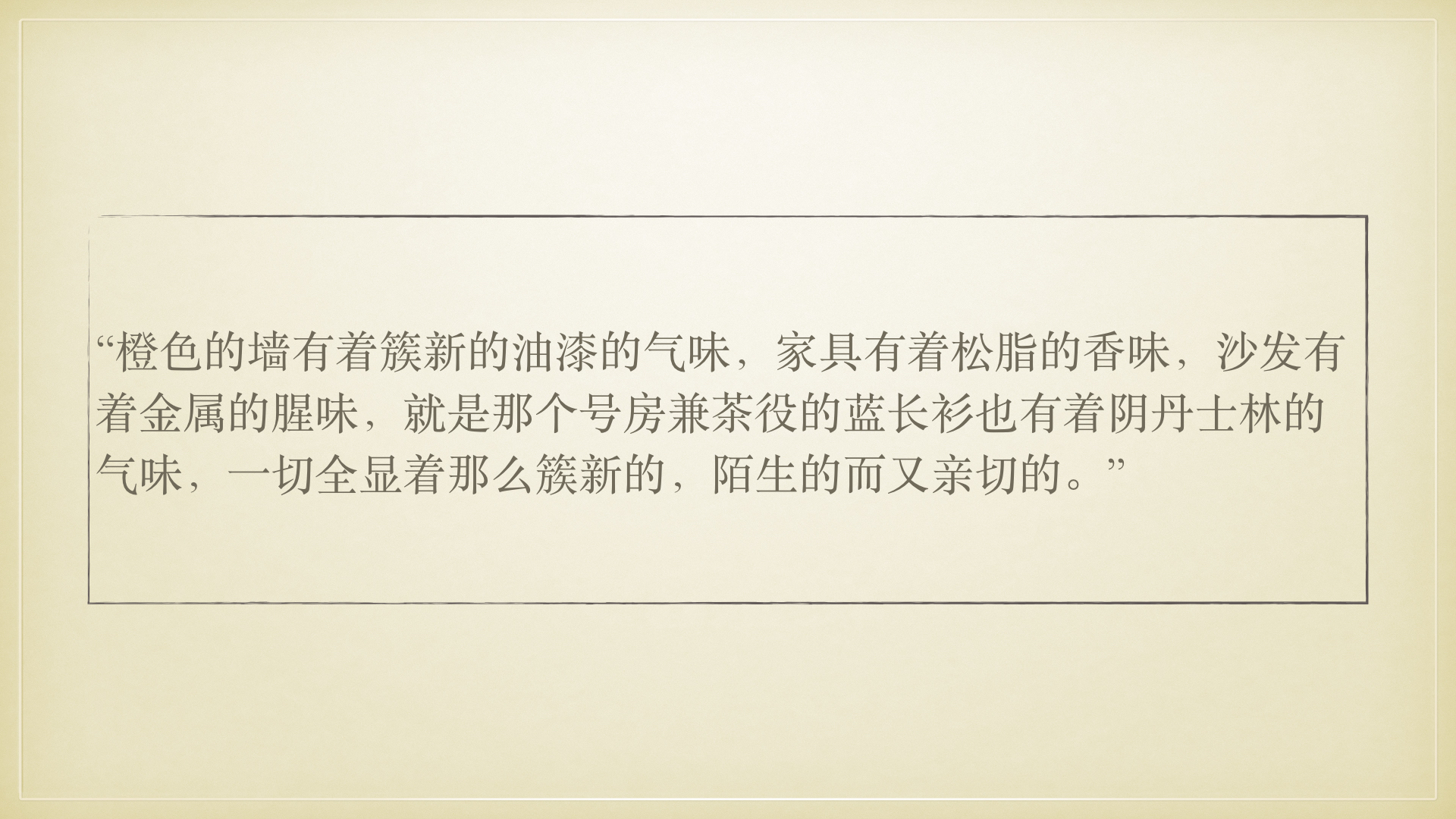
穆时英的短篇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中有一段,讲一位医生的感官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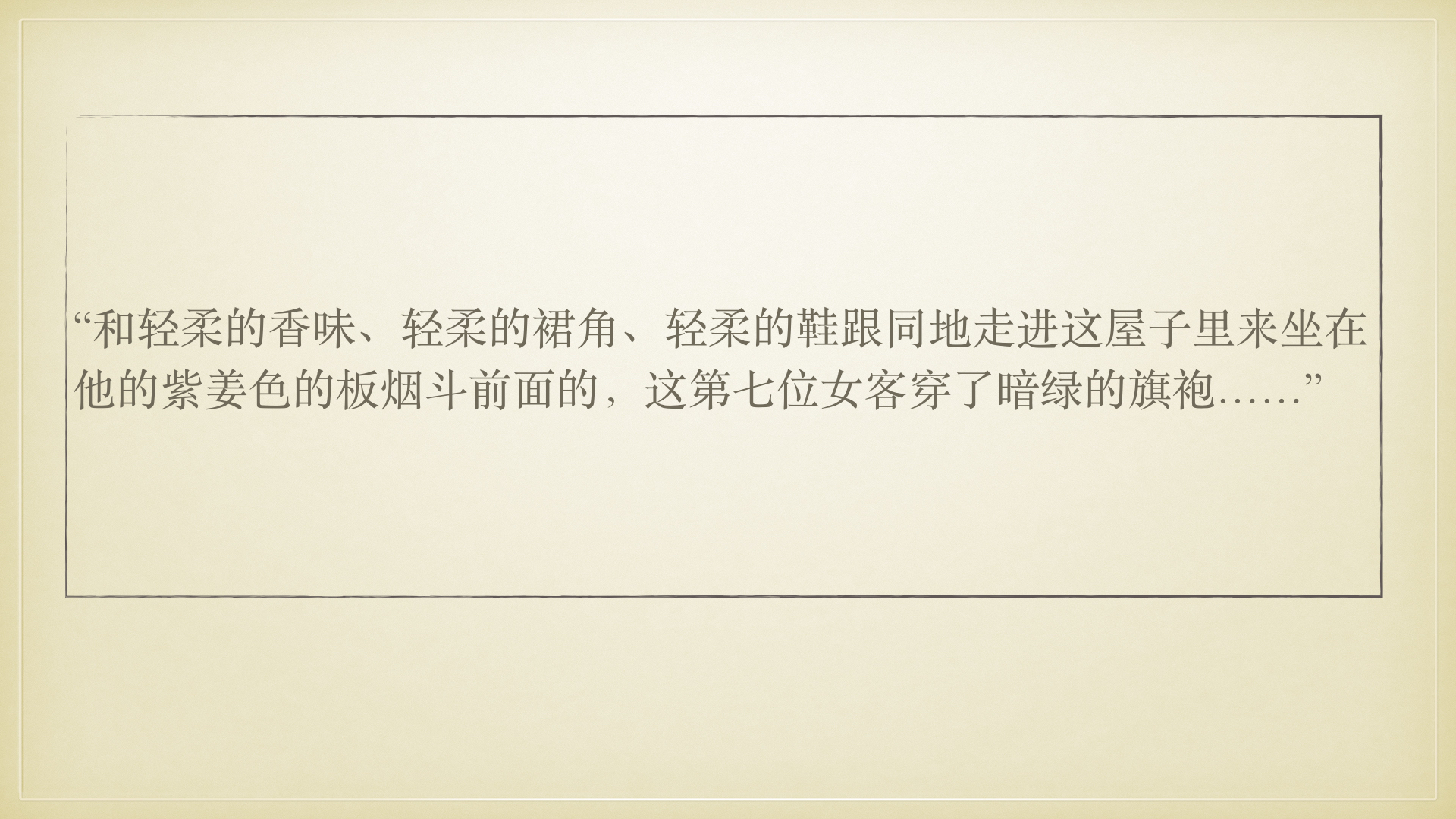
南京路上的写字楼,延续了1850年代以来的祛味理念。另一方面,这些空间也是对女性开放的,因此变成了一个欲望公共化的场所。感官,尤其是嗅觉,是重要的中介,其中也涉及性别资本的交换,某种意义上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差序。
让我们再回到《礼仪和卫生》。律师启明在办公室被挑动起欲望之后,决定提早下班,下楼来到南京路上。这一段调动了各种感官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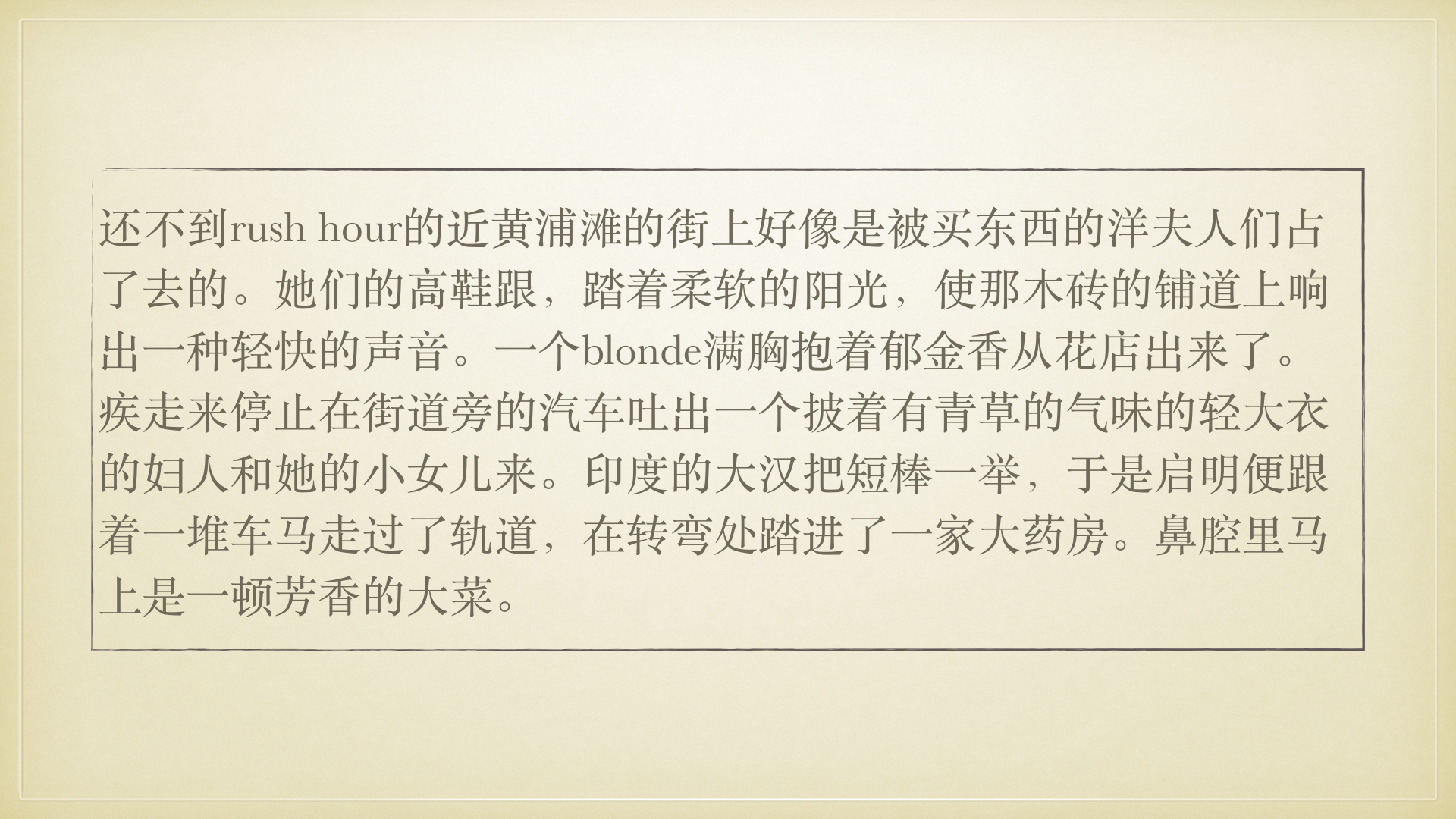
当他来到药房时,出现这样一段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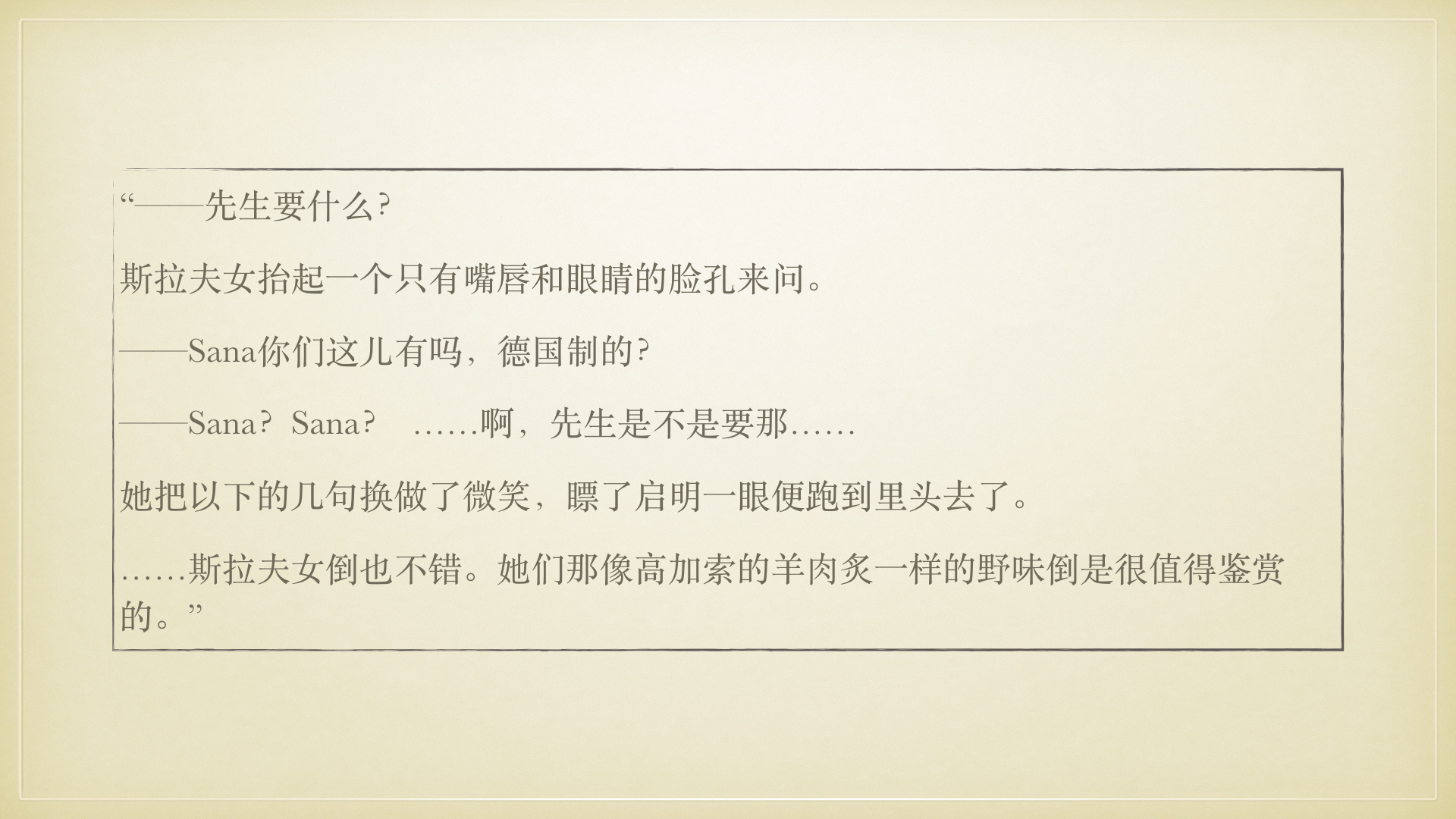
这段描述怎样解读?南京路的街道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主义的感官和权力游戏,也是半殖民地的现实图景。洋太太携带花香和青草的气味。低了一等的斯拉夫女,则散发野味的气息,更挑动欲望。对黄种人启明来说,他享受这种暧昧的欲望投射。嗅觉是一种既亲密又隐秘的媒介,但真正满足欲望的对象,要去别处寻找。
他去哪里寻找欲望的实现呢?——是离南京路不太远的一条弄堂。这里又有一段描述:

这里充分体现了分化的种族-空间结构。弄堂里市民生活的空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或南京路街区的精神图像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启明的感官感受,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上海弄堂蒙上一层异国情调。作为一名高等华人,他采纳了西方人的视角。至于满足自身身体欲望的具体对象,他选择的是一位中国的妓女。所以,半殖民地世界的分裂感也包括身心的分裂,而感官是折射意识形态的介质。
最后来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路的气味地图是如何被重塑的。这个文本以南京路为背景,叫《霓虹灯下的哨兵》,是1962年首演的舞台剧,1964年改编成电影。
作品缘起是1959年开始的“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好八连是参与解放上海的一支连队,被派驻到南京路。将好八连列为标兵,与南京路的象征意义有关。只有抵挡住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和香风毒草,社会主义才能够站稳脚跟。南京路的奢靡感官空间,必须被赋予新的意义。
有趣的是,刘呐鸥作品中的三种空间类型,也出现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气味同样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媒介。
开头几位反面人物出场的空间,类似启明的现代办公楼。两个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特务走进这栋楼,说了这句台词:“让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台词充满了感官上的刺激性。南京路的香气,与霉味、腐味形成鲜明对照。写字楼空间象征旧的秩序。新与旧的对决也是香与臭的对决。
整出戏的剧情主要发生在南京路的街道上。第二场开幕是这样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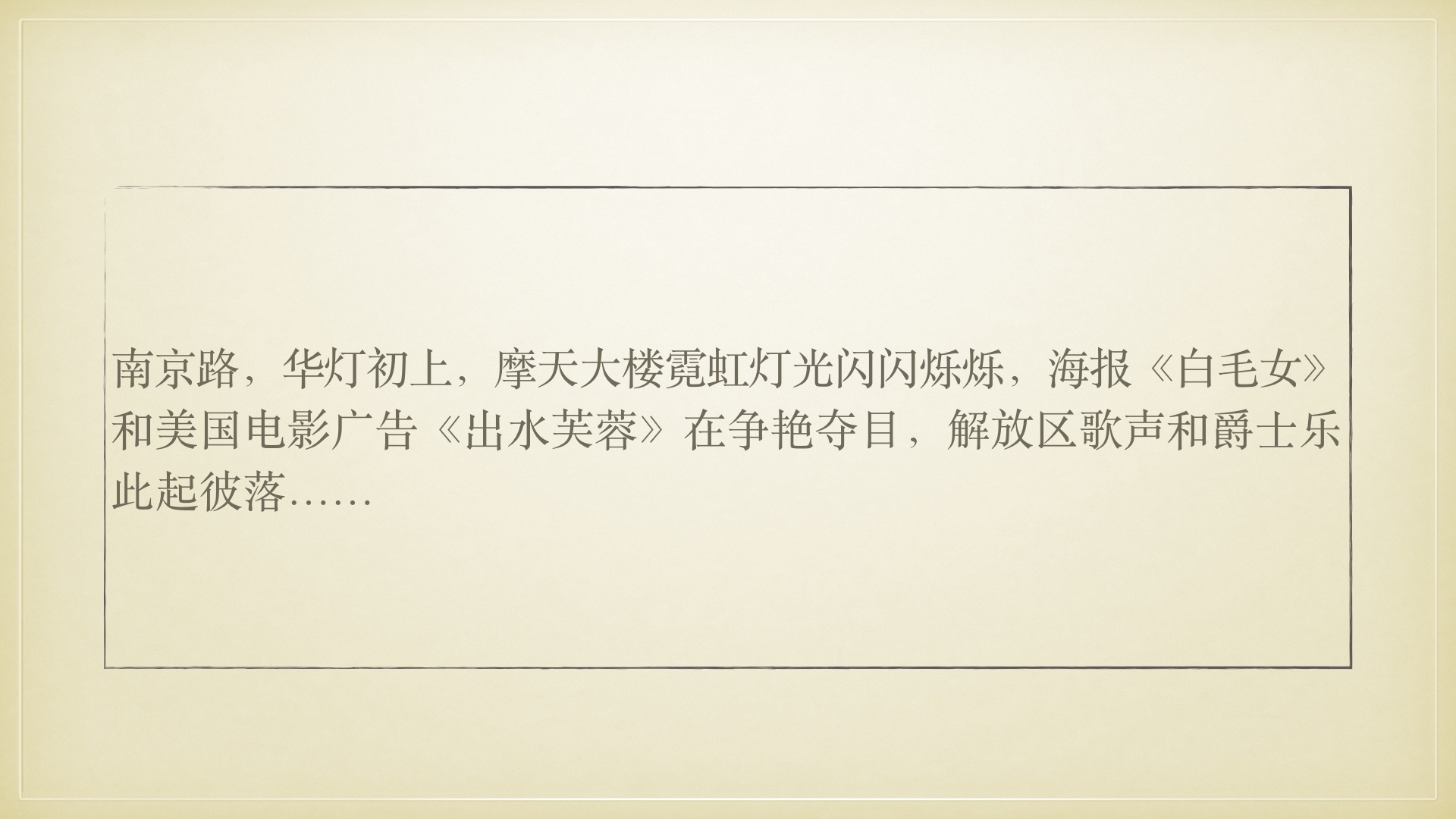
剧照上可以感受到大街上香水胭脂的气息。这里有先施公司的橱窗,还有穿着旗袍的女士。
下一幕,一位叫做赵大大的解放军战士在南京路巡逻,遇到一个卖花女叫做阿香。
阿香问赵大大说,夜来香要吧。赵大大赶紧躲开,阿香还是抓住不放。赵大大则继续背身。阿香强调说,花是香花,你看看,白兰花、栀子花、茉莉花、玳玳花,还有夜来香。随便捡一枝回去,放在房间里,到夜里保证特别的香,你太太一定会喜欢。赵大大不知所措,继续用语言强调,小大姐请你站得远一点,好不好?阿香说,那好吧,我不要你钱,你就去闻一闻,然后把花送到赵大大面前。赵大大继续回避,把鼻子捂起来。
这段话让我们联想到刘呐鸥笔下南京路的春日。但跟启明不同,赵大大把感官刺激和欲望剥离了开来。他把欲望放在献身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中,这当然是该剧的核心思想。有趣的是,也非常符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编剧还安排了一位动摇的战士陈喜。陈喜也是好八连的一位战士,在南京路上被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时他的爱人从老家过来,她非常热切地望着陈喜,而陈喜眼光中似乎有一些尴尬的表情。后来的对话显示,陈喜嫌她穿的衣服太土。
因为陈喜非常享受南京路的香气,就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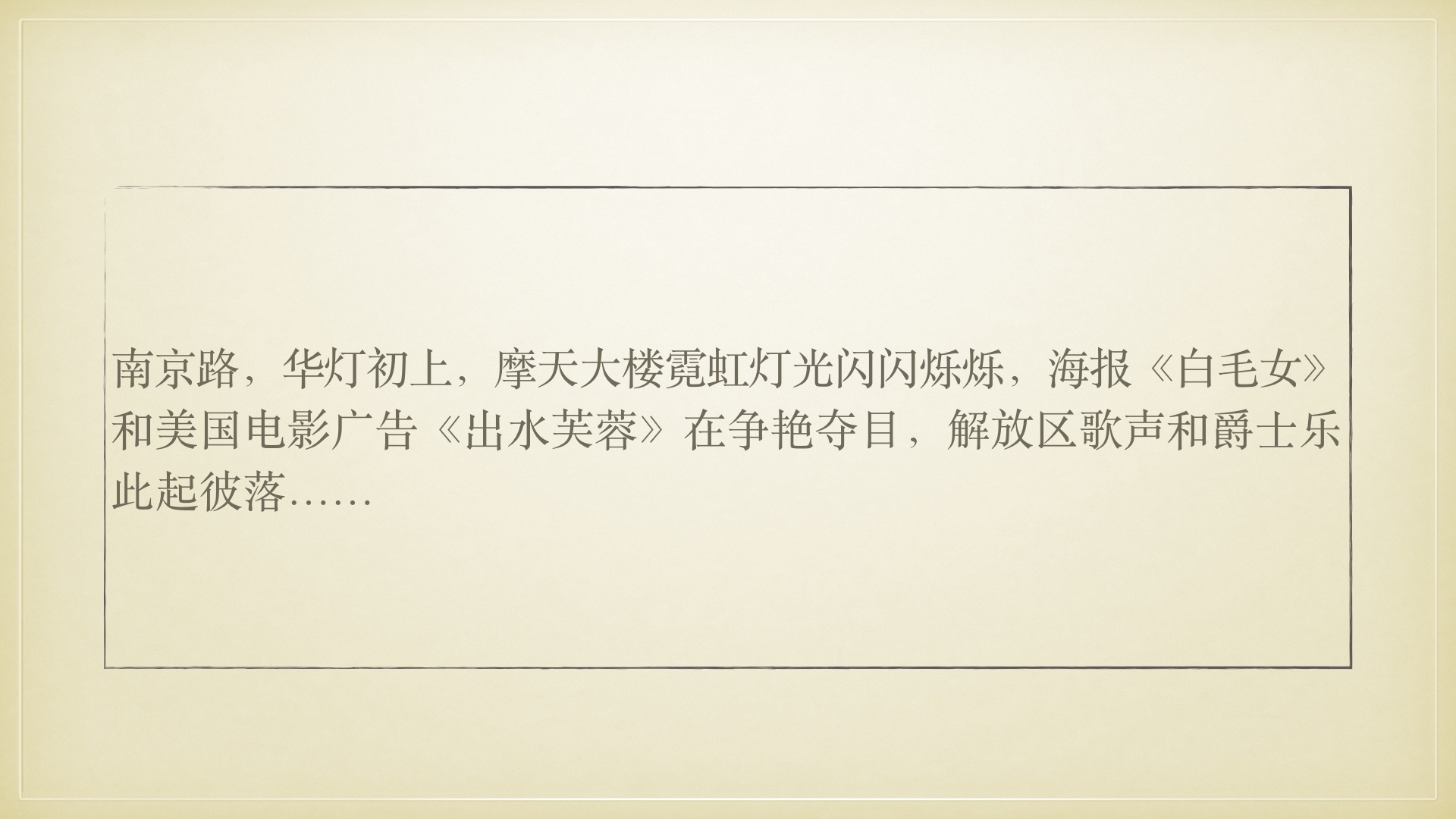
最终,陈喜这个反面教材,被转化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功能也在感官转化过程中彰显。香风一词,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流行语,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这些政治上的惯用语,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再看一个空间,是南京路周边的弄堂。这里又有一段卖花女阿香跟赵大大的戏。阿香因无力偿还欠债而遭遇毒打,将被贩卖到香港。赵大大出现解救了阿香,还给她还债的钱,令她感激涕零。这个弄堂大致应该是启明买春的街区,启明的故事里,它是半殖民主义夹缝中的情色空间,是满足小资产阶级个人欲望的场所。但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同样的弄堂空间,意涵更为单一。它是以南京路为代表的殖民现代性的对立面,是劳苦大众受压迫的象征性空间。
赵大大扮演的不是寻乐者,而是救赎者。他呼吸着劳动人民的气息,满足的是抽象的集体和国族的欲望。把这个场景跟前面的卖花场景放在一起,大家更可以体会到,欲望与感官是如何被剥离的。
有关弄堂空间,还有第六场的棚户区。根据剧本描述,它离南京路不太远。苏州河边上,当时有许多棚户区。电影画面中,我们仿佛闻到潮湿污秽的气息。剧本还提到馄饨的香气和五香茶叶蛋的味道,阿香的母亲去点香求菩萨保佑女儿不要被拐卖到香港。当然,菩萨没有帮助到他们,最终是解放军解救了阿香。在这里,城市的精神图像被二元化。棚户区和弄堂,是贫穷、迷信和绝望的化身,而馄饨和茶叶蛋的香气是人民的感官指涉,他们等待救赎。
来看一处非常有意思的尾声,是在红玫瑰和白玫瑰的香氛中做结。这幕戏发生在南京路的花店,间谍和解放军分别买了一束白玫瑰、一束红玫瑰。接下来场景发生在咖啡馆,咖啡馆的味道是殖民现代性的化身。但最终,南京路花店的味道和咖啡馆的意涵都被翻转,变成了敌我斗争的道具。间谍在白玫瑰中装了一颗定时炸弹,被手持红玫瑰的解放军识破。红玫瑰战胜了白玫瑰,从色彩符号学上,也象征了共产主义的胜利。
由此,可以看到南京路的气味地图得以重塑,所有新的意义都建立在旧的意义的基础上。所以,一座城市的精神图像,是在感官感受中层层累加,与历史紧密相连。
我简单报告到这。最后想以2022年底的南京路作结。人们戴着口罩,也可能嗅觉失灵。你闻到的南京路是什么样的气味,跟当下的历史又怎样勾连呢?它一定会化作我们个体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提问:气味分很多种,不仅是香和臭,背后的谱系,牵扯到心理机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个人经验,比如闻到气味产生情绪变化,导向什么样的研究。有没有一些感官史入门的书籍,或是研究方法导向性的理论著作?
答:香和臭中间有着广阔的谱系,但目前多数气味研究的书,重点聚焦在香臭两极。尤其是除臭。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瘴气与黄水仙:18—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ce: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可说是嗅觉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书里写的除臭与现代性,变成了主流的研究取径。
关于香和臭中间,细微的个人经验和感受,引发的情绪和心理机制,非常值得做感官研究的去探索。人对气味的感受,有很大的模糊空间,也被现代科学所印证。同样的化学分子,在不同情境中闻,会闻到不一样的气味。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视觉处理机制有比较清晰的模式,但嗅觉对应模式不明显,不是“一就是一”。闻到某个味道,觉得是香是臭,有很多阐释空间。
对于香和臭两极化的想法的反思,也跟当下后结构主义有关。我们试图重新建构一个并不是被启蒙主义的二元分化、理性和感性这种图谱决定的视野。关于感官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切入的话语。人的个体经验,包括正经历的疫情等,每一个人的感官感受、身体感受,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变化,无法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规约。
至于感官史入门的教科书,David Howes,康斯坦丝•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编了很多书。两位加拿大人类学家编的书不只涵盖人类学领域。2018年,David Howes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感官研究丛书(Senses and Sensat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2014年克拉森编了关于感官史的六卷本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是通史性的丛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当代,但重点局限在西方。这两套丛书中涉及的非西方的研究都很少。。
提问:当前景观史的研究,强调人对景观的认知和再形塑,也更强调视觉。这是对前面研究的反思和突破吗?另外,感官史和景观史的关系,不知是怎样的。
答:你提到,景观史强调人对感官的再形塑,人类学家早期引入感官研究时,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与其非常接近。就是说,感官过去好像只是科学家研究的范畴,现在强调感官是文化和社会去形塑的,他们喜欢用的词,是“culturally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这个论点今天并不稀奇。我想强调,某种程度上应跨越这样一个论述,重新思索景观本身,或感官本身、化学本身:当病毒把你的嗅觉神经破坏,瞬间什么都闻不到时,这种体验对我们理解文化和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十年前开始做气味研究时,我也主要想看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到底怎样形塑感官。直到最后快要写完全书时,才有更深一步反思。
近些年人文学术的发展,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后人类中心主义(posthumanism)等,都是比较前沿的视角。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让我们从人的角度稍微往后退一步,试图从动物的、环境的、物的角度,去看这个地球。尤其是2020年以后,疫情及环境问题,给了我们深刻触动。“人类中心主义”看问题的方式,到了值得反思的时间点。
提问:当我们从作品中捕捉到这样一些嗅觉元素,可以怎么向“嗅觉”发起正面强攻,关联到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命题?另外,比如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中,当时有没有去争夺、重新再造嗅觉?
答:古典文学宝库里,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材料。2022年10月我在台湾的中央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做了一个演讲,当时讲了红楼梦。我不是专门从事明清研究的学者,交流时听到不少有意思的反馈,从明清文学或更早期文学,都可以重新思索中国传统的感官视角。
怎样就嗅觉谈嗅觉。我想说的是,不谈外围,是不可能的。气味不只是感官的问题,它总是关联很多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嗅觉谈嗅觉,我想到科学和人文跨界的取径。两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Smellosophy。作者是一位科学史研究者,她的方法是采访很多科学家,写了类似嗅觉的科普读本。一个启发是,可以从神经元和分子的角度寻找答案,虽然未必一定能找到。当然,真正操作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没有科学训练,要讨论那些分子式有很大难度。但我读那本书读得入迷,它带领你进入脑神经元,去读解周边的气味环境。
第二个问题,关于左翼文学怎样争夺、重塑嗅觉,我自己书里有一章处理二十年代的创造社及鲁迅和茅盾。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中关于身体和情欲的味道。
除情色小说之外,古典小说中,对身体和情欲的味道,往往是概念化的,主要用兰麝一笔带过。到了二十年代,有个很重要的转向,对身体的描述开始采用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视角。
比如,闻到一个女性的香味,张资平会说,闻到一种弱醇性的呼吸的气味,而不再是兰麝了。这里透射出很重要的近代身体观和感官文化的变化。
前两年复旦大学康凌老师的著作《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讨论了诗歌中的身体技艺,是从声音的角度处理的,从诗歌带来的声音感中,讨论诗歌怎样与身体关联,是研究革命的一种不同取径。左翼文学中,我相信一定也有许多跟气味相关的,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