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克洛尔的隐匿、谵妄和国际主义
航行伊始,马克洛尔便闻到了厄运的气味,像是从“恶心的温热坟墓”散发出来。即便如此,他依旧像个偏执狂般逆流而上,穿过雨林,渡过险滩,奔赴谜一样飘忽不定的行程。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拨开索然无味的缕缕时光,不让他滑向那即将战胜他的虚无。读完《阿尔米兰特之雪》,许志强说:“非理性的洞察,打破人生的通俗教义以及对因果联系的寻常认知,试图将每一时刻的体验转化为‘我存在’的释义,这些便是马克洛尔的追求。”
马克洛尔的隐匿、谵妄和国际主义
许志强
一
《阿尔米兰特之雪》是系列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的第一部,原先是作者阿尔瓦罗·穆蒂斯创作的一首散文诗,在编辑这首散文诗的法语版时作者意识到,应该把它写成小说。他便写成了这部中译本近一百页的长篇小说。也许在作者看来它像是系列小说的一个引子,于是他又创作了另外六部小说。穆蒂斯在六十岁时开始创作,六年内写完七部长篇,于一九九七年结集出版马克洛尔七部曲,轰动西语文坛。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穆蒂斯 著
轩乐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2年9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的朋友穆蒂斯》一文中描写穆蒂斯,道出了一个作家的观察——“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名至实归”。换言之,不管是飞翔还是落地,诗人总是让人刮目相看,他们的精神高深莫测,行事不合常规;你看穆蒂斯,早不写晚不写,等到六十岁才写,一写就写七部,委实令人惊叹。书中有一个句子——“肥厚的花瓣里有迟缓而透明的蜜”,像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马克洛尔这个人物,最初出现在作者十九岁时写的一首诗中,和马尔克斯构思马孔多一样,很早就开始孕育了。在题为《阿尔米兰特之雪》的散文诗中,这位仿佛和作者一起步入暮年的人物,在高山旅店墙壁上留下了被人们记诵的遗言,例如——
“我是毫无条理的制造者,制造出了最隐秘的路径与最隐秘的码头。它们的无用和偏僻滋养着我的生命。”
“追随舰船而去吧。沿破旧、悲伤的船只犁出的航线行驶吧。不要停泊。避开哪怕最不起眼的可下锚的地方。溯流而上。顺流而下。在打湿床单的雨水中迷失。要拒绝堤岸。”
高山旅店的名称叫做“阿尔米兰特之雪”,店主人马克洛尔,自称“瞭望员”。他的格言说“要拒绝堤岸”,而他却隐居于高山之巅。这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我们只能从隐喻的意义上去理解;“拒绝堤岸”的意思是说,不管身在何处都要保持疏离,要制造偏僻和野性,要迷失于蒙蒙细雨之中。
散文诗为马克洛尔这个人物定下了调子。他涂写的警句格言,可以说是破解其生平故事的密码。或者不妨设想,作家穆蒂斯在写下这些包含河流和航行的句子时,他就意识到,他终归是要把水手马克洛尔写成一个小说人物的。这个人物在系列小说第一部中登场,带着一种奇怪的宿命感,开始书写他的“奇遇与厄运”。七部曲系列小说会把一个陌生的人物变成我们亲近的朋友。他,桅楼瞭望员马克洛尔,会成为你亲近的朋友吗?此书中译本将近七百页,你会有足够的机会走近他,与他同行。
摄影 | 寻找哥本哈根
二
马克洛尔的故事,封面标题让人以为是旧时代的海洋小说,英美文学中才会经常读到的水手和帆船的故事。第一部《阿尔米兰特之雪》是马克洛尔撰写的日记,叙事人假托于某地发现日记手稿,便将它们编辑出版,这也是旧时代小说常用的手法。该篇的外壳看似有点古旧,内核则是充满隐喻和内省;它是一篇讲述旅行、冒险、梦幻和征兆的小说,有浓郁的拉美文学的风味。
故事说的是马克洛尔在苏兰朵河里的航行,溯河而上,去往上游一座木材加工厂运送木材;途中遭遇意外和艰险,遇到土著和军人,差点被军人绑架;马克洛尔患上井热病,死里逃生,而船长病逝了;他们渡过湍流险滩,最终抵达目的地,发现木材加工厂是热带雨林中一个神秘的场所,由军人把守,游击队和政府军正在争夺这些设施;马克洛尔没有做成木材生意,他搭乘卡车离开,前往“阿尔米兰特之雪”旅店,而那艘船在返航时沉没,无一人幸存。
摄影 | 寻找哥本哈根
从故事情节推测,马克洛尔的航行应是在他的暮年,其航行生涯临近尾声之时,因为接下来是高山隐居,他将在旅店墙壁上涂写临终遗言了。难怪他在苏兰朵河上的航行充满了回忆,是对此前航行的回忆和总结。这也说明,《阿尔米兰特之雪》并不是计划中的七部曲的引子,作者原先可能并无这样的计划,而是只想写这一部小说。我们看到,七部曲系列小说不是讲述人物成长和变化的线性叙述;它的时间是回旋的,从接近终点的某个时刻开始回溯,进入人物特定时段的生活。这个回旋的时间在第一部中形成,就不会再有变化了;《阿尔米兰特之雪》的时间结构将在系列小说中一次次复现,成为它的翻版。
指出这一点是想要说明,马克洛尔的故事正如马塞尔的故事(《追忆似水年华》),其叙述时间和回忆时间是通过瞬间重叠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让小说的叙述在自由联想中出入;换句话说,马克洛尔的故事是以一种复合的方式展开,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精神历程和生活历程,在自由联想的万花筒中聚合,类似于普鲁斯特的“玫瑰花饰圆窗”结构,其大幅度展开(七部曲系列小说)的动力学法则就包含在这个结构中,而非取决于素材的数量以及社会图景的幅度与规模。
普鲁斯特的精神在穆蒂斯的创作中作用最为明显,它影响了马克洛尔故事的展开方式。以第一部《阿尔米兰特之雪》为例,我们看到,它的展开并非像前面梗概讲的那样,是要写一个贩运木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本有着足够的戏剧性张力,尤其是在航行接近终点时,军人把守的木材加工厂将一个更具悬疑色彩的情节抛了出来,这才是小说应该大写特写的地方,它有想象中的硬核,有黑暗和力度,有政治文化的揭示性意义,可以说,它包含拉美文学典型的创作主题;但事实上,我们设想的这种戏剧性在穆蒂斯笔下是弱化的。开篇出现的印第安土著,中段出现的井热病和船长之死,等等,他们和篇尾的木材加工厂并无特别的关联。加工厂的故事只是一个插曲,没有比其他插曲多多少分量。小说写了一场有头有尾的航行,其实是一种插曲式的叙事,从印第安土著的“像飞燕草”一样长长的阴茎包皮,到木材加工厂的奇异外观(玻璃和铝制的闪亮建筑),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主题,因而有许多个主题,出现在开篇、中段、结尾,其实是出现在马克洛尔梦幻般的内心之中。
马克洛尔的特点是内省和隐匿。人物内省的倾向导致了他的隐匿性。如果说这个人物让人想起康拉德笔下的马洛(《黑暗的心》),那主要也是缘于这种相似的内倾。相比之下,马克洛尔比马洛更具有隐匿性。所谓的隐匿是指,人物并不处在事件的中心,而是被放逐到事件的边缘,其存在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马洛航行的动机是寻找库尔茨,这个动机是明确的。马克洛尔的动机是什么呢?做木材生意。可他连木材加工厂是否存在都不清楚,其动机岂非显得可疑?所谓的溯河而上,与随波逐流似乎也并无区别;马克洛尔终究不是马洛;苏兰朵河上的航行比刚果河上的航行更具自我的隐匿性,像是循着梦境的边缘踟蹰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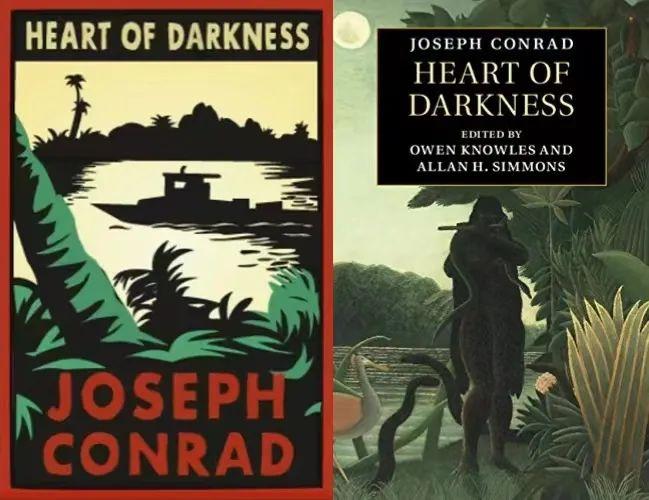
约瑟夫·康拉德作品《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隐匿性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主题,出现在乔伊斯、普鲁斯特、萨特、贝克特等人的作品中;与其说是主题,不如说是表征方式;它将事件的现实特质彻底虚无化了;人物的行为不具有趋光性,更像是一种避开光源的“趋暗性”,因其本质是沉思而非行动,是颓废的自我放逐,而非身份的同一性建构。这种表征方式故而呈现自我的隔离和虚无化的倾向。从叙事角度讲,用来讲述这种“隐匿性”的手段是精简的,其最大单位和最小单位就是语言,而非情节和事件。情节和事件多半是被转化为意象和隐喻,成为内心的投射和参照,被分解为一系列的内视场景,在“隐匿性”的幽光中得以呈现。
马克洛尔的故事,其展开方式如上所述,是一种现代文学的典型创作模式;它很难像一篇“小说作品”那样被人读懂;哪怕是寻常的细节似乎也浸润在并不直白的含义中。因为“隐匿性”貌似封闭,其实是缄默而开放的,要和亦真亦幻的体验发生感应。它把小说的阅读变成这样一种行为,我们好像不是在解读故事,而是在叩问存在。读者和日记撰写者马克洛尔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或不知皆如谜面,吸引探究的目光;这种目光和存在的“隐匿性”最为亲近,两者相互依存,亲如兄弟。换言之,如果不是马克洛尔的同类,你就读不懂这些日记。马克洛尔并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马克洛尔像是某类兄弟会成员,额头上印着同类方可辨识的标记。

《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小说插图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释读船长、上校和马克洛尔的关系。为什么船长要把内心的隐衷托付给马克洛尔?为什么上校素昧平生却要充当马克洛尔的保护人?
因为这些人彼此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阅读和被阅读的关系。船长知道马克洛尔能够读懂他的身世,上校认为他能够读懂马克洛尔的身份,故而他们都对马克洛尔倾心相告。上校对马克洛尔嘱咐道:
“我也看出来了,您在这军营里不太自在,和穿制服的人也合不来。您有您的理由,我完全理解。”“我知道您以前的人生大概什么样,也许您还遇见过我的哪个朋友。”“不要相信任何人,别指望军队帮忙。我们有别的事要做。没工夫去照顾怀揣梦想的外国人。您明白的。”
威风凛凛的上校,对身份低微的桅楼瞭望员说这番话,除了显示同类辨识的洞察力,还能说明什么呢?上校的外交辞令包含一种超越世俗身份的惺惺相惜。船长和上校似乎都有义务去保护这位“梦想家”。我们看到,马克洛尔的故事是建立在这种奇特的兄弟会同盟的基础上。系列小说第二部中的伊洛娜,第六部中的阿卜杜尔·巴舒尔,等等,他们都属于这个跨国的兄弟会成员。马克洛尔丰富多彩的情色故事,也都具有同盟的性质和吸引力。正如系列小说后面六部所展示的那样,马克洛尔和朋友一起从事不法生意,赚取大笔金钱,其同盟缔结的基础却不是金钱,而是超越世俗的精神默契。
《阿尔米兰特之雪》让身份的同一性建构(水手)显得次要,将“隐匿性”的存在置于叙述中心。它让一个水手说着迷离梦幻的语言,让他在超世俗的层次上和男男女女发生关系。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便是要进入上述性质的自我规范,进而体会其仪式化的语言构造。然而,这种叙述并非真的是以规范示人。马克洛尔的人生历程是以未知为导向,是以“拒绝堤岸”为准则,总是在“制造毫无条理的隐秘、无用和偏僻”,就此而言,生活的通俗教义和因果逻辑是难以阐释其处世方式和行为的。
三
如上所述,《阿尔米兰特之雪》聚焦马克洛尔的人生历程,而这段历程连马克洛尔自己都无法真正参透,遑论读者。换言之,该篇确立了精神的自我规范,而这种精神实际是越轨的,是孤独、愗乱、晦暗的。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洛尔是谁?
马克洛尔也经常这样问他自己。苏兰朵河上的航行,或许像此前的许多次航行,不过是他的又一次自我质问和探询。我们说马克洛尔是用一种奇特的宿命感讲述故事,便是指萦绕其心间的这个周而复始的问题——我是谁?所谓奇特是指,他没有答案,却是用一种本质论的语言在讲述。他说:
“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我身上:奔赴的行程总是谜一般不确定,总是经受着随意变更的厄运。现在,我在这里,像个偏执狂般逆流而上,心里却早已知晓,自己终将遇上些什么事,把一切都叫停。(中略)从生命初始,我便一次又一次落入泥沼,做出错误的决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让我万分不解却又极度着迷,这些没有出口的小路合而为一,组成了关于我的生命、我的存在的故事。对幸福的热望不断被背叛,日复一日地偏航,最终总是汇入注定的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在生命最深、最确实之处,我一直都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在不断渴求那些溃败,我对幸福的热望原本是可以被满足的。”
这段话出现在开篇第四则日记中。它更像是结语而非开篇。它暗示我们,苏兰朵河上的航行是他明知故犯的又一次“偏航”,此前如此,今后还将继续。我们感到,马克洛尔所谓的“未知”就像康德讲的物自体,并非全然未知,其边界当属已知。他心里知晓,未知是缘于迷雾般的边界在无限地扩展,就像黑格尔讲的“恶的无限性”,是因其意愿的方式而招致的迷误、过错和报应。马克洛尔说,航行伊始他便闻到了那种气味。什么气味?厄运的气味。厄运像是从“恶心的温热坟墓”散发出来。这片热带雨林在他眼中象征着一个偏执狂的野性、谵妄和纠结。
《阿尔米兰特之雪》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它确立了人物的气质和精神哲学。第一部将几个关键母题导引出来,隐匿性、兄弟会同盟、有关“奇遇与厄运”的存在论体验,等等,它们在后面六部长篇中出现,不过是被进一步验证和补充。大体而言,第一部的调子偏于晦暗,包含一种形而上的忧郁,后六部则出现了一抹市民性质的轻松的暖色调,叙述更有小说的味道,像是把主人公从沉思的山巅带回到丰富多彩的平原,而马克洛尔的情色体验亦显得更为从容、丰腴,更具有实感。
基调的变化并未改变人物的气质,也未改变系列小说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洛尔恒定不变的一个特点就是狂想,这是他的气质,贯穿了七部曲的叙述,紧张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时而偏于峻急,时而偏于松缓。紧张程度趋于激烈时多半表现为谵妄,如第一部中显示的那样;松缓时则多了一份嬉戏和机智,如后六部中表现的那样。无论是何种状态,都是体现为对谵妄的认可,即承认其内在的叙述逻辑是基于非理性的迷思。
马克洛尔的日记体写作无疑是最适合表达他的狂想;其私密、内省和自由联想的语言便是在表达一种主观性。但是主观性这个词用在这里还不够确切,容易造成误解,以为是不加约束的紊乱思绪的一种表现;我们在看待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等人的创作时便经常会有这种误解。意识流的自由联想的独白,从上述作家的创作来看,恐怕不是在表达一般意义上的主观性,而是在聚焦特定的精神状态,即孤独和狂想。通常所谓的主观性可以在任何一个对应的现实层面上反映出来,可以是温和的,中性的,而狂想则不然;狂想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躁动,是存在的隐匿性的表现,是自我隔离导致的虚无化倾向,是一种濒于精神深渊的临界状态。确切地说,现代派文学是表现临界状态的文学,而非只是表达主观紊乱思绪的文学。穆蒂斯的创作便是典型的一例,可以用来印证这个观点。
《阿尔米兰特之雪》的叙述,其真正的戏剧性,是源于这种临界状态的体验。因此,主人公即便已经知晓其命运的底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在不断渴求那些溃败,我对幸福的热望原本是可以被满足的”——其叙述的内在张力也仍然不会松懈。归根结底,人物并不是在渴求常态意义上的满足;他并不相信理性的解释和意义;他相信的是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把他带到理性的边缘,从濒于破裂的关头去迎接一个新生的混沌世界。对他来说,谵妄意味着偏执、梦幻和厌倦,但也包含非理性的洞察。可以说,非理性的洞察,打破人生的通俗教义以及对因果联系的寻常认知,试图将每一时刻的体验转化为“我存在”的释义,这些便是马克洛尔的追求。(也正是普鲁斯特的叙事人的追求。)
马克洛尔的隐匿和谵妄,就其文学史源流而言,是波德莱尔以降的诗学精神的体现,在主体的自我隔离中寻找灵感的源泉;就其创作手法而言,是意识流文学的继承和表现,对时间结构、内视场景和诗化语言的处理,具有意识流的典型特质;就其精神哲学而言,是广义的存在论哲学的表征,追求自我体验的特此性(thisness)和非理性,打破自我的同一性和稳定性,这是现代主体的一种自我定位。以此观之,马克洛尔的“奇遇和厄运”,不只是在标记一个奇怪水手的迷乱的人生,也是在诠释一个现代自我的“心魔”和理念。套用笛卡儿的名言可以表述为:我漂流故我在;或者说:我谵妄故我在。

阿尔瓦罗·穆蒂斯
摄影 | Graziano Arici
四
穆蒂斯是马尔克斯的同辈人,年长后者四岁。中文读者熟悉穆蒂斯的名字,主要是缘于马尔克斯的相关传记和访谈。印象中,穆蒂斯扮演着幕僚和高参的角色,他作为诗人、作家的身份倒是被忽略了。这部大型小说的翻译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创作力旺盛的作家。
由于译介还不全面,我们尚难判断这部小说在穆蒂斯创作中的位置,对作者的创作演变过程还知之甚少。穆蒂斯是作为诗人更重要还是作为小说家更重要,这样的问题就留待将来再作研讨吧。从这部小说的创作我们不难看到,作者拥有精深的文化修养和诗学功底,这一点几乎是从书中的每一页反映出来。将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等同起来,这固然是不恰当的,但要说马克洛尔身上投射作者的影子,这么说也未必就没有根据。穆蒂斯无疑是怀着钟爱之情刻画了这个主人公,此人不仅有广泛的阅历,而且有巨量的阅读。而这也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小说第一部的开篇我们就看到马克洛尔在读书,就着船头的白炽灯灯光,披阅十九世纪的法文书《巴黎城市首脑针对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刺杀案的调查研究》。阅读之于他犹如祈祷和呼吸,让我们油然而生敬意。阅读进入他孤独的梦境(他梦见滑铁卢和拿破仑一世)。阅读无疑也在滋长他的谵妄,让他分不清现实和梦幻的边界,甚至是刻意模糊两者的边界(他在警察局里声称:“我是迷失在二十世纪的舒昂党成员”)。马克洛尔在不停地阅读。阅读是渴望生活的刺激剂,也是抵御生活的武器。

阿尔瓦罗·穆蒂斯在家中
摄影 | Marcelo Salinas
第四部《货船最后一站》有一篇附录,题为《瞭望员的阅读》,短短的三页,颇有意趣。马克洛尔的阅读书目中最常见的是十八世纪作品《红衣主教莱兹回忆录》、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等。他偏爱比利时贵族利涅亲王的书信集和回忆录。他随身携带乔治·西默农的小说《1号船闸》,认为西默农是“巴尔扎克之后最好的法语小说家”。在他看来,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是“夏多布里昂之后最好的法国作家”,而“最好的小说家”当属西默农。
对作家和小说家作如此细致的区分,真不能说是普通读者了。这种区分是必要的,能够给人教益。总之,《瞭望员的阅读》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马克洛尔以其嗜好、怪癖和精当的见解将我们引入阅读的世界。如果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是一本有关阅读的小说,这也不算是夸张。它聚焦人物之间的阅读和被阅读的关系,而且至始至终都在描述马克洛尔专心读书的形象。
该篇的魅力,其迷人的气息,不正是从类似的画面中散发出来的吗?苏兰朵河上的挑灯夜读是一幅镇定的画面,平衡于迷乱的丛林和回旋的时间带给他的晕眩感,仿佛为这个世界的贪欲、腐败和不理智保留一点克制和善念。这么说当然是在讲一种象征意义了,像是在暗示形而上的忧郁以及作为陪衬的世界之空洞和无意义。不必如此愤世嫉俗吧。但是无可否认,在七部曲的叙述中,当形而上的忧郁达到饱和状态时,马克洛尔的冒险、性爱、谵妄以及徒劳的追逐总是显得最具张力,也最有魅力。
奇怪的是——其实也不奇怪——马克洛尔的书目中找不到一本南美洲的书,全是欧洲的,法国的。这个章节(《瞭望员的阅读》)因此不妨更名为《法语文学纵横谈》。穆蒂斯如此安排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国际主义渗透了这本书的叙述。且不说航行的船员是由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的,系列小说后六部的人物、空间和情节的设置,更是按照无国界漂流状态分布的。国际主义构成了马克洛尔故事的基调和底蕴。
第三部《绝美之死》中,南美洲丛林的军官历数马克洛尔的行踪,说后者“在塞浦路斯走私武器,在马赛走私做了手脚的海军军旗,在阿里坎特走私黄金和地毯,在巴拿马做皮肉生意……”。马克洛尔辗转颠簸的无国界之旅,于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系列小说的生成离不开一种跨国多元文化的生成。这是拉美先锋派和“新小说”共有的特质。“新小说”(马尔克斯这代人)尤其强调波西米亚跨文化杂交的国际主义。后来的作家延续这个倾向。穆蒂斯的小说正如波拉尼奥的小说,把这种倾向展示得淋漓尽致,其狂想的特质也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国际主义倾向已然成为题中之义,显得自然而然,好像毋庸多言。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讲,实质也并不是那么“自然”。文化发生学的命题不是本文能够展开论述的。不妨去读一读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著作《“爆炸”文学亲历记》,大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观点,即国际主义色彩并不是拉美文学的固有色;拉美文学是从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吸纳中走向国际化的。
穆蒂斯的创作,如果不能说是对当代拉美文学的一种发展,至少可以说是对拉美文学实验的一个延续,值得关注和探究。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探究“隐匿”和“谵妄”的母题,能够更清楚地揭示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层意义。
马克洛尔说,“我们从来都无法确认梦中人的确切身份”,而“那尖锐的乡愁留在我的记忆中”。此言道出的不只是马克洛尔的心声,恐怕也是拉美几代作家的心声吧。
2022年8月18日写于杭州城西
【作者简介】

许志强,浙江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部分诗学和普通读者》等。荣获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批评。近期有“看理想”音频节目《20世纪欧美经典小说》一百集正在热播。
原标题:《马克洛尔的隐匿、谵妄和国际主义 | 许志强读《阿尔米兰特之雪》》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