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回到河南小山村,我的精神自救探索 | 三明治
原创 坤依 三明治


2017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我的毕业论文是在导师的格外宽容之下,才得以过审的。我发短信告诉他:我写不出来,我想跳楼。导师对我放宽了标准。我没有学术造假。我只是写了一篇没有主题且毫无逻辑、连篇累牍凑字数的论文。当它作为我在这所学校仅存的痕迹静静地躺在数据库里时,我已经要和武大说再见了。
离开了武大,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那时我的焦虑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连续坐在电脑前不能超过15分钟,只想出门狂吼。而我的后背,像是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很难入睡,又很难起床。我很怕空调。炎热的夏天,进到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就会迅速手脚冰凉,而大脑血液快速流动。我很紧张,怕自己思维冻住,怕自己语无伦次,怕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废人」。我不仅担忧我的身体,也担忧我的精神。——它们都快接近崩溃了。
然而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在前一年,我的父亲因为意外从脚手架上跌落。那是我们全家都无法面对的伤痛。摇摇欲坠的三口之家(妈妈、弟弟和我),没有余力再去面对多余的波折。我只能一个人消化我的人生面临的困境。可是不幸中的幸运是,父亲的意外工伤让我们拿到了一部分索赔。我于是有了短暂喘息的经济空间,可以暂时不用去工作。
我决定考研,想去考清华美院的设计系。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专业跨度特别大,又是一所那么好的学校。我也没有美术功底。可我还是在为这个注定考不上的庞大目标作准备。实际上,我的备考状态并不好。那半年里,我一面饱受焦虑的折磨,另一面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想考研,只是在拿备考的痛苦逃避无事可做的痛苦。后来我决定放弃。既然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能支撑我去寻找一份985毕业生「应该」去做的工作,那我就去试试别的可能性吧。
幸运的是,我有同伴。我拉着同样在家以考研为理由逃避工作的闺蜜,一起去厦门参加瑜伽导师训练营。决定放弃考研和去学习瑜伽的那天,我们在从初中时就爱一起去的小城的体育场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那年冬天,雪下得很早。我们走在上面,踩得咯吱咯吱响,已经快冻僵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
“一定会有适合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我们给彼此打气。在那之前,我们都为自己「被大学上了」,是「到点儿清仓」的所谓高等教育的流水线产物感到难过。也为自己只能在「考研」和找一个亲友眼中「一个大学生应该去做的工作」之间做选择而感到憋屈。——人生,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
决定去学瑜伽,是我们第一次脱离常规的试探。四个月后,我们“学成归来”。闺蜜拿着瑜伽导师证,成功应聘了工作。而我没有。一方面,因为我的身体基础太差了,我对自己学成的技能很不自信。另一方面,我很恐惧。想到要为我的学员的学习进度负责,以及看了一些瑜伽课上学员出现意外的报道,我很害怕。——我那时过度谨慎。不管做什么,我都认为自己一定会出岔子。而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心理咨询那时对我来说还很遥远,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我在凭本能自救。瑜伽不行,我又想到了太极。实际上,我在学瑜伽的时候,已经对当时带我们的导师感到失望了。那不是我想要的瑜伽。他把它变成了机械的动作精准度训练、力量训练。而我大学时上过的瑜伽课并不是那样的。老师带着我们认真地感受每一个动作。一节课下来,让我感到身心放松。可我和闺蜜选择的那个瑜伽导师训练营里,助教每天喊着打鸡血式的口号,带着我们进行魔鬼式的训练。我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绷的。在参加完训练营,大致地了解了瑜伽市场的乱象后,我对这个行业已经感到失望了。

2018年夏天,我去到了一个小地方——陈家沟。大学时,我曾跟着班里一位热爱武术的女同学练过梅花拳,后来发现它不适合体质虚弱的我,就改学太极。我家乡县城里有一位太极拳推广者,我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从他的口中得知了这个陈氏太极拳发源地。
当我一个人拎着行李出现在陈家沟太极拳学校门口时,我不知道这一次的选择是否更正确。但我知道,我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一定不只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我还在继续探索人生的其他可能性。太极这样一个脱胎于“道”的武术运动,能教给我什么朴素的人生道理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一波一波追逐着新的浪潮。我站在其中,看不清楚,不知自己该去向何处。于是,我想到了“道”,那个传说中万物的源头。或许我在这里,可以找一找自己生命的「底层逻辑」。
在陈家沟,我遇见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人。大家给出各种各样的加入理由,被陈家沟一一接过。在那里,我感受到的除了「丰富」,还有「平等」。那种「平等」对我来说是一种久违的「同窗感」。陈家沟物资匮乏,但我们在学校的生活有滋有味。冬天热水不充足,一群人翻沟爬坡,浩浩荡荡地跑去隔壁村洗澡。食堂饭菜不好吃,我们就去采购,自己做饭吃。这些事情看起来平平常常,可是一想到是由不同经济阶层、不同认知层次甚至不同肤色的人一起做的,我会觉得格外地美妙。
还记得我刚到学校那晚,一群人正在校门口切磋“武艺”。有一位在少林寺习过武、后来又去武当的师兄教大家练八段锦。我兴奋地加入,感到自己正在接触一种全然不同于我日常所见的生活的另一种生活。在陈家沟的那一年,这种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成为了我新的日常。
我积极投入社交,凑各种各样的热闹。但与在人群中的活跃相对的,是我一个人时的清冷,和不停的自我斗争。一个“我”不停地攻击另一个“我”:你像个一事无成、蹉跎度日的「废物」,而且,练了那么久太极,身体还是时不时崩溃一下,可能会真的成为「废物」。另一个“我”,则像个鸵鸟一般,把头埋进沙堆——手机里的情色片和小黄文,不理会这些指责,假装看不见对现实的担忧和恐惧。两个我在同一副躯壳里不停地撕扯着,对彼此关闭了心扉,谁都不想理会谁。
我那时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在亲密关系里照见了更深刻的痛苦。我想透透气。于是从学校请假,去苏州找闺蜜。她那时也已兜转了一圈,准备去太湖大学堂教书。在一连串的巧合下,我们一起去了庙里,小住了半个月。我们每天盘腿坐,一边昏昏欲睡,一边听“人生八苦”,还和师兄们一起练习“走猫步”。那是太极拳里的一个动作,被师父单独抽出来作为基础训练课程。推开庙门,是一条静静的小河。但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过。
那段令我痛苦纠缠又始终放不了手的恋情,最终以对方提出分手告终。因为对方深度参与了我在陈家沟的学习和生活,我不想再在那里逗留了,决定离开。

回家后,我再一次面临「去哪儿」这个难题。我想,要不去北京工作试试吧?也许我可以。结果北京地铁里的冷风激起了我对空调的恐惧。我在陈家沟结识的一位姐姐也在北京,她收留了我,带我去看病治疗。那是一位中医,他一再强调我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怕冷。可我还是感到恐惧。
那位姐姐又带我去了邻省的内观中心,我在那里学到了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感受。后来,我一个人报名了另一座城市的内观中心,在那里待了40多天。内观中心的老师得知我呆了那么久,告诫我:“在这里学到的方法,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使用的。”可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面对生活。有一天我在洗碗时,随手拿走了别人的碗,等我意识到这件事,我感到更恐慌了:难道我的脑袋已经退化到这种程度了吗?我是不是真的「废」了?
快到过年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回家的路上,新冠爆发了,全球进入疫情时代。后来各个地方的内观中心陆续关门,我的心灵探索之旅,被迫暂停了。我被迫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里去。在我在外游荡的一年半里,家人是缺位的,父亲去世的阴霾还没散去,妈妈尚在悲痛中走不出来,弟弟还在读大专,尚未出校门。我谎称自己在工作,想让他们放心。实则一个人在各处游荡,不知该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妈妈每次打电话来,我都心惊胆战,害怕自己的谎话被戳穿,只能支支吾吾岔开话题,赶紧结束聊天。
不幸中的幸运是,那段时间里,我得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帮助,比如那位姐姐,以及其他几位在陈家沟认识的朋友。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资助我,也在情感上给了我许多温暖。在我后来陷入完全抑郁状态时,有几位依然在坚定地支持我。迄今,我还在和那位姐姐保持着联络,我告诉她,我能一直进行这些探索,以及我最终能从抑郁中走出,是大家一环接一环“众筹”出来的。她回复说很羡慕我,羡慕我勇敢、自由、有坚定的信念,得到过那么多人给予的温暖。
我很感谢她这样说。可是,我没问出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表现地「讨人喜欢」,你们还会帮助我吗?当时的我想,为什么别人能从家人那里得到的情感支持,我总是在东拼西凑,从不同的人身上去“获取”。而作为回报,我在关系里总是主动牺牲一些自我舒适度。一方面,我因为被「欣赏」而被「帮助」。另一方面,我因为被「帮助」以「讨好」作为报偿,让自己变得更加「讨人喜欢」。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证明了我的价值。可我的不安感依然如此强烈。我害怕自己被讨厌,害怕他们突然认为自己给出的帮助「不值得」,而我因此被厌弃。
这种「低价值感」,在我和家人的互动中逐渐显露端倪。我重新回家时,妈妈和弟弟分别有了稳定的工作。而过去一直因成绩优秀而被父亲格外优待的我,仍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从前那些像是仗着「成绩好」而享受到的资源和情感倾斜,一下子坍塌了。
2021年元宵节前后,矛盾集中爆发。我在那间家里后来买的县城大房子里,和妈妈、弟弟大吵一架,带着童年留守的委屈,大声地控诉他们:“你们知道吗?爷爷为了等你们回去,不舍得吃地里收上来的红薯,先吃坏的,好的留给你们。结果你们一直没回来,好的红薯也变坏了。那年冬天,我们吃了很多坏红薯......”弟弟挡在妈妈面前,对着我大吼:“你怎么只看到这些?你没看到你念高中,胃不好,吃不惯学校的饭菜,妈妈为你送了三年的饭吗?”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那如果我成绩不好呢?你们还会爱我吗?”那一刻,我心里憋了多年的疑问,终于问了出来。然而没有得到回应。
我在各种关系中的「讨好」,随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认为我的亲友们是因为我表现得友好而亲近我。我感觉自己被情感压榨了,或是被当成了情绪垃圾桶。我开始疏远他们。我还删了很多人的微信,包括我弟弟,只保留了几个——我的“债主”们。我想,我总要“还完钱”,才能删掉他们。我可以对人性失望,但我不能丢弃自己的品格。那位姐姐也是我认定的“债主”之一,我与她谈到这一点时,她说,“那你还是别还了。(这样我就没有被删掉的风险了。)”我听了心里暖暖的。
在经历了「删人」风波后,我开始了「控诉」风波。那时我已经开始接受心理咨询了。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我慢慢学会大胆表露自己的想法,比如加回了大学时软霸凌我的室友的微信,告诉她那些年她做得不对,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
在我为自己逐渐变得「有力量」而感到沾沾自喜时,妈妈和弟弟却因为我性格的「反常」对我愈加担忧。2022年年初,我被他们送进了精神病院,被诊断为「分裂式情感障碍」。出院后,我彻底坠入了抑郁的深海。我开始相信并接受自己是个「废物」了。我吃着药,身体变得浮肿。我讨厌自己,我觉得浑身上下的肉不属于我,连情绪都不是我的。我在药物的“帮助”下,看起来「开心」。可是,“肥宅快乐水”式的「开心」和发自内心的生命愉悦感,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我在精神病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回了家乡的村子。这一次我待在姑姑家,总觉得好像应该做点什么,休整了一段日子,就去县里的中学面试高中语文老师了。
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份工作呢?我其实很犹豫。我的状态还不稳定。之前每一次短暂的工作,我都会在兢兢业业几天后,突然不想做了。我起不了床。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抑郁症病人的情绪的「躯体化」。心理咨询师曾告诉我,他有个病人在床上躺了七年,没有任何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就是起不了床。而每当内心的焦虑感来袭时,我站在讲台上根本不记得自己上一句说了什么,下一句要说什么,培训期间一次都没能脱稿。我隐隐觉得,我仍会放弃这份工作。但我也知道,这份工作对我的亲人们来说意味着我的「稳定」,他们心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我希望我能达成他们的期待,可是我没能做到。
开学第二天,我就提出了辞职。人事部负责人告诉我,由于我们签了协议,我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违约金。我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在校长约我面谈的时候,我掏出了精神病院发的厚厚一沓病历本。我在赌他对一个精神病人的怜悯,就像五年前,我告诉导师“我写不出来论文”那样。我仍然在尽全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同时也摆脱不掉觉得自己“卑鄙”、“无能”的羞耻感。最后,我没给赔偿就被允许离开了,但病例被复印了几页作为存档。
我又回到了姑姑家。她知道我辞职了,但我已经放弃了满足亲人们的期待,放弃自己能找一份「正常体面的工作」的想法。先找一找我能「活」的方式吧。
那个夏天,我对农活起了短暂的兴趣。我拿着大麦铲,在离姑姑家不远的姥姥家门前翻麦子。我脱掉鞋子,赤脚走上金黄色的麦田,麦子硌得脚底微微地疼,但又很舒服。——我找到了久违的快乐。有一天,我把自己整个儿铺开,平躺在那堆麦子上。头顶是蓝蓝的天空,身后是稳稳承托我的大地。我感到放松且安全。我闭上了眼睛,想让这样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
在那片土地上,我逐渐找到了「松弛感」和生命原初的动力。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不是干农活儿的料。农忙时,我想帮忙,但吭哧吭哧撂了几铲就很累,于是干一干、歇一歇,艰难地维持自己的节奏。但农活儿是不等人的。一天夜里突然下了雨,我赶紧爬起来,想把晾在门口的麦子收拢,但节奏太慢了。我只能一脸愧疚地看着姑姑一家暴风式劳作,飞快地干完了所有的活儿。我再次体会到了「不被需要」的感觉。——我只是养在姑姑家的一个「闲人」。
随后,我陆续试了两份村子里的工作。一开始在防护服制造厂当缝纫女工,后来又去超市当起了店员。我对它们有非常特别的感情,可能因为它们是在我「生命重启」的时候出现的,我的工作参与感和沉浸感都更强。
踩缝纫机治好了我的「躯体化」症状。刚开始,我的肢体非常僵硬,重复简单的动作都感到腰酸背痛,一天下来觉得很疲惫。后来我渐入佳境,愉悦的感受多起来,大脑中的紧绷感也不再那么强烈。回去后,我还可以帮姑姑做些家务,一起做饭。从躺着,到坐着,再到站着,随着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生活中,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在超市工作训练了我的心智能力、注意力和抗压能力。理货时把乱糟糟的物品收拾整齐,让我感到很舒心。收银时,我总担心自己会错帐,或者在数钱时数着数着就跑神儿了,但都没有。村里的村民有时会在买完货之后,折回来纠结货品标价的问题,纠缠之中言辞粗鲁,后面的队伍排得长长的。我的心在因为老板交代「动作要麻利,不能让客人等」和「我到底应不应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而左右摇摆,急的脸颊发烫。后来老板跑来解决了,给他退了货。
我逐渐学会分清哪些事情应该交给老板去解决,哪些是我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和姑姑以及朋友交谈的功劳。我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面对这个世界都是如此笨拙,而一旦事情进展不顺利,我都会先责怪自己。但当我逐渐接受「我不可能一个人解决所有事情」之后,我发现我的安全感越来越足了。我在收银员的岗位上,也逐渐游刃有余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亲戚家,看到她家孩子的语文教材摊在桌上,就鬼使神差地翻开了。在粗粗看了几行字后,我感到惊喜。因为我预感到,下一步,可以驯服自己的「注意力」去做更细致的事情了,比如教孩子「如何分析一道题」。我“消失”的能力逐渐回来,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我回村时,我也不知是否会有这么一天,我能看见曙光。我只是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想到还有这个办法可以一试。它“成功”了,我很开心。目前已经在筹备考教师资格证和下一步拿下特岗了。逐渐找回在现实世界的位置,我的精神也随之轻松了不少。

直至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描述,自己是如何抑郁的。因为在我「正式抑郁」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拥有很多苦恼的人了。
我从高中开始神经衰弱,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作为村里仅存的还在上学的娃,我的父亲在替我承担着学业上的经济压力。我很担心,如果我考不上大学,父亲在我身上的投资将「满盘皆输」。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恐惧风扇的。因为我总是头痛,风扇吹出的风加重了我的头痛。我怕这影响我的身体,继而影响我的学习。我的高中同学比较友好,如果我提出关掉风扇的诉求,他们也会同意,但我看着一整排的人满头大汗,觉得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大家都热着。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高考冲刺期的,只记得我开始频繁地缺课。直到在高考考场上,我边忍着头顶那个吱呀乱转的风扇,边对着面前的考题奋笔疾书。
我以为「到了大学就解脱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太愉快的宿舍生活,和始终「不太懂」的专业,为我的大学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我的父亲,那几年工作行情不好,尝试跳到别的行业,又接连失败。父亲是在我大三下学期离世的。他离世前几年,是我们的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在咬紧牙关把我送入梦寐以求的学校后,父亲疲惫了。我大一时,被父亲视为精神支柱的爷爷离世。爷爷出殡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从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就每况愈下。
我在困顿生活里挣扎时,父亲几次尝试着表达需要我替他分担。我借了学校的助学贷款,也接受了贫困助学金,同时不停尝试校外兼职。可是没有头绪的我,总是经历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在经历被中介公司骗钱后,我把注意力放到校内,靠一些零散的兼职度日——在樱花节当护花使者、在图书馆里给书上架。有一天我带着电脑去工作台,整理完当天的书,回头发现电脑被偷了,而那台电脑,是接近崩溃的父亲能给我的最贵的「投资」了。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意外」,又无力解决。与此同时,我的精神状况也在不停恶化。我遇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我赖以生存的头脑,失灵了。某一个期末,我在一间自习室里坐了一个晚上,一个字都没看进去。那时的自我,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控」。渐渐地,我没办法安静地坐下来看一本书,或者对着电脑写论文。而我对于「不可控」是非常恐惧的,我害怕自己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我的大脑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各种「风险」,并为此而担心。
我曾靠吃药控制自己,但从精神病院出院后第三个月,我就主动断药了。随后经历了几天失眠,我用艾灸助眠扛了过去。如同进精神病院是被动的,我接受不了自己的情绪要依赖药物来控制。最重要的是,药物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的心理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认知问题,来自自己和环境的长期相互作用。我被「一叶障目」,看不见别的可能。只有我尝试去寻找与惯常行为思路不同的另一种思路,很多困扰我的问题才能逐渐得到解决。
从事心理行业的朋友告诉我,她也曾认为药物治疗不可取,但她的老师告诉她,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干预是必要的。药物可以帮助病人冷静下来,不再一味地与问题纠缠。但是,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缓冲空间,让患者停止自己与情绪或者问题的持续「绞杀」。
我也差点溺在“深海”里,但经历了近乎绝望的挣扎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求生的本能,我可以用生命的力量托起自己。于是,我“上岸”了。在这个“上岸”的过程中,我一直使用从内观中心学到的方法,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感受,让情绪自由来去,而不是被它带着走。
那么,在“深海”中“游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想,是逐渐了解自己的情绪窗口的容纳度,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有选择地接收、释放信息。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认真听内心发出的信号,决定自己与某个人或某件事,近一点或者远一点的距离。这样的能力,于很多人几乎是本能,我很羡慕他们天然地就知道应该怎样让自己快乐,这对于曾经陷入抑郁的我来说并不容易。但“学会如何轻松、让自己快乐”也是一道“题”,我还在学着慢慢解对自己来说新的难题,与此同时,我在“深海”中“游泳”的能力,也不断变强。
有朋友跟我说,从抑郁中走出的人,生命会变得更加舒展,我的感受也是如此。抑郁让我被迫停下一切,学会了解和倾听自己,当我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自己,也更明白他人了。在抑郁之前,我紧紧裹住自己的那层壳,也被击个粉碎。我从破碎的自我里,长出新的肌肤,一点一点向世界延伸。我还在享受这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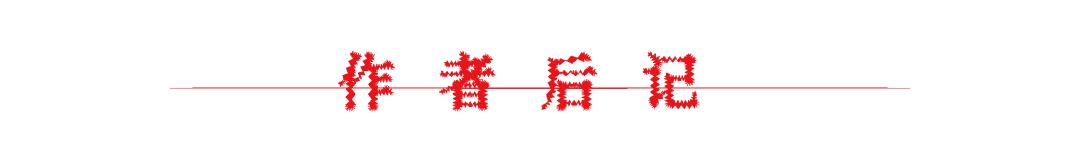
这篇文章原本是我为自己在短故事学院意外创作出的小说写的后记。但因为它更清晰直观地表达了我的病情演化的过程,以及好起来的过程,就变成了正文。
我在原本书写正文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语言寻找。我想找到一种方式,展示抑郁态的自己的言行,同时告诉大家,我是怎么解读自己在抑郁态的表现的。最终我创造了两个人物,“我”处在正常状态,“他”处在抑郁状态。但“我”不全是正常态的我,也是代入了自己在抑郁态时身边朋友和亲人视角;“他”也不全是抑郁态时的自己,我把自己和其他抑郁症病人接触所感,糅合到了一个人身上。
如果说抑郁是一面深海,我想带大家看看“深海”,又不希望有人「溺」在深海里。一篇虚构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一开始,我希望“我”能和“他”达成和解,但在写作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和解」,只要「了解」和「看见」就好了。
目前,这篇小说还在修改中。希望我的初次尝试,能够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尽可能地表达完整。感谢导师和笔友们的鼓励,让我有勇气讲一讲“我”和“他”的故事。

0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问我。”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痛苦。我于是停止了追问。
半晌,那个乱蓬蓬的脑袋突然上扬,一双眼睛略带羞涩地盯着我:“其实,我有时候会做梦......我正在上厕所,突然衣服不见了......我赤裸地离开厕所,闯到大街上......我很享受这个梦。我想,裸奔一定很快乐......把赤裸的自己展露于人前,我不敢想象......”
“你想说的是,你不敢在人前展露真实的你?”我尽量让自己问话的语气放的温和,看起来不带有任何攻击性。我希望我的朋友感受到我的友好,能放下一些戒备。
他点了点头,不敢看我。
02
“那......”,我试探着开口,“你有没有想过:废物也在等待被看见,也有他的价值。”
顿了顿,我又说,“就像那棵苍老的树一样。它会引起我对老去的悲伤。那么,人们在看到废物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厌恶!认为它不配存在!想让它消失!”他突然变得暴躁。
我停下来,静静地站立着。昏黄的路灯里,他的身形晃了又晃。我看见生命的能量从他体内汹涌而出。像是积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得到释放。路上依稀有行人走过。偶尔回头看着我俩,然后谈笑着走开了。
这里有一个灵魂在暴走。却几乎不被人看见。我感到孤独。我望着那些路人,很想问他们:会怎么面对朋友如此暴躁极端的一面呢?
03
“你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你!”我再次走上前,试图加深这个拥抱。
然而他却躲了过去,不肯给我回应。“那是假的。”他说,“真实的我没那么好。我善妒又很争强好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和善。”他一字一句地给自己下着判断。
我很不屑他这个说法。——我的朋友就是一个体贴可爱的人啊!和他在一起总是让我觉得很愉悦。可是他总会隔三差五消失那么几天,谁都不搭理。要是他能改掉这个臭毛病就好了,我想。
“不,你挺好的......”这次,我的语气有些敷衍。我想,聪明如他,一定能察觉得到。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原标题:《回到河南小山村,我的精神自救探索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