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乔叶《宝水》研讨会
原创 傅小平 文学报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农村题材或者乡土小说,还能写多久,还能怎么写,这是一度困扰文学界的话题。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乔叶长篇小说《宝水》研讨会”上,评论家孟繁华坦言,自己有一段时间对此很犹豫、很怀疑。但近年来像《宝水》这样的创作实践却告诉他,生活一直在发生变化,生活的观念和生活的力量要大于思想的观念、思想的力量。“我们的文学思想不太可能改变生活,反倒是生活会改变我们。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的话,乡土文学可以一直写下去,因为乡村生活一直在发生变化。”


乔叶《宝水》
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尤其是《宝水》,也确实写了一个变化中的乡村。在小说里,这个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也由此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如孟繁华所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家笔下的人物,从柳青《创业史》里的徐改霞到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等等,都是从乡村奔向城市,但是在《宝水》,以及付秀莹的《野望》里,却是城里人要奔向乡村,也就是说,他们和曾经的高加林们是逆向而行的。这种情况显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又很难说在文学上不成立。“我想,地青萍这样的人物,或许不具有典型性,难以引发强烈的共鸣,因为这种书写没有达到一定规模,还没有形成它的一些特点,但是乔叶和付秀莹发现它,并为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这么一点新鲜的东西,就非常了不起,这一方面当然是受了生活的启发,但也未尝没有观念的影响。比如,为了政治正确,为了完成新山乡巨变的创作计划,我们要寻找或者纠集一些类似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她们能发现,并把它写出来,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并不只是这两位作家发现了乡村的新特点,并且写了下来,诚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写新的乡村故事的小说,近几年已经出了一大批,只是这个“新”在他看来要打个问号,因为很多新的乡村故事,读起来让人觉得不真实,不是写的事情不真实,而是故事中的人物,特别是乡村人物不真实。但乔叶写的新乡村故事却让人觉得真实、亲切。以贺绍俊的了解,乔叶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她采取的是日常的乡土叙述,表现的是诚挚的乡村情感。“乡村叙述是有很强大的传统和优势的,有很多经典作品摆在那里,这也就给今天的写作带来突破的难度,尤其在乡村文明整体萎缩的趋势下,乡土叙述很容易在以往的固定模式中循环、重复。乔叶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看了她的一个采访,她把这些固定的模式归纳为牧歌式、悲歌式和审判式,该怎么规避?她认为,就得从乡村的日常生活写起,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特别敏感,这是她的优势,她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写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所以我说,这是日常的乡土叙述。”
但写好这所谓的日常的乡土叙述,却并非记一笔流水账那么简单。譬如,按照春夏秋冬的四时节序来写乡村,是不少作家都能想到的写法。因为如有过下乡经验的评论家李掖平在此前举行的另一场研讨会上所说,只有在农村原乡春暖花开、夏阳明朗、秋实丰饶、冬雪冰寒,这些自然风景的区分度才会来得格外明显,与之密切相连的人情事理和节令习俗的差异性也特别鲜活。而乔叶按四季顺序来写这部小说,显然不在于写四季本身,而是写出李掖平说的那种“只有在农村老家的日常生活中才随处可感可知的,那些纠结着无限复杂又无限广阔的人际关系,才更能见出传统文化中一切事物互为联系又互为牵扯的绵延和融合。” 由此可见乔叶对农民生命观和生存之道的独特思考与辨识。以李掖平的观察,小说分为四个章节,按时节序顺序写来,却不是简单的线性结构,而是线连着线并回环往复穿梭在一起的网状结构,它特别凸显的是冬和春之间、春和夏之间、夏和秋之间、秋和冬之间四时节序的相互缠绕与勾连。“由此乔叶成功创造出的这个宝水村,可以称之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一个典型的案例,她更由此建立起一个具有鲜明独特性的文学场域和文学地标。”
体现在《宝水》这部小说里,也可以说是乔叶主要借助于地青萍的视角,来建立这个独特的文学场域。就像评论家韩春燕分析的那样,地青萍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她介入到乡村生活,以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乡村。她的身份又非常有特点,她不像过去乡土小说的人物,多是由上级派下来体验生活,挂职锻炼,她没有这些政治身份,她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普通人,自愿到乡村去感受乡村生活,所以她没有任何政治负担。同时,地青萍本是福田庄人,她既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又有乡土社会经验,这就相当于在外视角上再加了内视角,她既可以以外来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乡村生活,又能把自己原来的经验被激发唤醒代入进去,从而有比较。而福田庄和宝水村之间又是有差别的,地青萍看到了宝水的独特性,也就把宝水村的生活空间打开了,这样使得宝水与城市生活、与外面其它乡村生活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联系和对比。也因此,在韩春燕看来,小说里绵密细致地写了乡村的气息、乡村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同时借地青萍这个视角,乔叶也就把乡村最根底的东西、更隐藏在深处的东西挖掘了出来。

在河南老家的豫北修武县大南坡村和村民聊天
(作者供图)
显而易见,地青萍这个人物既是在场的,也是不在场的,虽然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这使得她有倾情投入的一面,也有冷静观察的一面,还有不动声色的批判的一面,这种若即若离的设计,能去除小说的非虚构或新闻特写的色彩,使它真正小说化,但就像评论家何向阳质问的那样,地青萍这个人物多少带有文旅的色彩,她是一个旅者、一个过客,而不是一个驻扎者,而小说本身,即以散文化的结构写了文旅。何向阳坦言,以她的阅读,她找不到乔叶叙述的动力。“这个动力需要去表现,它是一个表现主义的东西。而《认罪书》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是仇恨,小说因此有了饱满的结构冲突。”
无疑,小说叙述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戏剧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结构的内驱力。评论家陈福民读《宝水》读出沉闷之感,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觉得其结构缺乏内驱力或推动力。“小说没有中心事件,没有中心人物,而地青萍作为旁观者是悬着的,她在中间,她是不进入历史洪流的。她虽然用养病的方式,用预言式的方式表达乡土文明的认同,也侧面表达对城市文明的忧虑。” 在陈福民看来,《宝水》用叙述或者人物对话完成对故事的推动,而舍弃描写,少有闲笔,也使得小说的结构紧致黏密,不够舒朗。“十九世纪的长篇小说是有闲笔的,《战争与和平》里,安德列伯爵受伤后,躺在地上看着天空、看着橡树,由此生发出的那些关于对人生的思考,就不可或缺。因为这里面有人物的心理深度,而人物的心理深度跟历史深度相关。”
有意思的是,在评论家郭义强看来,《宝水》恰恰是描写多了,叙述少了。以他的阅读,小说里更多是抒情的段落,描写景物、山水、植物的段落很多,乔叶对花鸟虫鱼、对农作物、农村吃食的熟悉程度,包括怎么腌酸菜,怎么烩面等等,都写得很精到。“相比之下,如果这部作品会修订的话,我建议她在人物主线、故事主线上再加强一些。”
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则是对何谓闲笔,何谓描写,以及两者在小说中应该起到何种作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无论描写,还是叙述,都仰赖于语言表达。在这一点上,评论家们却是不约而同给予了好评。陆梅觉得,《宝水》的语言是活的,是能够惊醒生命和生机,向着山河大地的好语言。汪政认为,小说以民间语言来进行叙述,可以编成一部宝水的方言词典,而体现在这部小说里,方言不是修辞,不是炫技,也不是猎奇,而是一个本体的东西。“《宝水》是我所看到的方言写作当中,走得最远也是最成功的,乔叶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用对话体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方言的“烩菜”,让我意识到民间的文化、民间的语言,尤其是方言,还能参与到现代性作品的建构当中去。”张清华进一步表示,在这部小说里,方言作为本体,使叙述能够沉浸到乡村生活的情境当中,方言还形成了《宝水》的信息流、情绪流和生活流,最终也形成它的语意流,成为具有强大裹挟力的叙事形式,最后变成一种生活的认同、价值的认同,甚至也是一种美学的认同。不只如此,在张清华看来,《宝水》还张大了中国乡土小说中诙谐的传统。“对于乡村社会生活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小说当中写了很多历史的苦难,现实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里的人民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来消解、承受这些苦难,所以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文化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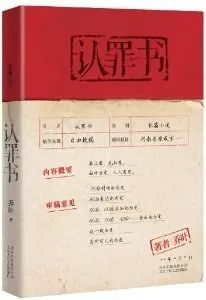

乔叶部分作品封面
乔叶写出了这种文化态度,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是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李敬泽在名为《经典70后》的序里对‘70后’做了探讨,他认为,‘70后’是为巨变所直接塑造的第一代人,他们在特殊位置上感知历史和现实。也就是说,‘70后’这代人,基本是为1985年以后的文学所塑造的,苏童、余华这些人,虽然比‘70后’大不了多少岁,却在无形之中成了立法者,基本上所有的‘70后’写作者都是在‘50后’、‘60后’那些迅速经典化的作家形成的巨大的压力下写作。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从乔叶的写作中,我明显能看出来,‘70后’自我立法的时代可能来临了,我不是他们写作有多么自信,而是说他们也在摸索和探求属于这一代人的写法,《宝水》是一部很好的样本。”
以谢有顺的理解,《宝水》固然是用了一种很典型的,属于“70后”的,细碎的、片断式的、带有个人浓厚情绪的写作方式,但在一定意义上,让个人的“我”,破碎的“我”,获得了一种整全感,她是大胆地要把本来也带着个体情绪和细碎的“我”放在时代里,放在所谓新时代的视野里,放在当下正在变化的时势里面来写,她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多的‘70后’还是在自己划定的边界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所谓的有‘我’的写作。但是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可能要经历一个从‘我’到庄子所说的‘吾丧我’的过程。比如现在讲到乡村振兴,我可能喜欢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但农民喜欢有卫生间的乡村,有污水处理的乡村,有垃圾焚烧的乡村,也喜欢有塑料袋的乡村。从小的‘我’跨出去,试图去理解我们不理解,甚至不能宽容的部分,这是很重大的转变。”
在谢有顺看来,很多“70后”作家都要面对这个难题。只有这样,他们的写作才会变得宽广有力。“当然乔叶以前的写作也有这种跨出去的,但是这次这步跨得特别好。比如‘我’,也就是地青萍是带着记忆,带着创伤,带着个人各种偏见,到了乡村,但当她进到一个更大的视野里的时候,这个‘我’慢慢被改变。甚至乔叶笔下的孟胡子,他是把乡村振兴当作一件事情来做的,并不是想通过做项目赚钱,或者想青史留名,他就是做项目,做完走人,继续做下一个项目。我们得怎样看这样一个人物?至少《宝水》做了自己的探索,乔叶让‘我’进到新的视野里,看到新的知识分子、新的乡村人,并要重新建构人和乡村的关系。这部小说也让我对乡村、对‘70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2020年春节,乔叶和朋友在修武县一斗水村走访
(作者供图)
而乔叶能写出这种“全新的认识”,自然是下了功夫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透露,乔叶其实在六、七年以前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了,其后改了三四遍,十易其稿,才完成了创作。相比而言,如今大多数乡土文学的写作,是如孟繁华所说的,那种望乡式的写作,亦即作家们坐在城里看着乡村写作,这样就难以写好。“乔叶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跑村与泡村》。按我的理解,跑村是横向的,泡村是纵向的,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这样才能熟悉生活。我们的乡村书写、农村题材为什么没有超过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到现在也仍然没有超过他们,就因为他们熟悉乡村生活,因为熟悉,即便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政治化的,受到各种规约的时代里,仍然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并塑造出梁三老汉、邓秀梅、肖长春这样的人物形象。”
应该说,乔叶对文学的敏悟,以及那种认真的写作态度,使得她写出这样一部充满当代性的作品。纵使如此,评论家岳雯依然觉得有不满足的地方。以她的理解,宝水很新,但它依然是一个脆弱的村庄,这种脆弱来源于地青萍可能会走,她在这里能待多久是一个不可定的因素。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宝水目前的“新”依然是依附性的,还没有建立起它的文化主体性。“乡村本身从经济上也好,从文化上也好,从审美上也好,还是依附于城市而存在,这就使得它现在的欣欣向荣,具有某种脆弱性,乡村将往何处去?乔叶是不是还可以从未来的向度,写宝水的‘新’,写出它的未来性,这同样值得探讨。”
原标题:《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乔叶《宝水》研讨会》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