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困在执念里的父亲「必须生儿子」|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 | 老歌m
编辑 | 吴筱慧
在过去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家里的女儿,刘宇和姐姐一直是在被父亲忽视中长大的,并深受伤害。为了生儿子,父亲投入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在一次次的挫败中,生活被撕裂得面目全非,伴随着无边无际的无助和屈辱。
最终,父亲彻底地败下阵来。
以下是刘宇的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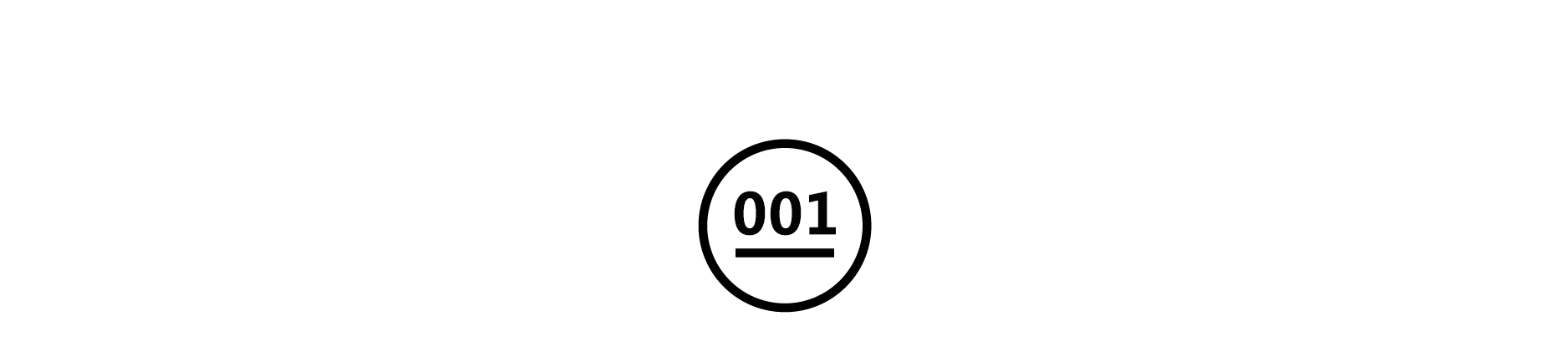 一个人要是跟自己杠上了,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最后把自己折腾得焦头烂额,神志弥散。
一个人要是跟自己杠上了,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最后把自己折腾得焦头烂额,神志弥散。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以前,我们家的生活在村子里算是不错的,父亲手脚勤快,又会做泥水活,母亲在村子里开裁缝铺,比别人家多挣一份活钱,姐姐和我,又都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
但一次起因于孩子之间玩闹似的打斗失败,引发了父亲必须生儿子的执念。从此,一家人的生活被搅得像一团乱麻。
1976年11月份的一天,秋收已经忙过,田地里没什么农活儿了,许多人就凑在刘二成家甩扑克打发时光。
刘二成那年四十来岁,他十八岁时外出闯世界,据说到过云、贵、川和东三省。等三十多岁回来时,父母已经双双亡故,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已经没有与他年纪相匹配的未婚女子,他被剩下,成了光棍。农闲时,村里人喜欢去刘二成家聊天、打牌,他家没有女人孩子打扰,可以玩得尽兴。但村里人背后议论说,养儿防老,刘二成现在过得自在,年纪大了要吃苦头。
那天大家正玩得高兴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匆匆跑来,说小灵和陈峰在后山上吵架。小灵是我的姐姐,那年九岁,陈峰是陈根土的三儿子,那年七岁。那天,陈根土也在刘二成家,正跟我父亲等人一起打牌。
两个孩子斗气,又翻不了天,吵上几句,过不了几分钟,又会玩闹在一起,大人根本不当一回事,依旧嘻嘻哈哈地打牌。
来报信的孩子不肯离去,站在一边喘着粗气,说再不去,小灵和陈峰要打起来了。刘二成就招呼大家:“走,瞧瞧去。”
村里人都把村子后面那一个山丘叫作后山,后山不高,实际上就是一些缓坡,上面有树林,有灌木,有各种野花,小孩子没事时特别喜欢往这里跑。后山离刘二成家不远,大家坐了半天,都想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于是起身,跟着孩子一起往后山上走去。一路上,父亲还跟陈根土说说笑笑,两个小孩子打架,又能掀起多大的波浪?
秋日里的乡村,风轻云淡,弥漫着草木和野果的香气。

村庄
原来,村子里的七八个孩子在后山上玩耍,小灵在一个草窝里发现了六枚野鸡蛋,拿回家是一盘不错的菜肴。正要取时,陈峰扑了过来,说野鸡蛋是他最先发现的,应该他拿。小灵和陈峰你不让我不退,就这样争吵上了。于是,一个孩子就回村给大人报信。
就这屁大点的事。父亲说一人一半,各取三枚野鸡蛋就了事了。但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刘二成说,干脆来个公平竞争,让小灵和陈峰摔一场跤,谁胜了野鸡蛋归谁,大家连声说好。
父亲想,小灵比陈峰大两岁,个子也比他高半头,虽然男女有别,但摔起跤来应该不会吃亏,就同意了。
摔跤放在一块柔软的草地上。小灵和陈峰开始摔跤了,拉来扯去,一时分不出高下胜负,大人们都笑得东倒西歪。当时,父亲一边笑,一边给小灵出招:“绊他的左脚嘛。”
小灵慢慢地占了上风。
突然,陈峰伸出双手,使劲扯住小灵的长头发,先是把小灵往下压,接着又转起圈来,小灵脚下步伐乱了。小灵也伸出手去抓陈峰的头发,但男孩留的是短短的小平头,根本抓不起来。这时,陈峰手一松,小灵跌出了几米开外。
看到姐姐被陈峰打败,我哭了起来,问父亲:“爸爸,你怎么不帮姐姐?”父亲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小孩的事情,大人怎么帮?”从此以后,父亲再没有如此好声好气地跟我说过话。
六枚野鸡蛋归了陈峰。小灵满心委屈,一路上都在哭。
父亲十分生气,有对小灵的不满,也有对陈峰的憎怒——摔跤扯女孩子头发算什么本事?但又不好表现出来,装着没事人一样。一路上,大家又都说笑起来,陈根土得意洋洋地对父亲说:“男的毕竟是男的,女的永远也比不上。”
这句话像一记重拳打在父亲的心尖上。
陈根土生了三个儿子,父亲生了两个女儿,那年我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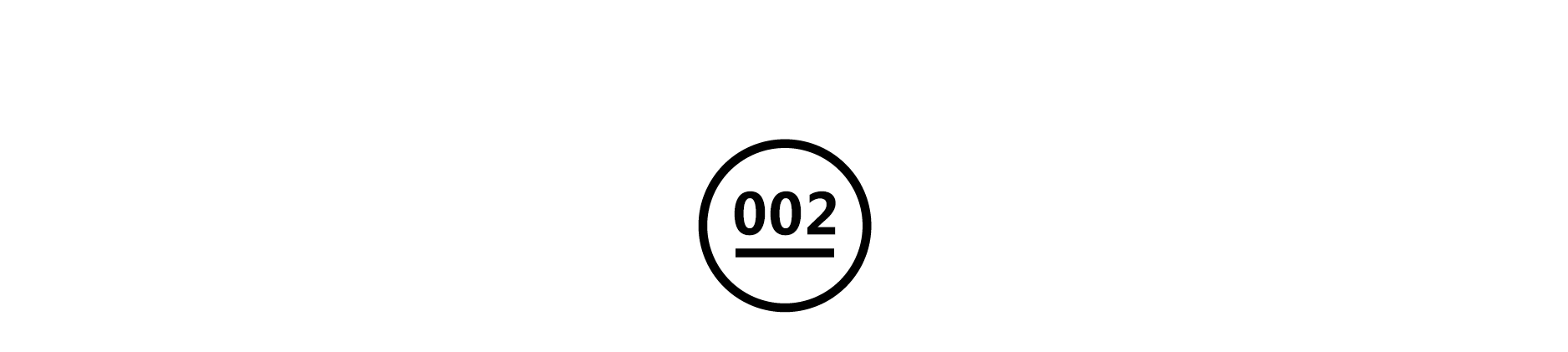 那个年代还没有分田到户,村民们参加的是集体劳动。野鸡蛋事件后不久,生产队组织冬种。学校里也放了寒假,许多孩子来到田间地头,姐姐在帮着大人干活,我在田边玩闹。
那个年代还没有分田到户,村民们参加的是集体劳动。野鸡蛋事件后不久,生产队组织冬种。学校里也放了寒假,许多孩子来到田间地头,姐姐在帮着大人干活,我在田边玩闹。干过一阵子,大人们屁股下垫着锄头柄,坐下来喝水、抽烟、聊天,陈根土坐在父亲的身边。
那天,父亲的口袋里装着一包进城做泥水活时东家送的纸烟,他拆开来分给边上的人抽,唯独没递一支给陈根土。看得出,父亲是故意这么做的。这种行为,在农村被看作是对一个人的轻慢和藐视。
陈根土觉得很没有面子,嚯地站了起来,拉着一张长脸对父亲说:“你是啥意思?”
“啥意思?就瞧不上你呗。”父亲挑衅道。
以前,父亲性格温和,很少跟人急眼,和陈根土的关系在村子里算是不错的,两家人的房子只相隔了几十步路,谁家里做了好吃的,有时候会端一碗给对方品尝品尝。
其实,陈根土那天根本不知道父亲生气的由来,顿时被这句话给惹恼了,准备走开离父亲远一点,父亲却不依不饶,把外套一脱,说:“要不我们也摔一次跤,要是你赢了,这包烟归你,敢不敢?”
父亲还没有从女儿小灵摔跤失败的气恼中走出来,更没有从陈根土那句“女不如男”的讥笑中走出来,他想给自己出一口气。
正坐着无聊的刘二成来劲了,立即在一边添油加火:“根土,这有什么不敢的?两人摔一跤比个高下,我来做裁判。不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切磋,点到为止,不能下重手。”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禁不住鼓动,父亲和陈根土就交上了手。
刚开始,两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僵持了一会儿,父亲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眼光扫到陈根土鼓鼓囊囊的裆部时,突然升上来一股莫名的怒气和怨恨,伸出右手佯装去抓他的腰带,手却往下一滑,在他的裆部狠狠地捏了一把,痛得陈根土龇牙咧嘴。陈根土对父亲吼道:“你下黑手,太缺德了。”抡起一拳,击中父亲的面门,鼻血喷出,涂了一脸。
局面顿时失控,两个人已经不管轻重,用尽全力只管将拳脚往对方的身上挥去。
这时候,陈根生的三个儿子——十五岁的大儿子陈明、十二岁的二儿子陈昌、七岁的小儿子陈峰怕他们父亲吃亏,也参与了进来,围住我父亲拳打脚踢。双拳难敌四手,一方力量彻底碾压另一方,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
那天,姐姐小灵和我也在现场,被这种场面吓傻了,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打斗中的父亲转过头来看了我和姐姐一眼,眼神中满是无助和绝望。
大家依然围在一旁看热闹。在当年的农村生活中,很多人都抱着看客心态,希望发生一些事情,给平淡如水的日子,增添一些乐趣和谈资。
发现再不干涉肯定会出事情,刘二成这时才站出来,将自己的身子横在父亲和陈根土与他的三个儿子中间,双方才停止打斗。
听说父亲与人打架,母亲和祖母也赶到了田地里,看到满是伤痕的父亲,都哭了起来,搀着他一瘸一拐地回家去。
在戾气十足的年代,打上一架,是高效解决纠纷以及发泄怨气的主要渠道,比较直截了当。赢的一方,趾高气昂,败的一方,垂头丧气。
父亲像是被打败的公鸡,只得认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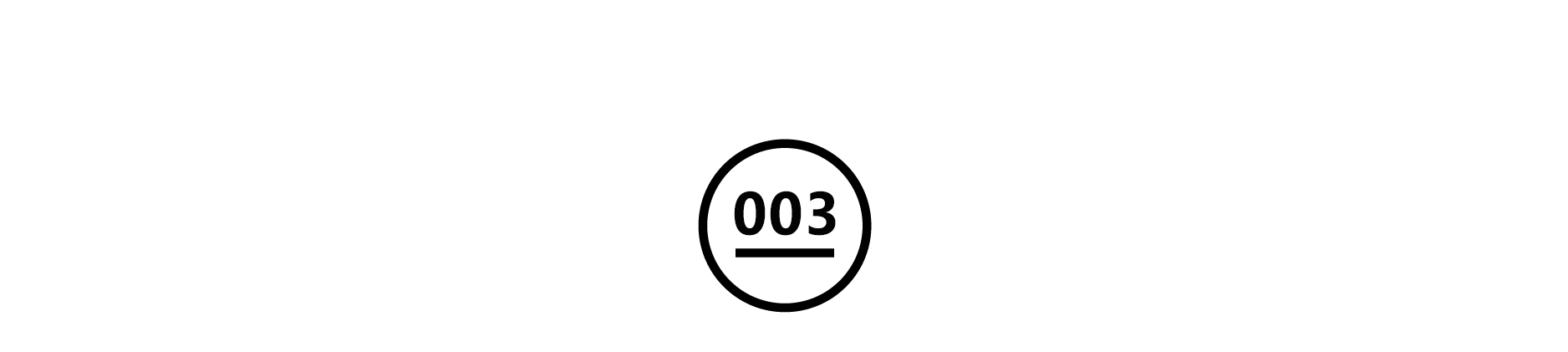 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根深蒂固,一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庭,常常不被人看重,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特别是经过那次与陈根土的打斗,父亲更加意识到儿子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重要性,要是自己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打斗时肯定不会吃亏。父亲下定决心,一定要生儿子,多生儿子。
在农村,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根深蒂固,一户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庭,常常不被人看重,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特别是经过那次与陈根土的打斗,父亲更加意识到儿子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重要性,要是自己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儿子,打斗时肯定不会吃亏。父亲下定决心,一定要生儿子,多生儿子。住在一个村子里,每天都抬头不见低头见,加上并无深仇大恨,在刘二成的调停下,父亲和陈根土又恢复了来往,为表歉意,陈根土某天还往我们家捎了三十个鸡蛋。
但此后父亲和陈根土的交往,表面上客客气气,实质里隔着一道沟坎。
特别是,父亲跨不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1977年春天,母亲怀孕了。孕妇贪嘴,母亲非常喜欢吃酸的东西,老辈人常说,酸儿辣女,孕妇喜欢吃酸,八九不离十生儿子,孕妇喜欢吃辣,八九不离十生女儿。这可把父亲高兴坏了,他经常自言自语:“我快有儿子了。”
在父亲的期待中,母亲分娩了,生下的是个女孩。
我非常喜欢这个妹妹,她小脸儿圆圆的,眼睫毛长长的,长大后肯定既漂亮又聪明。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放学回到家里,就去逗弄妹妹。但父亲决心已定,要把妹妹抱走。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什么事情完全由他做主。
妹妹出世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晨,母亲把她喂得饱饱的,给她穿上新衣服,还把一张写有她生辰八字的纸条放在她怀里。父亲把妹妹放进了一只竹筐里,提着它往县城方向走去。母亲在后面追了几步,又停住脚步,捂着脸轻声啜泣起来。
那些年,一般人丢弃孩子,主要放在县城的派出所门口、街路边或者菜市场这几个人员来往密集的地方。被遗弃的婴儿,除了身有残疾的,基本上是女婴。有的弃婴,会被人抱走,当儿女抚养;有的弃婴,会被福利院统一收养;有的弃婴会落入歹人之手,从小训练偷蒙拐骗的手段,替他们谋财。弃婴未来的命运,谁也不知道会怎样,完全凭运气。
那天,父亲将妹妹偷偷放在了县城菜市场的大门口,站在十几步开外的暗处,装着等人的样子,不时瞟上几眼。
没一会儿,竹筐前就围上了好些人,他们议论纷纷——“这当父母的真狠心,这么可爱的女娃都舍得扔。”一句句话像针一样扎向父亲的心口,他叹口气扭头就走,希望孩子能够被好心人收养。
那天放学回到家里,我跑进房间看妹妹,被窝里空着,问母亲,她扭过头装作没听见,我又问父亲,他粗着嗓子说:“家里轮得你多嘴多舌吗?早知道把你也抱给别人。”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掩住嘴,跑出了家门。
为了生儿子,父亲仿佛投入到了一场战斗中,经常带着母亲看医生吃中药,听说哪里的观音灵验,不管多远都要前去求子。
1978年,母亲又怀孕了。10个月后生下来,是女儿。满月后,父亲又将她抱给了别人。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话里话外都在责怪母亲,把不能生儿子的责任推到母亲身上。母亲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一边默默抹眼泪。
那时候我年龄尚小,但也隐约感觉到身为女性的无奈和悲哀。
村子里开始有了谣言,议论说:“刘家风水不好,绝对生不出儿子。女儿有什么用,以后都是要嫁出去的,撑不了门面,最多招一个上门女婿充充假。”
这话触碰到了父亲的痛处。
父亲把全部精力放在生儿子上,其他事情也耽误了。

进出村庄的道路
我们村子离县城不远,以前,忙完地里的活,父亲会进城帮人做做泥水活,赚点外快贴补家用。母亲在村子里开了一个缝纫铺,给人做衣服,那几年忙于备孕、怀胎、生育,铺子处于半开半关状态,根本没有什么生意,家里的生活条件与前些年相比,一落千丈,几乎成了村子里的贫困户之一。
连刘二成也看不下去,多次真心劝父亲:“命里没有的,别强求了,更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你看看我,无妻无子无女,倒活得轻松自在。”
父亲听不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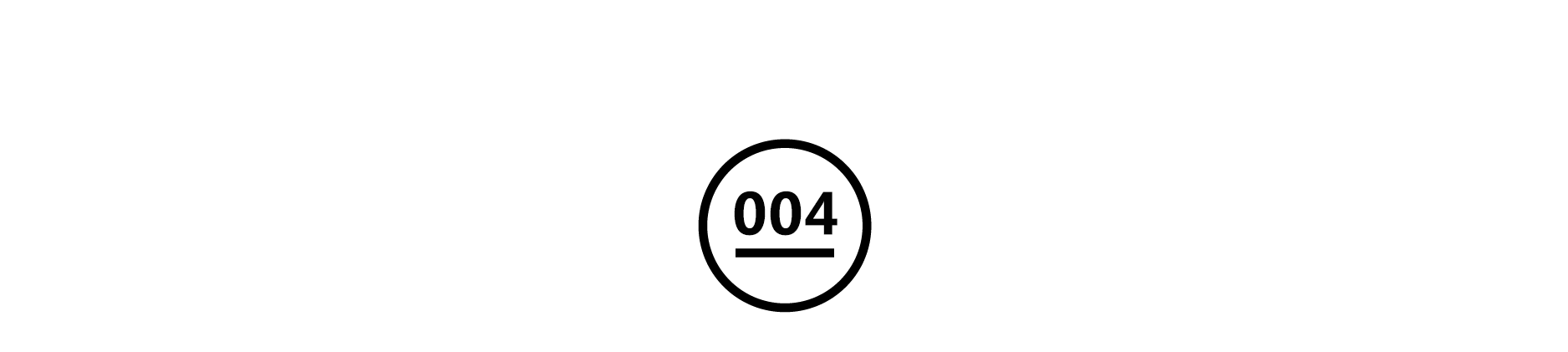 我十岁那年,母亲又有了身孕。为了尽早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父亲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一位远房亲戚的熟人在医院里做B超。一天,他提上一只老母鸡求亲戚的熟人给母亲做B超。对方刚开始不肯帮忙,父亲没有打退堂鼓,一次次地送东西,一次次地赔笑脸说好话。终于对方推辞不过,偷偷给母亲做了B超,结果还是女孩。父亲面无表情,让母亲把胎儿打掉。
我十岁那年,母亲又有了身孕。为了尽早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父亲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一位远房亲戚的熟人在医院里做B超。一天,他提上一只老母鸡求亲戚的熟人给母亲做B超。对方刚开始不肯帮忙,父亲没有打退堂鼓,一次次地送东西,一次次地赔笑脸说好话。终于对方推辞不过,偷偷给母亲做了B超,结果还是女孩。父亲面无表情,让母亲把胎儿打掉。这次流产,对母亲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她原来是村子里最好看的女人,经过这些年的折腾,皮肤松弛,目光无神,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大家都说她比同龄人显老。
一天深夜我起来上厕所,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轻声说话,母亲嘤嘤地哭了起来,说:“求求你让我过几年消停日子吧,我真的吃不消。”我屏住呼吸,生怕弄出响动,偷偷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父亲专注于生儿子,对于姐姐和我的存在几乎是无视的。
那年,姐姐读初中二年级,我读小学五年级,父亲不让我们去上学了,让姐姐去地里干活,让我烧饭洗衣做家务。父亲说,女儿以后要出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培养得再好,也是便宜了别人家,倒不如替家里省点钱。姐姐和我的成绩都非常不错,谁听了都觉得可惜。

地里种菜的父亲
学校的老师没有放弃我们,一次次来家里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但他油盐不进。那时,我的班主任有个朋友在派出所当民警,把他请过来,连哄带吓,父亲才答应让我们继续上学。
父亲没有关心过姐姐和我的学业,学校开家长会,他一次都没参加,我们拿回奖状,他看都不看一眼。我们姐妹俩越来越谨小慎微,在学校里几乎不跟同学交流来往,连在家里说话也都轻声细气,更不敢与父亲进行眼神对视,生怕引起他的不快。
之后两年,母亲没有再怀孕,父亲开始焦躁不安。
1982年9月,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父亲生儿子的计划彻底被终结。那段时间,父亲非常消沉。
但次年10月,三十九岁的母亲又一次怀孕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父亲不敢带母亲去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了,只是不停问母亲喜欢吃酸还是吃辣。
后来,父亲干脆什么也不问了,一个劲地让母亲吃酸的东西,把她折腾得老是干呕,苦不堪言。父亲还让母亲缝制了几件男婴的衣裤,说儿子的衣服要提前准备起来。
为了不透露风声,父亲让母亲足不出户,躲在家里养胎。后来又觉得不放心,便把母亲送到外县的一位亲戚家“躲生”。亲戚胆子小怕事,担心出什么意外,承担不起责任,半个月之后,又让父亲把母亲接了回去。
父亲怕母亲走远路动了胎气,专门借来一辆平板车,推着它去接母亲回家,大路不敢走,趁夜深人静,走乡间小道。
那天父亲和母亲回到家,已是凌晨,睡梦中被吵醒的我看到母亲一脸的疲惫,头发上沾满了露水,脸色苍白,身体瑟瑟发抖。而父亲倒是很兴奋。
此后,即使是大白天,我们家的大门也是紧紧关上,熟人要来家里走动,父亲也一概不接待。在家里,我和姐姐稍微发出一点声响,父亲就用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更不要说准许我们去外面玩耍了。
家里的气氛让我感到窒息。
没有不透风的墙,母亲肚子里的胎儿6个月大的时候,乡镇和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把母亲带走了。
父亲顿时傻了眼,等他火烧火燎赶到医院时,胎儿已被引产。父亲到现在还坚信,被引产的胎儿是个男孩。
这对父亲来说是致命一击,两颗眼珠子红得像血,头发根根竖起,像是要吃人。
从此父亲元气大伤,开始无节制地酗酒。很多个喝醉的夜晚,父亲号啕大哭,哭声传出很远,让人听了心里发毛。
可父亲似乎还没有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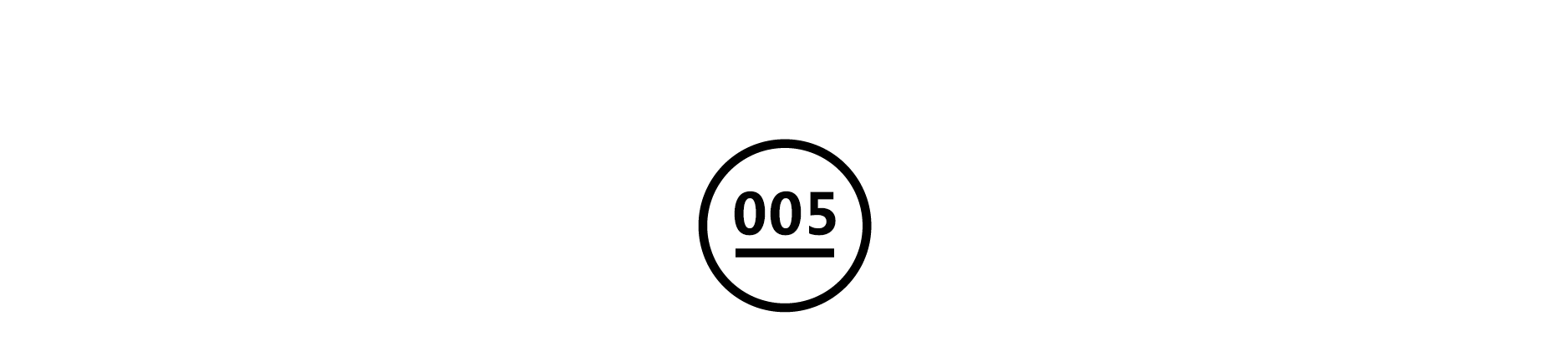 陈根土后来知道了父亲如此想生儿子的缘故,内心忐忑不安,不管什么场合,都躲着父亲。再后来,陈根土随在县城落户的儿子一起生活,很少回村子里。
陈根土后来知道了父亲如此想生儿子的缘故,内心忐忑不安,不管什么场合,都躲着父亲。再后来,陈根土随在县城落户的儿子一起生活,很少回村子里。在村子里,除了刘二成,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父亲来往。在村子里,父亲也只愿意跟刘二成说说话,没有后人的刘二成,在父亲眼里,跟自己没有什么区别。
一天晚上,父亲去找刘二成喝酒,几杯白酒下肚,父亲有了醉意,大着舌头对刘二成说:“二成,求你一件事?”
刘二成说:“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父亲说:“我身体已经不行了,干脆你跟小灵妈帮我生一个儿子……”
父亲已经狂乱到了这种程度。
刘二成听后,把酒杯往地上狠狠一摔,怒吼道:“你真是一个畜生,真是一个浑蛋,我刘二成虽然是又懒又浑的光棍汉,可干不了这种不要脸的事,你快滚吧。”
父亲跌跌撞撞地走了,那天他真的是喝醉了,连自己家也进不了,在门口睡了一整夜。
从此,父亲终于死心,经常长时间地坐在门口,沉默得像一棵枯树。
在这场生儿子的战斗中,父亲彻底地败下了阵。
那时候,姐姐在县城读高中,我在镇里上初中,两人都住校,周末可以回家,但我们总是找借口呆在学校,害怕回家。
不久,刘二成搬去了外村,也与父亲断绝了来往,他原来的老屋荒弃至今,墙上爬满了藤蔓。

刘二成爬满藤蔓的老屋
8年前我在路上碰到刘二成,他偷偷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听后,感觉有股寒气从脚底升起,一再告诫刘二成一定要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就像是路边的骆驼草,姐姐和我无声无息地长大了,先后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又都找到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偶尔,我会想起被父亲抱出去的两位妹妹,不知道她们现在生活在哪片屋檐下,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想起她们,想起的话,会不会感到内疚和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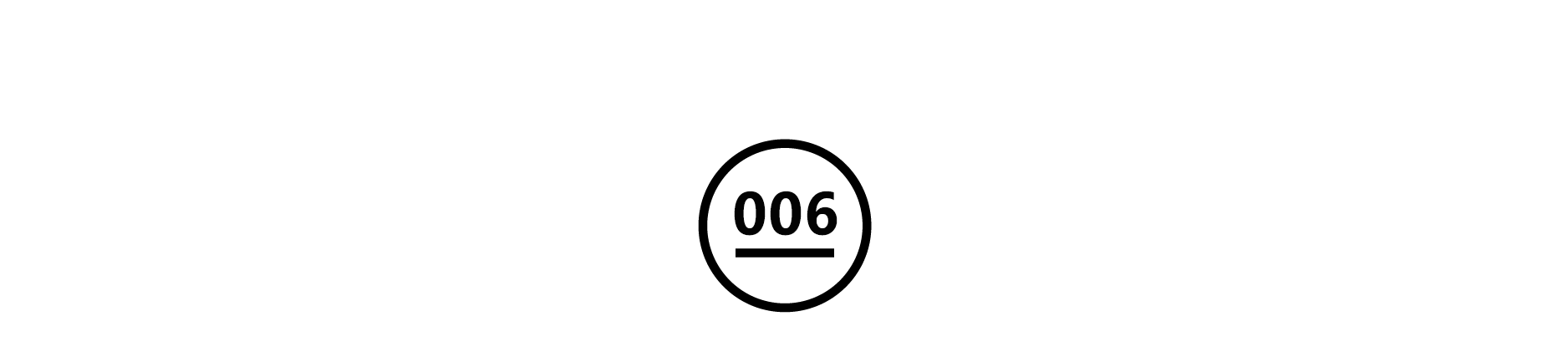 我结婚后,一直推迟生育,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个阴影。
我结婚后,一直推迟生育,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个阴影。婚后第3年,我怀孕了,却一直被肚子里胎儿的性别折磨得喜忧参半。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当我得知自己生下的是一个女儿,几乎不知所措。这时,丈夫和公公婆婆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位小公主,我们太喜欢女孩子了,真的。”
“真的”这两个字,让我顿时流下了眼泪。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由作者提供)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症候的非虚构作品等。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