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锐评 | 徐江玥:《十七岁的单车》:述说时代心事的青春残酷物语
《十七岁的单车》:述说时代心事的青春残酷物语
徐江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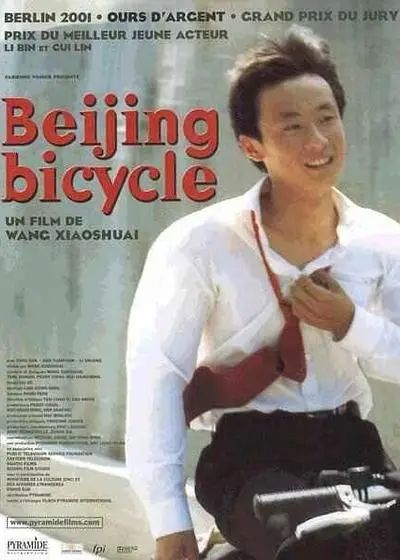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在访谈中,王小帅曾说:“我影像中的青春,往往遭遇自己内心的挣扎和外界的暴力,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告白人们,他们就此失落了自己的爱情、友情或亲情等等、等等。他们的反抗、异端、先锋乃至边缘性,往往被主流电影所忽略......”而《十七岁的单车》书写的正是青年的反抗、异端、先锋乃至边缘性。《十七岁的单车》英译名是“Beijing Bicycle”,这就十分耐人寻味。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部影片与城市,以及青春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它诉说的既不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并非十七岁少年的意气风发。相反,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青春残酷物语:无论是单车身上被寄予的希望与失望,还是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命运,或是电影在拍摄时流露出来的冷酷和倨傲,抑或是影片背后导演与电影行业无法直言的心事,都为我们呈现了冰冷的社会现实。
寄予单车的青春残酷物语
在开头,电影就将呈现了一组农村进城务工青年的群像,将其置于被观察的地位:黝黑的面庞、操着不知何处的乡音、被动地回答着仅在画外音中出现的面试者的问题。乡村青年进城务工的茫然、无知或无畏的面孔就这样被展现在观众的眼中。这样镜头的设计也充分表明了在当时城乡之间依旧割裂的场景:乡村青年对城市的懵懂与向往,与城里人对乡村人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大批农村人员进城务工,而小贵无疑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进入城市的时候,除了物质上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身份上的模糊与迷惘。在这批人走进城市的时候,城市用自己的规则对他们进行着改造。在开头,快递公司聘用了他们之后,就带他们洗澡、剃头、换了衣服。统一的米色工装、帽子,将这些来自各地的乡村小伙变成了城市运转线上同质化的部件。最重要的是,公司给他们每人发了一辆崭新的灰色自行车。这辆单车就此成为了小贵最大的依靠与精神支柱。影片特意呈现了小贵在刚拿到单车骑行时的喜悦:晃动的镜头,穿梭的身影,微微抿着,似乎在忍住笑意的嘴角,飞快的速度,无一不表现着他的喜悦。然而,即使再开心,即使是面对熟悉的同乡,他也没有吐露出多少言语,只有在同乡问他问题时吐出几个语气词来。
在这里,小贵作为“失语者”的形象被直观地呈现。事实上,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尽管作为主角,但小贵的台词寥寥无几,即使是必须开口的时刻,他也经常只能吐出简短的字句。这一方面是因为小贵本身处于一种不知如何发声的境地之中,他的不适应,他的内向,他对于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和隐忍,都让他不会有很多言语;而另一方面,导演有意或无意的略去了几乎所有的小贵长时间发声的镜头:无论是在他与同乡的交谈,还是他后期与小坚以及小坚父亲的交涉中,电影都直接以交谈对象的反应呈现出他们对话的内容,而这具体的谈话内容是可以预想得到的繁复与艰辛。这恰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个体的被沉默。这里被沉默的个体不只是实际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物,更映射着第六代导演们在权力边缘游走的暧昧地位,是精神上被边缘的一批人。
而作为城市化的标志,单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符号。当我们来观察单车这一物象时,会发现单车对于小贵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是他的生活依靠,更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异常珍视这辆单车,小心地擦拭,甚至还在上面做上标记。他在本子上一笔一划记下记正字,盼望着自己真正拥有这辆单车的一天。而伴随着小贵在城市中穿梭的镜头,一切都仿佛走上正轨。但时不时出现的窘迫局面始终提醒着小贵:你不属于这里。不管是和经理交涉时经理的不耐烦,还是误入酒店澡堂被洗澡,甚至是同乡坚持刷牙并喊他一起,都让小贵处于一种撕裂的境地:城市生活与他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单车被盗会对小贵造成如此重大的打击。他年轻的生命还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考验,因此一下子就慌张起来,甚至连工作都全然抛之脑后。最终也直接引来了老板的解雇。小贵没有求着老板不要解雇,也没有转头去找新的工作,却说自己能够找回单车,仿佛找回了单车,就能够重新拥有一切。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小贵已经将单车作为自己唯一的出路,仿佛抓住它就能成功在城市容身,也能够让自己拥有认同感。
与之形成镜像的是单车之于小坚,作为原住民的小坚相比小贵处于更中心的位置(也仅仅是相对的更中心一点而已),而这一回,边缘不再只是单纯的被看,相反,小贵和小坚之间通过单车建立起了联系,边缘和中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着互动。尽管同样是17岁的少年,但在这里,单车对于小贵不再是融入城市的工具。对于青春期的小坚而言,单车象征着身份与地位,也是爱情争斗场的入场券,是小坚青春期反叛的标志。无论是偷家里钱以取得单车,来反抗父亲的一再出尔反尔,与重组家庭中他的不受重视;还是取得单车后他与同伴们一起苦练技术,进行高超的炫技;抑或是拥有单车之后他得以与自己心爱的女孩共同上下学,都是小坚青春期反叛的表现。在这里,单车成为了小坚指认自我的工具,在拥有单车时,小坚才认为自己拥有了求爱的权力,而在后期失去自行车时,他就会生气地拒绝主动来找他的女孩。在这里,某种阳具崇拜被加之于单车。只有拥有单车,小贵才拥有了自信。事实上,围绕着青春悸动的所有话题也全都与单车相关,从他与潇潇的初遇,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包括潇潇在对小坚有好感并夸赞他时,说的也是“你的车蛮好的”。然而,后面我们会看到,单车之于小坚和潇潇的意义并不一样。
再重新拿到单车后,小贵骑着单车绕着潇潇来回骑动来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此时,更高的权力拥有者已经夺走潇潇的喜爱。小坚被屈辱地当成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甚至被送了一根烟。而烟向来隐喻着男性权力。事实上,烟在两位青年的生活中都扮演了权力的角色。小坚和朋友们抓住小贵并和他“套瓷”的时候,就递给了小贵一根烟,小贵一开始被呛的不行,后面却会偷偷拿起同乡未抽完的烟,深深地吸上一口;而在被屈辱地递烟之后,小坚身上也随时带着一包烟,甚至成为了他表示友好的工具。烟成为了暗示他们心理历程变化的物像,在电影中穿插出现。
可以说,单车之于两位少年意义的两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完整的“青春残酷物语”。一方面是初入城市的乡村青年对自己在城市中主体位置的找寻,另一方面则是青春期中男性渴望在两性关系中获得权力。当然,这二者事实上在彼此的故事中均有体现,但又有轻重之别。同样,单车又勾连起了这两个不同却又无比相似的个体,他们经受着青春期的各种风浪,他们在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走着近乎一模一样的路,意气风发、被打击、不甘心,甚至都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抽烟,最后都选择了拍砖,以及可以预见的,他们未来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的苦难。就这样,这种边缘人物的命运悲剧性在本部影片中达到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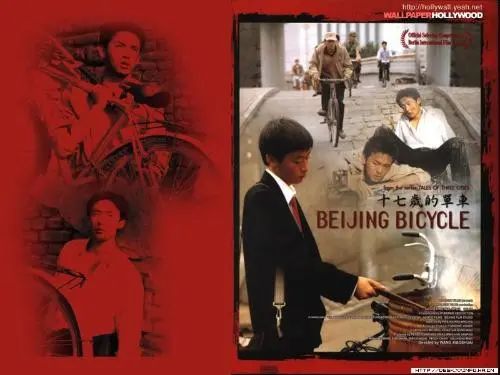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而这样的“单车”事实上不止一辆。在电影中,经常出现地面视角的单车车轮镜头。第一回是在小贵接受面试之后与身份改造之间,紧接着就跟着多个车轮滚过的画面。模糊的,连续滚过的车轮,昏黄的背景,营造出沉郁的气氛,暗示着小贵成为其中的一员。第二回则是在小贵决定去找单车之后,出现了对北京街道上单车涌动的镜头,从俯拍,到最后回到地面,出现密集、滚动的车轮。这不仅是对小贵寻找单车难度的暗示,也暗示着这样的单车只不过是北京九百万单车中的一辆罢了。或者说,小贵这样处于边缘,苦苦谋生的人,只是无数进城务工青年的一个缩影;而小坚也只不过是各有各的不幸中的一种不幸,尽管这样的不幸对个体而言已足以毁掉生活。
影片的结尾,伤痕累累的小贵终于拿起了砖头,狠狠地砸向正在破坏他单车的人,暗示着他的改变与反叛意识的觉醒,尽管也许来的太迟,也为此付出了太多代价。浑身是伤的小坚最后艰难地靠着墙站起来,看着小贵扛起了已经被砸的稀烂的单车,慢慢走出胡同,走入了北京的单车流中,镜头拉远,好像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仿佛是留了一个悬念,然而,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故事的结局早已被隐秘地预示出来。
红与灰:女性角色身上的隐喻
影片整体色调始终是灰黄的,而最为明艳的色彩均出现在戏份不多,但意蕴深刻的女性角色身上。高饱和度的、明亮的色彩不仅代表着女性,更代表着一种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这样的明亮在整部影片灰色的基调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饶有趣味。首先,不可否认的,两位成年女性表面上都是作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出现在影片当中的。无论是小贵在同乡的指引下窥视窗内的红琴,还是小坚对潇潇的靠近与追求,均反映了男性欲望凝视下的女性个体。而在影片情节上,女性也作为被争夺的对象推动了剧情的高潮迭起。甚至两个女生代表的两个不同的类型也恰恰是所谓红白玫瑰的幻想:一个艳丽张扬,一个温婉内敛。
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仔细去看这两个角色时,会发现她们的身份并不仅限于被凝视的对象,甚至于,仅用性别理论的中“视觉快感”来解读是有失偏颇的,她们更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另一种生活状态,只不过一个是一场美梦,终要破碎,一个则是实实在在的另一个世界;二者互相对照,再次呈现了城乡之间的割裂,让我们从更深入的角度去观察时代的角落。
我们不妨分别仔细来看。先是红琴。红琴的每一次出场都十分夺人眼球。同乡和小贵总是透过墙的裂缝去窥视高高在上的红琴。在窗中时,她既是被凝视的对象,也是凝望着窗外的人。尽管她总是身着鲜艳的服饰,但在窗户中出现时她始终是忧郁的,彷徨的。而她第一次出现在小卖铺,则是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踩着红色的高跟,涂着鲜艳的口红,哒哒的高跟鞋声成为了同乡和小贵辨认她的标识。她就是同乡和小贵心中城里人的象征:穿的好,漂亮,住的好,但是忧郁。可以说,小贵和同乡对他的凝视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而是男性对权力的凝视;同时,红琴也在这样的凝视中获得了被认为是城里人的假想性满足。可以说,这一场看与被看是双方的欲望共谋之下的结果。她穿的如此明艳,以至于同乡和小贵都下意识地忽视了与之格格不入的酱油瓶。此后每一次出场,红琴都穿着不同的艳丽服装。直到最后,红琴冲进小卖铺翻找,却被两个穿着时髦的人叫走,其中的女儿正穿着与红琴打酱油时一摸一样的红裙。至此,谜底终于被揭开:红琴原来只是从乡下来的保姆。而她最后的命运也就是:走了,不知道去哪了,如所有不被重视的人一般无声息的消失,无人在意,无人找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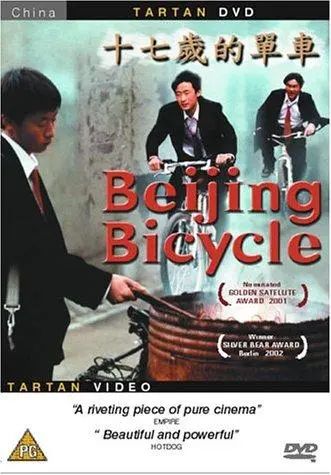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潇潇。尽管影片中没有直接给出潇潇的家庭背景,但从她的住所,以及她的一言一行,我们都能看到她与小坚,以及红琴的区别。比起红琴每一次出场都无比艳丽,潇潇每一次的出场都并不张扬,相反,可以说总是带着“岁月静好”的气质。如果说这一区别在小坚还拥有单车时并不突出,那么在小坚单车丢了之后,他们的区别就体现的格外明显。尽管单车丢了,但潇潇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说出了“再买一辆就好了呀”的话。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展现出一辆单车对于潇潇的家庭而言并不是负担。同样,在潇潇的心中,单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眼前帅气的人,于是她又提出“我骑车带你”“你骑车带我”的建议,而这恰恰表现了身在优渥条件中的人总会下意识地忽视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缺少这一条件的人却会对此耿耿于怀,正是所谓“越强调什么,越缺少什么”。但对于小坚而言,这是他的尊严,是这段关系维系的基础。于是,潇潇与小坚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终结。因为他们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也因此,尽管在小坚的视角中,自己重新拥有单车就能重新夺回女孩,但结果却是必然令他失望的。
而对于灰色,我们仅用影片最主要的场景来简单的进行阐述,这个场景就是胡同。它构成了最大比例的灰色主体。完全不似今日人们对胡同具有传统文化特色、住在里面的人都是有钱的北京土著的印象,影片中的胡同代表着落后与破旧,身处其中的人也都是穿着朴素的大爷大妈与小孩子,大多是搬着凳子在胡同里坐着,看着发生了什么事,也只会看着。他们成为了观众在剧中的替身,也构成了整部影片沉闷的基调。尽管与王小帅的前期电影相比,《十七岁的单车》已经是相对而言更明亮也有更多的动人的小细节的一部作品,但其中从影片本身来看,主旋律依旧是偏压抑的。
于是乎,青春的残酷物语最终的结局在灰色的胡同中,借由这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体现出来。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对于城市的想象已经被限制在了外表的时髦与明艳,但仅仅经由外表的改造却绝对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一如飞达快递公司对员工的改造般无力;而对于青春期浪漫关系的幻想也绝非系于一辆单车,拥有单车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拥有全世界。尽管有反叛与对抗,但依旧显得十分无力。就这样,影片为我们揭示了最冷酷的真相。
主旋律之外:时代的另一面与自我心事的倾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于国内国外而言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伴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开始,经济发展的春风似乎要刮到全国各地。在这个时代,既有人乘势而上一举成功,也有边缘人物苦苦挣扎而不得,陷于漩涡。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讲述后者的故事,其实与导演,与整个电影业的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逐渐开始真正创制电影的第六代导演们或许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路。20世纪90年代,国家加大了电影方面的意识形态宣传,花大力气推出了几部主旋律影片。这些影片也取得了不差的反响,但依旧无法改变国内电影行业衰落的局面:电视的兴起,盗版录像带的流行,以及后期好莱坞电影的引入,都让国产电影不复当年的荣光。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随着国企改制而不断调整,最后大多也逃不过关闭的结局。也因此,大多数第六代的导演都选择了自立门户,或自己集资,或接受来自欧洲的资助,他们的视角也大多集中在了物理意义上的社会边缘群体。王小帅也正是这样一位从国内电影制片厂“逃出来”的导演。然而,在特殊的时代,他们的意愿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原本是为了为自己的影片寻找承认的努力,即选择直接进军国外,最终也变成了政治意味十足的行为,他们的电影也被称为所谓的“独立电影”,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自不必多说。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既要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又要反抗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阐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边缘、个体成为了他们影片的主要题材,而不管是哪一部影片,通常都或隐或显地表达着边缘对中心的突围,或是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这不仅仅是时代的主旋律背后的另一面,更是他们自我心事的倾注。王小帅同样如此。他的代表作《冬春的日子》就是一部极低成本制作的电影,也直接去参与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并因此被列为禁片。而到拍摄《十七岁的单车》时,他已经获得了相对充裕的支持,甚至在2004年送审后被“解禁”,得到了在国内公映的机会。也因此,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作品也和以往的作品有比较大的区别,其中故事的主题就不再仅仅是单方面的边缘向中心突围,而是小贵和小坚二者分别作为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的互动,他们的互动又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于是形成了二重的互动关系。这部电影在整体的风格上也更为阳光,尽管依旧是现实主义的底色,关注着边缘,先锋与反叛。因此,影片对边缘人物的述说,不仅仅是反映时代的另一面,更是20世纪90年代电影行业与第六代电影导演们内心声音的投射。他们借社会物质意义上的边缘,书写着底层百姓的生活,也书写着自己身为精神边缘人的心声。
参考文献:
[1]傅莹. (2007). 激情所关注与生命所坚持的——第六代导演王小帅访谈录. 文艺研究, 08, 69–78.
[2]聂伟. (2006). 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王小帅论.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85–91.
[3] 戴锦华. (2000). 雾中风景 (1st ed.).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与文化批评》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冯萱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 | 徐江玥:《十七岁的单车》:述说时代心事的青春残酷物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