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让布罗茨基与苏珊·桑塔格推崇的作家,小说首度中文译介推出

近期,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长篇小说《狐狸》由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引进出版。
杜布拉夫卡1949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大学就读期间,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渡过意识之流》《谎言文化》《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多谢不阅》《疼痛部》《Baba Yaga下了一个蛋》《狐狸》等作品,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获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国际布克奖提名,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短名单。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她拥有一双局外人的眼睛,苏珊·桑塔格称赞她是“一个值得被仿效的作家。一个应当被珍惜的作家”。
杜布拉夫卡于1993年离开克罗地亚,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她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的写作者。今年3月17日,她在阿姆斯特丹去世。
《狐狸》分为六章,也可视作六部交相影绰的中篇,但最终,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物命运彼此互文,密度极高的文本碎片层层嵌套。杜布拉夫卡以各个文化中古老神话都具备的“狐狸”为原型,逐层揭示了“故事之为故事”的奥秘。
选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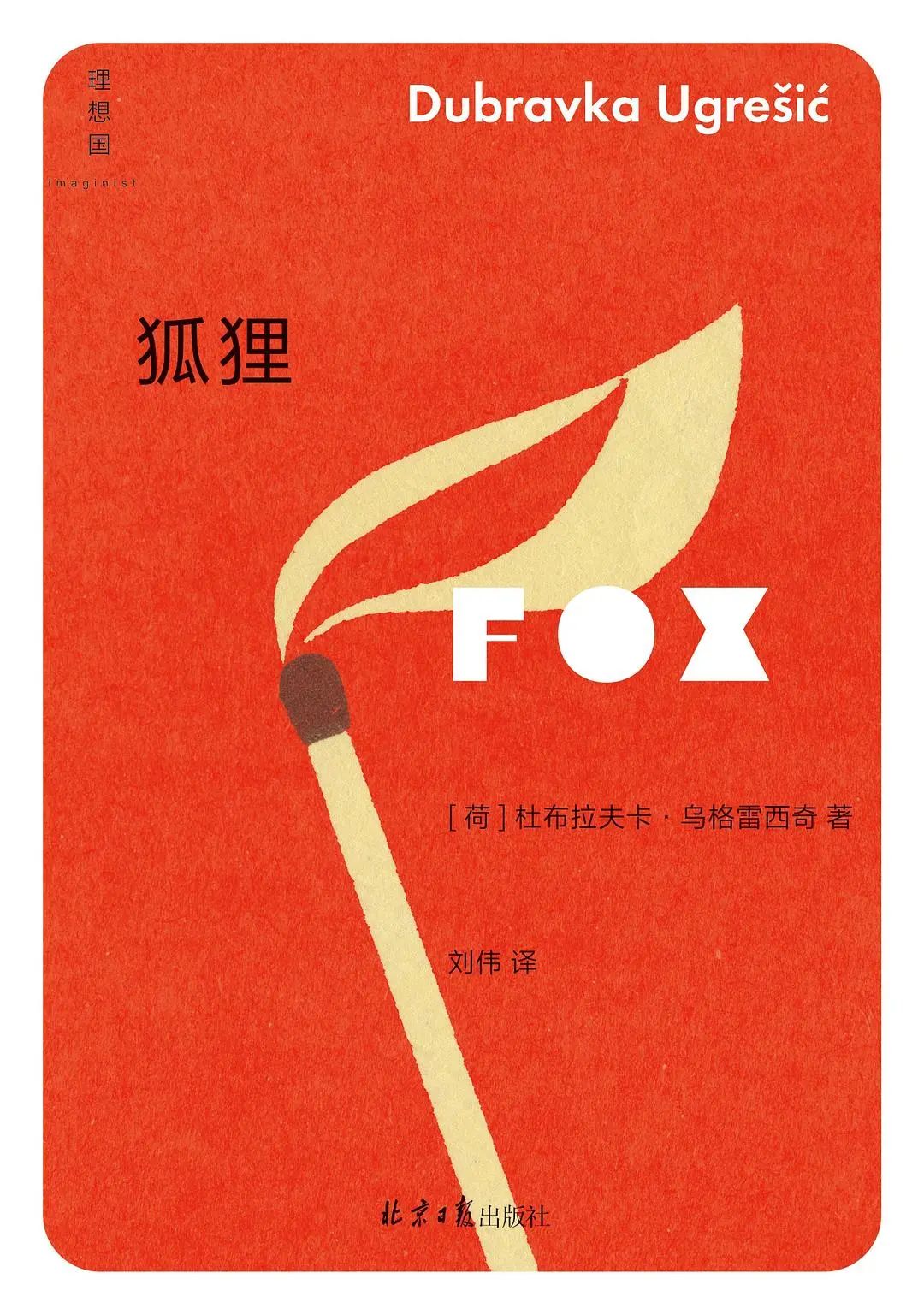
收到菲利斯的书一两个月后,我在网上搜索书评,寻找其他人读过它的迹象。同时,我也用谷歌检索了多伊夫伯·列文的名字,收到了跟以前一样的结果,但这次,我点开其中一个网页,本能地按下了打印键。直到第二天,我才想起去打印机上取打印出来的文字。就在我准备把它扔到废纸篓之前,我碰巧扫了一下那篇文字。它比我想象中要长。我检查了电脑显示器上的网页。一切都是它应有的样子:列文出生于哪一年,写了哪些文章,死于哪个时间。然而,打印出来的版本上却穿插着其他句子。这些句子并不像一个梳子的齿和另一个梳子的齿那样紧紧咬合在一起: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关联。插入的文字是胡言乱语,是阻碍信息流动的噪声。比如,在“1922年,多伊夫伯·列文进入彼得格勒的大学”这句话后面,跟着这样一个句子:“真是不可思议,蜘蛛侠对此一无所知。”虽然这两句话在理论上可以联系起来(第二句对第一句提供了有趣的评论),但后面的句子却是无稽之谈。我试着找出网站和这些胡言乱语之后的联系,一个隐藏的信息,但没有结果,这些句子都是被拆散的文章的碎片,没有一句能和其他联系起来。最后一句是:“就连安娜斯塔西亚·斯托茨卡娅都无法想象这种事情。”我猜这可能是某本小说中的一句话,或者藏着一个谜语。直到我明白安娜斯塔西亚·斯托茨卡娅并非虚构人物,而是一位风头正健的俄罗斯明星时,我才死心。

我启动杀毒程序,但电脑似乎是干净的。我又给几个熟人打电话,他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有人提示说,我看到的是附在正文上的早期版本,显示器上通常看不到修订痕迹,但由于某种电脑故障,它们显示到了打印的版本上。“一个很常见的小故障”,我的熟人说。我说什么都不能让他相信,这根本不是我对文本所做的修改,这个小故障也根本不常见。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我不想深究了,特别是因为我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它吸引了我的想象。
如果文字是一层一层叠加在一起的呢?那种印在无限小的透明层上的隐藏文字,但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因为它们永远隐藏在视线之外,只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像多伊夫伯·列文的网站那样,以可读的形式出现在电脑使用者眼前。如果有很多这种“粘附”的层次,而我们的眼睛却无法察觉呢?如果这些文本事实上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它们的连贯性呢?如果我们人类其实也是活生生的、呼吸着的文本呢?如果我们带着无数修订版的自我涂层走来走去,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呢?如果关于其他人(一个,两个,一千个?)的短评附着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呢?如果这些文本和我们融合在一起怎么办?如果我们所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被秘密的逗留者栖居过怎么办?为什么我被困在那个关于多伊夫伯·列文的脚注上那么多年?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是菲利斯梦见了关于列文的文字?还是关于列文的文字梦见了菲利斯?
不管怎样,菲利斯对于列文生平的迷恋可以简单解释为:她将自己的生命视为附加在文本上的脚注,而不是文章本身。由于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二流地位,所以把自己包裹在同样二流的多伊夫伯·列文身上,用自己的呼吸温暖它,好像它是一只冻僵的鸟。她对多伊夫伯·列文传记的还原可信吗?我无法确定。我只知道它表面上是可信的。事情完全有可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多伊夫伯·列文完全有可能是伊琳娜·菲利斯的生父。也许菲利斯知道父亲的存在,也许她把列文当成了自己想象中的父亲;也许那个拥有强大武器——印章——的“漂亮共青团姑娘”其实是她的母亲。我们别忘了,列文的同胞L.潘捷列夫和他碰面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我想知道他们的女儿艾拉现在在哪里。她多大了?七岁?”
菲利斯把自己裹在书中,好像那是她给自己织的一条简陋的围巾。她钻进自己的书里,就像一只老鼠钻进车轮奶酪,打算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它那小小的心脏停止跳动。在为列文树起一座纪念碑的同时,她把自己也埋在了同一块墓碑下。在菲利斯进入自己书中的那一刻起,她对于列文生平的发掘是否真实的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虽然菲利斯一点都不像真实艺术协会的成员,但她的姿态配得上它。
那么我呢?我又如何?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固执地吸附在我身上?菲利斯对列文的迷恋很容易理解:俄语是她的母语,她的噩梦与俄罗斯某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紧密相连,在她的噩梦中,历史像嗑南瓜子一样无情地蚕食着人类的生命,留下了一堆又一堆空壳。

1975年到1976年,我在莫斯科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承认一个关键的细节:我之所以没有任何恐惧,不仅仅是因为我年轻,也完全是因为另一个不牢靠的小东西:我的护照。凭借我的南斯拉夫护照,我被当作西方人对待,这意味着在除了短缺一无所有的莫斯科,我享有某些优势。当时我正在读《大师与玛格丽特》,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我真诚地相信手稿是烧不毁的,我为什么会牢牢盯上列文,把他当作一件微不足道的纪念品、路边一颗灰色的鹅卵石、一个文学脚注、一本不存在的小说的参考资料呢?然后我继续把他当成一件永久的精神财富。我对多伊夫伯·列文的同情,似乎并不仅仅是对一个脚注人发自原则的同情,事实证明,它预示了我接下来的经历,尽管我(当时)发誓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柏林墙倒塌仅仅两年后,我那个位于欧洲南部的小国家就崩溃成了六个更小的国家,我们那个小语种也分裂成了三四个更小的语种。家庭被拆散,父母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国家,而孩子们在另一个。
(《狐狸》[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刘伟/译,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4月版)
原标题:《让布罗茨基与苏珊·桑塔格推崇的作家,小说首度中文译介推出》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