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所有人都在挖掘慰安妇的痛苦,他却用镜头捕捉她们最后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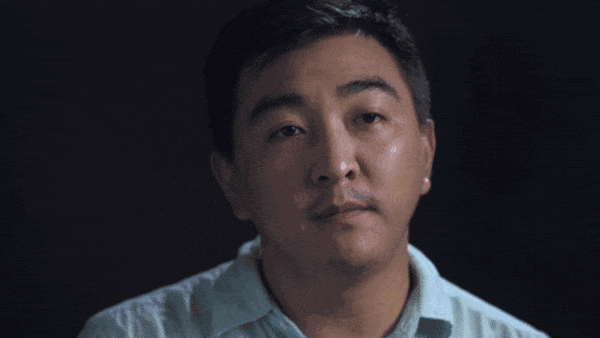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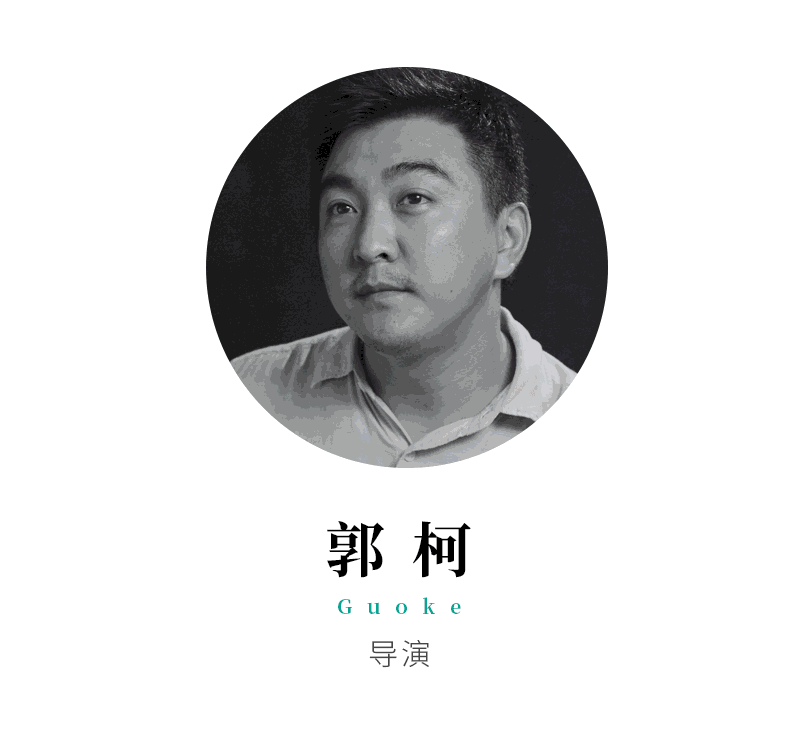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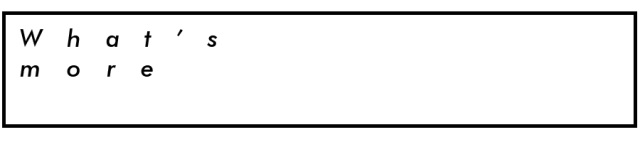
在Figure与郭柯导演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会有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打动我。导演的工作室在燕郊,一个普通小区的二楼,如果不是真的到过现场,你是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导演的工作室。参访当日,天气比较闷热,我们到达他的工作室之后,竟然发现里面是没有空调的,只有一台立式风扇,在拼命地摇头。
两年前,我在无意间看到了《三十二》这部纪录短片,知道了郭柯的名字。那个时候不论是他电影的叙事手法,还是对电影的镜头运用,已经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我觉得一个导演用了精致的音乐,用了唯美的镜头,采用一种新的视角去切入「慰安妇」——这群老人的生活,一定是想要去获奖的。

我不希望,他也是一个利用这群老人当作自己人生的助力器的功利主义者。两年后,在记录电影《二十二》海报里,我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也是我决定拍他的主要原因。
《二十二》算是郭柯的第一部长篇作品,此前他做了十几年的副导演,也合作过相当多的知名导演。他是有极强的创作欲望的,他也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去呈现这部作品,然而他还是以一个非常克制冷静的视角来记录「慰安妇」的生活现状。我觉得这一定是需要冲动和勇气,去完成的。
有很多时候,总会有一些人习惯性把「创作」这个词挂在嘴上。然而,在与郭柯导演的交流中,他却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没有创作,我只是去捕捉。」我的印象当中没有哪个导演愿意把本该属于导演的创作权利剥夺掉。他算是一个。
关于影片,他尽可能克制了自己的表达欲望,只有合适的距离,适当地捕捉,而恰恰正是他的捕捉,却从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曾经遭受苦难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她们不再是某个纪念日的封面,更不是某些人贩卖感情的借口。

郭柯并不想让人们更多的去关注到他本身,他只希望在老人的晚年,能有更多的人真正了解到这些老人的现状,能再静下心来听她们聊聊天,讲讲她们的故事。也许,这也将会是最后一次了。
自述 | 郭柯
遇到了慰安妇这个群体的时候,我觉得影像的价值就真的体现了
做纪录片是巧合,是因为老板觉得做剧情片的投资太大了。他预估的那个剧情片会上千万,所以他看了我的故事大纲,觉得投上千万给我可能风险有点大,就说能不能先投几十万我们试试,因为我在剧情片里面会涉及到这位老人的真实的画面嘛。先把剧情片需要老人的画面留下来,因为老人年龄大了,怕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所以先去拍。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慰安妇这个群体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就真的体现了,它可以把一些好像是快要消失的群体留下来,所以我当时觉得原来我们拍片子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做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所以我做了第一部短片以后就在一年以后,就在准备这个《二十二》的一些拍摄。
是韦绍兰老人改变了我
《三十二》是有一些表达的,包括一些机位什么的,我们都是有一些精心的选择。其实在这些精心的选择背后,还是一些剧情片的拍摄方式,但是我觉得对于纪录片来说可能不太真实,比如说摆好这个构图以后,你会请老人去在这儿走一下,或者是从这儿路过一下,但是你就违背了纪录片的这种真实的记录,它就不是纪录片了,它还是一个剧情化的片子。
以前我们还会有些辅助器材,包括剧情片都知道要用轨道,要用电子炮我们都拿过去了,但就会觉得特别假,因为我们也在不停的在摸索和进步的当中,所以我们觉得《二十二》的时候我们会退得更远一点,当然你退得远,这个事情就平淡了,这个事情就显得没有那么大的冲突了。所以拍摄《二十二》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连辅助器材都不要了,带着机器,带着脚架我们就去了。
说的矫情一点,是韦绍兰老人改变了我。她让我褪去了很多虚荣的东西,《三十二》这部片子获奖了以后,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是在得到满足的同时,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老人,你从她身上获得了那么多的东西,而她依然过着她自己的生活。你又是获奖,又是展映,又这个,又是那个,然后你背后你想想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944年的时候,韦绍兰是被日本人在山头抓住的,那一年她是24岁。所以我基本上是问她十几岁的时候,我记得结果完全没想到她,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在小时候到山上放牛,然后会遇到她们对面村里的一个爹爹,然后就叫她唱歌,她就回忆起来,她就完全停不下来,然后又开心,脸上又笑,有时候还会害羞,所以听她聊这个的时候,她就说她唱歌的时候,那当然想请她唱一下,她有点不好意思,再三请求下她还是唱了,最后我们也拍到了片子里。
我觉得我拍到一个不一样的老人,不能说不一样的老人,我觉得拍到了一位不一样的受害者,我们大家都会把「受害者」这三个字强加于她身上,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她身上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受害者」,但是大家忘了她是一位老人,是一位活生生的老人。
那一部之后,我就开始有一些认真的重新的思考,对于慰安妇群体她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她们,没想到她们身上有那么可爱,又那么积极,又那么能让我们去反思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时找到了方向。
我们从不离老人很近,怼着她拍,这是一种压迫感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题材来说,一个导演他要去创作可能不太对吧?我觉得我们把摄影机摆她门口已经非常明确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处于尊重来说,也不能把机器怼得那么近,我会退得很远很远,然后用变焦镜头推上去,我们从来不离老人很近,怼着她拍,这是一种压迫感,所以我以前接受的这种不管是教育也好,还是学习也好,一定是要尊重你的拍摄对象,要尊重你的演员。

我不会一上来说我们今天要表达什么,表达什么呀表达,对吧,我没有什么创作,不要表达。摄影师到了现场,不是先去摆镜头,我们先看看老人坐在哪儿,然后我们才去想,该怎么去捕捉。
捕捉是我们每天要做的,我会每天跟老人做什么,我就去沟通,比如说奶奶今天会做什么,她几点吃饭,她下午要做什么,中午睡了午觉,她下午要干嘛。我去了解她每一天的一些状况,然后来安排我们每天该拍什么东西。录音师也是,先听现场环境里有什么声音,然后最后再去收音,可能我们一个话筒收不到,我们可能用别的话筒去收。
我拍的时候,没想到要进入院线
2014年想拍的时候,我就没说这个片子一定要进入院线,也没考虑那么多,所以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当时是没考虑观众的。我为什么要拍?是因为我有感觉,有了感觉我想去纪录它,所以我会把我最直观的感觉放进去,我觉得加音乐,用资料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我们是在做减法。为什么要拿这些东西去烘托她的情感呢?我觉得老人坐在那儿就已经有情感了,你去提炼它们嘛。
我们去到老人家里边,你远远地看她不可能音乐就起了,不可能旁边拿的手机给你音乐起,这种东西是特别主观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她伤心了,音乐起。音乐起的目的是什么呢?来你们该伤心了,该哭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贩卖这种廉价的情感。
这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尊重什么?尊重观众的经历,尊重观众的阅历,尊重观众的思考。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没有音乐这些是问题。

就是她们受过的这个苦,都过了70年,70年是什么概念?70年是我现在还要活,从我生下来到现在这个时光,我才能体会70年。我现在的这种浅薄的理解,怎么能去讲她们?
凭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痛苦挖给你们看呢
如果一个记者在这样问你的奶奶的话,日本人怎么强奸你的?跟我说一些细节性的话,你是不是想去揣他一脚。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你得换位思考一下,不止她们老人,她们还有亲人,你在干嘛。你把东西挖掘出来给更多人看,你觉得你很牛吗?然后去国外参加电影节,外国人还给你鼓掌,想什么呢?
在韩国参加电影节的时候,我上边坐着日本导演,这边是韩国导演,都是关于慰安妇题材的这种纪录片或剧情片,韩国人就会问到你,问到你们中国现在民众跟政府跟这些老人是什么关系?我说什么关系,我说现在都非常好的关系,我们的大学生都非常关注这些老人。

难道我要把日本人脱她们裤子的事全部说出来吗?对不对。你老人拍成那样,拍成那么痛苦的样子,她不是那样的痛苦,你要痛苦给她引导出来。然后你要把她照片调成黑白的,我想问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你们可以揣摩我的动机,我拍着胸脯跟你说,我的动机,不能说是单纯的,但我的动机是善良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可能会深层的去理解,不是简单的一个受害者,就是象征国家和被害国家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你要看到老人晚年的生活,她们晚年的心里的状态,你做更深层的思考,去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样应该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