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年失业: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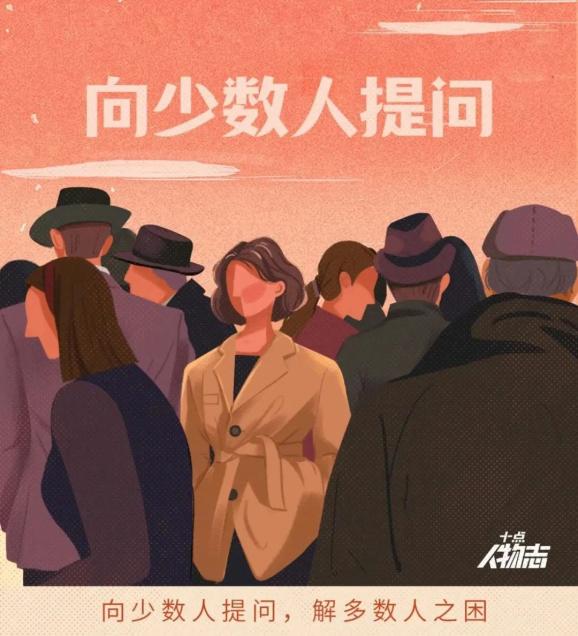
这里是十点人物志的名人专访栏目“向少数人提问”。我们将作为发问者,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聊一聊,从他人观念与经验中,寻找个体力量如何应对复杂世界的答案。
十点人物志采访到了人类学学者魏明毅,她研究码头工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伴随而来的“男子气概”的失落、社会关系网络与情感纽带的断裂,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个通道,重新思考:工作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采访、撰文 | 三金
十点人物志原创
踏入炎热的夏天,大厂裁员消息不断,曾经促进增长的互联网行业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停滞;另一边,网约车司机就业人数再创新高,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但订单数量却在减少。
一些人重新思考着工作的意义。工作早已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
某种程度上,工作定义着一个人。
那么,被迫失去工作之后,人会发生什么变化?
5月,我们视频采访了《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的作者、人类学学者魏明毅。她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近20年,平均一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半,却无力地发现,走进咨询室、有自杀倾向的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工作而减少。

魏明毅《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
2022年10月 世纪文景出版
2008年,四十岁的魏明毅辞掉工作,回到学校攻读人类学,选择了中国台湾省自杀率最高的基隆作为自己的田野调查地点。
她去到码头、候工室、茶店仔(类似茶馆)、海岸、小吃摊、船舱里、货柜车、甚至进入工人的家中,描画出工人们的劳动群像:他们努力奋斗,从未有过片刻休息,却依旧从“赚到盆满钵满”到跌入社会底层,基隆港口也从人声鼎沸走向静寂无声。近2000名工人瞬间失业,勉强留下的也收入减半。


电影《基隆》中的城市画面
她记录下这些人的生活,同时也被一种更大的无力感攥住。在工人们看来,“失去工作全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跟不上世界”而理所当然受到了驱逐。
但显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田野生活结束后,魏明毅重新回到了心理咨询的岗位,但视角、行动已经大不相同。采访中,她认真叮嘱,希望大家不只是通过这些故事同情工人,事实上,他们可能也是我们。
这让我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著作和讲述整理。

你觉得苦,总还有更苦的人
在台湾省,南投和基隆是在连续七八年间自杀率轮番占领首位的城市。我选择了对我而言更为陌生的基隆作为田野调查地点,希望把自己扔到无知的状态里,不含任何偏见地去观察一群人的生活。
基隆地处台湾省北端与东北端的汇合处,从地图上看,它正位于最北端U字型海岸线的最底部,紧邻东海。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基隆海港是作为日本与南方贸易的转运港存在的。
这港口码头在日本人离开后的四十余年间,为基隆带来了清楚可见的经济繁荣。

今天的基隆港口(图源:视觉中国)
我住进码头工人们的家,跟随数十位受访者,在不同时间、空间和关系里跑进跑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李正德是一位我的主要受访者,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把从桃园拉回来的空货柜卸在西岸二十一号码头上。
清晨六点三十分蹬上驾驶座,下午五点把拖车开出码头停靠在围墙边,登记好时间,每天能干多少活、领多少钱都取决于码头货柜的数量。
基隆码头的货柜车分为两种。一类是公司车,驾驶员属于车行员工,受到劳动合同的保护。另一类是像李正德这样的契约车,货柜车为驾驶员自有,他们和车行签订契约,每月交挂靠费给车行,与运输公司的关系仅仅是一纸车辆合同。
他的拖车头里,有几件东西总是吸引我的注意:
放在挡风玻璃面板上的两三罐500毫升装塑料瓶,装的是他母亲前一晚煮好、放在冰箱里结冻的养肝青草茶;驾驶座旁有一个已经开封的烟盒;两三个用来吐槟榔渣的白色塑料杯;车门上方悬挂着一小台对讲机,直到傍晚下工才关上。
他很少说话,总是静静听着同事们对讲机里的对话,偶尔会被逗笑。
李正德和车队同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等待”。
在货柜场卸货柜时等位置,出发到另一个货柜场领柜子,在高速公路上等车流,在码头上等卸柜,并接着等领空柜、等待码头现场人员午休时间结束,重复之前的流程。等到入夜最后一次回码头时,与其他货柜车一起排队等着通过岗哨。
很多次,我远远看着静止车阵驾驶座上的吞云吐雾,还有一些男人在各自的车头里,趴在远大于两肩臂膀的方向盘上。
李正德常常不在那条车龙里。自从1990年代末基隆港货柜进出量大幅减少,码头岸上像他这样的货柜司机,不论生计还是生活形态都大受影响:以前不分日夜赶拖柜子,现在多数司机晚餐时刻便可收工。
他44岁的体力被认为已经大不如前,比其他司机的下班时间还要更早一些。

电影《基隆》剧照
对于李正德来说,从小到大每一次换工作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
十六七岁时,他在五金行送货,认识了几位船员,觉得跑船的工作看起来自由惬意且收入不错,便跟着出海跑了两年。二十几岁退伍时,顺势离开“跑了一趟才知道有多辛苦”的船员生涯回到岸上,刚开始是开出租车,后来是载沙石的卡车,十多年前分期付款买来一辆二手拖车才开始拖柜子。
络绎不绝的国际货船曾经为李正德、为其他车队司机与港区居民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收入。
“每个人口袋都是满的,那时候挣得多”。司机们要跑到夜里才下工,下工后也不回家,总得跟朋友在茶馆里喝上几杯交流感情,对家庭的付出全部寄托在每月的生活费上。
那时的基隆港热闹非凡。这样的生活本身是特殊的,但当时间积累得够久,在无人察觉的时候,原本的“特殊”便已成为他们如呼吸般自然的“日常”,没有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一天也会结束。
与李正德这样的契约工不同,后来我在码头上遇到过一些临时工。他们要下到很大的船舱底,徒手把货柜装卸到码头上,干的是真正的“苦力活”。
早期,他们也是码头上的工人。因为老板将原本10个人做的工作都压缩给2个人来做,李正德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其中之一,那些临时工就是另外的八个人。他们原本工作有保障,收入尚可,但现在被驱逐出码头,只能以临时工的方式回来。
我听其他工人们说起,更多被驱逐后的工人走出了码头,成为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大卖场里的安保人员,“都跟码头没了联系”。
进入1990年代末,各个车队的收入都大不如前。有时为了能给家中生活费,支付每季度修车费用,他们还需要去借贷。没有位置,就没有身份,像李正德这样的契约车司机从来就不是银行借贷的对象。
日子还得过,司机们借贷门路通常来自亲朋好友。
李正德让自己的妻子跟父亲借了20万,买下二十几箱自酿米酒,准备拿来倒卖赚取差价来补贴家用。可等酒买回来,市场上卖不出去,他又不愿意赚同事朋友的酒钱,又不愿意低于市价卖出,最后只能堆在仓库,成了他每日在家无声的餐桌上的一杯杯酒水。
收入递减、借贷有限,男人们渐渐再也给不出生活费了,且在入夜前就回到家,出现在自己缺席多年的晚餐桌前,成为在妻子孩子看来陌生的丈夫与父亲。
时间改变的不只是港口码头停放的货船数量、码头公司的民营化、装卸手段的机械化,更是这群码头工人的生命世界。


失去的男子气概
李正德的家里好安静。不到七点,晚餐就已经摆在了客厅的长形矮桌上,李正德和妻子坐在一边,李正德的父母和快满20岁的儿子坐在另一侧。全家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播放的电视新闻上。
偶尔,李正德的母亲会对新闻评论两句,丈夫和儿媳会简短回应。仅仅半小时后,客厅里便只剩下李正德、新闻节目的声音和桌上的酒水。
李正德与儿子碰面和说话的时间并不多。他常常听到父母说起孩子做的一些让家长头疼的事情,但并不为此烦心。
“孩子还小,不懂事,等以后出社会有历练了,自然就比较会想事了。”他这样告诉父母。
“男人要有担当,不念书就去工作。”他这样告诉休学的儿子,就像他年轻时对自己说过的一样。
事实上,“像个男人”、“要有担当”这样的期待贯穿在他们的整个人生中。“像个男人”意味着你要在谈话中展现自己的阳刚、显示出你的能力。
一位码头工人喝着酒跟我说,“我们男人啊,就是要有酒讲话才会自然”。
码头民营化之后,公司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压低人力成本,这些男人有的是没有工作,有的是工作的薪资被打压到非常低。即使他们想要聚会喝酒,也无法在酒局上“很有男子气概”地说“这一顿我来付”。为了避开这种窘迫的处境,他们只能早早回家。
在李正德跟其他同事的聊天中,他们很少谈论工作的困境,更不必说自己家里的状况。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他们开口说出来,这让他们难以表露自己的脆弱。

电影《长江七号》剧照
偶尔,我会回到基隆去看望他们,每个人都会认真跟我道谢,谢谢我还记得他。这种感激中隐藏着他们对自己的贬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被记住的。
有一位七十岁的码头工人,每次去,他都会带我去小吃摊吃东西。有一次老板娘背着他跟我说,“小姐,这个大哥对你很好诶,因为你来的时候他都会点上两三道小菜,你知道他自己来的时候都只会点一碗阳春面。”
也就是说,即使我的经济条件优于他,即使他现在收入拮据,他也认为自己必须要照顾我。这两三盘小菜代表的不只是他对我这个朋友的看重,也意味着他如何界定自己作为男性应该呈现的样子。在许多地方,男性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女性。
失业带来的是什么?在李正德和所有码头工人身上,他们不只是失去一份工作,甚至失去了界定自己身份的方式。
这样的失去,同时影响着他们的家庭关系。
相对于缺席的丈夫,妻子会撑起一片天。我看到她们花了绝大多数的时间、用有限的金钱让家庭继续支撑下去。相对来说,这群码头工人的孩子就要更艰难一些。年幼的孩子不仅需要吃饱穿暖,他们同样需要心理上的关照,需要有成年人协助他们去了解自己与世界。但码头工人的孩子只能逼迫着自己急速成长,他们很容易感受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一旦出现这样的想法,任何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李正德的孩子后来跟毒品有关系,教育情况也并不稳定,在对自己的认知上,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不被爱的。这种情况的存在让我意识到:当我们习惯于用物质条件去连接人和人的关系,会形成非常糟糕的后果,情感会被物质所取代,我们再也找不到真情。
当这一连串的无力感、家庭中的争执与细微复杂的情感变化,历经足够的时间累积,便发展成为家庭成员中来来回回的自伤与自杀。
“平常都好好的啊,看不出有什么啊”的简要结论,呼应着李正德的“无法开口”,整片码头的静寂下,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No Jump(不要跳下去)”
电影《拆弹专家2》剧照

被时代抛下,是理所当然的吗?
2010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李正德的儿子打电话给他,说自己眼睛看电视屏幕越来模糊了,需要钱配一副新眼镜。那几乎是儿子会主动找他的唯一时刻。李正德没有提及自己半个月未上工的事,也没有说起几笔待付的修车费,他让儿子等着他。
李正德撑着扶手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车钥匙,朝自己停车的地方走去。货船离港之后,西岸已被弃置,他只能靠着远远的昏暗街灯前行,没走几步就被路旁花圃突出的铁钉划出血,到医院缝了三针。
他告诉我当时想回车上拿自己以前戴过的眼镜,让孩子试试合不合适。
我们不知道,这副眼镜是否可以遮掩自1990年代之后,他身为父亲响应不了伸出手的儿子而无法自处的难堪。但他似乎被钉子钉在了原地,不得动弹。
如同李正德一样的劳工,无论是在隐喻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被压扁成为一枚枚“螺丝钉”,成为被市场决定价值的对象。
这种情况下,失业影响着他们正确看待自己的价值。最让人悲伤的是,这明明是一次集体的坠落,但几乎每一位工人都认为是自己能力不够。
我并不是认为人生的不幸与个人毫无关系,但这群工人的失业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不够积极,他们只是先被这个时代“连接”,然后“挂断”。
你的时间和劳动能卖出多少钱?未来还能卖出多少钱?哪一天会因为“不合时宜”、“跟不上世界”而被抛弃?他们回答不上来,只能密切关注着时代的变化。
但在生活好的时候,人们很难去真正的“居安思危”,社会也并没有提供给码头工人这样的敏感度,相反,社会告诉他们“你现在一切都很好”。
高度的物质发展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当我的口袋是满的,当我现在有车有房,人会误以为目前的美好生活会一直持续。看得长远的码头工人可能会去买房,但这样的人很少。

电影《长江七号》剧照
我们常常说,向前走,别回头。行业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人拿时代没有办法。我们对这群工人的同情和怜悯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关怀?
我想说,当我们认为,劳工本来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公司就应该不懈追求利润的上升,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相信劳工被弃置、被像垃圾一样丢弃是理所当然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就会形成规律。
只有把这种理所当然视为“不正常”,我们才有可能去探索进一步的答案,去了解这种苦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写下他们的故事,正是因为我想要把褶皱翻开,再重新看一次,那些“理所当然”是不是会出现变化。

电影《长江七号》剧照

竞争过所有人,真的是你的目标吗?
起码对我个人而言,变化已经产生了。
做新书分享时,常常有读者问我类似的问题:如果结构性问题如此庞大、难以撼动,我们个人的改变有任何意义吗?今年3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受苦的倒影:一个苦难工作者的备忘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苦难里头,我们能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我想有两种,投降,或是被淹没,这很不一样。
“投降”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总有人会被抛弃、被取代,行业的兴衰更迭是自然规律,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做不了。
“被淹没”则完全不同。指我们还是要做正确的事,要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即使最后的结局没有任何改变,我们被淹没了,但这跟投降不一样。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有一些改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静寂工人》完成之后,我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改变。
首先,我决定停止向上流动,成为一个能够自由移动的人。当社会中每个人都被鼓励要从金字塔的底层爬到顶层,有没有人思考过,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会是自己的目标吗?
每个人的性情、爱好、渴望和在乎的东西都不尽相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同一座金字塔呢?拥有自由移动的能力意味着,不论是向上向下,或是东南西北,我都可以自由地去观看和体验。
老实讲,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的收入已经只有之前的一半了。可是我知道在工作这一身份上,我是有主体意识的,而非一个劳动的物件、一个被用完即弃的人。我的工作比之前更加繁忙,但我反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电影《基隆》剧照
其次,我决定坚持书写。
书写能够帮我去到更远的地方,触及更多的对象。如果足够幸运,有读者透过我的文字反思自己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我想社会性的苦难就有机会被缓解。
我们常常忘记,结构太庞大,也是由人组成的,我们只要将单独的个人变成少数、再变成相对多数,事情就在改变。它一定得变,它一定会变。
前几年,李正德去世了。去世前,他在医院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去看他时,他讲话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把书送到他手上,他没有办法翻开,但他很高兴自己的声音被看到,自己的生命被记录。我能感受到这本书对我们意义是什么。
生活是很现实的,无力感如影随形。但我听过一句话,用行动代替无力,即使你在最不知所措、绝望痛苦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事。这件事会有结果,只是时间未定。
如果我们现在走在前面,不要害怕看不到结果,播撒的种子就在后面。
未完待续,是永恒的真正结局。

《火花》剧照
部分参考资料:
1.《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魏明毅
2.《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美]凯文·贝尔斯
3.《被甩出全球供应链的基隆码头工人的境遇,如何预示了我们的未来?》界面新闻
4.《探索自杀踏上基隆的码头世界 静寂工人 唯有心疼》艺文副刊
5.《从人类学回到心理谘商 魏明毅用不同眼光看环境》艺文副刊
原标题:《中年失业:失去的不只是一份工作》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