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得传染病的日子,我看到了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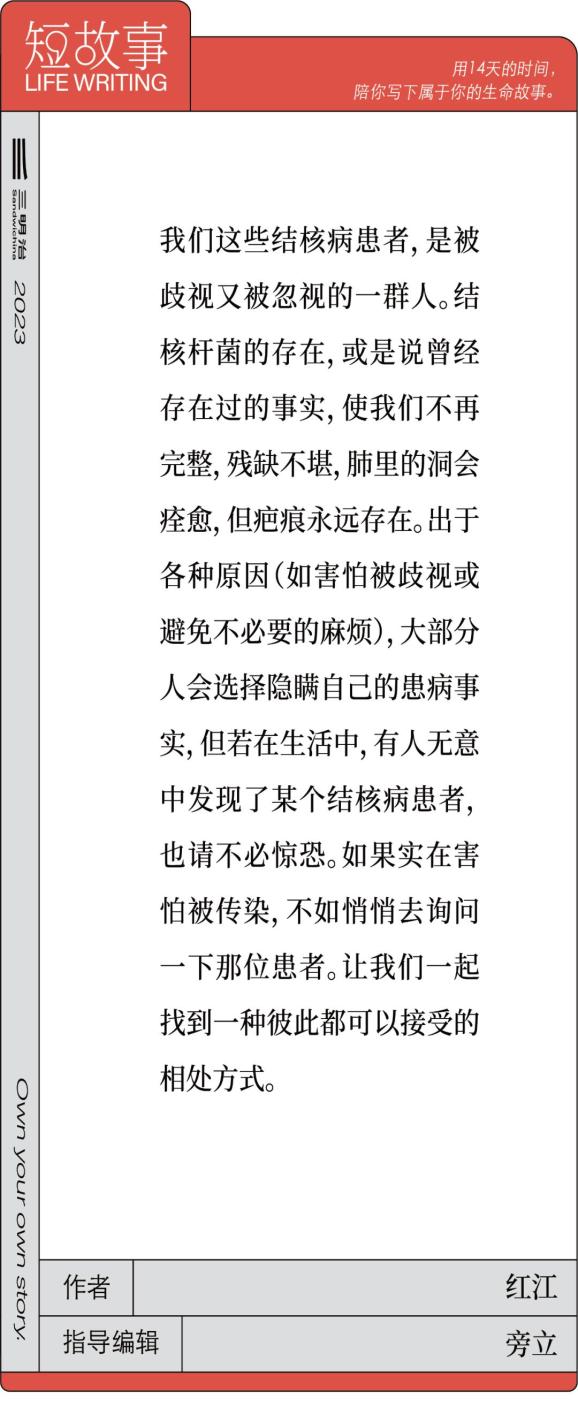

在一个黄昏,我走出医院,看着所有人工光线都重叠着,两层、四层、七层……它们显得迷幻、神秘,甚至模糊了我的思绪。相机里偶尔会拍出的眩光转移到我的眼睛,一个小光点拖出斜长的光线,不知要延伸到哪里。本该清晰的光点和一切在光下明暗分明的立体建筑成为了油画刚开始时的铺色,还隔着一层纱,乱糟糟的,像噪音,我闭上眼,耳边就听见了那句台词:“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我妥协了,我承认它的真实性,高楼、街道和灯光变幻了通常的形状,好似在电影里。这是我确诊肺结核的第63天,或许是高强度的药物治疗的原因,我眼中的世界不再清晰。
最初,我只是看到了肺上的那个洞。洞应该是慢慢扩大的,从2020年的第一声咳嗽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怀疑自己得了新冠,但每日被棉签戳到干呕后手机上显示的“阴性”否定了我的猜测。我的肺一定出了点问题,它在冬天会因为寒冷的刺激而收缩,带动支气管、气管、喉部一齐运动,直到听到一声“咳!”随后就停不下来,变成“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大脑会不满肺部的行为,它发出指令让鼻腔和口腔关闭对气体的输送,脸部的毛细血管因此而发涨,血液开始加速流动,肌肤发红,气道的紧闭阻止了肺部下一次收缩即将喷出的气体,世界得以安静。我可以呼吸了。
“感冒吧?”第一个医生推测。
“可是我连续咳了三个月了。”“估计是咽炎。”第二个医生尝试判断。
“我有点呼吸不畅,睡觉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慢性支气管炎。”这个中医很自信。
“X光片显示肺上有高密度阴影。”“肺结节吧,很多人都有。”呼吸科专家可能在安慰我。
在这些医生诊断的过程中,肺里的小洞在悄悄变大,在那个洞里,繁衍着一个细菌宇宙,这个宇宙体系在不断膨胀,直到2022年1月20日晚上经历了一次爆炸。我发烧了,41.2℃。这时,我爸妈还在因要不要去医院看病进行严肃地探讨与分析,听他们的语气,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应该是要造一艘宇宙飞船飞向火星。2小时35分钟后,护士们确定我没被新冠感染,把我放在了有点像太空舱的CT机里,机器转动着,它在探索另一个宇宙。
“小姑娘,你的肺里有个洞呀。”顺着医生的手指,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洞。医生说大概率是因为感染而产生的“空洞”,我觉得它是虫洞,可能连接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像是狭窄的甬道。

我住院了,呼吸科,医生们查房时这么称呼我:“那个肺上有洞的小肺炎。”这个三甲医院宽敞明亮,我是里面最小的病人。夜晚,持续咳嗽声不断从右边那个身材消瘦、整日裹着红色羽绒马甲的中年女性床上传来,左边躺着的是个赘肉快要从床上淌下去的老年人,她一直在呻吟,我呼吸不畅,被按着手臂抽了一管动脉血,整个病房不存在睡眠。还有10天过年,应该可以吃到年夜饭,喝掉那瓶我眼馋很久的红酒。我看着现在依旧摆在架子上的红酒,手边放着的今天还没服用的抗结核药物,苦笑那时候的自己居然这么乐观。
他们想要用一根管子从我的鼻腔滑入咽喉,进入气管,再伸进支气管里,看看它们的内部,并用冲洗液确定细菌的名称。我第一次做气管镜是半麻,管子通入咽喉的时候我仿佛要溺水,强烈的窒息感,求生欲让我开始挣扎,气管强烈收缩想要把侵入物挤出,我听见医生说:“放松。”我颤抖着强制自己不再紧绷,那时我暗暗发誓,如果可以快速康复,我一定早睡早起,按时三餐,坚持运动,把冰咖啡换成热水泡枸杞,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
两天后,医生悄悄叫去了我妈:“结核分支杆菌,去传染病医院吧,别在病房内声张。”妈妈的神情变了,她强制给我戴上口罩,拍开我想要拿她杯子喝水的手,跑去门外悄悄打电话。那时我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甚至为我爸担心了一会儿,我怕我想象中的“绝症”再次打击到他脆弱的心灵,他因自己得恶性脑瘤的弟弟和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被医院折磨太久了。
那天,我的眼前的世界还很清晰,天空是紫色的,月亮挂在冬日干枯的枝头,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白色的雾气,凋敝的村庄里没有路灯,我沿着漆黑的路向前走,月光照在前方的大理石指示牌上,似乎想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字:萧王庄墓群。由此再走五十米,就到了传染病医院门口。寂静到空气都停滞的夜晚,我突然想听到乌鸦的惨叫,以此来预示我即将腐烂在这个地方。

我得了结核,这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我的每一次咳嗽、流出的每一滴血液都可能伴随着结核杆菌,感染到其他“正常人”。在我被感染并发病的那一刻,就已经不被当作“正常人”看待,我是人人敬而远之的“异类”,即使这个世界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感染,即使每年都有100万人死于这个疾病,但作为仅次于COVID-19的传染性杀手,所有人都警惕着“我”——一个随时会散发病菌的传染源。
在济宁,唯一一家可以接收和治疗结核病的医院就在这儿,同时还治疗甲肝、乙肝以及新冠肺炎等传染病。当我第一次迈入医院大门进入病房,经过了三次人工确认和三扇需要人脸识别才能进入的智能门,智能门睁着它独有的眼睛,用编程式1与0的组合记住了我的相貌,随着“嗞啦”开门和“砰!”一下关上的声音,我与外界隔离了。在电影里,这样的场景往往会让人不安,你会害怕身后的门再也打不开,而又不知道在前方会遭遇什么。
2020年,我们城市的监狱出现了约500例的新冠感染者,他们被隔离在这里。为了监禁这些特殊的新冠患者,医院进行了一些改进。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甚至无法透进阳光。每个病房都有专门的氧气输送,可以在病房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保证人的存活,同时也避免了不同病房之间的空气流通。为了安装这些氧气输送管道,只能放弃房间的高度,屋顶很低,跪在病床向上抬手便能摸到顶部,我盯着那黑洞洞的输送口,时常能听到管道发出的野兽般的嘶吼,从氧气中心输送的气体像巨兽嘴中吐出的叹息,我怀疑它下一秒就要把我吞噬进去。病房很压抑,是被监禁在一个随时会遭遇威胁的盒子里,很少有病患会随意串门,当同病房的室友不在时,只能听到偶尔医护人员进出办公室的关门声和其他病患的呼叫铃声。“31床呼叫”“19床呼叫”“23床呼叫”,毫无感情的冰冷的机器呼叫声日日夜夜萦绕在耳旁,你见不到那些具体的人,只能通过抽象的病床数字去想象:今天19床呼叫了5次,是不是因为滞留针打久了不太通畅?31床的呼叫声响了6次才被护士按掉,但又迟迟没听到护士出门的声音,她们在忙着配药吗?生病之后,因为要长时间打针而难以活动,听力和思绪就变得异常灵敏。
一般来说,主要治疗结核的药物为: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链霉素。而这些药物在杀死结核杆菌的同时,也消耗着患病者的身体。每打开一瓶口服药,随之带出的是由密密麻麻小字列成的药品说明书,写满了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药物都会造成肝损伤,需要配合护肝药一起服用,此外,异烟肼可能会造成外周神经炎、精神失常,吡嗪酰胺会让尿酸增高,乙胺丁醇会引发视力模糊,严重者可能导致失明。而最开始,这些药物要通过静脉输液进入患病者的身体,以保证药物的剂量和吸收程度。

在我刚进病房的第一晚,已经有两位病患住在这个房间。她们一胖一痩,分别躺在我的左右两侧,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走到床边,她们甚至没有抬眼,只是呆滞地睁着眼睛望向一旁,偶尔发出干呕的声音,以及晃动药瓶回忆自己吃药的次数。我悄悄吸了下鼻子,空气里散发着积蕴了很久没能散去的饭菜的气味,在冬天高强度暖风的燥热下,透进我的鼻腔,窗户都封着,没法通风。不久,她们熄灯了。
医院总是在早晨八点醒来,被装着配好了药的推车摩擦地面的声音和护士沉默着开门、挂药发出的噪音吵醒,吊瓶里最显眼的是利福平,橘黄色的药水,会把你的所有体液都染成这个颜色,直到肝和肾将它全部过滤排出。病房里的呻吟也在此时开始,我的室友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药物刺激了她们手部的血管,滞留针也只能在手上待一天,这些药让她们的血管变得不再有弹性,塌陷在肌肤下方,滞留针的软管紧贴住她们的血管壁,为了让药物能再次滴入血管,护士往往会用力挤压滴壶,让液体猛地冲入血管中,这总会让她们发出尖叫,捂住手臂忍受钻心似的痛。我皱起眉头,让护士为我打上针,药滴得很慢。右边瘦高留黄色短发的女人在尖叫缓和过后看着我的针终于开口,她让我去做PICC导管,用比滞留针头还长几倍的软管植入我大臂的大静脉里,避免最终落得她的下场。我很害怕,去做了,在心惊胆战的同时感恩现代医学科技为我减轻一丝痛苦。
它保护了我手部的静脉,但阻挡不了药物的刺激。头晕、干呕、眼前发昏,一天中我清醒的时刻不再是16个小时,药物副作用让我很长时间都处于混乱之中。每天下午六点我才能真切地感到自己在活着,但晚上十点又不得不睡觉了,第二天醒来周而复始,喝水、吃饭成为机械式动作,忍住恶心习惯性硬塞食物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同时大量饮水让药物尽快代谢排出,然后享受一天中最后四小时的身体舒适,最后睡觉开启下一个需要忍耐度过的早晨。什么时候到头?我不清楚。
我躺在床上,酒精和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剩饭的余味钻进鼻子,我像植物人一样瘫着,任由护士拿起我右侧的手臂将输液管接在导管上,我不再是个“人”了,我是被动承受着药物的生物,只能视力模糊地盯着那橘红如血的液体注入我的体内,你猜它会有多少滴?我就这样呆滞看着,数着1、2、3、4……
你知道吗?萨拉·凯恩用鞋带勒死了自己,三毛好像用的是丝袜,我应该也可以用床头边的耳机线。死掉吧?不要。死掉好了。不可以。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不知道。那为什么不能结束?不能。再忍一天吧。那第二天呢?会好吗?会吧。还有多久?……还有多久?今天几号了?现在是几月?
不知道。但别死,别死……(我不能死)
“今天几号啊?”我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
“二月二十三。”来自外部女声回我,不是我自己脑内的声音。
“快出院了吗?”
“快了。”我睁开眼,是左边太阳穴长了老年斑的年轻护士,她很温柔。
“楼下好像有花开了。”我根本没看到花,我只是昨天听到左边那个女人给孩子打电话讲的,但我就是想说这句话。
“是呢,二月了,杏花该开了,你多下去走走。”她顺畅接下了我的胡言乱语,我活过来了。

父母很少来看我,有时我会坐在病房门前的地板上,盯着那个手提尿袋佝偻着的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进行眼神交流的老人拖拉着鞋一遍遍从走廊一头走到另一头,他慢吞吞的步伐带动着这儿漫长而无聊的不断循环的日子。我们病房的三个人都有支气管结核,气管里不像肺部有那么多血管,很难通过打针治疗,只能用药物雾化渗透。总结来说就是,很难治。主任会用轻快的语气,安慰我们并保证他会把我们治好。我们都能看出他努力的表演和刻意的调侃,但总比宣告绝症好一点。三个雾化机同时打开,将细微的水汽从鼻腔吸进再呼出,有点苦,它们渗进气管里、黏到皮肤上、漂浮在空气中,我想我的身体内部应该跟病房里一样变得雾蒙蒙,抗结核药物凝结成的带有一丝浪漫气息的雾暂时掩盖住了一些丑陋和冰冷,三个人互相都看不清彼此,我们边吸边笑,听着主任称自己来到了“仙境”。
我们每天有二十分钟活在童话里,其余时间都想逃,每个人都想快点离开。
左边床上的不到一米六的女人已经一个月没洗过澡了,她黝黑的头发因为出油更加黑亮,也显得更秃了。这是个十二岁和三个月孩子的妈妈,从村里过来,应该三十多岁,但我第一眼看到她穿着的卡通T恤,以为她跟我差不多大。她无时无刻不盯着自己的手机,一天里要有8个小时在打视频,是为了哄她三个月的儿子。白天,她丈夫要上班,孩子由大姑看着,这个女人就用视频盯着孩子。她对着手机唱儿歌,做着笨拙的搞笑动作,不停喊着孩子的名字,当孩子持续哭闹时,她恨不得钻进手机里,亲手抱住他。母爱溢出屏幕,穿过近百公里回到村庄。她是整个病区最想回家的人,她怕孩子会忘记自己是妈妈,为此,借钱治病的她依旧坚持用最贵的抗生素。
但那天,病房里没有唱儿歌的声音,她哭了,丈夫因为传染病拒绝她回家,尽管医生已经同意让她出院,她的痰检是阴性。最终,她选择在家附近租一间狭小的简陋单间。出院的时候她特别开心,把很多东西都扔在了病房,弄得保洁来收拾的时候一直骂骂咧咧,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回家的第一瞬抱到自己的小孩子。
那个提醒我去植入导管的女人如果不是因为生病应该会打扮得很漂亮,她看起来有四十岁,指甲染成大红色,偶尔会跟朋友们在软件上唱歌。她喜欢听歌,我经常看着她穿着睡衣、戴上耳机在破落无人的墓群后面的村庄里散步,有时我会悄悄跟在她的后面,不去打扰,我盯着她的背影,仿佛能看到具象化了的思绪飘散在她的四周,形成一个场域。她有点神秘。但是或许“神秘”难以在医院长久存在,尤其是在没有私密性的病房里。“泪水”大概是医院里含量仅次于药物的与我们身体相关的液体,我记得她忍受着被丈夫打断的肋骨疼痛时没有哭,被护士捏滴壶冲开被堵塞的滞留针时没有哭,那天她大哭着扯开了手上的滞留针跑出病房,我听说她的父亲去世了。她没有被治好,但再也没来打过针,前一天晚上她在担心自己回村会因为传染病被村里人在背后嚼舌根。
我的身体逐渐适应药物的注入后就会失眠。夜晚的医院应该是幽魂游走的地方,走廊的紫外线灯打开,企图杀死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菌群,我会穿过幽森的走廊,感受自己也在被炙烤。这里的护士都带着N95口罩,用一次性头套护住头发和耳朵,手机放在塑料套袋里,会随时用口袋里的小喷壶给自己的手消毒。大部分来这儿的医护都是迫不得已,他们去不了其他医院,只能来到这个充满传染性病菌的工作场所里。我几乎没见过他们整张脸的样子,只有被口罩挤压变形了的眼睛和没被头套覆盖住的额头,他们常抱怨N95口罩损伤了自己本该饱满的苹果肌。很多人刚开始来到这儿是恐惧的,他们害怕被传染,尤其是看到病床上被药物折磨得不像人的病患时。现在,他们有的适应了,有的被迫接受了,有的麻木了。我们共同漂浮在这个被孤立的岛屿。

有个00年的还在轮科室的小护士,比我还小一岁,她不想当护士,但高考失利只能学护理专业。这是护士长认定了要留下来的人,因为她壮实、干活利落、不拖沓。或许是年龄还小,看到同龄人总会讲得多,我觉得她还在适应这个环境。她是从后面肝病楼上调过来的,那里的病人脾气都很暴躁,带她的护师告诉她,干这一行不要有太多的同理心,冷漠一点对自己好。记得有天晚上她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该听护师的话,我不知道,只是告诉她要照顾好自己。
很显然她做不到像成熟的医护冷眼旁观一切,并注意对病患不要透露太多。我们聊天的前一天下午,我在医院一楼看到有家属来闹事,乌泱泱一群人堵在门口,没有一个医护回答我对这件事的疑惑,只是那晚他们加强了病房的夜巡。小护士偷偷告诉我,是一个男人查出结核,后续又被诊断出肺癌,基本没有活路但治疗费又很高,他还有妻子和小女儿,就想用自己的死给妻儿留下一些可供生活的费用,于是在晚上溜出医院,开着车冲向河里自杀了。那天负责这个男人的值班护士是小护士的朋友,自这件事后她被调到了最累的岗位。小护士语气沮丧,责怪的同时又无法不去同情那个自杀的男人。我在回忆自己的心理斗争,在想那个男人是怎么下定的去死的决心。这时是三月,河里还很冷,肩负责任的自杀是种解脱吗?
孙护士好像不属于我列的情况中的任何一类,她性格爽朗,大我十几岁,那天邀请我去办公室一起看电视剧,到的时候她刚刚吃完水煮青菜,我刚好瞥见了她没来得及戴口罩的脸上的勒痕。在医院里聊天,总免不了“疾病”“死亡”的话题,是“病痛”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同类”。
我和她聊起了爷爷。她的爷爷是个凶狠的乡下人,重男轻女,一生脾气暴躁的男人从未对孙女温柔过,在人生最后的时刻,这个好似不近人情的老人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孙护士用打趣的语气说她那天故意摸了爷爷早就秃了的头顶,若在以往,爷爷要站起来揍她,但那天,她的爷爷什么都没说,就任由她摸着,再也打不了她了。她像讲笑话一样告诉了我。
我告诉她,我的爷爷在人生末尾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那个年轻时扛过枪、行走过雪山的军人被绑在轮椅上,像小孩一样玩闹。他最后一次跟我视频时,推开了奶奶拿着手机的手,我觉得他是不想在视频里看到形如枯槁的自己,倔强、要强、从未讲过温柔话的爷爷那天对我说:“爷爷很想你。”我做不到像孙护士那样语气轻快,鼻子一酸,哽咽了一下。
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好像总会变得柔软,也可能是因为疾病让他们失去了对抗的气力。
后来,我们谁都没说话。在沉默中,两人之间好像搭建了一座真心铸就的巴别塔,连接着两个残破的有缺口的心灵,它给两个不完满的孤独灵魂提供了一条可供触碰的道路,通向彼此。
我们现在在医院里经历、对抗着疾病,也聊着疾病和死亡,疾病是一个契机、一种偶然、一次不幸,由个人的痛苦映照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千姿百态。我们,这些结核病患者,是被歧视又被忽视的一群人。结核杆菌的存在,或是说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使我们不再完整,残缺不堪,肺里的洞会痊愈,但疤痕永远存在。

传染病夺走了人们包容和接受的能力。拒绝,我们遭遇最多的就是拒绝。结核病会“传染”这件事比“生命”本身还要重要。我没见过那个因为结核被三甲医院拒绝接收的心脏病发作的老人,只是在办公室看到他的儿子来向我的主治医师请教如何将父亲拉回老家处理后事,这个戴着双层一次性口罩的平头男人声音低微,忧愁布满了整张面孔。我能够想象到这个老人最后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推入火化炉,成为尸体的他,甚至成为骨灰的他依旧会被警惕。他的墓志铭上也应该刻上“注意结核传染”的字样。
病区里的所有医护和病患都在为这件事情愤怒,原本监禁着我的碉堡突然让我有了归属感。肺里的洞是宇宙里的虫洞,狭窄的甬道链接着不同的平行宇宙——我们每一个身患结核的个体。
刚被确诊结核时,我说我成为了“异类”,没错,我是世俗人眼里的“异类”,很多行业的入职体检要求求职者说明自己是否感染过结核,“结核病史”在求职里是较为危险的经历。甚至在父母心里我也是“异类”,他们至今都没有告诉别人我得过结核,并警告我不许告诉其他人,但我此时违背他们的意愿正写着这个故事。在这个病院里,我是“正常人”。无数次,被药物折磨的我期盼着出院,想在宽阔的广场上飞奔,而在真正要出院之前我胆怯了,我害怕被歧视、恐惧会传染他人。甚至在五月我去复查时还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无法入学。主任坚定地让我放心去生活,正常生活,像正常人那样。
确诊结核的63天后,我出院了。我是在一个黄昏迈出的医院,没有人来接我回家,我的视力变得很差,医生停了我的乙胺丁醇。医院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应该像肖申克那样畅快地喊叫才对,但眼部的疼痛和扭曲的灯光让我无法兴奋,我还要继续服药,断药会增加结核菌耐药的几率。我离痊愈还很远,甚至此刻,我都在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痊愈。
我是个在新冠疫情时期患上结核的病人,我和妈妈曾因为一纸核酸阴性证明被阻隔在医院大门内外,核酸阴性证明的时间超出了限定的48小时,我们错过了那关键的两分钟。出院的时候是2022年4月,上海正经历封城,我在一些求助信息里看到过有人的抗结核药快吃完了。2022年9月,济宁也即将封城,我本以为只有传染病院是个监狱,现实显示并不只是如此。我得的不是新冠,但我宁愿自己得的是新冠,那样我就成为了被封控人群中的“异类”,并在“新冠疫情”的语境里是一个“正常人”,“结核病”不是正确的“出门口令”。这很荒诞,至少在那时新冠的致死率已经很低,而我很可能因为服药的肝肾问题死去。
“结核”在这时不值一提,传染病院的大部分医护被调去各处新冠采样点做核酸检测。因为交通的限制和药品管控政策,传染病院的抗结核药短缺,药店里也难买到肺部消炎药,我的药也要吃完了。第一次我有点觉得传染病院的智能门更加可爱,当我提出出门的要求和理由后,带着红袖章的社区管理人员用有生命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更谨慎地捏紧了口罩上卡住鼻子的金属条,并拒绝让我出门,即使我们小区没有一例新冠感染者。我曾因“疾病”被困在传染病院,如今我又被什么禁闭在小区?
经过层层审批我得以在第二天早晨出门,街上空无一人,我好像在流浪。我手里应该有一把猎枪,像《我是传奇》里的男主一样带着我唯一的狗寻找还存活的人类,并射杀黑暗中的威胁。所有的药店都是关着的,传染病院内的药物不再供给未住院的病人,幸运的是,我在出院后一个月接到防疫站的电话,他们告知我工人医院可以领免费的抗结核药,当时我觉得我并不需要,现在它是我最后的希望。医院里没有几个医生,大部分医生都被封控在家里,我等了很久,直到一个穿着绿拖鞋和紫色隔离衣的医生向我走来,她很焦急,不停地在抱怨我的打扰,斥责我没有早点把药屯好,但她没有停下为我准备领药手续的动作,严格来说,我只能领一个月剂量的药,但封控遥遥无期,她怕我再也出不来,给我的药能够吃到年底。我抱着她的善意回了家。
2022年12月底,我“如愿”感染了新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是一样的了。但我是个得了新冠的结核病患者。“新冠”的口罩可以摘下,“结核”的还不能。我摘下了蓝色的口罩还有白色的,白色的下面有粉色的,五彩缤纷的愉悦颜色印在口罩上是那么令人作呕,夹杂着并不存在但又随时可以闻见的消毒水的臭气。我是正常人中的异类,我是异类中的异类,我是异类变成正常人后的异类。

我是谁?
我的眼睛很痛,眼前的世界无法聚焦,我看不清一切。是我眼中的世界扭曲着,还是它本来就是这样。我站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中间,我吊在铁塔寺门口的铁桥上面,我躺在三月那个男人自杀的河里。河里飘下来的是各种颜色的口罩,天上落下的雨滴变成橘红的病患的尿液,染红了整片河流,大堆的流下的口罩最后只剩下一只蓝色的漂到我的手边,我戴上了它。一只猎狗叼着我的猎枪放在岸边朝我狂吠,我抵在一棵柳树下,先打死了我的狗,又对准了自己。
黄昏,天边的晚霞是被世界上所有的利福平药水染成的颜色,要浸透这个世界,杀死弥漫着无处不在的结核杆菌。我的体内会永远留存着结核的痕迹,橘红色的清洗不掉的颜色,褪不去的空洞的疤痕。
“砰!”我开了枪,想替晚霞杀死自己。
我打偏了。我看着我的狗流泪。

结核病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6-9个月,有肺外结核则需要一年以上。如果某人被确诊结核,医院需要上报当地防疫所,并进行相应治疗,轻症有时不用住院。结核病的出院标准是炎症有消退迹象且结核杆菌检测呈阴性,即出院后的结核患者一般不具有传染性。但是ta必须要继续服药,可能还要定期接受气管镜治疗。
出于各种原因(如害怕被歧视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部分人会选择隐瞒自己的患病事实,但若在生活中,有人无意中发现了某个结核病患者,也请不必惊恐。如果实在害怕被传染,不如悄悄去询问一下那位患者呢?让我们一起找到一种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相处方式。
希望我们都可以互相理解和包容,以舒适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原标题:《得传染病的日子,我看到了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