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苏辛《冰河》:拼图、编码及报纸的空白处丨新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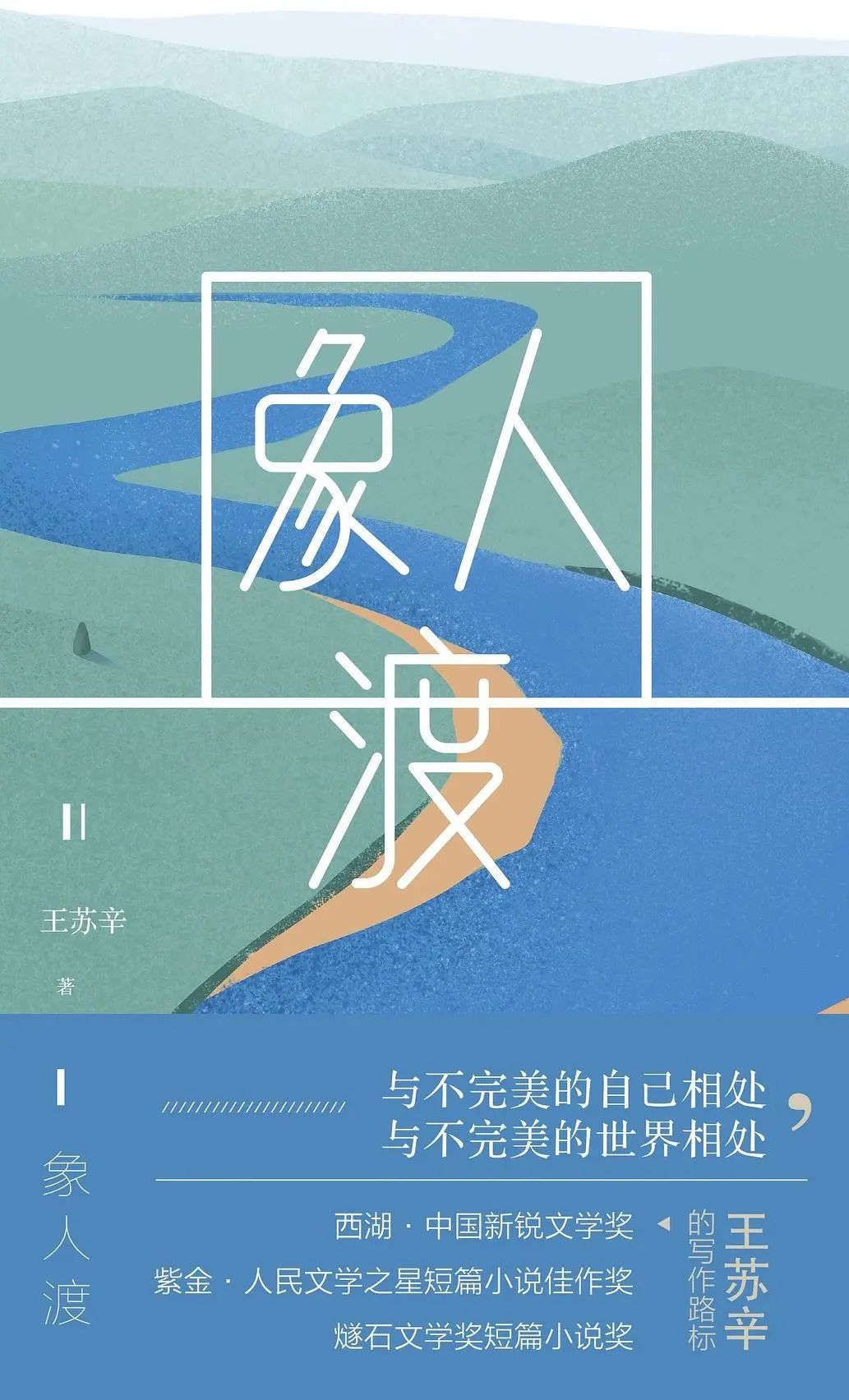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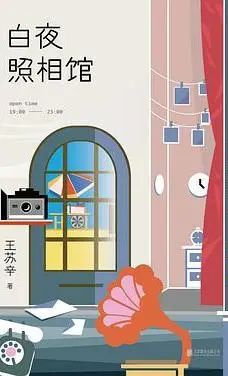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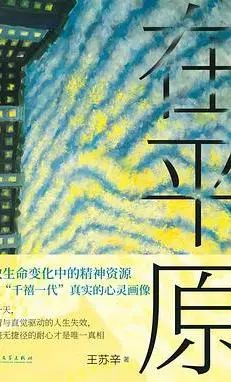
△王苏辛部分作品封面
小说《冰河》收录于王苏辛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再见,星群》里,本文作者认为,青年作家王苏辛的《冰河》表现出了当代人城市感的变迁,城市一直处于塑造之中,但在想象性地退出现代化之后,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仍然横亘着,人在城市中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状态。
拼图、编码及报纸的空白处
——读王苏辛《冰河》
文丨张雅婷
(刊于本报2023年6月29日)
读王苏辛的小说《冰河》,不免想到典型的灾难片《后天》,陷入停滞的人类社会似乎难逃“冰封”的命运。
但是,不同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的“科技元凶”设定,《冰河》的末日更多由于生态的破坏和消费主义的泛滥,一群难以负担高昂生活成本(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多余人”逃离到去现代化的封闭场所中,反复拼合又打乱一幅世界地图、逐渐习惯在签名簿上写下一串编码……即使是“共享”门卫室的四位主人公,也因轮班制而鲜有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交替而非互动。
因此,被“冰封”的不是作为异质空间的“城内”,而是生活在空间中的人与人。拼图、编码、报纸作为贯穿全篇的重要符号,其空白处恰恰暗示了人对自我身份及世界认知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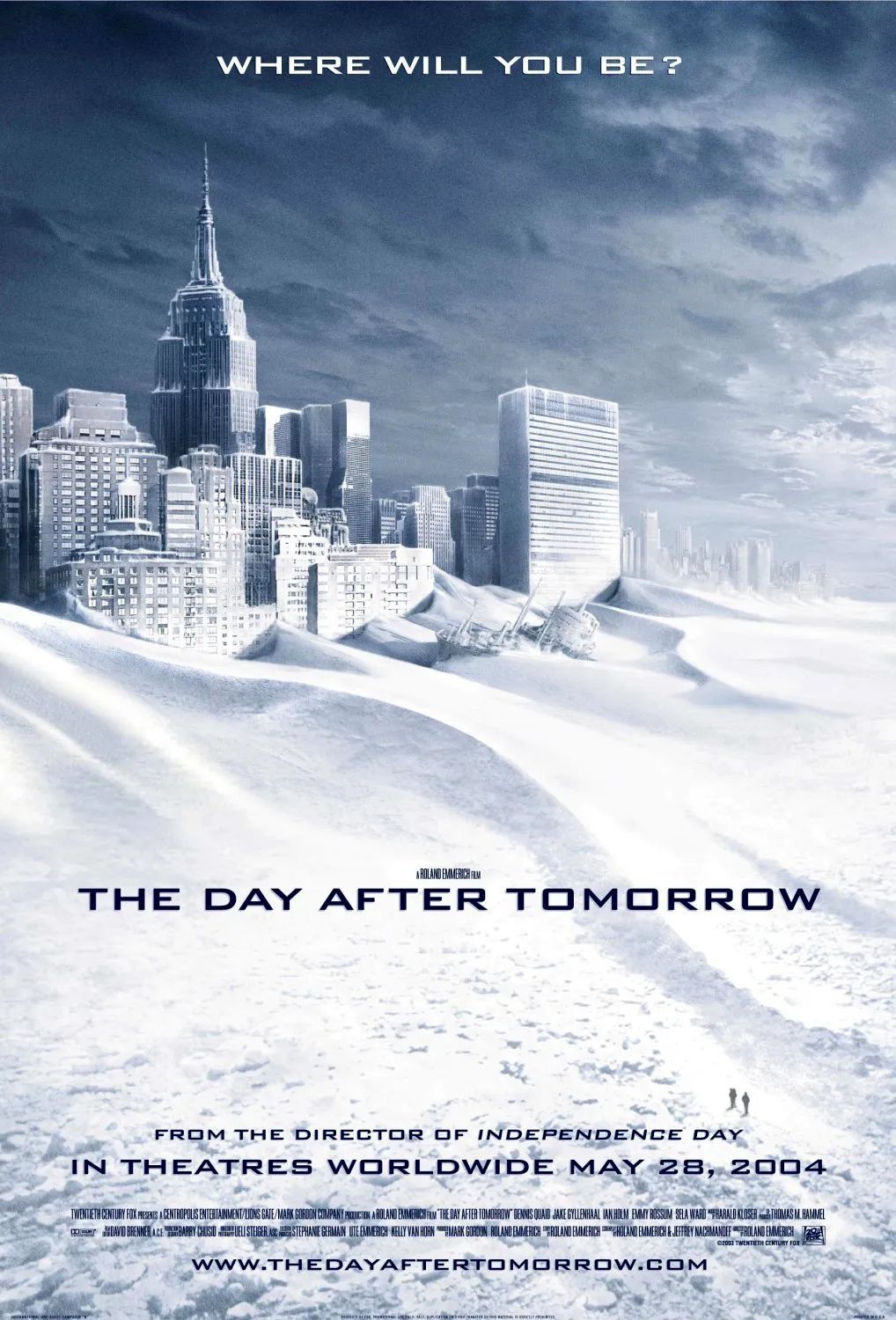
电影《后天》海报
门卫室桌上最显眼的是一幅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拼图,主人公们交替进行“完成”的动作,但在叙述的当下,章敬业“总想犯懒”“甚至没有完成一块拼图”,许亚洲“重新打散了拼图,从感觉上最远的南极洲开始拼起”,钟娟娟“把眼前的拼图一推,不同的小色块就四散逃逸了”,索罗“倒干净了新的拼图盒子,拼片堆满了桌子”……延宕、修改与推翻使得拼图永远不能被完成。这当然对应着定位的失败。
在经纬线缺失的状态下,打散的海岸线是相似的,这些轮廓无法被放置在绝对正确的位置,而是与章敬业“宽大的影子”、许亚洲“隐约的轮廓”、〇五三一“椭圆形的身影”一样,面目不清、难以识别。每个个体都和最后被剩下的“大陆边缘的岛屿和零碎裸露的洋面”一样多余。
可是,破碎的拼图之下并非一无所有,拿走拼错的部分,露出的是“女人”两个字:
“那是两个马克笔写出的粗体字,‘人’字的笔画是反复描画过的,因此边缘有些不够平滑,遮住字迹的拼图背面,还沾着马克笔的黑色痕迹。许亚洲很快想起章敬业在澡堂里给他讲过的故事——他孙女供职的机关单位,有一个女干部,有一次在集体澡堂洗澡,露出两边肩膀的两块大痣,那两个痣就像两个汉字——‘女人’。”
这是记忆唤醒的时刻,两个字符如同那枚“小玛德琳”点心,不仅唤起了许亚洲与章敬业的交往经验,唤起了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主体重新确认自我的时刻。可惜的是,这样的时刻稍纵即逝,以至于要通过“反复描画”来不断召回,费力又无力。

《后天》剧照
如果说“完成”拼图是对自我定位的顽强坚持,那么“城内”的编码制度则是抹去个性的强力趋势。一开始,门卫室的四人都是拒绝使用编号的,直到〇五三一到来,她固执地认为到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如果有的话,也是从他人那里继承来的。与她谈话的钟娟娟却固执地使用名字,即使“每个月的例行检查,他们会像报数一样报上自己的编号,在那些属于自己的快递或者其他物件上,像签名一样签上自己的编号”。
无力又可悲的是,这种坚持只是自欺,当她潜意识中仍然通过身份证号的“X”辨识出〇五三一来自很远的地方,这种坚持就失败了。谈话的最后,她也不得不承认,名字只是大家不会深究的代号。在这里,作者设置了一个极具仪式感的情节:
“〇五三一走进来,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编号用粗笔写在了窗户上,写完的那一刻,整个门卫室似乎也被这串数字标记了。”
选择用编码标记到达的经验,这是数据时代的“到此一游”,个体和场所的关系被固定在一串字符中,宣示着存在和所有权。连同个性化经验被抹除的,是对差异进行感知和想象的能力。上一秒写在黑板上的入住人姓名,在下一秒变成数字串,再也找不到想象其面貌的基准点,而当冰河镇的人们习惯用值班人的名字定义一天时,也就失去了对“星期几”这一概念的感知,时间的流动也不再具身。更讽刺的是原本鲜活的人变成了工具般的标识。
实际上,小说中明确出现的编码只有两个:神秘的外来者“〇五三一”和章敬业的门牌号“〇五一六”(索罗有时候也如此称呼他)。两个“〇”的符号显然是作者精心挑选的,既和现实中的编码规则呼应,也以其视觉效果增加了文本的解读空间——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空心的、等待填满的圆形。
闭环的圆形结构不仅是人物处境的写照,也构成了“世界”的基本空间形态:“同心圆”式的圈层分布。“如果朝着某条直线一直往前走,能发现很多和自己生活的镇子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别一圈圈地走,绕得慌”。在这个想象性的世界中,作者把经典的“城市分层”问题作了更当代的处理,空间上不再是垂直的“地上/地下”或水平的“市区/郊区”,层级之间的区别不再仅限于经济水平,而更多体现在获取信息的不对等上。

《后天》剧照
世界已经完全碎片化了,不同的部分被分到不同的地点,但由于沟通的不可能,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永远不可能得到呈现。在这样的“冰河”里,人的认识能力也相应变得不连续,整个世界是不可确定的,似乎无可挽回地滑向不可知论,带着典型的后现代特质。
有趣的是,这个“世界”的各个空间以“共时”的形态存在,〇五三一来自一个骑马、看天色判断时间、只有钱庄的“前工业社会”,“冰河镇”曾经是一个以物易物的“准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最近的“城外”正过着垃圾分类、戴口罩通勤的生活,最高的“核心城”用机器人走直线送信……
这是不同文化形式的密集并置,它们如此切近,似乎表征了信息时代的新特征——集聚和凝缩的“超”。并且,这些空间并不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简单并置,而是经历时间循环后的结果。在环形的时空观下,作者也将幻想与现实的连接点设置在那些被剪去的空白处,走出“城内”,亲身感受“空白”的世界。
总得来说,《冰河》表现出了当代人城市感的变迁,城市一直处于塑造之中,但在想象性地退出现代化之后,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仍然横亘着,人在城市中依然处于一种无根状态。在被反复拆解、重编、过滤的碎片化信息中,我们能否找到空白、填充空白,恢复“生活的厚重感”,本身就是一场未完的叙说。
原标题:《王苏辛《冰河》:拼图、编码及报纸的空白处丨新批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