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需要工作的40+东北大姐大哥,涌进麦当劳打工 | 吴楠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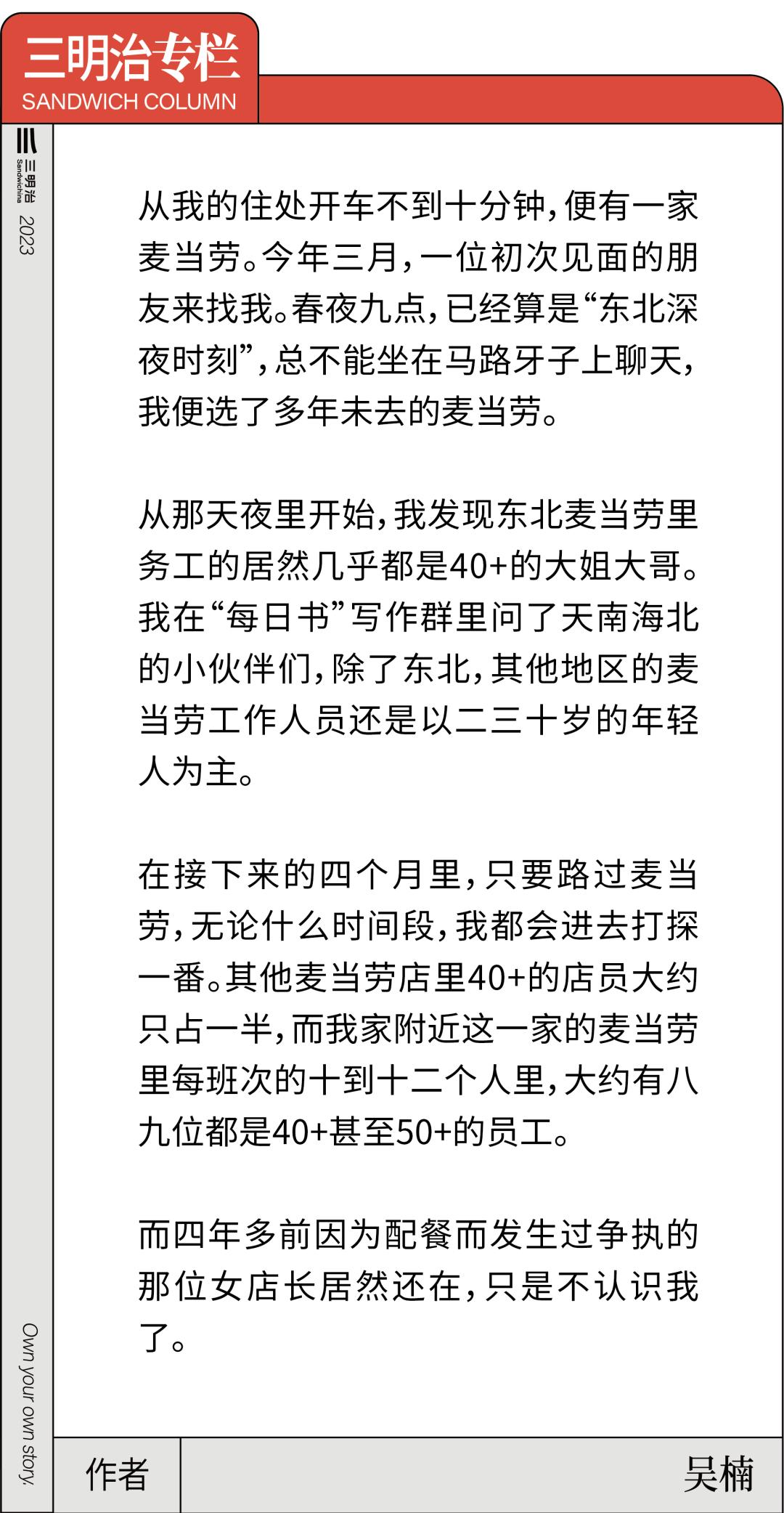
1
“你好,要我来帮你点餐吗?”这位头发刚过耳朵,经过熨烫看起来比较蓬松的大姐努力挤着笑,眼角褶子争先恐后想讲诉故事一样。她是麦当劳40+务工者之一。大姐判断了一下我的年纪,不至于连手机都不会用,“你用手机自己点,需要再叫我。”还不等我回答,大姐自顾自地转过身,往有椅子、可以靠墙坐下的经理办公室走去。大姐只迈出两步,就走进去了,空间安排得就是这么紧凑。
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大姐的脸上看起来有些浮肿。其实她只有四十五岁,但总让人感觉年近五十。我不忍心让大姐的热情落空,于是问了一句,“怎么点比较合算?”穿着浅粉色裙子、深粉色衬衫的大姐立刻又有了活力,拿出一张雪弗板做的餐牌,用手指一边指点一边介绍道,“这个套餐,加上一张卡,一共是四十六。但你下次买,就是二十六。一个月有效。”
麦当劳里不同的职位穿着不同的工装。这位大姐的装束被称作“麦当劳小粉”。我记得在2019年来这家店时,小粉还是二十岁的女大学生,站在明黄色的电子点餐屏旁边,付下上半身、声音温柔地问,“小朋友想要什么玩具呀?”如今这句话通过腰围足有之前女孩两倍的“老粉”口中说出,颇有力气,好像是黛玉变成了嬷嬷,“你家孩子想要哪个玩具?儿童套餐里的,我给你拿出来,让孩子自己选也行。”“老粉”是真的热情。只是带着孩子进来的爸爸妈妈们,似乎找不到以前麦当劳里被年轻女孩包围着的欢乐。
“你不要说我快五十岁行吗?”和小粉大姐熟悉一些后,她颇为不满。我说东北都喜欢按虚岁,但“老粉”就是不肯,并坚持让我称她为“小粉”。
这天,小粉大姐的动作明显迟缓,大嗓门都小了不少。昨天是周日,来的客人多。周末时,麦当劳的店里会来两个大学生,都是计时工。一般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小粉大姐则是早班,早上七点前就要到。她老公开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送她。
她和一位穿着黑色工作服衬衫的大姐有点“唧唧格格”(东北话,意思是很小的矛盾,彼此还说不出口,在心里又不舒服)。小粉和黑衬衫是近似的职位,工资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黑衬衫可以协助做一些食物,包括炸薯条、打甜筒和可乐。
其实在黑衬衫不来时,炸薯条和打可乐之类的外厨工作,小粉大姐也是愿意做的。但按照工作上的划分,小粉大姐负责前台,包括点餐和帮助等待的客人。那早,黑衬衫大姐尤其慢吞吞的: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打可乐的时候就不能同时打甜筒,拿薯条则不能同时拿鸡块。这让很多带着孩子的家长在前台扎堆等着。大家都不想等,七嘴八舌地报着自己的取餐号,闹闹哄哄,小粉大姐一次也只能应对最多两个客人,多了回答问题的时候就驴唇不对马嘴。两个女人暗自较劲,比谁的反应更慢。
女店长着急起来,叫小粉大姐,“你去把这个餐配了。还有那两个甜筒,是这位男士的。”小粉大姐当然不乐意,但也不能表现出来。她大声回应“好”,走到点餐台旁,挑了一个小五十、带着孩子的女人,帮其点餐。小粉大姐喜欢帮助同龄人,同龄人连手机小程序还用不好,可她却可以“帮”她们。这让她有成就感。
小粉大姐和黑衬衫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谁干的多,小粉大姐认为自己和黑衬衫大姐就不是一样的人。黑衬衫大姐虽然也是四十多岁,却是从农村来的,每天都扎着一个小辫子,之前听说还在火锅店干过。小粉大姐头发烫过、每天化妆。“精气神儿不一样。”小粉大姐常说两句话,一句是“精气神儿”,一句是“闲不着”。
小粉大姐生于1978年底,两年后实行计划生育,而她的父母原本打算再要个弟弟,结果没来得及,小粉大姐成了独生子女。父母一气之下把她的年纪改成了1980年出生,似乎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独生子女并领取补贴一样。
1997年,小粉大姐的大姨一家四口,下岗到家里只剩下一个上班的。大姨在三个月里连着来借钱两次。小粉大姐家也没什么钱,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自谋职业。一天小粉大姐放学回家,就听见母亲和大姨在屋子里低低地边哭边聊,“忙起来就好了。人不能闲着。你手工好,不然就开个裁缝店吧!”小粉大姐就是从那一天记住了一件事,人呀,忙起来,不能闲着。
但忙与不忙,很多时候大环境才是控制这一切的主要因素。小粉大姐生怕自己懒惰,生活就会没有着落。从1999年到2006年,小粉大姐顶岗上班,因为勤快还被评为“三八红旗手”。但当工厂里的大学生以每年一百多人的增量进入单位后,小粉大姐发现再忙也不会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下岗”,人都要经历这一步,但小粉大姐不肯,她开始寻找能让自己“忙起来”的地方。
2
小粉大姐去过英语培训机构。在那里,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东北也需要靠关系,最后竟会被校长的亲戚顶替。小粉大姐想,不要再去这种民企,“不正规”。她要去外企,这辈子还没去过外企。麦当劳成了她的梦想。
小粉大姐很快喜欢上麦当劳,这里的窗户很大,桌椅干净,阳光争先恐后地挤进来。她以为自己无法适应一年四季都穿着短袖上班,试过才发现也没那么难。小粉大姐买了两件七八十块的毛线衣,自己动手把长袖剪成短袖,然后套在衬衫里面,这样看起来“短”,却不怕冷了。尽管被年轻的小时工看到,偷偷笑。可同龄的后厨大姐却拉着小粉大姐,研究了半天,照猫画虎也来这么一件。
小粉大姐在大部分时间里会在一开始带一点台湾腔,她认为这就是普通话。但语气里的娇嗔感让人忍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她在偶尔走神时,会恢复到平日说话的状态,语气里些许对生活不满的东北味总是难以掩饰。或者多说几句以后,就变成东北普通话,尤其是每次早餐时客人让她续杯时。哪怕客人自己带了杯子,她都要对方把纸杯递给她,然后她把咖啡倒进纸杯里,再把纸杯递给客人,由客人自己把纸杯里的咖啡倒进水杯里。她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释,“除了店长,没有人可以直接往水杯里续杯。”
小粉大姐只认店长。这是一种东北人的智慧,只认自己能接触到的最大领导,至于做事好不好不重要,人情和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小粉大姐习惯了被人领导,只要是店长说的,不管对错,她都听。小粉大姐喜欢自己好像没有大脑一样。
这种心态得到了家里人的认可,她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听话,要肯干。但要听最大领导的话,干活干到大领导面前。这种东北家传,是不少东北人的普遍心理。
一次,顾客过来点餐。店长没看到,小粉大姐也装着忙碌。顾客着急起来,在前台大喊着。店长听到,让小粉大姐去帮忙,小粉大姐二话不说地过去。店长也明白,小粉大姐怎么可能看不见,前台一共就那么大点的地方。小粉大姐会在顾客走了以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对店长说,“他们怎么这么着急。”
前一阵子小粉大姐的邻居看到她每天很早出门,问她在哪里上班?小粉大姐大声回答“在外企”。“麦当劳算外企,对吧?”小粉大姐问我。
麦当劳本土化是非常明显的。加上至少这家麦当劳里以四五十岁的服务员为主,于是在称呼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很多麦当劳里的员工是相互称呼名字的,用来表示彼此的平等。但在这家麦当劳里,大家却叫着“伙伴”。
小粉大姐不知道“伙伴”这个称呼的来历,可她喜欢这个词。尽管只有店长大声叫“伙伴”时,大家才会回应,小粉大姐更多是处于应答的角色,但她喜欢这种感觉。“就像我父母参加工作时,那种车间里的氛围,一呼百应。现在都没有了。”经历过下岗,变化的不仅是工作,还有人们的精气神儿。
而“伙伴”叫得顺口后,麦当劳里的40+50+员工根本记不住彼此的名字。因此当我问“你知道那个负责外卖的大叔叫什么名字吗?”时,她也只是撇撇嘴,“名字不知道,面黄儿的(东北话,面熟)。”
麦当劳里送餐的大叔怕是店里年纪最大的。大叔总叫我“小伙”让人有点受不了。在东北,“小伙”的意思和“毛头小子”“办事不牢”差不多同意。
送餐大叔认为自己和麦当劳店里的其他人都不相同。因为大叔以前是做生意的。在东北,有三种特别笼统又很概括的工作:在工厂、做生意、体制内。而前两种在五十多岁的沈阳人看来似乎有着某种关联。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变革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离开东北“下海”的。更多人留了下来。
在1995年左右,沈阳夜市兴盛,其中太原街夜市首屈一指,“卖什么的都有,衣服最多,还有旅游鞋。”送餐大叔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了蓝白相间的旅游鞋。直到今天,他还是穿这种蓝白相间的旅游鞋。
关于“旅游鞋”,似乎是一个东北传说,至今父辈一代仍这么称呼这种介于运动鞋和休闲鞋之间的款式。口口相传的说法是这种鞋来自于香港,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穿着这种鞋,有一种去过香港旅游的意味,因此叫“旅游鞋”。还有人说,这种鞋生产出来,就是为了旅游的。旅游鞋,多浪漫的名字,带着说走就走的意味。那时人不知道什么叫说走就走,但心里有着类似的想法。
现在看起来,旅游鞋不过是一种老式运动鞋,甚至在市面上都看不到了。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五六百,一双旅游鞋就要八九十块钱。如今,大叔会去早市场上去找类似的款式,一双鞋才二三十块,可以穿半年。
大叔就踩着这样的旅游鞋,成为了麦当劳的送餐员。
3
和小粉大姐、黑衬衫两位麦当劳女士的特色鲜明不同,麦当劳送餐大叔们总是面目模糊的。每次看到他们,总会被红色的外套、黑色的外卖箱子占据了大部分的视觉焦点。
旅游鞋大叔成为送餐员时,美团之类的外卖还没那么火爆,而且麦当劳承诺半小时的送餐时限内可乐里面的冰都不会融化。奥秘就在送餐大叔背着的送餐箱里。送餐箱内分成一格格,把可乐、汉堡、圣代、麦旋风分别放置,保证不会倾洒。
最初,送餐箱是不锈钢焊接的,里面分三层,比24升的背包还要大一些。加上金属的材质,沉甸甸的,背在肩膀上时间久了,压得颇疼。现在则改成塑料材质,更轻更结实。可麦当劳的要求没变,“至少到了客户手里,可乐里是有冰的。拿手晃一晃,能感觉到。这才行。”这样的要求乍一听很难实现,实际上也有办法。
大叔会在配餐时往可乐时多放些冰,尽管这样会让可乐变淡,但足够的冰可以让这一杯可乐就算在盛夏送到客户手里依旧是浮着冰块的。同时,在送餐箱里,大叔也会放几杯冰,特别是在放可乐和冰淇淋的那隔断里,冰多了,自然温度就下来了。
当时配送人员很少,要求没那么苛刻,竞争也不激烈。加上每一单麦当劳都是额外计算配送费,一般是九块钱。这对于点单的顾客来说不算便宜。麦当劳的夜单很多,在数年前还算是颇有些昂贵的麦记炸鸡和汉堡,一些人比较看重的。在夜里,送餐路上不会堵、电梯也通畅,连小区的保安到了夜里也懒得管了。这些条件让大叔对如今卷得一匹的外卖遭遇颇为不甘。
那天送餐大叔刚回到店里,就接到了被投诉的通知。大叔纳闷,冰没化;装汉堡的纸袋也没有脏;自己的态度也很客气,都是按照话术讲的。等看到顾客投诉的原因竟是“串味”。
如今以80后90后为主的外卖小哥,和60后的麦当劳送餐大叔之间,怕是有着“工作代沟”。经历过下岗的那一代对于生活必需品的态度是“能用就行”。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但夜里点可乐、汉堡、冰淇淋,还要送上门来的人,又怎么仅仅是为了果腹?
“你的箱子里,的确有味。”店长煞有介事地闻了闻。送餐大叔没吭声。“你的衣服也要换一换。”店长又说。大叔不高兴了,“管得太多了吧!”
“我们那一代人”是经历过下岗的一代人,特点就是总觉得什么都跟自己有点关系,大叔称之为“责任心”。60后一旦认真起来,就有点古板。曾经在工厂里做工人的大叔,养成了“图纸上画着一毫米的尺寸,就不会加工到0.9毫米”的习惯。但这样的经验,大部分来自实践操作。送餐大叔以前在工厂时连图纸都不爱看,对于麦当劳厚得跟字典一样的员工手册上写着的那些条条款款,打心眼里认为,不如亲自骑上电动车,跑上几趟来的实在。“我们那些人也都没啥学历。看字费劲。”送餐大叔和小粉大姐一样,曾经获得的“大众学历”在如今是低学历。
责任心让大叔感觉“串味”是对自己的侮辱,他的嗓门大起来,“他是吃东西还是闻味道啊?我身上有什么味?这都是劳动人民的味道。他点个洋餐,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大叔在被人问到为啥配送费比别的外卖高时,也会说“我这是外企!”
4
对计时或者计件收入来说,新冠肺炎的影响的确不大。但对店面的影响还是很明显。以前这家麦当劳的二楼是有厕所的。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二楼的厕所便被封闭了。麦当劳里没有卫生间,只能去商场里,对一家24小时的餐厅而言,算是罕见。
但麦当劳里的中年店员,都爱夜班。有活就干,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在店里休息。很多年轻人会认为小时工的收入太低了,但是40+的大姐大哥们却无比珍惜这一个小时10块钱的收入。在新冠肺炎之前就一直努力工作,所以就算到了疫情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地辞退他们。何况在麦当劳,“外卖骑手都没地方休息。麦当劳随时都有热水喝,冬天夏天都有空调,多舒服啊!我要一直干到麦当劳不用我为止。”小粉大姐、送餐大叔都说着大实话。店长早已习惯了和这些中年员工打交道,“不是只有麦当劳才这样呀!”
在这一条街上,挨着麦当劳的餐饮店有日式牛肉饭店、韩式拌饭店、台湾卤肉饭店,里面的服务员和后厨基本上都是阿姨和大叔。只有连锁蛋糕店里还有年轻人。而其余饭店里的中年服务员们的标配是个个都有着热情的大嗓门。
这些日式、韩式、中式的料理,搭配上服务员、特别是大姐服务员的大嗓门,透着烟火气的热情,充满了东北家庭氛围。这在东北真是太常见了,服务员们的年纪越来越长,饭菜价格倒是纹丝不动。只是和米饭类的料理比起来,麦当劳这种西式的餐饮在东北很难有妈妈的感觉,谁家五六十岁的老娘会端着可乐和汉堡从厨房走出来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年轻人来麦当劳工作。前一阵子,一个农村孩子来应聘,一周后就不干了。他就是试一试。这里工资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如去大城市或者南方,反正都是离家在外,要么就学东西要么就赚钱。
“什么是学东西?”店长问。“学美发也比在这里打可乐强。学美发将来可以开美发店,但是学打可乐却开不了麦当劳。”“那肯德基也是类似的情况吗?”我问。店长立刻一改之前说话慢吞吞,准确而急切地吐出三个字,不清楚。似乎这么急切的语气有点好笑,我们就都笑了。
麦当劳里,最不东北的,大概要数“如果想做一个好员工,最好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去做,省脑子也省力气”。说这话的不仅是小粉大姐和送餐大叔,就连来这里当计时工的年轻人也如此想。每个小时十元左右的薪资,大学生都没啥兴趣。“到任何时代,有点本事的,还是要自己干点啥。”送餐大叔口中的“干点啥”指的是做生意。
一种做生意是自己干点小买卖,包括在夜市摆摊,以及开个小店。有点技术的,可能会开一个缝纫铺和修车摊。如果家里有矿,开个小型机加厂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种做生意是到五爱市场租个档口。五爱市场最初是露天的大棚,以批发价为噱头,主打便宜。营业时间是从凌晨三点到下午两点。凌晨是给批发上货的人的,用麻袋装好批发的货,直接送到货站,天亮前就可以发走。近年来,去逛五爱市场的人越来越少了,营业时间也延长到了下午五点。五爱市场做生意,无论是租了买了档口的,还是来打工当售货员的,都称之为做生意。
大商场里的那种做生意,多半是下海之后带着钱回到东北再赚钱的。在东北人口中那不叫做生意,那叫“大老板”。直到如今的沈阳,60后听说谁在五爱市场工作时,会顺口说一句“原来是生意人”。
很多留在东北的五十多岁中年人总觉得东北好。东北对于东北人来说,是家也是根。租个档口做小生意,是没有技术的人不得已采取的谋生手段,同时也是可以留在东北生活的保障。做生意不需要在麦当劳里工作那样需要遵守各种规矩。但麦当劳不累心,做生意则累心。“这把年纪,不想折腾了。”40+的麦当劳大哥大姐异口同声。
5
人手不够的时候,麦当劳会招聘计时工。计时工要求是大学生,一来好管理,二来有活力。有一个应聘的大学生问,在麦当劳里打工,是不是可以吃到免费的汉堡?小粉大姐、送餐大叔从来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他们似乎对麦当劳里的食物并不感兴趣。
小粉大姐羡慕台式卤肉饭的服务员,工作餐就是鸡腿饭或者猪排饭。自己吃完汉堡,总觉得肠胃火烧火燎的,而喝了咖啡则总是睡不着觉。顶多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吃多了又不舒服。“和监控与否都没关系,他们就是单纯不想吃。”店长说。
店长对小粉大姐等几个人说,如果顾客反映食物有问题,可以立刻重新做,不需要请示。这件事提了好几次,但是大家依旧会问,毕竟决定权在店长。一次,一个带小孩的老人给孩子买了个甜筒,孩子没拿住,掉在地上,哭闹起来。老人说自己身上没带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小粉大姐看到了,特意跑到办公室里去问店长,可以不可以免费给孩子打一个甜筒。
除了不愿意承担责任外,麦当劳里还有一些对于中年人不够“友好”的地方。这天一上班,送餐大叔就不吭声地往外走。另外几个中年员工都成了“哑巴”。原来,那天有了新规定,大家要对新来的员工称呼为“新番茄”。新来的员工不过就是那两个计时工,很年轻,中年人说不出口这三个字。“叫‘小番茄’也比‘新番茄’强啊!”小粉大姐说。可是其他中年人表现得宁愿当哑巴。
小粉大姐应该是并不喜欢大学生计时工的。早餐时段,大学生计时工还是新手,一口气接了十多杯豆浆,排成两排放在配餐区,免得人多时来不及。小粉大姐看到了,毫无预警地对着计时工大叫起来,“你知道早餐到几点吗?”计时工愣了一下,摇摇头。小粉大姐高兴起来,对店长说,“十点半。现在都十点二十八了,你打这么多,谁买?”
我第二天再去麦当劳时,提到昨天被小粉大姐训斥的计时工。“自己不干了,就说了她几句。”小粉大姐的嗓门大起来,声音也有点激动,“现在这小孩……”
记得在2002年前后,能来麦当劳作计时工是一种让人羡慕的职业。我曾经拿着简历去应聘过,负责面试的人似乎对我的外形并不满意。很应付地交流了六七分钟。后来我甚至还打电话过去追问,为什么自己不合格?对方很敷衍地说,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就是不太合适。或许就是由于这样的情节,我才会对麦当劳念念不忘。
可是现在麦当劳已经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快餐店。年轻人去哪里了呢?店长并不在意这件事,“这很正常啊!这个工作不体面,毕竟是服务员。”关键是没有未来。在麦当劳当服务员,年轻人能学到什么呢?管理、技能,都很难学到。用时间换钱,也划不来。
我建议店长开直播,她笑着摇摇头,说公司有统一的规定。正说着,小粉大姐又扯起大嗓门,“欢迎光临,我来帮您点餐吗?”这就是中年人的麦当劳,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出很有朝气的样子。而这种朝气并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大嗓门。这对中年人来说也是一种表演。他们用最擅长的大嗓门来表达热情和朝气,尽管在行动上看不出什么。
小粉大姐努力咧开涂着鲜艳口红的嘴唇,在角落里的送餐大叔也站了起来,应该是有外卖配送单了。中年人的努力,似乎没什么希望,但也没有什么选择。在此刻的热热闹闹,有些可笑和无奈。
这个月,我从成都出差回来,飞机因为大雨而绕行,在天上多飞了一个小时。饿着肚子回家路上,我看到这家熟悉的麦当劳,决定填一下肚子。而进去后,我发现五个多月前还在这里工作的小粉大姐和旅游鞋大叔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略年轻一些的男店员和一个精瘦的送餐小伙子。我诧异地问起他们的去向,店员们似乎都不知道。直到有一个女店员走过来,想起什么似的,“他们年纪大,被安排到夜班和早班了。”
原来,年纪大,到底也成了他们在麦当劳里被边缘的理由。而我们将来也都会走到这一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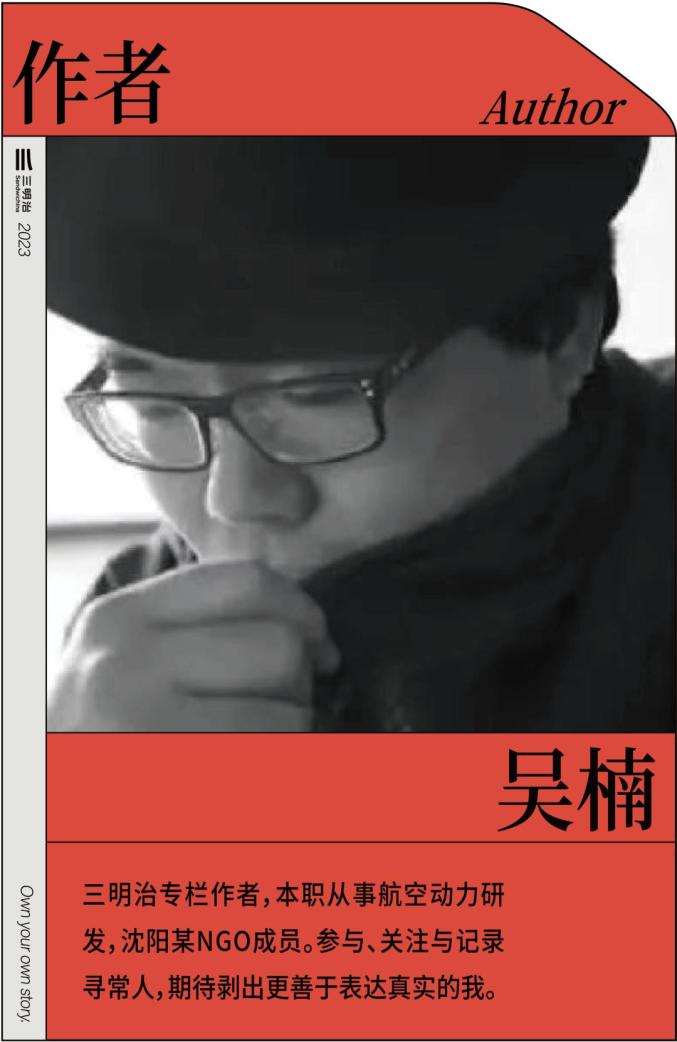
原标题:《需要工作的40+东北大姐大哥,涌进麦当劳打工 | 吴楠专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