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敬雅︱最后的超越:记高王凌先生新作《超越史料学派》

高王凌先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老师,学习清史十年以来,虽然没有正式拜入高老师门下,但是从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我追随着高老师听了很多他讲授的课程。我虽不曾涉足当代史研究,但是多年耳濡目染,对于高老师的学问,也有几分认识。记得今年7月底,我俩最后一次在微信上聊天,高老师跟我说,自己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联系起来看,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样呢,问题很多。但是所谓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实现了,这样来看,中间的那些“倒霉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作为一个当代历史的观察者,一个清代历史的研究者,高王凌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和视角,也时常教育我们,要以自身的视角(当身历史)去观察既有的历史(正面观察)。斯人已逝,斯言长存。这几日每每夜不能寐,辄起身翻阅高老师的新作《超越史料学派》,虽然某些问题,我有和高老师不甚合拍的认识——可惜他也不能把我“拧”过来了,但是我认为,在今后漫长的治学道路上,我将会对书中的言论,有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恩师高王凌。

一位观察者
所谓“当身历史”,就是你在历史中找到一个自己的角色,正如在剧场中,买一张票一样。位置的不同影响了历史观察者的视角,长期受限于史料的历史研究者,会因为后视之明产生出一种“上帝视角”的幻觉,好像自己在某段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然而这并不能做到,不如放低身段,作一名观察者。所以与其说历史是被叙述和阐释出来的,不如说是被观察出来的。
高王凌老师早年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些工作,并和当中的一些骨干人员熟识,可以说是他后来研究农村政策的一个立足点。用高老师的话说:“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我也不是正式组员”,但是“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我们很庆幸这样一位有着观察觉悟的“历史学家”置身于一些当代政治运行当中,因为这种观察是有历史自觉性的。在一个历史变革的时代,身临其境地思考问题,恐怕也不是所有历史学者都有的机会。所以后来高老师的当代史研究,一直申明一个“观察者”的姿态。我们不是统揽史料,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有心人。至于这股洪流要往哪里去,我们置身其中,随之而去。
高老师曾说,虽然自己的“户口单位”是研究清史的,但是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因为跟自己经历密切有关,在内心里,却是放不下的。他的计划,“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我们非常有幸能够看到高老师当代史研究的很多成果集结出版,如果说清史研究,高老师还是一个“场外”的观察者的话,那么对于当代史,他则是一位“场内”的观察者了。
除了“发展组”的经历外,与杜润生老的一段师生缘分,也对高王凌老师日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高老师于十余年前开始整理《杜润生自述》,他曾经说:
现在看到已出版的杜润生自述,几乎每章每节,都是自己从笔记本从录音带上剥下来,再由杜老批阅,一遍遍修改的。也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岁月,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友谊和师生关系。无庸讳言,在这中间,我向他学习了很多很多(其中是包含了多少经邦济世的学问啊)。因此这一段经历,也特别得我的珍重。
杜润生老作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对于农民和农村政策理解的精辟与到位,深深地影响了高王凌老师。后期高老师作品中对于太谷农民的调查,对于八十年代的反思,以及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都渗透着杜老研究的精髓。
可以说,有机会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观察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幸事;而可以读到一个有历史记录自觉性的学者,对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与评论,也是我们的幸事吧。

一位寻访者
用高老师的话说,历史的旨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场景的还原。如果说“农民的反行为”,是一句话就能讲得懂的道理,那么如何将这个“道理”放到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去,让这个场景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变得有声有色,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了。这种场景的还原需要一个观察者置身其中,而不是从故纸堆中翻检可得的。比如高老师在写道回太谷调查农民“瞒产私分”一节,就说到:
当晚,我见到了应宝(原大队支书)和爱生(原小队领导,他俩一个是长友的姑父,一个是他父亲)。据他们说,瞒产私分,只有某些村子敢搞,咱这儿没那么大胆。村里矛盾多,再加上村子小,干什么都看得见,所以弄不成。但有的时候,该分茭子(高粱且是劣等高粱)就改成糜子、豆子什么的(这些算是好粮食);队里分粮,十斤给十二、三斤(说是扣水份),也短不了。
如此一来,农民们在包产到户实行前的种种做法跃然纸上,这种活动的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镶嵌到大的经济环境中去,才是当代农民的真实图景。当然,这里的“真实”大抵也是要抛去了对于史料的执着,是一种“因信称义”的说法。
口述史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研究方式,本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当代史的研究当中。高王凌老师对于口述史的关注要更早一些,这源于他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段经历。1982年,高老师参加了“发展组”对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目的是探索“包产到户”的发展模式,找一个典型地区作为典型。虽然其自认为在“发展组”中只是一位“客卿”,但是正是这种实地的调研经验,给了高老师一种在历史中观察历史的视角。本质上看,这种农村调查和今天的“口述史”研究,在方法和性质上,都是一致的。
后来在写作《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时,高老师再次回到自己插队所在山西省太谷县某农村进行口述史收集,这次的收集可以说是对于其“口述史”研究的一次全面实践。
在这次走访中,高老师反复推敲农民的心思,不断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农民的想法,改变提问和方式。比如在讨论农民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粮食分配问题时,他就意识到,在跟农民的交流中,如果你用“偷拿”之类的字眼,对于他们来说,就“言之过重”了。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叫“抓搲”,就是顺带着,拿一些到家里,胆大就多拿些,胆小就少拿些。(犹记得高老师在清华讲此课时,将此二字写在黑板上的场景。)这些如何在口述史研究中前期调研、过程提问、后期验证的实践经验,被总结于本书的《口述历史——我的一孔之见》当中。
世殊时异,在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刚刚实行的时候,农民对于政策的认识不同,讲的话也不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不正是“史料”么?而这些史料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记录下来的,叙述者本身又想表达什么,囿于其本身,恐怕是无法得知的,如果迷信它们,更可能被史料作了个局,陷到了里面。因此,作为一个寻访者,我们就似乎不得不超越了这些史料,去领会后面的意味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表达的那样: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超越史料的初衷,不仅仅是还原农民在当时生活的情景,而是要探寻更深层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只要是人的行为,就一定离不开人性,就是一种制度和人性在互相博弈中取得妥协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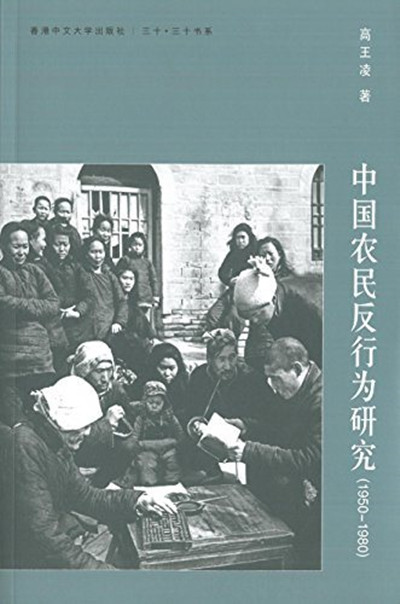
除了对于基层历史的发掘,高王凌老师也非常注重学人直接的交流,也是国内清史学界较早接触西方论著的一批学人。八十年代在美国访学期间,他陆续拜会了在美的汉学家们。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汉学空前繁盛的时代,在这种学术氛围下,高老师结识了费正清(Fairbank)、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帕金斯(Perkins)、曾小萍(Zelin)、白思鼎(Bereinstein)、黎安友(Nathan)、史景迁(Spence)、白彬菊(Bartlett)、施坚雅(Skinner)等国外历史、经济学家;也拜访了黄仁宇、王业键、唐婉、夏志清、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等中国学人,并与其中一些大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我认为,这应当是另一种对于历史的考察和寻访吧。
但是有趣的是,高老师在后期一直在提倡不要把中国历史做成“洋片儿汤”,也就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不假思索地往中国历史研究里面塞。因为这一番言论,高王凌老师还在学界中也算是开罪了不少人。他说:“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洋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它们都并不简单,并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回答。”这种勇气与锐利,是学人中很难得的。
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历史研究更像是“老夫子”的学问,一位葄枕图史的智者正襟危坐,于故纸中倾筐倒箧。但是熟识高老师的人都有体会,高老师的性子更像是一个大孩子。对于历史,他的研究是“冷眼热肠”的。高老师曾经说过:“不读博客的弟子将离我越来越远。”以至于每次上课或见面之前,我总要把老师的博客文章翻阅出来,揣摩一番。因为高老师总是会问我:“我的某某博客你读了没有?”如果没读,他会认真讲解,我则满心抱歉。
其实,这源于高老师总教诲学生,要做“活着的历史”,因此他认为历史是动态的,是要跟现实比对,不断思考的,不思考是一种懒惰的行为。高老师曾说,自己夜间读书,每有体悟,便是连觉也不能睡着了,定是要记下来才好。这种“洞察力”和反思的觉悟,使得这位老人在治史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反思者。
一位反思者
高老师在《研究题目与路径——阶段性总结的必要》一文前面,有一段按语:
我总以为,人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回过头来”,回顾、总结一番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一往无前”,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而且,这样做,相比起来,可能收获很大。因为你最多的东西可能不在前面,而在自己以往的历史之中。
这篇文章的主体是高老师在清史所成立三十周年(2008年)的时候所作的,这次收录书中,又做了一些增删。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高老师多年治清史的研究路径。高老师最先立足于经济区(四川地区)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做了向上和向下的拓展。所谓向上,就是就经济状况发展到国家决策,因此做了关于乾隆时期的粮政、垦政,官僚组织、政府决策、统治理念、宗教及精神生活的相关研究;而向下就是由经济组织形式向下挖掘,细化到租佃关系、人口、生产结构、农民的行为等问题的研究。
在清史的研究中,高老师可以说是“下学上达”的,政策上的研究使经济问题更具宏观性和现实性;而经济问题的研究又使政治研究更饱满、更立体。所以也无怪乎高老师后期会转入当代史的研究,这种在历史研究中的通达状态,已经无法用史料本身印证了。这就是为何在此书中,高老师强调要“超越史料”,要到“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看“无字天书”。
高老师的农村问题研究是一个不断在清代历史与当地历史中跳转和借鉴的过程。而两种方向相得益彰:在当代史中,研究者可以接触到政策的细节,目睹行政的过程,了解农民对于经济政策的反应和对策。而在三百年前的清史中,研究则可以掌握中央政策的流变过程,并观察事态的整体动向和结局。两相对照,边发现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
比如,清代与解放初期的中国,同样遇到“人口问题”;同样经历过对于可开垦耕地的错误估计;同样不能很好解决农村的多种经营问题;同样存在农村工业问题。藉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高老师的研究总是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并称“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宏观的视角可以了解政策的制定层,也就是“上层”;微观的视角可以体会政策是受众,也就是“下层”。“这样的历史,已不是传统的政治史,它更接近于社会。(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有所不同)它并不仅仅是关心‘社会’历史,‘底层’历史,‘民众’生活:老实不客气的说,它是直指‘上层’的,而且认为:只有到‘底层’去,才能解决所谓‘上层’的认知问题。”
高老师的研究,总是将史料穷竭后,再去探究文章后面的一层事实存在。他认为只有不断加以挖掘,才是所谓“真学问”。在其论著《乾隆十三年》出版后,他曾经说:“该书所涉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中国现代史观的改变,这样一个大问题。历史学家天生不是追求‘理论’的,他追求的是其他一些——可能使他拥有一些不易获得的‘观察能力’或曰‘洞察力’的东西(比如‘历史感’)。”
什么是有“历史感”的历史呢?那就是超越史料之后的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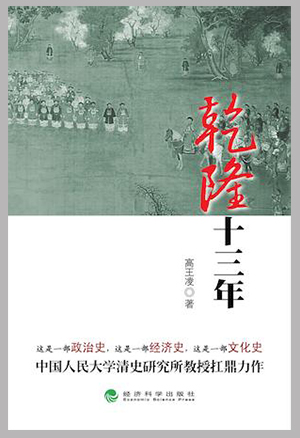
超越史料后的历史
高老师在书中记录种种的治学方法,最终都指向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历史最后的输出,应该是一种“不能使大家都知道”的状态。这种“含糊”当然不是过程或者结论上的“模棱两可”——高老师的论著中,结论都是相当犀利鲜明的——而是古人给后人,留下的一些余地。
在对史料重复考据的基础上,高老师发现了史料之上的问题。比如,就古代经济统计数据而言,古人对数据的“不真实”是了解的,也常常存心“留有余地”(无论是税收、产量、耕地数字等等),但到现代,却自以为那些数据是“科学”的,是“统计数字”,这就十分危险了。制度是“死”的,人可是“活”的,看到制度之外,历史才能活起来,才能应对实际生活的复杂多变。
比如农村的借粮问题,“究竟是一百斤,还是五七十斤,到底有多大意义?我想,这大约也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所了解到的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再说,它本来是一件隐秘的行为,如同‘雾里观花’:越想把它描清,可能就越为失真,越不清楚。而且,描述得再好,也无法改变它仍是一个‘外来者’的观察。”
高老师说,“总爱追问一个历史事件是出于什么原因?殊不知,许多事物是无所‘原因’的,即使有,也是个‘大概其’,万不可太当真的。”其实这种“大概其”,是普遍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大概其”,历史才能有弹性、有活力。
而史料中的其他部分,也如这些数字一样,并不那么仅仅是它表明呈现出的意义。在走访农民的过程中,高王凌老师发现,一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口述者,会把曾经的历史讲成文学作品。而现在留存的文学作品中,也隐匿了中国人千年未变的精神和人性。课上课下,高老师都多次提到,《阅微草堂笔记》不可不读。在书中,会有些狐仙作祟的故事,而因为这些狐仙拿捏到位,破坏力并不强,也未见被驱逐。因此,高老师悟到了中国人行为中对于“度”的自我考量。“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反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终于有意无意造成了一种‘不胜不负’的局面,成为一个‘维持会’。即令包产到户改革获得成功,我们也很难说是‘谁战胜了谁’。”
做学问是为了什么呢,高老师认为,不仅仅是学问本身。他曾经说一些学者,“生活在自己‘学术’小圈子和‘书本’的小天地里,离开单位,就好像一切都跟他藐不相干,无所谓了。”于此他是反对的。钱穆是高老师极为推崇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孟子意见,天地间一切道理,本由人心展衍而出。如人有恻隐之心,推广出去便成仁的道理。人有羞恶之心,推广出去便成义的道理。”因此学问做到最后,做的便是“人心”,便是“洞察力”与“通达”。
章学诚的言论也时常被高老师提及:“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我想,这些对于“超越”之后的历史的追求,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人的现实关怀。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做学问的目标,也许就在这种“下学上达”、“不明不白”之中了吧。正如高老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
真理,也可能须到那以外去寻找。历史学,不是为了寻求什么“标推答案”、(或已逝事件的)“正确路线”的。历史学的功用,不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是恰当的解读那些“当事人”、“决策者”的思想想法,以求进一步解读那个时代和那些个问题。当然,这里只是一种解读,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检视这一段历史。
后记:
从高老师去世时,我动意要写些东西,到这篇稿子完成,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拖拖拉拉,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法。因为书总是不忍快读,好似看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似的。我应该不是一个好学生,既没有犀利的文笔,也没有深刻的洞察,只是在我的位置,说一些学生的话吧。“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读书时,我还能时时忆起高老师讲这些话时的神色,这便是我所见到的,这一段的历史。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