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鄱阳湖边,一个正在消逝的渔村|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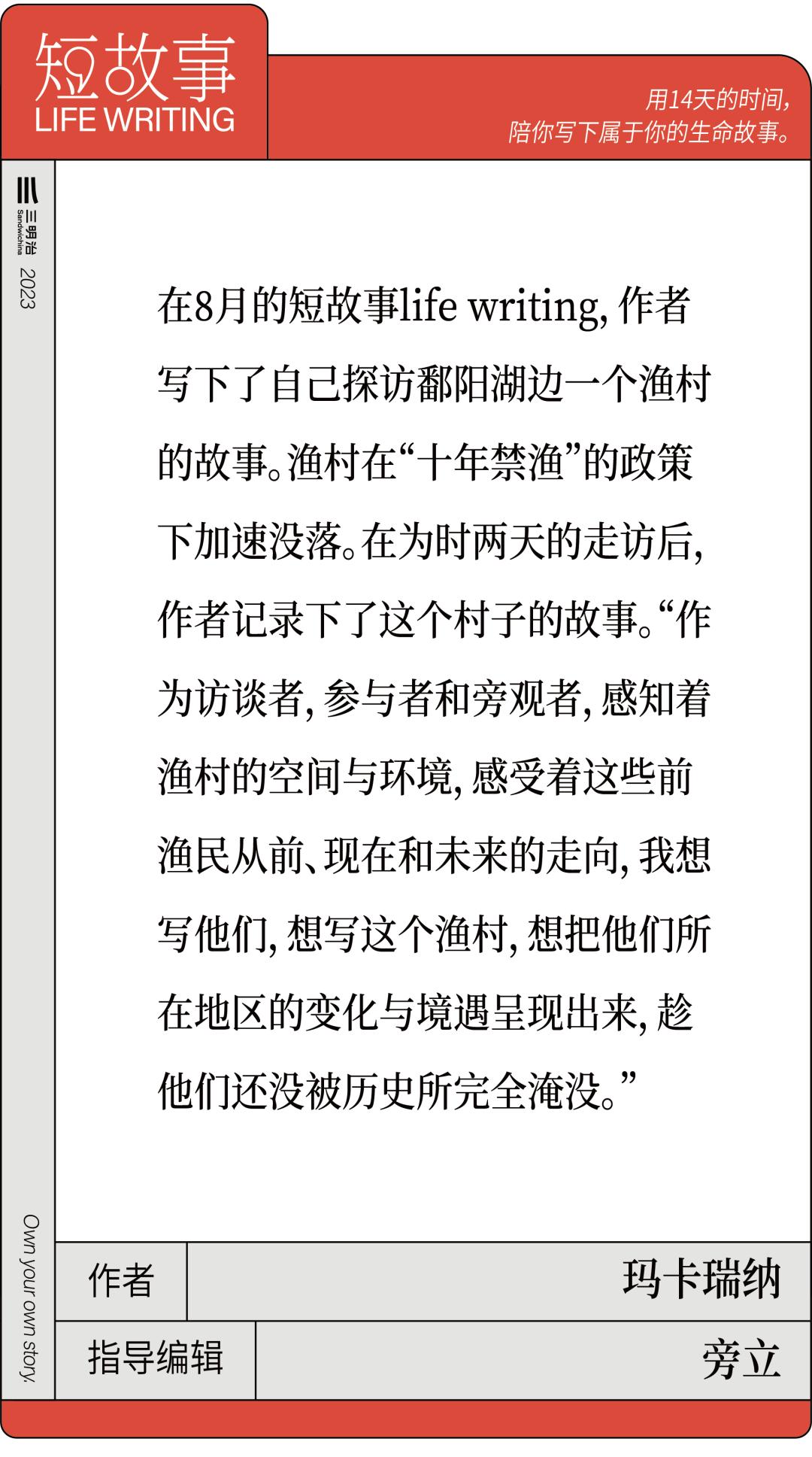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鄱阳湖边,
一个正在消逝的渔村
我们沿着渔村主路一直往前走,阳光直面打来,我本想向四处看看有无过往的村民可以询问,却被灼得睁不开眼。
渔村唯一醒目的是靠近渡口的饭店,门口摆着几张桌子,四五个村民围着在打牌聊天。我们刚走到饭店门口,几个村民探出身子,一言不发,脸上没有惊喜,也不带好奇,像鄱湖的波痕一样没有太大动静,只有提防、不解,用一种看外人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蛤蟆石渔村位于姑塘镇靠湖区的沿岸,从九江市濂溪区出发,驱车二十分钟就能到达。名字里的蛤蟆石就在渡口外裸露的滩涂上,涨水时根部被淹没,枯水时与陆地相连,现在被湖水淹过三分之一,巨大的两块石头原本合为一体。当年,蛤蟆石蹲在九江县地界,蛤蟆嘴对着都昌县,自古以来都是这边富那边穷,都昌人便觉着要砸掉这块石头,自家才能实现发展。“文革”,他们带来大堆炸药,义正言辞要扫四旧、破除迷信,于是轰的一声把蛤蟆头给炸掉了。1979年某一雷电之夜,大雨滂沱,冲断了石头的腰部,蛤蟆石倒塌,断为两截。

沿着173县道就能通往蛤蟆石渔村,村里只有一条主路
渔村不大,只有一条主干路,靠细长的堤坝支撑起来的173县道是外界唯一通往蛤蟆石渔村的陆路,沿路有很多工厂,水泥厂、水产厂、钢筋器材,不远处就是濂溪区的产业园,站在村口还能瞧见大烟囱往上冒烟,所有机器撞击的声音都从那里传来。入口码头处贴着褪色泛白的标语牌,“护鸟光荣”“爱鸟护鸟,保护环境”,彰显时代感的环保宣言。村路两旁的电线杆挂有感应式喇叭,车辆通过便自动播放:“鄱阳湖濂溪区水域从2020年1月1日零时起实行禁渔……”,声音环绕着整个渔村。紧贴居民楼的围墙一侧遍布着砂石贸易公司的招牌,“采砂管理、砂石交易、政府开票……”,而另一侧围墙喷漆着政府宣传“不可下水”的警告、保护江豚的彩绘图和一则用不浓的墨色颜料书写的《蛤蟆石记》。

渔村里如今遍布着砂石贸易公司的招牌。

渔村入口处的右侧围墙上,写着《蛤蟆石记》
见到他们的第一眼,我的内心并没有太大波澜。蛤蟆石渔村作为这次鄱阳湖「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站,我毫无头绪。渔民是我平日接触不到的群体,自2020年禁渔政策后,渔民成为失落的一代人,村子甚至也算不上渔民文化“保留地”,如何开口向不熟悉的“观察对象”询问,我缺乏经验,也不知道答案。在这里停留两天后,我见到了一个渔村如今落败的真实模样,越来越多的故事从平静的湖水中涌动出来,让我看见过去,也让我思索它的未来。
我们不是渔民了,
我们是无业游民
最先接我们话的是袁姐,她有着比周围的人更充沛的精力和姣好的面容,已经51岁的她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被烫成小波浪式的卷发用发饰扎起,穿着厚底运动鞋,手臂挎着黑色的皮质小背包,望向我们的眼神直直的,不带有任何的明显的忧伤,多了几分精明的警惕。
“你们之前都是渔民吗?”
“是啊。”袁姐伸出左手大拇指,朝我们晃了晃。我瞧见比常人更短的一截,不见指甲盖,肉团不自然地堆在一起,“喏,看吧,之前被网割断了,(禁渔)政策后我们就不打鱼了,现在打鱼是要坐牢的嘞……”袁姐说,刚开始禁渔的时候,周边村子有人偷偷去打鱼,被抓后就被判了刑,在牢里关了几年才放出来。
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是中国典型的季节性、吞吐型湖泊。在自然状态下,每年的4月、11月是鄱阳湖“河湖相”的转换期,5月至10月多为丰水期,湖水淹没洲滩;11月至次年3月为枯水期,湖底的洲滩出露,湖面退如河道,“湖相”转为“河相”,故称“高水是湖,低水似河”。鄱阳湖的江湖形态、连通性以及水沙交换,便成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湖泊南北长173公里,东西最宽处74公里,湖面面积3283平方公里,其整个水系流域面积约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97%,在生态和经济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湖的变化折射着江的变化,因此每一年湖泊的水文节律,都牵动着整个长江水域生态变化与人们的心。
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共同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指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中下游湖泊、湿地萎缩,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减少,枯水期提前。”2020年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宣布从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等重点水域全面实行十年禁捕制度。
此后,渔船和渔民消失在湖面水域,鄱阳湖回归平静。
“十年禁渔”的准备工作开启后,政府将渔民的船,包括渔具、渔民证、捕捞证等物件全部回收,渔船在岸边被当场肢解,根据各家船的大小,给了各渔民两万到五万价格不等的补贴。政府给到渔民的唯一优惠,就是渔民们交社保的时候只用交40%的钱,剩下的60%由政府出,一年总共8000元(今年涨成了8400元),要交15年,这样退休后就能享有补贴。
“诶,你们有听到说明年放开政策吗,如果可以打鱼……我替我老公去报名。”袁姐看我们不是本地人,反而追问我们。
这并非我预料之中的结果,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开门见山所怔住。稍短暂的尴尬停顿后,我们道明了来意,尝试把话题聊得轻松些,好进行下一步互动。后来,在饭店门口的多次探问中,我才慢慢观察和体味出袁姐话里的某些滋味和她极具鲜明的气质,试着在她语言之外的缝隙里探出某些东西,她的眼神飘动,她的语调激转,以及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袁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说,自己出生在湖北一户地主家庭,文革时期遭受打压,父亲成了遗腹子,一家人一直在陆上务农。成为渔民的缘由来自她的丈夫,丈夫虽也是湖北人,但从爷爷那一代起就开始到鄱阳湖打鱼,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后,袁姐便从湖北嫁到了当地,此后就跟着丈夫慢慢学习打鱼,成为了渔民。
从农民到渔民的身份转变并没有让袁姐不适应,相反,她在这样的环境里让自己变得更加灵活,她认识很多人,习惯于各类人打交道,你很难看出她脸上会浮现什么样的情绪。她与当地很多渔民不同,渔民几乎没有读过书的,而袁姐此前的农户家庭让她接受了初中教育,又识字,又积极,爱交际,精气神像个年轻人,笑起来像个少女,让她在饭店门口的人群里,好似自成一种灿烂的热烈朝外人散去。
然而这样的热烈也没法抵挡残酷现实的袭来。袁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在深圳打工,“疫情后钱就不好挣了。”袁姐说。女儿嫁到了浙江,在家里带孩子,也没有去外面找工作。当谈到现在渔村的情况后,袁姐语调微微高涨,“很不好,大家都没有工作,90%的人都不识字,老了后出去打工也不要你,年龄超过了……无业游民,我们都是……”她用手指圈了圈身后打牌的村民,“无业游民”们打牌打得正欢,没顾得上抬头看我们一眼。

村民常光顾的饭店,旁边就是渡口
“但你们会打鱼这门技术啊,很多人都不懂的。”
“这能有什么用?有技术也没办法施展,你们读过书,我们没有,我们不识字就没用。”
袁姐还问我们,重庆、四川和西藏是不是六月底会下雪,她说她在抖音上看到别人发出来的。
我们被问得说不出话。
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已经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渔民的湖上视角所见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有位大哥告诉我,打鱼有技巧,湖面也有地形,那在湖上所感知到的天气又是怎样呢?袁姐对未曾去过的陆地产生好奇,她不知道重庆、四川和西藏在祖国的哪块大陆上,我以陆上思维在评估她的世界,却在地理与空间感知中和这里的人早已产生了距离。
在半月后对那时田野的回忆中,如果让我讲给别人听,这一幕一定是最无言、又最有力的证言。
你还认为自己是渔民吗?
“我们不是渔民了,我们是无业游民。”
……
那是一种隐蔽的忧伤。从袁姐眼里看不出的忧伤。
悬浮着,织网着,等待着
渔村像是停留在更遥远的历史里。对刘安顺和夏国花来说,能说给我们听的都是过去发生的故事。
如今的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了。

渔村的居民房,清一色的桃红色屋顶
在老一辈口耳相承的宗族历史里,刘姓祖先因遇发大水,从湖北大冶逃荒到鄱阳湖边。刚来的时候,语言不通,口音不符,辗转多个周边村庄都不被接受,唯有蛤蟆石村愿意接纳这批远来的渔民落户,于是在此处扎根落脚。说是稳下来,倒也只是在船上每日摇摆,不定的根也跟着摇摆。那时候,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码头的兴盛,“打码头”之风跟着从湖北迁到江西,船民按水系和航道结成帮派,因为其水运优势,下游地区的物流和人流,小到食品、杂粮、皮革、棉纱,大到桐油、洋广杂货、矿石,都靠着这一带行帮帮派。
用刘安顺的话说,他们武功好,有本事搞来大船运输,同时对迁过来的渔民感到“可怜”,叫一声“鱼花子”,跟打发流浪汉一样。
有土地的农民才能受人尊敬,住在水上的渔民属于贱民,其地位是低于农民的,所以才被喊“鱼花子”,夏国花补充道。“搞鱼的人都可怜。”她靠坐在床沿边,时不时冒出来这么一句。
夏国花今年已经77岁了,她曾是渔船的孩子,也是渔船的女人。在船上出生,又在船上长大,接着在船上结婚生子,产后月子时,就接着收网干活。一辈子渔民命,一辈子酸甜苦辣都在船上尝过。我尝试去想象她眼里的渔上生活:她面前的世界或许和我面前的不一样,有自己的时间刻度,质地,感官,学会着看天空的颜色,听湖面下水纹呼吸的气息,能欣赏到广阔湖面之上每日上演的日出日熄。我无法描摹全貌,看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微暗明光缓缓盈满整间方型黑屋,看着床边的斑驳木桌上稳稳立着一座还未开封的金黄色毛泽东雕像,我有些出神。老人讲话的声音忽远忽近,一沉,一浮,这屋子就像一条船,我成为了在渔船上的孩童,在过往记忆里漫游,漂荡......
思绪拉回,我们的采访进展并不顺利。刘安顺说起当年打鱼的旧事时,时不时苦恼地指指自己的耳朵,抱歉朝我们笑笑:“老了,听不到了,记不住了。”遗忘成为他们追溯过去的一大难题。
可是,“孩子呢?”
渔民不像农户,渔民和水的关系就如同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船即为家,日出捕捞,日暮宿船,既当船工又当纤夫,顺风的时候扬帆,便小心有碰撞;逆风的时候撑篙,遇到航道狭窄,急流险滩时便靠撑篙划桨,到处漂泊,居无定所,与陆上世俗变迁相隔绝。渔民的孩子更与科举升官无关,能识字的几乎没有——打鱼只需学会祖辈留下的技巧,和看天的本领。以前孩子跟着大人一起打鱼,常在腰间系一根粗绳绑在船上,怕嬉闹玩耍跌进水里,就这样一户一船,在木板搭建的几平空间里共生。19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推上进程,刘安顺一家上了岸,在周边的水产养殖场养鱼,家里的小孩才入了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出现了一场空前的衰退,大量小农破产,农村经济陷入困境,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乡村危机”。与此同时,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开始放慢,增幅开始回落,亏损面日渐扩大,一些企业破产,一些企业改制,引起大量职工下岗。刘安顺和夏国花所在的水产养殖场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上岸的日子很清苦,但老人并没有教孩子如何打鱼,也不希望孩子重返打鱼生活。渔民的孩子不再成为渔民,早在这一辈人还正年轻的时候便已成为现实。孩子们外出读书、打工,不再以湖为生,从事与渔船和打鱼无关的职业,在更南的城市定居、成家,远离湖泊,过年的时候再回家与老人团聚,他们迈向属于年轻人的新世界,扎进建设都市化的进程之中。
这样的人生轨迹在蛤蟆石渔村并不少见,一代又一代的打鱼事业随着政策下的上岸浪潮被打翻在地,成为还留守在湖边的渔民印象里的记忆残存。
不过,渔民仍是想打鱼的。床边一张半扯开的,悬挂着的崭新丝网提醒了我们,那是一种对自身身份的潜在眷恋。在还没有鱼钩的1960年代里,刘安顺一家用竹卡子和丝制的渔网打鱼,这种渔网有粗细之分,粗的网格有五指之宽,能打到4斤多的大鱼。
在他们的观念里,“十年”禁渔的十年不是官方文件里敲定的执行数字,而是缥缈不定的时间概念。隐藏着的,是他们都在默默等待和期许这一天的结束,也许在明天,也许在明年。
他们处在一种被告知的状态,悬而不定,依旧如同一个个在水上漂浮着的渔船。政策在他们的原生环境下没有历史感和时代感,只要被下达什么样的通知,便如何照做。刘安顺和夏国花就用自己作为渔民最传统的方式——织网,来一步步计算和勾勒出对禁渔期限的理解。
我用目光比了比长度,五指?或许没这么宽,我想。我对他们从琐碎的记忆里挖掘出来的讯息不抱希望。
夏国花说,床头的网已经编了一年多了,还会继续编下去,等到禁渔政策十年之期解除后,她就拿着新网继续去捕鱼吃。
还有七年时间。七年里又会发生什么呢?
他们纯粹又茫然地等待着未知的将来,为生存而拖磨,把自己编织在不大的丝质网格中,如画地为牢。
挖砂之下
现在想来,其实袁姐是有工作的,村里很多人都有工作。
挖砂公司的人每天在船上工作,上下班、买菜、买水果、买生活用品,全都要坐船回到陆上前往镇里的街上采购,而从船上到陆上再到目的地的这两段路程的往来,要靠码头渡运公司的快艇和村民开车接送实现。

码头边停靠着渡运公司的快艇,远处可见正在作业的大型采砂船
而从事这些生意的人,都是之前村里的渔民,禁渔后他们辗转,留在水上的成为唯一会开船的人,留在岸上的花钱买辆私家车,改称陆上司机。他们如同湖中的鱼一般游动,为的是寻找栖息之地。
杨平就是其中之一。和他聊天,总不提当下,一开口就是以“当年”的句式开头,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感到亲切,但他却不记得上任国家领导人是谁,不记得禁渔政策究竟从何日开始。
他仍和生活在水上的前渔民一样,活在过去的历史里。
1990年代以前,杨平一家一年四季不停歇地打鱼。那时候湖里鱼多,渔民几乎不愁打不到鱼,晚上把渔网撒在湖里,凌晨三四点起床,然后打鱼收网直到天亮,再把鱼交给湖边等候的鱼贩子。1998年,为了方便小孩上学,杨平从船上搬到了岸上,住在离渔村不远的地方,他拿之前打鱼卖的钱买了台车,在渡口开车拉客。
说起禁渔前开车的日子,那是一片丰饶的水域,水是清的,能见着里边的鱼,渡口的码头停满了船只,“有一两千只船”,挖砂的,打鱼的,游玩的,运货的,码头特别热闹。人多,拉客的生意就好,有时等车的人还会排起长队。禁渔后,船只与人流不再,生意变得惨淡。故事的转折到这里时,便换了一个更为平淡的版本,也许一两千只船有夸张的成分,但仍能从杨平的话里,窥见到那时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比起上世纪90年代湖水的清澈,码头的繁盛,鄱阳湖如今的湖面已黄浊不堪,平整的水面时不时飘来几阵风,掺杂着带有鱼腥味的湿润气息,和新鲜的柴油星子。其实这水已是实施长江大保护后的模样了,采砂活动增多,水位下降,鱼种类减少,近年来频发的干旱,这些不光杨平看在眼里,一直在湖上开船的刘元民更是清楚。
刘元民快满60岁了,身手依旧敏捷,手劲儿仍有年轻时的力气,他笑着说这是打鱼的时候练出来的。禁渔后,他成为蛤蟆石水上渡运公司的船员,公司的船员都是渔民出生,水性好,又熟悉当地水情,曾经救起过俩乘客的命,现在码头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当年人家送来的锦旗。

船员宿舍门口的墙上贴着乘船安全须知和公司简介
因为会开船,刘元民也去给货船当过司机。从这里出发,钢筋水泥等工业材料被运往南京、上海等地,一个月钱不多,十几块钱,开船的房间里又热,“开空调都要花几十块钱”,他摇摇头说辛苦。
刘元民开着快艇,载我们前往昔日打鱼的水域。第一次坐上由渔船改装的小艇,才发觉湖上的视野与岸上截然不同,采砂船连成一片,密密麻麻地接着,景观变工地。在大船的映衬下,小艇就像城市庞然建筑物下的小车,一抬头,高不见顶的船体,我视线受阻,感到一阵呼吸不畅的压迫感袭来。
2002年起,《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自此长江干流的采砂活动受到很大约束和管理。而从1996年开始,江苏、安徽、湖北等长江沿岸各省陆续出台了禁止长江干流内的一切采砂活动的规定,大量采砂船进驻两个通江大湖——鄱阳湖和洞庭湖。2016年,江西先后颁布《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及《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中下游干流河道和鄱阳湖采砂规划(2019—2023年)》——「五河一湖」采砂规划出台以来,湖面的采砂乱象也得到了治理。
蛤蟆石渔村所在的鞋山湖区地处江湖交界处,转运便利,采砂船格外多。渔村一般是下游省份的老板前来做中间商生意,一头是政府,一头是公司,向政府缴钱并获得行政许可后,才能进行采砂活动。采砂时间看季节和政府的态度,丰水季节,采砂大船便能入湖;退水季节,只能允许小船进出。
船在湖上漂了半小时,偶尔惊见悬停在半空的白鹭俯冲而下,叼起浅水下的鱼虾飞起,羽翅搏腾掀起一阵小水浪。采砂船上,一头是挖掘机,一旁是被摞成一座座小山的砂石,正在作业。好不协调的场景。
靠近一块裸露的河床时,我忽见一条翻着肚皮漂浮的死鱼,我指给刘元民看,他也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他猜想是禁渔后没人捕鱼,而政府还在给湖里投放鱼苗,鱼多,鱼食就不够了,才会出现死鱼。同时,他也猜想可能是干旱搁浅的原因。
毕竟,“之前是没有死鱼的。”他说。
2022年,中国长江流域遇上了自1961年以来的最大干旱,伏秋连旱。进入9月后,副热带高压依旧异常强大,江西、湖南等地持续缺乏有效降雨,而10月以来南方旱情仍在持续。据统计,去年夏天,鄱阳湖流域降水量只有同期的 46%,鄱阳湖面积「缩水」八成左右,部分河段甚至干涸,水位一度跌破7.1米,为70余年来最低。
今年,就在不久前的7月20日,据鄱阳湖标志性的水文站星子站监测,鄱阳湖水位再次退至12米以下,预计下半年的情况仍不乐观。
旱情依旧延续,鄱阳湖低枯水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
鄱阳湖之上,采砂之下,人和生态都在悄然发生变化着。渔民为生计辗转,以往会打鱼的技术被政策所掩盖,却学会了用自己的生存之道来延续曾经的经验智慧。渔村仿佛被固定在当下进行时,不考虑过去,也不问将来,脱离渔民身份的他们,如今在庞大的采砂产业下被滋哺,求得一线生机。
离蛤蟆石渔村八公里开外有一座寺庙,叫姑山寺,附近过往的船只偶尔会去祈求平安。刘元民送我们到岸边,里面一位光头和尚接待了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才知道他是安徽过来的,在鄱阳湖边住了几年了,平日里只待在寺庙,也不怎么跟本地人交流,照和尚的话说,来到这里全凭缘分。
我们好奇他是否了解村里渔民的情况,他乐呵呵的,带着佛性的笑容说道:“禁渔后政府都给他们找了工作呢,现在都安稳下来了……”
天快黑了,我们悻悻地离去,仿佛明知寻找不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但还是被渔村正在落寞与被遗忘的事实所击倒了。
*文中照片均由作者拍摄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今年夏天,我去到了江西鄱阳湖湖区周边的村庄和乡镇进行田野调查,我们小组是以生态人类学为主题,其间在九江市濂溪区旁的蛤蟆石渔村里待了两天时间,和村民们的相处时间里我了解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禁渔政策实施后,这个渔村逐渐被世界所遗忘,他们不再从事打鱼,有的去到了城市打工,有的留下作为政府庞大的挖砂产业下的一员,有的闲散在家,他们又只会打鱼,在这一政策的笼罩下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过迷茫与等待,遭遇过生存之迷。整个过程中我作为访谈者,参与者和旁观者,感知着渔村的空间与环境,感受着这些前渔民从前、现在和未来的走向,我想写他们,想写这个渔村,想把他们所在地区的变化与境遇呈现出来,趁他们还没被历史所完全淹没,做一件作为一名正在学习的人类学者该做的事情吧。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原标题:《鄱阳湖边,一个正在消逝的渔村|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