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潘绥铭:因为是我,所以才构建出如此这般的性社会学

学人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性社会学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等。
访谈人:罗宇翔,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下文简称“学人”。(黄盈盈老师协调了访谈进展,潘绥铭老师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特此致谢)
几个月前,我们有幸和潘绥铭老师聊了时隔十余年再版的《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在访谈中潘老师曾提到,他的学术自传《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下文简称《风痕》)即将问世,这也为我们的再次采访埋下一个伏笔。

《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
作者:潘绥铭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3-9
一、我做了学问,学问也做了我
学人:《风痕》是您的学术自传,在上次访谈中您提到,本书是想要留下史料,说明“有人曾经做过这些研究”。写作《风痕》的想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整个写作过程有多久?
潘绥铭:我是2014年初退休的,当时没想过要写自传。2018年我做直肠癌手术加上意外,总共住院一个月,做好了随时离去的准备,所以就想留下一点什么。2019年底基本写完之后,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一直到2023年9月才得以面世。其中的一些内容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作为史料我也仍然保留下来了。
学人:在结构安排上,《风痕》采用了时间(纵向)与事件(横向)两条线并行讲述,并未按照年份平铺记录,这种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潘绥铭:这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写着写着,发现很多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都是相互交叉的,先后都做过,有的甚至相隔数年。所以编年史(平铺记录)就没法搞了,只能是以内容为线索,把前前后后做过的事情串起来。
学人:书中处处彰显出书名所说的“互构”一词,您的个人经历与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您的人生史也是一部学科史。
潘绥铭:互构的“互”字就是说,世间万物都不可能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与运行的,都必然跟另外的某些事物发生某些互动。我和性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也是如此。
互构的“构”字来源于建构主义的思路,就是说,大千世界不是天生如此,更不可能一成不变,都是一砖一瓦、绵绵不绝地盖出来的。本书的“互构”就是说,因为是我,所以才构建出如此这般的性社会学;同样地,在构建这样的性社会学的过程中,我也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通俗地说就是:我做了学问,学问也做了我。
学人:您提到,自己的研究越往后越从性社会学向性研究靠拢,性社会学和性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潘绥铭:“性社会学”这个称呼,更加强调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性的现象,因此也就显得更加经典一些、学究气一些。
“性研究”(sexuality study)这个词主要是指西方1960-70年代开始,80年代以来新发展出来的、受历史和社会建构主义影响的、延伸到更加广泛范围的、运用多学科方法的、更加多元化与多样化的、对于性现象的研究。在英语世界中,普通人往往认为“性研究”更多地与“性少数”(LGBTQ)联系在一起。

学人:有的同学说,就性社会学的发展史而言,《风痕》还不够全面。您觉得呢?
潘绥铭:性社会学当然一直包括西方学术界在“性研究”方面的历史发展,但是《风痕》并不是标准的教科书,所以这方面的内容都没有写进去。
此外,1980年以来中国的性社会学,并不是我一个在研究,广为人知的还有刘达临教授(1932-2022)和李银河教授;至少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的研究者,林林总总有几十位;还有更多的研究者是偏重医学、计划生育、预防艾滋病或者文艺评论。
只是由于《风痕》是一本学术自传,所以其他人的研究和成果才没有纳入本书。有需要的读者可以参见《中国性与生殖健康 30 年:1978~2008》第六章《权利与快乐的兴起 :性与社会性别多元化》(张开宁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学人:在我看来,《风痕》更多地是对于历史、文化、社会、思潮的总结和思考,对于普通人而言,可以应用的内容并不多。但是您又在注释里列出了大量的通俗文章的标题,是不是可以说,您有意舍弃了这些通俗内容?
潘绥铭:是的,书的篇幅有限,我也想侧重谈自己思考的成果,所以舍弃了通俗内容。但是这绝不是说理论思考就一定高大上,通俗文章就一定俗不可耐。
其实,自古以来,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究心一直就是直接指向性的行为、感受、体验和反馈。在西方,最早的性研究就是针对“性心理”(那时候“行为学”还没有独立出来)而不是性社会学。全世界各种语言中,性研究一开始都被称为“性行为(动作)学”。在中国,阴阳和合主要是一种思想和文化,而“房中术”才是真正的“性行为学”,距今大约两千年了。
尤其是,一百多年来,国际上的“性行为学”早就超出“A片”的水平,已经发展到中国一般民众很少知道的很高阶段。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性学家”们,研究了“性的内分泌学”(例如化学阉割)、“性的脑电波学”(例如“性高潮的脑电波辅助器”)、“性的偏爱学”(例如行为学而不是药理学的“性治疗”);再加上方兴未艾的“虚拟的性”、“感应的性”等理论与实践,“性学”早已成为一个高深的学科。可惜在时下的中国,一些人(男人居多)一说到“性”就是“十八般武艺”或者“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使得性玩具的制造商除了造假器官也再无想象力。
因此,现在的通俗和科普的文章还是太少,例如我在上世纪80-90年代写的一些性心理方面的通俗文章,仍然不断地被一些杂志重新发布而且发来稿费(在此致敬)。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方面:最通俗易懂的科普资料就是“A片”,虽然它确实很有问题,例如强奸误导、性技巧迷信、人文缺失等等,但是恰恰因此才更加应该广泛深入地进行全民大讨论,形成一个最大共识的底线(例如私人私下即可)。目前这种“一禁了之”的立法,实在是掩耳盗铃,害得我在《风痕》里也知难而退,说了也白说。
因此我愿意补充三个与苍老师(苍井空)有关的小故事。

苍井空
第一个故事:十几年前,我的一位男同事告诉我,他那个上初二的儿子在偷偷看苍老师的视频,藏在硬盘里,被他发现了,问我怎么办。我笑了,说:咱们朋友多年,你还问我怎么办?跟他一起看啊!这才能在交流中传达你想说的意思啊。结果几个星期以后同事告诉我:现在儿子都跟他拍肩膀、称兄道弟啦。
第二个故事:2012年9月我62岁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回家,听到车上有三个身穿人大附中校服的男孩子(目测初二)在相互议论。其中一位说:“你说苍老师为什么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另一位答道:“她在中国挣的钱太多啦。”这时我就忍不住插了一句:“她挣不到多少钱的,咱们都是网上(免费)下载啊。”沉静片刻,一位男孩子感慨到:“同道中人啊。”这还没完,他们三个与我一起下车后,一起毕恭毕敬地向我鞠躬,说“谢谢叔叔”,我也开玩笑地答道:“应该叫爷爷!”
第三个故事是2017年5月,凤凰卫视邀请我去谈女性乳房保健,因为女编导听过我的课,想把女性乳房的进化这个必备知识传播开。她事先问我,她还请来苍井空,问我是否介意,因为先后两位女性医学专家都拒绝了,只好请一位男医生来出镜。我关心的是:她懂吗?这才知道,苍井空早就是乳房保健的国际代言人了。
当天在拍摄现场,我送给她一首事先写好的诗,就是“苍井空君”这4个字的藏头诗。可是一开始他的经纪人拒绝我与她合影(大概是商业考虑),还是她一把把我拉过来合影,还破例与我专门带去的女研究生也合影。作为教授,我敬她是公益大使;作为观众,我敬她专业上炉火纯青;作为沧桑人,我则敬她不卑不亢坦然面世。总之,我们平等相处,相聚甚欢。
二、每一代年轻人都亦步亦趋地重新走过
学人:本书开篇您就说到,这是一本学术自传,因为“我的个人生活索然无味”,但是读来却让人觉得您的生活经历不仅仅是丰富,简直就是充满传奇色彩。在您看来,学术与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
潘绥铭:我的一生平淡无奇,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一)经历
16岁到26岁处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被关押两年,母亲被逼成精神分裂症,全家骨肉分别下乡,一人一地,我也曾流落街头;然后下乡5年,进厂当工人5年。但是这并不独特,至少有数百万同胞比我惨得多,我们都是幸存者而已。
“文革”不堪回首,总的来说就是日子过得苦哈哈、惨淡淡,前途黑漆漆。最痛苦的就是刚刚初中毕业就断了上学的路。后来跟国际学者交流越多,就越发痛感,“文革”这10年我如果持续上学,到“文革”结束刚好应该是博士毕业,那么与国际水平也就不会拉下这么大的空挡。可是我是31岁才跳过高中和大学,直接去读硕士,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先天不足。
改革开放给了我新生,这是真真切切的心里话和至死不渝的“三观”。在那火红的八十年代,在我们那一代三十而立的时候,我们有幸进入了世界,复原为人类。最近我在整理我父亲(1931年的共产党员)在1927-1931年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录。他那时考进了美国教会在山西办的洋学堂。他说:“新奇充满了我的生活,我就贪婪地吸允着所遇到的一切。”这让我倍感亲切,跟我在八十年代一样。我们都是一代代历史的儿女,个人可以不服输却很难不认命。

我后来一旦走上学术之路,日常生活就变得味同嚼蜡。除了社会调查期间,我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尤其是,体制内的仕途和荣誉我一无所有,社会上的风浪和机会我敬而远之,物质生活则是得过且过,婚姻家庭则是凡夫俗子;再加上天生木讷,就连搓麻、喝酒、拉关系、攒人缘都不会,哪有什么戏剧性内容可写呢?
说到底,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书呆子,所以除了写文章写书,别的就没啦。
(二)青春期
我属于19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我们在“性发育”与“性成熟”方面很特殊,因为我们是“新中国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第一代,又从青春期的1966年开始经历了十年“文革”。
从宏观视角来看,2000年我进行第一次全国“性调查”的时候,特意把被调查者的年龄上限规定为64岁,因为64岁的人出生于1936年,到1950年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们已经14岁了,开始进入青春期了。因此他们可以反映出整个1950到1960年代的情况。这次调查的结果很惊人:与那些解放初期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相比,在“文革”期间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不仅第一次过性生活的年龄被推迟了,甚至推迟了男青年的首次自慰和遗精的年龄。尤其是自慰和遗精,从来被认为是纯粹的生理本能,“精满自溢,势不可挡”,结果居然被强大的革命文化的力量生生地给推迟了。看到这个统计结果之后,与我合作的那几位美国教授沉吟良久,私下里相互讨论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说:据他们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然后仔仔细细地观察我的反应。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生怕伤了我的文化自尊心。时至今日,我再来讲这个历史奇观,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根本无法相信了。

从中观的层次(阶层与群体)来看,“文革”前和“文革”中,我是北京五中的初中生,只能说一些大城市里的情况。我们学校是一个男校(此外也有专门的女校),就是清一色的秃小子,连女老师都没几个。这种男女分校制度,是西方传来的修道院/修女院制度加上儒家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狼狈为奸。它为了“培养革命新人”而从一开始,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的“性交往”。这在当今中国,年轻人恐怕也难以相信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我这样的男孩子,只见过某些在家长严密监视之下的邻家女孩,完全是雾里看花、莫名其妙,真的谈不到什么看法和态度,甚至连做“性梦”都没有女同学能梦到。1965年的国庆节,上面要求我们跟北京女二中的女生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可把大家吓坏了,最终也没搞成。当然,电影或文艺作品中的有关描绘,那很可能是因为编剧与导演当时生活在不同的群体中,做出了多彩的想象。
就我个人而言,性梦、性幻想、单相思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但是刨根问底的话,在那个年龄上,谁又说得清楚自己恋没恋呢?更别提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那简直就是无解之谜。每一个成年人都会记得自己不堪回首的青春期,每一代年轻人又都亦步亦趋地重新走过;这就是《风痕》中讲的“生物因素不可取消”原则,也因此才能成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
当然,自从1968年“知青”下乡之后,我们那一代就开始另外的故事了。这方面的文艺作品璀璨夺目,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大同小异;只不过我去的是一个半军事化的国营农场,男女知青是完全隔绝的,而且没人真的打算在那里“扎根”,所以我还是没恋成。直到“文革”结束前,我去上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中专,才与同班女同学相识相恋相婚直到现在。
学人:书中提到,“无论男人、女人还是性少数,所谓的‘性行为’,同样都是从勃起到摩擦到高潮到消退的一个过程”“性快乐是不问来源的,根本不在乎对方是什么性别”。如果说性快乐是不问来源的,是否可以理解为性行为是无需受伦理道德所限?它与人类的吃饭、喝水、睡眠等生理活动有何不同?如今在不同社会中,人们似乎仍然愿意给“性”附加很多特别的意义,这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吗?
潘绥铭:当然是这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一直被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塑造为“全性”。那些林林总总的限制、制约和形塑的社会因素与条件,就被人们认为是“性道德”。
在西方,犹太-基督-伊斯兰的宗教体系就是最强大的性道德,也是西方性革命的打击对象。在中国,由于我们没有西方那样成型的宗教,所以汉族的性道德主要是儒家主张的那些人伦原则;对个体生活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因此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来源于冲击意识形态,也不会作用于宏观的社会局势。
你提到的“性行为无需受伦理道德所限”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它说的仅仅是个人权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不可以损害个人的性权利。可是只要“性”还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那么双方各自的权利就可能产生差异甚至是冲突,那么就还是需要某些“性道德”来加以调节与控制,只不过已经不再是社会管控的道德,而是私人之间的平等互动的“人权道德”。
正因如此,所以我在《风痕》中的《互联网给性带来了什么》这一节里,专门论述了:网上的种种性活动,由于都是“隐身”的,所以可能极大地减少双方之间的性权利的冲突。这样的话,将来就连“性的人权道德”也可能会被极大地削弱,“全性”就有可能实现最充分的自由。这才是最后的性革命。可惜,到目前为止的评论与采访中,大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学人:今天的中国性观念更开放了,认识异性的机会也增加了(比如各种交友软件层出不穷),为什么结婚率反而更低了,甚至连找对象都更难了?
潘绥铭:我现在已经不做研究了,所以无法判断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只说一个小窍门:任何一个数字,如果不是调查的结果,就不看;如果不说怎么调查出来的,也不看。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结婚率”,也不包括那些婚前的、婚外的、同性的同居在一起的人们,哪怕已经一辈子了。所以所谓“结婚率越来越低”,很可能仅仅是同居不婚的人们越来越多而已,而且,同居与结婚,仅仅是社会制度强行规定的差异,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真的有那么大的差距吗?

另外一方面,除非是专业的研究者,如果普通人在议论某种“性现象”,往往并不在乎是否真的如此,往往只是在抒发自己的情绪或者价值观。例如“结婚率低”,很可能说的其实是“找对象更难了”,想婚的人可能痛心疾首,不婚的人欢欣鼓舞,离婚的人则喜忧参半。
可是,找对象越来越难,难道不是必然无疑的吗?独生子女个性越来越强,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再加上一味鼓吹白头偕老,谁不胆战心惊?尤其是,不婚而有性更是方兴未艾,结果就连最基本的生理动力(性趣)都日减,所以现在还敢找对象,真的是英雄虎胆。
三、一个终极追问:人真的能够如实呈现自己吗?
学人:大概在2007年时您曾说过,“如果我70岁的时候写回忆录,你不要相信”,因为“作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解释自己的一生”,您自己也必然如此。现在再来看《风痕》这本书,里面似乎更多地讲述自己的“教训”,而不是所谓“成功的经验”。那么此时,您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自传?
潘绥铭: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呈现真实的自我”这件事,不是谁想不想、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做得到的问题,至少也是只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的问题。尤其是所谓的“内心生活”,难道心电图或者核磁共振就能够“如实记录”下来吗?
我才疏学浅,无法从哲学或者认识论的高度来谈这个情况,只能从“生活实践社会学”的水平上通俗地说:真相是靠语言来构成,来表达的。可是人生的绝大部分内容,自己既想不清楚,也说不出来,所以即使真的有个真实的自我,自己也很难使别人了解和明白。结果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你自己内心的绚丽多彩或者惊涛骇浪,其实不可呈现,至少不可能完整完全完美地呈现。
这就是《风痕》里着力推荐的“主体建构”的理论解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除了骗子,无论谁写什么回忆录,基本上都希望真实地反映自己。但是这是那种自然科学般的、可以加以客观验证的、经得起灵魂拷打的“事实真相”吗?天啊,怎么可能?任何回忆,一定是当事人自己现在对于当时自己的活动所做出的解释和描绘。这就必然会有掩饰、修正、回避与曲解。如果没有,那反而不真实了。即使是24小时监控录像,也需要当事人后来加以解释才能明白那个活动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主体建构”,只要是个人就逃不掉的。
但是,人类总是需要较真的,否则无法进步;所以有相当多的人会不由自主、耿耿于怀地追究“真实不真实”这个天问。好像不真实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一棍子打死。其实,“真实”这个事情不应该穷追到“终极”,因为那很容易陷入玄学和不可知论,那人类就只能疯掉了。真实必然是主体建构的真实,是当事人主诉的真实,是“不撒谎即真实”。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人类才可能进行最起码的相互沟通与协作。说句得罪人的话:阅历不够,“求真”来凑。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所谓的真实,其实存在于读者的心中。任你作者写得天花乱坠,如果读者不以为然,那么就会说作者“不真实”。可是人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理解和判断任何文字记载的,其实跟那个作者写得真实不真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按理说,一切文艺作品都是虚构的吧?可是只要它能够引起足够多的共鸣,那么它讲的故事也在这个世界上就真实存在了,谁管他是不是真的有过一个贾宝玉呢?
《风痕》当然是,而且很自豪地是主体建构的产物,区别只在于,作者(尤其是社会学家)是不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坦诚相告。这就是有没有主体建构论视角的学术差别。
但是,这等于说我们就不需要多维了解、多方求证了吗?
历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当事人写的回忆录,不是必然可以成为“史料”,还需要多加认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里,更是严格区分三种情况:自我陈述、调查结果、文本分析。这三者意义不同,无法相互替代。
在自我陈述里又需要分成两种写法。一种是呈现式,就是信马由缰,自说自话即可;另外一种则是论证式,就是回忆者需要拿出某些证据或者资料来证明自己的经历。例如某些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就大量引用官方文献,以便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做的,而不是“下楼梯时的反悔”:完事之后才想起应该这样而不是那样,然后自己也信以为真,就写进了回忆录。
《风痕》努力做到论证式的回忆,因此才不厌其烦地列举出林林总总的文章、书籍、培训与会议的情况。这并不是说它们多么有价值,而是希望证明我那时候真的这样想过,这样做过。当然,这样做也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实”,因为《风痕》中有一个终极追问:人真的能够如实呈现自己吗?

潘绥铭出版的部分著作
学人:从书中可以看到,您在性研究的探索过程中也伴随着对方法论的提炼与反思,比如“全性”、主体建构论、“性化”这些关键概念的诞生都离不开置身田野中的体验与感悟。理论与田野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
潘绥铭:研究方法的背后是世界观。如果只关心性的社会设置(制度)和“治理”性文化,那么不需要什么方法论,屁股决定脑袋就完了。可是我立志研究生活实践,那么如果不运用这些田野的研究方法,就连人们对于“性”的主体建构都搞不清楚,那写写感言就足够了。尤其是,我做过四次全国的性调查之后,曾经想出一个“论方法”的广告词:“如果连性都能调查出来,还有什么不能?”这从“互构”的视角来看,就是各种调查催生了我的“论方法”,而“论方法”也推动了我的各种调查。
对于理论与田野的关系,最乖巧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吹“两相结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这两者的基本逻辑就是不一样的,理论只要自圆其说(逻辑自洽)就可以,田野则必须亲临现场,证据充分,光推理是不行的。因此我主张,各干各的,最后看谁对于什么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学人:在书中您曾提到,鼓励学生“研究始于兴趣”,而自己却是“入手在于可能”,这二者的差异很有意思,呈现出一种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境的张力。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怎样开始一个自己的研究?
潘绥铭:你眼真尖,连这都看出来了。这其实只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在你刚开始的时候(例如1981年的我),两眼一抹黑,就连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都无法分辨,只能是一咬牙一跺脚直冲上去,干了再说。然后入门了,心中有数了,当然就会“找木板最薄处去钻”。所以,初学者就应该横冲直撞,只不过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而已。
学人: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书中多处提及的一个线索,比如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在您看来,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是否存在一定的限度?
潘绥铭:这没什么可讨论的,就是三个字:我胆小。
学人:在长达几十年对性的研究中,您感觉到最大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
潘绥铭:不断地有人问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哪些阻力,言外之意就是社会给我的阻力,而不是我自己才疏学浅的阻力。这就让我很为难了,只好如实诉说:真的没什么外来阻力,至少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戏剧化。
现行体制来源于长期的秘密斗争,保密就是保命;所以在执政以后,内外有别、层级分明、秘而不宣就成为管理现代社会时的惯例与规矩,而且一直高效。这样一来,别说性社会学,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有什么来自体制的阻力,那么很少是明令禁止,绝大多数都是内部保密、悄悄处理的,不仅被管理的当事人极大可能闻所未闻,就连基层的执行人员也非常可能不明就里。尤其是,由于过度保密,含含糊糊的甚至南辕北辙的事情也就并不罕见了。所以,即使真有什么阻力,我也真的不知道。
另一方面,如果我不认为它是阻力,那么它还存在吗?
我的第一本书《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在1985年出版了。1986年冬天我去深圳,那时候还要办理《边防通行证》。在过“边防检查”的时候,一位中年警察专门拉我走一个单独的通道,然后问我:“你又出什么新书啦?”我当时一惊,因为办理《边防证》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到我出书的事情。后来我才听别人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警察的个人行为,也有可能是故意提醒我,还有可能是催你干点什么。可是傻乎乎的我,当时完完全全不认为我研究和写书有任何问题,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那么,这能算是阻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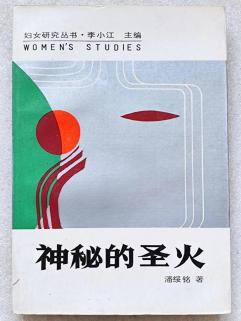
潘绥铭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是一个天网体制,可是“性”恰恰是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机构、机制来管的,主要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犯罪、婚姻、生育、传播等等,才会有人来管。反观1960年代开始的美国“性革命”,青年左翼与宗教势力一直闹到街头对垒、誓不两立,然后直到今天,政治正确与保守主义依然形同内战。这就是因为犹太-基督-伊斯兰的教会体系就是专业“管性”的,所以有敌人才有斗争。
在性方面,汉文化一直实在是太世俗了,太私人化了。这既是1980年代中国发生性革命和21世纪之初进入“性化”时代的充分条件,也是一种先天不足,就是很难得到体制的资源,哪怕是负面的也没有。
四、我与性社会学一辈子都仅是两者互构,形单影只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了“前知青教授”(或者“知青社会学家”),他们大多有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在您看来,年轻一代社会学家与这一代社会学家有哪些不同点?这种差异对于未来的研究格局会带来哪些影响?
潘绥铭: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评论这两代社会学家,只能说说自己。我别说没有理论功底,就连理论的皮毛也残缺不全。一是由于我是“文革”后直接从初中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没机会好好学习理论;二是我的英文太差,口语近无,因此国际学术交流的水准很低;第三嚒,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料,哲学对我就是天书。
有些年轻学者认为,像我这样的“知青学者”其实就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一代幸运儿,恰好赶上“文革”后学术界的青黄不接,才得以出头;因此我们没有后劲儿,退休就完事。我深以为然,但是也不服气:“知青一代”有上亿人,进入人文社科研究的不过千百人,总还应该有些诀窍吧?
我下乡期间的一位复员兵领导,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过:“善于总结才能进步。”这在那时候绝对是真理,因为在“文革”中流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就是自己总(bian)结(zao)出一个高大上的故事,对别人宣(hu)传(you),自己得(ru)利(dang)。这种事我实在玩儿不转,但是如果说“总结”就是“深思、反思、奇思”的意思,那么我可就受益匪浅了,说白了就是“爱琢磨”,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很招人讨厌)。所以《风痕》里的绝大多数见解和思考,都不是翻译过来的,而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然后反思出来的。
这方面,我大概有一点“童子功”。早在1965年前后,中学生已经开始大搞“忆苦思甜教育”了。有一次我们全班去看一个控诉旧社会的电影(具体内容忘了),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可是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学习拉二胡,听出来电影的配乐是《江河水》,这是一首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的二胡独奏曲,我自己一个人拉着拉着都可能哭出来。于是我就想了,我和同学们究竟是因为看到旧社会的苦难才哭了,还是被二胡独奏给催哭了?我当然没敢跟任何人说过,但是“逆种”大概就此植下。
当然,所谓“实践出真知”只是人类认知的途径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总是最佳的,仅仅是因为汉民族从来就缺乏抽象思辨的能力与传承,从来就是世俗的文化,一直讨厌形而上学,所以才会觉得“土生土长”的格外亲。在《风痕》里我写了大量的反思“西化理论”的内容,但是这也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天问”:这究竟是不是我自己坐井观天或者吃不到葡萄就说酸?
学人:虽然您写道自己对“本土化”这个话题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您在后面的章节似乎又给出了一些看法,比如您说要梳理清楚学问内部的差异性,再进一步探讨这些差异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对“本土化”的一些态度?
潘绥铭: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学术界吵的天翻地覆。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是:
首先是“生命周期”,人越老就越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很难有人逃脱。所以,我自己可能真的变成儒家了,开始相信“叶落归根”了。
其次,我一直是研究社会实践活动的,越来越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宏大理论或者思潮,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性”,远远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人们其实是按照习以为常的、模糊不定的、随时善变的一些生活经验来为人处世的。这就是“本土文化资源”,最典型的就是汉族男人信奉“劳色伤身”和“修身养性”的千年传统。这与西方某些人说“男人是性的永动机”,根本就是天差地别。如果总是对着汉族人讨论美国的问题,那也太没出息了。
第三,本土化绝不是排外,而是应该呈现出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与解释我们自己的性文化。其实,自从“五四”以来,所谓的“本土”就一直在“西化”,所谓的“复归传统”根本不是该不该,而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我仅仅是希望,汉族的性文化应该像非洲土著的舞蹈那样,终有一日成为传遍全球的迪斯科。

学生送给潘绥铭的画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从事性研究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都因为这一背景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产生过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能否请您再详细说说?
潘绥铭:总的来说,我的学生们在考我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的时候,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位是从高中看了我调查小姐的书以后就决心已定。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别人商量过,更没有向亲友解释过。我把他们叫做铁头男、钢心女,对此深深感激,无以名状。
可是反过来说,他们也不是娇嫩之人。他们考研时已经是成年人,绝不会风声鹤唳,不会去听那些噪音与杂音;去调查小姐的时候几乎全都爱过,自己的情感原则早已确立,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当然,也曾经有两位女生要求退出小姐调查,但是这与她们的个人情感或者观念无关,而是受不了爱莫能助的煎熬,是出于一种道义的责任心。
一位去企业的学生说:“比如会在日常聊天或者饭局上被拿来当作调侃的由头。如果是不重要的人或者局,我一般就是笑笑不理,也不会有其他影响。对于需要解释的场合,我通常经过进一步说明,对方会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另外一位去机关的学生说:“一些和我有竞争关系的人,在一些公共场合介绍我的时候,总忘不了提一句:‘他是研究性学的’。有时候,还不忘强调一下,‘他的老师是中国性学第一人’。当然,几乎所有时候,都伴有猥亵的笑,然后,引起星星点点的‘噢,噢’的回应。每每这个时候,我都有吃了苍蝇的感觉。当然,也有红利或者福利,因为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女网友居多),往往因为听说一个人是研究性的,就想当然认为这人肯定是一个高手……”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的人际交往最大特点就是“只敢背后议,绝无当面驳”。在社会调查里就是“不敢拒绝,却善于撒谎”。所以研究“性”,其实没什么人真敢当面贬低,我只遇到过一回,而且是一位比我大12岁的老太太教授,有点像大姨妈在训斥,我当然只能俯首帖耳。
学人:书中有一处讲到,在1996年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您一项比较满意的研究被一位学者的一句话问住了,您说“这当头一棒使我受益终身”,学术批评中双方的坦荡跃然纸上。但在如今的学术界,似乎依旧强调“长幼尊卑”有序,如果要破除掉这种所谓的“学术面子”文化,我们或许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潘绥铭:从根子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目前的“学术面子”则是直接来源于学术研究正在复古,日益蜕变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学术批评就变成了“断人财路”。如果真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真的是自得其乐、乐此不疲,那么批评是求之不得啊。
我与性社会学一辈子都仅仅是两者互构,形单影只,在国内基本上没有遇到真的学术批评(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同行太少)。只有在预防艾滋病的领域中,有一位早已去世的老先生,主张洁身自好、反对推广安全套,因此直接批判过我。但是他又跑到人民大学去要求“处理”我,结果学术之争就变质了。在出版《风痕》时,编辑删去了他的名字。
至于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不是我能回答的。

退休后的潘绥铭
学人:在当下的环境中,“上岸”、按部就班、步步跟上的人生轨迹几乎成了唯一“正确”的选择。反观您那一代人,即使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似乎也很少会有这样的焦虑。对此,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潘绥铭:哈,这个问题超出我研究的性社会学的范围啦。
仅仅从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有什么样的焦虑,而在于如果走其他的路,风险究竟有多大?1981年我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结婚生女,分配到两室一厅的住房,月工资也足够用(那时没什么额外消费),整个一个小康生活。但是我仍然可以确信,即使走上学术之路,也一定会步步高。现在,历史会给你这样的保票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1980年代我们那一代刚刚从文革走出来,无论走哪条路,都吃得苦中苦,也没什么可损失的。现在的一代年轻人,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极盛期,不仅可能具有娇贵化的倾向,也更加输不起,这就加剧了焦虑。
学人:在我们上一个访谈发出后,许多读者都把访谈最后您那句“无话可说”看作一个点睛之笔。短短四个字,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无奈,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洒脱,对于这些解读,您是否愿意做一些回应?
潘绥铭:横看成岭侧成峰。
*学人Scholar志愿者李梅对访谈也有贡献。

专访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我已完全彻底退出学术,开始全新的生活
原标题:《专访潘绥铭:因为是我,所以才构建出如此这般的性社会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