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

下文为《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冯亚琳著。摘自《文化研究(第50辑/2022年·秋)》,陶东风为执行主编,周宪为主编,胡疆锋、周计武为副主编。
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
文 | 冯亚琳
记忆不能没有媒介。后者既是前者的载体,又是其实现的通道。正像阿斯曼夫妇所言,“人们与世界所能够了解、思想和言说的一切,只能依靠交流这一知识的媒介得以了解、思想和言说”。不仅如此,媒介还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会点,比如原本仅对个体有意义的书信或日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进入集体记忆的维度。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阿斯特莉特·埃尔称记忆研究史也是媒介研究史。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聚焦文学与记忆之间的交互关系,出于论证的原因,首先讨论记忆媒介的种类及其记忆功能,然后转向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特征与优势。
一 记忆媒介
记忆媒介有各种形式,阿莱达·阿斯曼曾在她的论述中,提到“文字”“图像”“身体”“场地”四种形式。事实上,记忆媒介的范围还可以扩展和细化,如具体到仪式、建筑物、纪念碑与纪念地、博物馆、档案馆、图像、收音机、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鉴于文学与文字的密切关系,我们权且在下文中先将讨论的重点置于“文字”及其相关概念“文本”之上,同时拓展到其他媒介形式,如“图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记忆的媒介,“文字”与“图像”一直处于竞争之中。
回到埃尔“记忆研究史也是媒介研究史”的断言,可以说,这一观点首先适用于文字。从发展的角度,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字史总结为四个阶段:“象形文字”(Bilderschrift)、“字母/拼音文字”(Alphabetschrift)、“印迹的类比文字”(Analogschrift der Spur)、“数字文字”(Digitalschrift)。她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文字发展史,以抽象化程度的提高为特征。如果说字母相对于象形文字已经抽象化,那么作为同是一种“编码”的电脑时代的数字文字更加抽象化。其特点在于,在对自身进行极端减缩之后,对图像、声音、语言和文字等不同的媒介进行编码,从而将其一网打尽,融入自身。

学者阿斯曼夫妇(左:阿莱达·阿斯曼,右:扬·阿斯曼)
就记忆与文字的关系而言,后者的媒介性首先不是体现在其对记忆的支撑作用上,而是体现在它可以是永恒的保障上。这一设想显然与肉体—精神的二分有关。因为肉体会随着人的死亡而腐烂,精神则可在文字中找到其流传百世、永久性的家园。应当说,这种对文字的崇拜最初建立在对图像的不信任之上,因为与文字的永恒性不同,图像、塑像和建筑物等“不能够有效保护它们的表征之物不受时间的侵蚀;‘时间的风暴’会席卷它们,使之变为风化的废墟”。如此,物质化的图像和建筑物与肉体的命运相同,它们会有朝一日在时间的摧残下消失殆尽,而文字的能指有可能在另外任何一个时间重新复活。扬·阿斯曼用“分散延伸情景”(zerdehnte Situation)这一概念解释文字更新记忆的功能,在历时的维度上将其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记忆在互动中代代相传奠定了基础。这一核心观点也体现在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定义中,他认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文化记忆的这一总括性定义将社会学的记忆与生物学的遗传彻底区别开来。如果说后者的“知识是本能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记忆是储存在基因之上的”,那么前者的记忆则是一种不断进行的对知识的建构。
不断对知识进行建构的基础是文本。扬·阿斯曼将“文本”(Text)定义为建立在“回忆、流传和再接受”基础之上的语言表达。他认为,形成文本的关键在于“使(语言)成型”。扬·阿斯曼借鉴语言学家康拉德·埃里希(Konrad Ehrlich)的概念,将文本定义为“再接受信息”。之所以是“再接受”,是因为文本所传达的信息虽然依然存在,但直接对话场景中说者与听者的共存早已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的接受不外乎对元场景的重构活动。于是,“在说者和听者共同存在的一个直接场景的位置上,出现了‘分散延伸情景’(zerdehnte Situation)。这个‘分散延伸情景’可以在两个到无穷尽的虚拟场景中得以展演,其界限仅仅通过文本的存在和流传的过程得以确定”。扬·阿斯曼所谓的“分散延伸情景”,借助交往媒介理论或许更好理解。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典型的交往模式:交往的主体是说者/作者[即信号的发出者(Sender)]和听者/读者[即信号的接收者(Empfänger)],媒介是交往的渠道(Kanal);交往的过程则是编码(Kodierung)和解码(Dekodierung)的过程。如此理解下的“分散延伸”应当是交往在时空上的移位。在这一维度上,扬·阿斯曼的文字几乎就是文本的同义词。但事实上,相对于文字,文本概念对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建构更重要,其含义也更为广泛。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带来的文本概念的扩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扬·阿斯曼的关注点其实并非文本形式,而是文本的记忆功能,即文本的“存储与流传行为”以及它是否具备“特殊的规范性和业已形成的约束性”。正是基于这一特性,文本形式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它也可能是口头的或图像的。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观察到某种对文字作为记忆媒介的破界,那么这一破界早在18世纪就已有雏形。那时人们甚至认为,“文字脱离了精神,作为一种陌生的东西出现在后者的面前”,它不仅不能给“充满活力的感受和精神的能量”提供保障,还成了后者的禁锢与枷锁,对其造成威胁。遗忘和损失的经验促使人们寻找新的通向过往的桥梁,这一次,人们找到的是“印迹”(Spuren):“印迹开启了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文本的通往过去的通道,因为它将一种过往的文化的非语言表达——废墟和遗迹、断片和碎片,也包括口头传统的残留物,都吸纳了进来。”阿莱达·阿斯曼指出,文字和印迹常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但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因为如果说可以将文字定义为“以视觉符号显现的对语言的编码”,“印迹”却不能,因为它不是“代表性符号”,而是要传达“一种印迹和印象的直接性”。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随着“印迹”概念的引入,“各种不同的‘写入’(Einschreibung)超越文本,扩展到照相图片和(其他)由主体对客体的力量作用。这一步,即由文本到作为过去能指的印迹和遗迹,相当于由作为意图语言符号的文字到作为物质刻铸(Einprägung)的一步,这种刻铸虽然并不是事先有意为之的符号,却在之后被读作符号”。
埃尔同样强调媒介对于“真实”(Wirklichkeit)的构建力。她的出发点是德国媒介学家苏比勒·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的研究成果,后者认为“媒介不是简单地传达消息,而是生发出一种影响我们思维、感知、回忆和交往的方式”。鉴于电脑、因特网等新媒介的迅猛发展,埃尔建议在“印迹”概念之上再加上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的“器具”(Apparat)概念,以凸显记忆媒介的双重性,即媒介不仅是“记忆符号中性的载体或者保存内容。在媒介支撑的回忆和阐释行为中,同样有记忆媒介的‘印迹’”。也就是说,媒介在记忆的同时,也被记忆着。与此同时,“记忆媒介如纪念碑、书籍、绘画和因特网”——这些被统称为“器具”——远远超出“存储”个体记忆的功能,而是在此过程中将个体记忆延伸到集体记忆,从而促使记忆共同体的形成:媒介“根据其特殊的记忆媒介功能,生产集体记忆世界,没有这样的媒介,记忆共同体不可能认识这一世界”。
根据这一理解,媒介在记忆行为中不再仅仅是处于第二位的载体,而是能对记忆行为甚至记忆内容的选择产生影响的前提。媒介与集体记忆的这种密切关系,被埃尔描述为“媒介为记忆文化提供可能并产生记忆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文化学框架下对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以何种理论为出发点,人类几千年来的媒介发展史——从口头文化到文字文化,从文字的使用到印刷术的产生,再到电脑时代——证明,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记忆文化的转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如果说印刷术大大促进了书本文化的发展,从而将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存储记忆”的容量扩大到几近无限,那么19世纪初期欧洲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则是书本文化日益机构化的表现。反过来讲,没有处于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对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追求,没有其“参与文化记忆”的要求和需求,这些机构的蓬勃发展同样难以想象。到了20世纪末乃至今日,电脑和因特网的普及,同样不仅对记忆的方式,而且对记忆的内容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记忆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不能忘记的是媒介的“社会体系维度”,也就是作为生产和使用媒介的主体的人,因为“记忆媒介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也积极从事建构工作”,而他们的参与总是在“特殊的文化与历史语境中”进行。

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重新回到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有关个体记忆是在集体框架下进行的观点,来观察记忆的媒介显现,就会发现记忆的媒介框架也是记忆的社会框架的一部分,因为正像埃尔所说的,“个体通过媒介找到的,不仅有通往具有群体特征的知识如数据和事实的通道,还有通向社会思维和经验潮流的通道”。无须赘言,这一过程不是死板的,而是动态的,是充满矛盾和变数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步论述“文学作为记忆媒介”时涉及。
埃尔在关于媒介作为记忆媒介的编码的机构化和功能化的讨论中,提出记忆文化语境中媒介的三个功能:存储、循环和调用。
所谓“存储功能”,指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内容进行储备,让其随时听候调配。这是集体记忆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在阿斯曼夫妇的理论构架中,完成这一功能的是前文涉及的“文本”。虽然扬·阿斯曼的“分散延伸情景说”在理论上为文本的不断重构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埃尔看来,存储媒介必定会受到时间维度的左右,一旦文字系统不再能够被解读,纪念碑的象征意义不再能够得到阐释,集体记忆的编码就会遭遇衰落的危险,成为“僵死的物质”。
所谓“循环功能”,指媒介不仅给超越时间的文化交往提供可能性,也使所谓穿越空间的交往得以实现。而循环媒介的任务就在于,当“面对面”的交际在一个大的记忆群体中不再可能时,让交际通过另外的形式得以实现。埃尔指出,承担这一功能的,“近代早期是书籍印刷,在18世纪、19世纪是杂志,全球化时代则是电视与因特网”。埃尔强调,“循环媒介是大众媒介”。
埃尔所说的记忆媒介的第三个功能是“调用”。她认为,随着形式的变化,媒介所具有的记忆功能亦发生变化。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说的各种“纪念场”那里,媒介的功能主要是“为记忆群体提供与特定的过去建立关系的联想”。埃尔认为,对于某个记忆群体来说,“调用”功能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它“既没有一个发送者(Sender),也没有语义上的编码”,“在记忆文化的语境之外无法实现”,因此对记忆群体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
二 文学作为记忆媒介
作为文本的文学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字流传形式,其文化记忆媒介的功能不仅已经在研究者那里达成共识,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一批英美文学学者的研究,其中首要的是埃尔的《记忆小说:一战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和德国记忆文化的媒介》、埃尔和古姆尼希以及纽宁合作的《文学,回忆,同一性:理论构建与个案分析》以及前文中已反复提到的阿莱达·阿斯曼在她的《回忆空间》中对文学现象的讨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学不仅是文化记忆的媒介,还是文化记忆的对象。前者指文学作品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对记忆的演示,后者则指涉文学的记忆。本研究用文学的记忆(Gedächtnis der Literatur)来指称后者,而用文学的回忆或文学中的回忆(die literarische Erinnerung)来讨论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问题。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在文学研究中,它们所构成的聚焦点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不排除交叉):“文学的记忆”涉及对文本样式、主题和文学经典的研究,也就是说涉及文学学作为学科积淀下来的知识的记忆,而“文学的回忆”关注在虚构的基础上,文学是怎样展演文化记忆的。本研究讨论的是后者,也就是文学中的回忆。
这一命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回忆本身与文学之间存在密切的交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密集性(Verdichtung)、叙述性(Narration)和体裁模式(Gattungsmuster)。
所谓“密集性”,是指复杂的过往事件往往附着在一些特定的概念、人物、图像甚至比喻上。无论是哈布瓦赫、诺拉,还是扬·阿斯曼,显然均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分别用“记忆图像”“记忆场”“记忆形象”来指称这一现象。而“密集性”恰恰也是文学的核心标志之一。因为文学原本就是“符号化”中意义“在最小空间内”的聚集,这一聚集过程不仅涉及隐喻、借喻等修辞手法,还有包括人名、地名、主题等在内的各种与神话、圣经或其他经典文本的互文指涉。
文学与回忆的第二个交会点,是它们所共有的叙述性。如果说“集体记忆世界是一个叙述的世界”,那是因为回忆具有被叙述的特性。甚或可以说,回忆的基本结构就是叙述。历史事件或过往的体验只有在被纳入叙述结构之后,方能获得意义。恰恰在这一点上,回忆与文学具有很大的同构性。按照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文学文本具有选择和组合、塑造叙述对象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这一区分对于“记忆实践”亦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体层面,记忆都只能容纳一定的内容。所以,首先要从“印象、数据和事实”中选择要回忆的内容,然后将这些内容加以整理和归类,使之成为有关联的整体。
“体裁模式”之所以也构成回忆与文学的交会,首先是因为个体在接受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文学体裁的通识知识本身就属于文化记忆的内容。诸如“成长与发展小说、冒险小说、灵魂日记、朝圣之旅等体裁包含的发展模式”,往往会被“个体用来解释自己的生活道路”。其次,文学体裁本身就是记忆文化语境的产物。在德国,可以说,假如没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市民阶层的觉醒,就不会有修养小说的诞生与发展。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对创伤回忆的需求,成就了短小说(Kurzgeschichte)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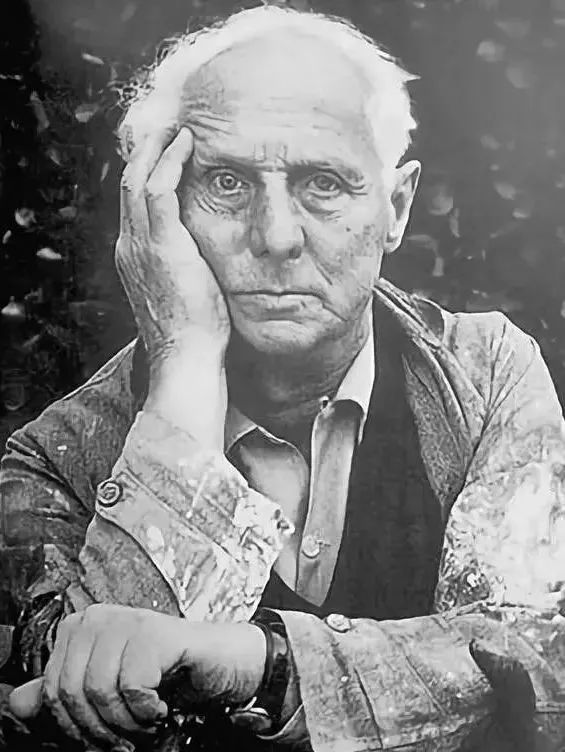
学者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埃尔引用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观点,认为“文学是记忆文化的一种独立的象征形式”。这一论断之所以在现今被普遍接受,应当归功于阿莱达·阿斯曼对“文化文本”和埃尔对“集体文本”的论证。如果说阿莱达·阿斯曼的贡献主要在于把文学文本也纳入文化记忆考察的范畴,从而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那么埃尔的“集体文本”则突破了“文化文本”的存储功能,从而凸显出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循环媒介”的功能。埃尔强调,诸如19世纪的历史小说[如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的《争夺罗马的一次战斗》(Ein kampf um Rom)和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祖先》(Die Ahnen)等],20世纪的战争小说[如埃里希·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以及德语国家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如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蟹行》(Im Krebsgang)以及乌韦·提姆(Uwe Timm)的《以我的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等],所有这些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品在未来的时间里可能会被经典化,成为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文本”,也可能会被逐渐遗忘。应当说,这种或被经典化或被遗忘的过程,正是一个民族不断选择自身价值观的过程。在另外一个层面,作为集体记忆循环媒介的“集体文本”同样有一个接受框架。一部展演过往的文学作品,只有当它被阅读并被社会上多数人视为对过往的适当展现时,才能成为“集体文本”。它与“文化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不是文化记忆的核心对象,而仅仅是关于过往的不同阐释的媒介。正因为如此,文本本身有可能被逐渐遗忘,但它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会经过沉淀,进入民族的文化记忆。换句话说,“集体文本”是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播和循环媒介,它激发、陪伴并加强社会关于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的讨论和思考;半个世纪以来,德国舆论界关于文学作品所传达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激烈争论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文学与其他记忆媒介之间存在不可抹杀的区别,因此不能概而论之。用埃尔“集体文本”概念,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集体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在内,反过来说,文学文本只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文本。与其他记忆文本相比,文学文本在演示文化记忆方面,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lser)
虚构优势(fiktionale Privilegien):按照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lser)的观点,每一种虚构描写都建立在两种形式的“越界”上。即文学之外的现实因素在虚构媒介中被重复,在这一过程中,被重复的现实成为符号并获得意义;相反,幻想因素经过虚构媒介的描述得到一种形态,并以此获得它之前并不具备的某种确定性和现实性。也就是说,现实和幻想这两个文学之外的领域在虚构媒介中分别被“非现实化”(如前者),或者被“现实化”(如后者)。在虚构中,通过对现实的和幻想的东西的结合,文化感知方式得到重新建构。
跨话语性(Interdiskursivität):文学作品是一种“多声部媒介”。它能够展示不同的言语和话语方式,并能将其进行综合表达。作为一种跨话语形式,文学与其他专业学科话语(如历史学、神学和法学)相比,它更具有广泛的容纳性,它可以通过言说音乐、身体、仪式等不同的记忆媒介,将其他与记忆相关的媒介和形式纳入自己的体系。
多配价性(Polyvalenz)和反思性(Reflexion):文学作为回忆的媒介的多配价性和反思性,建立在上述两个特征的基础上。如果说选择性是记忆本身的最大特征之一,那么文学则因其虚构的特征更加强化了记忆的选择性,于是它可以言说历史语境中被主流文化记忆所忽略甚至排挤的因素,聚焦隐藏于过往中的矛盾和变数,把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交互关系放到同一个框架中去考察。文学允许多元意义的生成,它在描写过去的时候无须追求恢复事实,而是可以构建所谓的“另外一种真实”。基于与想象的特殊关系,文学可以发挥“叙述者”甚至“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功能,通过对不确定性叙述策略的运用,调动读者对历史和文化现象进行反思,从而对扎根于历史的深处、经过长期沉淀、已经相对固化的文化记忆不断地从个体的角度进行观照、反思和批判。
总而言之,媒介是记忆的载体,是其实现的通道,同时将自身作为印迹深深雕刻在后者身上。作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文学既是文化记忆的对象,又是文化记忆的媒介,两者之间存在多重交会。与其他文化文本相比,文学在展演文化记忆时,还具有其他记忆媒介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如虚构性、跨话语性、多配价和反思性。这些优势使它不仅能选择性地建构过往,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还能够表达希望,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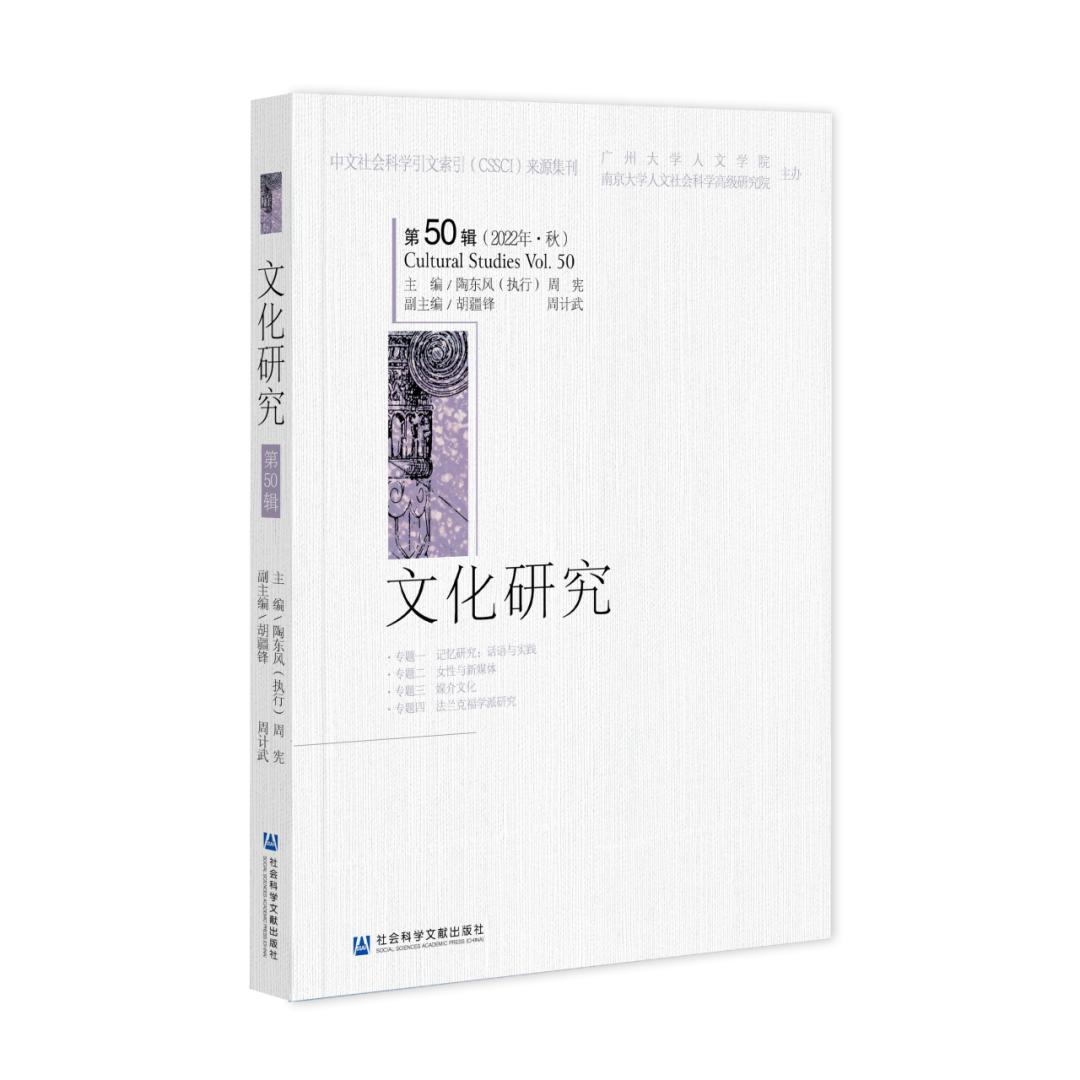
文化研究(第50辑/2022年·秋)
陶东风 执行主编
周宪 主编
胡疆锋 周计武 副主编
2023年7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1756-9
内容简介
本辑主要由四个专题组成。专题一“记忆研究:话语与实践”,四篇论文分别探讨了记忆与文学、哲学、数字技术、当代艺术的关系。专题二“女性与新媒体”,三篇论文都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呈现了新媒体中的女性议题,包括女性数字化健身、离异母亲的身份重构、“冠姓权”争论等。专题三“媒介文化”,三篇论文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洁运动在媒体上的反映,抗战时期国产电影在香港的传播,以及关于电影的器物批评的个案研究。专题四,三篇译文涉及本雅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在1968年西方思想场域中的位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题之外的论文《现代医疗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从周作人丧女说起》也非常精彩,该文以周作人丧女引发的医疗纠纷为起点,揭示了启蒙者与大众在现代医病关系中的态度差异,以及国人的医疗境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资料扎实,启人深思。
书籍目录
专题一 记忆研究:话语与实践
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 冯亚琳
连接转向之后怎样?——数字记忆的嵌入、汇流与激荡 李红涛
当代艺术中的“记忆的政治” 夏开丰
胡塞尔记忆哲学及其影响的衰减 杨庆峰
专题二 女性与新媒体
数字化健身中的女性身体与文化协商:以Keep女性用户的经验为例 周舒燕 葛诗凡
“离异母亲”新媒体短视频中的身份重构与女性社群重建 张颖 娄雪晶
“我的孩子,你的姓氏”:基于豆瓣“冠姓权”讨论的话语分析 郭燕平 蔡若彤
专题三 媒介文化
垃圾清洁与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代媒介文本中的上海垃圾治理叙事 兰凯伦
抗战时期内地电影在香港的传播及影响——以港版《申报》为中心 王保平 陈雨人
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中的“三轮车”——兼谈电影的器物批评 郎静
专题四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本雅明·学习·中国
——朝向一种普遍的“万物一元论” 彼得·芬沃思 著 李莎 译
经由相似之道:论本雅明对辩证法的道家式复兴 郑慈恩 著 高竞闻 杨雯 编译
扩展场域内的1968年:法兰克福学派与崎岖的历史进程 马丁·杰伊 著 周梦泉 译
其他论文
现代医疗境遇中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从周作人丧女说起 邓小燕
《文化研究》稿约
原标题:《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