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涿州急与困:三位记者的洪水报道手记
原创 深度营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
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
今年8月初,京津冀暴雨,水淹了半座河北小城。
2021年,深度训练营曾推出“记者在汛区”系列,对话了多位参与河南暴雨报道的记者。时隔两年,我们向参与涿州洪灾报道的记者们发出邀请,希望掌握更多灾难报道的操作方式,也希望得到一些非常规的启发。
我们对话了线上完成报道的文字记者傅一波、两度前往涿州的视频记者郑海鹏、《南风窗》记者何国胜,和他们一起复盘作品诞生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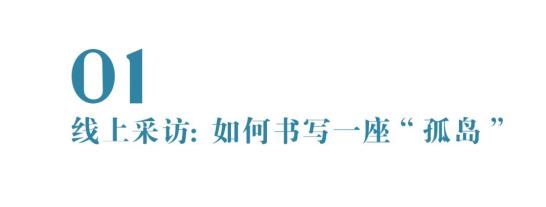
一场暴雨,把一个平凡的小区推到关注焦点。“水尚仁佳”因地库塌陷,占据微博实时热搜,成为涿州最牵动人心的小区。
人们关心“水尚仁佳”,不仅因为被困其中的家庭,还因联想到同处城市生活的自己:住进高楼里,习惯了现代化生活的人们,该怎么应对灾害?
记者傅一波也因热搜关注到“水尚仁佳”,在他的报道中,城市的灾情有其特殊性:高楼为低层住户提供了退路,但居民的高密度也让一栋楼的救援任务更加艰巨。
傅一波的目标是找到这栋楼里的人,在手机电量、受困者的身心状态、新闻的时效性等多重考验之下,他穿透空间,详尽地了解这栋楼里发生的事情。发稿前三小时,他终于再次拨通一位采访对象的电话,并将文章的摘要改成了一行小字:“全部获救!”
傅一波放弃了宏观层面的解释性内容,聚焦一座“孤岛”被拯救的故事,在一众长稿中,就像一个自带放大镜的视点。和人的遭遇同时被放大的,还有生存智慧、善意与来自记者本人的关怀。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与傅一波的对话:
深度训练营:你是怎么找采访对象的?
傅一波: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微博上的互助文档。我一共找到了17个人的联系方式,有一个是微博私信的,一个是其他的媒体老师给到我的,另外的15个全是通过互助文档。最后实际打通电话的不到一半,因为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水,没有电,能打通已经很不容易,有些人打通之后,聊了一句两句就挂了,聊得最久的大概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试着打过去,就再也没有接通过了。
在这个事件中,有些采访其实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提前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
深度训练营:你在打电话之前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傅一波:首先,我会确定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就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时间地点人物,然后问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最后来确定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身边环境如何,其实有很多个点,缺水怎么办?缺电怎么办?缺吃的怎么办?三号楼那一栋的一楼和二楼被淹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去了哪?
甚至他们有提到救援队路过,那为什么救援队没有办法救这个小区,他们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些对我来说是关注的重点。由于时间紧,我没有办法耽误太多时间聊更多细节。这篇稿子整体操作的时间也很短,从头到尾只有一天半。
甚至在七点刊发前,我都一直不停地打这些电话,因为定稿的结尾是人还没有救出来。我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打,一直打不通,直到四点多的时候才打通一位三号楼的居民,他告诉我,在发稿的那天早上的八点钟,小区开始得到救援,所以人都已经救出来了,我重新调整了结尾。
深度训练营:对于被困的居民来说,手机是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方式,但是断水断电的情况下,接受你的采访会消耗电量,他们接受媒体采访的动机是什么?
傅一波:在我打通电话的几个人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向我表达了他们缺水缺吃的,希望我通过有限的资源去帮助他们,去向救援队说明情况,这是肯定的。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帮助,大家都看到了公羊救援队动用了直升机救援,因为三号楼周边的塌陷,但是悬停的直升机一次只能坐七八个人,同时还需要动用极大的人力物力,它有航空管制,有报备,有油费,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们会特别慎重,也会优先救老弱病残、小孩,所以当时三号楼的居民也会有一些抱怨。
深度训练营:他们跟你反映后,媒体有介入其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吗?
傅一波:我会在群里面说情况。和公羊救援队聊的时候也会转达,并问他们未来几天的救援计划,我当然尽可能地把信息扩散出去,给到一些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人。
深度训练营:一般救援类的新闻都是写群像,这一篇的主要人物不算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安排?筛选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傅一波:这个小区有特殊性,就是被困的人比较集中,加上楼的塌陷。其实没有去特别设计,反而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人物)没有那么多可供选择。标准可能是,这些人里面要有一两个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这几天的经历。
深度训练营:采访主要依靠采访对象的讲述。那怎么对其中的细节进行核实?
傅一波:一是通过其他媒体的报道,或者通过视频去看当地情况。二是在这样的稿子里面,需要第三方的印证,比如A说了一个点,就要看B怎么说,身边是不是可能有C,来保证A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这篇稿子只有一个采访对象,那就不能这么做,因为会有很多主观的东西,产生各种问题。
深度训练营:稿件中被困的细节很充分,有什么采访技巧可以分享吗?
傅一波:其实就是要不断地去push追问这些细节,比如说采访对象告诉我,第一天晚上和弟弟睡在二楼,那我就会问:你几点钟醒来,看到了什么,水大概到什么位置?按照常理,夏天都很热,他们如果困在里面,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脱衣服,会赤膊吗?坐在哪里,怎么消耗时间?这些都会是场景的一部分。
有一个细节是,当时所有的媒体报道都集中在弄清楚地库塌陷时间点,包括塌陷的声音,在问到的所有人里面,都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时间,早中晚都有人说。我就很好奇。
直到有一个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命都难保,谁会管这是什么时间,谁会去注意那个声音?塌陷时,我推测会有挺大的声音,但是雨也很大,他们的体感全部在保命上。
深度训练营:稿件中体现了被困人员的生存智慧,比如说用电瓶车的电池给手机充电、用打火机点燃棉花来泡面,这样非常小的细节,你是怎么注意到的,又是怎么去引导提问的?
傅一波:我会顺着衣食住行提问,吃怎么办?采访对象说吃泡面。那我又问泡面是煮的吗,你们怎么生火?他就说是用食用油浇在棉花上,用打火机点着,也说如果真不行了,他父母再嚼干泡面。
如果需要这些细节,就得不停地去追问“为什么”,带着好奇和困惑。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懂,我也不知道电瓶车的电瓶怎么去给手机供电,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方法。不过也要注意,在那样的环境下,追问可能会让他反感,对方一开始也会说一定要留着手机的电量,和外界保持联系。
深度训练营:整篇报道的文字处理得非常有现场感,有没有可借鉴的方法?
傅一波:我会比较在意去询问他周边的情况,这个度也要去把握下,太追求场景可能读起来会很像小说,但不能无中生有,我觉得周边场景的细节,可以比较清晰的还原出当下的状态。比如说成功生火之后,他们的表情是什么,或者看到那个抽水马桶溢出来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深度训练营:给被困居民打电话,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快速传达意图,说服对方接受采访?
傅一波:在灾难面前要去表露的,第一是关心和提供帮助——我知道你们被困的情况,我是来关心的,尽可能提供帮助。第二,在提供帮助的同时,我也需要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同时告知自己的记者身份。第三,我希望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群体,更多人关注能够得到救助的可能性会更大。
深度训练营:怎么和采访对象保持联系,跟进最新的进展?
傅一波:我会在采访最后提一下“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开头说太多是会耽误时间的,让对方进入状况慢,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去聊这些开场白、铺垫。我就很直接地告诉对方:我来提供帮助、我是记者、我会把你的情况扩散,然后直接进入主题,甚至有时表明身份之后边聊边问。
深度训练营:有些采访对象手机电量不足,这时候就直接放弃这个采访对象吗?
傅一波:不会,尽可能地问一些情况,能聊一会儿就聊一会儿。但前提是对方已经告诉我,“手机只有10%电量了”,我确认他自己也有分寸的。
深度训练营:稿件中的时间点比较清晰,采访对象对于时间的记忆力有这么敏感吗?你怎么样去推动他们还原具体的时间点?
傅一波:其实有一两个人被我问得有一些烦,我会不停问,因为我需要确认这个时间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这件事究竟在什么时间点发生。
深度训练营:被困的两天时间里,他们的灾情可能会发生变化,媒体关注的点也可能会变化,你在做报道的同时如何关注灾情走向,不失去对灾情最基本的判断和跟进,同时又保证自己专注在报道当中?
傅一波:我一定会非常紧密地跟进,搜集当地的情况,包括小区的情况,甚至于我每一个采访对象的情况。我隔两个小时就会给他们发一条信息,问现在的进度。在我写得差不多的时候,也会赶紧问一下有什么进展,他们有没有得到救援,或者通过一些救援群去看实际情况。

八月初的涿州暴雨,前凤凰网视频制片人郑海鹏带着相机去了两次现场,带回两条长视频和一只小白猫。
他的行动大都被记录现场的目标牵引,订票出发时没顾得上额外做准备。在水里前进时,潜意识里提醒自己摔倒后先保护相机。“这里每时每刻发生的都是新闻,我只要记录下来就好了。”
抓紧拍摄,抓紧剪辑发布,《涿州救援8小时》和《泡在洪水里的图书老板》,两个超过十分钟的长视频均获得不错反响,他说自己喜欢跑现场,喜欢做原创,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给主人公带来一些实质的改变。
现场拍摄充满未知,郑海鹏坦言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他向我们回顾了在涿州的行程和拍摄,以及对视频新闻的感悟。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郑海鹏的对话:
深度训练营:你是怎么去涿州的?
郑海鹏:我是8月2号坐高铁到的,因为我两年前去过720河南水灾的现场,也是坐高铁。一般发生灾情之后,高速可能会因为不可抗力中断或者封闭,铁路干线作为主要的交通大动脉,临时中断的几率比较小,我看到北京到涿州高铁只要20分钟,但票也不好买,候补了好几列才抢到。
只要到了涿州,再去现场,想办法打车或者是找私家车这都可以。有其他记者去涿州,他们开车或是租车,往往会堵在高速上,又下不了高速,高速口可能临时封闭,需要多次绕路才能到达更接近现场。面对这种情况,我的经验是高铁比较稳妥,没有高铁再想其他办法。
深度训练营:你大概待了几天?
郑海鹏:我待的时间比较短,两个视频分两次去的。
8月2号下午我去了涿州107国道附近的一个村子,当时水很深,我进不了现场。这里相当于一个集合地,各种救援队都在,我遇见了上海蓝天救援队的人,是我之前的采访对象,他人很好,有自己的私人救护车,从上海开车过来,就想去救人,之前郑州大水他也去过。
当时的郑州很多人需要救护车,结果这次到了现场发现,涿州并没有像郑州那样短时间接近瘫痪,它的医疗系统正常运行。救护车的用处并没有特别大。
进入灾区现场,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比如找当地人带你进入新闻现场。有时候,核心现场因为安全问题,会设立几道封锁线。救护车属于特殊车辆,它可以畅通无阻,到达涿州后,救护车司机载我顺利跨过封锁线,到达核心现场。在涿州107国道附近,我看到很多救援队接力,把村民挨个救出来,拍了很多素材。当时我的任务是找到可以报道的新闻故事,因为不管是文字特稿还是深度点的新闻视频,做群像可能并不讨巧。
深度训练营:还有一个主角。
郑海鹏:对,一个核心的新闻当事人,或者说是故事主人公。在现场,我不能一直围观,我得跟人搭上话,并且近距离拍摄。那时候,我很想让救援队带我进现场,救援队的集合地水深有半米多,到膝盖,再往里面去,水就特别深了。
每一次出差我焦虑的是,到了现场要突破,找人,初到现场往往并不如意,压力很大。但是我也很享受那种重压下,慢慢释放,突然柳暗花明的感觉。
由于水深,光凭我自己进不去,听当地人介绍,救援队集合地距离里面的村子还有两三公里,我开始和各路救援队搭话。现场很多橡皮艇只能容纳6个人,后来我发现河南永城水上救援队有一条船能容纳20人,是一条十多米的不锈钢船,当时我第一感觉:不差我一个座位吧?有希望能搭船。
因为船只特殊,我主动上去搭话,永城救援队队员的态度很好,果断答应我跟拍的请求。由于拒马河泛滥,之前从涿州市区到达百尺竿镇仅有十多公里,但是我们不得不绕路70公里,当天晚上从涿州到达房山修整,第二天早上6点到达百尺杆镇救援。

涿州水灾现场 图片来源:郑海鹏
深度训练营:你在现场是全程举着相机的吗?
郑海鹏:全程举着相机。但是会有阻力,比如身穿制服的人看到我泡在水里一直拍摄,会让我走开,并质疑我的身份。
当时人太多了,比较混乱,身穿制服的人顶多说一两句,我一般不会和当地人起正面冲突,要讲究迂回策略。他让我走,我就短暂离开现场,一会儿又迂回过去。
我到达的2号下午,拍摄的素材都很好。印象特深刻的是,老人和大概2岁多的小孩坐在船上,被转移出来。小孩的妈妈站在岸边一直踮着脚,向积水深处张望,当看自己的孩子被护在橡皮艇中央,年轻妈妈顿时跳入水中,含着泪去抱自己的孩子。
深度训练营:天黑了,当天救援就结束了?
郑海鹏:对,天黑了,救援队就不会再涉水冒险进村了。当然,村子里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撤离的村民。到了晚上,永城救援队接到新的任务——前往附近的百尺竿镇进行第二天的救援,我们绕行70公里,在房山修整。
8月3号早晨,雾气笼罩百尺竿镇,有几位村民涉水走到高处,告诉我们之前的水位有三米甚至四米,后来我们涉水往村里走,积水和淤泥都特别深,可以淹没整个小腿。
深度训练营:第二天的拍摄过程是怎样的?
郑海鹏:我在现场背着一台小型定焦相机,还拿着一台DV,当然是设法保住自费购买的设备。水位到达一定深度,就可以行船。如果在水位浅的地方,永城救援队就要艰难的推着船在淤泥中挣扎。我则跟着救援队,一路拍摄,行进速度很慢。
这是我第一次涉水拍摄,我并没经验。在淤泥中行走,我不得不脱掉附着淤泥的鞋子,直接穿着袜子走在淤泥中。现在那鞋还在我家阳台,已经坏掉不能穿了,我觉得当时那双鞋大概有10多斤,特别重,全是淤泥。在水中,我把鞋子脱掉之后直接绑在书包的背带上,行进速度加快了不少。事后我和朋友聊,他们发问:你不怕脚下有玻璃或者尖锐的异物吗?我没有假设过,现场也不允许想很多。走了大概四五百米,水流开始变快,淤泥慢慢就少了,我们到达水深大概没过腰的地方,于是开始正常行船。
最终救援队到达百尺竿镇的大住驾村开始救援和转移受灾群众,我开始正常拍摄。
深度训练营:你在现场会和救援队一起救援吗?
郑海鹏:不会,因为我在现场一直拿相机,我的任务是跟拍整个救援过程。
有人看了视频,可能说这是摆拍,或者有过设计过的细节,其实这种突发现场对于我来说,拍摄比较简单,我只要到了现场,这里每时每刻发生的都是新闻,不需要刻意营造。只要拿相机拍下来,这就是很核心的场面,后期剪辑是很简单的。
深度训练营:一整天都在拍摄的情况下,如何对大量素材进行取舍?
郑海鹏:首先是我8月2号在107国道附近拍的救援画面,包括刚才说的年轻妈妈含泪接过小孩的视频,最后这些素材我都舍掉了,当时是很不舍得。如果按照我的剪辑初衷,估计能剪出25分钟左右的视频,涵盖的信息、细节以及故事性都会好些。但是往往这样的视频,对很多受众来说,觉得太长或者节奏慢,观看的延续性会降低。所以我还是删减了很多比较好的视频素材,来保持视频故事性和整体的节奏。
深度训练营:在现场有点碰运气?
郑海鹏:跑过的现场多了,越来越发现在突发现场可能真的需要运气,救援队本来是要去一个关注度还比较大的葱园村,很多人被安置在一个十几层的楼房里,在楼道中扒着栏杆等待救援,整个视觉感相当震撼。最终由于大住驾村也需要及时的救援,我们就过去了,于是拍到了视频中的很多细节。
深度训练营:在行进的时候你停下来拍摄,前面的救援队会停下来等吗?
郑海鹏:这就是一个痛点,他们基本不会的,如果停下来等我,我就更有负罪感了。当时我们最远距离有100米了,我就很着急,但是在淤泥里实在走不动,我不能走得特别快。我手里要拿着一个很大的DV,脖子里背着一个小的相机,在拍视频的同时,有一些瞬间,我会拍完视频后,再拍摄照片。
我从事视觉报道,是因为我喜欢拍照片,但是摄影记者的职位基本绝迹江湖,越来越少了,我就开始学习拍摄视频,毕竟说出去也是在深耕影像内容。
深度训练营:你是带自己的设备去的吗?
郑海鹏:机构有设备,但是便携性的相机是我自己的。因为考虑到现场,和受困的群众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所以我带了一台DV,DV能变焦,拍摄到更远的景象,同时用DV拍摄也更具现场感。在现场跑新闻,我从来不在乎设备有多先进,也不在乎很多人追求的画质和虚化,比如大光圈虚化,我不仅觉得油腻,甚至丧失了很多新闻细节。我拍的是新闻现场,哪怕用手机拍下来,最后剪出来现场的张力仍会很强,所以我不太追求视频画质有多好,虚化有多好,我的前提是单兵作战,力求真实,先拍下来。
当时我在淤泥里摔了一下,被旁边的小伙扶住没有完全倒下,我的相机和DV被溅上了很多淤泥,现在DV的缝隙里还是有好多泥,没有清理出来。扶着我的那个小伙是从村子里涉水出来的。他介绍说村里的水位到达他的脖子,只能露出一个头,让我进村子要格外注意安全。
深度训练营:“涿州救援八小时”的拍摄充满了未知,拍摄图书老板提前策划过吗?
郑海鹏:拍摄泡水图书老板是有计划的,而且操作时间更短。8月3号晚上我跟拍的救援队结束救援,返回涿州市区。
大住驾村救援过程拍摄完毕,如果视频想出圈,速度一定要快,所以8月3号我连夜返回,大概晚上11点到家休息,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开始剪辑成片,中午把初版剪出来送审,下午就发布了。拍摄剪辑和发布整个操作也就24小时,我是一个人完成的,上传、运营也是自己做。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会副业不同的栏目,承担2-3人的工作量。
当时我发现,各个媒体一窝蜂的都在关注中图网,好像也不太需要我去关注,我决定关注其他书库老板。那时候没有关于图书书商的深度影像报道,他们的损失巨大。
正好有朋友是图书行业的,帮我引荐了纸上声音书店的老板。
我算去得比较早的,那时候水刚刚退掉。去了后发现,如果再提早一天两天,水没退的时候视觉效果会更好。视频里他们显示出愤慨和无奈,一位书商说这都是知识,这种话很触动人心。她损失了将近1000万,处在很崩溃的境地,突然看到有媒体来关注她,她一直和我倾诉。


图书仓库受损严重 图片来源:郑海鹏
他们很愿意接受采访,我到了现场,很多书商不停的找我,问我能不能去他们的库房拍一下,他们觉得我的拍摄能帮助到他,或者是留个现场的备份,当时拍摄进展很顺利。
图书的视频我拍摄时间最短,大概是中午到的,拍到下午六点,中间只拍摄了3、4个小时,本来我预计要拍两天,起码一天多。结果拍了半天后感觉,其实内容的延展性也没那么强,只是在现场呈现他们的状态和困境。
主要原因是我在现场遇到了一只在洪水中幸存下来一只猫,大概1个多月大,我临时决定带它回家,这只猫目前在我家已经“作威作福”,很健康。
深度训练营:您是怎么遇到的这只猫?
郑海鹏:纸上声音书店老板的库房里有两只玄猫,我视频里有一只出镜了。当时洪水没有淹没到书架二层,两只猫在书架二层躲过一劫。
老板说图书库房很多人会养猫,养猫就意味着书库没有老鼠,他家那两只猫中,有一只在发洪水的时候肚子很大,要临产了。洪水退去,工作人员去仓库时发现母猫已经下崽儿,但是小猫去哪儿了,他们没有找到,以为被洪水冲走了。
在拍摄其他书库的途中,我听见一只小奶猫的叫声,叫得很惨,应该是很饿,我就在书库角落的淤泥周围找到了他,它全身是白色的,毛还比较干净。
当时书库位置洪水深达3米多,这只小猫是怎么求生的?它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大。纸上声音的员工给我找了一个箱子,投了很多狗粮,是的,书库仅找到了一些狗粮。它一边吃一边嗷嗷叫,一定是饿了很多天。喂了它之后,会觉得这只猫和我有缘分,想带回家,让它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当时拍摄的素材,我心里是没底的,但是见到这只猫,我只想连夜带回北京,安置这只涿州“难民”。
当天晚上,书店老板开着车就把我和猫载回北京。比较神奇的是这只猫吃百家饭长大,什么都爱吃,也不认生。它现在俨然成了我家的老大,十分亲人,十分淘气。
回家之后,它喜欢在成堆图书缝中穿梭,甚至睡在书上,有感这只猫可能从小在涿州书库中出生,长大,毕竟也是书香门第,于是果断赐名“Reading”。
我拍完涿州书库视频以后,过了一周,纸上声音书店老板给我发了张照片,他们在书堆深处,找到了洪水中出生又失踪的那一窝小猫,他特别开心,那些小猫眼睛还没睁开,在书堆中活了下来,生命有了延续。

书堆深处的小猫 图片来源:郑海鹏
深度训练营:有一些记者在拍视频的时候,会做视频大纲,你在拍摄的时候会提前做规划吗?
郑海鹏:我去现场拍,和去一个固定的场合不一样,新闻没有剧本,没有预设。
每次跑突发,基本上是到了现场再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未知是一种考验,在不确定因素的加持下,压力会很大。但是在靠自己上下求索,左右突破的过程中,慢慢释放压力的感觉也会让人愉悦,甚至说有种快感,以及后期作品发布后的成就感。
其实,要做大纲的可能就是比较静态的故事讲述,比如去采访一位案件的当事人,我会简单做一个提纲,主要是问题,同时提前想到一些传播点,大概假设了对方可能会怎么回答,但很少会这样。
这种突发现场,没有想要拍成什么样,或是怎样传播。我理解的是到了新闻现场,只要你拍到就赚到了,很多时候是拍不到理想的故事或者影像。
采访相当于有节奏的聊天,一切是自然发生的。可能某个问题我不问,对方就自己说了。比如涿州洪水现场,受灾群众坐在船上,我就问了昨天的水位到哪个位置?在那个大环境下,很多人是有倾诉欲和表达欲的,有人指着旁边的参照物,说昨天水位还三米深,我们这儿没有救援队……然后其他人就开始对话,聊天,很多要问的问题,就自然有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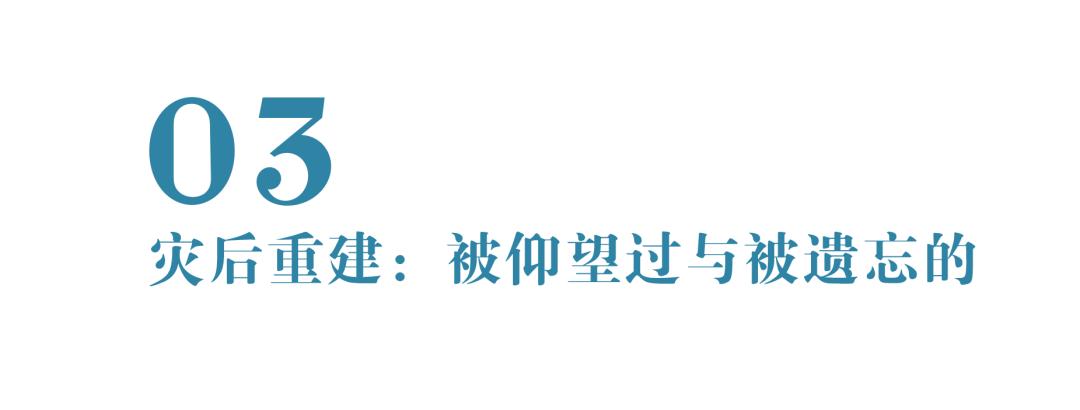
“热度过了,救援完成后,恰恰是老百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议程设置滑向下一个落点,涿州的曝光度越来越小。洪水退去,污垢、垃圾、臭味......灾害的背面才真正显现。
尚有四五米积水的地下车库、一户户空空荡荡的民居,超出身高的积水痕迹和玉米地里成片枯死的黄色。这些都是何国胜的所见。
白沟河和北拒马河是流经涿州的主要水系。来涿州前,何国胜计划以河流为坐标,去沿岸村庄看看。抵达现场后,除原计划外,他还遇到了旧衣商人、“甜蜜蜜蛋糕店”、无处倾诉的困境和亟待关注的眼泪。
“哭诉一番后,他们抹抹眼泪,再踩着厚厚的淤泥和蹚过一些未退的洪水,收拾已经“破烂”的家。”
各色的被水泡过的痕迹依旧清晰,话说完了,泪擦干了,于这些心碎的人而言,生活还要继续。
当涿州走出视野中心,记者持续跟进,记录了灾后重建的故事。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何国胜的对话:
深度训练营:我们看到你去了现场报道,当时距离灾难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考虑去涿州?
何国胜:我是8月11号从天津到了北京,然后再从北京赶到涿州。差不多12号(到达现场)开始采访。
当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考虑去东北,那时东北也正在经历(水灾),另外是考虑去涿州灾区。当时东北的情况不太明朗,我不知道那里具体什么情况,原本想找个救援队带我进去,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选择去涿州看一下。
那时候,虽然涿州的热度、关注度都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灾害很严重。我在微博上看到求助,说涞水县的一个村子里受灾严重,有十几人遇难,我就一直惦记着去村子里看看。后面发现有媒体已经过去了,发了很详细的报道,考虑到基本信息已经被报道出来,没必要做重复的报道,就选择去涿州看灾后情况。
深度训练营:在现场采访的过程中,如何和编辑进行有效沟通?
何国胜:第一次和编辑沟通是在去之前,和他确定了要去涿州。当时广东佛山菠萝救援队在那里排涝,我就跟着他们去看现场情况。跟了半天发现受灾情况严重,排涝需求很大。
当晚和编辑定了写作方向,打算从关注排涝问题、受灾情况两点来写。
等我碰到旧衣商人时,我又和编辑沟通了下,想着是要把旧衣商人单独写还是融进来。经过一番商量,觉得单独成篇体量撑不起来,完成度也没那么强,所以就把它纳到整个文章里。
总体来说,出差期间和编辑的交流分为三次,刚去现场观察完,沟通后面具体怎么做,有大概的方向。中途有新发现,会和他讲下,汇报进度。最后,采完了说下采访拿到什么信息,觉得采访的差不多了,就准备撤了。
深度训练营:你在涿州个人的交通、住宿如何安排?
何国胜:我从北京过去,本来想坐高铁,但是那两天的高铁票抢不到,很多人去涿州。然后我就看到北京到涿州的公交,在我到的前两天刚刚恢复了运营。我就去坐公交,到后发现也在大排长龙。我觉得等太久了,看到有黑车在拉人,就坐了黑车,花了50块钱到涿州。
到了涿州后条件稍好的酒店都住满了,我就在美团上选了个还可以的地方。
当时涿州不是所有的城区都淹了,它有一小片的区域是没有被淹的,那里已经恢复了供电,其他的大部分区域还没有。我去酒店住下来发现它整个环境都比较潮湿,还有酒店不供水,因为涿州的地表自来水厂都被洪水冲坏了。
当时涿州市启动了城区的自备井水,把井水抽上来给大家用。井水没有二次供水设备,没法抽到高层。我住的酒店除了一楼,其他都是没有水的。我用垃圾桶去一楼接水回来冲厕所。洗澡问题是在当地一个澡堂子解决的,澡堂子也是用井水。澡堂老板很有爱心,当时菠萝救援队在我去的时候已经待了快一周,他们没地方住,老板就让他们住在澡堂子里。澡堂旁边是个牙科医院,医院的人也腾出地方让他们住。
深度训练营:你的采访路线是怎么安排的?整体阅读下来,会感觉文章排布很有逻辑性和空间感。
何国胜:第一天是跟着救援队。他们给我介绍了情况,让我有了大概的感知。跟着救援队的时候,我在一个京津冀的救援群,看到了求助信息。对方说码头镇的某个村子是回迁房,积了很多水,排不掉要求助。救援队队长没有空,我就说去看下什么情况,再给他们回复,如果严重就派一个抽水小组过来抽。
第二天我是自己租了车去码头镇的北港村,这里也是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到了以后发现回迁房还没有建好,它只是一个工地,里面有积水。当时我就判断说这个地方目前还没人住,相比于那些有人住的小区和村子,这里反而不是特别紧急。
抽水设备资源要优先用于特别紧迫的地方,我就和那里的人说,目前没法立马排,要等那边资源稍微宽裕一点,以后再来排。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紧急,就开着车往外走,走在半路上看到一条街全是垃圾。稍微开一点窗户,臭味也很浓重,所以我就下车去看一下。
在街上转时,碰到了文章里写的甜蜜蜜蛋糕店的夫妻,北芦村育英街就在这里。
【尽管收拾了几天,店里还是很乱,难有下脚的地方。所有的东西横七竖八,包括平日里三四个人抬不动的大冰柜。高飞的妻子拿出洪水来前在店里拍的照片视频,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片脏乱的空间,曾是他们暖亮的“甜蜜蜜蛋糕店”。】
我和他们聊了一下大概的情况。聊完以后,中午了,我就回城区去吃饭。
回去路上我就看到马路边晒了很多的衣服,但当时没留意,就走了。
下午,我想要找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村子去看看。我觉得沿河岸的村庄受灾应该最严重,所以就选了小柳村。去找村子的路上,我又看到一个村口,从村口到里面延伸了有100多米全是垃圾,我就下车往里走。这是北辛庄户村,是我写到搞装修和做啤酒的人住的村子,进去以后碰到他们就采访,了解受灾情况。
【洪水一进来,啤酒倒的倒,破的破,库房里一股浓烈的酸啤酒味。张猛没算到底损伤了多少啤酒,被水泡过后,大部分不能再喝。一同被泡的,还有9辆车,7辆送货的,2辆汽车。】
采完后,我就去小柳村。当时没有信号,手机导航也不能用,看了个大概,我就上路。
没走多久,我就看到马路一边晒着很多衣服。我好奇就下车去靠近去看,拍了几张照片。准备走的时候,一辆轿车上来,问了下是这些衣服的主人。他们听到我是记者,就带我到他们的旧衣仓库去看,那里一片狼藉。随后,这位又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个旧衣商人,说他更严重。后来,我的微信被他们推给了码头村一位生意做得更大的、衣服种类更丰富的旧衣商人,我就去看了他的状况。我发现了旧衣商人后,他们像滚雪球一样给我推荐,就了解到了很多信息。
【各种式样、花色的衣服,占据了两个车道。李军说这些晒出来的衣服约有两吨,是洗洗以后还能勉强出售的,其他更多的在库房里被淤泥包裹,散发出腐烂的恶臭。】

占据车道的旧衣 图片来源:南风窗
看完旧衣仓库,天已经不早,我就抓紧往小柳村赶。公路一边被封了,只有一边能通行。走了一段,我发现一个受灾物资发放点,停了车下去看,才知道已经到了小柳村。接着我和领物资的村民聊了聊他们的受灾情况,接着又到村里看了几户人家。
晚上,救援队提供了新的信息,说他们第二天要去受灾严重的大柳村抽水,我说到时候我也去看看。第二天,我提前到,先在村里采访,受灾确实严重。在那里我碰到了搞建筑的工头,还有文章开头讲到的张土坡,他们家里都被洪水掏空了。
【几个卧室里的衣柜、衣柜里的衣服、床垫、床架全部泡水,都扔了。院子车棚里,一辆农忙时用来耕地的大拖拉机、一辆三轮电动车、两辆电单车,全裹着一层泥,等着报废。】
之后,在他们抽水的现场,我详细看了救援队具体排水的过程。
【可排涝并非易事。抽的是脏水,有些已经发臭,救援队员没有什么防护装备,直接进脏水去安水泵。抽到后面,水泵进水口被堵,队员们再下脏水里清理。】
整体来看,我计划要去看的,一个是码头镇北港村,一个是小柳村、大柳村,我就找沿河岸边比较严重的一些村子,这是我预想中的。另外,旧衣商人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过程中恰巧碰到,然后就聊到、采到,写出来。这可能就是去现场的一种魅力。没去之前可能会有疑惑,没联系采访对象,去了以后会不会采访不到位,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所以就不敢去,但其实好几次经历告诉我,去了现场肯定会有收获。只要你去了,就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像我碰到旧衣商人,完全在意料之外,碰到了,就把他们记录下来。
深度训练营:在文章的逻辑安排上,为什么考虑将排涝和受灾善后放在一起?
何国胜:排涝是很重要,我去了涿州后才知道。
对城市来说,很多小区和公司,包括涿州大批的产业园区,都有地下车库或地下室。洪水过后,地面上的水基本退掉,但地下室都被灌满了水。车库和地下室都很大,我去的有些地库深度有11米,里面都灌满了水。规模大些的小区都有两层地下车库,算下来水深也有四五米。积水量很大,这些水都要排掉。
而且城市大部分的电力设备和供电设备都在地下,不把水排掉、泥抽掉,整个小区的区域供电就没法恢复。供电,牵扯到居民生活,家里没水电,什么都没法进行。
排涝需求如此重要,但排涝的资源比较少,这也是我去了当地才发现的。
事实上,灾后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太关心了。热度过了以后,或者说生命救援完成后,大家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在这个灾区,它滑向别的地方,但这个时候恰恰是灾区老百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排水,如果靠自己排,要排十天半个月,因为积水量动不动就是上千、上万立方,甚至十几万立方,自己拿小泵(去抽不现实)。我们去的一个地方,他们用自己的小抽水泵抽了一天,水位才下降十公分,而现场积水有两米或四米深,按照这个速度抽太慢了,而且他们的抽水泵也无法连续工作。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救援队的大型抽水泵,一两天之内可以把水抽掉。
但是当地政府,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不会储备那么多排涝资源。我去了以后,菠萝救援队队长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除了一些老百姓求助,还有像城建局、城管局、应急管理局等当地政府部门都会打来说哪里需要排涝,可以去看一下。
单从这一个救援队的忙碌程度上来看,就能看出排涝的需求量有多大,但是政府又没有多少资源。所以,这里就产生了排涝需求旺盛和排涝资源不足的矛盾。如果排涝不解决,那灾后的重建和恢复就没法进行。文章里面谈到这部分就是和灾后的重建紧密联系在一起。
深度训练营:你在现场采访时,大家愿意接受采访吗?
何国胜:现场哪怕不是记者,随便一个人进去问,他们都很愿意讲,因为确实很惨。
像我去的还晚一点,带我的救援队刚开始去的时候,路上开着车,碰到几个人在门口铲泥,救援队队员就把头伸出窗外问一下受灾情况怎么样,对方会立马开始说情况很严重,眼泪也很快就出来了。在他们拍的视频里,我看到有些女性抱着救援队的女队员在那哭。那个时候他们是很有倾诉欲的,他们会配合采访,把自己的遭遇、现状、需要的帮助一股脑全都告诉你。比如我在村里采访拍照,路过一个人问这个人拿着照相机是干什么的,听说是记者,对方就说能不能到我家里看一下,我家里也特别严重。所以采访是很顺利的,大家都会告诉你具体的情况。
深度训练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是8月20号发布的,距离水灾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月,但是它还是出现了10万+的传播量级,你有预想过有这么好的传播效果吗?
何国胜:我是没有预期的。因为我们之前发的一篇相关的稿,比这篇早十天,发出来以后阅读量很低,只有3万多。当时他们还在想,我还要不要去。是就此回来,还是再花一周时间?还要租车要住宿花那么多钱再去做,还值不值得?最后觉得确实要去看一下,记录一下,就去了。
当时这篇稿子写完时,我对阅读量是没有信心的,它现在在公众号可能有差不多50万的传播量,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我觉得可能最多到四五万也就到头了。
因为看了前一篇的表现,感觉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关注量,大家已经不关心涿州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它刚发布时表现不是很好,是后面慢慢起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关注量?
第一是,关于反映灾后真实情况的内容比较少,这方面的信息是欠缺的。但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想看到灾后的真实情况。
第二是,稿子反映出来的情况超乎很多人的想法。可能人们觉得,虽然这里遭了水灾,但应该没有很严重。这稿子发出来以后,大家没想到水灾竟然这么严重,老百姓的生活面临如此大的困境。
它的传播是靠大家转载转出来的。我们看到后台从公众号里打开的数量不是特别大,比较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朋友圈的分享和看一看机制。
深度训练营:到达现场后,除了录音之外,一些无法被录音覆盖的信息如何保存?
何国胜:去每个地方我都会把定位搞清楚,发到手机上。这个地方是哪里。
一些视觉的东西,我会拍照片拍视频留下来,写的时候去回看一下当时是什么场景、什么空间。
去的时候编辑提了一嘴,这种灾害类事件,在视频和图片面前,语言是比较无力的。可能一张图、一个视频放出来,大家都一目了然,很清楚灾害到底有多严重,破坏力有多大,所以编辑交代多拍一点照片和视频。本来这种重大的突发性报道一般都会去两三个记者,是会配一个摄影记者的。这次因为它到灾后阶段,也没那么紧急,加上我最开始是去采访救援队的,所以就没有带摄影记者,就我自己去的。这里的文字、照片、视频的工作就都交给我一个人,稿子里的视频拍得就不是很专业,录音也没有拿专业设备,就是相机直接录的,效果没那么好。
原标题:《涿州急与困:三位记者的洪水报道手记|稿件复盘》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